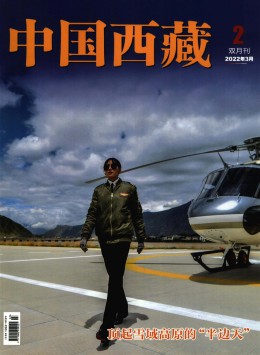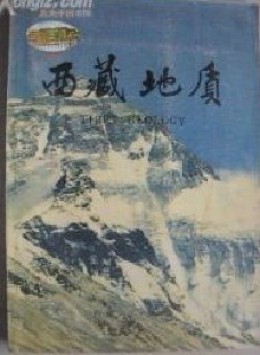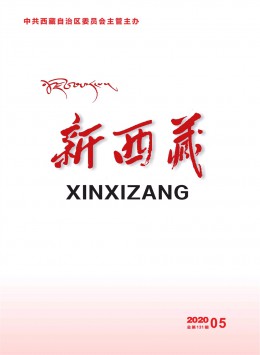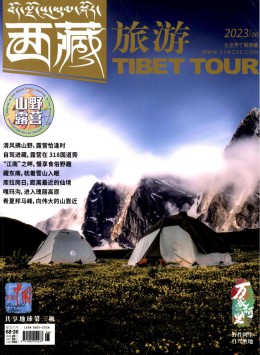西藏茶文化探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西藏茶文化探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西藏傳統社會長期實行政教合一的統治模式,政治與宗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東嘎•洛桑赤列(1981)認為,政治利益的角逐直接反映著宗教教派利益的沖突,宗教教派間的矛盾也體現著對政治領導權的爭奪。因此,研究茶在西藏治理中的功能,應該至少涉及宗教與政治的多個方面。實際上,茶在西藏治理中發揮的功能與其在西藏傳統生活世界中發揮的功能是緊密相關的,有研究者“通過‘茶’在藏族生活中的語言學地位證實茶在藏族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意義”[2]。因此,我們假設:在生活世界中實現的作為文化的社會凝聚功能成為茶在治理中功能發揮的基礎,也是重要體現,而社會治理中功能的發揮又成為其生活世界中的一種功能升華。二者相互關聯,不可分割。
宗教政治傳承中的茶
宗教政治的傳承有一個相互銜接的過程,這一過程會有多種因素介入,其中包含有茶的內容。最主要的是法主身邊的“司茶侍從”常常會被選入宗教政治系統核心集團之中。在帕竹噶舉的傳承中涉及了在法主身邊司茶的侍從。當時因帕竹一系在康、藏都有眾多僧眾,即使一些小事務,上師都需要親自處理,護持兩部法座。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帕竹的僧眾提議應有一人主持事務。后與法主請示,提議一位曾在法主身邊任司茶侍從的人擔任,法主同意,命此人擔任法座,即后來的京俄法主(京俄意為眼前),是朗氏家族第一個由知事僧人擔任帕竹法座的人。①在地區的治理中,有萬戶長一職,對萬戶長的選擇是格外重要的。京俄曾有一位司茶侍從擔任過洛扎雪寺的堪布,被稱為堪布仁欽堅贊,擔任過萬戶長。期間,一個名叫多吉貝的人被委派為司茶侍從,大小事務都處理得井井有條。被京俄派到內地辦事后,得到皇帝和上師的喜愛,賜給他世代管領帕竹萬戶的權利。他返回烏斯藏后于陽木虎年修建了雅隆南杰和乃赤康,并擔任萬戶長13年。在香巴噶舉歷史中,相傳穹波南交功德無量,他廣收門徒弟子,智慧空行母普賢女前來贊頌道:“你的門徒最終達到八萬,你最后的弟子為六人,你最終享壽一百五十,你最后升入極樂凈土。”于是,穹波南交在10日上午宣布召開大法會,召集了所有弟子門徒,熬茶布施。在法會上他交代了諸多身后事宜,對6大弟子寄予厚望,強調弟子們要團結一致,服從6人的領導。[3](P323-325)在諸如此類的法會上,“熬茶布施”是必須的環節,平時的說法法會也必然有此環節。在說法時,聽法僧眾都以錦緞為坐墊,每次法會時大量煮茶,一般在五十大包以上。因此寺院中的用茶量也以法會期間最盛。《頗羅鼐傳》記載,頗羅鼐晚上夢見一位白臉的婦女告訴他,天亮后早動身行程,路上見著吃的,不管好壞全都摻起來,自己要吃,也要給別人吃,這樣緣分才好,否則不會有什么好運氣。第二天在路上遇到一個少女提著一桶牛奶走來,頗羅鼐依夢中的指示,把牛奶據為己有,然后隨從拿來一箱好茶,攪到牛奶里去,屯氏首領的奴仆拿來鹽巴也摻了進去……總之凡是吃的都摻到一起。頗羅鼐先喝了三碗,屯氏、江洛堅巴、白策巴、白席巴、嘉康巴、吉甫唐巴等人也喝了下去。喝過這種混合物的人都很富貴,當時沒喝的后來遭遇到了不幸。因此,傳記中寫道:“像這樣的因緣,真是命中注定的。”[4](P201)通過這段記載可以發現,在頗羅鼐逐步走向宗教政治的核心領域過程中,“天賦神眷”的宗教政治觀發揮著一定作用。夢境傳達了神的意旨,而頗羅鼐很好地遵奉并實行了意旨,從而保證了他以后的大有作為,得到神佛保佑。而分析夢的實現過程發現,除了“一箱好茶”之外,其他見到的可吃之物,包括牛奶、狗的剩食、野牛角里的酒、吃剩的碎野驢肉、剛死去老狗的肋骨均非頗羅鼐隨身攜帶之物。茶是頗羅鼐出行攜帶之物,而且數量較大(一次就用掉一箱),一方面表明當時茶葉對社會上層出行的重要性,包括對日常生活與政治活動兩個層面;另一方面通過“天賦神眷”,表明茶已經成為神旨的一部分,由于頗羅鼐出行隨身帶有大量的茶,因此,即使沒有其他可吃之物,茶也必在其中。無論是純粹的宗教內部的上下傳承,還是政治系統管理人員上下傳承(如萬戶長),亦或是召開各種各樣的法會都涉及西藏自身茶文化的內容,這種文化擺脫了純粹的文化形式,上升至一種宗教與政治的判斷、識別和傳達精神意旨的重要手段(政治的與宗教的),這種手段進一步交織運用(即把政治與宗教相結合)即發展成為整合社會治理的社會外在強制力,而超越個人的命令或意志。這一作用長期以來在西藏傳統社會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以宗教活動形式出現的“入藏熬茶”現象中蘊含的政治與宗教的雙重交叉意義深刻闡釋了這一作用。
入藏熬茶
“熬茶”也稱“熬廣茶”,是藏、蒙古、土、納西等信仰喇嘛教(即藏傳佛教)的各民族的一項宗教活動,是到寺院禮佛布施的俗稱。主要流行于西藏、青海、新疆和內蒙古地區。藏傳佛教與茶有著密切的聯系,酥油茶是藏傳佛教的重要日用品,而藏傳佛教則成為推動西藏茶文化發展的重要力量。[5]“入藏熬茶”約起源于16世紀末,隨格魯派在蒙古地區傳播而漸盛,早期常與西藏教派斗爭、政治斗爭交織在一起。“入藏熬茶”者人數不等,少則十幾人,多者數百,甚至上千人。布施物品有各種牲畜、金銀、綢緞、茶葉、各種工藝品等。清政府統一西北后,封建主入藏熬茶現象成為一種不成文的規矩,10人以上要有請票程序,由駐藏大臣給予執照方可以實行。“入藏熬茶”作為一種宗教文化現象,成為西藏之外藏傳佛教信徒與西藏藏傳佛教相互聯系、有機互動的重要文化力量。這種宗教文化現象以“熬茶”為名,表明了茶事活動在藏傳佛教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對信徒具有的重要象征意義,成為重要的宗教儀式。另外“,入藏熬茶”也成為一種政治角逐的手段。噶爾丹策零曾多次請求“入藏熬茶”,被清政府拒絕,期間雙方多次發生戰爭。呂文利、張蕊在《乾隆年間蒙古準噶爾部第一次進藏熬茶考》一文中詳細考證了有關細節,認為其中都有一定的政治意圖。尤其對清政府而言,既把握了噶爾丹策零的政治意圖,又對其展示了權威,同時也進一步籠絡了僧俗領袖,增強了其歸屬感。還有一點不可忽視,即通過“入藏熬茶”也增加了西藏與其他省份的貿易往來,對推進經濟互動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乾隆八年(1743),噶爾丹策零多次命人向頗羅鼐刺探,試圖拉攏。十一月,策巴喇嘛、宰桑巴雅斯瑚朗試圖探聽頗羅鼐振興黃教(藏傳佛教的格魯派)經驗,被拒。接著又提出:準噶爾地方無好額木齊(醫生),噶爾丹策零吩咐他們來藏熬茶事畢,將好額木齊與通經典之大喇嘛延請一位帶回。對此,頗羅鼐答道:“汝等欲請好額木齊與通典大喇嘛,并未奏請大皇帝諭旨,此事我何敢專主?”(《清高宗實錄》)。噶爾丹策零,衛拉特蒙古準噶爾部首領。借熬茶事由,其他部族力量會向清中央政府提出一些請求。此次是噶爾丹策零請求派遣好的醫生和僧侶(喇嘛),但頗羅鼐非常堅決地予以回絕。這是一種政治手段,即傳達一種信息:清中央政府對西藏的一切事務具有絕對權威。頗羅鼐諸如此類對中央政府權威的樹立與維護非常多。清中央政府對此是持積極支持態度的。《清高宗實錄》中多處記載了相關情況。乾隆九年(1744)元月,在給頗羅鼐的諭旨中曾褒獎頗羅鼐在對待“準噶爾之人入藏熬茶”中所采取的恰當措施“,甚屬可嘉”。清政府的嘉獎也產生了積極的效果。準噶爾入藏熬茶者在臨別的時候表達恭順且兵戈永息之意,“群生亦皆樂業”,并誠懇表達了“結信于大皇帝”之愿望。頗羅鼐在此時再次傳遞了清中央政府的無尚權威,“大皇帝包容四海”,對待各方各族均一視同仁,對來熬茶者格外加恩,賞馬駝、路費等等諸多信息。
賜茶
傳統社會中西藏治理的路徑是眾多而復雜的,除了以上分析的形式外,還有一種最為直接的“政治對宗教的治理術”,即運用賜茶方式來加深中央政府與藏傳佛教間的聯系與紐帶。作為一種政治手段,清朝統治者在與蒙藏上層人物的政治互動中,茶葉成為賞賜和饋贈的重要物品,也就是成為了恩威并施政治手腕中的“恩施”內容。茶往往比金銀和其他財物更具有重要意義。明朝實行“群封眾建”、“寬容優撫”的政策,對藏傳佛教各派領袖進行分封,允許他們按級別定期朝貢,并給以高于朝貢的賞賜。進貢的物品包括銅佛、銅塔、犀角、珊瑚、左髻、毛纓、刀劍之類。朝廷賜給黃金、白金、錦帛、法器、鞍馬、茶、米等物。這一政策對藏族地區大小僧侶領袖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因為通過貢賞得到了豐厚的經濟賞賜,也維系和加強了自身與中央政府的關系,有利于維護自身既得利益。《明史•西域傳》記載了噶瑪巴第五世黑帽派活佛于1406年朝貢時,享受到了極高的禮遇:“帝延見于奉天殿,明日宴華蓋殿,賜黃金百,白金千,鈔二萬,彩幣四十五表里,法器、茵褥、鞍馬、香果、茶米諸物畢備。”[6]1408年,明朝遣使來迎請格魯派領袖宗喀巴,賞賜各色絲綢、彩綾、水晶念珠、金剛杵、茶葉等近二十種物品。這種“厚往薄來”的治理政策刺激了西藏寺院僧侶與內地的聯系。宣德、正統年間(1426-1449)入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年間(1450-1457)增到300人,到天順年間(1457-1464)猛增至二三千人,每年朝貢二三次。弘治年間(1488-1505),朝貢人數劇增,入貢者一次多達三千八百余人;嘉靖十五年正月(1536年2月)一次最多達四千一百七十余人。除有名望的僧侶朝貢外,寺院也組織僧團朝貢,從而獲取賞賜。《明實錄》記載,正統十四年(1449年)麥思奔寺(哲蚌寺)朝貢;景泰二年(1451年)些臘寺(色拉寺)朝貢;成化六年(1470年)葛丹寺(甘丹寺)朝貢;成化十六年(1480年)扎矢論卜寺(扎什倫布寺)朝貢。每次朝貢都是帶著豐厚的賞賜而歸。《明代宗實錄》載:景泰年間藏僧“貸買和茶至萬數千斤及銅、錫、磁、鐵等器用”[7]。通過朝貢爭取到了明朝政府的恩賜,為寺院提供了物質保障,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寺院經濟的發展。清政府時期,繼續推行厚賞政策。《五世達賴喇嘛自傳—云裳》記:1653年2月18日賞賜50兩金制茶桶兩個、金盆兩個、銀茶筒八個、白銀一萬兩等。1674年,康熙皇帝在賞賜五世達賴的物品中有重達135兩的金曼陀羅、百兩重的金錠、銀茶筒和元寶410兩等。康熙皇帝曾規定由打箭爐稅收項下,每年撥給達賴喇嘛白銀5000兩,撥班禪茶葉50大包。
《六世班禪洛桑巴丹益西傳》中也有相關記載。作為歷世班禪中第一位進京向皇帝祝壽的班禪喇嘛,六世班禪巴丹益希在進京前的1748年10月,皇帝遣使臣送了大量資費,包括:誦經費黃金29兩2錢,僧茶費白銀1000兩。僧茶費成為皇帝特別關注的重要資費,并且數額巨大。這些表現了當時的幾種社會現象:一是茶在西藏高層僧侶中極為重要;二是“僧茶費”已經成為一種僧侶日常消費的代稱;三是清政府對西藏寺院與僧侶的用茶極為重視。雍正二年(1724),鑒于達賴喇嘛每年派人到打箭爐,沿途征收“鞍子錢”,清政府決定每年賞賜給達賴茶葉五千斤、班禪二千五百斤,每年由打箭爐撥運,此外并給運費銀二百兩。這些茶由邊茶商人采辦,實際約為5000斤至15000斤。這些賞賜大大超過達賴于各地所收的“鞍子錢”,同時要求達賴停止在上述地區征收“鞍子錢”。賜給達賴、班禪的茶葉稱為“賞需茶”,每年由邊茶商人采辦。《雅安縣志•鹽茶》中記載:“賞需茶單年三百包、雙年二百包,由道署領價。賞給達賴喇嘛茶七十五包,包重五十斤,除折扣核減,實領銀三百四十五兩,另由地丁坐支。”每當清政府舉行各項大典及蒙藏上層朝貢時,茶葉常常是重要的賞賜品。歷代清帝逝世、西藏各大寺廟大做法事,清政府則賜以大量茶葉等賞項。如雍正帝逝世時“,頒賞三大寺熬茶銀三千兩、大小哈達各三百根,茶八百甑。其余寺廟只給銀三千兩,小哈達三千根,茶八百甑。蓋遵舊例以為布施資福也。”[8](P176-177)此外,清政府歷任駐藏官員均在赴藏前在打箭爐等地購備茶葉等物、以備沿途和至拉薩時對藏族上層的饋贈,這已成為一種慣例。道光時期,姚瑩在《康輶紀行》中說“:賞需以茶為主,然后雜以它物。余計半年之用,市茶百八十包。從行諸人亦各買數十包而行。”除了直接賜茶外,清政府還向西藏高層賜予大量的飲茶用具,這些器具多為金銀或美玉制成。如崇德八年(1643),圖白忒部落達賴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及厄魯特部落戴青綽爾濟等至,除令察干格隆、巴喇袞噶爾格隆、喇克巴格隆等人口悉諸多內容外,“外附奉金碗一、銀盆二、銀茶桶三、瑪瑙一、水晶杯二、玉壺一、鍍金甲二、玲瓏撒袋二、雕鞍二、金鑲玉帶一、鍍金銀帶一、玲瓏刀二、錦緞四,特以侑緘。”在與噶爾馬書中同樣有“銀茶桶二”,與昂邦薩斯下書中有“銀茶桶一”等之說。[9](P2-4)另外還有“銀茶筩(筒)”、“嵌綠松石珊瑚金茶筒”、“金茶筒”等制茶、存茶用具。[9](P13-15)20世紀初葉,僅拉薩三大寺的佛事活動所需賞賜茶量已經非常之大。當時三大寺有寺僧1.65萬人,最低年需茶葉兩千余包,酥油17.5萬余斤,糧食、服裝、柴、鹽等生活大量開支不計其數,年共需大洋174.5萬余元,宗教開支占全藏各項開支的69.5%。[10](P283)這些均由政府貼款補助。
抵御印茶
除宗教與政治以某些方式結合起來維護統治模式外,茶也滲透入其他形式的政治治理之中,其中重要的一種是茶葉政治的嘗試:抵御印茶。英國在印度扶植茶葉發展,并大力推進茶葉公司建設,開展機器生產。印度茶葉公司數量,1924年為140家,資本總額為3960萬盧比,1934-1935年為672家,資本總額為16920.2萬盧比,生產規模以及生產效率均有了很大提升。但針對印度茶業的機械化過程,國內較長時間持一種不屑的態度。以世界茶業鼻祖自居,認為中國茶的香味為最好,印茶只能販運到英國銷售,而英國人也不喜歡。[11]但面對嚴峻形勢,有人開始覺醒,相關報紙刊物上介紹印度、錫蘭、日本、爪哇等國茶業的文章不斷增多,《申報》等許多報紙不斷宣傳機器制茶的優點。1905年兩江總督周馥命率團考察了印度茶業,回國后寫了《乙巳考察印錫茶土日記》一書。在南方涉及邊茶生產與貿易的許多地方設立茶葉人才培育機構,如1909年湖北設立的茶業講習所,1910年四川灌縣創辦通省茶業講習所,1923年云南設立的茶葉講習所等等。一些茶葉公司相繼成立,并購入機械,向機械化生產過渡,涉及藏茶生產的是四川雅安川藏茶葉公司。與此同時,在與中國茶葉的競爭中,英國采用多種手段在國際、國內市場中打壓、排擠中國茶葉。把中國內地所產之茶摻到印茶之中,再以印度茶的名義在英國各地出售。英國還誣蔑中國綠茶不衛生,營養價值低。[12]印茶入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搶占中國的第二大出口國美國以及其他海外市場,如澳大利亞和俄國市場份額;二是向中國內部大量傾銷茶葉;三是侵入康藏邊茶市場。四川、云南所產邊茶大量運銷西藏,這成為歷代封建統治者增加國家財源,強化政治統治,鞏固邊防的重要舉措。英國利用印茶入侵西藏茶葉市場,實質是企圖以印茶傾銷西藏,達到驅逐邊茶,進而達到侵略西藏的目的。在印茶一步步緊逼下,國際市場中,中國茶葉市場份額逐步萎縮(見上表)。這是以茶為紐帶的抵御印茶入侵的宏觀背景。輸藏邊茶生產經營方式長期處于封建的手工作坊階段,而新興的資本主義茶產業在印度、錫蘭等地逐步興起。1840年前后,印度已經相繼成立了五十余家茶葉公司。1881年成立了“印度茶業聯合會”,并在產茶區設立分會,聯合會旨在加大對茶產業管理以及對茶葉的種植、制造、采摘進行科學研究。印茶產量因之得到迅猛發展。1950年,印茶出口量躍居世界第一位。印度茶業快速發展是和英殖民者侵略野心密切相關的。“英人海斯汀任印度總督時,看到這種情形,就企圖將印、錫的過剩之茶,千方百計設法傾銷于康藏,欲削弱我國在藏之勢力。”[11]早在1869年,英帝國主義分子枯柏在《由中國到印度之游記》中已經明確提出了印茶銷藏可帶來經濟與政治的雙重收益。
俄國人居涅爾在《兩藏記述》中也指出,英國人強行在西藏銷售印茶是把實際政治政策問題與商業掠奪結合在了一起。[8](P224)經濟掠奪是政治掠奪的先導,甚至二者在印茶入侵西藏過程中同時實現。光緒十九年(1893年)簽訂《藏印續約》,光緒三十年(1904年)英軍武裝侵略拉薩,簽訂《拉薩條約》,已經明顯表現出英國要強行在西藏開展印茶侵略的目的。1908年,印度事務副大臣在致外交大臣函中直白地表明了印茶在西藏的銷售是英國侵略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抵制印茶的入侵雖然主要表現在幾個歷史人物身上,但總體而言是當時清政府與西藏當局的一個共識:捍衛內地輸藏茶葉,捍衛主權與領土完整,抵御經濟侵略。如川邊鎮守使張毅在《請改由川邊印發茶票案》中寫道:“查邊茶額票十萬張,現極力提倡保護,以杜印茶欄入。”表明抵制印茶入侵西藏已經是川邊防衛中的重要內容。據趙爾豐分析,②《藏印通商章程》雖然當時尚在談判之中,但從長遠看來,印茶向西藏的入侵已不可避免。因此,他呼吁以四川茶業為主的邊茶供應產地迅速采取自強之策,通過改良、整頓,提升競爭力。他指令雅州、清溪等地方官員召集各縣茶商,探討形勢、妥籌對策。最后選擇了籌設“邊茶公司”的道路。這一設想雖最終未見大的成效,但卻成為中國邊茶,尤其是與西藏相關的茶產業發展的重要事件。標志著中國茶產業的一種自強、自救、自我發展的探索歷程。面對英帝國主義及印茶的大規模入侵態勢,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月,張蔭棠在致電外務部時再一次提出自己觀點,力主改變藏政,維護主權,抵制印茶入侵。在當時形勢之下,清政府意識到整頓西藏政務的必要性,西藏一旦失去,其毗鄰的川、滇、甘、青也將難保。鑒于此,光緒三十二年四月癸卯(1906年4月29日),命張蔭棠整飭西藏事務,嚴懲貪污腐化、魚肉藏民人員。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張蔭棠又提出“治藏芻議十九條”、“治藏大綱二十四款”,進一步實施治藏政策,涉及政治模式、稅賦管理、人口流動管理、軍隊設置及管理、建筑交通、教育設施、礦產開發、農業種植、風俗文化等方面。其中在農業種植方面包括了種植茶樹以及抵制印茶輸入兩項重要內容。在《中英印藏通商章程》的談判中,他不遺余力地抵制印茶侵藏,主張對入境印茶采取重稅政策。張蔭棠堅持重稅印茶,其用意顯然并不在于多征稅收,即使對印茶征再多的課稅也無法彌補英國經濟侵略給西藏帶來的損失,因此,其用意在于抵制英帝國主義的雙重入侵。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張蔭棠在《奏復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中寫道“:茶宜自種也。西藏向銷爐茶,運道艱阻,爐茶市價一錢三分,至藏須購至二兩五六錢。現在印茶力謀進藏,印度報紙載三十二年(1906年)由噶大克運至后藏茶值盧比三十二萬,將來可望暢銷。印茶無稅,運費較輕,爐茶萬難相敵;而藏民亦歲失運茶腳費數百萬。查四川從前不準茶種至藏,系為保護爐茶起見,今時移勢變,似宜以爐茶茶種輸藏,教藏民自種。查大吉嶺、哲孟雄一帶均能種茶,則西藏卓木、工部等處土性亦想能種。藏民素嗜爐茶,印茶苦澀,一時未必能廣銷,但價廉,貧民樂于購用,數年后習慣自然,茶利必盡為所奪。若以爐茶茶種輸藏自種,茶味不殊,而市價稍平,雅州茶利或猶可保。至打箭爐茶稅,或應豁免或應酌減,以輕成本;并修道路以利轉運,而省運費。”[14](P275)這是張蔭棠在奏折中提出的十六條之一,也是張蔭棠主張讓西藏自種茶的最鮮明表達。從中可發現當時四川向西藏輸入茶葉的諸多問題,如交通不便,稅費過高,造成茶葉入藏后價格過高,社會底層茶消費受到抑制。另外,“查大吉嶺、哲孟雄一帶均能種茶,則西藏卓木、工部等處土性亦想能種。”這一表述體現了當時清政府對西藏的農業,尤其是種茶方面沒有系統調查,所以,張蔭棠只能對西藏自種茶的可能性進行推測。他也看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即印茶價格便宜,目標客戶為社會底層百姓。事實證明了張蔭棠這一判斷的正確性。事實上,張蔭棠在光緒三十三年上半年已經草擬了一個具體草案來應對西藏受到的印茶威脅,其中包括在西藏種茶。在《咨外部為西藏議設交涉等九局并附辦事草章》(1907年5月)中,張蔭棠已經提議在西藏設鹽茶局,作為九局之一,專門負責茶鹽事務。“鹽茶局應辦事宜。總辦二員,委員八員,文案四員。由四川采辦茶籽,教民間自種;派人往四川、印度學種茶制茶之法。凡種茶宜于天氣暖熱之地,山溝巖間,當先從拉薩、工部、巴塘毗連貉貐野人一帶和煦之地試種。設官運茶局于打箭爐,務輕成本,照市價除運腳平沽,以抵制印度茶入口。又須分小包零賣,或每包一加剛,或兩包一加剛,以便貧民零買。”[14](P253)張蔭棠的計劃已經相當成熟與周全,除了讓西藏自種茶葉外,他還注意到了社會底層茶葉需求的滿足情況,這也是應對印茶入侵的重要舉措,最大程度減少印茶以廉價爭取到的目標客戶。
總體而言,張蔭棠所主持的種植茶樹行動是在西藏植茶的前期嘗試,為新中國成立后實現西藏地區大面積植茶做了有益的探索。這也表明當時張蔭棠已經注意到西藏植茶的可能以及自身產茶的重要性。究其原因,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茶對西藏政治及百姓生活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發展西藏的茶事業能夠一定程度推進西藏社會發展,并對抵御外敵產生良性影響。二是英帝國主義的侵略為印茶向西藏侵略打開了通道,如何更加有效地抵御印茶入侵,自產茶是一條最好的選擇。三是自產茶是最大程度減少四川茶向西藏輸入諸多弊端影響的最有利最直接措施,從而成為抵御印茶入侵的最有力武器。因此,張蔭棠在大力推進嘗試茶樹種植的同時,也采取各種措施聯合各種力量共同抵制印茶的入藏過程。趙爾豐與張蔭棠力主抵制印茶入侵,雖然側重點不同,但均體現了維護自有統治、捍衛政治利益、國家利益的政治立場。實現了以茶為紐帶的政治凝聚功能,聯合了各階層力量。雖然這一功能的實現并未真正改變時局發展,但至少表明了以茶為紐帶的各階層、各民族在國家危難面前能夠表現出一種政治向心力:一致抗外。清政府推進的抵制印茶的政治策略,在西藏地方政府中得到了積極的響應。光緒十八年,駐藏辦事大臣升泰在《復赫稅司政函》中表達了西藏地方政府請求清中央政府嚴禁印茶入藏的態度。甚至十三世達賴喇嘛親自呼吁制止印茶銷藏,并請求清政府配合行動。[8](P233-234)西藏地方政府之所以竭力抵制印茶入藏,歸結起來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印度及錫金的亡國之痛深深警示了當政者。二是印茶的入侵將直接打擊川茶、滇茶等入藏茶的發展,這對西藏財政會產生一系列惡性影響。三是邊茶貿易催生的西藏各階層的飲茶文化直接影響著西藏人民飲茶口味的選擇,印茶在侵藏初期未能通過西藏人民的口味關。[15]無論出于何種原因,西藏地方政府在面臨危難之時,能夠主動向清政府求援,并與清中央政府全力配合抵御外來侵略,成為當時中國政治現象的一道美艷風景,也成為茶在西藏傳統社會中西藏治理功能發揮的重要體現。
結語
在歷史的長河中,西藏茶文化不僅構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成為了西藏治理的重要內容。研究這些內容,有助于我們看清歷史中的諸多現象與問題。正是這種清晰的認識讓我們發現,小小的茶葉曾經在西藏社會和宗教政治中產生過如此大的影響,發揮過如此大的作用,茶文化是西藏社會秩序與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西藏茶文化中的諸多內容隨著社會的進步與歷史的發展已經逐漸被淘汰出了日常生活范疇,但有許多內容仍然深深影響著人們的言行與生活,對這些內容不能簡單抹殺,也不能隨意全盤沿襲,而應該以傳承發展與創新的態度去認真研究,使其在西藏社會生活與文化發展繁榮中發揮積極向上的作用。(本文作者:趙國棟 單位:西藏民族學院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