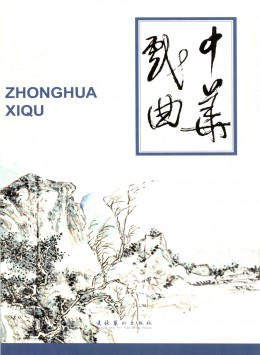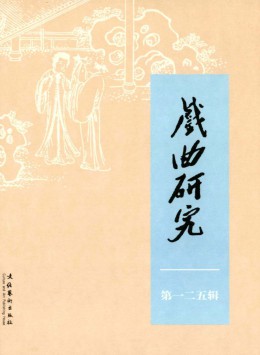戲曲價值論文:傳統戲曲的歷史價值思索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戲曲價值論文:傳統戲曲的歷史價值思索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本文作者:李冬梅 單位:河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傳統戲曲反映歷史有兩種情形,其一是對一般性歷史的反映,包括生活場景,倫理觀念,官場制度,生活風俗等。比如,《竇娥冤》及《趙氏孤兒》對官場政治的反映,《西廂記》對當時愛情生活和倫理觀念的反映,《琵琶記》反映出“災荒年月中人民的苦難、社長和里正的為非作歹”等元代社會風貌3等等;其二是對音樂自身歷史的反映,包括所各時代所使用的樂器,樂曲的結構,角色行當的衍變過程,音樂自身的發展脈絡等。譬如,《琵琶記》的“臨妝”、“吃糠”等場次為單角兒獨唱的重頭戲,這乃是對北曲“一人主唱”之定規的借鑒(“實近于北雜劇的旦或末主唱的一折,對演員的表演技藝,有著極高的要求;如果沒有雜劇一人主唱形式在表演藝術上的開拓,而光靠南戲自身在《張協狀元》中那種插科打諢方式的基礎上作漸進的積累,也是很難想象的”4);另,該劇在音樂上也采用了北曲的若干曲牌甚至是整個套曲。這些都印證了南戲在發展歷史上受北曲影響甚巨的史實5。當然,傳統戲曲所反映的諸多方面(歷史、風化、文學、藝術)之間是相互聯系而非彼此孤立的,這些頭緒猶如一根繩子的眾多纖維,每一根都有自己的開頭、結尾、卷曲、纏繞。《琵琶記》在音樂方面所受北曲的影響也是與其在文學方面對北曲的借鑒相輔相成的,前者的“吃糠”、“剪發”等出便可看作是“直接受到了元雜劇如《漢宮秋》、《梧桐雨》第四出的因物起興的寫法的啟發”6。
傳統戲曲可以“溝通時代”,一方面,藝術作品可以穿越時空向我們說話,另一方面,后時代的人可以通過對原戲劇素材或主題的不同理解、不同處理、不同反應、不同評價來和古人對話。就《琵琶記》來說,故事藍本7所反映的一系列“事件”具有強烈的悲劇性、現實性和批判性,如下層勞動人民的生活疾苦:荒旱災害,民不聊生;科舉功名改變命運的極端重要性;身為人子不行孝道、身為人夫薄情寡幸(蔡伯喈)的丑惡行徑,及好人不得好報(趙五娘),終被“馬踏而死”的悲慘命運等。可以說,此類現實性和悲劇性反映出,原南戲戲文的意圖更多是在于“揭露”而非“說教”,在于“批判”而非“引導”(這與另一個歷史事實有關,即當時從事南戲演出和創作的多是平民百姓,沒有受過太多文化教育,故此保持了慘烈、直白的藝術品質)。而相比之下,高氏的版本則反映出另一種價值取向:一代名士蔡伯喈不能無故蒙受“不白之冤”,趙五娘這樣的全忠(對丈夫)全孝(對公婆)之人不能落得“馬踏而死”的下場等。高氏在揭露和諷喻現實社會的同時,也使該劇負擔起了教化民眾、移風易俗的使命,所以,“妻賢子孝”、“好人好報”、“鄰里親近”等向善主題和結局當然更合意圖;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社會現實和思潮風氣,故而面對同一部作品會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和興趣指向,處于當下的我們所更為關注的,可能不是蔡伯喈到底是好是壞,忠、孝能否兩全,妻妾妯娌能否和睦等問題,而可能是“知識”對于改變命運究竟有多大作用,以及封建傳統禮教對人性所造成的束縛等問題。由此,三個時代(宋代的故事藍本,元代高明8的改編,即當今時代的讀解)可以在精神層面展開對話。
傳統戲曲的另一個重要功能在于“揭示人性”,人性課題也是溝通歷史與當下的核心中介。如果說“反映歷史”、“溝通時代”是所有藝術品所共有的功能的話,那么“揭示人性”便是傳統戲曲最獨特、最擅長的功能。它不光是“寫人”(反映人的生活狀況、思想觀念和復雜性格),“給人看”(各階層、各領域的觀眾),而且最重要的,它要“由眾多劃分為不同角色的人來扮演”,由此可見,人性探索全程貫穿于戲曲當中。傳統戲曲就是借助多種藝術手段,在舞臺上向我們敞開一個復雜的亦真亦幻的人性世界,通過與這個世界溝通和對話,我們體認和反省自我,從而獲得心靈的凈化和提升。人性解讀是戲曲解讀的核心,約瑟夫•科爾曼認為,是否反映了人所未知的人性側面,是否觸及重大的人生命題,當是評判一部戲劇作品立意高下的重要指標9,這條準繩對于中國傳統戲曲也同樣適用。就《琵琶記》而言,愚見以為其立意并不僅簡單在于為一代名士蔡伯喈正名10,不在于對弱勢群體生活疾苦的同情,也不在于探索忠、孝能否兩全的問題,而是在于反映人性的脆弱和無奈。對于這種脆弱和無奈,可從如下三個方面來理解:其一表現在個人性與復雜社會關系發生抵觸時。所謂“三不從情節”即為明證:辭考不從,是由于個人性必須服從“父為子綱”的社會關系規范;“辭婚不從”,是由于個人性要服從于“惟命是從”的上下級社會關系規范,而“辭官不從”則是由于個人性要服從于“君為臣綱”的社會關系規范,還有,趙五娘含辛茹苦地替父盡孝,也是由于她的個人性要服從于“夫為妻綱”的社會關系規范,同樣,牛氏在婚姻關系上陷于被動,也是由于她同時要服從于“父為女綱”、“夫為妻綱”這兩條社會關系規范。其二(是第一項的引申),人性的脆弱和無奈也表現在知識分子在當理想與現實發生沖突時,蔡伯喈赴京應考,本來是為了取得功名之后,在行“事親”之“小孝”的同時,行“事君”之“大孝”,然而,就在他金科得中、赴考之初衷即將兌現時,卻出現了變故,被迫再婚,有了知識,卻依然主宰不了自己的命運,為“事君”則不能“事親”,為“納妾”則要“拋妻”,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脫節,他軟弱而無能為力;牛氏渴盼夫妻和睦,夫唱婦隨,但一旦理想與現實發生矛盾,也只能被迫接受,作出犧牲和讓步,趙五娘的情形更是如此。其三,脆弱、無奈還隱含了另一層意思,即人的易妥協性。個人性與社會關系發生矛盾,以及理想與現實脫節等,這從古至今都是常有之事,但矛盾并不總是導致“無奈”,面對矛盾勇于斗爭,甚至“殉身”以“酬志”者也大有人在,而該劇中,雖然蔡伯喈在滯留牛府時也曾閃過尋死的念頭,但并不堅決、徹底,故而《琵琶記》所著力刻畫的,不是人性的堅強的勇于斗爭性,而是脆弱的易妥協性:蔡伯喈、趙五娘、牛氏無一不是如此。
當然,高明對人性的脆弱、無奈是持有同情心的,他在同情之中帶有批判,具體而言,他所給予全部同情的人物是趙五娘和牛氏,不是蔡伯喈。對于蔡伯喈,作者雖然著意強調了他的“被逼無奈”(所謂“三不從”情節),從而弱化了其反面形象,但這種同情是部分性的。我們隱約感到,最者最終并沒有原諒他,而是通過終場老鄰居張公叔在墳前的怒罵(所謂“三不孝”:生不能養,死不能葬,葬不能祭)和責打流露了這種態度;作者放棄了“暴雷震死”這種簡單的浪漫主義想象筆法,而是設置了一個更為復雜也更合情理、更具現實性的結局,旨在引發觀眾或后人對蔡氏這個人物的更深刻的關注和思考。對于趙五娘,作者雖然也“免她一死”,但卻使她經歷了更為艱難的抉擇,對丈夫是原諒還是懷恨,對牛氏接受還是拒絕等,以此來提升她的品格和形象,對牛氏也是如此,突出了她的賢惠、體貼和深明大義。
總之,通過一個說喜也喜(夫妻團聚、妻妾睦和、領受恩旨的嘉獎),說悲更悲(這一切卻是以犧牲父母的性命,妻子的幸福,以及知識分子的尊嚴為代價)的情節,揭示了人性的弱點,但也就在表現出弱點的地方,人性也閃耀出光輝,千百年來,正是由于人性有具勇于犧牲讓步、顧全大局、親和為貴的品格,人類才能夠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繁衍至今。
綜上,中國傳統戲曲是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活化石,特別是經典劇目,集中承載著多方面的歷史信息,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歷史的、人性的等等。戲曲帶有鮮明的民族性,正所謂“有什么樣的文化就有什么樣的戲劇”11。經典劇目不僅對戲曲史本身發生影響,更加持續地對一代代戲曲受眾發生重要影響。雖然它產生于特定的時代和社會,但由于表現出對人性問題的關注,在斗轉星移之后持續地激起回聲,人性探索是永恒的課題,傳統經典戲曲在這方面為我們奠定了豐厚的基礎。品味“經典”,需要當下人以視域融合的方式重新解讀,由此,今人與古人展開對話,傳統與當代融會貫通。只有認清了歷史與當下,我們才能更好地把握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