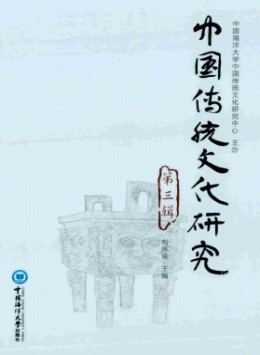傳統文化對黎族文學創作的作用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傳統文化對黎族文學創作的作用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本文作者:曲明鑫 單位:瓊州學院人文社科學院
黎族是我國具有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積淀的民族之一,是海南島最早的居民和開發者。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黎族創造了斑斕多姿的文化,如神話、歌謠、樂器、舞蹈、黎錦、圖符,以及禮儀、風俗、民族體育等。黎族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文化的概念是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在他的著作《原始文化》中,將文化定義為“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能力與習慣的復雜整體”。《現代漢語詞典》對文化的解釋之一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1]P1318這里我們將文學放在文化系統中進行探討。作為文化系統中子系統的文學,在功能、特征等多方面都受到文化的影響和制約。
第一,我們通常把文學作品分為內容和形式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從作品的內容與文化的關系上看,不同文化背景下會產生出不同的文學作品,比如人類在原始文化時期,文學作品包含有神話內容,這是因為原始文化中人類是以幻想的方式去看待和解釋人與自然的關系。到了農耕文化時期,以及后來的工業文明階段,文學也有相對應的農耕文化及工業文明的內容。我們經常提到的文學的“時代性”、“民族性”等,實際上是文學的“文化性”的一部分。相對來說,文學的形式與文化的關系并不是那么直接,但也是文化的產物,而且是在更為深入的層面上產生的聯系。文學結構、風格色彩等諸多問題,都可以在文化中找到根源。
第二,文學創作是作家對客觀世界的信息進行主觀的選擇、加工并表現出來。從創作成作品,到發行流通,再到讀者閱讀接受,文學活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同時,讀者將自己的文化修養和對客觀世界的解讀帶到閱讀接受中,賦予了作品新的意義,形成了對文學作品的再創造。讀者的閱讀效應又作為客觀世界文學信息的一部分,影響作家的文學選擇和表現。在這個雙向的文學活動過程中的每個關鍵環節都可以看到文化的作用和滲透。由此,我們能看出文化對文學的制約和影響,而且從根本上說,文學受制于人類文化的發展規律。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力所在,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民族所創造的物質文明成果或許較為容易消失,并且不停地變化,但是宗教信仰、價值體系、文化傳統等精神文明的成果會相對長久的留存下來。對這些精神文明成果的認同是決定一個民族之所以成為一個民族的根本所在。各個民族創造的文化被該民族所繼承、發展、延綿不斷,一旦民族文化沒有了,這個民族的個性特征也就不復存在了,可見文化傳承的重要性。因此,黎族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十分注重對黎族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
在幾千年的文明史中,黎族創造了燦爛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黎族人民長期生活中創造和積累的器物、貨品、技術、思想、習慣、風尚、價值、信仰、心理結構、思維方式、情感方式、行為方式等,即黎族的文化,一直影響和制約著黎族作家們的文學創作活動。黎族作家文學作品中對黎族傳統文化的記錄、傳承、保護和新的思考,體現出黎族的傳統文化對黎族作家文學的深刻影響,也體現出黎族作家對文學民族性的堅持。
一、黎族傳統美德對黎族作家文學的影響
黎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其優秀的傳統美德,在民間世代相傳,長久以來成為人們的生活理念和行為準則。黎族作家龍敏的一系列小說創作都是以黎族傳統的優秀的品德、價值觀等作為思考的起點。他的短篇小說《年頭夜雨》中的黎族青年阿元,在黎族鄉村土生土長,受到民族的教養,曾是個“連掉在地上的青芒都不敢碰一下”的老實人,“路不拾遺,見難相助”的黎族傳統美德在他身上得到充分的體現。雖然在“四害”橫行的動亂年代,黎族傳統美德在他身上泯滅了,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社會風氣又重新走上了正軌。阿元回歸了常態:捉田雞“捉公留母”、“母的留做種哩”;替別人的漁籠除水蛇:他“微笑一下,一手從籠里抽出一條一尺多長的大水蛇”、“迅速抽出尖刀把水蛇斬成兩段”、“蛇腹里塞滿了死魚。他邊擦著尖刀邊哼哼地說:‘壞種,差點把魚吃光了’。……‘我們這一帶誰不知道?人家的好東西不能拿,人家壞了的東西不要夸,這是祖先立下的規矩嘛!”;路過南豐河,又幫助“守漁床”,絲毫不要求回報。還有《黎鄉月》中的秀嫂,為了成全阿良和清玉而忍痛犧牲了自己的愛情;《同名》中的亞因,不僅以親生母親般的行動消除了丈夫對孩子遭后母虐待的擔憂,而且還與丈夫齊心走向致富路。在其他作家的多部作品中也都有體現黎族人民傳統美德的描寫。黎族傳統文化中,贊揚人性的善,也唾棄人性的惡。龍敏的《黎山魂》中對“宰合牛”的描寫就是如此:那改看見該來的人都來了,就大聲對他們說:“叔伯兄弟們,今天是大年三十,是宰合牛的日子。宰合牛,不僅是為了過年吃肉,還有另一層意思,那就是要我們所有的人都要懂得,不要頑,不要犟,不要惹出麻煩事,不要得罪人家,不要偷,不要搶,不要打人罵人,不要放牲畜去田間糟蹋別人的莊稼,不要欺老,不要辱小,年輕人不要去勾引人家的老婆……一句話,不要做壞事。你們都知道,這幾頭牛都是它們的主人干了壞事而挨罰的。我們吃了它們的肉,就要牢牢記住,犯了逆是要罰牛的,大家聽到了嗎?”這席話,在每年宰合牛前都必須由奧雅重復一遍。上述作品中對人物形象以及社會生活的描寫,體現了作家們用本民族那些足以展示人們品德、情操的傳統美德作為標尺,從多視角、深層次,刻畫人物,使主人公形象閃現出本民族優秀傳統美德蘊含的思想火花和精神風貌,形象更加豐滿而富有活力,同時也增強了作品的民族特色。
二、黎族傳統信仰對黎族作家文學的影響
在黎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還有黎族的民間信仰。黎族同大多數少數民族一樣,有著自己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這種原始宗教延續了幾千年,其原始宗教的質地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發生了演化,以致原始“宗教性”淡化,許多觀念及行為演變為民間民俗,成為黎族民間具有很強的民眾性的民間信仰。因此,把黎族的原始宗教,稱為“民間信仰”更為恰當。黎族民間信仰的核心是“萬物有靈”、“靈魂不滅”。這種“靈魂”被黎族人統稱為“鬼”。在黎族人看來,凡是有靈性的自然物、實物以及其鬼魂都會作祟于人,導致人生病。為了消災避禍,唯一的方法就是對這些自然實物之“鬼”頂禮膜拜。這些傳統的民間信仰已經滲透到黎族人的血液中,融入到黎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就連日常言行中也透露出對“鬼”的敬畏。
黎族作家們也大多生活在黎族村落,對黎族的習俗風情非常熟悉。黎族民間信仰也成了作家們表現黎族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例如亞根的《婀娜多姿》中就有很多黎族民間信仰的描寫:處置“禁母①”、“道公②”作法占卜和驅鬼等,都有細致地描寫。小說沒有停留在對這些黎族民間信仰儀式的描寫,而是對這些傳統的民俗進行了重新的審視。小說主人公之一的嫵斑,幼年時父母被寨主當作“禁公”、“禁母”殺害,嫂子也被當作“禁母”遭追殺而被迫離開家逃亡在外,哥哥在嫂子逃走后由一個正常人變成了傻子。這是對黎族傳統宗教中的惡俗的揭露與鞭笞,體現了黎族作家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重新審視,這也是黎族作家文學創作逐漸成熟的表現。而龍敏的《黎山魂》將黎族地區特定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部落斗爭、族系關系、飲食方式、服飾工藝、婚喪習俗、愛情情趣、傳說神話、歌謠諺語等融為一體。除了《婀娜多姿》和《黎山魂》這兩部作品外,還有很多作品涉及到黎族文化的描寫,有的描寫黎族人民歡慶傳統節日“三月三”的熱鬧場面、有的描寫婚喪嫁娶等祭祀儀式等等。
龍敏在《黎山魂》的前言中寫到:“所有的奇風異俗都是真實的,它們在歷次搜集和發表的資料中是絕對沒有的。我不想讓它們在無形中消失,決心把瀕臨失傳的本民族風情介紹給讀者”[2]P1。很多黎族作家在創作中都有意識地記錄、傳承和保護黎族文化,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人類的歷史進程是一個傳統繼承的過程,同時又是在傳統繼承的基礎上不斷對傳統進行審視和否定的過程。在黎族作家文學的作品中,除了對黎族的文化進行了多方位的記錄和探討,還應和時代的步伐,將黎族的文化與現代文明相對照,以新的思想觀念去考查黎族的文化、反映黎族社會、揭露矛盾。這也成為許多黎族作家創作中的一種自覺,體現了黎族作家文學在創作中“民族性”與“現代性”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