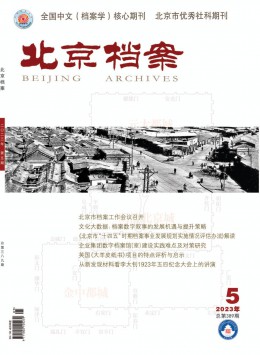北京文壇的思想戰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北京文壇的思想戰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本文作者:陳芝國 單位:廣東第二師范學院
艾勒克博埃默在論及文化殖民時說道“:文化表征(culturalrepresentations)在對別國實行殖民化和再后來從殖民者手中贏得獨立的過程中,始終都占據著一個中心的位置。對一塊領土或一個國家的控制,不僅是一個行使政治或經濟的權力問題;它還是一個掌握想象的領導權的問題。”[1]日本侵略者在抗戰時期的北京,正如他們在中國的其他淪陷區一樣,他們不僅要奪取淪陷區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權力,對于控制淪陷區思想文化,“掌握想象的領導權的問題”,與所有的殖民主義者一樣,也有著充分的認識。然而,抗戰以前就已經根深蒂固的京派文學傳統在淪陷時期北京不僅依然頑強存在,甚至以其或疏離或抵抗的文化政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作為文化殖民手段的“思想戰”。
一、“思想戰”與京派文學傳統
日本筆部隊極其強調在中國大陸實行思想戰的重要性。神谷正男曾言“:欲確立東亞共榮圈,為完成日本于世界史的使命的重大任務,對于東亞共榮圈內思想戰之問題,不能加以忽視:尤其在中國大陸的思想,是為確立東亞共榮圈的中心。”[2]早在1938年,近衛聲明已提出“新文化創造”的問題,在討論“大陸文化”時,“大陸文學應當屬于報道文學”成了日本最流行的議論;甚至還有人提出,大陸文化“屬于日本文化里的一個部門”。大久保武認為,如果把近衛聲明提倡的“東亞新秩序”,或“東亞協同論”、“東亞聯盟論”,僅僅當作日本的一個口號,那么“新文化”,即“以‘八纮一宇’、‘民族協和’的理論為中心的,全體主義的文化”,仍無法取代自由主義的“舊文化”;因此,應當以大亞洲主義和三民主義為基礎,日本中國“共同提倡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具體的口號”,一邊檢討舊文化,一邊創造新文化。只有這樣,“八纮一宇”這一句日本語,才能夠“變成了東亞語或者是變成了世界語,而被譯成了各種不同的語言、文字”[3]。“七七事變”之后,大批日本作家被派到中國。他們以文人的身份,自覺或不自覺地為鞏固日本占領區的殖民統治服務。
“七七事變”后進入中國的日本文人和思想家起初并非全都認同日本的侵華戰爭。竹內好寫于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的一篇宣言《大東亞戰爭與吾等的決意》,就表露了他們這些人內心的疑惑:“我們對于支那事變有著完全不同的感情。我們為疑惑所苦。我們熱愛支那,熱愛支那的感情反過來支撐著我們自身的生命。直至支那事變爆發,這確信土崩瓦解,被無情地撕裂。殘酷的現實無視我們這些中國研究者的存在,我們遂開始懷疑自身。我們一直在懷疑,我們日本是否是在東亞建設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4]
然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覆沒了這些日本學者對于弱小中國的感情,他們積極主動地清除自己內心殘存的道德疑惑。于是,竹內好代表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進行宣誓“:從東亞驅逐侵略者,對此我們沒有一絲一毫進行道德反省的必要。大東亞戰爭成功地完成了支那事變,使它在世界史中獲得了生命;而現在使大東亞戰爭本身得到完成的,應該是我們。”[5]對于這些曾經有過疑惑的日本在中國的學者來說,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得日本侵華戰爭的性質,由非正義變為正義,由侵略變為解放。日本“筆部隊”成員和文化人士自此開始毫無疑慮地投入大陸“思想戰”,他們企圖通過對淪陷區中國文人的文化和文學活動進行干預、控制和滲透,進而奪取“想象的領導權”。這種干預、控制和滲透的思想戰首先體現為召開由日本人掌控的文學大會和重組各類文藝家協會,將日本的大東亞共榮的思想灌輸給中國作家,從而通過他們對于殖民文化的書寫,在淪陷區民眾中進行廣泛的殖民意識形態建構。
然而,北京淪陷區作家對于殖民意識形態的接受程度以及他們對大陸“思想戰”的配合程度,對日本人來說,卻始終是一個問題。換言之“思想戰”必然會遭遇到此前已經在京津地區文壇成型的京派文學傳統。由周作人、沈從文、鄭振鐸、卞之琳、何其芳、廢名、李健吾、朱光潛等人開創的京派,雖然成分復雜,但根據吳福輝的說法,大致可歸納為:(1)他們強調普通人與日常生活的精神狀態,有強烈地方風味,比如沈從文與師陀的作品。(2)弘揚人心純潔、自然之美以及理想童年,有一種典型的回憶式敘述方式,以及詩意的懷舊氣氛。(3)強調鄉土中國的視角,懷疑現代城市文明。(4)對鄉村進行贊美,對城市進行諷刺,努力通過文化批判,再造民族品格[6]。京派文學傳統內蘊的詩、美、優雅、尊嚴、簡樸、克制、和諧等特質遭遇到“思想戰”誠然不如出現于國統區和解放區的抗日愛國主義文學來得激烈,但辯證地看,也正是它在政治和倫理層面所主張的克制與和諧難以與思想戰構成正面沖突,從而也就使得它在審美層面所主張的詩、美、優雅等特質不僅得以茍活下來,而且也因為其為文學而文學的自由主義文學觀念,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思想戰咄咄逼人的鋒芒。
二、北京文人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1942年至1944年連續三屆由日本“筆部隊”成員操控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本質上是為了進行殖民統治宣傳,身處北京淪陷區的某些作家也受邀參加。這些作家尤其是其中早已成名的京派作家,對這三次大會的反應與態度,以及與這三次大會相關的文學作品的主題,具體地反映出京派文學傳統與思想戰不相耦合甚至產生齟齬。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于1942年11月在日本東京召開,北京代表錢稻孫、沈啟無、尤炳圻、張我軍和日本華北駐屯軍宣傳顧問片岡鐵兵,基本上都是不太知名的人物。不僅大會的議題是配合日本侵略亞洲各國的所謂“大東亞精神的梳理”、“大東亞精神的強化普及”、“以文學為途徑的思想文化融合方法”和“通過文學協力完成大東亞戰爭的方法”,就連會議的日程安排以及開會方式也表明,日方完全以統治者自居,處處炫耀日本文化的優越,日語成了大會的唯一工作語言,所有其它語言一律翻譯成日語,日語發言不翻譯成任何語言。對此,即使投敵的中國代表也不乏異議。錢稻孫就在會上發言“:我們應該改變各自的立場并且努力尋求一個共同的基礎,換句話說,我們應該抱著這樣一種情感來聚會,即我們的國民應該設法成為你們的國民,你們的國民應設法成為我們的國民,并且在考慮問題時達到這種境界。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會有真正的同情并因此而達到感情融洽嗎?當前,這似乎是對某種優越感的一種強烈警告。”[7]
這種投敵者對于殖民者的批評一方面毋庸置疑是基于共同目標的內部歧見,但從中也可窺知自五四以來受文化世界主義影響的中國文人對“想象的領導權”的潛意識留戀。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于1943年8月25日至27日在日本東京舉行,與會的北京代表有沈啟無、陳綿、張我軍、徐白林、柳龍光、蔣義方。熱衷于樹立儒家文化思想中心論,在思想觀念上跟不上日本軍國主義步伐,實際行動上仍以京派文學傳統內在的自由主義心態對待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不出會的淪陷區權威作家周作人,在這次充滿決戰意味的文學大會上,自然難逃日本人的缺席批判,最后甚至引發他與其弟子沈啟無及日本人片岡鐵兵之間的激烈沖突。其實,即使參加大會的淪陷區文學代表也并沒有徹底地表現出“做穩了奴隸”的言行。中國代表只“帶回來滿篋歌頌日本風土名勝古跡之類的文章,而不曾見過一篇如何致力于大東亞文學建設的方案”[8]。從第二次大會結束到1944年底,淪陷區的文學創作,也沒有響應“完成文學的報國的使命,顯示大東亞主義的新文藝的特色”的號召,“依然是在廢墟上嘆息著悵惘的氣息,依然在風花雪月里吟詠著感覺與幻想;依然在離奇的戀愛氣息里構撰著浪漫的傳奇”[9]。當然,第二次大會的某些提議也的確實施過,比如評選和頒發“大東亞文學賞”。然而,來自于北京文壇的獲獎作品,無論是袁犀的《貝殼》、予且的《予且短篇小說集》,還是后來由日本文學報國會事務局長久米正雄到北京后追加為“大東亞文學副賞”的梅娘的短篇小說集《魚》、林榕的散文集《遠人集》和莊損衣的詩《損衣詩抄》,都與日本軍國主義文學觀無關,袁犀本人更是中共地下黨員。當然,我們也很難從這些作品中讀出民族主義的意旨,這些獲獎作品從主題到技法,大多是戰前京派現代主義文學觀念的延續。
第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遲至1944年11月12日才在南京召開,代表北京方面出席的有錢稻孫、趙蔭棠、楊丙辰、山丁、王介人、梅娘、林榕、雷妍、辛嘉、蕭艾、侯少君等11人,與前兩次相比,人數大為增加,看似盛況空前。然而,由于此次主辦方為偽國民政府,地點為南京,中方代表人數也多于日方,更主要的是,隨著二次世界大戰進入最后的階段,日本在這些中國代表心目中的地位就更加削弱了。在大會上,日本人根本沒法將代表們的聲音集中到他們仍試圖倡導的軍國主義文學觀上。除了表面上呼應大會的宣言和議題外,中國代表們更關注的是諸如作家的生活保障、文學工作者的合作消費以及老年作家年金這樣一些與自己的生活待遇密切相關的問題。針對中方代表的“發言沒有一個順應日本國策”,只關心個人生活的情況,日方代表再也不能像前兩次大會中那樣厲聲批判,只能在背后說說“真是壞透了!他們完全不顧精神方面的問題”[10]。至此,作為日本侵華期間大陸思想戰在文學領域最集中體現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三、京派傳統與官方文學團體的內在疏離
成立于1942年9月的華北作家協會是北京淪陷時期持續時間最長也最有影響力的官方文學團體。發起人柳龍光將協會目標“求文學藝術的發展,與大東亞的進展一致”解釋為“:我們要建設文藝學術,于作家們也得要求視察地方治運狀況為作品增加資料的機會,我們要求文藝學術之進展與大東亞建設之進展一致。”[11]協會目標以及柳龍光對于目標的解釋,皆表明該文學團體服務于大陸思想戰。華北作家協會的成員包羅廣泛,它的干事會和評議會的成員不乏滯留于華北的文化名人。周作人任評議會會長,在沉默中蟄居京城的俞平伯和郭紹虞也位列評議員隊伍之中,似乎具有行業團體的性質,然而其組織形態是自上而下的。起初,它并沒有明確的行政隸屬關系和固定的經費來源,依靠日偽機構的“捐款”進行運轉。此后,華北作協更加積極地為新民會出力,甚至參加了新民會于1943年6月8日舉辦的華北各民眾團體剿共講演大會,并為當日成立的華北民眾團體防共大同盟起草宣言。因此,正如張泉所言“:盡管它號稱是一個民間團體,盡管它的許多成員的作品與日偽的宣傳綱領無關,有的甚至還表達了不滿和反抗的意向,但就一級組織而言,它是一個忠實追隨殖民當局的文化控制機構。”[12]這種為殖民者服務的政治色彩,在抗戰末期愈發濃重和直露。1944年9月24日召開的華北作家協會第三次全體會員大會緊跟日本,也將會議名稱改為“決戰文學者大會”。這次大會對機構、人事和簡章都進行了調整。領導機構改為執行委員會,主要負責人由當局的文化宣傳行政主管機構從會員中選定,取消了評議員會,由執行委員會聘請若干評議員,其任務縮減為向執行委員會提供會務方面的“咨詢參劃”,在作協舉辦的事業中,醒目地添加了“實踐國府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及大東亞宣言昂揚文化之原則”之類的內容。至此,它已徹底暴露出為殖民統治搖旗吶喊的真面目。到1944年12月底,中國戰場的態勢以及日偽當局的財力狀況,已使得作為思想戰一部分的文學宣傳,在“大東亞戰爭”中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華北作家協會也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雖然從整體而言,華北作協自始至終都是一個殖民文化機構,但正如淪陷區諸多與日本殖民者有關的文學團體一樣,它的政治性質并沒有成為作家寫作時的必然參照。以它所設立的“華北文藝獎金”為例,也可見出二者之間的疏離和錯位。第一屆“華北文藝獎金”聘請錢稻孫為主審委員,聞國新、俞平伯、梅娘、徐白林、南星、朱肇洛、張鳴琦、張鐵笙、李景慈為審查委員。馬驪的小說集《太平愿》獲正選,楊鮑的長篇《生之回歸線》、雷妍的中篇《良田》、蕭艾的短篇集《萍絮集》、穆伊芒的詩《夜鶯吟》、王羅的劇作《長命百歲》獲副選。盡管這項獎金的設置是在步日本“大東亞文學賞”的后塵,但獲得這項獎金的作品和獲得“大東亞文學賞”的作品一樣,幾乎很少為日本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搖旗吶喊。尤其獲得正選的《太平愿》,其藝術價值不僅在當時已獲得肯定[13],在時下的淪陷區文學研究界也已獲得定評。至于認為這些作品“在殖民體制中產生,受到殖民當局的獎勵,然而作品的主題,卻是與既存制度對立的”[14]。似乎稍欠妥當,因為無論是“大東亞文學賞”還是“華北文藝獎金”,獲獎的作品幾乎都很少為日本的大東亞戰爭和殖民政策進行宣傳,但這些作品似乎也沒有呈現國統區和解放區抗日文學那樣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換言之,獲獎作品與“思想戰”之間,更多地呈現為疏離的關系,而不是對立的關系。雖然日本試圖控制北京淪陷區的文學場,并進而將之轉變為殖民主義的宣傳領域,但決定著文藝獎歸屬的淪陷區知名文人,無論其投敵與否,似乎都仍普遍地懷抱著一種京派自由主義文學想象。正是這種藝術至上的自由主義觀念,使他們將文學分裂成作為藝術的作品與作為宣傳的文字。由于淪陷區的文化殖民并未完成,這種在淪陷區文人中普遍內在的審美與意識形態的疏離與分立觀念,直至抗戰勝利都依然存在。
四、校園文學的抵抗策略
校園文學也是爭奪想象領導權的重要領地。被研究者稱為北方“孤島”的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的文學社團,不僅受到京派文學觀念的影響,更因為校園師生面對侵略者的殖民主義統治在文學方面所采取的抵抗策略,使我們在官方和半官方文人赤裸的獻媚或曖昧的疏離之外,終于看到了京派文學傳統在抗戰時期北京文壇作為一種抵抗策略的可能性。日軍占領北平之后,曾經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宋淇,作為燕京大學燕京文學社的主要成員,在《燕京文學》的“發刊詞”中寫道“:在這長長的,嚴冷的冬日里,我們帶不來‘春天’。我們沒有這能力,也沒有這野心。我們要說話,我們要歌唱,可是我們的‘歌聲’也許會很低,很輕,輕得別人連聽都聽不見,更不用說能使別人的心‘異樣的快樂’。但,假如這歌唱不是為別人,它至少是為我們自己。我們至少能聽見自己的歌聲。一個人不見得是他自己最好的欣賞或批評者,可是在這種情形下,欣賞和批評并不是最重要的。我們要的是一點自信,一點慰藉。況且一切并不如我們所想的那樣壞,我們一定可以得到反響,也許我們歌聲能在這片空曠的‘莊園’里引起一陣回聲,引起一點攪動。”[15]
在侵略者的環伺之下,打破內心的沉默,進行自由的言說和寫作,是校園文學抵抗文化侵略的策略之一。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后,日本對英美宣戰,日軍進入校園,旋即查封了燕京大學,長期堅守純文學立場的《燕京新聞》之文藝副刊和該校的《燕京文學》文學社,皆被迫停刊。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已與德意結盟,輔仁大學由于是德國天主教圣公會所辦,該校遂能長期存在于淪陷的北京。該校輔仁文苑社的《輔仁文苑》一度成為華北淪陷區影響最大的純文學刊物。其核心成員查顯琳乃地下鋤奸隊隊員,其辦刊宗旨則是指導人生,“要求每篇作品對人生都有好的影響,最低限度也要不至于發生惡的影響”。這種主張實際上是對京派另一面的堅守。因為“為人生”的京派本身并非只有周作人式的閑適與虛無,也有看重生命的意義與不朽的一面,后者在老舍和沈從文的筆下有精彩的表現。此外,燕京大學與輔仁大學的校園刊物從不介紹日本的文學和文化,即使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古典文學也從未出現過,而校外的官辦和民辦刊物往往每期都專門介紹日本文學和文化。翻譯和介紹日本文學在“九一八”之前大受歡迎,似乎與戰爭和文化殖民沒有關系,但以青年為主力的學子似乎對日本文學和文化沒有好感,實已牽涉到民族共同體的現代性想象問題。《輔仁文苑》逐漸走向校外,甚至行銷至華北各地,在青年們中的影響越來越大,以至于可與民辦的《朔風》和官辦的《中國文藝》爭奪讀者市場。“這份愛國的刊物,卻因太受歡迎而遭到日偽的嫉視了!”[16]
日偽礙于該校的圣公會背景,沒有直接查封該刊編輯部,但他們卻試圖以利誘方式對其進行控制。編輯之一的張秀亞事后回憶起來仍是義憤填膺:一天,我們在輔仁文苑社那間格門紙窗的辦公室中,接到了一張裝在大信封中的一紙“公文”,發文者是投敵的周作人主持的偽教育督辦總署,受文者是《文苑》全體編輯、負責人,這公文開頭先贊美了這刊物幾句,然后“總署”擬每月給予若干津貼以補助我們出版費用,并且要我們每個人填具三代宗親的名字,到總署去登記,以后將發給我們每人聘書一紙,可以按月支薪[16]。
輔仁文苑社成員收到此“收編”函,即當場撕毀,投諸火中,自行停刊以示抵抗。五、結語日本“筆部隊”成員既明確意識到“思想戰”在掌握北京淪陷區文化藝術領導權方面的重要性,也通過邀請北京文人召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頒發“大東亞文學賞”,成立官方色彩濃厚的文學團體,壓制和利誘具有進步傾向的校園文學社團,對北京的文學場域實行具體的干預、控制和滲透。然而,由于北京文壇盛行的仍然是京派文學傳統,“思想戰”不僅被具有官方色彩的文人從審美層面加以疏離,而且被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的校園文學社成員分別以沉默中的歌唱與利誘下的沉默予以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