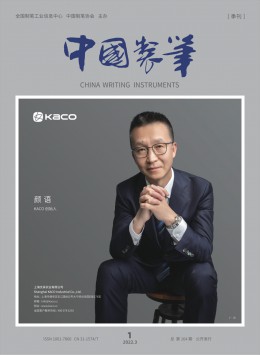中國比較文學的轉向分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中國比較文學的轉向分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中國比較文學在它的成長之路上經歷了全面向西方學習、對外開放,關注比較文學自身文學性問題,再次回轉歸向東方的實踐探索歷程。但回歸并不是一種倒退,反而體現出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不斷成熟與發展的良好趨勢。學界在開放與退守、文化研究還是文學研究、向西方看齊還是向東方回轉等諸多問題上相互爭鳴,各抒己見,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較文學“度”的圍欄與框架,使得比較文學在平衡中不斷發展,走向繁榮。
關鍵詞:比較文學;對外開放;文學性;回歸東方
時至今日,比較文學之跨界色彩鮮明,包容范圍之深之廣有目共睹。在其開放性和國際性不斷滋養下的民族交流之樹日益繁茂,但學科發展中也存在著學科邊界日益泛化,理論體系不夠完善,創新思維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立足點而成為西方理論闡釋的注腳等問題,這使得比較文學經歷了一次深刻而嚴重的危機。對此,比較文學走向問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中國首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導高層論壇”提出了中國學者應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與他種文化共同建構新的文化語境,從而形成一種文化自覺的命題。葉舒憲也在其論文《論西方思想的“東方轉向”問題》中談及“比較文學學者研究的興趣點發生了轉移,因而呈現出一種‘自西向東’方向性的改變,‘東方轉向’問題從某種意義來說具有其雙重顛覆性,它既顛覆著西方沙文主義的知識現狀,又質疑其社會科學的基本假設和思維方式,進而引發人們對獨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資源的探尋熱潮,以及對其文化價值的重估”[1]。由此可見,針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缺少獨立性和自主性的現狀,學界基本上采取從東方文化與文學自身內部尋求未來發展的途徑,這種“向內轉”的趨勢已然成為一種潮流,逆向與比較文學的“文化”轉向,比較文學的“翻譯”轉向、比較文學的“人類學”轉向等潮流溝通交流,雙向疏通比較文學國際性之河。本文旨在歸納梳理轉向時期的重要文獻,勾畫出一條近些年來比較文學轉向路線。
一
中國比較文學自成立之日起,就確立了“走出去”的戰略方針。此時探討重點還集中在學科建設是否具有合理性、學科的本體論究竟為何、比較文學的名與實等一些基本問題的探討上。同時,一些民族主義者拋出“不忘國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銳命題來挑戰比較文學界因年幼而暫時的無所適從。中國學派所應對的方式就是在保持傳統文化特質的同時,吸納法國影響研究學派和美國平行研究學派的學科理論體系,研究方法的同時,自創闡發法研究,用西方理論解讀中國文學,從而推動中國文學國際化進程。正如曹順慶所展望的那樣:“在構建文化軟實力上,他國化也給我們開辟了一條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徑。當前,如果要想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就必須對軟實力的兩翼———‘拿來’和‘送去’的他國化狀況進行深入的研究,從中探討文化發展與創新的規律,分析既能增強我們的文化資源基礎,又能提高我們的文化影響力的文化傳播規律。”[2]
由此可見,比較文學學者的確具備開放性的眼光,在研究過程之中立足比較文學這一根本特性,可以說沒有開放性,比較文學自身難以為繼,開放性是比較文學的動力之源。有三位學界權威無疑促進了比較文學未來發展的對外開放性。一是中國比較文學學術帶頭人樂黛云先生,她提出在當前文化轉型時期比較文學研究應當更加關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傳統中“和而不同”思想為基,大力促進世界異質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寧教授,他在《比較文學、世界文學與翻譯研究》一書中表明:在經濟全球化、國際一體化的當下,人文學者應當充分順承這一浪潮,推動中國文化與文學走向國際化。三是天津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孟昭毅教授,他在論文中談及從文化多元主義的思想來分析,人們企圖以強調不同族群藝術表達的多樣性,來改變民族文學一統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間的文化交流與連接,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時代表現得異常強大。因此,新的族群離散與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種沖擊民族的力量[3]。
他認為,一個民族能夠成立的前提是應具有相同的語言文字,獨特的文化傳統,積淀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結以及審美準則。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極力沖刷這一切,它讓人們通過各種交流媒介了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并在此過程中學習對方的語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溝通的過程中,已經成為主流的文化強者的偏好以及審美準則往往都會在很大程度上沖擊文化弱者的頭腦,因而造成其學術心態的失衡,在一味學習中忘記了自己研究的立足點。而這個問題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為正是它敲響了比較文學開放性的警鐘,學界應該反思對外開放“度”的問題,以及自身研究“質”的問題。在文化交流的進程之中,在強勢的“他者”眼中,中國比較文學為歐洲中心主義所輕視,所扭曲,安門立戶的闡發法不過被其當做一種注腳而非一門學派來對待。在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進程中,應正視其所存在的問題,一是闡發法既然過度依賴于對文學文本進行生搬硬套的理論分析,因此很容易成為西方先進理論的注腳,同時也局限了學界研究方法的創新。因此,有的學者認為比較文學研究應當從關注自身的“文學性”轉向關注比較文學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轉向。葉舒憲認為,由于比較文學具有跨語言、跨學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較早地接受來自外界的形形色色的理論信息,領先于一般的學科研究,較早地把握學科探索變異的節奏與趨勢[4]。劉貴珍在評論王寧新著《比較文學、世界文學與翻譯研究》時介紹了王寧本人對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之間關系的看法。王寧認為,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并非單純是對抗性的關系,其間也能達成通力合作。他們認為,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不是對立性的,而能構成一種張力,互相推動雙方的發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他們認為關注“文學性”,關注“經典”的做法有失恰當。因為當某些作品一旦被認為是“經典”,其中的某些杰出表達就具有了“文學性”。
而這種認定不過是特定審美情趣在讀者的腦海中固化,它的背后豎立著某種具有統治秩序的意識形態之墻。人們呼吁“回歸文學性”,“回歸文學性經典”,他們實際上是希望能退回到這面墻體之后保護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則恰恰相反,它恰恰質疑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并試圖從整體的歷史關系中探尋其形成過程。持此觀點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場上,而不是一個文學人的眼光看待此問題。二是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泛化問題值得關注,并且有待改善。比較文學在其文化轉向階段雖然日勝一日,但漸漸脫離開了它的文學本質,從而使比較文學學科模糊泛化,邊界不明。比較文學雖然具有包容性的特點,但又不是無所不包,否則就不能作為一個正統學科來界定它的內涵與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極為認真地反思比較文學本體論意義之后,提出比較文學學者應當關注對文學文本的細讀。他認為,比較文學歸根結底還是關于文學的研究,無論它包含的范圍有多廣,文本研究還是其最終的根基。離開文學的特性來談比較文學研究是一種極其錯誤的方式,這種現象的出現值得當代學界去反思。此外,還有一些文章也關涉到這一問題,如王志耕提出:“比較文學危機的真正原因是學科邊界的泛化,其出路在于找到與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其實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都具有明顯差別。
文化研究的對象是文化系統中文化諸要素與藝術文本的隸屬關系,比較文學則是文化系統中藝術文本的并置結構關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統中非文學因素與文學的各種隱喻關系,是一種縱向研究;比較文學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統中不同文學因素之間的各種轉喻關系,是一種橫向研究。基于此,比較文學應當放棄跨科際研究的屬性,通過退守的形式維護其學科的完整性。”[5]這篇文章更為系統地分析了比較文化與比較文學在對象、范圍、研究重點等方面的差異性,比較文學應當更加關注對文學要素的研究。筆者認為如此的倡導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較文學的脈搏?無論是走出去也好,退回來也罷,比較文學自身的特性決定著它發展變化的軌跡,學界需要認真體會它的“度”到底在哪里。因為比較文學在中國屬于新興學科,它還像個未發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征并未充分表現出來。
二
至于退守到何種程度,學界見仁見智。但較為權威的觀點認為,回歸后的“文學性”有了某種升級的意味,它不僅涵蓋歷史與傳統,而且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富有人文關懷。不僅注重文本中呈現的“個體”的生存境遇,更加關注其“人類學”走向。葉舒憲在《“世界文學”與“文學人類學”》中表示,原來人們關注“文學性是什么?”,現在則思考“族群的種類與各自的文學性”,還有“到底哪一種文學性具有普適性?歐洲中心主義標榜的文學標準是否能一直延續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為歐洲中心論已經阻礙了比較文學健康平衡的發展,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內部的多樣性構成,理所當然成為未來研究關注的焦點。這不僅僅為中國學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源,還成為國外研究者轉換新視角的巨大寶庫。
于連的《對比較的重新思考》中談及不應將“遠東”視為一種歐洲理性的神話式反面,要研究這樣的反面還要關注自身內部。這與葉舒憲提到的比較文學研究東方轉向不謀而合。可見比較文學的轉向趨勢已經為中外學者所覺察。其實,當人們去關注比較文學“文學性”這一要素時,自然而然的會界定出“文學性”的范圍。它的根基是文本,但是不止文本研究那樣簡單。它研究文學內部要素的問題,也關注文學研究的安身立命,發展趨勢,獨立地位等重大課題。簡單講就是比較文學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問題。而關注“文學性”問題的時候,必然會涉及到“東方轉向的問題”。葉舒憲認為,西方世界雖然依靠強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榮之路,但是工業革命的成功卻扭曲、異化了現代西方人的靈魂,很多人都經歷了重大的精神危機,但是他們卻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來治療,因此,東方文化便成為他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劑。20世紀西方哲學也同樣在質疑自身傳統的形而上學觀。他們主張承繼并發揚舒本華、尼采的悲劇意識,進而探尋東方智慧的神秘樂園,在伊甸之中尋找精神慰藉,開掘苦難之源。
這可以看做是比較文學實現其“東方轉向”的外在條件。此外,葉舒憲在《再論20世紀西方思想“東方轉向”》中,分別從哲學、經濟學、生態倫理學、心理學、女性主義等方面論證了東方轉向與中國密不可分。上述幾種思潮已為中國學者廣泛借鑒并加以運用,幾乎研究任何一個稍有名氣的文人學者,抑或詩人理論家,都要從這幾種思潮擇取一二加以分析,成為注腳解讀的典型現象。但是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經歷了歷史的沖蝕之后,也開始轉向東方,關注東方,因為東方的特質是如此的明顯,蔓延范圍是如此的深廣,存在數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為距離的遙遠而被永遠忽視。比較文學是一門與時俱進的學科,它隨著歷史的發展,經歷了全面學習西方、對外開放———回歸文學性———再次回轉歸向東方的歷程,這種回歸并不意味著是一種形式上的倒退,反而體現出它的不斷成熟與發展。學界在開放與退守,文化研究還是文學研究,向西方看齊還是向東方回轉等問題上相互爭鳴,各抒己見,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較文學“度”的圍欄與框架,使得比較文學在平衡中不斷發展,走向繁榮。
這條回轍型的流動軌跡,體現出中國比較學界在學科體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斷地自我完善與自我更新,它仿佛一條長河一樣溝通南北,跨越東西,將比較文學流動成一種國際性的學科。在交流之中不斷重視自身的特性,不斷豐富發展,精益求精。當然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廣大學者能夠真正做到求同存異,海納百川,探索鉆研,共同促進比較文學之大興盛、大發展。
【參考文獻】
[1]葉舒憲.論西方思想的東方轉向問題[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2).
[2]曹順慶.“他國化”:構建文化軟實力的一種有效方式[J].當代文壇,2014(1).
[3]孟昭毅.從民族文學走向世界文學[J].中國比較文學,2012(4).
[4]葉舒憲.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后文學時代”的文學研究展望[J].新東方,1995(2).
[5]王志耕.比較文學:在退守中得到生機[J].中國比較文學,2006(1).
作者:楊岱 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