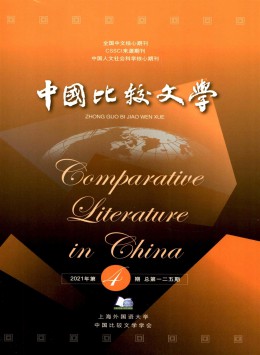比較文學(xué)的變異學(xué)研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比較文學(xué)的變異學(xué)研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毛姆的許多作品里都刻畫了民國時期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毛姆雖然游歷過中國,并且是以冷靜、客觀的態(tài)度觀察中國,但是由于文化的“異質(zhì)”性,毛姆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其實已經(jīng)是發(fā)生“變異”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存在著許多的誤讀和想象。從比較文學(xué)變異學(xué)角度,將更容易幫助我們理解這種“差異性”。
關(guān)鍵詞:毛姆;民國時期;小說;中國人;變異學(xué)
一、引言
毛姆是20世紀英國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頗豐,無論是小說、劇本、隨筆、游記還是回憶錄,都廣受好評。毛姆一生愛好旅行,他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毛姆于1920年前往中國游歷,并把能激起他興致的人和地方都一一記錄了下來。而這50篇長短不一的文章就形成了游記《在中國屏風上》(OnaChineseScreen,1922),在其中毛姆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優(yōu)美犀利的文筆,描述了他在中國游歷時見到的古老而神秘的山川風物、人文景觀。另外,涉及到中國或是以中國為背景的還有作品《面紗》、《刀鋒》以及《蘇伊士以東》。毛姆用文字為英國讀者描繪了一幅幅光怪陸離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對于毛姆筆下民國時期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我國學(xué)者也進行了積極的研究。普遍的研究觀點認為“毛姆心目中的中國形象還停留在中國古代,特別是停留在中國的漢唐時期……在毛姆的心目中,西方文化優(yōu)越論的觀點充斥其心中……更多表現(xiàn)的是傲慢與偏見、鄙夷和不屑”。[1]還有一些學(xué)者用后殖民主義批判理論來解讀毛姆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因此難免在批判中偏向了民族情緒的發(fā)泄和自我辯護,而失去了客觀公正的立場。本文將基于比較文學(xué)變異學(xué)研究的范疇,從比較文學(xué)形象學(xué)和文化誤讀的角度來對毛姆筆下民國時期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進行分析與探討,以期能獲得一些新的成果。
二、比較文學(xué)的變異學(xué)問題
變異學(xué)研究是比較文學(xué)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義的研究領(lǐng)域。“比較文學(xué)變異學(xué)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變異性,同源的文學(xué)在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傳播與交流中,在語言翻譯層面、文學(xué)形象層面、文學(xué)文本層面、文化層面產(chǎn)生了文化過濾、誤讀與‘創(chuàng)造性叛逆’,產(chǎn)生了形象的變異與接受的變異,甚至發(fā)生‘他國化’式的蛻變,這些都是變異學(xué)關(guān)注的要點,在這里,變異性成為可比性的核心內(nèi)容。”[2]31“而文化過濾帶來一個更為明顯的文學(xué)變異現(xiàn)象就是文學(xué)的誤讀,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學(xué)現(xiàn)象在跨越文化圈時產(chǎn)生一種獨特的文化過濾背景下的文學(xué)誤讀”。[3]50比較文學(xué)形象學(xué)的形象“是異國的形象,是出自一個民族(社會、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個作家特殊感受所創(chuàng)作出的形象。”[3]25巴柔也清楚地闡釋了比較文學(xué)意義上的形象,他認為“比較文學(xué)意義上的形象,并不是現(xiàn)實簡單的復(fù)制物,它是按照注視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構(gòu)、重寫的,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4]這種形象既然是一個“社會集體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視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構(gòu)的,那么發(fā)生變異就成為必然了。在創(chuàng)造性想象和變異理論的視角下,毛姆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現(xiàn)而是主觀與客觀、情感與思想混合而成的產(chǎn)物,生產(chǎn)或制作這一偏離了客觀存在的他者形象的過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視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觀念模式對他者的歷史文化現(xiàn)實進行變異的過程。”[2]123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來源于一種存在論上的邏輯辨識,而后轉(zhuǎn)隱為一種更深的神學(xué)指認和倫理學(xué)。比較文學(xué)形象學(xué)中的“他者”,并不僅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學(xué)作品以及相關(guān)的游記、回憶錄等各種文字材料中,像異國形象、異國地理環(huán)境、異國人等,這都可以納入比較文學(xué)形象學(xué)“他者”研究的范疇。[2]127因此,我們得到的啟示是,在異質(zhì)文化相遇時,“毛姆對中國的關(guān)照,用的是兩種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靈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實而客觀的邏輯,后者反映的是聯(lián)想與主觀的法則。”[5]因此,雖然毛姆極力用“感官的眼睛”來“注視”中國,但是毛姆在書寫時,勢必受到“心靈的眼睛”的影響,毛姆筆下的中國與中國人形象其實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異,甚至誤讀。
三、毛姆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
1.中國人的形象變化
小說《人生的枷鎖》創(chuàng)作于1915年,毛姆還未開始中國之行,此時毛姆筆下的中國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與虛構(gòu),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葛桂錄先生就對此做了精彩的總結(jié):“回顧西方人表述中國的歷史,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早期多為贊美、傾慕的態(tài)度,18世紀中后期隨著歐哲啟蒙運動的高潮,西方現(xiàn)代性的確立,西方世界的中國形象發(fā)生了根本改變。……十九世紀中期,西方的中國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現(xiàn)為兩個層面的混合存在。中國既是‘黃’的代表,一種讓人鄙夷、唾棄,反證西方優(yōu)越性的異己存在;又是‘禍’的代表,一種壓迫、威脅西方秩序,使人恐懼的客觀存在”。[6]《人生的枷鎖》里的中國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經(jīng)歷了這樣一個由好到壞的轉(zhuǎn)變過程。起初,雖然宋先生長著一副異于西方人的形象“黃黃的臉”。但是在他身邊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總是笑瞇瞇的,為人和善,舉止優(yōu)雅”。[7]94東西方文明在沒有冒犯對方利益的情況下,安然相處。但是,當宋先生和法國小姐凱西莉的戀情曝光后,這群西方人震驚了,在房東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會這么糟嘛,黃皮膚、塌鼻梁、一對小小的豬眼睛,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癥結(jié)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讓人惡心。”[7]130此時,西方人就帶著種族優(yōu)越感來看待中國人,因為他們覺得東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們的利益,威脅到了他們高貴的西方血統(tǒng)的單純性,使他們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寧。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這個時期,毛姆就是以“心靈的眼睛”來注視“中國人”。在小說的結(jié)尾,宋、西二人的戀情并未以分手結(jié)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這說明了毛姆雖然受西方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但是他對中國人的看法也還是持保留態(tài)度,這也是他對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種新的嘗試。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國游歷了四個月后,毛姆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面紗》和游記《在中國的屏風上》。此時,正處于一戰(zhàn)前后時期,中國社會正經(jīng)歷著劇烈的變革,而資本主義工業(yè)革命對西方社會的消極影響也日益顯露。早年的學(xué)醫(yī)生涯,使毛姆能夠冷靜客觀地體察中國,對現(xiàn)實中國的書寫也還是比較客觀真實的。在《面紗》里,毛姆就借凱蒂之口,表明了他對中國的認知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以前,凱蒂聽到別人講起中國人時,總是說他們腐敗、骯臟,壞到難以形容的地步,現(xiàn)在凱蒂覺得以前聽到的話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頓的話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凱蒂從這兒窺探到一個色彩豐富、含義深刻的世界,這是他以前做夢都沒有想到的。”[8]在《在中國屏風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畫了貪婪的老派官員、新式的學(xué)者和舊派的文人,還以濃墨重彩刻畫了中國普通勞苦大眾的形象。在《馱獸》里,對于中國苦力的描寫“不論心跳有多快,瘡疤有多么疼,也不論是大雨瓢潑還是驕陽似火,他們都在永遠地走著,從早到晚,一年到頭,從孩童走到垂暮。你會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頭,干癟的皮膚垂了下來,他們枯瘦的臉上布滿皺紋,像猿猴一樣,而稀疏的頭發(fā)早已斑白;他們挑著重擔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進墳?zāi)共拍苄菹ⅰ!保?]50再如《江中號子》里關(guān)于纖夫的描寫:“那些纖夫拼盡全力,好像著魔一樣,深深地彎著腰,有時氣力用至極限,他們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獸。”[9]90這些文字都飽含了毛姆對中國勞苦大眾吃苦耐勞精神的欽佩和深切的同情。“在中國馱負重擔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9]50“他們的勞苦讓你心中覺得沉重,你充滿憐憫之情卻又愛莫能助。”“他們的行動全都像快馬奔馳,沒有什么力量能使他們止步,這不是很可悲嗎!他們終身承受役使卻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輩子困頓疲勞卻不知道自己的歸宿,這能不悲哀嗎?”[9]50-51“這聲音幾乎不是人發(fā)出的,那是靈魂在無邊苦海中有節(jié)奏的呼號,它的最后一個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實在是太艱難、太殘酷了,這是他們最后的絕望的抗議。這就是江中號子。”[9]91但是無論怎樣,毛姆依舊是以“他者”的眼光來“注視”中國,他身上所浸潤的西方文化傳統(tǒng)對中國形象的界定,以及作為“異質(zhì)文化”的中國文化,毛姆在書寫中國時對有些中國文化還是產(chǎn)生了不正確的理解。毛姆同情中國的“苦力”,因為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業(yè)社會都是由機器或是由牲畜來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夠理解從事這種體力活的艱辛。但是毛姆并不能夠真正理解當時中國下層民眾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嘆苦力勞動的艱辛時,還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僅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條褲子,而如果這套衣服開始穿的時候還是整潔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補的時候,他卻從不考慮找塊顏色相同的布料。”[9]49當時的中國各地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底層人民長期過著貧困的生活。他們?nèi)找箘谧鳎€是吃不飽,穿不暖,甚至衣不蔽體,遇到災(zāi)荒年,賣兒鬻女是常事。這樣又如何還有閑錢去買相同顏色的合適的布料來給破衣服打補丁呢?毛姆只是“眼觀”中國苦力的艱辛勞作,并未與之進行更進一步的言語溝通。也因為中國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語堂先生把“忍耐”歸為中國人“三大惡劣而重要的德行”[10]39之一。并且認為“忍耐的特性為民族謀適合環(huán)境之結(jié)果,那里人口稠密,經(jīng)濟壓迫使人民無盤旋之余地。”[10]40處于“異質(zhì)”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無法理解中國人的“隱忍”。毛姆雖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護,寄養(yǎng)在伯父家,但依舊是衣食無憂,所以他根據(jù)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當然地認為那些苦力穿著五顏六色補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審美的情趣。
2.鴉片的書寫
鴉片是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重要的歷史文化現(xiàn)象,對于近代中國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鴉片吸食的泛濫造成了近代國民的孱弱和病態(tài),構(gòu)成了近代中國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親身游歷過中國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對中國民眾吸食鴉片的記錄和書寫。《面紗》里,“抽大煙,但是有節(jié)制,抽得不兇”[11]171的神秘優(yōu)雅的滿洲格格,甚至毛姆還借韋丁頓之口說出了鴉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從鴉片里尋求這個道,有的人從上帝那里尋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11]174在《鴉片煙館》里,毛姆把中國的“鴉片休閑文化”刻畫得淋漓盡致,“他領(lǐng)我進入一間干凈明亮的房間,它被分成許多小的隔間,墊高的地板上面鋪著干凈的地毯,形成一個簡便的鋪位。其中一個鋪位上有一位年長的紳士,頭發(fā)灰白,手十分秀氣;他在安靜地讀著報紙,長長的煙槍放在一邊。另一個鋪上躺著兩個苦力,他們把煙槍放在中間輪流享受。他們都是年輕人,顯得精神飽滿;他們對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個還請我抽上一口。在第三個鋪位上,四個男子正盤坐在棋盤四周下棋。不遠處有個男子在逗弄一個嬰兒……”[9]35毛姆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樣,舒適而溫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歡的小酒館,每天晚上,勞累了一天的人們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時光。”[9]35-36毛姆認為,他曾經(jīng)在小說中讀到過的關(guān)于中國人吸食大煙的情景:“……房間低矮又污濁……一個留著長辮的中國人踱著步,冷漠而陰郁,在破舊的床鋪上,躺著幾個大煙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們中不時有人發(fā)出癲狂的胡言亂語。還有個頗具戲劇性的場面,某個可憐的家伙付不起錢以滿足他的煙癮,就向惡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緩解自己極度的痛苦。”[9]35簡直是太離奇了。“虛構(gòu)總是比事實更離奇。”[9]36中國民眾吸食鴉片,在毛姆筆下變異為了一種高雅的“鴉片休閑文化”。而當時在英國國內(nèi),大部分作家都把鴉片看作是能給英國帶來經(jīng)濟價值的貿(mào)易,把鴉片給中國人帶來的危害當作是對中國人的懲罰。由于這種文化的“異質(zhì)性”,也由于旅行時間的倉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國民眾吸食鴉片的眾生相,自然也是發(fā)生了“變異”。中國當時的文人也紛紛在作品里對鴉片的危害進行了揭露和批判。1895年到1911年,中國近代小說中出現(xiàn)了鴉片書寫的高潮。傳教士傅蘭雅在1895年公開舉辦了抨擊“三弊”———鴉片、時文、纏足的新小說的競賽。在160多篇的“時新小說”中,屬于小說創(chuàng)作體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鴉片書寫,并且大都以鴉片批判作為小說的主題。在《澹軒閑話》里,作者詹萬云就在序中抨擊了鴉片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危害:“間嘗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國困民貧之故,實由鴉片之害遍于天下而無藥以救之……”[12]格致散人《達觀道人閑游記》也提到“……寫來貧士凄涼,半是芙蓉有癖……”[13]小說《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鴉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態(tài):“任你是拔山舉鼎的英雄,銅澆鐵鑄的羅漢,只要煙癮已發(fā),頓時骨軟筋酥,連一些氣力都沒有。所以吃煙的,一個個扛肩縮腮,面黃肌瘦,三分像個人,七分倒像個鬼。把錦繡似的山河,都被這煙氣熏得天昏地黑,日暗無光,簡直成了一個煙鬼世界了!”[14]
3.中國文化的誤讀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對中國人形象的誤讀和鴉片書寫的偏差,對于中國的文化毛姆也是“霧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論斷。比如,在《哲學(xué)家》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學(xué)說牢牢地控制著中國人的思想,這是因為它解釋和表達了中國人的思想,而沒有其他的思想體系能夠做到這一點。”[9]107這說明了毛姆對中國文化的理解還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已不再是純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匯合而成的文化形態(tài)。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國人民的游戲姿態(tài),而孔教則為工作姿態(tài)。”[10]99“佛教在中國可說控制了大部分民間的思想。”[10]86“中國近世,佛教似較道教更為發(fā)達,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觀’倘有一所,則佛教的‘廟’當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10]105毛姆深受叔本華悲觀主義思想影響,所以毛姆對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較熟悉的,他也讀過莊子的一些書,對道家文化還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毛姆對中國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會有“大殿中做出各種手勢的奇奇怪怪的菩薩”[9]159的感慨。在佛教寺廟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異的姿勢,這稱為“結(jié)手印”,又叫“印契”。所謂手印,是指佛、菩薩空手時的手勢,是其公式化的造型。連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態(tài)以及所持物品,總稱為“印相”。各種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這是識別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據(jù)。最常見的手印有說法印,即以拇指與中指(或食指、無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這一手印象征佛說法之意,所以稱為說法印。另外常見的還有禪定印、降魔印、與愿印、施無畏印。以上五種手印,合稱為釋迦五印。另外,在《天壇》里毛姆也為西方讀者刻畫了中國的圣殿天壇,“它向著蒼天而立。三層圓形的漢白玉露臺,一層高于一層,四道大理石階梯,分列于東西南北四方。這象征著天壇及四個基本方位。天壇被一個大花園圍繞,花園又被一道高墻環(huán)繞。冬至標志著天時的周而復(fù)始。年復(fù)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會來到這里,莊重地祭拜皇族先祖。”[9]17雖然毛姆對天壇的外觀進行了詳實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對中國禮制文化的陌生,這里就存在著典型的誤讀。天壇始建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兩朝皇帝舉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筆下的“三層圓形的漢白玉露臺”應(yīng)該就是圜丘壇。圜丘壇是天壇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臺。古代中國是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大國,農(nóng)業(yè)與天時季節(jié)有著密切關(guān)系。中國皇帝又稱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風調(diào)雨順,國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壇舉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禮及重大國事的“告祀”禮儀也在圜丘舉行。天壇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來牌位移至太廟。太廟是明清兩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廟。是根據(jù)中國古代“敬天法祖”的禮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東巡沈陽(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廟祭祖。所以毛姆這里把天壇當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顯然是不正確的。
四、結(jié)語
毛姆極力用客觀真實的筆調(diào)來描摹他親身體察到的中國,在跨文明交流中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較文學(xué)變異學(xué)視野的觀照下,毛姆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書寫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見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觀念、思維方式以及社會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國游歷時間不長,對于中國的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馬觀花。因此,對于中國和中國人形象的書寫,也只能是“霧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誤讀是不可避免的。盡管毛姆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是他透過自身的文化模子進行重組變異而成,但是這種變異的看法還是非常有意義的。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們可以重新認識自己。這種“異”的對照,將有助于我們對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變。此外,也有助于我們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因為20世紀西方的中國形象,最終不是“反映”中國的現(xiàn)實,而是“表現(xiàn)”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與恐懼[15]。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對于“他者”所建構(gòu)的“變異”的中國文化形象,我們也應(yīng)該持寬容的態(tài)度,對于異質(zhì)文化我們應(yīng)該盡力去吸收和理解,這樣將有利于東西方文明的對話和人類文明的共同進步。而且對于促進各國人民之間的互相了解,構(gòu)建和諧世界也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參考文獻
[1]石黎華.東方主義的傲慢與偏見———論毛姆作品中的中國[J].東京文學(xué),2009(5):8.
[2]曹順慶.比較文學(xué)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讓-馬克•莫哈.試論文學(xué)形象學(xué)的研究史及方法論[C]//孟華.比較文學(xué)形象學(xué).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1.
[4]Jean-Mariecarré.Avant-proposàlaliteraturecompareé[M].Paris:PUF,1951:6.
[5]吳曉東.毛姆與中國之間的屏風[J].新聞周刊,2007(2):86.
[6]葛桂錄.跨文化語境中的中外文學(xué)關(guān)系研究[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8:93.
[7]威廉•薩姆賽特•毛姆.人生的枷鎖[M].張柏然,張增健,倪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8]威廉•薩姆賽特•毛姆.彩色的面紗[M].劉憲之,譯.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95.
[9]威廉•薩姆賽特•毛姆.在中國屏風上[M].唐建清,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
[10]林語堂.吾國吾民[M].黃嘉德,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
[11]威廉•薩姆賽特•毛姆.面紗[M].阮景林,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12.
[12]周欣平.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一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
[13]周欣平.清末時新小說集(第二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02.
[14]彭養(yǎng)鷗.黑籍冤魂[C]//楊愛群,王維良.中國近代珍稀本小說(第17冊).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98.
[15]葛桂錄.比較文學(xué)之路:交流視野與闡釋方法[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4:214.
作者:鄭素華 單位:福州大學(xué)海洋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