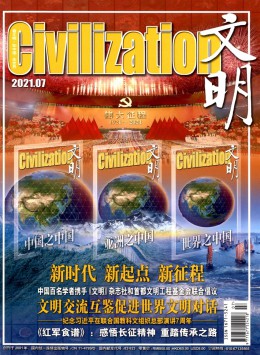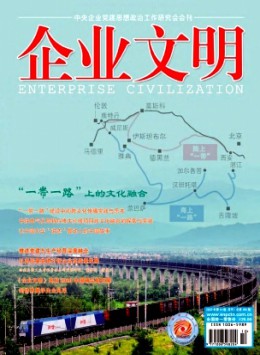跨文明研究比較文學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跨文明研究比較文學論文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可比性的兩種聲音正如上文所提及的,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并不是一種新出現的理論,但是這一研究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中還沒有真正得到學理上的梳理與完善。如由法國比較文學學者馬利•伽列(又譯卡雷)給出的法國學派比較有代表性和最明確具有權威性的定義:“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個分支:它研究在拜倫與普希金、歌德與卡萊爾、瓦爾特、司各特與維尼之間,在屬于一種以上文學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構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間所曾存在過的跨國度的精神交往與實際聯系。”以及由美國學者亨利•雷馬克提出的美國學派最有概括性的定義“: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可以說,上述兩派關于比較文學的界定均不涉及跨越異質文明的內涵,法國學派關照的視野往往局限在歐洲各國之間,而美國學派雖進一步拓展了學科的范圍,但其視域的投射依舊集中在西方文明的領域內。因此,這樣一種傳統的西方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其研究的觸角僅僅局限在自身單一的文明圈內,并沒有討論跨文明的可比性問題。不過,隨著東方比較文學的繁榮發展,以及比較文學學科自身的演進,逐漸有西方學者意識到長期被西方文明掩蓋或忽視的其他文明的存在,開始在比較文學領域內思考關于跨越異質文明的問題。而縱觀中外不同學者對于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思考,我們會發現有兩種聲音較為突出并富有代表性。
(一)不具備可比性
20世紀90年代,著名的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出版了他頗具時代意義的專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極具爭議的“文明沖突論”。他在此書中曾這樣討論到:“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主導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國際議題中的關鍵爭論問題包含文明之間的差異。權力正在從長期以來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轉移。全球政治已變成了多極的和多文明的。”“在這個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顯然,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間必然存在著異質性,并且由于這樣一種差異帶來了彼此的矛盾與沖突。而正是他忽略了文明間可能存在共通性的看法暗含了比較文學學界內關于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一種代表觀點———不具備可比性。關于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不可比”的看法,最具代表性的可以說是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學者韋斯坦因所提出的觀點:“我不否認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卻對把文學現象的平行研究擴大到兩個不同的文明之間仍然遲疑不決。因為在我看來,只有在一個單一的文明范圍內,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發現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維系傳統的共同因素。”可以看出,韋斯坦因開始意識到跨文明研究的問題,這對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更新和發展無疑是有推進意義的,但是他的“遲疑不決”也表達出他對于跨文明研究的態度是消極的。他認為,比較文學一旦越出單一文明的范圍,開始涉及異質文明之間的比較將不再具有合理性。因此,不同文明雖然客觀存在,但是跨文明研究卻沒有必要開展,比較文學學科的實踐應該堅守西方單一文明圈的陣地。又如雷馬克在《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能》一文中探討平行研究可行性時所提到的作家和作品名單“:赫爾德和狄德羅、諾瓦利斯和夏多勃里昂、繆塞和海涅、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白鯨》和《浮士德》、霍桑的《羅吉•摩爾文的葬儀》和特羅斯德-烏爾肖夫的《猶太山毛櫸》、哈代和霍普特曼、阿座靈和法郎士、巴洛耶和斯丹達爾、漢姆遜和基奧諾、托馬斯•曼和紀德”。可以說,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以雷馬克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學者關于跨文明研究不具備可比性的看法。
(二)“求同”的可比性
相異于上述跨文明研究不具備可比性的看法,比較文學學界內還有另一派的聲音認為跨文明研究是可行的,其可比性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礎上。美國比較文學學者韋勒克曾明確提出,比較文學應該“研究各國文學及其共同傾向、研究整個西方傳統———在我看來總是包括斯拉夫傳統———同最終比較研究包括遠東文學在內的一切文學之間,會產生相互影響。”而且,他在思考比較文學與總體文學之間的關系時也曾提到,“無論全球文學史這個概念會碰到什么困難,重要的是把文學看做一個整體,并且不考慮各民族語言上的差別,去探索文學的發生和發展。”可以說,韋勒克是認同跨文明研究的,他認為比較文學應該將研究的視野拓展到異質文明之間,在尋求不同文明的共性方面積極探索。而法國學者艾金伯勒也曾提出與韋勒克相似的看法,認為不同文明之間具有“求同”的可比性。他“批評了比較文學中的狹隘地方主義、沙文主義、政治干擾等等傾向,進而提出‘比較文學是人文主義’的觀點,主張把各民族文學看做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看做相互依賴的整體,以世界文學的總體觀點看待各民族文學及其相互關系;把比較文學看做能促進人們的相互理解、有利于人類團結進步的事業”。正如錢鐘書在《談藝錄》的序言中所說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雖然時代與民族等文化特性會深深地印染在文學作品中,但是超出這一切因素之外的人類情思卻有著驚人的相同之處。不管時代與民族等文化上存在怎樣的歧異,人類的最崇高的情思是能夠互相了解的。人性共通的前提使得異質文明之間存在了溝通的可能性,跨文明研究也因此確立了一種“求同”的可比性。
二、求同存異:變異學視域下
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縱觀上文所提及的關于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兩派看法,雖然體現了不同學者對于該問題所進行的有益探索,但是這兩種觀點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局限性。如果我們在變異學的視域下考察這一問題,會發現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必然存在,并且其可比性的內涵又比單純的“求同”要更為豐富。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不具備可比性”的觀點其局限性所在。認為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不可比的相關論述中,韋斯坦因的看法較有影響力和代表性。不可否認,他的觀點具有一定的時代合理性。因為當時的比較文學領域,由于以雷馬克為代表的美國學派大力倡導被法國學派拋棄的平行研究,使得比較文學的邊界無限擴大。所以,韋斯坦因在權衡了法國學派過于狹窄的研究視野以及美國學派過于寬泛的研究范疇之后,采取了這樣一種“中間道路”。但是,這個所謂的“中間道路”卻把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整體置于“窮途末路”之中。因為反對跨異質文明的比較文學研究,所以自誕生之日起就天然具備了跨文明性質的中國比較文學,其合法性幾乎被完全顛覆。我們熟悉的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錢鐘書的《管錐篇》等等一大批優秀的比較文學研究都將失去學理上的合法性,成為一種“亂比”之作。顯然,這是一種無稽之談,中國比較文學百年的探索不可能是一種“天真的游戲”。相反,它是在大量實踐與探索中積聚起深厚學理基礎,具備成熟合理因素和凸顯自身特色的一門大學問。因此,我們要推翻以韋斯坦因為代表的片面觀點,明確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具備可比性,并且這種可比性是建立在充分的學理基礎與實踐經驗之上的。然而,揭示了“不具備可比性”這一派觀點的片面性后,并不代表將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單純“求同”之上的第二派觀點就完全正確。
一味地“求同”,忽視異質文明之間的差異,將會引發嚴重的話語失衡問題。作為跨文明研究思潮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薩義德在其著作《東方學》中有過這樣的認識:“東方學的策略積久成習地依賴于這一富于彈性的位置的優越,它將西方人置于與東方所可能發生的關系的整體系列之中,使其永遠不會失去相對優勢的地位。”也就是說,長期以來,我們“對東方事物富于想象的審察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識———這一意識的核心從未遭到過挑戰,從這一核心中浮現出一個東方的世界———的基礎上”。因此,透過薩義德的分析,我們應該意識到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世界上所認為的東方,更多是西方話語霸權下被扭曲了的東方,而其真正的面貌并沒有得到應有的揭示。表面上西方文明看到了東方文明等非西方文明的存在,但這樣一種在話語覆蓋下的關注,恰恰是更深層次的忽略。而且,這樣一種“走樣”的東方文明,不僅不能彰顯東方文明真正獨特的價值所在,甚至連東方對自身文明的感知和把握也因此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法國著名學者弗朗索瓦•于連就曾對此說過:“我們正處在一個西方概念模式標準化的時代。這使得中國人無法讀懂中國文化,日本人無法讀懂日本文化,因為一切都被重新結構了。中國古代思想正在逐漸變成各種西方概念,其實中國思想有它自身的邏輯……如果忽略了這些,中國思想的精華就丟掉了。”循著這樣一種思路,于連曾明確對錢鐘書、劉若愚等學者的研究提出批駁。他認為,錢鐘書在進行跨文明研究時那種“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求同”方法是值得反思的,“他的比較方法是一種近似法,一種不斷接近的方法:一句話的意思和另一句話的意思最終是相同的。我覺得這種比較收效不大。”也就是說,于連覺得錢鐘書只看到不同文明之間的相同之處,沒有將更有價值的異質性凸現出來,這樣的跨文明研究并不全面。而對于劉若愚在中西比較詩學方面的研究,于連批駁的力度更大。“我認為他的出發點錯了,他試圖用一種典型的西方模式考察中國詩學,這種方法得出的結果沒有什么價值。”他甚至說,劉若愚套用西方詩學模子的“求同”研究,只能使中國詩學“貧乏化”。因此,從于連的上述觀點我們可以看出,他所理解的跨文明研究,除了要追求一種“求同”的意義以外,還應該彰顯出不同文明異質性的價值所在。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意識到不同文明之間的異質性,只是一味用西方單一話語體系覆蓋其他文明的話語體系,那么非西方文明將會“被死亡”,從而進入一種“假死”狀態。譬如,當我們完全套用西方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來考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中國傳統文人的創作風格時,其結論往往是標簽化的、平面化的。因為浪漫主義的李白不是真正的李白,現實主義的杜甫不完全就是杜甫,白居易的風格也不能單以浪漫主義或現實主義就能簡單概括。若我們的研究僅僅停留在這樣的層面,無疑是對中國文學的曲解,使其原有的旺盛生命力逐漸喪失。又譬如中國文論的失語癥問題,傳統的中國文論并沒有西方現代文學理論意義上的“批評”概念,如果依舊保持現代以來全盤西化的文論話語,將使得中國批評史,變成“中國批評死”。所以,跨文明研究不僅要關注“同”的一面,還要明確關注不同文明之間的“異”。其實,有許多異質文明間的要素也體現出承認異質性是必然的選擇。如中國文明體系中的中醫、圍棋等等,這些與其他文明體系存在絕對異質關系的文明成分,是無法用他者的文明體系去透析的,一味“求同”的思路只會使研究走進“死胡同”,使得真正的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無法全面開展。至此,我們不妨引入中國學者葉維廉在思考中國比較文學實踐時所提出的“模子”理論來總結一下上述的分析。
他認為“,要尋求‘共相’,我們必須放棄死守一個‘模子’的固執,我們必須要從兩個‘模子’同時進行,而且必須尋根探固,必須從其本身的文化立場去看,然后加以比較和對比,始可得到兩者的面貌。”也就是說,在進行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的時候,對于不同文明間的差異是不能忽略的,異質性是比較的價值得以彰顯的關鍵。所以,唯有確立了“求同存異”的比較思維,跨文明研究才能在一種正常的文化生態中全面而深入地開展。但是,僅僅確立了這樣一種“求同存異”的可比性還不夠,我們還需要借助中國學者曹順慶所提出的變異學理論來進一步分析其可比性的深層內涵。所謂比較文學變異學,其定義是“:比較文學變異學將比較文學的跨越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研究支點,它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現象交流的變異狀態,以及研究沒有事實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在同一個范疇上存在的文學表達上的異質性和變異性,從而探究文學現象差異與變異的內在規律性所在。”所以,將變異學理論引入比較文學學科體系中將使其原有的可比性進一步豐富為:同源性、類同性、變異性、異質性與互補性。從上述分析中我們清楚地了解到,跨文明研究的關鍵在于跨越異質文明,也就是說“異質性”是其核心概念。而由于這樣一種異質性,文明交匯之處就必然會有“變異性”因素存在。變異的終點又往往指向文明間的相反相成,體現出一種“互補性”。因此,變異學理論一方面將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由單一文明拓展到了跨越異質文明的層面。另一方面,這一理論也使原有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單純“求同”的局面被打破“,求異”的部分得到彰顯。而這兩方面的理論創新都為跨文明研究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撐,進一步確立起跨文明研究“求同存異”可比性的合法性。另外,正是在變異學理論的指導下,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求同存異”的可比性體現出了更為深層次的內涵:“求同”不是“同化”,“存異”不是“孤立”。所謂“‘求同’不是‘同化’”是指:我們承認影響趨同的同時,不排斥這一過程中的變異因素;在揭示共同詩心、文心的時候,不同于原有研究中的話語覆蓋,而是保留異質特征。而“‘存異’不是‘孤立’”則是指:彰顯異質性不是一味地追求差異,更不是一通亂比;相反,異質性可比的內涵是建立在原有同源性和類同性的基礎之上,這不僅可以更好地進行文明間的平等對話,而且文明間的對話預示著新因素的產生。
三、結語
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體現了學科跨越性的最新內涵。可以說,它突破了傳統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西方中心主義”。而且,當跨文明研究真正將研究視野拓展到不同文明之間時,其“去中心化”的意義就更為凸顯了。不同文明之間的正常對話,將不再形成新的中心,而是真正將比較文學引向世界文學的終極追求。另外,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在變異學視域下提出“求同存異”的可比性,將比較文學的學科價值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平。比較文學的學科視野本來就比許多學科要寬廣,其跨越性所帶來的學術價值不是其他學科能隨意替代的。而跨文明研究既關注不同文明的共性,又凸顯不同文明的異質性,還體現出文明對話下的變異性,可謂全方位將“比較”的價值呈現了出來,在新的內涵指導下更加顯現出學科獨有的魅力。最后,正是因為“求同存異”可比性的彰顯,使得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最終呈現出了一種“和而不同”的追求,正所謂“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百川合流的結果不是一潭死水,而是充滿生機的海洋。跨文明研究走向“和而不同”,于世界的層面是多元文明的互識、互補和互動。互識在于,平等對話下的不同文明能夠真實地認知對方,不再出現像傳統“西方中心主義”框架下被扭曲的東方文明等現象。而互補則是指,異質文明通過對話,將對方有益之處吸納進自身的文明體系中,實現一種新的發展。也因此,互動就指向不同文明由于異質性的碰撞,生發出新的變異因素,體現出一種創造性。而跨文明研究其“和而不同”的追求于中國而言,除了上述“互識、互補和互動”的意義以外,還有一層更為迫切的意義,那就是中國文化的“走出去”問題。因為,跨文明研究其話語平等認可的意義使得這種文化的外散,一方面體現了“送出去”的民族自信,另一方面又彰顯了對于他者的尊重。所以,跨文明研究很好地昭示出,中國文化的復興和“走出去”不是新的霸權意識覺醒,我們將自身的文化“送出去”是為了在人類文明進程中貢獻應有的價值,真正實現“和而不同”的追求。
作者:曾詣 曹順慶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