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dāng)代比較文學(xué)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當(dāng)代比較文學(xué)論文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lái)靈感和參考,敬請(qǐng)閱讀。

一、“文學(xué)”之維和“語(yǔ)言”一樣
“文學(xué)”/“文學(xué)性”也是韋斯坦因確立比較文學(xué)研究對(duì)象的重要一環(huán)。在完成了什么算是“比較的”文學(xué)的回答之后,對(duì)于什么樣的文學(xué)可以進(jìn)入比較文學(xué)研究,韋斯坦因也作了深入細(xì)致的探討。在韋斯坦因看來(lái),“文學(xué)”/“文學(xué)性”也和“語(yǔ)言”一樣,有著豐饒的立體構(gòu)成和深邃的理論價(jià)值,它既指文學(xué)和比較文學(xué)研究的對(duì)象范疇,也指研究對(duì)象所具有的美學(xué)價(jià)值和學(xué)術(shù)價(jià)值。在其重要理論著作《比較文學(xué)與文學(xué)理論》中,韋斯坦因?qū)Α拔膶W(xué)”作了言簡(jiǎn)意賅的探討:在英語(yǔ)和法語(yǔ)中,“文學(xué)”一詞原來(lái)是“學(xué)問”(learning)或者“博學(xué)”(erudition)的意思。例如,伏爾泰談到夏普蘭時(shí),就說他有“淵博的學(xué)問”(une littérature immense)。直到18 世紀(jì),研究的焦點(diǎn)才從主觀的人轉(zhuǎn)到了客觀的作品上。但即便在這一較晚的發(fā)展階段,文學(xué)所包括的還是所有出版物,不管它們?cè)趯?shí)質(zhì)上是什么類型的作品(在英、法、德諸語(yǔ)言中,“文學(xué)”常常用來(lái)指那些非文學(xué)的作品)。
在 18 世紀(jì),非功利的作品常常被稱為“詩(shī)”(poesy)或詩(shī)類。直到 19 世紀(jì),才將實(shí)用性作品與非實(shí)用性作品作了系統(tǒng)的區(qū)分。只有當(dāng)這種區(qū)分獲得了普遍性的時(shí)候,“文學(xué)”才獲得其真正的含義。正如西蒙•格諾在《七星百科辭典》的序言中告訴我們的,“在搞技術(shù)的人們逐漸把他們的專業(yè)提到科學(xué)這一高度”的時(shí)代,“文學(xué)是與功能性地使用書面語(yǔ)言完全不同的寫作方式”。但我們不應(yīng)忘記,直到世紀(jì)之交,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還多次授予那些杰出的自然科學(xué)家和哲學(xué)家呢。由上,韋斯坦因總結(jié),文學(xué)可分為“科學(xué)的”和“美學(xué)的”兩部分(里面也有像科幻小說這種屬于兩可的情況),但是,因?yàn)橛兄T如歷史小說、散文、日記、自傳等雜交類型的出現(xiàn),這一領(lǐng)域往往不能劃出準(zhǔn)確的界限。他說:“從理論上講,如果希望充分考慮文學(xué)研究,就應(yīng)當(dāng)限制研究非文學(xué)現(xiàn)象,而集中探討文學(xué)現(xiàn)象。但在實(shí)際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把研究的范圍擴(kuò)展到文學(xué)界限之外。”
韋斯坦因主張一種“收”與“放”兩相結(jié)合的“文學(xué)”研究。所謂“收”,是指他對(duì)“文學(xué)”范圍的考察和規(guī)范,他所強(qiáng)調(diào)的立基于文學(xué)基礎(chǔ)上的比較研究,他的“文學(xué)”研究所指,乃為出色的語(yǔ)言藝術(shù)品和文學(xué)性相結(jié)合的作品,而非一切文字作品,韋斯坦因和韋勒克一樣,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藝術(shù)品的美學(xué)價(jià)值,他說:“文學(xué)研究如果降格成為材料的堆砌,它就喪失了尊嚴(yán),因?yàn)椴辉倥袛嗥涿缹W(xué)價(jià)值了。”所以他認(rèn)為,研究莎士比亞戲劇的歷史淵源,應(yīng)該是英國(guó)文學(xué)史家和批評(píng)家關(guān)注的題目;研究《高老頭》中金錢的作用,則是傳奇學(xué)者和經(jīng)濟(jì)史學(xué)家感興趣的題目。此外,他將尼采定位為“詩(shī)人”,認(rèn)為他可以進(jìn)入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這不僅因?yàn)樗麑戇^詩(shī),他的散文風(fēng)格具有文學(xué)性,而且也因?yàn)樗麑?duì)許多德國(guó)和非德國(guó)作家產(chǎn)生過影響。”但是叔本華、博格森、康德、休謨就戴不上“詩(shī)人”的帽子,因?yàn)樗麄兊闹鲗I(yè)性太強(qiáng)。所謂“放”,是指韋斯坦因?yàn)轭愇膶W(xué)和雜交文學(xué)類型留下足夠的比較研究空間,他注重具有文學(xué)性的作品。韋斯坦因在梳理比較文學(xué)史時(shí),曾對(duì)布呂納季耶有所贊譽(yù):“從今天的觀點(diǎn)看,布呂納季耶的思想比他那位杰出的同伴的思想更具現(xiàn)代意識(shí),巴爾登斯伯格后來(lái)曾在許多關(guān)鍵問題上采取了他的見解。布呂納季耶說:‘什么叫“文學(xué)的”? 不就是有意識(shí)地創(chuàng)造那種獨(dú)特的東西嗎? 或者說得確切些,不就是作者,不論他是知名的還是無(wú)名的,本身力圖按照自己的意愿實(shí)現(xiàn)的某種雅和美的觀念嗎?’”迪尼對(duì)布呂納季耶這一進(jìn)步的觀念同樣贊賞,迪尼還進(jìn)一步評(píng)論道:“布呂納季耶主張文學(xué)批評(píng)不但必須集中于文學(xué)作品的本身,而且須將文學(xué)研究與傳記、心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以及其他學(xué)科分開。這種見解為 20 世紀(jì)的批評(píng)藝術(shù)做了不少鋪路的工作。”"7#(331)從中可見,迪尼和韋斯坦因?qū)Α拔膶W(xué)”的規(guī)定既涉及了文學(xué)種類問題,同時(shí)也將作品的藝術(shù)價(jià)值、藝術(shù)形式等涉及美學(xué)的問題考慮進(jìn)去。韋斯坦因既為“文學(xué)”劃分了疆界,但是又不將其框定死,因?yàn)樗庾R(shí)到文學(xué)研究中“充滿了活躍離題的地帶”。與此同時(shí),他仍是反對(duì)立足狹隘的文學(xué)范圍內(nèi)的比較研究。韋斯坦因有針對(duì)性地否定了同行學(xué)者將比較文學(xué)嚴(yán)格地限定在文學(xué)的范圍內(nèi)的做法,“我的同道中有些純粹派,希望把比較文學(xué)嚴(yán)格地限制在文學(xué)的范圍內(nèi)。
對(duì)他們來(lái)說,如果我答應(yīng)永遠(yuǎn)把文學(xué)作為起點(diǎn)和目標(biāo),也許可以消除疑慮。弗利德里希建議我們把學(xué)術(shù)研究和教學(xué)分開,以便撫慰我們語(yǔ)文學(xué)家的良心,但即使如此,我仍然懷疑這種方法是否明智。”這種收放結(jié)合的靈活處理方法,為韋斯坦因的比較文學(xué)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發(fā)展空間。對(duì)于構(gòu)成“文學(xué)”(此處專指比較文學(xué)研究)的內(nèi)核,韋斯坦因劃定了純文學(xué)、美學(xué)、科學(xué)(包括社會(huì)科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的“圓周環(huán)”。他說:“在我看來(lái),在文學(xué)和非美學(xué)的或基本上非美學(xué)的‘人類的表現(xiàn)領(lǐng)域’(例如哲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神學(xué)、歷史編寫學(xué)和純科學(xué)或應(yīng)用科學(xué))之間的研究,答案真不簡(jiǎn)單。”他按照歷時(shí)的順序,論述從法國(guó)學(xué)派肇始的“文學(xué)”在名與實(shí)上發(fā)生的變化和引起的討論。同樣,他劃定圓周而不定死邊界。韋斯坦因認(rèn)為,“索邦的創(chuàng)立者們”最初建立學(xué)科,就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它的某些褊狹,決定它必定會(huì)把自己限制在一種文藝的氛圍之內(nèi),他也指出,法國(guó)人和德國(guó)人在其中不斷作出努力試圖將比較文學(xué)的范圍擴(kuò)展出“純文學(xué)”;然后,二戰(zhàn)之后,布朗(C. S. Brown)開始從事文學(xué)與藝術(shù)的比較研究,他的觀點(diǎn)漸漸成為學(xué)科內(nèi)的潮流和常規(guī);“構(gòu)成比較文學(xué)內(nèi)核的第二個(gè)更大一些的圓周環(huán),是對(duì)文學(xué)和科學(xué)之間關(guān)系的研究。它超出了美學(xué)范疇,因此更有爭(zhēng)議。……從歷史上來(lái)說,社會(huì)科學(xué)與文藝學(xué)的關(guān)系要比自然科學(xué)密切。”從韋斯坦因的論述來(lái)看,他有一種非常明確的傾向,那就是非常青睞文學(xué)與其他藝術(shù)互相闡發(fā):“只要文學(xué)是一種藝術(shù),即它是非功利的積極創(chuàng)造的產(chǎn)物,所以盡管它們的媒材不同,但是它們之間似乎可靠而且很有可能存在的一些共同的因素(反之,它們也為比較提供一個(gè)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這使得文學(xué)與其他繆斯控制的領(lǐng)域有某種自然的親和力。”至于其他學(xué)科范圍的比較,他認(rèn)為既然“文學(xué)”范圍只是相對(duì)固定的,那么只能“討論方法上較為穩(wěn)妥的”影響研究,后來(lái),他修正了這一觀點(diǎn),“(我)拋棄了后浪漫主義時(shí)代的、似乎是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思想,并恢復(fù)了世界文學(xué)的觀點(diǎn)。”所以,他強(qiáng)調(diào)將諸如科幻小說、歌劇、芭蕾舞、漫畫等文學(xué)的混合形式納入比較文學(xué)研究;他尤其關(guān)注純文學(xué)和其他藝術(shù)之間存在的聯(lián)系和互相交融的現(xiàn)象,比如瓦格納的綜合藝術(shù)品,或具有多方面才能、用兩種或多種不同媒介進(jìn)行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家(如米開朗琪羅)。想要指明比較文學(xué)的“比較”需要什么樣的條件,韋斯坦因認(rèn)為,必須首先界定“整個(gè)鏈條上的各個(gè)環(huán)節(jié)”,即民族文學(xué)、比較文學(xué)、世界文學(xué)和總體文學(xué)。韋斯坦因主要考察的是其余三者與比較文學(xué)有所關(guān)聯(lián)之處。
韋斯坦因認(rèn)為,民族文學(xué)是“那些形成比較文學(xué)基礎(chǔ)的基本單元”,它們?cè)谡Z(yǔ)言的區(qū)別上與比較文學(xué)形成了分水嶺;總體文學(xué)和比較文學(xué)之間的區(qū)分是人為的,二者在方法學(xué)上沒有什么意義;世界文學(xué)與比較文學(xué)有關(guān)或重疊的幾層含義有:第一,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學(xué)”,包含著對(duì)各民族文學(xué)的求同存異、相互理解尊重之意,“因?yàn)楦璧聫?qiáng)調(diào)國(guó)際接觸和富有成果的文學(xué)之間關(guān)系,阻止根除民族文學(xué)特色,所以歌德所提出的這個(gè)概念對(duì)我們的學(xué)科是極其有用的。”[5](20)第二,其延伸的含義,“用以指一切時(shí)代和世界各地的杰作”,但是在教學(xué)中一般只是介紹并講解它們,這種實(shí)踐阻礙了比較研究。第三,作為“世界文學(xué)史”的縮略用語(yǔ),必須被理解成世界上所有文學(xué)的歷史,涵義更為繁雜,在某種程度上,已經(jīng)屬于文學(xué)理論研究的范疇。以上術(shù)語(yǔ),涉及包羅諸多相對(duì)流動(dòng)的邊界,需要結(jié)合實(shí)際,決定它們的歸屬。綜上所述,韋斯坦因以 20 世紀(jì)西方語(yǔ)言學(xué)轉(zhuǎn)向時(shí)期的理念反思比較文學(xué)歷史;他通過整理比較文學(xué)史和梳理文學(xué)理論,將語(yǔ)言問題作為區(qū)分文學(xué)研究中的比較方法和比較文學(xué)研究的首要標(biāo)準(zhǔn)提出來(lái);他在 20 世紀(jì)六七十年代,就已經(jīng)敏感地意識(shí)到,和語(yǔ)言密切相關(guān)的翻譯問題將成為比較文學(xué)領(lǐng)域中的重要課題;這些,都是極為難能可貴的。不止于此,因?yàn)閷?duì)藝術(shù)史的稔熟,在將藝術(shù)(主要是造型藝術(shù)和歌劇)與文學(xué)進(jìn)行跨學(xué)科的比較研究時(shí),韋斯坦因的“跨語(yǔ)言”已經(jīng)超越了字面意義上的“語(yǔ)言”,既包含時(shí)間維度,也具有歷史意識(shí),而成為關(guān)乎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關(guān)乎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接受等問題的鏈接點(diǎn),成為理解文學(xué)和藝術(shù)及其關(guān)系的一個(gè)符號(hào),從而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立體交叉地綜合統(tǒng)一起來(lái),把比較文學(xué)研究推入到一個(gè)縱深階段。
二、結(jié)語(yǔ)
總之,“語(yǔ)言”和“文學(xué)”這兩個(gè)術(shù)語(yǔ)是韋斯坦因視為決定學(xué)科獨(dú)立與否的關(guān)鍵性詞匯,“語(yǔ)言”和“文學(xué)”將比較文學(xué)集成為立體渾成的有機(jī)體,既有歷時(shí)的發(fā)展脈絡(luò),也有共時(shí)的彼此觀照,呈現(xiàn)出穩(wěn)定中的變化、變化中的穩(wěn)定色彩。可見,“(跨)語(yǔ)言”和“文學(xué)(性)”的標(biāo)準(zhǔn)之于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的規(guī)定,是韋斯坦因在比較文學(xué)理論建樹上的重要貢獻(xiàn)之一。
作者:李琪 單位:黑龍江大學(xué)文學(xué)院
相關(guān)熱門標(biāo)簽
相關(guān)文章閱讀
- 1當(dāng)代農(nóng)業(yè)論文:當(dāng)代循環(huán)農(nóng)業(yè)建設(shè)策略思索
- 2當(dāng)代動(dòng)態(tài)建筑技術(shù)探析
- 3當(dāng)代文學(xué)傳播研究
- 4職教當(dāng)代技術(shù)應(yīng)用
- 5當(dāng)代山寨文學(xué)影響分析
- 6當(dāng)代會(huì)計(jì)審計(jì)技術(shù)分析
- 7當(dāng)代護(hù)士具備的職業(yè)素養(yǎng)
- 8當(dāng)代建筑進(jìn)展趨向研究
- 9當(dāng)代影視創(chuàng)作思路的啟示
- 10當(dāng)代體育文化認(rèn)知思考
相關(guān)期刊推薦
-

當(dāng)代護(hù)士 · 學(xué)術(shù)版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kù)(CJF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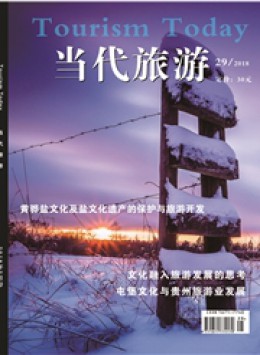
當(dāng)代旅游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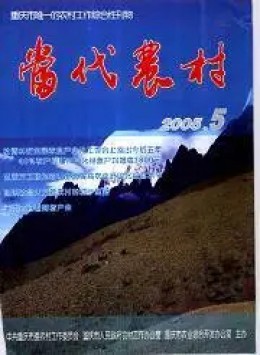
當(dāng)代農(nóng)村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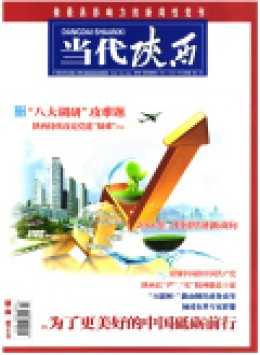
當(dāng)代陜西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當(dāng)代蔬菜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