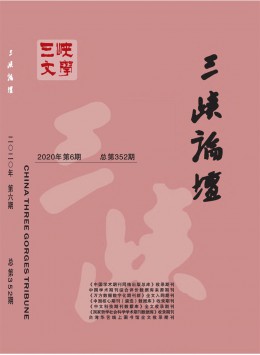屈原的離騷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屈原的離騷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屈原的離騷范文
屈原在《離騷》一開篇就首先追溯了自己的出身--帝高陽之苗裔,也就是說,這位受盡磨難的文化英雄血脈中流淌著神的血液。這里屈原對自己出身的追溯,絕不是為了炫耀,也不是隨便為之,他的這個出身至少有兩層作用:一,恰是這高貴的出身而決定著屈原先天就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精神追求與責任意識;二,這出身是屈原在《離騷》后文遠游面見重華,回到昆侖的依據(jù)。
屈原在一個高貴的日子--庚寅日出生,容貌俊美,自幼勤奮好學,胸懷大志,早年受楚懷王信任,參與法律制定,主張章明法度,改革政治,連齊抗秦。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遭受了張儀賄賂的靳尚鄭袖等人的陷害,屈原被疏遠,遭受迫害,并被流放。但是他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在被流放時候也從未忘了努力,對內(nèi)保持自己的高潔品質(zhì)并努力提升自己: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對外不忘為國培養(yǎng)賢才: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但結(jié)果卻還是靈修還是繼續(xù)聽從眾女的謠諑謂余以善,而終不察夫民心。屈原郁邑侘傺,獨自窮困,卻寧溘死以流亡,不忍為此態(tài)也。為什么呢?他明確交代了原因--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還是追溯到了自己的出身,他認為自己本是鷙鳥,與時俗工巧之流的不同自前世而固然,先天決定的,他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的選擇是追隨前圣的腳步的。
既然在人世中他竭盡全力也無法求得認同,他又曾試圖獨善其身--退將復修吾初服,但反顧游目觀乎四方,最終卻還是逃不掉心頭的堅貞與責任感--雖體解吾猶未變。然后女嬃代表著一些愛他卻不懂他的人,以鯀的例子來勸導責備他的堅守。這神話中的人物鯀倒恰好提醒了他的出身,他開始渡過水湘水南征,對舜陳述自己的忠貞與一腔熱情,希望得到舜的肯定和精神支持。但是文中沒明確說舜怎么回應他,只交待他從此開始了上天入地的神游求索。作為神的后裔的屈原在神界似乎如魚得水:他從蒼梧出發(fā),一路經(jīng)過了了縣圃崦嵫咸池扶桑等神話傳說中的地方,又試圖追求宓妃、有娀氏之女、有虞氏之女等。這游歷似乎使他可以解脫了,終于放手了心里的郁結(jié),回到了自己神界先祖美好光明的精神家園。
接下來靈氛為他吉占,他也決定離開,折瓊枝為羞,精瓊爢為粻,以飛龍為駕,以瑤象飾車,揚云霓,鳴玉鸞,奏九歌,舞韶樂,朝發(fā)天津,夕至西極,他就要回到昆侖山了。可是偏偏在一切順利進行,就要完成的時候,屈原一低頭,忽臨睨夫舊鄉(xiāng),然后立刻,一切的熱鬧、光明、美好就瞬間萎縮不見,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他終究是化不開對那塵世中祖國與國君的摯愛,雖然國無人莫我知、莫足與為美政,他也拗不過自己的心,而終為他們殉情,從彭咸之所居。在中國古代神話里,昆侖山是絕地通天之前的神山,也是中國古代人意識里的宇宙山,而顓頊帝則代表著屈原的人生之源,也代表著絕地通天之前神人和諧共處的社會時期,屈原向重華陳詞和在神游中向昆侖靠近的選擇和西方文學中的重回伊甸園主題不謀而合,體現(xiàn)著人類精神情感的共共通性。但是,屈原卻沒有完成這一回歸,他在即將到達的時候驀然放棄,而毅然決絕地回頭轉(zhuǎn)向了人世。在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中,第一次如此明確地:人戰(zhàn)勝了神!
第2篇:屈原的離騷范文
關(guān)鍵詞:兩漢 屈原作品 文學觀
兩漢文學在其發(fā)展中體現(xiàn)出了由漢初注重情感抒發(fā)到向儒家思想靠攏的總體趨勢。這一趨勢一方面體現(xiàn)在漢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即其創(chuàng)作目的由抒情向“潤色鴻業(yè)”和諷喻當下統(tǒng)治者發(fā)展。將作品中的自我情感壓抑在內(nèi)心深處,以致于在作家作品中很難發(fā)現(xiàn)個人化的東西。另一方面體現(xiàn)在文學批評中,即漢人對文學作品的評價由重視作品盼隋感發(fā)展到把政治功利作為文學評價的第一標準。這兩種趨勢都可以從漢代對屈原作品的接受中得到反映。
從楚文化及屈原作品對漢人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這一角度看,漢初文學作品中的情感與形式都受到楚文化或屈原作品的影響,下面分別論述之。
首先是情感抒發(fā)。漢高祖起于楚地,對楚文化懷有一種獨特的感情,我們可以稱之為鄉(xiāng)土情節(jié),在《漢書》中多有高祖好楚聲的記載,《漢書?禮樂志》:“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不僅用于宗廟的房中樂為楚聲,高祖自己也創(chuàng)作詩歌,而這些詩歌最大的特點也是帶有楚地色彩。《史記?高祖本紀》云:“置酒沛官,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fā)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nèi)兮歸故鄉(xiāng),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shù)行下。”高祖以布衣起家,提三尺劍而為天下主,在《大風歌》中我們讀出了劉邦統(tǒng)一天下后的自得和酬躇滿志,但在其中也隱含著他統(tǒng)一天下后內(nèi)心孤獨與無所歸依的惆悵。其情感與屈原作品中個性化的情感抒發(fā)是相一致的,一為情感的真摯表達,一為情感的悲涼格調(diào)。漢武帝《秋風辭》在情感色彩上與《大風歌》相似。帝王如此。文士何論焉?漢初文士賈誼受屈原影響最為明顯,《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m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司馬遷將二人合傳就是看到二人在命運遭際與情感歷程上有相似之處。司馬遷說:“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指出了《離騷》產(chǎn)生的原因,并暗示了作品的格調(diào)。賈生又何嘗不是?在《吊屈原賦中》借對屈原的憫悼一方面陳說仕途之淹蹇,一方面抒發(fā)備受壓抑之郁悶,無論是情感抒發(fā)的方式還是所抒情感的內(nèi)容都與《離騷》若合符契。此外,其后所作《鵬鳥賦》也是情感上的自傷自悼。漢初文人作品較少,文學史上能留下幾筆的僅有幾篇,就著幾篇來看,此時文學創(chuàng)作尚處于以情感為主要傾向的階段。盡管此時文學創(chuàng)作尚未進入自覺的時代,文學家創(chuàng)作的目的尚不能以抒情稱之,但在他們的作品中的確大量充斥著情感的內(nèi)容,而且是以悲情、怨情的成分為多,這不能不說是在屈原作品影響下形成的風格。
其次,在作品形式上,無論是詩歌還是賦都帶有明顯的楚地痕跡。劉邦的《大風歌》以及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中很多詩作具有明顯的楚地特色,劉邦《大風歌》“兮”字的運用明顯是受楚地詩歌的影響。蕭滌非在《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中對《安世房中歌》與《九歌》中的篇章做了對比,認為:“三言旬,《詩經(jīng)》中以有之,然無全篇,未成一體。楚辭則無獨立之三言句,惟具有退化為三言句之可能性,故今世之三言詩人樂者,不得不首推《安世房中歌》,而其淵源則《山鬼》、《國殤》是也。”而騷體賦在形式上也是楚辭影響下的產(chǎn)物,最明顯的就是其句式結(jié)構(gòu)上對屈原作品的模仿。
以上從漢初文學創(chuàng)作這一角度對漢初的文學觀做了闡釋,可以看出漢初文學很明顯受到了楚文化及屈原作品的影響。下面就漢人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中體現(xiàn)出的文學觀作一論述。此一時期漢人評價”楚辭”的依據(jù)多為儒家經(jīng)典,這發(fā)生在漢代把儒學作為官方學術(shù)之后,漢代評價”楚辭”者有以下幾家:劉安、司馬遷、揚雄、班固、王逸等。最早對屈原及其作品作出評價的應該是淮南王劉安,其文為司馬遷《史記》所采用:
《國風》好色而不,《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可見是司馬遷采納了劉安的觀點。劉安、司馬遷一方面承認了《離騷》的創(chuàng)作意圖,即因“怨生”而作,這是看到了《離騷》主情的一面,但同時又將《離騷》與《詩經(jīng)》之風、雅相比,謂其可以兼?zhèn)滹L、雅的特點,劉安、司馬遷的評價標準明顯帶有價值評判的傾向,即以儒家經(jīng)典作為衡量《離騷》的標準,以是否符合儒家詩教作為文學作品評價的依據(jù),當然這種評價標準還處于起步階段,評價者在注意到經(jīng)典標準的同時并沒有忽視情感在文學作品形成中的作用。“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就是很好的注腳。最早把功利化思想引入文學評價中的是孔子,孔子在解說《詩經(jīng)》時常常從政治、倫理的角度進行闡釋,如:“詩,一言以蔽之,日思無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將其政治倫理功能提升到首位,而漢代伴隨統(tǒng)一國家實力的增強,政治、文化大一統(tǒng)局面的形成。儒學獨尊地位確立,孔子這種文學觀自然會被漢人移植到其文學批評當中。
如果說劉安、司馬遷等人對《離騷》的評價中尚且保留著注重情感的因素,那么其后揚雄、班固、王逸等人的評價則進一步脫離情感的因素,將文學功利化傾向推進了一步。揚雄對屈原及其作品評價如下:
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
揚雄對屈原的態(tài)度是“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同樣是注意到了屈原作品中的情感因素。但揚雄又對屈原提出了批評。對屈原投江持否定態(tài)度,認為臣子應該做到被重用就施展自己的才能,不被重用就作龍蛇蟄伏。頗有“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意味。上述文字中還體現(xiàn)出揚雄對屈原作品的傾慕之情,“怪屈原文過相如”,“賦莫深于《離騷》”,但將屈原、司馬相如的二人作品作比較時卻對屈原作品頗有微詞:“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云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云,長卿亮不可及也。’”“過以浮”當指其作品中充滿幻想色彩的神話傳說,即班固《離騷贊序》中所說:“多稱昆侖、冥閽、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jīng)義所載。”背離了儒家經(jīng)典質(zhì)實的特點,因此,在揚雄看來,屈原在作品情感 上沒有遵守“遇不遇命也”的儒家人生理想,在風格上違背了經(jīng)典質(zhì)實的特點。
揚雄對屈原人格及作品的態(tài)度在班固《離騷序》中得到發(fā)展和系統(tǒng)闡述。班固《離騷序》中說:“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guān)雎》哀周道而不傷。……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shù)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絮狂狷景行之士。多稱昆侖、冥閽、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jīng)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情感已成為一種多余而被排除在外,甚至處于被抨擊的地位,班固認為屈原不應該對君主有“不敬”的言論,同時符合儒家經(jīng)典成為了作品價值評價的唯一標準。班固認為《史記》對屈原的評價過高,其理由是《離騷》的內(nèi)容不合經(jīng)典,但在這段文字中班固又對屈原的文采加以肯定:“宏辭雅麗,為辭賦宗”這只是從文體自身特點出發(fā)作出的評價,而不涉及作品的內(nèi)容。從中我們可以窺見班固的文學觀念:文學的功利性并不排斥文學的形式化。這就為兩漢時期大賦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很好的解釋。兩漢大賦,其特點是“鋪采摘文,體貌寫志”一方面注重文采的鋪張,一方面注重文學的政教功能,即“寫志”,這里的“志”與“詩言志”中的“志”所指應該是相同的,并不是指個人化的情感,而是指“關(guān)乎國家及公共生活不可缺少的道德準則。”班固《離騷序》中所體現(xiàn)的文學觀可以視為兩漢文學觀之典型。
王逸對屈原的評價集中體現(xiàn)在《楚辭章句》中,在《離騷敘》中,他一反揚雄、班固等人對屈原的批評態(tài)度,肯定了屈原的人格:“且人臣之意,以忠正為高,以伏節(jié)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zhì),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近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城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并對屈原作品作出了很高評價:“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辭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竊其華藻。”在文學形式上充分肯定了屈原作品對后世的影響。王逸與班固對屈原及其作品持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只不過班固是從對君主的“敬”出發(fā),屈原對懷王可以說“不敬”,故班固對他持否定態(tài)度;而王逸則是從對君主的“忠”出發(fā),屈原對懷王可謂忠心。故王逸稱贊他。二人出發(fā)點均為政治,只不過角度有所不同。這種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正好說明二人在文學政治功利性觀念上的相同。從對屈原及其作品的功利化解讀方式上來看,二人沒有本質(zhì)差別。因此,班固和王逸在對待《離騷》等作品上主要是以政治功利目的為主,對文學形式也加以肯定,但文學的抒情功能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湮沒于政治功利之中。
以上從屈原作品接受的視角,針對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評論中所體現(xiàn)的文學觀進行了論述。需要注意的是。兩漢文學觀念是一個漸變的過程:經(jīng)歷了由漢初的重情到重言志,再到漢末向情感回歸的發(fā)展歷程。
參考文獻:
[1][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2][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
[3]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5][南朝粱]蕭統(tǒng)編,[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
[6][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第3篇:屈原的離騷范文
關(guān)鍵詞: 揚琴;情感表達 ;《離騷》;二度創(chuàng)作
前言
《離騷》是我國春秋戰(zhàn)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的代表詩作,是屈原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是中國古代最為宏偉的抒情詩篇,全詩372句,2400余字[1]。詩文以熾烈的情感抒發(fā)理想,以堅定的意志抨擊黑暗現(xiàn)實,表達詩人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人格的信念,展現(xiàn)詩人不與邪惡勢力同流合污的斗爭精神和至死不渝的愛國熱情,具有深刻現(xiàn)實性的積極浪漫主義精神,閃耀著理想主義的光輝異彩,極富藝術(shù)魅力。《離騷》是中國文學的奇珍,也是世界文學的瑰寶,具有極高的藝術(shù)價值,它為中國民族傳統(tǒng)文化留下了一個深深的烙印,已成為冠絕千古的名篇,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催人奮發(fā)進取的名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被世人做為勵志名言傳頌至今。
以屈原的人生經(jīng)歷作為藍本的藝術(shù)作品在文學藝術(shù)、影視戲曲、音樂美術(shù)等方面有不少作品。在民族器樂揚琴方面,也有王沂甫先生的《汨羅江上》、項祖華先生的《屈原祭江》、汪志平先生的《汨羅江隨想曲》》以及黃河先生的《離騷》等創(chuàng)作佳作。這些揚琴作品各具特色,在旋律的調(diào)式調(diào)性、和聲織體、技巧技法等方面,充分運用和發(fā)揮了揚琴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展示了藝術(shù)家對屈原及其詩作的思索和審美詮釋。在表達情感的揚琴曲《離騷》的樂曲演繹過程中,演奏者必須深入細致的分析《離騷》的意境和作曲家的樂境,理解把握作品的情感脈絡,結(jié)合高超的演奏技巧,對作品進行二度創(chuàng)作,完美地詮釋詩境樂韻,更好地實現(xiàn)用音樂感受和傳承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目的。
一、作品的意境和樂境
屈原(約前340――約前277)名平,字原,是楚國的同姓貴族。年輕時受到楚懷王的高度信任,官為左徒,據(jù)推算,他當時僅二十多歲,可謂少年得志。后有上官大夫在懷王面前進讒,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職后,轉(zhuǎn)任三閭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大約在懷王二十五年左右,屈原一度被流放到漢北一帶,這是他第一次被放逐。懷王30年,秦人誘騙懷王會于武關(guān)。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帶,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時屈原眼看自己的一度興旺的國家已經(jīng)無望,也曾認真地考慮過出走他國,但最終還是不能離開故土,于悲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羅江,以身殉國。
《離騷》是屈原對自己生活經(jīng)歷的記實,表達屈原了對于過去和未來的思考。從作品的文學角度分析,可以把《離騷》分成前后兩大部分。前半篇側(cè)重于對以往經(jīng)歷的回顧,多描述現(xiàn)實中與政治對立方激烈的矛盾沖突情況;后半篇則主要通過幻想方式,詩人駕飛龍,乘瑤車,揚云霓,鳴玉鸞,自由翱游在一片廣大而明麗的天空中,著重表現(xiàn)對未來道路的探索。作品的波瀾壯闊,氣象萬千,反映了作者所經(jīng)歷的復雜的斗爭生活和堅貞熾熱的愛國之心,是屈原用血淚凝成的生命挽歌。
揚琴曲《離騷》,是我國著名揚琴演奏家、教育家、中央音樂學院黃河教授,滿懷對屈原的敬仰而創(chuàng)作的一首結(jié)構(gòu)新穎、風格獨特的揚琴佳作。作品以屈原《離騷》的意境為藍本,用揚琴的音樂語言詮釋著屈原精神。它借鑒了中國傳統(tǒng)戲曲的音調(diào),應用揚琴演奏的諸多表現(xiàn)技法,把人們帶到“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遠古場景中。音樂主題緊扣人物形象,用揚琴獨特的音色講述著《離騷》的故事,感受屈原的民族氣節(jié)。樂曲中宏壯的樂段強調(diào)著屈原執(zhí)著不屈的政治理想和信念;緩慢流暢而優(yōu)美的旋律展示屈原憂國憂民的愛國之心;跌宕起伏的音調(diào),正如屈原坎坷的一生;現(xiàn)實與虛幻交替的力度,舒緩與急促的節(jié)奏,是對屈原不愿隨世俗而墮落、堅持自我理念的精神寫照。當曲終音散時,留給人們的是無盡的緬懷、思索和感悟。黃河教授運用揚琴的音樂語匯將文學作品《離騷》的意境,做異曲同工的演奏陳述。作品的音樂表現(xiàn)技法多樣化,把握住了屈原的“情”魂精髓,緊扣屈原精神的神韻;音樂織體內(nèi)涵深厚,引人入勝,曲調(diào)布局蕩氣回腸,扣人心弦,塑造了一個栩栩如生的愛國英雄屈原的形象,是一首極富藝術(shù)感染力的揚琴佳作。
二、作品的二度創(chuàng)作
音樂表演自從與音樂創(chuàng)作相分離,獲得它的獨立品格以來,一直被人們稱為二度創(chuàng)作。顧名思義,它是在一度創(chuàng)作的基礎(chǔ)上進行的,必須把一度創(chuàng)作作為出發(fā)點和規(guī)結(jié)點。所謂出發(fā)點是指:音樂表演必須對一度創(chuàng)作的成果――以樂譜為存在形式的音樂作品,繼續(xù)認真的研讀和準確的解釋,并以此作為二度創(chuàng)作的依據(jù)。所謂歸結(jié)點則是指:音樂表演的最終結(jié)果,體現(xiàn)為對音樂作品的正確傳達和再現(xiàn)。[2]記在譜面上的音符,僅僅是作者在一度創(chuàng)作時的樂思陳述,而演奏者經(jīng)過活的演奏,對作品進行二度創(chuàng)作后,才能使作品的應用感染力有進一步的升華,甚至會產(chǎn)生原作者意料不但的演奏效果,這正是古代樂人所說的死譜活奏。[3]在二度創(chuàng)作中,轉(zhuǎn)化樂譜的視覺感受到音樂的聽覺感受中來,把潛在的作品意境變成真實可感的外在表現(xiàn),實現(xiàn)對音樂作品內(nèi)涵的揭示和美的展現(xiàn),是賦予音樂作品以生命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行為。因此,如果只是單純的按照樂譜原原本本的進行演奏,只能是完成了作品的一度創(chuàng)作,作品的表現(xiàn)僅只是一大堆演奏技法的堆砌,音樂也只能顯現(xiàn)出一種膚淺的無病之狀,散在無神。在教學中我們經(jīng)常會碰到學生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常被喻為是“念經(jīng)”似的演繹:學生用技巧完成了演奏曲目所組成的基本框架結(jié)構(gòu),而忽略了在表演語境中對音樂本身的理解對音樂的體驗,蒼白空洞,缺乏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其實一切演奏技法都是服務于音樂表演的工具,演奏是否成功取決于演奏者對作品的理解與感悟是否到位,只有 “重技重藝”,體現(xiàn)作品二度創(chuàng)作的“重藝”過程,并將二者充分地結(jié)合起來展現(xiàn)音樂的內(nèi)容,實現(xiàn)音樂表演的“意深技全”,才能達到音樂表演的真正目的。
1.作品“演繹前”的二度創(chuàng)作
對于作品“演繹前”的二度創(chuàng)作,要避免單純的 “炫技”,而藝術(shù)性地表達《離騷》的“樂韻”,就必須重視音樂在音符以外的各種信息,充分做好演奏前的“案頭工作”,盡可能深刻、準確地理解和剖析處理作品。對此我以為在學習《離騷》的過程中,要在演繹前做好以下三個方面的準備工作。
(1)視譜體驗
音樂是聲音的藝術(shù),存在于作品中的音高節(jié)奏、樂句樂段、調(diào)式調(diào)性、聲部織體、曲式結(jié)構(gòu)、表情術(shù)語、力度術(shù)語、速度術(shù)語等諸多音樂符號的信息匯集于作品的一度創(chuàng)作中,要將作品實現(xiàn)以聲音音響的傳達顯現(xiàn),一定得先通過視覺從樂譜中獲得音樂的結(jié)構(gòu)信息,因此要建立一個主觀上的認知――視譜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通過有表情的視唱方式獲取樂譜樂中句樂段的音高、節(jié)奏、樂感(音樂的三大要素)等信息,體驗段落之間的起承轉(zhuǎn)合的呼應關(guān)系,由此構(gòu)建一個全曲的整體的內(nèi)心聽覺和知覺系統(tǒng),以理性分析和感性體驗活動來感知和表達音樂效果,為樂曲的演奏演奏奠定良好的開端。“一首樂曲的正確演繹,來源于正確的理解,而這又得完全依靠細致的正確視譜”。因此,對樂譜進行深入細致的了解,通過視譜熟悉并把握音樂的全貌,是準確詮釋音樂的前提。
(2)內(nèi)涵體驗
通過視譜的認知過程對的音樂分析,并不意味著音樂的理解就此結(jié)束,而應隨著演奏的展開進一步的滲透到音樂的內(nèi)涵中去。本世紀偉大的大提琴家卡薩爾斯要求演奏者:“不要機械地照搬和理解樂譜上的術(shù)語,因為樂譜是無法記錄下作曲家無限的精神和感情的。演奏工作者的價值在于最大限度地再現(xiàn)作曲家的精神。”[4]中國古典音樂文獻中也有許多論述音樂表演的篇章,都強調(diào)了音樂藝術(shù)應該具有深邃的精神內(nèi)涵,演奏不光要有音樂結(jié)構(gòu)上的詮釋,更應強調(diào)在樂曲之外的更廣闊的社會和人文的背景,從中去挖掘?qū)σ魳返睦斫猓愿玫谋磉_音樂,所謂 “功夫在詩外”就是這個道理。旅英鋼琴家傅聰在談到自己的演奏時,曾意味深長地說:“我得益于中國古典的文學、詩、詞。”可見,多方的積累才能更好得表現(xiàn)音樂。因此,對于有著“有據(jù)可查”的《離騷》的音樂作品的表述,絕不能是完成好譜面上的各種術(shù)語要求的簡單演奏。而應是在演繹樂曲前通過查閱文學、電影、戲劇、美術(shù)等作品資料,或是通過傳統(tǒng)民俗中跟紀念屈原有關(guān)的 “端午節(jié)” 劃龍船、吃粽子、掛艾葉等的習俗活動,了解屈原的人物背景、政治背景,及作曲家在音樂作品的各個段落所要表達的風格意圖,來理解體驗作品的音樂內(nèi)涵,這將對我們理解和表現(xiàn)音樂有很大的幫助。用曲作者黃河的話來說:“情動未然,感悟于心”。這個心應該是對作品內(nèi)涵理解的藝術(shù)之心,是情感表達最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本文為全文原貌 未安裝PDF瀏覽器用戶請先下載安裝 原版全文
(3)技巧相長體驗
揚琴獨奏曲《離騷》在技術(shù)和音樂方面都達到了一個高標準高要求的層次。演奏者除了要具備極高的音樂素養(yǎng),還要完善理解作品的能力、表現(xiàn)音樂內(nèi)涵的能力以及技術(shù)與音樂表現(xiàn)相結(jié)合的能力。本樂曲需經(jīng)過較長時間科學的練習,提高完善基本功,對速度、力度、音色表現(xiàn)等方面技術(shù)上的難點要解決攻克,才能使演奏水平提高,使作品的完成達到意深技全的高度。
2.作品 “演繹中”的二度創(chuàng)作
作為二度創(chuàng)作的音樂表演,將演奏前的“案頭工作”挪動到演奏的“現(xiàn)場操作”中來,做到分析作品要深刻,表現(xiàn)作品要傳神,演奏作品要激情。使得“紙上談兵”的音樂構(gòu)想轉(zhuǎn)化成具體的音響效果,表演者在演奏中必須體現(xiàn)出“演繹”的創(chuàng)造力,賦予音樂作品以鮮活的生命力。即在演奏的二度創(chuàng)作中,要求正確地表達情緒,深刻的描寫意境,準確的刻畫形象,并強調(diào)技術(shù)與音樂表現(xiàn)相結(jié)合。
揚琴獨奏曲《離騷》由五個部分組成,現(xiàn)就演繹中的作品進行二度創(chuàng)作的探解(樂譜引自《揚琴曲選》[5]中央音樂學院黃河編著。由于篇幅有限,只選用相關(guān)典型意義的譜例為例)。
(1)引子部分:樂曲一開始采用極強的輪音和反向和音進行的戲曲音調(diào)旋律,結(jié)合由上到下的八度分解,營造出一種動蕩不安的環(huán)境感,發(fā)音時兩臂用力氣沉丹田,每一擊都要使力度和彈性恰到好處,要有震攝人心的“亮相”氣勢,把音樂場景推出來(曲例1)。
隨著主題旋律用長輪音的線性表現(xiàn)手法的弱起輕出,又馬上漸強進入到一個由高到底的倍低音雙音演奏的弱音,像是吹起了斗爭的號角, 感受詩人發(fā)出的“路漫漫其修遠兮”的感嘆,散板結(jié)構(gòu)似故事開始了慢慢地講述…樂曲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強烈的戲劇性,音樂對比樂句構(gòu)成了激烈的矛盾沖突,因此,引子段的力度強弱對比和速度快慢對比是演奏關(guān)鍵,注意腕指結(jié)合的發(fā)力點,強奏音色要集中、響亮,但要亮而不燥;弱奏的琶音樂句的演奏似若有所思般地一點一點地由弱漸進到強奏,再次弱致無聲。在強弱的進行中,要運用好丹田氣息配合樂句的起音落音的呼吸,表現(xiàn)好音樂的內(nèi)涵。
(2)慢板部分:緩慢的速度,頓挫的節(jié)奏,高大的屈原形象展現(xiàn)出來,感受到他突出的外部形象特征:“高于冠之及及兮,長余佩之陸離。”隨即壓弦和空靈的泛音,飽含憂憤和痛苦不解的情緒。(曲例2)
樸素的旋律,如訴如語,由單音的輪奏發(fā)展為雙音,音樂變得厚重濃烈起來,密集的輪音隨后又迂回地漸漸消退,單雙輪音要根據(jù)意境采用無頭無尾和有頭有尾即輕起輕收或強起強收的方式,像在述說屈原憂國憂民的長吁短嘆的心聲。演奏的情緒應深沉而略帶憂憤,要進入到屈原憂國憂民的精神境界中去。演奏時要用“腹式呼吸”,配合好演奏情緒。在散板的稍自由段部分,三連音與延長音的樂匯結(jié)構(gòu)做不斷自我變化反復時,演奏時內(nèi)心要激動,力度要保持住,表現(xiàn)出屈原不屈不饒的人物性格和高尚氣質(zhì)。調(diào)性轉(zhuǎn)至F調(diào)時,音樂變得緊張起來,氣氛逐漸悲壯。通過大小臂及腕指的發(fā)力感受并訴說受出屈原受讒落敗的痛苦和悲懣之情。轉(zhuǎn)入D調(diào)后,旋律重復著G調(diào)主題的音調(diào),情緒又從F調(diào)的陰影中走了出來,右手的伴奏織體由原來的和聲型變化成分解和弦型,使得主題再現(xiàn)不光是調(diào)性的改變,更是在情緒上推進了音樂結(jié)構(gòu)的發(fā)展,但演奏并不夸張明朗,而是在“回憶地”標題上做文章,氣口也在弱拍位置上進行轉(zhuǎn)換,整體音量要控制住,為進入快板部分做好養(yǎng)精蓄銳的鋪墊。
(3)快板部分:旋律的戲曲音調(diào)連貫而流暢的上下穿行,配以左手的切分節(jié)奏以及音域上的大幅度跳動,突出了力量感,給人以斗志昂揚的感受。低音區(qū)的八度音程的重復出現(xiàn),猶如屈原孜孜探索的腳步在奔走穿梭。從D調(diào)上升轉(zhuǎn)為G大調(diào)音樂情緒的遞進,達到了揚琴演奏的最佳高音區(qū),表現(xiàn)了屈原對真理的堅定的信念和執(zhí)著追求。是對《離騷》后半篇詩人駕飛龍,乘瑤車,揚云霓,鳴玉鸞,自由翱游在一片廣大而明麗的天空中的意境描寫,當調(diào)式再返回到D調(diào)時,音符更加稠密,快速的十六分音符,加上右手中低音區(qū)的推進,使音樂愈顯得激昂,尤其是升四級的巧妙運用,增強了音樂戲劇化的色彩,將音樂氣氛推向,揚琴的音樂表現(xiàn)力和音樂感染力在此處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曲例3)。
快板段落充分展現(xiàn)了屈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意境,是全曲畫龍點睛的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演奏時各段的變化重音及節(jié)奏速度一定要奏得干凈有力,要用上腕臂結(jié)合的方法,手臂不能僵硬影響到發(fā)揮。樂段內(nèi)涵有張有弛,情緒變化有聲有色。
(4)急板部分:八度三連音與重音的強奏,動作和氣息的配合要統(tǒng)一,每小節(jié)要屏住呼吸在小節(jié)線上換好氣,要奏得干凈有力,進而漸快由低沉轉(zhuǎn)向高亢,完全地放開的力度似訴說屈原對政治發(fā)出的最后的吶喊,當音樂逐漸在低音區(qū)趨于平靜,似江水悲憤無奈的嗚咽,山川依在,逝者已去(曲例4)。
此段要緊緊圍繞屈原投江的悲壯氣氛做好速度力度、快慢強弱的對比,演奏者的表情亦要投入到對屈原的情感當中去,內(nèi)心悲痛凄悵。
(5)尾聲部分:表現(xiàn)人物形象的主題旋律再次緩緩的呈現(xiàn),但已是對逝者吟唱的緬懷挽歌,轉(zhuǎn)入A調(diào)的調(diào)性旋律讓人再次重溫屈原精神的內(nèi)涵,最后以輕柔空靈的泛音來結(jié)束全曲,表達了人們對屈原的深深懷念和對未來的無限遐思……這一段是慢板主題的變化再現(xiàn),演奏時要沉穩(wěn)內(nèi)斂,力度上保持弱奏,琶音的運用突出思念緬懷的樂段意境,樂曲要結(jié)束在沉思冥想中(曲例5)。
結(jié)語
《離騷》這部文學作品作為優(yōu)秀的中國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被后人重視和傳承,至今仍然顯現(xiàn)出強大的藝術(shù)生命力。揚琴曲《離騷》用民族音樂的表現(xiàn)方式表達了對屈原精神的詮釋,為傳承民族傳統(tǒng)文化譜寫了新的樂章。以文學作品《離騷》背景下的意境,對作品進行二度創(chuàng)作,結(jié)合高超的演奏技巧,三足鼎立支撐出一個完美的藝術(shù)作品,實現(xiàn)意深技全的琴詠,用揚琴講述屈原的故事,具有非常現(xiàn)實的社會意義。
參考文獻:
[1]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M].復旦大學出版
社,1996年第一版
[2]張前. 《音樂二度創(chuàng)作的美學思考張前音樂文集》[M].
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7年
[3]鄭寶恒編著《揚琴演奏藝術(shù)》[J].中國物資出版社,
1995年
[4](波)約•霍夫曼.《論鋼琴演奏》[J].人民音樂出版
社,P36
[5]黃河編著.《揚琴曲選》[J].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3
第4篇:屈原的離騷范文
翟璇 湖北體育職業(yè)學院
摘要:屈原的作品較多的運用了比德理論,《離騷》繼承了比德的傳統(tǒng),集香草、美人、瓊佩、鳳凰等多種意象組合成一個渾然
整體,以香草自比也用來喻臣喻君,以女性形象喻君,以瓊佩章現(xiàn)性情,用鳳凰自比以及預示美好的未來。自屈原之后,比德理論在
大量文學作品以及繪畫等藝術(shù)作品中運用,成為中國文人重要的審美理想。
關(guān)鍵詞:比德;《離騷》;香草;美人;瓊佩;鳳凰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對自然美的欣賞中,往往將自然物的屬性
比擬人的品格,將自然物的屬性與人的精神情操聯(lián)系起來,由此
形成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為發(fā)端的比德理論。屈原的作品,
在自然物比擬人物品質(zhì)的審美觀中,繼承并發(fā)展了《詩經(jīng)》比興
的傳統(tǒng),進行比德,其文言微而義遠。
一、以香草比德
屈原在《離騷》中選取了一系列香草比德,《離騷》中提到
的香草主要有江離、芷、蘭、木蘭、宿莽、椒、菌桂、蕙、 茝、
荃、留夷、揭車、杜蘅、芳芷、薜荔、胡繩等,分別在數(shù)十個句
子中出現(xiàn),有的甚至反復使用,通過統(tǒng)計研究,這些香草可分為
如下三種喻指:
第一,“自比”。《離騷》開篇明義“紛吾既有此內(nèi)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于是乎“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其
中“江離”、“芷”、“蘭”,王逸皆注為“香草”,屈原在這
里要表明自己修身清潔,行為端正,清廉仁德。“余既滋蘭之九
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其中
“蘭”、“蕙”、“留夷”、“揭車”、“杜衡”、“芷”,也
是“香草”,這是第二次屈原連比香草,一來,以香草之美表明
自己修身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二來,與世俗截然分別,
表達自己為政的態(tài)度和立場。 屈原抱者忠貞愛國之心, 修身清明,
即使奸臣當?shù)溃骰栌梗耘f種植香草,配飾香草。“攬木根
以結(jié)茞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
即使“謇朝誶而夕替”也要“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茞”
“攬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對君王的一片忠正之心不
會改變。“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蘇糞壤以充祎
兮,謂申椒其不芳”中,“艾”與“蘭”、“糞”與“椒”,是
香草與污穢的對比,君子與小人的對比,是屈原與世俗眾奸佞的
對比,是屈原一顆清凈之心與世道昏暗腐敗的對比,屈原佩飾香
草,不與眾小人同流合污。此外,“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
宿莽”中“木蘭”、“宿莽”雖不是香草,但木蘭具有去皮不死,
宿莽具有遇冬不枯的品質(zhì),這種植物作為屈原的寫照再合適不過
了,雖有讒人引誘自己,但受自己天性的影響,讒人的奸計終不
可達成。值得注意的是“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此二
句,屈原將荷葉作成自己的衣服穿戴于身,荷之“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蓮而不妖”的特點最恰切的形容了屈原的素質(zhì)。
第二,喻臣和君。“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
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茞”,其中“椒”、“菌桂”、“蕙”、
“ 茞”皆香草,以喻眾賢之士。昔日歷代有作為的圣君,都“雜
用圣賢,以致于治,非獨索蕙茞,任一人也。” ①整篇《離騷》
中,喻君的香草只有一句“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
“荃,香草,以諭君也。人君被服香草,故以香草為喻。惡數(shù)指
斥尊者,故變言荃也。” ②荃這個香草在這里用來指君王,君王
以香草為衣裳為佩飾,所以用香草來比喻君王。
另外,《離騷》中也提到惡草,有如下三句,“ 薋菉葹以盈
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
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 薋”、“ 菉”、“ 葹”三
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于側(cè)。
二、以女性比德
第一,以“美人”喻君,在《離騷》中的運用廣泛而深刻。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楚辭章句》說: “美
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遲暮”是說美
人會把他遺忘,美人在這里就是指楚懷王。屈原求美人,盼美人,
愛美人,但也怨美人,內(nèi)心對美人具有一種矛盾復雜的心情。
第二,以“靈修”喻君。在《離騷》當中,屈原以“靈修”、
“靈”謂君王,一共出現(xiàn)四次,“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
故也。”“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shù)化。”“怨靈修之浩
蕩兮,終不察夫民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靈的意思是聰明睿智,修的意思是高遠有遠見,睿智而高遠是君
王的品質(zhì),所以用靈修指君王,是說君王不僅睿智高遠而且也不
斷修養(yǎng)身心。本來“靈修”是妻子對丈夫的美稱,在這里借“靈
修”用作臣對君的美稱。
第三,以“女”喻君和喻臣。一方面,屈原以“女”喻君。
“思九州之博大兮, 豈惟是其有女?” 這里的 “女” 指的是 “君” ,
屈原取來瓊茅,“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后言“欲
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由此看來,屈原并沒有聽占
卜的話,說明向他處“求女”的意見沒有采納,而后屈原投河自
盡也正是因為他不想離開楚國, 因此, 這里的 “女” 指的是 “君” 。
另一方面,以“女”喻臣。《離騷》中有五次“求女”的過程。
第一次“吾令帝閽開關(guān)兮,倚閶闔而望予”這里明為求見“天帝”
而實為求“玉女”,即“求君”,其后四次“求女”過程,皆為
“求臣”。“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一個國家要治理
好,不但要有圣明的君主,更需要賢良之士的輔佐,而如今滿朝
上下“無女”,讓屈原傷心流悌。“吾令豐隆乘云兮,求宓妃之
所在”、“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及少康之未家
兮,留有虞之二姚”,在這里,“宓妃”、“佚女”、“二姚”
皆喻為臣,屈原希望為楚國求得賢明之人與其共同輔佐楚懷王振
興楚國。將男女愛情暗喻君臣契合,用求女表現(xiàn)求君,以女喻君,
是“男女君臣”之喻。此外,“女”也用來喻奸臣,“眾女疾余
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眾女”類比的是朝中的那些阿
諛奉承的小人,而把自己比作溫良的女子,是說自己被周圍的那
些小人污了名節(jié)而被君王放逐。
三、以瓊佩比德
佩玉有比德的意義,自東周以來佩玉之風大盛。 《詩· 秦風· 小
戎》有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孔子曰:“昔者君子比德
于玉。”他教導大家要向玉學習,不斷提升自己的素質(zhì)。屈原引
以自傲的正是“內(nèi)美”,“紛吾既有此內(nèi)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屈原以身佩的玉比德,顯示自己獨特的美質(zhì),本身光亮的玉自然
成為屈原比德的對象。“何瓊佩之偃蹇兮,眾蓑然而敝之,惟此
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
歷茲”。屈原身佩美玉,與眾小人截然分別,良玉正是屈原本身
品質(zhì)的真實寫照。“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廉以為棖”,“為余
駕飛龍兮, 雜瑤象以為車” ,“揚云霓之噸藹兮, 鳴玉鸞之啾啾”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軟而并馳”,屈原“求索”的路途中,
駕駛的是以玉柱為車輪軸的瑤象之車,車上的玉鈴發(fā)出啾啾的鸞
和聲,無處不玉,玉貫穿于整幅圖景之中,玉所擁有的品質(zhì),正
是屈原孜孜以求的品德。
四、以鳳凰比德
鳳凰自古就被看作吉祥之鳥,是和美、和諧與吉祥的象征,
是儒家仁、義、禮、智、信的表現(xiàn)。《離騷》中也提到鳳凰,共
計五次:“駟玉虬以乘翳兮,溘俟風余上征”“吾令鳳鳥飛騰夕,
繼之以日夜”,“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鸞皇為余
先戒兮, 雷師告余以未具” ,“鳳皇翼其承旗兮, 高翱翔之翼翼” 。
由此可見,屈原認為他是正直、忠貞、賢能、美好的化身,是符
合先王之道的臣子,在五句有關(guān)鳳凰的文字中,他用與鳳凰同行
的方式怒斥楚國無道無德的政治環(huán)境。作為文化意象的鳳凰,是
中華民族共同的神祉,同日月齊輝。鳳是楚國的圖騰,鳳為楚人
的祖先,為楚人所尊重所敬仰,是楚族、楚國尊嚴的象征。由此
觀之,屈原筆下的鳳凰是升平氣象的體現(xiàn),是與世俗格格不入,
又象征美好意義的鳥,鳳鳥受詒,鳳鳥承旌表現(xiàn)屈原為楚國美好
明天作出貢獻的全身心的投入,鳳凰也帶有屈原自己的影子。 ③
“比德” 在屈原作品中的運用可謂爐火純青、 出神入化,《桔
頌》幾乎句句是比德,《離騷》中的香草、美人更是深入人心。
佩飾香草、佩玉瓊,目的只有一個,以所佩戴之物之特質(zhì)顯自身
之品格,香草馥郁芳香,美玉高潔脫俗,這種品質(zhì)都是屈原畢生
不懈追求不斷完善不斷擁有的。以身佩之物比德,從屈原開始,
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幾千年的歷史。“比德”的審美觀,既增添了自然
美的活力又豐富了人物精神的內(nèi)涵, 相應的引類譬喻、 托物言志、
感物傷懷等藝術(shù)手法的運用充實了作品的意蘊,幾千年來成為中
國文人重要的審美理想。
參考文獻:
[1]孫元璋.《屈騷藝術(shù)的美學意蘊及其流變》,《煙臺師范學
院學報》1994年第3期.
[2]王逸注,洪興祖.補注:《楚辭章句補注》,吉林人民出版
社2005年7月版.
[3]夏文波.《致用·比德·暢神——隋唐以前山水審美歷史管
窺》,《沙洋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年第4期.
[4]周均平.《“比德”“比情”“暢神”——論漢代自然審美
觀的發(fā)展和突破》,《美學》2003年第十期.
[5]黃震云.《〈離騷〉若干興象解說》,《中國古代、近代文
學研究》1995年第一期.
注釋:
①王逸注,洪興祖.補注:《楚詞章句補注》,吉林人民出版
社2005年7月版,第8頁.
②王逸注,洪興祖.補注:《楚詞章句補注》,吉林人民出版
社2005年7月版,第9頁.
③參見黃震云.《〈離騷〉若干興象解說》,《中國古代、近
代文學研究》1995年第一期.
作者簡介:
翟璇,女,漢族,1986年2月出生,湖北人,畢業(yè)于西北民族
第5篇:屈原的離騷范文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位偉大的詩人。他的詩篇,“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并能”[1],千百年來受到無數(shù)人的景仰與追慕。他以政治家的社會身份行事,卻以文學家的名義成就了不朽。屈騷之所以千古流傳,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作品唱出了詩人靈魂深處的聲音,彰顯了不屈不撓的人格魅力。屈原的作品大多創(chuàng)作于詩人被頃襄王流亡到漢北以后。漢北山川奇麗,有峻峰幽谷之美,但更多的是水氣波光。沅、湘、澧、洞庭、云夢等水曲溝澤星羅棋布。面臨滾滾江水,孔夫子發(fā)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喟嘆。屈子臨水自鑒,自然也著凝思者的嘆息。《離騷》云:“朝搴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湘夫人》云:“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涉江》云:“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抽思》云:“望北山而流涕,臨流水而太息”。在放流的九年時間里,屈原肯定無數(shù)次地舟行水上,行吟江畔,凝目以思:為國家的生死存亡擔憂,為黎民的饑寒溫飽擔憂,還有對自我價值、個人命運的思索。他發(fā)現(xiàn):賢主明君只是理想的神話。自己所處的環(huán)境,君主出爾反爾,利令智昏;群芳隨波逐流,紛紛變節(jié);奸佞沆瀣一氣,蠅營狗茍。“眾人皆醉我獨醒,舉世溷濁我獨清”。四海之內(nèi),沒有賞識自己、理解自己的知音。這種深沉的孤獨感,將屈原推上了顧影自憐的境地。他只有對著水中的倒影,自我欣賞,以此獲得心靈的滿足,達到人格結(jié)構(gòu)的平衡。所以,屈原是東方的納西索斯,他的作品也是自戀者的沉思。學者周憲也指出:“屈原不是神,他的憤世嫉俗不過是基于個人不幸遭遇挫折的必然反應而已,不過是他的自戀傾向的另一種表現(xiàn)而已。”[2]
屈原對中國文人的影響是深遠的。賈誼、陶淵明、李白……皆視屈原為自己的精神避難所。屈原的人格蘊含了中國傳統(tǒng)文人所有的“根源特質(zhì)”,他的人生際遇預示了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歷史命運,他的作品也帶有中國古典文學的普遍特征。“文學與神話一樣,都產(chǎn)生于共同的心理內(nèi)驅(qū)力。這些內(nèi)驅(qū)力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為它們是一切人類發(fā)展過程中所固有的。”[3]
在人的心理結(jié)構(gòu)中,意識處于表層,猶如冰山露出海面之上的那一小部分,可以用語言表達。屈原心理中的確存在自戀傾向,但還尚未達到班固所詆毀的“狂狷之士”的程度。作為一個傳統(tǒng)文人,屈原的感情是內(nèi)斂的。在意識層面,屈原認為他有足夠的自戀資本。
首先是先天因素。《離騷》開篇稱道自己的族系、誕辰、名字,“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帶有明顯的炫耀意味。關(guān)于帝顓頊高陽氏,《大戴禮?五帝德》曾有這樣的描述:“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敬。”[4]可見是一位顯赫、尊嚴的大神。至于屈原的誕辰,蔣南華根據(jù)古代天文學、歷法學的科學推算,認為是寅年寅月寅日,這是一個日月交匯、千載難逢的祥禎之日。而“靈均”,靈,即是神靈的意思,也可謂不同凡響。先天的優(yōu)勢是他的自戀心態(tài)最基本的起點。
其次是外在風采。屈原對自己的外貌也是很自信的。《湘君》云:“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水中倒影,是一位身材頎長的美男子。因此,有時屈原索性以“美人”、“佳人”自謂。如“恐美人之遲暮”(《離騷》),“惟佳人之永都兮”,“惟佳人之獨懷兮”(《悲回風》)。對于自己的美貌,屈原重點突出的是自己的服裝與配飾。《離騷》最為集中。詩中寫道,“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在《涉江》、《招魂》中還有類似的贊美。他對自己的服飾甚至到了癡迷的程度。實際上所有的衣著都著復雜的代碼。“在日常世界中,衣著所起到的正是這樣的作用:它總在設想中看到自己被別人注視。”[5]
另外,屈賦的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詩人絲毫不加掩飾地贊美自己的美德和才能。對于自己的美德,詩中有直接贊頌的,如“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涉江》),有比德之頌揚的,如“秉德無私,參天地兮”(《橘頌》),還有在歷史追憶中以前賢來標榜自己的,如“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涉江》)等等。詩人給后人最深刻的印象也是他高蹈絕塵的德行。司馬遷評其品格,“其志潔,故稱其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6],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于自己的才能,詩中有“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離騷》)的自夸。司馬遷對此也作了“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候”[7]的贊譽。
上述的幾點,都是屈原自身所意識到的與眾不同之處,但在屈原的意識中,尚存在主次先后之分。先天的因素是天賦的內(nèi)在美質(zhì),屈原將它們統(tǒng)稱為“內(nèi)美”。《離騷》中聲稱:“紛吾既有此內(nèi)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楚辭》中的“修”字,大都含有“美”的意義,如“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離騷》)。“重”是“增加”之義。詩人認為,縱使自身的內(nèi)在美質(zhì)眾多,仍需要德行和才能的提升。屈原之所以能得到楚懷王的重用,也不僅僅是祖上的福蔭,而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博聞強識,明于治亂,嫻于辭令”。
在文學傳統(tǒng)里,美貌往往有更深刻的含義。《詩經(jīng)?衛(wèi)風?碩人》是詠莊姜的,據(jù)《左傳?隱公三年》記載莊姜是一位有色有德的女子。《詩經(jīng)?邶風?簡兮》末章又云:“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8]《鄭箋》注:“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9]美貌是賢者的烘托。屈原對此理會甚深。當社會文明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時,服裝便不僅只包含御寒遮羞的原始意蘊,而是一個民族的共同審美心理的表現(xiàn),是一種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屈原愛好楚之華麗的服飾,當有著深層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意義。”[10]他對楚國服飾的贊美,也是其愛國德行的一個表征。古人常有佩劍的嗜好。劍既是一種裝飾,更是一種警示。告誡自己大敵當前,要奮勇殺敵,盡忠報國。關(guān)于詩中的香花芳草,前人早有認識。王逸在《離騷序》中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11]所以,屈原選擇花草作裝飾,是取其馨香以喻己之高潔。屈原對外在風采的展示,目的同樣是突出高潔的德行。在其意識層面,屈原的自戀,最主要的是因為他所擁有的無人能敵的德才。這也符合儒家“太上立德”立人觀的標準。
在人的心理結(jié)構(gòu)中,還包含無意識的部分,它是沒于海水中碩大無比的主體部分。它處于大腦的底層,是一個龐大的領(lǐng)域,占主導地位,起支配作用,能夠影響人的行為。弗洛伊德將人的無意識視為一種本能,并主要是指性本能。
《離騷》虛構(gòu)了三次神游。其目的之一,是“求女”:宓妃、簡狄、二姚等。據(jù)王逸注,這些女性皆為古代的神女圣妃。屈原對她們恭敬神往,沒有實際意義上男歡女愛的褻瀆。其實,“求女”也并非屈原的首創(chuàng),在先秦以至漢代諸子中均不乏其例。《莊子?逍遙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吸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12]誠如黑格爾所言:“如果哲學家運用神話,那大半由于他先有了思想,然后才尋求形象以表達思想。”[13]屈原糅合遠古神話傳說,假借虛構(gòu)的帶有神性因素的形象,也是為了寓托自己主觀的愿望和理想。導致屈原自戀的無意識,并不是性本能而是另有他情。
屈原是楚國的同姓貴族,又具有高潔的道德修養(yǎng)、杰出的政治才能,屬于中國古代的士階層、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他矢志不渝的人生信條,“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是他的人生理想,也是其實現(xiàn)人生價值的有效途徑。從他踏上政治仕途之始,他便時刻不忘臣子的義務,知識分子對社會應盡的職責。周王室東遷以后,“楚在短短一百多年內(nèi),經(jīng)濟得到迅速的發(fā)展,社會出現(xiàn)了飛躍的轉(zhuǎn)化,從而在較短的時間內(nèi)形成了興盛的封建社會。”[14]楚先人的開拓進取,國家的經(jīng)濟實力,使他對政治無限熱忱,甘愿為社稷蒼生效犬馬之勞,對國君盡忠,為楚王排憂解難。在內(nèi)政上,為懷王擬訂憲令,“循繩墨而不頗”(《離騷》),修明法度,以法治國;重視培養(yǎng)和選拔賢能,“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離騷》),表現(xiàn)出政治家的遠見卓識。在外交上,他主張擺脫強秦的,臨危授命,出使齊國,聯(lián)齊抗秦,至死保衛(wèi)楚國。他的政治藍圖是明君賢臣共興楚國,體現(xiàn)了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意識。
但是,在傳統(tǒng)的社會――政治格局中,傳統(tǒng)文人所處的地位相對又是尷尬的:他們是社會理想精神的代表,也是道德良知的體現(xiàn)。然而封建君主掌握了社會的話語權(quán),政治理想的實現(xiàn)卻又必須借助君主的權(quán)勢,這決定了他們在社會中的明顯依附地位。屈原也不例外。他提出了“美政”理想,但也只能感嘆“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離騷》)。懷王聽信讒言,他便被疏遠;頃襄王受到迷惑,便被放逐出郢都:君王的遺棄讓他深感報國無門的焦灼。屈原曾悉心培養(yǎng)人才,但結(jié)果“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離騷》),事過景遷,他們也紛紛變節(jié)與墮落:群芳的凋零讓他感到了無人同行的孤獨。屈原深愛著楚國的百姓。黎民的流離失所,讓他發(fā)出了“哀民生之多艱”(《離騷》)的憂慮。當他憂愁憂思之時,漁父卻好心地“規(guī)勸”他隨波逐流:群眾的疑惑又讓他感到忠貞者的悲涼。他愛國、忠君、育人、恤民,滿腔生命的熱情,換來的是現(xiàn)實殘酷的打擊,無人理解,更無人回報。
“現(xiàn)實生活中的失敗使屈原把對內(nèi)心真實和內(nèi)在神性的頑強執(zhí)著,轉(zhuǎn)化成了表達這種內(nèi)心真實和內(nèi)在神性的創(chuàng)作沖動。”[15]屈原內(nèi)心的焦灼、孤獨、悲涼需要尋找釋放的突破口,于是他實現(xiàn)了由政治家向文學家的轉(zhuǎn)換。他需要知音,需要有人欣賞他的道德與才能,所以才有了詩歌中的自戀。因此,在他的無意識結(jié)構(gòu)中,傳統(tǒng)文人的使命感和責任意識才是屈原自戀的心理內(nèi)驅(qū)力。
屈原的遭遇是大多數(shù)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共同悲劇,作品所反映的自戀傾向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普遍心理特征。理想與現(xiàn)實的差距讓他們對社會、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們尋求依附性地位不可得,無奈地轉(zhuǎn)向自我價值的獨立性追求。他們不愿茍且,不愿同流合污,秉持著寶貴的人格操守,閃耀著道德的璀璨之光,理性的批判之光。他們執(zhí)著追求精神自由的勇氣也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寶貴財富。
參考文獻:
[1]周振甫著《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1986年,第45頁。
[2]周憲《屈原與中國文人的悲劇性》,《文學遺產(chǎn)》,1996年第5期,第34頁。
[3][美]諾曼?N?霍蘭德《神話與心理學》,[美]約翰?維克雷編,潘國慶、楊小洪、方永德等譯《神話與文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105-106頁。
[4]王聘珍撰《大戴禮解詁》,中華書局,2004年,第125頁。
[5][美]宇文所安著《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程章燦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第22頁。
[6][7]司馬遷撰《史記?屈原列傳》,中華書局,1979年,第2482頁。
[8][9]《毛詩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卷四,《十三經(jīng)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94頁。
[10]毛慶《屈原文化心理初探》,《屈原文化研究論文集》,宜昌市炎黃文化研究會編,1997年,第283頁。
[11]洪興祖撰《楚辭補注》,中華書局,2002年,第2-3頁。
[12]《莊子》,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頁。
[13][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商務印書館, 1959年,第86頁。
[14]《楚的神話、歷史、社會性質(zhì)和屈原生平》,楊公驥著《中國文學》第一分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9頁。
第6篇:屈原的離騷范文
關(guān)鍵詞:《詩經(jīng)》;二雅;怨刺詩;屈原;沿革
《詩經(jīng)》和《楚辭》之間有密切關(guān)系,這一點,前人已有許多論述,如劉勰《文心雕能?辨騷》認為,《離騷》有“典誥之體”,“規(guī)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觀茲四事,同與風雅者也。”①《漢書?藝文志》云:“春秋之后,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②明徐師曾云:“按《楚辭》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然江漢之間,皆為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列于《二南》,乃居十五國風之先,是《詩》雖無楚風,而實為《風》首也。”③清人程廷祚認為詩騷在“陳情”、“陳志”和“體物”方面都是相通的。④今人對詩騷關(guān)系的研究更細微和具體。趙逵夫先生認為誦詩的形式在春秋以前就有了,《詩經(jīng)?大雅》的《崧高》、《民》便是明證。但充分發(fā)揮語言本身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因素以盡可能造成詩的形式美,卻是屈原的功勞。⑤李金坤《詩較新論》,楊仲義《詩騷新識》、潘嘯龍《詩騷詩學與藝術(shù)》、葛曉音《四言體的形成及其與辭賦的關(guān)系》等著作和論文從不同角度探討了詩騷體式的特征及其演變和因革關(guān)系。總之,詩對騷有影響這一事實是肯定的。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通變》中所說,“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但風、雅、頌三體對騷的影響到底哪個更大呢?陳師道說:“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后效風。”⑥本文對詩騷文本進行比較分析后認為《詩經(jīng)》二雅怨刺詩對《離騷》影響最大。而“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之說是因為沒有意識到《離騷》中的虛構(gòu)世界和神話傳說已與《詩經(jīng)》中的頌詩有了本質(zhì)的區(qū)別。
一、“二雅”怨刺詩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和屈原生活時代的相似性
《詩經(jīng)》二雅怨刺詩多產(chǎn)生于厲王和幽王時代,這與厲、幽時代時局的動蕩密切相關(guān)。《國語》記載:厲王暴虐,使衛(wèi)巫監(jiān)視謗者,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的高壓弭謗行為激起國人的反抗,最后被流放于彘地。宣王在邵公等大臣的幫助下勵精圖治,出現(xiàn)中興局面,但無法挽救西周社會的衰頹之勢。幽王寵褒姒而導致眾叛親離,在公元前771年,被申侯聯(lián)合犬戎、繒人所殺,西周滅亡。所以說,從厲王到幽王的一百多年中,社會經(jīng)歷了劇烈的變亂,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經(jīng)歷了劇烈的沖擊。時局的動蕩激發(fā)了怨刺詩的大量產(chǎn)生。
四百年后的楚國懷、襄時代與西周末年的厲、幽時代一樣,其政治形勢也是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懷王初年尚能繼承祖業(yè),國勢強盛,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中曾一度形成“縱則秦帝,橫則楚王”的格局,然而由于用人不當,又不能及時改革弊政,很快衰落下去。隨著楚國政治形勢的急劇變革,屈原作為楚國有著強烈的政治抱負和責任心的大臣經(jīng)歷了由最初的“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史記?屈原列傳》)到被楚王疏遠,遭饞放逐的人生遭遇。這種遭遇促使其“發(fā)憤抒情”,在被流放之后創(chuàng)作了《抽思》《思美人》《惜誦》《離騷》等大量充滿怨憤之情的詩歌作品。
西周末年的二雅詩歌除了宣王中興時期的一些頌美之詩外,多為怨刺現(xiàn)實之作,所謂的“變雅”多做于這一時期。與西周末年的二雅詩人多怨誹的抒情基調(diào)一致,屈原作品集中而深刻地表現(xiàn)了詩人“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幽怨之情,這種情感與對楚國的政治現(xiàn)狀、國家命運的憂慮以及對小人當?shù)赖纳鐣F(xiàn)實的憂憤之情交織在一起。相似的政治環(huán)境、身份地位以及人生境遇使相距四百多年的詩人產(chǎn)生了情感共鳴,創(chuàng)作了相似的詩歌作品。
二、“二雅”詩歌主題與屈原作品主題的相似性
1. 怨刺上政
二雅怨刺詩和屈原作品都表現(xiàn)了對君王昏聵,用人不當而造成的社會動蕩、國運衰敗的憂慮與憤慨。如《民勞》是警告同列大臣并以之警戒周厲王的詩。《毛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鄭玄《箋》:“時賦斂重數(shù),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為奸宄,強陵弱,眾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板》也是諷刺周厲王的詩篇。《毛序》云:“《板》,凡伯刺厲王也。”《桑柔》,芮良夫作,《詩序》:“《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十月之交》諷刺幽王寵信褒姒、任用小人,逼走了宣王朝的老臣皇父及其盟友,致使國亂政衰,人心離散。《蕩》篇,《毛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其獨特之處是模擬周文王斥責殷商的口吻表達對現(xiàn)實政治的不滿,其詩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強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全詩用這種表述方式貫穿始終,開借古諷今之先河,表現(xiàn)了人民在周室衰敗環(huán)境下的掙扎和對統(tǒng)治者的憤怒之情。以上詩作是朝中大夫從國家興亡的角度對時政表示不滿和擔憂。下層人民也從自身的遭遇出發(fā),抒發(fā)國政混亂對自己造成的災難和傷痛,《北山》是周幽王時一個下層官員所作,《毛序》謂“《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于從事,而不得養(yǎng)其父母焉”。《無將大車》也是周幽王時下層官員所作,詩中表達了政繁役多、勞苦憂思、感時傷亂的情感。詩人借用推大車而自招塵埃起興,告誡自己遠離紛擾,否則只能自討苦吃。《四月》是幽王朝的一位“君子”所作,他被周王派遣駐守江漢之間的南國,但因朝中發(fā)生禍亂,過期而不得歸家,于是寫下這首詩,對造成禍亂的當政者表示極大的怨憤。厲王就小人,遠賢臣。奸人當?shù)溃Y(jié)黨營私,人心離散。面對這種情形,詩人禁不住怒斥小人:“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大雅?桑柔》)
戰(zhàn)國后期楚懷王朝中的情形也是如此。小人結(jié)黨營私,舊貴族不顧國家的前途命運,極力阻撓屈原等有遠見的大臣的改革舉措,這些小人“規(guī)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而楚王又昏庸“不寤”。面對這種情形,屈原既怨憤又無可奈何:“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離騷》)。“靈修之浩蕩”與大雅中稱厲王為 “蕩蕩上帝”、“上帝板板”、“上帝甚蹈”一樣,表達了正直大臣對最高統(tǒng)治者的失望之情。可以說對昏庸君王的勸諫、斥責和怨憤之情是二雅怨刺詩最突出的主題。而屈原以《離騷》為代表的大量作品也貫穿著對“哲王不寤”的幽怨之情。
楚懷王十年(前319)屈原任左徒之職,他對外主張“聯(lián)齊抗秦”,對內(nèi)主張政治改革。屈原對未來的政治事業(yè)充滿熱情,但楚王前后不一,數(shù)次變化:“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shù)化。”(《離騷》)這種情形西周末年的小雅詩人早已深有體會。如《小雅?菀柳》: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焉。俾予靖之,后予焉。
有菀者柳,不尚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后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兇矜。
《毛序》:“《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魏源《詩古微》則以為是刺周厲王,他的理由是:“試質(zhì)諸《大雅》刺厲刺幽之詩則了然矣。厲王暴虐剛惡,乃武乙宋康之流;幽王童昏柔惡,特后漢桓靈之比。故刺厲之詩欲其收輯人心;刺幽之詩皆欲其辨佞遠色。”又說:“征以厲王諸詩,一則曰‘上帝板板’,再則曰‘蕩蕩上帝’,與此《菀柳》‘上帝其蹈’,皆監(jiān)謗時不敢斥言而托諷之同文也。”⑦魏說較之《毛序》,更合情理。詩中反復說“上帝甚蹈”,是由于厲王暴虐,監(jiān)謗于人,故假托上帝,如同《離騷》之言楚王為“靈修”一樣。 蹈:變動,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言其喜怒變動無常”。⑧“俾予靖之,后予極焉。”意思是先使我治理國事,后來“王信饞不察功考績,后反逐放我。”這里抒發(fā)的幽怨之情與屈原“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如出一轍。不同的是,小雅詩人不像屈原那樣欲罷不能,因為屈原與楚王同祖同宗的關(guān)系,他對楚王和楚國的命運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所以顯得格外悲憤交加。而《菀柳》的作者在遭到不公的待遇和傷害后,可以毅然決絕:“上帝甚蹈,無自昵焉”。并且大聲質(zhì)問:“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兇矜。”這是作者和周王的親疏關(guān)系決定的,也是屈原無法做到的。
2. 斥責饞人
伴隨著政治的衰頹,讒毀和中傷行為滋生。關(guān)于讒言現(xiàn)象的描述和對饞毀行為的斥責是厲幽時代詩歌和屈原作品又一共同的表現(xiàn)主題。《小雅?青蠅》寫道:“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gòu)我二人。”《青蠅》是衛(wèi)武公所作之詩,刺幽王信讒言,廢申后、放太子。⑨詩中以營營亂飛的青蠅起興,表現(xiàn)了讒言的盛行及其危害之大,并對讒言和饞人者充滿了憤怒和厭惡之情。《小雅?巷伯》是周幽王末世,寺人孟子遭讒罹禍而作。《毛序》謂:“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詩中對譖人者的憤怒之情達到了極致:“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而對譖人者羅織罪名的伎倆更是極盡諷刺之能事:“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活畫出了譖人者的蠅營狗茍、“預謀譖人”的丑惡行徑。在《小雅?巧言》中,詩人痛斥小人進讒言而天子不察,遂使國家禍亂頻生。作者遭受了讒害,悲憤的情緒難以抑制,所以用憤激之詞直斥讒佞之人。可以說對于饞毀現(xiàn)象的描述在西周末年的詩作中俯拾皆是。看來饞毀現(xiàn)象的確是厲幽時代的政治亂象之一。奸邪小人饞毀賢臣的現(xiàn)象歷朝都有,但西周末年對這一現(xiàn)象的反應之強烈和深刻確是文學史上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
四百年后,饞毀現(xiàn)象在楚國重現(xiàn),傷害著楚國的賢臣良士,進而損害著楚國的國家利益。楚懷王時期,屈原對外主張“聯(lián)齊抗秦”,對內(nèi)主張政治改革。他受命草擬憲令,因妨害了舊貴族的利益,受到上官大夫、寵臣靳尚、王妃鄭袖等人的讒毀。屈原是小人饞毀的直接受害者。他對讒言誤國和讒言中傷的憤懣比西周末年的詩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他更痛心的是楚王對讒言的聽信:“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怒。”(《離騷》)他怒斥饞人:“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離騷》)但與小雅詩人不同的是,屈原并沒有像《小雅?巷伯》那樣用咒語的形式對饞毀者進行詛咒。這是因為對饞毀現(xiàn)象描述較多的小雅詩人大多是中下層貴族,身份地位較低;而四百年后的屈原時代,人們的思想觀念又有了新的發(fā)展。屈原深知對于奸饞小人,說教是無意義的:“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離騷》)與西周末年的詩人面對饞言的態(tài)度相比,屈原顯得更理智、更清醒。屈原在經(jīng)過一番抗爭之后,深知自己已無力改變外部世界,也無法改變世人,最后剩下的只有改變自己了:“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父》),他可以選擇自己不同的人生道路。這也是后世有氣節(jié)的文人立身處世的基本法則。班固曾經(jīng)批評屈原“露才揚己,忿沉江”不合二雅,不合《左傳》,也是針對屈原的桀驁不馴和傲岸不群而言的。劉熙載謂班固此論“殊損志士之氣”(《藝概?賦概》),實在是確論。
3. 生不逢時之感和孤獨無援之嘆
時局的動亂、饞毀中傷以及不公的待遇必然使詩人產(chǎn)生生不逢時之感和孤獨無援之嘆。這是人遭受不公的待遇和誣陷之后的必然反映。《小雅?苕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小雅?正月》:“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后。”意識到自己的生不逢時,就會對時間產(chǎn)生一種追問和思考,同時又會產(chǎn)生日月易逝,人生易老的悲哀。《小雅?小宛》:“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離騷》中這種意識更強烈:“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我國古代社會以農(nóng)耕為主要生產(chǎn)方式,人民從上古時期就對時間很敏感,產(chǎn)生了許多時令歌謠。但小雅詩人的有些時間意識顯然與時令時間不同,而是一種對生命時間的反思,是人生價值在時間維度上的思考。只不過這種思考還是朦朧的、樸素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兮,雨雪霏霏。”(《小雅?采薇》)“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憂心,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怒。”(《小雅?小弁》)到了《離騷》,已經(jīng)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時序主題的書寫了。在這種生不逢時的感嘆中,必然產(chǎn)生三種心理反應:一是孤獨體驗。二是悲傷情緒。三是產(chǎn)生想象和幻想,這表現(xiàn)在詩歌中,就是對抒情空間的擴展。前兩點在《小雅?小弁》中表現(xiàn)得很突出:“弁彼斯,歸飛提提。民莫不谷,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焉如。假寐詠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如疾首……”《小弁》,《毛序》:“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漢代以后的學者對于《毛序》的說法頗多疑問。朱熹《詩集傳》:“《序》以為大子之傅述大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jù)也。”⑩姚際恒《詩經(jīng)通論》據(jù)此駁《毛序》:“詩可代作,哀怨出于中情,豈可代乎?況此詩尤哀怨痛切之甚,異于他詩也。”{11}從文本來看,此詩更像太子宜臼自作。其中抒發(fā)的孤獨感和悲傷之情的確是代做者無法做出的。班固《漢書?馮奉世傳贊》云:“饞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jīng),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12}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通過想象來擴充抒情空間在《詩經(jīng)》中基本上是以比興的暗示和聯(lián)想實現(xiàn)的。“且《詩經(jīng)》比興的幾種主要聯(lián)想方式都很單純直觀。”{13}這種聯(lián)想大多都沒有脫離人間性和現(xiàn)實性。然而二雅怨刺詩在抒發(fā)憂憤之情的探索中,大幅度的聯(lián)想思維卻突破了其它《詩經(jīng)》作品比興聯(lián)想的現(xiàn)實界限,從而使《詩經(jīng)》的現(xiàn)實主義表現(xiàn)方式向《楚辭》浪漫主義表現(xiàn)方式的轉(zhuǎn)變邁進了一大步。
三、二雅怨刺詩表現(xiàn)出了由現(xiàn)實主義向浪漫進行思維跨越的嘗試
比興本來是《詩經(jīng)》最主要的聯(lián)想方式。興更是由于某種感觸而進行的相似情形之聯(lián)想,但這種聯(lián)想都不出現(xiàn)實生活的經(jīng)驗世界。在二雅詩歌產(chǎn)生的時代,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還是傳說的重黎“絕地天通”以來的秩序格局。《尚書?呂刑》和《國語?楚語》所謂的“重上天,黎下地”其實是天官系統(tǒng)和地官系統(tǒng)的政治文化模式,后來發(fā)展為《周禮》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大體系。{14}“絕地天通”其實是上古政治與原始宗教在社會權(quán)力分配中的一種共謀,其結(jié)果是形成了政權(quán)與神權(quán)緊密結(jié)合的社會秩序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只有巫祝等神職人員有權(quán)溝通天人,神的世界被賦予“神圣”的不可置疑的權(quán)威性,反映在《詩經(jīng)》中就是用于祭祀的儀式樂歌(《頌》)與人間的樂歌(《風》和大部分《雅》詩)有明顯的區(qū)別。《風》《雅》之詩基本立足于現(xiàn)實世界,《頌》詩則立足于神靈的虛幻世界。這個神靈的虛幻世界當時從主觀上來說不是文學藝術(shù)的,而是神圣權(quán)威的世界。這種虛構(gòu)也還不是文學藝術(shù)的虛構(gòu)。與《詩經(jīng)》相似,《楚辭》的表現(xiàn)內(nèi)容也可以分為現(xiàn)實世界和虛幻世界兩大部分。有研究者認為,盡管屈原作品中,不像《詩經(jīng)》將其明確劃分為風、雅、頌三類,但其實質(zhì)性內(nèi)容卻具有《詩經(jīng)》風、雅、頌相同的體制特征。{15}作為貴族詩人的屈原與《詩經(jīng)》二雅的作者身份相似,故其大多數(shù)作品更與雅詩相類。屈原作品可以看做是楚國的雅詩和頌詩,而在《詩經(jīng)》的《周南》《召南》《陳風》和一些逸詩中有一部分作為楚辭上源的早期抒情詩歌{16},這些詩歌可以說具有楚風的性質(zhì)。《九歌》即具有“楚頌”的性質(zhì){17},表現(xiàn)的是神靈的虛幻世界,《招魂》和《大招》也是如此。而《橘頌》和《離騷》以及《九章》中的作品可以看做是雅詩,是立足于現(xiàn)實世界的,盡管其中也有虛構(gòu)世界,但這種虛構(gòu)世界已與“九歌”的虛構(gòu)世界有了本質(zhì)的不同。因為《離騷》和《九章》中的虛幻世界是神靈世界的權(quán)威性被打破之后,文學思維從現(xiàn)實世界向虛幻世界的跨越,虛幻世界不再是神圣的神靈世界,而成了文學書寫的領(lǐng)地。這一思維的跨越也是文學從現(xiàn)實主義向浪漫主義表現(xiàn)手法跨越的前提。
而一向被認為與《詩經(jīng)》差別較大的《楚辭》的一些體式上的特點也正是在這種思維跨越的影響下產(chǎn)生的。不過這種思維跨越在《詩經(jīng)》中已經(jīng)露出了端倪:《小雅?大東》在比興的基礎(chǔ)上將聯(lián)想的觸角伸向宇宙空間,詩人在“西人”的壓迫和剝削下,不禁展開想象,借天上的星辰來抒發(fā)對西方統(tǒng)治者的不滿情緒: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佩,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jiān)亦有光。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雖然這種聯(lián)想方式也是“比興”,但跟《詩經(jīng)》其它詩篇不同的是,詩人借以比興的事物在天上,這一過渡對人們拓展思維空間和抒情技巧打開了一扇門。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說:“從詩的內(nèi)容來看,作者可能是一位精通星象的文人”{18},但這些天象顯然已經(jīng)不是“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小雅?漸漸之石》)這樣的天象描述,而是一種象征,一種幻想和浪漫主義的情感表達。只不過這種浪漫主義的表達是不自覺的,而到了《離騷》,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手法就已經(jīng)是完全自覺的表現(xiàn)方式了。《大東》由人間到天上的想象式抒情是后來屈原神游天界的文學思維之端倪。《大東》詩人想象天上那些人們崇拜的星宿徒有虛名,只居其位而不做實事,對其產(chǎn)生了質(zhì)疑。這種對神圣事物由崇拜走向質(zhì)疑再到完全抽去其神圣性,變?yōu)槲膶W表現(xiàn)素材的轉(zhuǎn)向,其背后隱藏著巨大的思想史變革。
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中華民族的理性精神在精英知識階層覺醒,這種理性精神強調(diào)人的作為在社會治亂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說在哲學上,這一時期是真正的“絕地天通”,即人跟神決裂,重、黎的“絕地天通”模式已不復存在。人不再將現(xiàn)實治亂依托于神靈的庇佑,神的權(quán)威失墜。而在文學上正好相反,是“地天通”,神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崇拜物,人可以在想象中與神同游。神話人物和神話事物成為說理、敘事、抒情的對象和載體。這一點在戰(zhàn)國時代的各種文體中都有體現(xiàn),而表現(xiàn)最突出的是屈原的作品。屈原在其極具哲學意味的著作《天問》中對神話傳說表現(xiàn)出了極為強烈的懷疑和否定。他以實證精神將神話幻設解構(gòu)了。在《離騷》中,屈原把以神為核心的原始傳統(tǒng),包括神靈形象、神話境界、神的超凡能力以及祭祀神的儀式等提升為一種有意味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19}在其憂憤之情噴薄而出的時候,詩人的思維也是天上地下,讓自己在神游天地中盡情抒發(fā)難以抑制的思想感情。他指揮云霓,喝令眾神聽從自己的命令。對于那些傳說中的神人,屈原也是大膽的予以評判。《大東》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了浪漫主義的思維傾向,在屈原作品中,這種浪漫主義思維逐漸展開:在作為楚頌的《九歌》中,與神的交通只限于巫咸,到了后來的《抽思》《思美人》《惜誦》乃至《離騷》,詩人自己開始與諸神“交通”,而且也是由試探再到全面地進行神游。在《抽思》中,其陳辭是對懷王的,在《離騷》中變?yōu)閷Φ鬯矗⒂苫貞涀兂闪讼胂蟆T凇端济廊恕分校@種從現(xiàn)實向想象的思維跨越更進了一步:“愿寄言于浮云兮,遇豐隆而不將”,“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到了《離騷》詩人就已經(jīng)完全打破時空界限,通過神游將現(xiàn)實、歷史、神話、幻想融為一體了。
四、《詩經(jīng)》“二雅”在辭章句法和抒情風格方面為《離騷》作了鋪墊
人遇到不平之待遇后,必然言多辭長。二雅怨刺詩的篇幅明顯加長。多數(shù)二雅詩歌已是完全意義上的誦詩,只不過不象屈原作品那樣成熟和有自覺的藝術(shù)加工。誦詩就不像歌詩那樣需要用重章疊句來延長演唱需要了,大部分雅詩不做重章。另外,每一章的句數(shù)從一章四句到章十二句不等,但總體的趨向是章內(nèi)句數(shù)增多,個別章節(jié)句式加長,以章八句居多。不論是章四句、章六句還是章十句、十二句,二雅的句式在章節(jié)方面完全以抒情敘事的需要來決定。不過一旦一章確定用某一句數(shù)則會一貫到底,并且基本上是偶句作結(jié)。其總體上還是處于章節(jié)安排的自發(fā)、自然狀態(tài),不像屈原已經(jīng)形成了自覺的以四句為一節(jié)的抒情形式單位,注重詩歌章節(jié)的形式結(jié)構(gòu)。西周末年的雅詩已經(jīng)按照抒情內(nèi)容的完整性和層次性自然分章,這一點為屈原所借鑒。他“繼承了《詩經(jīng)》中 ‘雅’ 詩的藝術(shù)經(jīng)驗,在南楚民歌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了六言騷體詩形式”。{20}
可以說二雅怨刺詩與屈原作品由于抒情內(nèi)容和風格的相似直接誘發(fā)了其在體式上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表現(xiàn)在:篇幅的加長;以情馭文,不做重章;句式有意向規(guī)范整齊靠攏,體現(xiàn)了詩歌的建筑美。如果把二雅怨刺詩與屈原作品做一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除了一種是四言,一種是六言;一個語言古樸,一個語言明麗之外,在情調(diào)風神方面幾乎如出一轍。如果把分散于二雅各處的有關(guān)內(nèi)容集合起來,幾乎已經(jīng)勾勒出來《離騷》主題的大致輪廓和主人公的基本形象。{21}另外,二雅怨刺詩抒情風格的邈遠纏綿、彷徨悱惻都開啟了屈騷作品的抒情基調(diào)。下面試將《小雅?正月》變成楚辭體的形式加以比較:
正月繁霜兮我心憂傷,民之訛言兮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兮憂以癢。父母生我兮胡俾我愈?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后。好言自口兮莠言自口,憂心愈愈兮是以有侮。憂心兮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兮并其臣仆。哀我人斯(兮)于何從祿?瞻烏爰止兮(于)誰之屋?瞻彼中林兮侯薪侯蒸,民今方殆兮視天夢夢。既克有定兮靡人弗勝,有皇上帝兮伊誰云憎!謂山蓋卑兮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兮甯莫之懲!召彼故老兮訊之占夢,具曰予圣兮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兮不敢不局,謂地蓋厚兮不敢不。維號斯言 兮有倫有脊,哀今之人兮胡為虺蜴!瞻彼阪田兮有菀其特,天之我兮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兮如不我得,執(zhí)我仇仇兮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兮如或結(jié)之,今茲之正兮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兮寧或滅之,赫赫宗周兮褒姒滅之。終其永懷兮又窘陰雨,其車既載兮(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兮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兮員于爾輻。屢顧爾仆兮不輸爾載,終逾絕險兮曾是不意!魚在(于)沼兮亦匪克樂,潛雖伏(矣)兮亦孔之。憂心慘慘兮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兮又有嘉。洽比其鄰兮婚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殷殷。彼有屋兮蔌蔌方有谷,民今之無祿兮天夭是。哿矣富人兮哀此煢獨!
同樣,如果將二雅中的許多感時傷亂之詩都變成騷體的形式,再將其整合,似乎就是《離騷》的雛形了。組合后的“召彼故老兮訊之占夢,具曰予圣兮誰知烏之雌雄”一句與《離騷》的“就重華陳辭”和“巫咸降神”之情節(jié)是如此的相似,其書寫內(nèi)容和抒情風格完全具備后世《離騷》的風神。從形式上來說,八句一章的抒情單元通過兮字的鏈接,形成了令人吃驚的四句一節(jié)的“離騷體”意義單元。也許是人類抒情天性的自然節(jié)奏,二雅詩人抒情中自然形成的章八句結(jié)構(gòu)正好可以表達一個完整的情感單元,雖然其中也有章十句和章十二句的,但章八句占了大多數(shù),這是人們在文學抒情的探索過程中不經(jīng)意發(fā)現(xiàn)的一種天然節(jié)奏和抒情單元。因為《詩經(jīng)》中的一句只承載半句的意義{22},因此其兩句才能構(gòu)成一個意義上的足句,《詩經(jīng)》的八句一組就相當于《離騷》的四句一組。《詩經(jīng)》二雅章八句的結(jié)構(gòu)和節(jié)奏單元后來經(jīng)屈原的改造,形成了四句一章的詩歌抒情節(jié)奏。
綜上所述,《詩經(jīng)》二雅怨刺詩從內(nèi)容到體式都對屈原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影響,《離騷》的出現(xiàn)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盡管《詩經(jīng)》后的先秦詩壇似乎沉寂了許多年,沒有出現(xiàn)其它詩集,但沒有詩集不等于沒有詩歌創(chuàng)作。《詩經(jīng)》是禮樂制度的產(chǎn)物,戰(zhàn)亂和禮樂制度的破壞使《詩經(jīng)》之后的大量詩歌無暇收集。《離騷》的出現(xiàn)代表了戰(zhàn)國時代詩歌發(fā)展的最高成就,是先秦詩歌繼《詩經(jīng)》之后的繼續(xù)發(fā)展,從中我們?nèi)匀豢梢钥吹健对娊?jīng)》的傳承和影響。
注 釋:
①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6頁。
②{12}班固:《漢書》,顏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56頁,第3308頁。
③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徐志嘯《歷代賦論輯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51頁。
④程廷祚:《騷賦論上》,《青溪文集》(卷三),道光丁酉年(1837)鐫東山草堂藏版,第14頁。
⑤趙逵夫:《屈騷探幽》,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4年,第163-166頁。
⑥陳師道:《后山詩話》,何文煥:《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13頁。
⑦魏源:《詩古微》(中編卷六),《續(xù)修四庫全書》(第7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47頁。
⑧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771頁。
⑨陳奐:《詩毛氏傳疏》(卷二十一),《續(xù)修四庫全書》(第7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90頁。
⑩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86頁。
{11}姚際恒:《詩經(jīng)通論》(卷十),《續(xù)修四庫全書》(第6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64頁。
{13}顏方明:《古詩意境的認知與闡釋機制》,《求索》2012年第6期。
{14}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shù)源流》,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第300頁。
{15}韓紅宇:《論〈楚辭〉的民本思想及其時代特征》,《求索》2012年第3期。
{16}趙逵夫:《作為楚辭上源的民歌和韻文剖辨》,《屈騷探幽》,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4年,第119頁。
{17}韓高年:《〈九歌〉楚頌說》,《詩賦文體源流新探》,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4年,第73頁。
{18}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629頁。
{19}趙敏俐、譚家健:《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先秦兩漢卷》,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7-259頁。
{20}趙逵夫:《先秦佚詩與先秦詩歌的發(fā)展》,《江海學刊》2005年第1期。
第7篇:屈原的離騷范文
釋義:這是我心中所追求的東西,就是多次死亡也不后悔。出自屈原的《離騷》。
《離騷》是戰(zhàn)國詩人屈原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是帶有自傳性質(zhì)的一首長篇抒情詩。全詩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屈原,約公元前340或339年至公元前278年,中國戰(zhàn)國時期楚國詩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國秭歸,今湖北宜昌。羋姓,屈氏,名平,字原。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楚辭”的創(chuàng)立者和代表作者,以屈原作品為主體的《楚辭》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之一,與《詩經(jīng)》中的《國風》并稱“”,
(來源:文章屋網(wǎng) )
第8篇:屈原的離騷范文
這句話出自于屈原的《離騷》,原句是“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句中“厚”的意思為:重視,看重。
原句的翻譯為:堅守芳潔的言行和廉貞的節(jié)操而死于正直, 這本來就是前代和圣人所稱許重視的。
第9篇:屈原的離騷范文
——題記
五月,多么美好的時光。又是一年端午,又是一個“詩人節(jié)”,又是一個飄滿粽香的日子。家家都備好粽子、雄黃酒,掛上菖蒲,為紀念屈原這位愛國詩人。
屈原是戰(zhàn)國時期楚國丹陽人,今湖北秭歸縣人。屈原出生于楚國貴族家庭,從小就沒有富貴子弟身上的那種猖狂、任性,這使他成為了一個愛國詩人。屈氏子孫在楚國都曾擔任過要職,到了屈原這一代,屈氏當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來被秦國俘虜?shù)拇髮⑶ぁ.敃r這個貴族家庭已經(jīng)衰落了。
楚國朝廷中,與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懷嫉妒,與屈原爭寵,他向懷王進讒言,懷王庸懦昏聵,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最后,懷王不聽屈原的勸告,客死于秦,當時屈原已經(jīng)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漢北地區(qū)。楚懷王死了以后,長子頃襄王繼位,再次將屈原流放到江南, “百姓震愆”,“民離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鄉(xiāng)而就遠。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屈原長嘆一聲啊,止不住那眼淚流了下來,他是在哀嘆那人民的生活是多么的艱難!他的一生詮釋了世上最真誠的愛國情懷,他用他的一片真情譜寫了《離騷》這一古代瑰寶。
即使這樣的愛國情懷、赤子之心也無法挽留他。昏庸的楚王聽信了奸臣的讒言,卻對屈原的忠言不管不顧,屈原最終不忍看到國家滅亡,在五月初五這天,懷抱一塊大石頭,帶著滿腔的憤怒、滿肚的冤屈投向了汨羅江。聞此事,世人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