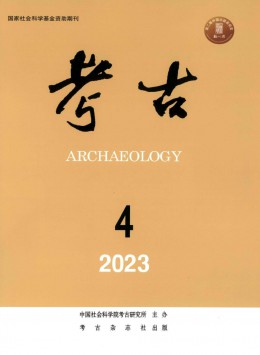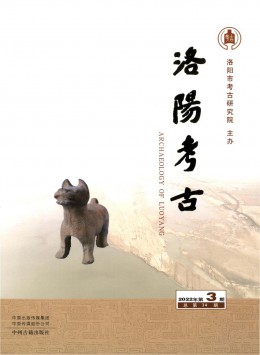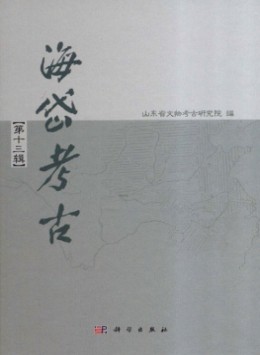考古學基本方法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考古學基本方法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考古學;意義;發展歷程;計算機應用
考古學是通過古代遺存來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會發展。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的聯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層位學、考古類型學都是自然科學中借鑒而來的。考古學不僅對研究過去的歷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對現代社會也有指導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國的近代古代學起始于20世紀初。在大量古籍和歷史證據的存在下,中國考古學對考古學的發展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但考古學在研究歷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學可重建和復原中國的古代史。歷史研究者可以從考古學中獲得大量資料,比如出土文獻和大量考古實物,它們包含著很多歷史信息。通過考古學家對文獻和實物的解釋,更有利還原當時的社會和人們的生活,把歷史展現在我們面前。
考古學可以證明文獻的真偽。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主要通過遺留下的文獻,考古學與遺留文獻的結合,可以解決很多難辨真偽的歷史問題。有的考古發現可與文獻相對照,彌補了文獻的不足或者從根本上彌補了文獻的缺失。
考古學的出現,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考古學還沒有盛行以前,歷史學家只是從文獻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近代考古學出現后,一些史學家將目光轉向考古學,希望從考古中找出歷史問題的答案。
(二)考古學促進了歷史研究的進步。
現代考古技術的發展和大量應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樣化,這樣從考提取的信息也會大量增加,就不斷的為歷史研究提供新課題。今天來,計算機技術被引入到考古學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電子化保存考古數據。
考古學家經過多年的努力,考古學文化的編年和譜系在多數地區基本完成。考古學家還應該應積極引入外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未來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綜合理解和解釋。
二、考古學的發展。
(一)萌芽期。文藝復興至19世紀20年代是考古學的萌芽期,其主要特點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調查古跡。中國的考古萌芽是從宋代開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遺跡的研究。
(二)形成期與初步發展期。19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歐學者西蒙森和湯姆森相繼提出的“三期說”,即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在這一時期,考古學者開展了一系列考古發掘,如對意大利龐培遺址的發掘。
(三)初步發展期。初步發展期大約處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發掘逐漸科學化。此時,出現了“考古類型學”,就是根據遺物的形狀和紋飾的不同,對其進行分類研究,研究和發現這些遺物之間內在的關系。考古學理論則是運用與考古相關學科的傳播論和進化論。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紀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學的基本成熟期,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從20世紀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豐富和創新、考古工作范圍的擴展,在這一時期,重大的考古發現的增多。后期從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改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由注重研究遺物的形式向將年代學與遺物的功能研究相聯系的轉變;根據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人的行為;注重研究文化變化與環境之間關系等。
(五)轉變期。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學的轉變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學,即“過程考古學”的興起。在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由于與外界缺少聯系,國外的各種流派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是考古學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學派和理論,如社會考古學、認知考古學、中程理論等,它們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統稱為“后過程考古學”。
在這一時期,自然科學技術手段被用于考古學,如DNA分析、物理探測和化學成分分析等。同時,中國考古學界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系增加、交流不斷加強。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國的考古學在國際影響日益擴大。
(七)繼續發展期。進入21世紀,考古界各學派之間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現相互包容、百花齊放的局面。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體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應用也越來越多,考古發現層出不窮。
三、計算機在考古學中的應用。
(一)對數據的處理。計算機的出現,為考古信息的管理帶來了極大的方便,還可對發掘的信息進行智能化技術處理,在考古過程中,有些工作僅憑人腦是難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機綴合卜甲碎片。計算機還可以對各種儀器分析的數據進行綜合處理,以及利用信息進行模擬試驗等。
(二)對遺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員不能實地工作的時候,比如對日軍731部隊遺址考古時,發現了在被日軍自毀的地下建筑遺跡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體細菌實驗的罪證物還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員利用現代地球物理勘測技術進行了先期勘測,然后利用計算機繪圖技術對遺址群進行繪圖,考古人員則根據勘測數據顯示的重點區域進行考古鉆探工作。
(三)數字建模處理。在考古遺址發掘中,所有關于遺跡、遺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在考古過程中,傳統的繪圖、照相以及文字記錄手段限于某種因素,已無法適應現在考古的發展,也無法準確地記錄遺跡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資料。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在考古工作的應用,如GPS、數字相機等一些新技術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遺址信息獲取的能力。
四、結語
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在原有考古經驗的基礎上,新的科學技術會越來越多的被應用。由于考古學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全世界的考古學家的數量也在迅速地增長,考古討論會的舉行也大量增多。未來的考古學將進一步科學化、規范化和現代化。為實現這些目標,全世界的考古學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學科的積極參與和配合,只有這樣,考古學才能不斷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弗雷德?T?普洛格,陳虹.考古學研究中的系統論[J].南方文物,2006(4).
第2篇: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
該書共分藝術考古學理論基礎、音樂考古、美術考古、建筑藝術、四川少數民族美術考古、宗教藝術考古六大章節,第一章主要是對藝術考古學學科背景的介紹,以及對該學科領域的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的總結,對“藝術考古學”概念的提出、學科的設立、理論研究現狀作了梳理和概述。其后五個章節分門別類地對藝術學各個研究領域的考古研究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概說。
一、藝術?考古――學科交叉新思維
藝術考古學研究的專業性十分明顯,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藝術學的研究更加專業化,其中包含的科學技術和專業技能有許多已經超越了考古學研究的范圍。《藝術考古概說》第一章詳細地介紹了藝術考古學基礎理論,對學科的相關研究論著進行了梳理歸納。
1978年國務院批準編撰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列出有關藝術類考古學的條目,成為中國藝術考古學科的正式提出和設立。《藝術考古概說》以《中國大百科全書》為基本理論構建,指出,由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親自撰寫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總論中,將“美術考古學”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說明美術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與目的:“美術考古學是從歷史學科的立場出發,把各種美術品作為實物標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復原古代的社會文化。”②之后正式列出了“美術考古學”和“音樂考古學”條目,對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與美術史、音樂史的關系等作了規定,也成為我國明確設立“美術考古學”和“音樂考古學”專業學科的依據。作者依據上述文獻,對藝術考古學的分類、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進行了闡述,說明藝術考古學是探究中國古代精神文化的起源和發展,探究藝術的起源和發展規律的學科。許多藝術遺跡和遺物,凝結著古代物質文化發展的高級形態,因此藝術考古研究也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重要補充資料,并且涉及許多自然科學知識,是研究我國科學技術發展史的重要補充。作者除采用考古學、藝術學研究基本方法外,還特別指出運用自然科學原理和方法研究藝術考古的重要性。
二、案頭?田野――研究領域新突破
在第二章至第六章的分類介紹中,作者“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作為推動藝術考古學研究的學術背景。20世紀80年代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發掘,引起國內外關注,兩個遺址挖掘清理出土大批文物,在世界尚屬首次,它們的文化內涵有待于進一步深入探究。兩個大遺址的保護和利用,已被列入國家大遺址保護工程,并取得了成功經驗,為四川省藝術考古的全面研究、開發、轉化、利用,打下基礎。例證、圖片豐富,每一部分的參考文獻也十分標準,可以看出,作者在前期的搜集和考證中的扎實案頭工作。
我國藝術考古理論的探索實踐,可追溯到20世紀初期西方科學技術和學術思想對我國學術理論界的影響,書中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創建中國美學、音樂學、甲骨學、考古學、古建筑學的奠基人的理論思想作了論述。如我國第一代美學思想家朱光潛、宗白華先生;我國第一代音樂理論家王光祈、楊蔭柳先生;我國第一代考古歷史學家李濟、郭沫若、夏鼐、馮漢驥先生;我國第一代古建筑學家梁思成、劉敦楨、童、楊廷寶先生等。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赴西方或者日本留學后,回到中國,運用西方理論方法,研究中國古代藝術,在古物考證、文化內涵分析以及建立方法論等方面,填補了中國某項專業理論研究的空白,開啟了中國美學、中國音樂史、中國考古學、中國古建筑學等理論研究之先河,中國藝術考古學的基本理論思維,也在這些專科研究過程中產生。
三、實用?前瞻――文化產業強推動
藝術考古學,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也成為藝術事業建設中快速發展的一種藝術類型。作者認為,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對藝術欣賞需求的不斷增長,隨著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不斷發展,藝術考古成果的開發和轉化,將成為文化藝術事業、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強勢品牌,在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中,在豐富國內大眾文化鑒賞娛樂活動中,都會以其不可替代的獨特品質,受到觀眾的喜愛,成為展演、影視市場上不斷創新的類型。在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工程中,進一步明確了人類精神文化起源。
《藝術考古概說》一書中,作者分析了目前藝術考古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如缺乏統一的綜合研究機構,出土文物的調查研究受到行業管理約束,各類藝術考古所需用的科技手段如“音樂聲學測量”等專業性強、技術上難度大等問題,提出了建立藝術考古學綜合學科、在大學或研究機構開設專業課程、建立藝術考古研究協會等設想。在書中,作者還從打造精品品牌、推廣多媒體制作和傳播、規范旅游區開發、加強對外人文交流和宣傳、籌建藝術考古專業六個方面,提出了針對四川地區藝術考古成果的開發與轉化建議。在開發轉化方面,四川落后于湖北、湖南、河南等省,歸結原因是缺乏資源整合與合作開發。四川應在已有成果,如三星堆博物館、金沙遺址博物館等的基礎上,合理利用地方考古資源和考古人才,推動四川藝術考古發展。
四、巴山?蜀水――古老文化的煥新
《藝術考古概說》一書的藝術考古地域基本集中于巴蜀地區,這一地區藝術考古資源非常豐富,但研究卻相對滯后,成果形式也基本停留在紙質書著階段,對這一地域的藝術考古研究來說,需從最基礎的工作入手,更大限度地實現成果轉化。編者以四川藝術考古研究取得的成果為基礎,對古巴蜀區域的音樂考古、美術考古、建筑藝術、四川少數民族美術考古、宗教藝術考古等,作了歸類整理和闡述;對目前作好四川藝術考古成果轉化開發作了可行性研究,提出總體構想和開發建議。
第3篇: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考古學;區系類型學;文化區
中圖分類號:K8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0)19-0100-02
考古學文化的區,指的是文化區。在考古學上的意義就是指一個考古學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間范圍。一般情況下,一種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間范圍(相對比較大的地理空間)就是一個文化區。研究它的首要目的,是為了區分各種考古學文化在一定時期內的空間分布,從而為進行較大范圍內的橫向考古學文化研究奠定基礎。
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學是建立在文化遺存之間或遺址之間的比較之上的。比較是人類認識事物的最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類思維中最經常的一類活動。有比較才有鑒別,沒有比較,人類認識事物的過程就不可能完善,人類的知識體系也無法存在。只有在研究中比較考古學文化的不同現象,才有可能發現出他們各自得內涵,才有可能對他們產生概念上的認識。區、系、類型的研究方法就是一種比較法,這里所指的比較不是潛在的、無意識的,而是刻意的、有意識的。世界上各事物都存在某種聯系與依托,同時,這些事物都處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只有通過比較,才能使事物的特征更加鮮明。
由于不同地域的人類所處的自然環境,獲取生活資料的方法各不相同,生活方式也各有特色,因此,古人遺留下來的文化遺存或多或少地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就是我們區分不同考古學文化或不同文化類型的關鍵依據。
我們在做判別和區分的時候,是離不開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來做依托的。首先,我們應根據考古地層學原理,與自然科學相結合,借助現代科學測年法,確定某一地區考古學文化發展的序列及相對年代;其次,在具體開展考古發掘和研究時,應先從單件的器物,或個體遺跡入手,從對遺跡遺物形態特征的研究,上升到聚落群體的研究,其中包括聚落內各遺跡之間的關系。接下來,從聚落之間的比較上升到聚落群的比較,通過聚落群之間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的比較研究,確定文化區,這便是所謂的從器物本位上升到聚落本位,再上升到文化本位,最后上升都最高層次,即社會層次。在對某地區的田野考古發掘積累到一定量之后,根據一定數目的已發掘的遺址,設法搞清某種考古學文化的特征,包括墓葬、建筑、陶器、農業生產等。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通過考古類型學的研究,在更大范圍內比較不同遺址,從而認定同一考古學文化的分布范圍。要確定一個考古學文化區,一定要經過反復比較;同時,這些要比較的遺址,必須經過正式發掘并具備一定量的遺跡遺物基礎。在進行兩個遺址比較時,主體部分至少應有50%以上相似特征的文化因素,這樣才可確定兩個遺址或兩個遺址中的某個文化層屬于同一文化。如果僅有少量相似的文化特征,一般情況下,僅僅能視作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而非同一文化。
同時,在比較中,我們還應注意某一文化區周邊器物的其它文化區。在同一文化區內,最典型的文化特征集中的地區為中心地,即文化中心。而離文化中心最遠的地區為文化邊區地區。這些邊區的文化由于多數情況下處于兩種文化區的交界地,一般都是兩種文化的交界處,包含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因素。因此,劃分邊區文化區的范圍十分繁雜,一定要格外留意,要經過正式發掘并且加以量的比較,才能比較準確地做出劃分。當然,確定文化區的中心也很重要。如果中心確定不準確,那整個文化區的范圍就會被劃大或是圈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區的范圍,即文化邊區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動態的,是隨著時間的發展不斷變化的。因此,我們要通過精確的分期及大量的研究比較,才有可能確定出不同時期文化區的范圍。
考古學文化的系,是指文化發展的系統或者系列,也就是考古學文化縱向的發展脈絡。一般情況下,它是由若干個有時間發展關系的考古學文化構成的,是某一區域內文化發展的先后序列。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都有一定的時間范圍,與此同時,每種文化又一定與該地區先后的文化有著某種關系。反映到考古學文化上,則表現為每一種考古學文化都具有其產生淵源及發展方向。所以,每一個考古學文化系統都是由若干縱向發展關系的文化構成的,而要確定一個文化系統,也必須建立在考古地層學與考古類型學的基礎上。具體來說,考古地層學主要靠研究判斷在某地區內各種考古文化出現的先后順序,而考古類型學則是通過對具體的遺物的研究分析,以此來確定器物之間前后承襲的發展關系。
考古學文化的類型,指的是文化類型。關于它的具體含義,目前還存在一定爭議。多數學者認為它指的是在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分布區域內由于微環境的條件差異,包括自然環境、地理條件、其它文化的影響等因素,在主體文化因素一致的前提下,表現出某種地域性的差異。這種地域性的差異通常就會用考古學文化類型來定義。當然,每種文化類型也存在一定的區域性。
一種考古學文化可能由幾種考古學文化類型(地區類型)構成,由分布在一個區域內相似的若干個遺址構成。因此,盡管文化類型也有時間上的差異,但更多的表現卻是空間上的不同。這種文化類型,也可以叫做文化分支,它對于進一步了解考古文化發展的復雜性,是相當有意義的。
在人類學研究中,人類文化即有普遍文化與亞文化之分,亞文化表現出不同的地域性、民族性、甚至是職業性。在文化的主題因素一致的前提下,文化類型就可以視為一種考古學文化的分支、或是類似于文化人類學上所說的亞文化。文化類型主要表達的,是一時期內不同空間上所表現得文化差異,而分期則注重表現相同空間內不同時期的文化差異,應該把它們的側重點搞清,不要混淆。
從理論上講,統計的器物類型越多越好,這種文化因素分析法是從具體的器物、遺址、到遺址群、再到文化區、最后再到不同文化區之間的文化因素比較,也包括早晚文化的比較,這樣才能建立出某一地區文化發展的時空框架。
在運用比較法的時候,我們不能僅依據某單一方面,如果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只能依據一個方面,也必須盡可能得從多角度全面加以分析。例如,一個考古學文化的陶器比較,我們要從紋飾、器形、陶質、陶色、制法等多方面,只有這樣才能比較準確地判別出文化的屬性及某些文化因素的來源與早晚關系,不能僅依靠簡單的比較就得出某兩種文化屬于同一考古文化或不同文化,一定要有一個全面的定性、定量的研究。
在考古學的研究中,無論是在史前時期還是在歷史時期,區、系、類型學都是一項基本的研究問題。在史前時期,尤其是新石器時代,它更是一項基本任務。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框架的建立,為我們從宏觀上探討歷史文化,探究民族的形成發展以及民族文化的變化等重大問題奠定了基礎。區、系、類型學是從實踐中得出,再回到實踐中檢驗,并且在反復檢驗中指導更高層次的研究方法。確立區、系、類型學的基礎前提是正式發掘的大量田野考古資料。也就是說,只有當考古工作者通過考古發掘獲得了一定量的可靠的資料,才能設法確立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同時,這個區系類型必須在日后的發掘中不斷檢驗并完善,并進一步指導更高層次的研究分析。要通過反復的驗證,不能拘泥不變,輕易下結論。我們知道,仰韶文化是我國第一個被確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然而,自從它最初被確立開始,直到今天,有關它的認識都是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斷發展,資料的不斷豐富,以及研究的逐漸深入日益完善并改進的。并不是從它一經發現便得出今天的結論。我們對任何一種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研究,都要經過反復驗證,要掌握大量的真實材料,同時采取科學的態度。
任何文化都有一定的時空范圍。對于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來說,區是塊、系是條、類型則是分支。這三個方面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在研究中,我們要從宏觀上加以注意,不能將它們割裂,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考古學文化有一個更為科學的認識。
第4篇: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
黃洋(鄭州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生)
采寫: 許捷
如果你喜歡看《鬼吹燈》《盜墓筆記》之類的盜墓小說,是不是對洛陽鏟、黑驢蹄子、地質錘之類的盜墓工具特別熟悉?甚至還很羨慕那種入山下海探索古代文明、揭示未解之謎的生活,想要做個考古學家?現在我們就來揭開考古學專業的“面紗”,看看考古工作者是不是都像印第安納?瓊斯(電影《奪寶奇兵》中的考古學教授)那樣,生活中充滿了冒險與奇遇。
Step1:內功篇
想要學考古,并不是只要有一股子挖土的熱情就行了。想想不管是《鬼吹燈》里的Shirley楊還是《盜墓筆記》里的吳邪,都對歷史和古代文化有著相當程度的了解,使得他們在遇到冥器或古墓壁畫的時候都能分析得頭頭是道。雖然小說里的那些分析不一定都靠譜,但至少說明了一點――理論知識是萬萬少不得的,否則挖到了寶貝自己還未必知道。
現在國內大學的考古學專業,在本科階段基本會安排三年到三年半的理論學習課程,余下的時間就要去考古工地上實踐。
考古學的理論課程大致可以分為歷史課程、考古學基礎課程和專題類課程這三大塊。
歷史課程不用多說,就是從夏商周到元明清的各個朝代史。
考古學基礎課程則主要包含《考古學概論》《田野考古學》,以及從舊石器時代一直到宋元各階段的考古學(明清兩朝因為年代較近,還不屬于考“古”的范疇)。由于古代的實物資料多被埋在地下,必須經過科學的調查發掘才能被系統、完整地揭示和收集,所以考古研究的基礎就在于田野調查發掘工作,這也就體現了《田野考古學》這門課程的重要性,它教給同學們田野考古的理論、方法與技術。而各階段的考古學則主要是介紹各個時期的文化特點,這也是考古學基礎課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秦漢考古》就會介紹秦漢時期的城市遺址所在地(比如咸陽),墓葬特點(包括墓的結構和隨葬品的種類等),這一時期的陶器、瓷器、鐵器的形態、花紋和工藝水平特征等。
專題類課程通常包括青銅器、玉器、錢幣之類的器物課程,以及《體質人類學》等。“體質人類學”是關于人種進化的科學,主要研究各人種的體質特點,比如骨骼的特征、如何區分男女等,使你能夠通過考古發掘出的古代人類骨骼、古人類化石等來研究人類的進化、演變過程。由于存在地域性差異,各個大學的專題課程開設情況還會有所不同,形成各自的特色,例如廈門大學的海洋考古、西北大學的沙漠考古、吉林大學的邊疆考古等。
另外,考古學專業的學生還要學習《文物攝影》《文物繪圖》之類的課程,也都是為考古實踐做準備。
Step2:神兵篇
考古“神兵”――洛陽鏟
洛陽鏟可能是大家最為熟悉的考古工具了,但凡對考古有點興趣的都聽過它的大名。在探測古墓、確定發掘區域時洛陽鏟能發揮極大的作用,它已經成為了中國考古鉆探工具的象征。
但考古發展到今天,所用到的“兵器”可遠不僅是洛陽鏟了。今天已經不是光靠有經驗的老先生憑眼力來鑒定器物的年代了,而是結合了先進科技和傳統考古方法的科技考古時代。最尖端的科學技術如熱磁共振、微量元素分析等都在考古發掘和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
以往由于保存技術的落后,發掘和保護總是成為一對矛盾體,而科技考古的發展使得不破壞遺址就弄清整個墓葬情況成為可能,所以科技考古成了當前考古專業中的熱門方向。同學們要是想往這個方向發展,那就必須要具有跨學科的知識背景,也就是說除了練好“古墓派”的“內功”,“洋槍洋炮”也得熟練掌握。
Step3:實戰篇
三年或者三年半的“內功”修煉,最終還是要在考古工地上見真章的。不過在下工地前你還得做點心理準備。俗話說:“考古苦,考古累,考古得把墓道睡。”雖然睡墓道是夸張了點,但基本也算是考古工作的真實寫照。通常干了幾年的考古工作之后,整個人看起來就和常年種地的農民沒有太大區別了。而且在考古這一行,還真是做到了男女平等――男女考古隊員,都得干一樣重的活。
黃洋畢業于鄭州大學考古系,入學前還是“白面書生”的他,在畢業離開工地一年多之后還是沒“白回來”。他說他永遠忘不了那些在工地上一邊穿著棉襖防凍一邊戴著草帽防曬的日子。
在考古工地,你可能還得做點其他“犧牲”。黃洋記得剛進考古系的時候,老師就說學考古得先學會兩件事,一是抽煙,二是喝酒。這并不是教唆大家“學壞”,而是因為考古工作往往要深入農村,工作中經常需要和當地的村民打交道,為了更好地跟他們溝通,酒和煙是必不可少的。張敬國教授談起當年發掘凌家灘的過程,至今還唏噓不已,他硬是豁出去和村長喝了一斤半白酒,醉倒在村口的稻草堆里,才得以順利地把挖掘項目進行下去。
憧憬考古工作的人可能都對皇陵大墓充滿了好奇心,但事實上,真入了考古這一行,可能一輩子也沒機會挖個大墓。因為國家政策的保護和技術的限制,除非是為了解決重大的歷史問題,或者是基礎建設中挖到了大墓,又或者墓室被盜需進行搶救性發掘,皇陵大墓基本都是不允許動的,這也就是為什么“考古總在盜墓后”的原因。
干考古工作最需要的是耐心,現場挖掘很枯燥,每個人都要在規定的范圍內,一點一點地往下挖。開始還能痛快地用手鏟鏟土,到了含文化遺物的地層可能就得一點一點用刷子刷了。有耐心還不夠,考古還得看運氣,運氣好的可能就發掘到了意義重大的文物,然后就成為了這一領域的專家;運氣不好的,可能重大發現就在離挖掘點1米遠的地方,和你擦身而過。
Step4:出山篇
“內功”“實戰”都過關了,考古達人就算是“練成出山”了。考古專業的畢業生最對口的就業去向當然是進入考古研究所,如果有了重大發現,就可以成為這一領域的專家。但是這往往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心血,在考古這一行,成功總是來得比較晚。
第5篇: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
這三位考古學家及其代表作是: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上篇》(注: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集選》,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蘇秉琦《陜西寶雞縣斗雞臺發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注:蘇秉琦:《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及《瓦鬲的研究》(注:蘇秉琦:《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鄒衡《試論殷墟文化分期》(注: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及《天馬——曲村(1980—1989)》[5]。
一
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上篇》是對小屯10座墓葬中出土的76件青銅容器所作的類型學研究。他研究青銅容器形態時,像處理人頭骨數據一樣,把每個容器視為由若干部分即形態元素組成的復合體,為了便于研究他對容器的各部位進行了劃分,并列表給出各部位的名稱。
在此基礎之上再進行容器型式的劃分,起到了明顯的規范作用。至于青銅容器的形式劃分,作者仍沿用《殷墟陶器圖錄》提出的容器的分類標準,有以下四條:
(1)以最下部作為第一數的標準:圜底000—099、平底器100—199、圈足器200—299、三足器300—399、四足器400—499,……
(2)每目內再按照上部的形態,定0—99的秩序,大致依口徑與體高相比的大小容器的淺深為準;口大的,身淺的在前;口小的,身深的在后;中間又以周壁與底部的角度,唇緣的結構等作更詳細的劃分準則:向外撇的居前,向內拱的居后。
(3)他種形式上的變化,如周壁的曲線,最大截面所在;耳、把、鼻、柄、嘴、流等,附著品的有無,往往構成該件器物的個性;這些變化并無秩序可循,只能隨著具有這些附著品的器物一般的形制排列;序數后加羅馬字,分辨型別,表示它們的個性。
(4)在形制上可以獨立的器物,即構成一“式”,照所列秩序,予一數字,以為標本,名為“序數”;每一式內再分若干“型”,用羅馬字標明,以類別形制相近而有小異的標本。
李先生的分類,首先將容器整體分解成上部“容量部分”和下部“底或足”,也就是非容量部分;器物下部為分類的第一標準,根據形態特征分為五類,即五“目”,器物上部的幾何輪廓由倒梯形—寬扁長方形—正方形—高扁長方形—正梯形的順序用01至99加以區分。首先,每種器物外輪廓的基本形態以三位代碼的形式標記識別,編碼打破了整體器形的限制,如在三足目中305、313、325、368都是鼎形器,中間的310卻是爵形器,這種編碼的實質是對器物形態分類的一種管理手段,而不是對器形整體演進的排序。其次,同一序數標記的器物,以更細致的外形要素的特征,特別是通過測量和計算得出的數據作為區分型別的指標。如248式觚形器,用腹徑比體高的百分數得到高寬指數,數據區間為10.4至30.48,每進五點即設一個新型,由此得到P、Q、R、S、T由粗矮至細長五個型別。這種用數據的區間范圍劃分型別進行分類的方法,和自然科學研究的分類方法頗為類似,比如按光波的波長由長到短分為紅外線、可見光和紫外線三類。李濟稱:“這樣分目排列的辦法只具有一個極簡單的目的:便于檢查。至于這個排列的秩序是否可以看出形態上的關系出來,卻是另外的問題”。舉個例子,如M388出土的觚形器標記為248Q,其中第一位數字(2)和第二、三區位的數字(48)均為序數,第四位羅馬字(Q)為型別。
蘇先生首先從全器的結構和腹足的形式即基本形制特征研究如何分類,繼而提出從產生原型去探討不同形制陶鬲譜系的問題。后來他在《瓦鬲的研究》一文中又對這四個類型鬲的相互關系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前后兩篇文章使用的類型符號及其指代的陶鬲的命名對照見下表。
《瓦鬲的研究》用單個大寫英文字母表示型,與之對應的小寫字母表示亞型,兩個大寫英文字母表示中間型,大寫字母加阿拉伯數字表示組別。作者有著鮮明的追求歷史過程的研究取向,以進化論的思想按發生學的原則論述了瓦鬲由產生而經歷從A演進至B,從B演進至C,進而演進至D并最終衰亡的過程。《瓦鬲的研究》一文“結論”里提出的陶鬲發生、發展及其譜系關系,充分表達了作者對于陶鬲的分類系統的認識。本文根據《瓦鬲的研究》一文“結論”的文字和附圖制成表5,結合這個表閱讀有關瓦鬲的論述就不難發現,作者先擬定出一條陶鬲進化的鏈條,每一類型下的組排列成具有演進關系的小鏈條,各個類型之間在通過中間型連接成更長的、較完整的鏈條。因此在陶鬲類型學研究中,作者排序的邏輯思維十分突出而分類的邏輯思維卻不很清晰,《陜西寶雞縣斗雞臺發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提出的分組標準,既含有排序又含有分類,推測作者原本打算先把標本區分開,待找到確切的證據后再將其排序,但實際上并沒有做到。
鄒衡《試論殷墟文化分期》的類型學研究對象,是殷墟各地點的發掘報告中對于作者而言有分期意義的陶器和銅器。該文首創的表述器物型式的語言范式,已為當今中國考古學界普遍使用,即用漢字標示“類”,大寫英文字母標示“型”,小寫英文字母標示“亞型”,大寫羅馬數字標示“式”。例如陶器的型式有三種情況,最多見的是劃分型、亞型、式三個層次,其次是劃分型、式兩個層次,最少見的是只用式別來區分。按照作者對17種陶器研究的先后順序,歸納出陶器的類型學研究的體系結構,這一體系結構如左圖一所示。從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這個類型學研究體系包括分型和分式兩部分核心內容,即分類和排序,換言之,分型就是分類,分式就是排序(注:陳暢:《試論考古類型學的邏輯和原則》,華夏考古,待刊。)。體系中的型式符號突出體現了標本之間的形態邏輯關系,但卻不能由型式符號得出標本的具體形態,也就是說,這種型式符號所代表的僅僅是一種抽象的關系。
如果要說《天馬—曲村》一書和《試論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在類型學研究方面的區別的話,前者是田野考古報告,首要的問題是準確真實地發表好資料,因此在這個前提下,報告編寫者著重考慮的是器物類型規范化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器物標本編碼體系和器物標本形態特征之間關系的探索,并以青銅容器和戈、圭、璋三種非容器作了實驗。
報告將青銅容器分為“底或襠”、“足”、“領、口或沿”、“肩”、“腹”五部分,分別將各部分的形態特征分類列表,并給予每類特征一個指定代碼,參見表6。所有青銅容器都按照以上五部分的順序用符號表示,形成該器物的型別編碼,這樣,一件青銅容器標本的整體基本形制特征的“標準化”通過其各個組成部分特征的“標準化”得以實現。例如如果將《天馬—曲村》與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的類型學研究相比較,就會發現二者均以便于發表資料和研究為目的,按器物形態組成要素的特征進行分類,用大寫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為代碼標示。鄒衡將器物的組成部位大致按照非容器部分和容器部分分開,先列出底、襠、足的特征代碼,之后再由從上至下的順序列出領、口、肩、腹的特征代碼,似乎也是受了李濟的影響,但又有別于李濟的劃分方式,如《天馬—曲村》中銅甗M606
9:2,型別為HFC01′,這件甗為弧襠、柱足,顯然“襠”是一種特殊的“底”,和“足”不能混淆,不同于《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將甗歸入“三足目”的做法。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天馬—曲村》的分類系統采用面分類的方法,《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則基本采用了線分類的方法,即分類模式的差別(注:關于面分類方法和線分類方法,陳暢:《試論考古類型學的邏輯和原則》,華夏考古,待刊。)。 二
考古類型學研究是研究者的思維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維能力和方法的體現。而抽象思維能力是個人接受社會化的一個重要條件,抽象思維能力的形成與提高是和學校的教育與培養分不開的。從三位考古學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學術成長過程的學科背景中可以領悟出他們各自的研究風格背后傳遞的學術思想。
李濟在清華學堂畢業后,先后在美國麻省克拉克大學學習心理學和社會學,后轉入哈佛大學學習人類學。“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國人的腦袋量清楚,來與世界人類的腦袋比較一下,尋出他所屬的人種在天演路上的階級來”(注:張光直:《人類學派的古史學家——李濟先生》,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來他對器物形態的研究深受量人腦袋的啟發,特別注重器物形態元素的組合方式,而其研究目的則深受美國人類學學科人本主義精神的感染,試圖通過器物分析探究社會文化而非考古學文化的變遷,即意在研究人。例如,他認為小屯出土的原始土質爵形器的器形脫胎于龍山文化,這一點符合文化傳承,滿足人們的審美要求;口部結構的演變則是工匠長期實踐不斷改進提高器物的實用功能的結果。李濟按器物形態元素特征分類的類型學體系,為早期的中國考古學的器物研究打下一個新基礎,并且一直影響到今天。
蘇秉琦畢業于北平師范大學歷史系,由于學習中國史學的經歷和史學傳統的學術背景,致使他認為“近代考古學的目標就是修國史”(注: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商務印書館(香港)1997年出版。)。他的考古類型學研究大都采取史學的研究方法,十分注重事件的因果關系及過程;而發軔于生物界的進化論理論,又恰好滿足了他以物的發展過程序列為研究目的的研究方式,于是進化過程和歷史因果關系,構成了他的研究特色。這種特色在《陜西省寶雞縣斗雞臺發掘所得瓦鬲的研究》1983年《補序》(注:蘇秉琦:《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里表現得最為充分。“系統的類型學理論,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在1903 年出版的《東方和歐洲古代文化諸時期》第一卷《方法論》中開始建立起來的。在我國,至三十年代,蒙氏的書有了兩種中文譯本;四十年代以后,蘇秉琦先生則在大量實際分析、綜合考古新材料的工作中,從中國考古的具體研究出發,為正確運用和發展這種方法論,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注:俞偉超、張忠培:《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編后記》,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超級秘書網
第6篇: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海龍囤 公眾考古 實踐
中國分類號:K8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4)01-103-107
在古代文化遺產與現代公眾之間,考古學無疑像一座橋梁,溝通古今。但這一切并不會無端端地發生,而且隨學科專業化的逐步加強,原本有趣的發現往往被轉述為生硬的研究成果而在小圈子內流傳,成為“考古方言”,很難成為“普通話”而走進公眾的視野,被廣泛認知。如何使文化遺產保護的成果惠及大眾,轉而使其得到更加有效的保護與利用?這屬“公眾考古學”(public archaeology)討論的范疇。
2012年4月-2013年1月,在對播州羈縻·土司遺存海龍囤遺址展開首次大規模考古發掘的過程中,我們依托考古現場,開展了一系列公眾考古實踐活動,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本文即擬以之為例,試對公眾考古相關問題進行初步剖析。
一
海龍囤位于遵義老城西北約30里的龍巖山巔,又稱龍巖囤,是一處宋明時期的羈縻·土司城堡遺址。遺址三面環溪,一面銜山,僅東西各有仄徑可上下,地勢十分險要,《明史》稱其為“飛鳥騰猿不能逾者”。遵義舊屬播州,公元9-17世紀為楊氏所據,世守其土達724年,共傳27代30世,即30人先后出任播州統領。據現有文獻,海龍囤始建于宋寶祐五年(公元1257年),而毀于明萬歷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的平播之役。1982年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晉升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11月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2012年度的發掘取得了重要收獲,概括起來有以下四點:
第一,基本廓清了海龍囤的整體格局。經過多年的調查與試掘,現已探明海龍囤有約6公里長的環囤城墻,其所圍合的面積達1.59平方公里。囤東有銅柱、鐵柱、飛虎(三十六步)、飛龍、朝天、飛鳳(五鳳樓)六關;囤西有后關、西關、萬安三關,彼此圍合的空間形成兩個甕城。囤頂平闊,“老王宮”和“新王宮”,是其中最大的兩組建筑群,面積均在2萬平方米左右。另有軍營(俗稱“金銀庫”)、敵樓(如“四角亭”與“繡花樓”等)、校場壩等遺跡。
第二,發現環繞“新王宮”的城墻,框定了“新王宮”的范圍,基本厘清了其格局、性質和年代。環“宮”城墻長504米,其圍合的“新王宮”面積達1.8萬平方米,探明其內建筑20余組,并對其中的F1、F2、F7、F8、F9、F10、F11等數組進行了重點清理,出土青花、青瓷、勾頭、滴水、石構件、礌石、彈丸、鐵鎧甲片、石硯臺、錢幣等遺物上萬件。發掘揭示,“新王宮”具有中軸線、大堂居中、前朝后寢等特點,與衙署的布局一致;而明代文獻中亦明確稱其為“衙”、“衙院”、“衙宇”等。因此,“新王宮”實質上是一處土司衙署遺址。從出土遺物看,它是一組明代建筑群,嘉靖、萬歷時期是其鼎盛時期,最后毀棄于萬歷年間的大火。
第三,基本確認了石、磚、瓦等建筑材料的來源。為了解磚、瓦和石料的來源,對海龍囤及其周邊展開了針對窯址和采石場的調查和清理,發現民間傳說的“采石場”確系一處采石遺跡,清理出采石所遺的各類楔眼上百個,與“新王宮”建筑石材上所見楔眼完全一致。另在“老王宮”東北角發現窯址數座,對其中一座進行清理(Y1),系一座明代磚窯。由此可知,建囤過程中石材、磚瓦等建筑材料均就近取用。
第四,通過調查與發掘,對海龍囤的性質有了更深的認識。海龍囤是一處融保衛國家利益與維護土司家族利益于一體,集關堡山城與土司衙署于一身的羈縻·土司城堡。特殊時期,堅不可摧的海龍囤是土司的重要軍事防御據點;和平年代,風景秀麗、氣候怡人的海龍囤則可能成為土司的別館離宮。從南宋中期開始,穆家川(今遵義老城)一直便是楊氏統領播州的政治中樞,而不久之后修建的海龍囤與之并行不悖,前者為平原城,偏重于政治,后者為山城,偏重于軍事,它們一起構成了播州楊氏完備的城邑體系。
發掘的意義表現于:
第一,海龍囤特別是“新王宮”的整體格局與明故宮契合(同時也保存了本地建筑的一些特點),反映了土司在意識形態上的國家認同,這種一致性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有效維護了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
第二,海龍囤是我國羈縻·土司制度的實物遺存,它完整見證了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政策由唐宋時期的羈縻之治到元明時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開始的“改土歸流”的變遷,它的發掘為從考古學的角度深化中國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討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視角。換言之,其對推行羈縻之治以來,中央如何開發、經營與管理西南疆,邊地又是如何逐步漢化而與華夏漸趨一體等問題的深化有著積極的意義。
第三,這處設有衙署的軍事屯堡,是中國西南規模最大、保存最好、延續時間最長的羈縻·土司城堡,它“利用地形、融入地形”的建筑特點,對中國西南同期以及后來的同類建筑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四,海龍囤的發掘可能引發考古學界新的學術關注點,即將視線從中原的、早期的遺存更多的投向邊地的、民族的、晚期的遺存中來,從而拓展考古研究的領域,并可能有益于考古學方法與理論的發展。
該發掘榮膺201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并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1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俗稱“六大發現”),在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二
如何在這樣一個遺址上開展公眾考古活動?首先牽扯到我們對“公眾考古學”的理解。
多數人將“公眾考古學”理解為考古科普。中國考古學的科普工作起步較早,曾以“考古學的大眾化”示人,但現在流行的“公眾考古學”卻是一個舶來品,內涵也較前者豐富。換言之,考古科普只是公眾考古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到底何為“公眾考古學”?
20世紀70年代,由西方考古學家對考古學與社會的相互關系以及考古學家社會責任的思考所引發的討論,最終產生了考古學一個新的分支——“公眾考古學”(puhlic archaeology)。它將焦點聚集在“我們為什么要了解過去”,“過去對我們而言到底意味著什么”等責任感問題上,因而超越了對“過去到底發生了什么”的學理探討而上升到對“過去為何發生某事及其對于當下的意義”的闡釋的哲學層面,以及具體踐行活動中。其目的是通過參與式的實踐,調合各利益相關者的矛盾與利益,從而助益文化遺產的保護。
問題在于,誰是“公眾”?他們又如何能為文化遺產保護貢獻力量?英文的“public”一詞,是一個與私人領域對立的公民集合體,譯作漢文,有“公共”(國家及其公共機構)和“公眾”(彼此間有爭論并消費文化產品的大眾群體)兩層含義。相應的,“puhlic archaeology”也存在“公眾考古”和“公共考古”兩譯。雖然強調的對象各有偏重,但都涉及了民眾、考古學家和行政部門這三個主體。公眾考古的實踐,實際上就是這三方圍繞著考古資源的最優配置展開的一系列博弈活動。考古學家通過推動行政部門的制度供給,達到建立和完善考古資源保護和管理的相關法規的目的;通過與民眾的合作,使其利益在考古活動中得到體現,從而實現其了解自身過去的公共權力。
關系錯綜復雜,但對考古者而言,公眾“這一名詞只是方便用來指代一個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為職業的人群。在我們的語境中,‘公眾’只是因非專業考古學者這一特征而集合成的一個概念”。具體到某一個遺址中,我們認為除了在此開展工作的考古者以外的所有群體,包括外來的考古學家均可稱之為“公眾”。進而言之,在具體考古活動中,凡發掘團隊與其自身以外的所有“公眾”的互動,均屬公眾考古的范疇。此時,開展考古活動的遺產地就變成了“交流”與“解釋”的一個重要場域,來自遠古的信息在此破解,在此擴散,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得到適當滿足。被視作公眾考古學核心思想的“交流”、“解釋”與“考古學利益相關者”均在此場域中得以呈現。相對于博物館、陳列室等傳統展示渠道,考占現場則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三
2012年5月起,土司城堡海龍囤遺址的考古現場就變成了這樣一個重要的場域。借配合“申遺”而對海龍囤展開大規模考古發掘之機,經過周密的籌劃,我們在海龍囤考古現場開展了一系列公眾考古的實踐活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作為遵義重要旅游目的地海龍囤,因為與土司政治及其生活的密切關系,對包括考古學家在內的公眾都充滿誘惑,這是相關活動能順利開展、各方利益得以體現的重要前提。加之此次考古工作是在“申遺”背景下開展的,地方政府對此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并積極投入到考古活動中來。匯川區人民政府通過專題會議、現場辦公、文件等方式,極力推進考古發掘工作的順利進行,行政部門和考古者的利益均得到充分體現。而針對專業化和公眾直接參與的不和諧,我們則通過講座、媒體宣傳、現場體驗等方式,讓公眾了解自身過去的公共權力得到部分滿足。
首先,在中國第七個“文化遺產日”之際,策劃了“親歷考古,觸摸四百年土司生活”的系列公眾考古活動。于6月10日文化遺產日當天,邀請著名學者在貴州省圖書館舉行主題為“聆聽海龍囤”的大型學術講座,并從聽眾中產生70余名幸運者,于次日與考古者一起登囤,在考古現場“觸摸海龍囤”。此后又組織了黔籍知名畫家進海龍囤,用他們手中的畫筆描摹400年前的土司生活的“畫中海龍囤”活動;組織遺址所在地的高坪鎮中小學生將課堂搬至考古現場的“愛我家鄉,考古進課堂”活動;以及與遵義市政協共同組織了政協委員參觀考察與文藝演出相結合的“走近考古,支持申遺”的活動。當考古工作接近尾聲時,我們邀請了全國20余位知名的考古學家親赴海龍囤,并召開現場座談會,請他們為海龍囤的發掘、研究與保護出謀劃策,此舉在“交流”中實現了海龍囤價值于更大范圍內的傳播。如果說“聆聽”只是一個引子,其后開展的“觸摸”則是活動的重點。包括外來考古學家在內的“公眾”通過現場的觀摩與體驗,對海龍囤有了更為深入的認知,相關感受又通過他們傳達給更廣的“公眾”。
但能到現場“親歷考古”者畢竟少數,如何進一步調適專業化發掘與公眾參與的不和諧?無疑,通過媒體與公眾形成互動是最佳的選擇。因此,在“親歷考古”活動之外,我們與媒體開展了密切的合作,使海龍囤的最新發現得以及時呈現在公眾面前,盡可能滿足了其解自身過去的公共權力。通過媒體與公眾的互動,從“非專業人士的普及性利用和專業研究者的提高性利用”兩個方面展開:前者是報紙、網絡、電臺及電視臺的記者在田野一線采寫稿件,在相應的媒體持續刊播;后者則是發掘者親自撰寫“考古手記”,對相關發現作出權威解讀,在當地媒體連續刊登。其廣度、深度及長度,貴州此前所未有;所取得的社會影響也是空前的。據不完全統計,在發掘期間及獲獎前后的近一年時間里,全國各媒體共推出關于海龍囤的各類報道140余篇(則),曾三上央視、三上“貴州新聞聯播”、數次登省內媒體頭版,并有多篇深度解讀海龍囤考古的大版塊文章,使海龍囤的最新考古成果得以迅速呈現在公眾面前,甚至出現讀者收集“考古手記”登囤請教的插曲。
國內外近百家媒體通過報刊對海龍屯的考古發掘進行了報道;海龍屯聲名鵲起,成為國內外考古界關注的焦點。
而基于考古發現的專題學術講座,實現了另一個渠道的傳播與互動。第一期發掘過程中及發掘結束以后,我們在海龍囤、遵義、北京和貴陽舉行了多場面對不同聽者的學術演講,廣受好評。如9月22日,應遵義“名城大講壇”之邀,在遵義市圖書館舉行《海龍囤:兩千里疆土家與國》的專題學術講演,數百名聽眾出席。10月16日,在“中國海龍囤·婁山關國際戶外挑戰賽”舉行期間,在海龍囤巔向來自澳大利亞、新西蘭、臺灣、香港、北京等地的約200名運動員、教練員講述海龍囤故事。2013年1月9日,在北京舉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1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頒獎儀式上發表《貴州遵義海龍囤遺址2012年度發掘》的學術講演。2013年4月11日、5月20日,海龍囤遺址榮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后,走進社區、走進校園,與社區居民和大中學生進行交流與互動,受到普遍歡迎。
所有“公眾”中,當地村民無疑是與遺產地關系最為密切的利益相關者,他們的利益如何在考古活動中得以體現?相當部分當地村民在考古工地做工,在增加收入的同時也完成了與海龍囤事實上的“親密接觸”。部分村民則長期在海龍囤從事牽馬、導游、餐飲等旅游服務,考古工作開展后劇增的游客量也增加了他們的經濟收入。這些都是考古活動所帶來的直接后果。此外,發掘期間,針對當地村民的貧困狀況,我們聯合媒體通過微博發起“考古探秘+公益慈善”活動,使城市中人在進行海龍囤考古探秘的精神之旅的同時,也能對當地貧困村民予以捐助。這一活動被新華社等媒體譽為“走出文化扶貧新路”,予以高度評價。更有當地村民寫詩傳揚此舉,稱“楊雀記得千年樹,乞丐記得賢惠人”。我們相信,當地政府會充分考慮村民的利益訴求,未來海龍囤“申遺”一旦成功,他們的生活條件將會得到進一步改善。
三
貴州具有影響力的公眾考古實踐始于2008年出版的《赫章可樂:2000年發掘報告》。為便于普通讀者的閱讀,該書在傳統考古報告里開設了一些小窗口,用通俗的語言來描述相關章節的內容,即在“考古方言”里穿插了“普通話”的環節,使其曉暢易讀。這一嘗試引發了圈內圈外的廣泛討論,先后有約10篇書評公開發表。貴州省文物局從2011年開始策劃的“貴州文化遺產叢書·考古貴州系列”,計劃推出解普及性讀物8本,將貴州考古的最新成果用普通大眾能夠接受的方式予以刊布,即用文學化的筆觸來表述嚴謹的學術成果,從而令其在更大的世界產生更為廣泛的影響。叢書目前已完成撰稿工作,預計2014年初能推出部分成果。這兩項實踐,應屬“考古科普”的范疇,無疑也是公眾考古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而以考古現場為依托,開展深度的、廣泛的公眾考古活動,海龍囤開貴州先河。基于海龍囤的公眾考古實踐,在面對面或通過媒體與大眾的互動中回應了社會的關切,盡可能調適了各方利益,對文化遺產保護有著正面的、積極的意義;同時強化了考古學科存在的價值,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效應。
第7篇: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相對年代,絕對年代,參照點
中圖分類號:K85;N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578(2011)01-0039-04
On the Relative Chronology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of Archeology
ZHAI Shengli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relative chronology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is not the precision of time but the reference points. The reference point of absolute chronology may be a time point or time zone which is specifically known; however, the reference point of relative chronology must be a time point or time zone which is not known by now.
Keywords: relative chronology,absolute chronology, reference points
考古學是一門關于時間的科學。在整理考古發掘資料時,最基本的環節就是對考古遺物和遺跡的年代加以判定,這就是考古年代學。年代學的研究涉及一對基本概念:“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對于這對看似簡單的概念,學者在理解和使用的過程中卻多有分歧。筆者不揣簡陋,嘗試厘清二者之間的關系。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 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基本含義
對于“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基本含義,學術界還沒有形成整齊劃一的定義。學者們對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爭議,多體現在適用范圍與精確度方面,主要觀點大致分為以下幾種。
一些學者將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研究限制在考古學范疇之內,他們認為相對年代是考古學研究的一項特定內容。有學者認為[1]:相對年代是指各種遺跡和遺物在時間上的先后關系,絕對年代是指遺物和遺跡形成時距今的具體年代。這也是多數考古學家的觀點。
考古學上,人類的歷史遺存按形制分類,形制相近或相同的遺存歸為一類,以某一方面的特征為標準來確定它們的標準型式。然后按照型式差異程度的遞增或遞減序列,排出一個“系列”,這個“系列”便代表該類遺存在時間上的演變過程。各遺存在這個系列中的位置,就表明了它們的相對年代。“相對年代”的研究就是通過考察多個考古遺存在演變系列中的位置,來判定其相對早晚關系。
另一些學者則將相對年代的研究推廣至歷史學范疇。《辭海》認為:“在歷史上可以確定的具體年代,稱為絕對年代。不能確定具體年代而僅能比較和推定先后時序者,稱為相對年代。”[2]持此觀點的學者不再限定相對年代的研究對象,他們認為考古學與歷史學都是關于時間的科學。無論對于考古遺存還是歷史人物、事件,如果只能比較先后序列而不能確定具體的年代,都可以稱為相對年代。
劉華夏先生認為:“絕對年代是以現今或與現今距離可知的定點為起點,用公認的時間單位(如一年、一世紀等)計算的年代。相對年代則不同,其既無起點,亦非用時間單位來計算,僅僅指甲早于乙而已。”[3]劉先生對絕對年代的界定是比較中肯的,但其關于相對年代的看法卻存在問題。遺存之間既然有早晚關系,那么至少是互為時間起點的。
也有學者從時間軸方面對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作出定義。曹書杰先生認為:“絕對年代是將歷史事件置于時間軸上(例如公元前1975年)或時間區內(例如12 000~10 000年)的紀年法,年代可以直接測定并用阿拉伯數字表示。所謂相對年代紀年法,就是把一段時間、事件或對象安插到已經確定好的時序之內的紀年法。”[4]這種說法較為形象,但其對于相對年代的界定卻較為模糊。
以上幾種觀點都有合理之處,然而又都存在不足。筆者認為二者的概念可以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形式。從狹義方面:相對年代是指一系列考古遺物和遺跡的相對早晚關系;絕對年代是指某一個或某一系列考古遺物和遺跡距今的年代數據。從廣義方面:相對年代是指歷史上的人物、事件或者遺存之間的相對早晚關系;絕對年代是指歷史上的人物、事件或者遺存之間距今的年代數據。
二 兩者之間的關系
在相關論述中,不少學者都曾涉及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關系問題。學者們多將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區別理解為時間精確度的差異。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有不妥之處。
1.二者的命名與時間精確度無關
為了說明絕對年代和相對年代的聯系和區別,有學者曾經提出“具體年代”“精確年代”等概念。有人認為絕對年代就是具體年代,相對年代就是大致年代。曹書杰先生將歷史年代分為絕對年代、具體年代、概括年代、穩定年代、約定年代等幾種類型。他認為絕對年代是指那些已精確到某一具體年份的月和日的時間結論,而且是確定不疑的,也可稱為精確年代[5]。
馬承源先生提出青銅器絕對年代和相對年代的區別在于時間幅度的不同。馬先生認為:“絕對年代是青銅器鑄造的年代,或非常接近于鑄造的年代。相對年代是指用一定的時間幅度彼此對比而借以決定的期限。”[6]馬先生所謂的絕對年代是指青銅器鑄作于某一時間點,而相對年代則是指對比研究以后所能確定的時間段或時間區。二者精確度有所區別。
林先生曾說:“考古發掘中的層位,只能用以判斷遺物的相對早晚關系,對遺物的具體年代則只能提供大致的估計。”所謂“相對早晚關系”無疑是指相對年代,那么“具體年代”應該是指遺物的絕對年代[7]。彭裕商先生則認為:“根據確切年代或其他有關內容的銘文資料和考古學地層關系,就可以知道某個型式的器物的絕對或大致的年代。”[8]此處的“絕對的年代”相當于確切年代,而“大致的年代”應該指相對年代。
以上專家所論雖不無道理,卻有不妥之處。例如:“高盧人攻占羅馬是在羊河戰役后19年,留克特拉戰役前16年,與斯巴達人批準同波斯國王簽定的安達爾西達斯和約同年。”這些年代是通過幾個重大歷史事件的相互對比系聯而得出的,顯然屬于相對年代,然而它們都是非常具體的數據。人類舊石器時代開始于三百萬年前,雖然三百萬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數據,但仍然屬于絕對年代。所以筆者認為絕對年代與相對年代的本質區別并不在于二者精確度的高低。
2.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所選參照點不同
相對年代之“相對”,在于必須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考古遺存或歷史事件相互比較才能得出其先后關系。而絕對年代之“絕對”應指某遺存或事件可以與今天的紀年系統產生關聯,進而能表明它與今天的時間距離。正如李雅書先生所論,人類歷史上最古老最直接的紀年方法只能是相對紀年:即把要記的事件同前后已知的著名事件聯系起來,用它們之間的距離來標明該事件發生的時間。例如:“特洛伊陷落后六十年,彼阿提亞人定住于現在的彼阿提亞。再過二十年,多利亞人和赫丘利的子孫們占領了伯羅奔尼撒半島。”[9]這里用著名的特洛伊戰爭為紀年起點,顯然是一種相對紀年。
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經使用的紀年方法主要有帝王紀年、干支紀年、年號紀年、大事紀年等幾種形式。帝王紀年以某一位帝王即位時間為起點,干支紀年以天干、地支組合為周期循環運轉計算,年號紀年以某一帝王的年號為紀年起點,而大事紀年則以過去某著名事件為起點計算年數。這些紀年起點都是主觀選擇的結果,先民們將后來的事件與主觀選擇的起點相聯系,所得即為相對年代。現在通行的西方公元紀年,以耶穌誕生為紀年起點,從科學上并無道理可言。其實公元紀年與其他紀年方式一樣也都屬于相對紀年,那么可以說,包括公元紀年在內的一切年代都可以被稱為相對年代。
另一方面,一切被使用的紀年在當時人看來肯定都屬于絕對紀年。因為被當時人選作參照點的事件或者時間在他們看來肯定是明確無疑的,這是該事件或者時間被當做參照點的前提。今天也是如此,公元元年即耶穌誕生的時間,這一點必須是公認的。假如由于歷史的變遷,今天的人已經無法了解某種紀年的使用情況,歷史上的絕對紀年就會變成今天的相對紀年。考古學與歷史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進行年代學的研究。首先要了解歷史遺存或者事件的相對年代,然后將相對年代轉變為與今天相關聯的絕對年代。
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都是將遺存或歷史事件置于歷史發展的時間軸之上,其區別在于參照點的不同。絕對年代以當下或其他能夠與當下產生關聯的時間為參照點,目的在于了解某一遺存或事件與當下的時間關系。而相對年代則可以用當下以外的未知時間為參照點,將數個遺存或事件聯系起來,以標明它們的先后關系。每一個記錄下來的年代,只有明確它們在今天的紀年體系中所占的位置,這個年代才有意義。也就是必須把相對年代換算成今天通用的紀年體系的年代,相對年代才能起到紀年的作用。這樣,這個相對年代即變成了絕對年代。作為判定絕對年代的紀元,“公元”顯然并非唯一可能的起點。公元起點是約定俗成的,因此最終推斷出來的絕對年代可能有好幾種表示方式[10]。
在進行考古學斷代時,考古學家經常將遺存與某一王世年代進行擬合。彭裕商先生認為:“指出銅器的絕對年代,即將某器具體歸入某王世。”[11]而杜勇、沈長云兩位先生則認為,彝銘記事內容所在的王世即西周金文的相對年代[12]。
以上專家的兩種說法都是有道理的,將遺存與王世擬合后的年代既可稱為相對年代又可稱為絕對年代。例如漢武帝元鼎三年,當我們對漢武帝或漢代一無所知時,它只表明該年比元鼎元年晚了三年,其實是一個相對年代。只有當我們弄清楚該年代與公元紀年的對應關系,或者漢武帝在位的大致年代,這個相對年代才能被稱為絕對年代。當然,僅知道漢代在中國古代史上的大致位置,也足以將元鼎三年稱為絕對年代,時間精確度的高低并非決定因素。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都是相對而言的,二者之間并沒有十分嚴格的界限。它們都是將歷史遺存或事件置于時間軸上,其區別在于所選參照點的不同。絕對年代的參照點是當下已知的某個時間點或時間段,相對年代的參照點則可以是當下未知的某個時間點或時間段。
參 考 文 獻
[1]段小強,杜斗城.考古學通論[M].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7:15-16.
[2]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歷史\考古\世界史分冊[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310.
[3]劉華夏.金文字體與銅器斷代[J].考古學報,2010(1):43-72.
[4]王乃新.羅馬年代學與卡皮托執政官表[G].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9:139-140.
[5]曹書杰.中國歷史年代學若干問題思考[J].史學集刊,1991(2):1-5,76.
[6]馬承源.中國青銅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09-410.
[7]林.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C]//古文字研究(9).北京:中華書局,1984:148.
[8]彭裕商.組卜辭分類研究及其它[C]//古文字研究(18).北京:中華書局,1992:46.
[9]李雅書.古羅馬的歷法和年代學[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86(2):40-50.
[10]劉華夏.金文字體與銅器斷代[J].考古學報,2010(1):43-72.
第8篇: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
編者按:音樂考古從文玩鑒識到樂音追蹤,從研究之手段到學科初創立,及至于新世紀以來的人才輩出、專著涌現、機構設立、群賢輻輳。但繁榮的學科現實更需要學界理性的思考:今日之“音樂考古學”,歷史的脈絡如何梳理?繁榮的基石是否牢固?學術的困局與研究的縱深是什么?學科的未來趨向又將何往?……面對諸如此類問題,我刊特約請五位業內專家以不同的視角予以探討。
音樂考古學在中國,有著特別豐厚的文化和學術基礎,并且成果豐碩。
在宋人的“金石學”中,已涉及到出土古樂器的研究。如北宋呂大臨的《考古圖》,趙明誠的《金石錄》,著錄中不乏古樂器的拓本。這些樂器主要是鐘和磬之屬,據其材質,即所謂的“金”與“石”。其中最有意思的事件,是當時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俅的《嘯堂集古錄》和王厚之的《鐘鼎款識》,都注意到了當時出土于湖北安陸的2件楚王含章鐘(又作曾侯之鐘);其中薛氏不僅著錄最早,還研究了2件編鐘上的樂律標銘“卜翆反 宮反”和“穆商 商”,正確地指出其是用來標示“所中之聲律”。至于銘文的確切含義,他一時還說不清楚。1978年湖北隨縣曾侯乙編鐘出土,這個千古謎底才被揭開:“卜”為“少”字的減筆之形,為某個音名的前綴術語,意為該音的高八度;“翆”即音階第六級的“羽”在當時的寫法;“反”亦為當時的音樂術語,為“半”、“半律”的意思,是表示高八度的后綴專用辭。如此,“卜翆反 宮反”的含義便一清二楚:“(此音為)高八度的羽音之再高八度”。又據曾侯乙鐘中層一組1號等鐘銘文,可知當時楚國音律體系中有“穆鐘”一律;其音高,在曾鐘中層三組2號鐘背面左鼓銘文:“穆音之宮穆音之在楚號為穆鐘”中有明確的對照,因知楚國的穆鐘一律就是曾國的“穆音”律,其音高相當于今日國際標準音高的bB。如此,“穆商 商”意即“楚律穆鐘(或曾律穆音)商調之商”——這一曾讓人們費盡心思猜測的謎底,豁然于眼前。
應注意的,還有北宋沈括在他的《夢溪筆談》中,提到了古代樂鐘的音樂音響性能:
古樂鐘皆扁,如盒瓦。蓋圓鐘則聲長,扁則聲短。聲短則節,聲長則曲。節短處聲皆相亂,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為圓鐘,急扣之多晃晃爾,清濁不復可辯。
大量的出土文物表明,大約在西周早期,鑄鐘的工匠為了節約當時無比貴重的“金”——銅料,抑或也是為了方便樂師的編鐘演奏,已經發明了“一鐘二音”的造鐘技術和雙音鐘的調音技術。他們把編鐘的鐘體設計為“合瓦形”(沈括所謂“盒瓦”)——即兩塊弧曲朝外的瓦對合之狀。這樣的鐘體,在人們分別敲擊其正鼓部位(即鐘體兩面近于口部位弧曲的最高點)或側鼓部位(即鐘體兩面近于口之弧曲最高點與“合瓦”對接點“銑角”的中心部位),可以獲得兩個不同音高的樂音。雖然,當時沈括還不可能認識到這個中國古代音樂科學上重大發明的物理學含義;但他已經發現,先秦的編鐘都是合瓦形的“扁鐘”;扁鐘的一大發音特點是余音較短;而若將編鐘鐘腔設計為正圓筒形,編鐘的余音就會很長。他還發現,余音的長短,直接影響到編鐘的音樂性能:在實際的音樂演奏中,如果人們演奏節奏較快的樂曲時,整套編鐘就呈現了一片混響之狀,音樂的旋律被破壞:即沈括所謂的“急扣之多晃晃爾,清濁不復可辯”了。沈括對樂器的音樂音響性能的研究,顯然進入了對音樂本體的探索,是今天的樂器學、音樂聲學所要探討的問題。
宋人的金石學著錄和相關的音樂理論著作,盡管已涉及到先秦的一些鐘磬樂懸等古樂器,乃至已在探索它們的音樂和音響方面的物理學性能;但這些研究還都是零散的,往往局限于某一側面的。他們注意的重點,顯然也不在于探索音樂藝術的歷史問題。并且他們的研究,還不具備運用今日音樂學和考古學的基本理論、方法的可能性。故還不能算是音樂考古學的研究。作為一門自有研究目的、對象、方法的獨立學科,中國音樂考古學還得在金石學的卵翼下,經歷八百余年的漫長歲月。
北宋以后的青銅器著錄和研究,仍以銘文和文字訓詁為重點。自20世紀初以來,王國維、郭沫若、羅振玉、容庚、于省吾、方溶益、吳大瀲、唐蘭、徐中舒等一大批學者皆有相關青銅樂器的論著。首先打破這一局面的是王國維、郭沫若等人,他們開始以研究社會歷史的眼光來解讀商周青銅樂鐘,并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王國維的《觀堂集林》中,有多篇關于青銅鐘類樂器的重要研究。如《夜雨楚公鐘跋》,他不僅確認了孫詒讓對楚公逆镈“逆”字的考釋,認為其人即文獻所說的熊號;并由此進一步對楚之中葉的歷史做了較精辟的闡發。王國維研究的對象,同樣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古樂器;但他的研究目標,已轉向探索商周社會發展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擺脫了北宋以來把音樂文物僅僅作為“古玩”加以著錄、研究的傳統。特別是在《古史新證》中,面對當時中國如火如荼的田野考古事業以及學術界盛行的“疑古”思潮,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
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
字里行間,已足見他對現代考古學的重視。“二重證據法”成為中國史學領域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郭沫若的巨著《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收錄了511件青銅器。針對兩周的不同特點,他將西周銅器按王世排列,對東周銅器則按國別分類;并將青銅器的發展分為濫觴期(約相當于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后期及西周初至昭、穆之世)、開放期(恭、懿至春秋中期)、新式期(春秋中葉至戰國末年),使傳世青銅器第一次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系,成為可供古史研究之用的科學資料。他提出的標準器斷代法,對于中國青銅器的研究同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筆者的《中國青銅樂鐘的音樂學斷代》中以編鐘音階結構特征斷代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借鑒了此法:以各時期重要編鐘的音階結構做為標準尺,建立“刻度”;隨著材料的逐漸豐富,可使“刻度”逐漸細密;以此標尺為基礎,將新發現編鐘的音階與相應“刻度”進行比對,以判斷其相對年代。不過,王國維和郭沫若們的這種研究所要實現的目標,卻與音樂藝術本身并無多大的關系。故從根本上說,他們的研究,仍難算是“音樂考古”。
第9篇: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認知考古學;新石器時代;祭祀遺跡;文明起源
普遍意義上講,認知考古學是通過考古遺存來研究人類認知活動的一種理論方法,具體來說就是根據人類物質文化遺存所凝聚的象征意義來研究古人的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1]。肯德.弗蘭那利和喬伊斯.馬庫斯則將宇宙觀、宗教、意識形態和肖像作為認知考古學研究的合適課題,并認為這四個領域已基本涵蓋了認知考古的大部分課題[2]。宗教祭祀作為其中之一,是最能反映遠古先民的思想意識的有效途徑。我國新石器時現的那些祭祀遺存就是人們祭祀天地、祖先等祈求生存發展的考古學遺跡。
一、現有考古學資料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境內已發現的祭祀遺跡主要分布在遼河流域、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包括祭壇、祭祀坑、廟宇、積石冢、石圈遺跡和少數房屋內繪畫遺跡等。
遼河流域祭祀遺跡以牛河梁女神廟、東山嘴石砌建筑基址和胡頭溝石圈遺跡為代表,年代基本處于紅山文化晚期。黃河流域多以祭祀坑和“石圓圈”為主要發現,如青海大華中莊卡約文化墓地發現的2處祭祀坑、西安客省莊文化發現的6座人畜埋葬坑、洛陽王灣和鄭州大河村遺址發現的人骨堆葬坑以及青海羊洼坡遺址[3]、甘肅大何莊遺址和永靖秦淮家齊家文化墓地等處發現的“石圓圈”遺跡現象。祭祀坑有人祭、畜祭和人畜祭,有的坑內也堆有糧食并常伴出有完整的動物骨架和陶器。長江流域則以太湖良渚文化祭壇更為重要,發現的最具代表性的祭壇有瑤山祭壇、匯觀山祭壇、福泉山祭壇以及寺墩祭壇,除此之外還有江蘇吳縣張陵山、浙江余杭反山、杭州莫角山等地的“圜丘”,另外在湖北房山七里河遺址的一處半地穴房址中發現有一個完整人顱和成排斜線分布的顱頂碎片。在內蒙古大青山西段發現的祭祀遺跡也以祭壇為主,主要有莎木佳祭壇、黑麻板祭壇和阿善祭壇,其中前兩處祭壇的形制基本相同,為繞近圓形土丘一圓形石圈,后者為圓錐形石堆,平面近似呈弧線形[4]。
二、祭祀活動
從原始宗教的角度考慮,祭祀活動是人類對自然神靈的崇拜,都是人類為了得到上天的庇佑、祈求風調雨順或長久的生存和發展,因此賦予了這些祭祀遺址多重的祭祀內容。
原始農業萌芽于新石器時代并自此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人類對自然神的崇拜特別是對農神、谷神、天神、地母神和山神的崇拜成為祭祀活動的主體。在遼寧喀左東嘴山發現的祭壇遺址,位于該山梁中央平緩突起的臺地上,平面呈長方形,根據布局可將其分為:中心大型方形基址部分,基址內分布大量石塊,伴有玉璜、石彈丸、陶器碎片和少量骨料等遺物以及大片紅燒土遺跡;東西兩翼部分為相互對稱的石墻基,墻基外有石堆分布;前端部分由石圈形臺址和多圓形石砌基址組成,石圈形臺址東側有孕婦造型的雕塑出土,后端發現有長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在房址東墻中端有一埋葬人體骨架和打磨精良的非實用性石斧的長方形土坑。不難看出,這是一座由祭壇、祭臺組成的宗教祭祀性場所,將祭壇修建于凸起臺地上正是為了拉近與天的距離,發現的紅燒土表明火祭是當時祭天的方式之一,紅燒土面積之大則可說明該處祭祀地點舉行過多次儀式。而祭壇內大量的石塊應與祭祀地母有關,孕婦造型的雕塑則是對女性生殖的崇拜,也是傳世文獻中設壇祭祖的原形,種種現象都反映了該祭壇也同樣是禮地的場所。
內蒙古大青山西段發現的三處祭祀遺址,從形制和結構上分析似乎與當時人們的物質生活并無聯系,近年來,綜合考古學材料許多民族學家認為敖包起源與祭壇在形制、功能和祭祀形式上有許多相似之處,按《祭壇與敖包起源》一文:“兩者之間應具備更深層次的淵源關系――首先,在修建時都選取高出地面的臺地、山丘;其次,在外形上均為用石塊壘起的圓形建筑,酷似山峰;再者,在功用上均為祭祀為主要功能;第四,二者最初都已祭祖活動為主;最后,從原始宗教儀式里的祭壇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進程才發展成敖包”。
太湖地區的祭壇遺址則多與墓地聯系在一起。發現于浙江省的瑤山祭壇就位于該遺址墓葬區的北部,13座墓葬分列南北兩側打破祭壇,出土隨葬品中女性色彩濃厚的紡輪、玉璜等多見于北側諸墓,而代表男性的琮、鉞和三叉形飾多則見于南側墓葬。由此可見瑤山祭壇不僅是一處祭祀場所,也可能是當時巫祝死后埋葬的專屬墓地。反山祭壇的情況于此也十分相似,但由于發掘失誤,未能清晰地辨認出來。針對這種墓葬打破祭壇的現象,許多學者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其中有兩種觀點截然不同:以蘇秉琦先生為首的一些專家認為,墓葬的年代要晚于祭壇的廢棄年代,兩者可能并非為同一代人所修建使用;另一派意見則堅持兩者就是同一代人所為,并認為祭壇是為墓葬服務的或者說墓葬作為祭壇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承擔了特殊的功能。而在趙陵山、福泉山發現的祭壇遺址卻多是與墓葬共存,以祭壇為中心,墓葬繞之。
牛河梁遺址的積石冢和女神廟是紅山文化大型祭遺跡與墓葬的第一次明確發現和正式發掘。三座積石冢自東向西依次分布,冢內帶有某種“墓祭”含義的圓壇,這是我國較早的墓祭資料,肯定了原始墓祭的存在及其出現的大體時間。廟中還出土了大量的泥塑女性雕像,形態各異,大小不一,尤其引人注目的出土的一尊較為完整的女性頭像。有研究表明,這些人像可能象征的是當時社會上的權勢者或收到崇拜的祖先,出土數量如此之多足以表明是古人為求得氏族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而進行的女性生殖崇拜。
三、祭祀與文明起源
中國文明起源經歷了從單一地區起源論到多地區起源論的成長歷程,隨著祭祀遺址的發現,大量有關祭祀的考古學資料使其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越來越重要。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展開的對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討論,仍有一部分學者講禮制性建筑作為文明起源的要素之一。如張光直先生將青銅冶金、文字、國家組織、廟宇和大型建筑成為文明初期的一般標志,并認為中國的許多文明標志都與巫術息息相關;安志敏先生則把文明的特征和要素總結為國家、城市、金屬冶煉和禮制性建筑。但也有學者認為,文明是文明諸要素累積在一起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不可單純的將某些物質文化所反映出的文明現象就判斷已經文明階段的到來,而促成上述那種質變的根本標志是階級社會和國家的誕生。在發現的諸多的禮儀性建筑中,尤以祭壇與文明的關系最為密切,可將其作為文明因素增長到一定程度的體現:第一,祭壇這種大型建筑的出現說明當時已存在一個極具支配力量和凝聚力的社會組織;第二,出現了專門從事宗教祭祀活動的人員,這一階層由于擁有溝通神靈的職能而在社會地位上遠高于普通大眾。
四、結語
本文通過認知考古學研究的相關內容,對原始社會復雜的社會生活、宗教文化和社會歷史進行了簡單論述。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對我國新石器時代祭祀遺跡的分布狀況和所代表的文化內涵進行綜述。就目前的考古資料和實物遺存可以看出,原始宗教的基本內涵主要就是生死、食物和繁殖。因此,遠古先民祭拜的對象也無非都是與人們日常生活休戚相關的農神、天地、祖先等神靈。而近年來民族學材料的不斷豐富也為我們解讀原始宗教的祭祀儀式提供了有力證據。
參考文獻:
[1]欒豐實,方輝,靳桂云.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M].文物出版社,2006.
[2][美]肯特.弗蘭那利和喬伊斯.馬庫斯著,尋婧元譯,陳淳校.認知考古學[J].南方文物,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