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范文
合同詐騙罪從普通詐騙罪中分離,其目的在于對(duì)利用合同實(shí)施詐騙的犯罪行為從重打擊,其原因在于一般詐騙罪所侵犯的是公私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而合同詐騙罪不僅侵犯了公司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更侵犯了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秩序和合同管理制度。然而,在兩罪法定刑量刑幅度基本一致的情況下,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授權(quán)地方制定的合同詐騙罪“數(shù)額較大”、“數(shù)額巨大”的標(biāo)準(zhǔn)均高于一般詐騙罪的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導(dǎo)致司法實(shí)踐中出現(xiàn)同一個(gè)合同詐騙行為依合同詐騙罪條款無(wú)罪或罪輕,依詐騙罪條款有罪或罪重的悖論。
關(guān)鍵詞:合同詐騙罪;詐騙罪;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重新厘定
中圖分類(lèi)號(hào):DF62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4.01.15
引入案例:2010年6月3日,犯罪嫌疑人崔某利用和男友秦某同居的機(jī)會(huì),獲取秦某母親的個(gè)人信息后,在秦某及其母親均不知情的情況下,使用偽造的身份證、房產(chǎn)證,冒用秦某母親之名,通過(guò)簽訂房屋租賃合同的方式,將秦某母親位于某市高新區(qū)107號(hào)附1號(hào)一單元10-3的房屋出租給被害人周某,并騙取其“房屋押金”和“租金”共計(jì)人民幣15000元后逃匿。
案例中崔某的行為是否構(gòu)成犯罪,應(yīng)當(dāng)如何定性,在辦案過(guò)程中存在較大爭(zhēng)議。
一、罪與非罪的悖論
有觀點(diǎn)認(rèn)為,犯罪嫌疑人崔某的行為不構(gòu)成犯罪,理由在于:首先,崔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冒用他人的名義簽訂合同,騙取對(duì)方當(dāng)事人財(cái)物的行為屬于合同詐騙行為,但因其犯罪數(shù)額未達(dá)到合同詐騙罪數(shù)額追訴標(biāo)準(zhǔn)的要求,故不構(gòu)成合同詐騙罪。其次,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系法條競(jìng)合關(guān)系,應(yīng)適用特別法條優(yōu)于普通法條的適用原則。該原則體現(xiàn)了特別法條與普通法條的排斥關(guān)系。這種排斥關(guān)系不僅意味著行為人的行為在按照特別法條和普通法條都構(gòu)成犯罪時(shí)應(yīng)按照特別法條處理,還包括了在行為人的行為屬于特別法條所意欲規(guī)范的行為類(lèi)型時(shí),具有排斥普通法條適用的可能性。簡(jiǎn)言之,當(dāng)特別法條與普通法條并存時(shí),應(yīng)當(dāng)絕對(duì)排除普通法條的適用。因此,本案中崔某的合同詐騙行為既不構(gòu)成合同詐騙罪,也不能認(rèn)定為普通詐騙罪,只能作無(wú)罪處理。
也有觀點(diǎn)認(rèn)為,犯罪嫌疑人崔某的行為構(gòu)成詐騙罪。理由是嫌疑人崔某的行為同時(shí)符合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的行為特征,當(dāng)一個(gè)行為同時(shí)符合同一法律的普通法條與特別法條規(guī)定的犯罪構(gòu)成時(shí),應(yīng)根據(jù)以下兩個(gè)原則來(lái)適用法律:(1)特別法條優(yōu)于普通法條;(2)重法條優(yōu)于輕法條。兩個(gè)原則的關(guān)系是,一般情況適用前一個(gè)原則,后一個(gè)原則是前一個(gè)原則的修正和補(bǔ)充。因此,雖然嫌疑人崔某的犯罪數(shù)額未達(dá)合同詐騙罪立案追訴標(biāo)準(zhǔn),但已達(dá)詐騙罪的追訴標(biāo)準(zhǔn),可以根據(jù)重法條優(yōu)于輕法條的原則認(rèn)定其構(gòu)成詐騙罪。
筆者認(rèn)為,依據(jù)現(xiàn)行法律和司法解釋?zhuān)瑹o(wú)論認(rèn)定崔某的行為有罪或者無(wú)罪,在刑法解釋的過(guò)程中均存在障礙,其根源在于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授權(quán)地方制定的法規(guī)中關(guān)于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規(guī)定不盡合理。
二、值得商榷的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
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法定刑量刑幅度基本一致,但兩者的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卻相差甚遠(yuǎn)。以重慶市為例,根據(jù)《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guān)于公安機(jī)關(guān)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定(二)》、《重慶市法檢關(guān)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定》【渝高法發(fā)〔2011〕25號(hào)】等相關(guān)規(guī)定,個(gè)人進(jìn)行合同詐騙數(shù)額特別巨大和詐騙公私財(cái)物數(shù)額特別巨大的標(biāo)準(zhǔn)均為人民幣50萬(wàn)元,但不知何故,前者關(guān)于“數(shù)額較大”和“數(shù)額巨大”的標(biāo)準(zhǔn)卻遠(yuǎn)高于后者:(1)個(gè)人進(jìn)行合同詐騙數(shù)額在人民幣 2 萬(wàn)元以上的,屬于“數(shù)額較大 ”;個(gè)人進(jìn)行合同詐騙數(shù)額在人民幣10萬(wàn)元以上的,屬于“數(shù)額巨大”。(2)詐騙公私財(cái)物價(jià)值人民幣五千元以上的,為“數(shù)額較大”;詐騙公私財(cái)物價(jià)值人民幣五萬(wàn)元以上的,為“數(shù)額巨大”。上列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在司法實(shí)踐過(guò)程中存在如下問(wèn)題:
(一)導(dǎo)致對(duì)合同詐騙行為罪與非罪的認(rèn)定出現(xiàn)爭(zhēng)議
第2篇: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范文
一、法條競(jìng)合犯的類(lèi)型
(一)獨(dú)立竟合犯
獨(dú)立競(jìng)合犯是在特別關(guān)系的法條競(jìng)合基礎(chǔ)上所形成的法條競(jìng)犯。獨(dú)立競(jìng)合犯同時(shí)觸犯的是具有特別關(guān)系的兩個(gè)具體犯罪構(gòu)成,獨(dú)立競(jìng)合犯的行為恰好符合兩個(gè)具體犯罪構(gòu)成的重合部分,或者雖然較之重合部分豐富但卻不具有法律上的意義。例如,行為人盜竊軍用物資情節(jié)嚴(yán)重的行為,屬于同時(shí)觸犯盜罪與盜竊軍用物資罪的獨(dú)立競(jìng)合犯等等。
(二)交互竟合犯
交互競(jìng)合犯是在交叉關(guān)系的法條競(jìng)合基礎(chǔ)上所形成的法條競(jìng)合犯。交互競(jìng)合犯同時(shí)觸犯的是具有交叉關(guān)系的兩個(gè)具體犯罪構(gòu)成。與獨(dú)立競(jìng)合犯類(lèi)似,交叉競(jìng)合犯的行為恰好符合兩個(gè)具體犯罪構(gòu)成的重合部分,或者雖然較之重合部分豐富但卻不具有法律上的意義。例如,軍人冒充其他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詐騙數(shù)額較大的財(cái)物的行為,顯然符合詐騙罪和招搖撞騙罪交叉重合的具體構(gòu)成要件,同時(shí)構(gòu)成詐騙罪和招搖撞騙罪,可以被兩罪予以評(píng)價(jià)。
(三)偏一競(jìng)合犯
偏一競(jìng)合犯以交叉關(guān)系的法條競(jìng)合或者補(bǔ)充關(guān)系的法條競(jìng)合為基礎(chǔ)而形成的法條競(jìng)合犯。與獨(dú)立競(jìng)合犯和交互競(jìng)合犯相同,偏一競(jìng)合犯仍然是同時(shí)符合數(shù)個(gè)具體犯罪構(gòu)成的復(fù)雜犯罪形態(tài)。其中,以交叉關(guān)系的法條競(jìng)合為基礎(chǔ)形成的偏一競(jìng)合犯,其產(chǎn)生機(jī)制主要在于:具有交叉關(guān)系的數(shù)個(gè)法條中某一具體犯罪構(gòu)成要件存在著或然性要件,從而使符合該具體犯罪構(gòu)成的行為存在多種可能性,并導(dǎo)致不同犯罪樣態(tài)的出現(xiàn)。例如,軍人冒充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詐騙數(shù)額較大的財(cái)物和感情等非財(cái)產(chǎn)性利益的行為。
二、法條競(jìng)合犯的法律適用原則
雖然只有當(dāng)行為人的行為同時(shí)觸犯具有競(jìng)合關(guān)系的數(shù)個(gè)法條時(shí),法條競(jìng)合犯才實(shí)際形成,也才出現(xiàn)法條適用的選擇問(wèn)題,但是對(duì)于具體法條競(jìng)合犯選擇法條適用的實(shí)然性條件,并不排斥從應(yīng)然性角度分析并明確針對(duì)不同類(lèi)別的法條競(jìng)合犯應(yīng)當(dāng)采用的法律適用原則。明確適用規(guī)則是必要的。行為人的行為同時(shí)符合數(shù)個(gè)具體犯罪構(gòu)成而成立法條競(jìng)合犯,并非意味著其所符合的數(shù)個(gè)法條最終均被適用。因?yàn)樽鳛榉l競(jìng)合犯前提的法條競(jìng)合的形成乃是刑法立法技術(shù)使然,即立法者期望數(shù)個(gè)法條之間的相互協(xié)調(diào)實(shí)現(xiàn)刑法合理且嚴(yán)密的規(guī)制作用,由此決定了法條競(jìng)合犯的罪數(shù)本質(zhì)只能是一罪,也必然決定了在法條競(jìng)合犯所符合的規(guī)定具體犯罪的數(shù)個(gè)法條中,只能選擇一個(gè)最具合理性、全面性評(píng)價(jià)的法條予以適用。換言之,當(dāng)法條競(jìng)合犯實(shí)際形成時(shí),數(shù)個(gè)規(guī)定具體犯罪構(gòu)成的法條才實(shí)際發(fā)生適用沖突的現(xiàn)象,為避免法條適用沖突背景下的法律適用不一致的結(jié)果,必須以相對(duì)統(tǒng)一的適用規(guī)則予以應(yīng)對(duì)。法條競(jìng)合犯的法律適用原則應(yīng)當(dāng)定位為定罪規(guī)則,而非量刑規(guī)則,此為筆者對(duì)法條競(jìng)合犯法律適用原則的基本功能的理解。也就是說(shuō),法條競(jìng)合犯的適用規(guī)則著重解決的應(yīng)當(dāng)是定罪的準(zhǔn)確性、合理性問(wèn)題,而并非是處刑輕重與否、量刑均衡程度的問(wèn)題。
(一)對(duì)于獨(dú)立競(jìng)合犯適用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原則
首先,在立法層面,應(yīng)當(dāng)著重考察獨(dú)立競(jìng)合犯形成的法律邏輯基礎(chǔ)。立法者通常是以一個(gè)普通法條對(duì)應(yīng)若干特別法條的方式,即以特別關(guān)系的法條競(jìng)合的方式,形成由若干具體犯罪構(gòu)成的特定罪名體系,如詐騙罪與各種金融詐騙罪、合同詐騙罪等罪名構(gòu)成的詐騙罪罪名體系等。其中,特別法條規(guī)定之罪是對(duì)普通法條規(guī)定之罪的細(xì)化,它所規(guī)定的具體犯罪構(gòu)成要件更為詳盡、明確,針對(duì)性更強(qiáng),內(nèi)涵更豐富,與此相應(yīng),其所設(shè)置的法定刑也更體現(xiàn)罪刑均衡的要求。
其次,在司法層面,應(yīng)當(dāng)注意確定獨(dú)立競(jìng)合犯法條適用規(guī)則的合法性基礎(chǔ)。司法官對(duì)于同時(shí)構(gòu)成特別法條規(guī)定之罪和普通法條規(guī)定之罪的獨(dú)立競(jìng)合犯,可以選擇的方案無(wú)外乎有兩種:適用普通法條定罪,抑或適用特別法條定罪。比較兩種方案,答案應(yīng)當(dāng)是唯一的,即選擇適用特別法條定罪才能使定罪結(jié)果更為符合立法原意,才能使相關(guān)罪名體系所包含的具體罪名的功能得到充分發(fā)揮,才能使行為人的行為受到最為恰當(dāng)、全面的否定評(píng)價(jià),才能使犯罪人被實(shí)際判處的刑罰合乎立法者的安排。
(二)對(duì)于交互競(jìng)合犯適用重法優(yōu)于輕法原則
交互競(jìng)合犯是在交叉關(guān)系的法條競(jìng)合基礎(chǔ)上形成的,因而探討交互競(jìng)合犯的法條適用規(guī)則,必須以交叉關(guān)系的法條競(jìng)合的特征作為切入點(diǎn)。在立法上,數(shù)個(gè)具體的罪刑規(guī)范之所以形成交叉關(guān)系,主要是立法者為了嚴(yán)密刑事法網(wǎng)所致,亦即立法者試圖通過(guò)數(shù)個(gè)具體罪刑規(guī)范的交叉關(guān)系,避免出現(xiàn)某些特殊的犯罪行為難以被評(píng)價(jià)的法律空白;另一方面其實(shí)際效果甚至能夠同時(shí)避免特殊的犯罪行為數(shù)罪并罰的可能,也就是說(shuō),這種法條設(shè)置總體上甚至是對(duì)行為人有利的。
在司法上,由于具有交叉關(guān)系的數(shù)個(gè)法條彼此地位是平行的、平等的,即對(duì)它們難以作出特別法條與普通法條的界分并據(jù)此確定法條適用規(guī)則,所以,若實(shí)現(xiàn)對(duì)交互競(jìng)合犯最為合理、最為完整的否定評(píng)價(jià),就應(yīng)當(dāng)充分考慮立法者在具體法條中所設(shè)定的全面評(píng)價(jià)的內(nèi)容。具體就交互競(jìng)合犯所符合的數(shù)個(gè)法條而言,這種全面評(píng)價(jià)的內(nèi)容不僅涉及具體犯罪構(gòu)成要件,而且還當(dāng)然包括法定刑的種類(lèi)及程度,所以在確定交互競(jìng)合犯的法條適用規(guī)則時(shí),就應(yīng)當(dāng)同時(shí)兼顧具體法條所包括的定罪要素和刑罰輕重的評(píng)價(jià)功能,即在優(yōu)先考慮以何種罪名對(duì)交互競(jìng)合犯進(jìn)行恰當(dāng)、合理評(píng)價(jià)的基礎(chǔ)上,也應(yīng)充分兼顧與特定罪名相對(duì)應(yīng)的法定刑種類(lèi)及其程度所包含的否定評(píng)價(jià)的完整性,才能妥當(dāng)解決交互競(jìng)合犯所面臨的法條適用沖突問(wèn)題,才能實(shí)現(xiàn)對(duì)交互競(jìng)合犯的全面否定評(píng)價(jià),唯此對(duì)于交互競(jìng)合犯只能選擇重法條優(yōu)于輕法條的適用規(guī)則。
(三)對(duì)于交叉關(guān)系的偏一競(jìng)合犯適用全部法優(yōu)于部分法原則
解決該類(lèi)偏一競(jìng)合犯法條適用問(wèn)題應(yīng)當(dāng)注意兩點(diǎn):第一,適用何種法條能夠保證否定評(píng)價(jià)更為全面。這無(wú)疑是確定任何法條競(jìng)合犯法條適用規(guī)則應(yīng)當(dāng)堅(jiān)持的精神,就基于交叉關(guān)系的偏一競(jìng)合犯而言,關(guān)鍵是看處于平等地位的兩個(gè)特別法條哪個(gè)更能實(shí)現(xiàn)相對(duì)全面的否定評(píng)價(jià),其中,足以相對(duì)全面評(píng)價(jià)的法條屬于全部法,與之相對(duì)的法條屬于部分法。第二,適用何種法條能夠更有利于被告人。正如前述,立法上設(shè)置具有交叉關(guān)系的法條,其功用之一就是避免犯罪行為人受到不當(dāng)?shù)闹貜?fù)評(píng)價(jià),而立法所設(shè)置的這一功能的實(shí)現(xiàn),則必須以在數(shù)個(gè)具有交叉關(guān)系的法條中選擇其一適用為前提。所以,對(duì)于基于交叉關(guān)系的偏一競(jìng)合犯適用全部法優(yōu)于部分法原則,不僅有助于實(shí)現(xiàn)相對(duì)全面的否定評(píng)價(jià),而且是有利于犯罪行為人的選擇。
(四)對(duì)于補(bǔ)充偏一競(jìng)合犯適用基本法優(yōu)于補(bǔ)充法原則
第3篇: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范文
關(guān)鍵詞:票據(jù)質(zhì)押;糾紛;規(guī)定
中圖分類(lèi)號(hào):F06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6.002
文章編號(hào):1672-0407(2012)06-003-02
收稿日期:2012-03-21
一、票據(jù)質(zhì)押的設(shè)立與生效
在我國(guó)的現(xiàn)行法律體系內(nèi),票據(jù)質(zhì)押是一個(gè)兼跨《擔(dān)保法》和《票據(jù)法》的法律行為,而這兩個(gè)法律對(duì)票據(jù)質(zhì)押的設(shè)立與生效又規(guī)定了不同的條件。
《擔(dān)保法》第76條規(guī)定:以匯票、支票、本票、債券、存款單、倉(cāng)單、提單出質(zhì)的,應(yīng)當(dāng)在合同約定的期限內(nèi)將權(quán)利憑證交付質(zhì)權(quán)人。根據(jù)這一規(guī)定,票據(jù)質(zhì)押的生效條件有兩個(gè):一是合意,必須簽訂書(shū)面的質(zhì)押合同;二是交付,必須將票據(jù)交付給質(zhì)權(quán)人。票據(jù)質(zhì)押自票據(jù)交付給質(zhì)權(quán)人時(shí)起生效。
從《擔(dān)保法》和《票據(jù)法》現(xiàn)行規(guī)定可見(jiàn),《票據(jù)法》和《擔(dān)保法》對(duì)票據(jù)質(zhì)押的設(shè)立與生效條件的規(guī)定不相統(tǒng)一,主要區(qū)別在于是否要求背書(shū)并記載“質(zhì)押”字樣。依照《票據(jù)法》,經(jīng)背書(shū)“質(zhì)押”的票據(jù)質(zhì)押有效成立,而依照《擔(dān)保法》,出質(zhì)人雖未在票據(jù)上記載“質(zhì)押”字樣但另行簽訂了質(zhì)押合同或者質(zhì)押條款的,構(gòu)成票據(jù)質(zhì)押。這樣就會(huì)出現(xiàn)這樣的問(wèn)題:這兩種規(guī)定之間是什么關(guān)系,究竟應(yīng)以哪種規(guī)定為準(zhǔn)?筆者認(rèn)為,從債權(quán)擔(dān)保角度來(lái)說(shuō),《擔(dān)保法》是債權(quán)擔(dān)保的普通法,而《票據(jù)法》是票據(jù)的專(zhuān)門(mén)法律,其關(guān)于票據(jù)質(zhì)押的規(guī)定構(gòu)成了債權(quán)擔(dān)保的特別法,按照一般法理,在普通法與特別法規(guī)定不一致時(shí),適用“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原理,優(yōu)先適用特別法的規(guī)定。因而,有關(guān)票據(jù)質(zhì)押的設(shè)立與生效應(yīng)當(dāng)適用《票據(jù)法》的規(guī)定。據(jù)此,票據(jù)質(zhì)押的設(shè)立與生效必須具備下列三個(gè)條件:一是必須以背書(shū)方式為之,出質(zhì)人為背書(shū)人,質(zhì)權(quán)人為被背書(shū)人,出質(zhì)人應(yīng)當(dāng)簽蓋,否則背書(shū)無(wú)效。對(duì)此,《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票據(jù)糾紛案件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第55條作了明確規(guī)定:依照票據(jù)法第三十五條第二款的規(guī)定,以匯票設(shè)定質(zhì)押時(shí),出質(zhì)人在匯票上只記載了“質(zhì)押”字樣未在票據(jù)上簽章的,不構(gòu)成票據(jù)質(zhì)押。二是必須記載“質(zhì)押”字樣。因?yàn)槠睋?jù)是一種文義證券,而質(zhì)押背書(shū)乃是一種非轉(zhuǎn)讓背書(shū),如果不記載“質(zhì)押”字樣,不能以票據(jù)出質(zhì)對(duì)抗善意第三人。第三,必須將票據(jù)交付給質(zhì)權(quán)人。只有將票據(jù)交付給質(zhì)權(quán)人,其才能行使質(zhì)權(quán)。
解決票據(jù)質(zhì)押的設(shè)立與生效的條件之后,隨之而來(lái)的另一個(gè)是:如果當(dāng)事人未在票據(jù)上記載“質(zhì)押”字樣,而是另外簽訂了質(zhì)押合同或質(zhì)押條款,此時(shí)票據(jù)質(zhì)押是否有效?如果有效,票據(jù)質(zhì)押人如何行使票據(jù)權(quán)利?筆者認(rèn)為,如果當(dāng)事人未在票據(jù)上記載“質(zhì)押”字樣,不能產(chǎn)生票據(jù)質(zhì)押的效力,但是如果其符合了《擔(dān)保法》的規(guī)定,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以票據(jù)為權(quán)利憑證的一般債權(quán)質(zhì)押,按照《擔(dān)保法》的相關(guān)規(guī)定行使質(zhì)權(quán)。質(zhì)押字樣的記載只是票據(jù)質(zhì)權(quán)的對(duì)抗要件,在不存在善意第三人的時(shí)候,以票據(jù)為權(quán)利憑證的一般債權(quán)質(zhì)押權(quán)利不應(yīng)當(dāng)被否認(rèn)。因而,即使未記載“質(zhì)押”字樣,但質(zhì)權(quán)人的擔(dān)保權(quán)利是成立的。對(duì)于此類(lèi)質(zhì)權(quán)的行使,持票人可以依據(jù)質(zhì)押合同和票據(jù)向人民法院,要求實(shí)現(xiàn)質(zhì)權(quán),但是質(zhì)權(quán)人必須依法舉證,證明自己取得票據(jù)權(quán)利的合法性,證明自己享有質(zhì)權(quán)。由于此時(shí)的質(zhì)押標(biāo)的為一般債權(quán),所以質(zhì)權(quán)人除了證明其質(zhì)權(quán)外,還需證明其債權(quán)已到清償期限,否則不得行使質(zhì)權(quán)。
二、票據(jù)質(zhì)押的效力
票據(jù)質(zhì)押一經(jīng)有效設(shè)定,即產(chǎn)生如下法律效力:
1.行使票據(jù)權(quán)利的效力。雖然背書(shū)人經(jīng)設(shè)質(zhì)背書(shū)將票據(jù)轉(zhuǎn)讓于被背書(shū)人占有,但是票據(jù)權(quán)利人依然是背書(shū)人,持有票據(jù)的被背書(shū)人并沒(méi)有取得票據(jù)權(quán)利,只能代背書(shū)人行使票據(jù)權(quán)利而已。所以質(zhì)權(quán)人行使質(zhì)權(quán)時(shí)有一定的限制:即須等到主債務(wù)到期且債務(wù)人未履行債務(wù)方得行使。
2.可以在票據(jù)上再背書(shū)。但質(zhì)權(quán)人在票據(jù)上的再背書(shū)僅以委任取款為限,不能為轉(zhuǎn)讓背書(shū)或轉(zhuǎn)質(zhì)背書(shū),因?yàn)橘|(zhì)權(quán)人對(duì)票據(jù)只享有占有權(quán),而不享有處分權(quán)。
3.質(zhì)權(quán)設(shè)立的證明。設(shè)質(zhì)背書(shū)的持票人可以背書(shū)的連續(xù)性證明自己為合法的質(zhì)權(quán)人,不需另行舉證。基于票據(jù)行為的無(wú)因性,設(shè)質(zhì)背書(shū)一經(jīng)成立,即獨(dú)立于原因關(guān)系發(fā)生效力,即便原因關(guān)系不存在,或者不合法,也不致持票人的質(zhì)權(quán)。當(dāng)票據(jù)關(guān)系與原因關(guān)系不一致時(shí),除直接當(dāng)事人之間可依此抗辯外,須等到票據(jù)關(guān)系實(shí)現(xiàn)后再依原因關(guān)系在各方當(dāng)事人之間進(jìn)行清算。
4.切斷人的抗辯。質(zhì)押并非,設(shè)質(zhì)背書(shū)的被背書(shū)人是以自己的名義、為自己的利益行使票據(jù)權(quán)利,背書(shū)人與被背書(shū)人是在票據(jù)法上人格與利益分離的兩個(gè)獨(dú)立的主體,票據(jù)債務(wù)人不能象委任取款一樣以對(duì)背書(shū)人的抗辯事由來(lái)對(duì)抗被背書(shū)人。因?yàn)樵O(shè)質(zhì)背書(shū)的目的是以票據(jù)權(quán)利的安全性和信用性作為設(shè)質(zhì)債務(wù)的擔(dān)保,如果允許以對(duì)背書(shū)人的抗辯對(duì)抗被背書(shū)人,就會(huì)妨礙質(zhì)權(quán)的行使,破壞票據(jù)作為權(quán)利證券的安全性和作為流通證券的信用性,與票據(jù)行為的獨(dú)立性原則不相吻合,票據(jù)作為設(shè)質(zhì)標(biāo)的就失去其特有的意義了.
5.票據(jù)責(zé)任的擔(dān)保。票據(jù)質(zhì)押設(shè)定后,出質(zhì)人作為背書(shū)人,對(duì)票據(jù)仍要承擔(dān)擔(dān)保責(zé)任,在其后手得不到承兌或付款時(shí),要承擔(dān)付款責(zé)任。因?yàn)橘|(zhì)押背書(shū)在質(zhì)權(quán)人要實(shí)現(xiàn)質(zhì)權(quán)時(shí),和普通背書(shū)完全一致,一旦遭到拒絕承兌或付款,可以向其任何一位前手行使追索權(quán),但是出質(zhì)人可以質(zhì)押合同中的正當(dāng)理由來(lái)對(duì)抗質(zhì)權(quán)人,這也就是票據(jù)行為中直接當(dāng)事人之間的抗辯。但是當(dāng)事人如果將設(shè)質(zhì)背書(shū)的票據(jù)再背書(shū)轉(zhuǎn)讓?zhuān)鳛楸硶?shū)人的出質(zhì)人只對(duì)直接后手也就是質(zhì)權(quán)人承擔(dān)擔(dān)保責(zé)任,不對(duì)質(zhì)權(quán)人再轉(zhuǎn)讓背書(shū)的被背書(shū)人及其后手承擔(dān)責(zé)任。
第4篇: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范文
案情:
2002年7月19日,一個(gè)叫王小歌的嬰兒出生三天后,因病危被送進(jìn)河南省某縣婦幼保健院監(jiān)護(hù)室的暖箱(塑料制品)中實(shí)行特別看護(hù)。當(dāng)晚8時(shí)左右,醫(yī)院突然停電,為了便于觀察,當(dāng)時(shí)值班護(hù)士就在暖箱的塑料邊上粘上兩根蠟燭。當(dāng)天晚上10時(shí)50分,護(hù)士張某接班后,見(jiàn)蠟燭快燒完了,就在原位置上又續(xù)上一根新蠟燭。第二天凌晨5時(shí)左右,張某在未告訴任何人的情況下,將嬰兒一人獨(dú)自留下去衛(wèi)生間,當(dāng)她返回后,發(fā)現(xiàn)蠟燭已經(jīng)引燃了暖箱,王小歌因?yàn)橹舷⒍劳觥?/p>
分歧意見(jiàn):
關(guān)于本案的定性,有三種不同意見(jiàn)。
第一種意見(jiàn)是應(yīng)定失火罪。因?yàn)閺埬巢⒉皇欠e極主動(dòng)地去實(shí)施放火,她只是因?yàn)檫^(guò)失行為才引起了火災(zāi)事故,從而造成了王小歌死亡的結(jié)果,故應(yīng)當(dāng)對(duì)張某定為失火罪。
第二種意見(jiàn)是應(yīng)定為重大責(zé)任事故罪。因?yàn)閺埬吃谥饔^上是出于過(guò)于自信的過(guò)失,主體上是特殊主體——事業(yè)單位婦幼保健院的職工,并且她還負(fù)有堅(jiān)守工作崗位、保證護(hù)理工作準(zhǔn)確及時(shí)進(jìn)行的職責(zé),客觀上她因?yàn)檫`反了該醫(yī)院的規(guī)章制度,從而導(dǎo)致火災(zāi)發(fā)生,造成了王小歌死亡的悲劇,張某的行為完全符合重大責(zé)任事故罪的所有犯罪構(gòu)成要件。
第三種意見(jiàn)是應(yīng)定為過(guò)失致人死亡罪。因?yàn)橥跣「璧乃劳鼋Y(jié)果是因?yàn)閺埬车姆枪室庑袨榧催^(guò)失行為造成的,她對(duì)王小歌的死亡結(jié)果所持的是過(guò)于自信的過(guò)失態(tài)度,且不屬于刑法分則中另有專(zhuān)門(mén)規(guī)定的過(guò)失致人死亡的其他犯罪,如交通肇事罪,因而應(yīng)定過(guò)失致人死亡罪。
評(píng)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jiàn)。
第5篇: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范文
美國(guó)認(rèn)為,巴基斯坦在指責(zé)美國(guó)采取的措施時(shí),使用WTO其他協(xié)議解釋紡織品協(xié)議第6條的過(guò)渡性保障機(jī)制是錯(cuò)誤的。從紡織品協(xié)議的過(guò)渡性,其逐步與GATT1994一體化的目的,以及關(guān)于"國(guó)內(nèi)產(chǎn)業(yè)"定義和處理的用語(yǔ),與其他非過(guò)渡性協(xié)議都有很大不同。例如,如果談判者不是為了體現(xiàn)過(guò)渡性保障機(jī)制與保障措施協(xié)議的差異,就不會(huì)在紡織品協(xié)議中增加保障措施的規(guī)定,而只要援引GATT第19條和保障措施協(xié)議就行了。因此,解釋第6條,專(zhuān)家組應(yīng)當(dāng)看紡織品協(xié)議的文本和目的,而不是其他WTO協(xié)議及其解釋。
巴基斯坦則主張,在確定紡織品協(xié)議用語(yǔ)的含義時(shí),可以考慮其他協(xié)議的解釋。所有WTO協(xié)議,包括紡織品協(xié)議,都是《WTO協(xié)定》的組成部分,[2]是一攬子談判達(dá)成的協(xié)議。[3]因此,專(zhuān)家組解釋一個(gè)協(xié)議的用語(yǔ)時(shí),從對(duì)其他協(xié)議中類(lèi)似用語(yǔ)的解釋中尋求幫助,是合法的,也是常見(jiàn)的。例如,在危地馬拉水泥案中,專(zhuān)家組使用保障措施協(xié)議的規(guī)定證實(shí)其反傾銷(xiāo)協(xié)議的解釋?zhuān)籟4]阿根廷鞋類(lèi)保障措施案專(zhuān)家組援引美國(guó)內(nèi)衣案和美國(guó)襯衫及上衣案,以證實(shí)其對(duì)審查標(biāo)準(zhǔn)、收集證據(jù)的方式以及是否應(yīng)當(dāng)考慮所有產(chǎn)業(yè)狀況的相關(guān)因素等的裁決。[5]既然紡織品協(xié)議的解釋可以被用于解釋其他協(xié)議,反過(guò)來(lái)為什么不可以呢?
因此,巴基斯坦的觀點(diǎn)是,當(dāng)紡織品協(xié)議中某個(gè)用語(yǔ)所涉及的事項(xiàng)與其他協(xié)議中對(duì)語(yǔ)涉及的事項(xiàng)相似時(shí),那么其他協(xié)議中用語(yǔ)的解釋就是相關(guān)的。例如,保障措施協(xié)議和紡織品協(xié)議都要求確定因果關(guān)系。沒(méi)有理由僅僅因?yàn)樗鼈兪遣煌谋U洗胧陀貌煌姆绞浇鉀Q這個(gè)問(wèn)題。再如,GATT1994第3條和紡織品協(xié)議第6條都涉及市場(chǎng)準(zhǔn)入問(wèn)題,都使用了"直接競(jìng)爭(zhēng)"一詞來(lái)說(shuō)明產(chǎn)品的范圍,沒(méi)有理由因?yàn)樗鼈兪怯嘘P(guān)市場(chǎng)準(zhǔn)入的不同措施,就對(duì)這些用語(yǔ)作不同解釋。
專(zhuān)家組認(rèn)為,WTO爭(zhēng)端解決諒解(DSU)第3條第2款規(guī)定,爭(zhēng)端解決的作用之一,是按照國(guó)際公法的習(xí)慣解釋規(guī)則,澄清WTO各項(xiàng)協(xié)議的規(guī)定。對(duì)于"國(guó)際公法的習(xí)慣解釋規(guī)則",上訴機(jī)構(gòu)多次提到《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維也納公約)第31條和第32條。第31條規(guī)定,應(yīng)結(jié)合上下文對(duì)條約用語(yǔ)的通常含義進(jìn)行解釋?zhuān)簧舷挛氖侵?條約"本身,包括其序言和附錄,以及締約方之間就條約締結(jié)而訂立的與該條約有關(guān)的任何協(xié)議。在本案中,條約就是《WTO協(xié)定》,而紡織品協(xié)議是其組成部分。因此,紡織品協(xié)議第6條的上下文,是WTO協(xié)定整體。[6]專(zhuān)家組舉例說(shuō),保障措施協(xié)議第5條第1款規(guī)定,保障措施應(yīng)當(dāng)在防止或補(bǔ)救嚴(yán)重?fù)p害和促進(jìn)調(diào)整的必要范圍內(nèi)實(shí)施。雖然一般保障措施與過(guò)渡性保障機(jī)制有區(qū)別,但在必要范圍內(nèi)實(shí)施應(yīng)當(dāng)是普遍適用的。[7]
美國(guó)在上訴中提出,專(zhuān)家組借助"上下文",將保障措施協(xié)議中的用詞和概念用在紡織品協(xié)議中,忽視了紡織品協(xié)議第6條的特殊之處;紡織品協(xié)議與GATT第19條和保障措施協(xié)議是不同的,按照保障措施協(xié)議第11條第1款(c)項(xiàng)的規(guī)定,保障措施協(xié)議不適用于紡織品協(xié)議第6條的過(guò)渡性保障措施機(jī)制。[8]
第6篇: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范文
關(guān)鍵詞:公司人格 法人性 法定性 營(yíng)利性
公司人格的意義
私法上 “人格” 一詞有多重含義。第一種含義是民事主體資格。江平先生(1994)認(rèn)為,人格中的“人”為權(quán)利主體,“格”為這種主體的資格,人格即民事權(quán)利主體資格。凡是具有人格的私法上的人皆為權(quán)利主體。從這種意義上講,自然人具有人格,法人也具有人格,而且都是獨(dú)立的人格。因?yàn)樽匀蝗撕头ㄈ耸莾煞N民事主體,而人格即為主體的含義,凡是民事主體皆為人格。人格的這種含義在民商法學(xué)上廣為流傳和使用。在民法學(xué)上,自然人和法人都擁有獨(dú)立的人格,自然人是法定的民事主體,盡管其民事行為能力有差別,但其作為民事主體的資格是法定的。所有自然人都具有獨(dú)立的人格且人格均為平等,這是貫徹憲法上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表現(xiàn)。法人在民法學(xué)上一般認(rèn)為是具有民事權(quán)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dú)立享有民事權(quán)利和承擔(dān)民事義務(wù)的組織。法人是《民法通則》等法律確認(rèn)的民事主體,即依法設(shè)立、有一定的財(cái)產(chǎn)和經(jīng)費(fèi)、有自己的名稱(chēng)、組織機(jī)構(gòu)和場(chǎng)所,能夠獨(dú)立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法人是獨(dú)立的民事主體,因此法人也就擁有獨(dú)立的人格。在商法學(xué)上,商主體擁有獨(dú)立的法律人格,商主體即企業(yè),包括個(gè)人獨(dú)資企業(yè)、合伙企業(yè)和公司企業(yè)。商主體的獨(dú)立人格意味著三種企業(yè)都是獨(dú)立的商事主體,而非客體,具有商事權(quán)利能力和商事行為能力,依法獨(dú)立享有商事權(quán)利和承擔(dān)商事義務(wù)。
第二種含義為人格是民事權(quán)利能力。民事權(quán)利能力是民事主體依法享有民事權(quán)利和承擔(dān)民事義務(wù)的資格。所有民事主體的民事權(quán)利能力一律平等。這種認(rèn)識(shí),不同于人格即為權(quán)利主體資格。因?yàn)椋袷轮黧w資格不僅包括民事權(quán)利能力,還包括民事行為能力和民事責(zé)任能力。有民事權(quán)利能力者,不一定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或民事責(zé)任能力,所以?xún)煞N學(xué)說(shuō)存在區(qū)別。將民事權(quán)利能力等同于人格,也能夠說(shuō)明所有民事主體一律平等,因?yàn)樗忻袷轮黧w都具有平等的民事權(quán)利能力,沒(méi)有不具有民事權(quán)利能力的民事主體。史尚寬先生就認(rèn)為,人格是民事權(quán)利能力的別稱(chēng)。然而,在商法學(xué)上,主體與權(quán)利能力資格的區(qū)分確實(shí)客觀、清晰。以公司為例,公司的主體地位由公司法確定,而且公司是典型的法人,法人是民法上獨(dú)立的民事主體,而公司的權(quán)利能力則體現(xiàn)為公司章程中載明的營(yíng)業(yè)范圍,營(yíng)業(yè)范圍說(shuō)明了公司的權(quán)利能力的范圍和大小。從這一實(shí)例可以說(shuō)明,公司的主體資格與公司的權(quán)利能力不同。在民法學(xué)上,自然人的主體資格與自然人的權(quán)利能力的區(qū)別不是十分明顯,人格作為主體資格與民事權(quán)利能力的確可以等同。但從整個(gè)私法的角度看,情況就不同了。筆者認(rèn)為,上述兩種學(xué)說(shuō)存在根本區(qū)別。
第三種含義為人格是人格權(quán)。民法是調(diào)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guān)系和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法律規(guī)范的總稱(chēng)。其中調(diào)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guān)系,從權(quán)利角度上講即為人身權(quán),包括人格權(quán)和身份權(quán);調(diào)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從權(quán)利角度上講即為財(cái)產(chǎn)權(quán),包括物權(quán)、債權(quán)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等。身份權(quán)隨著近代社會(huì)人人平等已被各國(guó)憲法確認(rèn)的事實(shí)而日趨消亡,僅剩下配偶權(quán)、親權(quán)和親屬權(quán)等。人格權(quán)與身份權(quán)正相反,近代以來(lái)發(fā)展極為迅猛,這是由于人人平等觀念深入人心和人權(quán)意識(shí)高漲的結(jié)果。人格權(quán)包括一般性的人格權(quán)和具體性的人格權(quán),前者包括人格平等、人格自由;后者包括物質(zhì)性的人格權(quán)和精神性的人格權(quán)。物質(zhì)性的人格權(quán)又包括生命權(quán)、身體權(quán)和健康權(quán);精神性的人格權(quán)又包括姓名權(quán)、名稱(chēng)權(quán)、名譽(yù)、隱私權(quán)等。將人格認(rèn)為是民事權(quán)利中的人格權(quán),這是從權(quán)利角度看到了人格權(quán)是民事權(quán)利主體與生俱來(lái)的不可分離的權(quán)利屬性。
第四種人格的含義是權(quán)利能力、行為能力以及名譽(yù)、自由等的總稱(chēng)。這種意義上的人格可以認(rèn)為是抽象的法律世界中的能力和資格。對(duì)于本文所專(zhuān)指的公司人格不具有指導(dǎo)意義。
上述四種關(guān)于人格的認(rèn)識(shí),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站在不同的角度觀察人格,都會(huì)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筆者所謂“公司人格”中的“人格”,除非作出特別說(shuō)明,皆為第一種意義上的人格含義,即人格是權(quán)利主體資格。公司人格,即公司是權(quán)利主體。
公司人格的本質(zhì)特性
(一)公司人格的法人性
公司這一商事主體,完全符合法人的條件或構(gòu)成要件,公司是最典型的私法人。
首先,公司依法而成立。規(guī)范公司的法律包括公司領(lǐng)域的普通法和特別法,普通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公司法》,特別法比如《證券法》、《保險(xiǎn)法》、《信托法》、《商業(yè)銀行法》等,分別是證券公司、保險(xiǎn)公司、信托公司和商業(yè)銀行的特別法。如前所述,公司人格具有法定性的特點(diǎn)。
其次,公司有必要的財(cái)產(chǎn)和經(jīng)費(fèi),即公司有其獨(dú)立的財(cái)產(chǎn)。獨(dú)立的財(cái)產(chǎn)意味著該財(cái)產(chǎn)不屬于出資者,出資者出資后,財(cái)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即歸公司所有,出資者享有相應(yīng)的股權(quán);獨(dú)立的財(cái)產(chǎn)區(qū)別于其他公司的財(cái)產(chǎn),該財(cái)產(chǎn)屬于公司所有;獨(dú)立的財(cái)產(chǎn)不同于債權(quán)人的財(cái)產(chǎn),該財(cái)產(chǎn)是公司對(duì)外獨(dú)立承擔(dān)責(zé)任的依據(jù),體現(xiàn)了公司償還債務(wù)的能力。
第7篇: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范文
(一)為行政行為提供法律依據(jù)
依法行政是行政行為的基本原則,按照這一原則,行政行為需滿(mǎn)足主體合法、權(quán)限合法、內(nèi)容合法、程序合法等形式合法性的要求,這種形式合法性最終指向行政行為的實(shí)質(zhì)合法性。行政行為形式合法性的實(shí)質(zhì)是要求行政行為的作出必須要有法律依據(jù),即“有法律則行政,無(wú)法律則不得行政”。從行政法法源的角度來(lái)看,行政行為法律依據(jù)的檢索過(guò)程實(shí)質(zhì)上是行政法法源的查找過(guò)程。行政法的法源為行政行為法律依據(jù)的檢索提供了路徑,就形式合法性而言,行政主體可以從行政法的直接淵源、正式淵源、形式淵源、成文法淵源以及必須的法的淵源和應(yīng)當(dāng)?shù)姆ǖ臏Y源中查找行政行為的法律依據(jù),如果窮盡這些法源仍然找不到相關(guān)的法律依據(jù),則行政主體不得作出行政行為。行政行為除了要滿(mǎn)足形式合法性的要求以外,還要以實(shí)現(xiàn)實(shí)質(zhì)合法性為最終目的。行政行為的形式合法性在一般情況下與其實(shí)質(zhì)合法性是相統(tǒng)一的,實(shí)現(xiàn)了形式合法性也就實(shí)現(xiàn)了實(shí)質(zhì)合法性。但在特定情況下形式合法性與實(shí)質(zhì)合法性可能會(huì)發(fā)生分離,兩者發(fā)生分離時(shí)協(xié)調(diào)形式合法性與實(shí)質(zhì)合法性沖突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般情況下形式合法性?xún)?yōu)先;特定情形下實(shí)質(zhì)合法性?xún)?yōu)先。從行政法法源的角度來(lái)看,行政行為實(shí)質(zhì)合法性的標(biāo)準(zhǔn)需要從行政法的間接淵源、非正式淵源、實(shí)質(zhì)淵源、非成文法淵源以及可以的法的淵源中進(jìn)行選取,這些淵源最終指向法的公平正義的目的性?xún)r(jià)值,公平正義是判斷行政行為實(shí)質(zhì)合法性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
(二)為法官“找法”設(shè)定路徑
大陸法系的判斷從邏輯結(jié)構(gòu)上看是一種典型的三段論模式,即以法律依據(jù)為大前提,以個(gè)案事實(shí)為小前提,判決結(jié)果則是三段論的結(jié)論。對(duì)于一個(gè)具體案件的裁判而言,小前提(個(gè)案事實(shí))是通過(guò)當(dāng)事人舉證和法院查證來(lái)完成的,而大前提(法律依據(jù))則是通過(guò)法官對(duì)法律依據(jù)的查找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法官查找法律依據(jù)的過(guò)程即為法官“找法”的過(guò)程。法官找法是一個(gè)復(fù)雜的過(guò)程。對(duì)于一個(gè)具體的個(gè)案而言,與個(gè)案事實(shí)相關(guān)聯(lián)的法律是復(fù)數(shù)的而不是單一的,出于司法效率的考慮,法官找法并非漫無(wú)邊際,因此法官找法存在找法“范圍”與找法“次序”的問(wèn)題。如何確定法官找法的范圍?從法的淵源的角度來(lái)看,法的淵源即設(shè)定了法官找法的范圍。“法源,即是其中何種形式的法才能成為法院審判標(biāo)準(zhǔn)的問(wèn)題。”從司法認(rèn)知的角度來(lái)看,法官找法不可能超出法的淵源所劃定的范圍;從訴訟效率的角度來(lái)看,法官找法也無(wú)必要超出法的淵源所劃定的范圍,法官找法應(yīng)以法的淵源所劃定的范圍為限。從找法的次序來(lái)看,法官找法首先需要從直接淵源、正式淵源、形式淵源、成文法淵源以及必須的法的淵源和應(yīng)當(dāng)?shù)姆ǖ臏Y源中找法。對(duì)于非疑難案件而言,第一序位的查找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已經(jīng)能夠滿(mǎn)足法官找法的需要,法官并不需要進(jìn)入第二序位找法。對(duì)于疑難案件,由于法官在第一序位中無(wú)法找到可以適用于具體案件的法律依據(jù),此時(shí)法官往往需要到第二序位,即從間接淵源、非正式淵源、實(shí)質(zhì)淵源、非成文法源和可以的法源中去查找裁判具體案件的法律依據(jù)。
“法官不得拒絕裁判”是司法權(quán)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包含兩層含義:對(duì)于存在明確法律依據(jù)的案件,法官當(dāng)然應(yīng)當(dāng)進(jìn)行裁判;而對(duì)于并不存在明確法律依據(jù)的案件,法官也不得以法無(wú)明文規(guī)定為由拒絕裁判。從找法次序的角度來(lái)看,是否存在明確法律依據(jù)是以法官第一序位法的查找為衡量標(biāo)準(zhǔn)的。就一般的理解而言,“存在明確的法律依據(jù)”是指法官可以從第一序位的法的淵源中找到適用于具體案件的法律依據(jù);“不存在明確的法律依據(jù)”則表示法官無(wú)法在第一序位中找到法律依據(jù)。法的淵源的兩個(gè)層次的劃分則為法官在“不存在明確法律依據(jù)”情況下找法提供了思路:此時(shí)法官應(yīng)從第二序位的法的淵源中查找法律依據(jù),由于第二序位法的淵源具有廣泛性和多元性,因此法官必定能在這一序位的法的淵源中查找到適用于具體案件的法律依據(jù)。需要明確的是,在嚴(yán)格的依法裁判原則的要求下,第二序位的法的淵源一般不能成為法官判案的所“援引”的法律依據(jù),更多情況下是成為法官判案的“理由”,而這種理由實(shí)質(zhì)上起到了裁判案件法律依據(jù)的作用。
二、行政法法源的效力等級(jí)
我國(guó)《立法法》對(duì)行政法法源的位階作出了全面的規(guī)定,我國(guó)行政法法源的效力等級(jí)遵循下列原則:(一)上位法優(yōu)于下位法第一,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guī)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第二,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規(guī)章。行政法規(guī)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規(guī)、規(guī)章。地方性法規(guī)的效力高于本級(jí)和下級(jí)地方政府規(guī)章。省、自治區(qū)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guī)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區(qū)域內(nèi)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guī)章。
(二)特別法優(yōu)于一般法特別法是指對(duì)特定主體、特定事項(xiàng)有效,或在特定區(qū)域、特定時(shí)間有效的法。一般法是指對(duì)一般主體、一般事項(xiàng)、一般時(shí)間、一般空間有效的法。特別法優(yōu)于一般法的含義為:就適用對(duì)象而言,對(duì)特定主體和特定事項(xiàng)有效的法優(yōu)先于對(duì)一般主體和一般事項(xiàng)有效的法;就適用時(shí)間和適用空間而言,在特定時(shí)間和特定區(qū)域有效的法優(yōu)先于對(duì)一般時(shí)間和一般空間有效的法。特別法優(yōu)先于一般法是有條件的:對(duì)于同一機(jī)關(guān)制定的法才當(dāng)然適用特別法優(yōu)于一般法的原則,而對(duì)于不同機(jī)關(guān)制定的法則并非當(dāng)然適用。我國(guó)《立法法》第83條規(guī)定:同一機(jī)關(guān)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guī)章,特別規(guī)定與一般規(guī)定不一致的,適用特別規(guī)定。這一規(guī)定所體現(xiàn)的即是特別法優(yōu)于一般法的原則。《立法法》同時(shí)對(duì)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經(jīng)濟(jì)特區(qū)法規(guī)作出的“變通”性規(guī)定的適用作出規(guī)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依法對(duì)法律、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作變通規(guī)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適用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規(guī)定。經(jīng)濟(jì)特區(qū)法規(guī)根據(jù)授權(quán)對(duì)法律、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作變通規(guī)定的,在本經(jīng)濟(jì)特區(qū)適用經(jīng)濟(jì)特區(qū)法規(guī)的規(guī)定。變通規(guī)定相對(duì)于所對(duì)應(yīng)的一般法而言屬于特別法,按照特別法優(yōu)于一般法的原則,變通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優(yōu)先適用。
(三)新法優(yōu)于舊法法的制定存在一個(gè)長(zhǎng)期連續(xù)的過(guò)程,當(dāng)法對(duì)同一對(duì)象發(fā)生法律效力時(shí),法之間往往存在新法與舊法的沖突,處理新法與舊法沖突的原則是“新法優(yōu)于舊法”。新法優(yōu)于舊法的適用有兩個(gè)前提條件,一是同一主體制定的法,二是同一位階的法。對(duì)于不同主體制定屬于不同位階的法則不適用新法優(yōu)于舊法的原則。我國(guó)《立法法》第83條規(guī)定:同一機(jī)關(guān)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guī)章,新的規(guī)定與舊的規(guī)定不一致的,適用新的規(guī)定。
三、行政法法源的適用原則:效力優(yōu)先原則與適用優(yōu)先原則
(一)效力優(yōu)先原則與適用優(yōu)先原則的內(nèi)涵
法律位階理論由奧地利法學(xué)家梅爾克首先提出,他認(rèn)為,法律是一個(gè)有等級(jí)秩序的規(guī)范體系,即由條件性規(guī)范和附條件性規(guī)范組成的體系,附條件性規(guī)范是由條件性規(guī)范決定的。梅爾克的法律位階理論后來(lái)得到了規(guī)范法學(xué)派的創(chuàng)始人凱爾森的繼承和發(fā)展。凱爾森認(rèn)為,法律規(guī)范有著一個(gè)內(nèi)在的等級(jí)體系,高級(jí)規(guī)范決定著低級(jí)規(guī)范的范圍與內(nèi)容,低級(jí)規(guī)范的效力來(lái)源于高級(jí)規(guī)范,高級(jí)規(guī)范是低級(jí)規(guī)范存在的理由。梅爾克—?jiǎng)P爾森位階理論的要義存在于兩個(gè)方面:一是上位法規(guī)范是下位法規(guī)范的效力依據(jù),二是下位法規(guī)范是上位法規(guī)范的具體化和個(gè)別化。就第一個(gè)要義而言,所有處于下位階的法律要服從于上位階的法律而不得與上位階的法律相抵觸,它體現(xiàn)出來(lái)的原則就是“效力優(yōu)先原則”;就第二個(gè)要義而言,在法的適用過(guò)程中,法的位階愈低,其對(duì)社會(huì)關(guān)系的調(diào)整就愈加具體和細(xì)致,因此法的適用應(yīng)選取下位法予以適用,這也就是“適用優(yōu)先原則。”德國(guó)法學(xué)家毛雷爾對(duì)效力優(yōu)先與適用優(yōu)先原則進(jìn)行了深入闡述,他認(rèn)為適用優(yōu)先相對(duì)獨(dú)立于效力優(yōu)先原則,不能以效力優(yōu)先取代適用優(yōu)先原則:“位階確立的是上階位規(guī)范效力的優(yōu)先性,而不是其適用的優(yōu)先性。實(shí)踐中往往是優(yōu)先適用下階位的規(guī)范。因此,如果具有相應(yīng)的法律規(guī)定,行政機(jī)關(guān)就沒(méi)有必要直接適用憲法。只有在法律規(guī)定出現(xiàn)缺位的情況下,才有義務(wù)和必要適用憲法”。
他同時(shí)指出了適用優(yōu)先的必要性:“適用的優(yōu)先性來(lái)自于各個(gè)規(guī)范均更為具體、更可實(shí)施的法律的約束力。如果決定機(jī)關(guān)直接適用具有普遍包容性的基本權(quán)利或者憲法原則,就會(huì)損害這種規(guī)定”。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學(xué)者對(duì)效力優(yōu)先與適用優(yōu)先原則也進(jìn)行了深入研究。臺(tái)灣學(xué)者陳清秀對(duì)這一對(duì)概念及其區(qū)分作了如下區(qū)分:“在法源位階理論中有‘效力優(yōu)先原則’與‘適用優(yōu)先原則’,前者是指高位階法規(guī)范之效力優(yōu)先于低位階法規(guī)范,故普通法律(低位階法規(guī)范)抵觸憲法規(guī)定者無(wú)效。后者是指適用法律機(jī)關(guān)(如行政機(jī)關(guān)或行政法院)適用法規(guī)范審判時(shí),應(yīng)優(yōu)先適用低位階之法規(guī)范,不得徑行適用高位階之法規(guī)范,除非缺乏適當(dāng)之低位階法規(guī)范可資適用。”他進(jìn)而闡述了適用優(yōu)先原則的具體內(nèi)涵:“若系爭(zhēng)法律問(wèn)題已有相關(guān)低位階法規(guī)范(如法律)加以規(guī)范時(shí),法官即應(yīng)適用該普通法律審判,不可舍棄內(nèi)容較具體的普通法律規(guī)定于不顧,反而直接引用內(nèi)容較抽象的憲法上基本權(quán)利規(guī)定,否則即有違立法者負(fù)有憲法所委托將憲法規(guī)定加以具體化、細(xì)致化與現(xiàn)實(shí)化的合憲性義務(wù)。”
(二)效力優(yōu)先原則與適用優(yōu)先原則的作用機(jī)理
⒈效力優(yōu)先與適用優(yōu)先的作用方式。究其實(shí)質(zhì),效力優(yōu)先原則與適用優(yōu)先原則均是以法的位階為基礎(chǔ)的法的適用方式:效力優(yōu)先原則是依法的位階自上而下的適用方式;適用優(yōu)先原則則是依法的位階自下而上的適用方式。按照效力優(yōu)先的原則,憲法作為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的效力,這種法律效力是先定的和毋庸置疑的,憲法效力是位于其下的一切法之效力的源泉,其它一切法律都不得與其相抵觸,如有抵觸則當(dāng)然無(wú)效。位于憲法之下的其它法律也遵循上一位階法律效力高于下一位階法律效力的原則,這樣所有的法律都依其所具有的不同的法律位階“對(duì)號(hào)入座”,從而形成一個(gè)結(jié)構(gòu)完整的法律位階“金字塔”體系。按照適用優(yōu)先的原則,無(wú)論是行政機(jī)關(guān)還是司法機(jī)關(guān),它們作出行政行為或司法裁判時(shí)都需要從處于法律位階相對(duì)底層的法律中尋找法律依據(jù),有法律依據(jù)則予以適用;若無(wú)法律依據(jù)則沿法律位階向上檢索,一直到檢索出相應(yīng)的法律依據(jù)為止,這一過(guò)程體現(xiàn)為沿著法律位階金字塔體系自下而上“逆向”適用的過(guò)程。
⒉效力優(yōu)先與適用優(yōu)先的作用環(huán)節(jié)。比較而言,效力優(yōu)先主要作用于立法環(huán)節(jié),而適用優(yōu)先則主要作用于執(zhí)法和司法環(huán)節(jié)。議會(huì)立法與行政立法相結(jié)合是現(xiàn)代國(guó)家的立法發(fā)展趨勢(shì),無(wú)論是議會(huì)立法還是行政立法,都需要遵循效力優(yōu)先的原則。效力優(yōu)先原則要求各立法主體在立法時(shí)必須以同一領(lǐng)域的上位法作為參照,所立之法不得與上位法相抵觸,包括立法精神不得抵觸、立法范圍不得抵觸和立法內(nèi)容不得抵觸。但由于受到立法者認(rèn)知能力和立法技術(shù)的限制,所立之法完全、絕對(duì)地與上位法相吻合只能是一種理想狀態(tài),所立之下位法與上位法之間的抵觸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效力優(yōu)先原則一方面對(duì)下位法之立法提供指引,另一方面對(duì)改變和撤銷(xiāo)與上位法相抵觸的下位法提供依據(jù),因此效力優(yōu)先原則既控制下位法立法之過(guò)程,也控制下位法立法之結(jié)果———如果所立之下位法與上位法抵觸,則可以依據(jù)上位法對(duì)所立之下位法予以改變或撤銷(xiāo)。相對(duì)于立法這種法的創(chuàng)制行為而言,執(zhí)法和司法都是對(duì)已經(jīng)制定的法的執(zhí)行———行政執(zhí)法是行政主體依據(jù)制定法作出行政行為;行政訴訟則是對(duì)已經(jīng)作出的行政行為進(jìn)行合法性審查。無(wú)論是行政執(zhí)法過(guò)程中作出的行政行為還是行政訴訟中作出的司法裁判,它們都是將既定的法律規(guī)定作用于具體個(gè)案事實(shí)的結(jié)果。這個(gè)三段論推理過(guò)程的一個(gè)重要的環(huán)節(jié)是要選取作為三段論之大前提的法律依據(jù),由于上位法相對(duì)于下位法而言具有原則性、抽象性和廣泛性,而下位法則具有靈活性、具體性與特定性,因此無(wú)論是行政執(zhí)法還是司法裁判,都需要選取下位法來(lái)作為三段論之大前提,因?yàn)橐韵挛环榉梢罁?jù)作出的行政行為更加具有針對(duì)性,同理,以下位法為法律依據(jù)而作出的司法裁判更加具有確定性。從兩個(gè)原則的功能來(lái)看,效力優(yōu)先原則與適用優(yōu)先原則并不處于同一序位———效力優(yōu)先原則處于第一序位而適用優(yōu)先原則則處于第二序位。適用優(yōu)先的前提是下位法與上位法不抵觸,如果抵觸則不應(yīng)適用下位法而應(yīng)適用與之相對(duì)應(yīng)的上位法。從這里可以看出,適用優(yōu)先原則是由效力優(yōu)先原則所決定的,在下位法與上位法相抵觸時(shí),適用優(yōu)先原則則為效力優(yōu)先原則所取代。
⒊效力優(yōu)先原則與適用優(yōu)先原則的作用前提。效力優(yōu)先原則與適用優(yōu)先原則的作用前提是出現(xiàn)“法規(guī)競(jìng)合”情形。法規(guī)競(jìng)合是指不同位階或同一位階的法律對(duì)同一事項(xiàng)都作出規(guī)定。由于一個(gè)國(guó)家的立法是由多層次、多領(lǐng)域的立法所組成的復(fù)雜的法律體系,因此,處于不同位階的多個(gè)法律或處于同一位階的多個(gè)法律對(duì)同一事項(xiàng)同時(shí)作出規(guī)定的情形就是一種普遍的現(xiàn)象。對(duì)于不同位階的法規(guī)競(jìng)合而言,往往上位階越高的法律所作出的規(guī)定越抽象,而位階越低的法律所作出的規(guī)定越具體;對(duì)于同一位階的法規(guī)競(jìng)合而言,這些法律往往是從不同角度、不同側(cè)面對(duì)同一事項(xiàng)所作出的規(guī)定,這種“相同之中有不同”的立法主要是為了滿(mǎn)足不同職能管理部門(mén)對(duì)同一事項(xiàng)進(jìn)行管理的需要。法律依據(jù)的確定性是法的適用的基本要求,這是由法的指引作用所決定的:如果法律依據(jù)不具有確定性,則守法主體會(huì)顯得無(wú)所適從,因?yàn)樗麄儫o(wú)法明確究竟應(yīng)以哪一個(gè)法律作為自己行為的指引。法律依據(jù)的確定性要求行政行為和司法裁判的作出都必須要有明確具體的法律依據(jù),具體而言,當(dāng)出現(xiàn)法規(guī)競(jìng)合情形時(shí),行政機(jī)關(guān)和司法機(jī)關(guān)一般只能選擇競(jìng)合法規(guī)中的某一部而非多部法律作為依據(jù)。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旦出現(xiàn)法規(guī)競(jìng)合,執(zhí)法主體就需要對(duì)競(jìng)合的法規(guī)進(jìn)行選擇適用。適用優(yōu)先規(guī)則有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對(duì)于同一位階的法規(guī)競(jìng)合而言,適用優(yōu)先規(guī)則表現(xiàn)為“特別法先于一般法”和“新法先于舊法”;對(duì)于不同位階的法規(guī)競(jìng)合而言,適用優(yōu)先規(guī)則表現(xiàn)為“特別法先于一般法”和“下位法先于上位法”。①
第8篇: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范文
關(guān)鍵詞:民商法;海商法;遲延交付;留置權(quán);貨運(yùn)法
在我國(guó)司法實(shí)踐中,只要是《海商法》沒(méi)有明文規(guī)定的,便遵照民商法理論來(lái)審理海事?tīng)?zhēng)議案件。本文從海商法與民法的密切聯(lián)系作為切入點(diǎn),依次從海商法遲延交付、承運(yùn)人留置權(quán)等多個(gè)貨運(yùn)法角度探討民法和海商法之間的融合。
一、海商法與民法之間的融合
(一)海商法與合同法承運(yùn)人留置權(quán)的融合
我國(guó)《海商法》第87條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向承運(yùn)人支付的運(yùn)費(fèi)、共同海損分?jǐn)偂谫M(fèi)和承運(yùn)人為貨物墊付的必要費(fèi)用以及應(yīng)當(dāng)向承運(yùn)人支付的其他費(fèi)用沒(méi)有付清,又沒(méi)有提供當(dāng)擔(dān)保的,承運(yùn)人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內(nèi)留置其貨物。”這條規(guī)定有一點(diǎn)頗具爭(zhēng)議,就是對(duì)“其”的解釋?zhuān)降资侵競(jìng)鶆?wù)人所有還是與債務(wù)人有牽連關(guān)系即可,在學(xué)界爭(zhēng)議極大。
為此,我們引入《合同法》第315條的規(guī)定:“托運(yùn)人或者收貨人不支付運(yùn)費(fèi)、保管費(fèi)以及其他運(yùn)輸費(fèi)用的,承運(yùn)人對(duì)相應(yīng)的運(yùn)輸貨物享有留置權(quán),但當(dāng)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這里使用的是“相應(yīng)的”一詞,即該條款注重的是貨物與債務(wù)人之間具有的牽連關(guān)系,而不一定必須為債務(wù)人所有。我認(rèn)為,對(duì)于海商法承運(yùn)人留置權(quán)問(wèn)題應(yīng)該融合入合同法的規(guī)定,這樣才能更好地貫徹了法律規(guī)定承運(yùn)人,留置權(quán)的目的,也符合利益衡量所要求的法律原則.更能滿(mǎn)足實(shí)踐的要求。加之我國(guó)已經(jīng)逐漸注意了善意留置權(quán)制度的合理性,《海商法》第25條所規(guī)定的船舶留置權(quán)也沒(méi)有要求標(biāo)的船舶必須為債務(wù)人所有。所以,在承運(yùn)人留置權(quán)問(wèn)題上,應(yīng)當(dāng)融入合同法的相關(guān)規(guī)定。
(二)海商法中對(duì)遲延交付的規(guī)定與民法中相關(guān)規(guī)定的融合
我國(guó)《海商法》對(duì)于貨物遲延交付的規(guī)定有著明顯的漏洞,我國(guó)《海商法》第50條第1款規(guī)定:貨物未能在明確約定的時(shí)間內(nèi),在約定的卸貨港交付的,為遲延交付。何為“明確約定的時(shí)間內(nèi)”?如果承托雙方遲遲不能達(dá)成共識(shí),并且承運(yùn)人違反直航適航義務(wù),進(jìn)而遲延交付給貨方造成損害,貨方如何以法律為依據(jù)向船方索賠,成了一個(gè)棘手的問(wèn)題。
《合同法》第290條第1款規(guī)定:“承運(yùn)人應(yīng)當(dāng)在約定期間或者合理期間內(nèi)將旅客、貨物安全運(yùn)輸?shù)郊s定地點(diǎn)。”可見(jiàn),承運(yùn)人在運(yùn)輸期間的適當(dāng)履行,表現(xiàn)為其按照運(yùn)輸合同約定的期間履行其義務(wù)和在合理的期間履行運(yùn)送義務(wù)兩種情況。但對(duì)于《合同法》第290條和《海商法》第50條的關(guān)系,學(xué)者眾說(shuō)紛紜,有人認(rèn)為《海商法》與《民法通則》、《合同法》是普通法與一般法的關(guān)系,《海商法》對(duì)于遲延交付已有明確的規(guī)定,故根據(jù)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的法律適用原則,《民法通則》、《合同法》的規(guī)定理應(yīng)不予適用,《海商法》所規(guī)定的遲延交付的文字意義極其明確,不具有擴(kuò)充解釋的空間,對(duì)其進(jìn)行司法解釋無(wú)異于二次立法,不符合立法原則和程序。也有人認(rèn)為,《合同法》第290條應(yīng)該適用,因?yàn)椤逗I谭ā返?0條并沒(méi)有對(duì)遲延交付進(jìn)行確切定義,所以,《合同法》的規(guī)定仍然可以補(bǔ)充適用。
二、民商法與海商法在合同相對(duì)性原則上的沖突與協(xié)調(diào)
(一)提單關(guān)系下對(duì)合同相對(duì)性原則的突破
提單關(guān)系中對(duì)合同相對(duì)性的突破是指承托雙方簽訂運(yùn)輸合同后,當(dāng)提單轉(zhuǎn)移到第三方手中時(shí),收貨人可以直接依據(jù)提單向承運(yùn)人行使運(yùn)輸合同下的權(quán)利,同時(shí)承擔(dān)相關(guān)義務(wù)。本來(lái)按照合同的相對(duì)性原理,合同權(quán)利義務(wù)只能由合同當(dāng)事人來(lái)行使,即貨物到了目的港后一旦發(fā)現(xiàn)貨損或遲延,應(yīng)該是收貨人通知發(fā)貨人,由發(fā)貨人根據(jù)運(yùn)輸合同來(lái)向承運(yùn)人主張違約責(zé)任。但根據(jù)目前的海商法的規(guī)定,收貨人可以直接根據(jù)提單向承運(yùn)人主張違約責(zé)任,如果承運(yùn)人拒絕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提單持有人還可以依據(jù)提單直接對(duì)承運(yùn)人提起訴訟。海商法的這種對(duì)合同相對(duì)性原理的突破從實(shí)踐的角度而言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原因在于國(guó)際貿(mào)易的買(mǎi)、賣(mài)雙方處于不同國(guó)家,如果收貨人或提單持有人不能直接依據(jù)提單行使運(yùn)輸合同下的權(quán)利,那么一旦目的港發(fā)生貨物的滅失、損壞或遲延交付,則收貨人只有兩種選擇:第一種選擇是向發(fā)貨人尋求幫助,但如果發(fā)貨人不幫助怎么辦?而另一種選擇則是依據(jù)貿(mào)易合同向賣(mài)家(發(fā)貨人)提起訴訟,但貿(mào)易合同和運(yùn)輸合同畢竟是兩個(gè)不同的合同,收貨人很可能無(wú)法根據(jù)貿(mào)易合同來(lái)保護(hù)自己的利益。因此我國(guó)《海商法》承認(rèn)在收貨人和承運(yùn)人之間的合同關(guān)系的存在。
(二)有關(guān)實(shí)際承運(yùn)人責(zé)任的規(guī)定亦是對(duì)合同相對(duì)性原則的突破
我國(guó)《海商法》第61條規(guī)定承運(yùn)人的責(zé)任適用于實(shí)際承運(yùn)人,第63條進(jìn)一步規(guī)定了當(dāng)承運(yùn)人與實(shí)際承運(yùn)人都負(fù)有賠償責(zé)任時(shí),在此責(zé)任范圍內(nèi)負(fù)連帶責(zé)任。即發(fā)貨人、收貨人既可以向承運(yùn)人主張賠償,也可以向?qū)嶋H承運(yùn)人賠償,或者同時(shí)向二者主張賠償。
承運(yùn)人與發(fā)貨人、收貨人之間是運(yùn)輸合同關(guān)系,而承運(yùn)人與實(shí)際承運(yùn)人之間也是運(yùn)輸合同關(guān)系。如果固守合同相對(duì)性,那么一旦出現(xiàn)糾紛,解決辦法就只能是發(fā)貨人、收貨人與承運(yùn)人之間依照運(yùn)輸合同解決,而后承運(yùn)人再根據(jù)運(yùn)輸合同向?qū)嶋H承運(yùn)人追償。但考慮到實(shí)際承運(yùn)人是實(shí)際履行方,最終結(jié)果都由實(shí)際承運(yùn)人承擔(dān),因此允許發(fā)貨人、收貨人直接與實(shí)際承運(yùn)人解決其糾紛就是可行的。從訴訟的角度來(lái)說(shuō),同一個(gè)訴訟標(biāo)的,能夠通過(guò)一次訴訟解決肯定比通過(guò)兩次訴訟解決更能節(jié)約時(shí)間和成本。因此,通過(guò)立法,允許發(fā)貨人、收貨人直接對(duì)實(shí)際承運(yùn)人提起訴訟是對(duì)合同相對(duì)性的又一突破。
三、結(jié)語(yǔ)
第9篇: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范文
一、拒不執(zhí)行判決、裁定罪與妨害公務(wù)罪的相同
拒不執(zhí)行判決、裁定罪,是指對(duì)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zhí)行而拒不執(zhí)行,情節(jié)嚴(yán)重的行為。妨害公務(wù)罪是以暴力、威脅的方法,阻礙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依法執(zhí)行職務(wù)的行為。拒不執(zhí)行判決、裁定罪與妨害公務(wù)罪有一定的相似之處,表現(xiàn)在:
其一,兩者可能是妨害國(guó)家機(jī)關(guān)正常行使職權(quán)、發(fā)揮職能的行為;
其二,二者都是故意犯罪,且都有可能存在對(duì)抗國(guó)家公務(wù)活動(dòng)的故意;
其三,當(dāng)拒不執(zhí)行判決、裁定罪表現(xiàn)為行為人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人民法院的強(qiáng)制執(zhí)行活動(dòng)時(shí),其客觀行為表現(xiàn)就與妨害公務(wù)罪完全相同。
二、拒不執(zhí)行判決、裁定罪與妨害公務(wù)罪的區(qū)分
二者相區(qū)分的關(guān)鍵在于其犯罪的客觀這方面、犯罪主體不同:
其一、妨害公務(wù)罪通常必須是以暴力、威脅方法實(shí)施,且行為人侵害公務(wù)人員的行為必須發(fā)生在后者依法執(zhí)行公務(wù)期間,而拒不執(zhí)行判決、裁定罪則不要求必須使用暴力、威脅的方法,可以是能夠損害法院裁判約束力、權(quán)威性的任何方法,比如欺騙隱瞞、消極抵制、無(wú)理取鬧等等。而且,拒不執(zhí)行判決、裁定罪也不要求必須發(fā)生在人民法院依法執(zhí)行職務(wù)期間;
其二、妨害公務(wù)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而拒不執(zhí)行判決、裁定罪的主體則是特殊主體,即必須具有執(zhí)行判決、裁定義務(wù)的當(dāng)事人或者依照法律對(duì)判決、裁定負(fù)有協(xié)助執(zhí)行義務(wù)的人。本條(妨害公務(wù)罪)與第313條(拒不執(zhí)行判決、裁定罪)相比而言,前者應(yīng)系普通法,后者應(yīng)系特別法。故對(duì)這類(lèi)案件應(yīng)該依本法第313條的規(guī)定,以拒不執(zhí)行判決、裁定罪定罪量刑。
三、區(qū)別二罪應(yīng)注意的問(wèn)題
實(shí)際上,拒不執(zhí)行判決,裁定也是一種妨害公務(wù)的行為,但本罪客觀方面不以使用暴力、威脅方法為要件,其妨害的公務(wù)內(nèi)容是特定的法院裁判的執(zhí)行,因此,本條相對(duì)于《刑法》第277條妨害公務(wù)罪而言,是特殊法條,是交叉型的法條競(jìng)合關(guān)系。
四、觸犯二罪的處罰
相關(guān)熱門(mén)標(biāo)簽
相關(guān)文章閱讀
相關(guān)期刊推薦
-

中國(guó)普通外科
級(jí)別:SCI期刊
榮譽(yù):Caj-cd規(guī)范獲獎(jiǎng)期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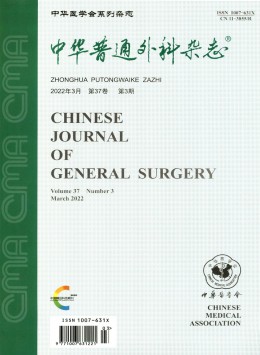
中華普通外科
級(jí)別:北大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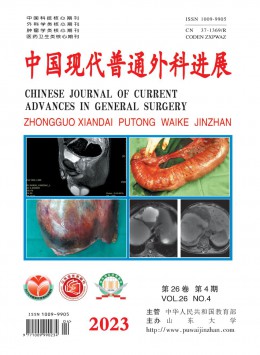
中國(guó)現(xiàn)代普通外科進(jìn)展
級(jí)別:統(tǒng)計(jì)源期刊
榮譽(yù):Caj-cd規(guī)范獲獎(jiǎng)期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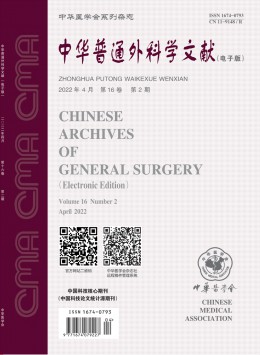
中華普通外科學(xué)文獻(xiàn) · 電子版
級(jí)別:統(tǒng)計(jì)源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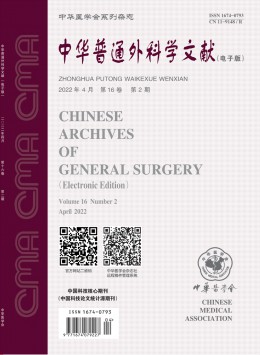
中華普通外科學(xué)文獻(xiàn)
級(jí)別:統(tǒng)計(jì)源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