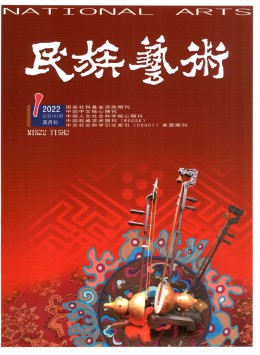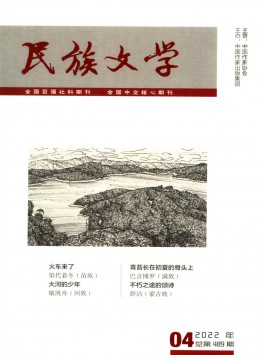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重要性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重要性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重要性范文
論文關(guān)鍵詞:親情倫理;普世倫理;環(huán)境倫理;類;共同體
“親情倫理”、“普世(普遍)倫理”、“環(huán)境(生態(tài))倫理”是當(dāng)前倫理學(xué)討論與研究的幾個(gè)熱點(diǎn)問題,本文將三者放在一起來考察,嘗試在揭示三者之間內(nèi)在的理論關(guān)聯(lián)性的過程中,一方面更好地理解這些問題,推進(jìn)研究的深入發(fā)展;另一方面,試圖通過這種關(guān)聯(lián)性研究,探討和說明人類道德共同體與倫理學(xué)理論演化的內(nèi)在關(guān)系及其基礎(chǔ)這一倫理學(xué)理論的基礎(chǔ)性問題。
一
對(duì)于傳統(tǒng)儒家倫理思想和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的“親情(家族)本位”定性,幾乎沒有異議,而如何看待和評(píng)價(jià),是爭(zhēng)論的主要問題。
就本文的論題而言,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講,這種“親情(家族)本位”的社會(huì)關(guān)系與倫理思想其實(shí)并不只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所特有的,在人類歷史上,各人類群體都經(jīng)歷了這樣一個(gè)階段,其實(shí)也體現(xiàn)著倫理關(guān)系與思想的起源和發(fā)展演化的普遍性。馬克思關(guān)于人的存在依次經(jīng)歷“人的依賴關(guān)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chǔ)的人的獨(dú)立性”和“建立在個(gè)人全面發(fā)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huì)生產(chǎn)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huì)財(cái)富這一基礎(chǔ)上的自由個(gè)性”三個(gè)階段或形態(tài),也是人作為倫理主體的基本存在形態(tài),就是通常所謂群體主體、個(gè)體主體、自由人聯(lián)合體即類主體。
由于中國古代奴隸制的形成是由氏族直接到國家,國家的組織形式與血緣氏族制相結(jié)合,其后以血緣宗法關(guān)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形式完善,歷史漫長,加上缺乏促使西方倫理普遍化的社會(huì)、宗教、科學(xué)文化背景,這種特殊的社會(huì)歷史條件,使得“親情(家族)本位”這一倫理道德傳統(tǒng)與思想觀念顯得特別突出,使我們?cè)谂羞@種“特殊性”時(shí)可能忽視了它的“普遍性”,但對(duì)于本文的論題而言,這種普遍性是有重要意義的。
自然主義倫理學(xué)家拉蒙特曾說過,“人類的良心”、“是非觀念”等,最初以家庭為其活動(dòng)范圍,逐漸發(fā)展成為一個(gè)部落或城市的標(biāo)準(zhǔn),然后擴(kuò)展到民族,最終則從民族推廣到全人類。…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人類倫理關(guān)系與倫理思想演化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
從進(jìn)化論的角度看,人類社會(huì)的道德是和導(dǎo)致人類出現(xiàn)的有機(jī)體進(jìn)化的整個(gè)過程聯(lián)系在一起的,達(dá)爾文認(rèn)為,人所特有的、使其與動(dòng)物區(qū)別開來的道德品質(zhì)的自然根據(jù)存在于某些動(dòng)物所具有的社會(huì)本能里。恩格斯也曾指出,社會(huì)本能曾經(jīng)是從猿發(fā)展到人的重要杠桿之一。社會(huì)本能使得一個(gè)動(dòng)物對(duì)其同類有一定的“同情”,并對(duì)它們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wù)”,這些感情和服務(wù)絕不會(huì)擴(kuò)展到同一物種的所有個(gè)體,只是局限于同一群體的成員。
因而最初的人類道德共同體及其意識(shí)范圍也不是整個(gè)人類,或者說,這時(shí)的道德主體不會(huì)像有的論者認(rèn)為的那樣已具有普遍意義上的“類意識(shí)”和“類道德”。這時(shí)的“類”只能是群體性的,比如氏族或者部落,氏族、部落的圖騰崇拜可能說明,原始人并不把其他群體看作自己的同類。據(jù)人類學(xué)家考證,人類歷史大概已有四百多萬年,其中大多數(shù)時(shí)間人類都以幾人到十幾人、幾十人為一群體,幾個(gè)小群體為一群落。也就是說,人類早期關(guān)系基本是一種群體性關(guān)系,而構(gòu)成群體的紐帶是血緣親情關(guān)系。
雖然傳統(tǒng)倫理學(xué)一直認(rèn)為,對(duì)動(dòng)物來說不可能有“共同體”意識(shí),更不會(huì)有“道德”意識(shí),人類只有從自然狀態(tài)進(jìn)入社會(huì)狀態(tài)之后,從“自然共同體”進(jìn)入“社會(huì)共同體”,真正的倫理道德及道德意識(shí)才會(huì)出現(xiàn),但在環(huán)境(生態(tài))倫理蓬勃發(fā)展的今天,探詢?nèi)祟惖赖碌淖匀黄鹪春突A(chǔ)也就具有了重要意義,環(huán)境(生態(tài))倫理使“自然”問題進(jìn)入了倫理學(xué)理論視野,也必然帶來了對(duì)傳統(tǒng)倫理思想的“類”基礎(chǔ)與“類”性質(zhì)的挑戰(zhàn)和系統(tǒng)反思。
二
就傳統(tǒng)儒家和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中“親情本位”倫理思想而言,其背后的“類”意識(shí)首先與貴賤等級(jí)思想意識(shí)聯(lián)系在一起,這種等級(jí)思想背后也是一種“類”意識(shí)。在孔子看來,作為貴族士大夫的“君子”與作為普通大眾的“小人”之間有“類”的差別。在人類歷史中存在過的各種“歧視”,實(shí)質(zhì)上就是不把被歧視者看成是自己同類從而不公正地對(duì)待他們。
因此也可以說,所謂人類的“進(jìn)步”歷程,一個(gè)重要的方面就表現(xiàn)為越來越把我們自己和看起來與我們很不相像的人們之間的相似性看作在重要性上超過差異性的過程。從歷史的角度看,道德進(jìn)步的過程也是一個(gè)道德關(guān)懷的對(duì)象不斷擴(kuò)大的過程,所謂人類的“類意識(shí)”是與其存在“共同體”和交往活動(dòng)的范圍相伴隨而發(fā)展演化的。
但人類歷史也表明,將“同類”外延擴(kuò)展到一個(gè)國家內(nèi)部的全體成員是相當(dāng)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各種種族歧視還未離我們遠(yuǎn)去。但時(shí)至20世紀(jì)、尤其是進(jìn)入21世紀(jì),社會(huì)歷史發(fā)展已經(jīng)顯示出人類的生存單位越來越從民族國家的層級(jí),轉(zhuǎn)移到全人類的層級(jí),全球化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人類間的相互認(rèn)同以及生存共同體的進(jìn)一步擴(kuò)展,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清晰,這就是“普世倫理”問題產(chǎn)生的社會(huì)歷史背景。雖然與“普世倫理”相關(guān)的具體問題目前仍然充滿爭(zhēng)議,但有一點(diǎn)應(yīng)該可以看到,在人類實(shí)踐與交往進(jìn)入全球化的時(shí)代,我們需要在全人類范圍普遍適用的倫理與行為規(guī)范,需要某種普世倫理來處理全球性的問題,以及為人類的交往與協(xié)作提供規(guī)范指導(dǎo)。社會(huì)發(fā)展的實(shí)際進(jìn)程已使所有人類群體之間形成越來越密切的依賴關(guān)系,站在這個(gè)基點(diǎn)之上思考,任何主體都不能把別人看成是與自己不同的存在。普世倫理研究中受到普遍關(guān)注的“金規(guī)”,其核心基礎(chǔ)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共同性與共通性,即“類”的共同基礎(chǔ)。
在這種歷史與理論背景中,國內(nèi)一些研究者提出人是一種“類存在”,人類的“類本質(zhì)”、“類屬性”是倫理學(xué)的基礎(chǔ),認(rèn)為體現(xiàn)“類本位”的倫理道德“類生命一類價(jià)值”范式是當(dāng)代倫理學(xué)的根本要求,甚至明確提出21世紀(jì)倫理學(xué)的走向是“類倫理學(xué)”。
但是,另一方面,與這種人與人之間“類意識(shí)”以及人類倫理道德和倫理學(xué)理論普遍化相伴隨的,卻也是“人”與“自然”、“社會(huì)”與“自然”分離的發(fā)展和演化趨勢(shì)。因?yàn)椴徽撌恰坝H情倫理”還是“普世倫理”以及所謂的“類倫理”,其視域都是在人際之間的范圍內(nèi),在此意義上,都屬于“傳統(tǒng)”倫理思想。在傳統(tǒng)倫理學(xué)中我們只對(duì)標(biāo)準(zhǔn)的人類及其共同體負(fù)有義務(wù),即便在近現(xiàn)代傳統(tǒng)倫理思想的視域中,倫理學(xué)也是研究“人倫之理”、“做人之理”,是有關(guān)人與人關(guān)系的學(xué)問。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在于某種“人類例外論”,即,強(qiáng)調(diào)人性在自然與宇宙中的特殊性,只有人類才有道德身份或資格,其他事物只有在服務(wù)于人類利益時(shí)才有價(jià)值。亞里士多德和阿奎那認(rèn)為人類有道德身份是因?yàn)樗麄冇兄R(shí),可以思考和選擇.而其他生物缺乏這種能力;在笛卡兒那里,意識(shí)是道德身份的判斷根據(jù);康德把權(quán)利和道德身份限制于“主體”和“目的”,只有能自主的生物,有自由意志和理性的生物才有道德身份。
l7世紀(jì)以來,西方所謂“現(xiàn)代性”思想發(fā)展中的“自然(世界)祛魅”,其背后就是一種主客二分思維模式與機(jī)械論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描畫的世界圖景中,只有人是主體,一切非人的存在皆為客體,人類征服自然是完全正當(dāng)?shù)摹_@種對(duì)世界與自我及二者關(guān)系的認(rèn)識(shí)和理解,一方面使西方倫理學(xué)主流確立了普遍化的發(fā)展方向,它強(qiáng)調(diào)人類的同質(zhì)性,以及倫理學(xué)理論的邏輯一致性、科學(xué)性,這一切都導(dǎo)向“普遍性”,尋求普遍倫理。另一方面,認(rèn)為人屬于社會(huì)存在,社會(huì)獨(dú)立于自然,甚至與自然相對(duì)立,因而只能從人類自身的社會(huì)文化與思想成就中探詢自己的本性和生存意義。目前一些有代表性的觀點(diǎn)對(duì)環(huán)境倫理學(xué)的批評(píng)就是認(rèn)為人在本質(zhì)上是社會(huì)性的,與自然界其他生物有本質(zhì)區(qū)別,因此,如果認(rèn)為自然與人具有平等的權(quán)利或地位,就是沒有抓住人的社會(huì)本質(zhì)。以自然或自然物的價(jià)值或權(quán)利等來論證環(huán)境倫理理論,就是犯了“自然主義謬誤”。不同意見者則認(rèn)為,只強(qiáng)調(diào)人類的社會(huì)性,忽視甚至否定人類存在的生物性.必然看不到人類對(duì)自然的依賴以及人類與自的內(nèi)在統(tǒng)一性。仔細(xì)看一下,在這種“自然”與“社會(huì)”問題背后仍然主要是一種“類”思維方式與“類意識(shí)”,即人的“類本質(zhì)”以及與其他生命形式的“類差異”或“類同一性”。
三
不論是“親情倫理”還是“普世(普遍)倫理”,以及歷史上其他的倫理思想,其思想理論基礎(chǔ)都是關(guān)于“類”的觀念,“類”與“類思維”、“類意識(shí)”成為道德共同體與倫理學(xué)思想的核心理念。這里的“類”有兩種意義,一是人與人之間的“分類”,一種是人類相對(duì)于其他物種而言的“類”。“類”與“共同體”之間的關(guān)系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就第一種意義的“類”而言,“類”與“共同體”范圍基本一致,在第二種“類”的意義上,“共同體”往往比“類”的范圍小,普世倫理是在這一意義基礎(chǔ)上尋求“類”與“共同體”一定程度上統(tǒng)一的努力。但不論在哪一種意義上講,在這種倫理學(xué)觀念與思維模式中,人與植物、動(dòng)物和土壤以及包含著各種生物的大自然顯然不是任何道德意義上的共同體。如果要認(rèn)真嚴(yán)肅地對(duì)待環(huán)境(生態(tài))倫理學(xué)問題,就不得不對(duì)傳統(tǒng)倫理學(xué)的“類”及“共同體”概念進(jìn)行反思。
從環(huán)境倫理學(xué)各種理論來看,動(dòng)物權(quán)利論和動(dòng)物解放運(yùn)動(dòng)將倫理道德關(guān)系的范圍擴(kuò)展到了動(dòng)物;生物中心主義進(jìn)一步認(rèn)為所有生物和生命形式在倫理道德關(guān)懷上都應(yīng)該是平等的;生態(tài)中心主義再進(jìn)一步將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作為倫理學(xué)的基礎(chǔ)和道德對(duì)象;生態(tài)中心主義和深生態(tài)學(xué)以進(jìn)化論為基礎(chǔ),以宇宙演化和復(fù)雜性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為論證形式,論證宇宙中人類以外事物的內(nèi)在價(jià)值以及與人類的平等地位。各種理論形態(tài)為它們各自提出的理論提供了理論基礎(chǔ)和論證,其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有:(1)論證人類之外的其他物種以及自然本身的內(nèi)在價(jià)值; (2)希望通過對(duì)其他動(dòng)物的知覺和忍受痛苦的感受的論證來將倫理關(guān)懷的范圍擴(kuò)展到動(dòng)物身上;(3)論證動(dòng)植物與自然物具有與人類雖然程度不同,但實(shí)質(zhì)上一樣的“主體性”。其中主要是圍繞“內(nèi)在價(jià)值”問題而進(jìn)行論說的。環(huán)境倫理將自然物也作為倫理思維或道德關(guān)懷的對(duì)象,要求人對(duì)自然也履行道德義務(wù),實(shí)質(zhì)上也就承認(rèn)自然物也是人類的同伴或人類與自然也構(gòu)成道德共同體關(guān)系,這看起來是對(duì)傳統(tǒng)倫理學(xué)與倫理思想的“反叛”或“顛覆”。
但另一方面,環(huán)境(生態(tài))倫理學(xué)的各種理論形態(tài)雖然在具體理論上相差很遠(yuǎn),但思維與論證模式具有一致性,那就是或者論證動(dòng)物、植物、生命、生態(tài)系統(tǒng)等也具有內(nèi)在價(jià)值,或者尋求一種能夠獲得道德身份或道德資格的共同屬性,比如感受痛苦的能力、目的性、自組織性等。這些思路的目標(biāo)在于通過這些論證,想方設(shè)法使它們與人類具有某種質(zhì)的同一性,反映著追求共同本質(zhì)的本質(zhì)主義思維模式,實(shí)質(zhì)上是對(duì)傳統(tǒng)倫理學(xué)中“類”概念的延伸與拓展,只不過這里的“類”不再局限于人類,而是所有動(dòng)物或者所有生命的“類”,但其思維方式和推理基礎(chǔ)還是“類”概念與“類”思維模式。環(huán)境(生態(tài))倫理學(xué)討論中的人類中心主義與生物(生態(tài))中心主義之爭(zhēng),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類”與“共同體”涵義與范圍之爭(zhēng)。
這樣,構(gòu)成倫理學(xué)思想基礎(chǔ)的“類”意識(shí)和“類”概念,隨著人類社會(huì)歷史的發(fā)展演化,從家庭(氏族、部落)發(fā)展到民族(宗教、文化),到全人類的范圍和視域,再進(jìn)一步擴(kuò)展到自然環(huán)境,關(guān)注一般意義的生命——不僅人的生命,也包括動(dòng)植物的生命。在這樣的一種視野中,全球(普遍)倫理、生命倫理、環(huán)境(生態(tài))倫理等領(lǐng)域中許多問題的爭(zhēng)論其實(shí)就是關(guān)于我們應(yīng)該給予倫理關(guān)心的“類”的外延問題。那就是,從自己的家庭、家族到本民族,從自己的民族到世界各民族人類,從現(xiàn)實(shí)的人到潛在的人類(胚胎與后代),從現(xiàn)實(shí)與潛在的人類到其他自然物種、一切生命形式。現(xiàn)代倫理學(xué)的許多重要問題,比如全球倫理、生命倫理、克隆人、代際倫理、生態(tài)與環(huán)境倫理等,歸結(jié)起來,在最根源處,仍然與我們對(duì)“類”的內(nèi)涵及其外延的歷史性理解密切相關(guān)。
在環(huán)境倫理學(xué)中,有人明確地意識(shí)到這種共同體的擴(kuò)展方式,文茲(peterwenz)把環(huán)境倫理學(xué)中擴(kuò)展共同體理論稱為“同心圓理論”,西爾凡(richardsylvan)和普蘭伍德(valplumwood)則比之為樹的年輪。以這種視角來看,在離自我最近的圓圈里是對(duì)家庭和鄰人的義務(wù),往外依次為對(duì)社區(qū)、國家和對(duì)全人類的義務(wù),還有對(duì)未來的后代的義務(wù),再往外推是自然界,包括動(dòng)物、植物、大地的義務(wù)。這種思想與先生關(guān)于傳統(tǒng)中國社會(huì)的“差序格局”概括和人際關(guān)系的圈狀“波紋”比喻實(shí)質(zhì)上是一樣的。
以羅爾斯頓為代表的環(huán)境倫理學(xué)理論提出用“整體主義”的世界觀來看待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認(rèn)為人與其他生物以及整個(gè)自然界形成一個(gè)生態(tài)共同體,具有存在的直接同一性,這可看作是對(duì)環(huán)境倫理的“共同體式”論證。他們將整個(gè)自然作為一個(gè)整體和大系統(tǒng),人的社會(huì)只是其中一部分,并且從屬于這個(gè)整體。人與人的倫理是從關(guān)于人與所有生命的普遍關(guān)系中推導(dǎo)出來的。雖然這種思想重新用生機(jī)主義的觀點(diǎn)來看待自然與自然物,主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共同體”,以“共同體”及其意識(shí)作為人與自然倫理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但“共同體”與“類”思維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在最根源處,不論是“類”還是“共同體”,背后都是某種存在與利益的一致性與相關(guān)性。不過在人與環(huán)境的倫理關(guān)系上,“共同體”論證具有更多合理性。“類”更多地帶有形而上的抽象性,與傳統(tǒng)倫理學(xué)的人性論聯(lián)系密切,帶有更多靜態(tài)特點(diǎn)。“共同體”思想與進(jìn)化論能更好地結(jié)合起來,體現(xiàn)出動(dòng)態(tài)性與相互性,更適合人與環(huán)境之間的關(guān)系。這種“共同體”思想一方面為多元文化背景下“同質(zhì)性”人類及群體間的關(guān)系提供了基礎(chǔ),另一方面,也為人類處理與其他物種、自然界等“異質(zhì)性”元素之間關(guān)系提供了思想資源。
四
有不少論者將環(huán)境倫理中的“整體主義”、“生機(jī)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聯(lián)系起來。著名的后現(xiàn)代主義者大衛(wèi)·格里芬也持一種整體主義和有機(jī)論的自然觀與科學(xué)觀,并且針對(duì)現(xiàn)代主義的“自然祛魅”提出了“自然的返魅”觀點(diǎn),確與環(huán)境(生態(tài))倫理許多理論觀點(diǎn)相合。
但就整體而言,在后現(xiàn)代主義視域中,以上所述研究方法與論證模式表現(xiàn)著傳統(tǒng)(古希臘以來)哲學(xué)與科學(xué)尋求確定性、普遍性的思維方法。這種思維方式被稱作“本質(zhì)主義”、“基礎(chǔ)主義”、“歸約主義”,它們都屬于一種“系譜”式的論證,或者是一種“根的神話”。這種思維模式與論證方式在普世倫理研究及其思想資源中的表現(xiàn),我們已有專文論述,并對(duì)相關(guān)概念和思想進(jìn)行了比較詳細(xì)的闡述,這里不再贅言。需要指出的是,在關(guān)于環(huán)境倫理的研究與論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思維方式與論證模式的影響,不論是對(duì)“內(nèi)在價(jià)值”、“生命主體”、“主體性”、“感受痛苦的能力”還是“整體性”、“有機(jī)性”、“神圣性”、“共同體”的論證,實(shí)際上都在尋求一個(gè)支撐點(diǎn)或第一原理,以此來確立判定倫理道德身份的標(biāo)準(zhǔn)和理論建構(gòu)的合法性。因此,就環(huán)境倫理學(xué)思想中體現(xiàn)的環(huán)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生物(生態(tài))中心主義、整體主義、有機(jī)論等思想理論,一方面確實(shí)區(qū)別和反對(duì)原子式、人類中心主義、機(jī)械論的“現(xiàn)代性”思維模式,但另一方面在思維與理論范式上表現(xiàn)出的仍然主要是“現(xiàn)代性”特征。
對(duì)傳統(tǒng)倫理思想的批判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認(rèn)識(shí)已有的自我與他人、人與自然關(guān)系以及關(guān)于自然本身的思想觀念框架,從這一意義來講,不論是否贊同環(huán)境倫理思想的主張,我們都不得不重新思考“類”和“共同體”這兩個(gè)范疇。而近年來大量關(guān)于“類倫理學(xué)”的觀點(diǎn),顯然沒有意識(shí)到這個(gè)問題。
第2篇: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重要性范文
[關(guān)鍵詞]公民性 公民社會(huì) 汶川地震
澄清“公民性”內(nèi)涵,是闡釋建構(gòu)“公民社會(huì)”為什么應(yīng)當(dāng)成為我們值得追求之目標(biāo)的理由。如學(xué)者所論,衡量一個(gè)社會(huì)是否進(jìn)入公民社會(huì),可以通過一系列外在指標(biāo)來觀察,如相關(guān)的法制建設(shè)、社團(tuán)的發(fā)展水平和生存環(huán)境、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的關(guān)系、個(gè)人對(duì)公益事業(yè)的參與等等,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檢驗(yàn)它的內(nèi)在屬性,這就是civility,也可譯為“公民品格”、“公民屬性”或“公民精神”等等。這里將其直譯為“公民性”。按美國學(xué)者希爾斯的說法,所謂“公民社會(huì)”(civil society),就是“社會(huì)成員相互之間的行為體現(xiàn)公民性(civility)的社會(huì)”。根據(jù)希爾斯的論證,從三個(gè)方面對(duì)“公民性”做概括理解。
“公民性”是關(guān)懷整體社會(huì)福祉的一種態(tài)度
“公民性”的關(guān)懷視域不是某一局部,它是超越階級(jí)、黨派、地域、血緣群族、性別、種族、等等的界限,而關(guān)懷整體社會(huì)福祉的一種態(tài)度。所以,公民性是具有同時(shí)涵蓋個(gè)人主義(individualistic)、地區(qū)或集團(tuán)性(parochial)和“整體性”(holistic)三種要素的特質(zhì)。它以實(shí)現(xiàn)整體性的福祉和較大的利益為依歸。這種關(guān)懷的視域,不在于共同體規(guī)模的大小、人口數(shù)量以及內(nèi)部種族的異質(zhì)性,而在于強(qiáng)調(diào)對(duì)多樣性包容的層次究竟達(dá)到一個(gè)什么程度。換句話說,在一個(gè)固定的共同體中,不同的個(gè)人、群體或派別之間,產(chǎn)生不同和差別是必然的。面對(duì)這些差異如何行為?進(jìn)一步深究,實(shí)施這些行為所依據(jù)的原則又是什么?它具有哪些特質(zhì)和表現(xiàn),就是“公民性”所涵蓋的內(nèi)容。
任何一個(gè)社會(huì)共同體都有自己獨(dú)特的內(nèi)在精神和民族秉性,這是該共同體之所以可以區(qū)別于其它共同體的要害所在。現(xiàn)代社會(huì)學(xué)的鼻祖之一的涂爾干(EmileDurkheim)把它稱之為“社會(huì)力”(Social force)。并認(rèn)為,雖然一個(gè)共同體的內(nèi)在屬性是只能意會(huì)不能言說的,但它本身卻內(nèi)含著極大的能量,有什么樣性質(zhì)的“社會(huì)力”,就會(huì)呈現(xiàn)什么樣的社會(huì)關(guān)系,進(jìn)而形成什么樣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例如,在中國古代社會(huì),儒家思想占統(tǒng)治地位。在這其中以“孝道”為基礎(chǔ)的家庭倫理是中國的“社會(huì)力”表現(xiàn),于是在處理人際關(guān)系時(shí)就會(huì)倡導(dǎo)“子為父隱,父為子隱”,并此外推,從“修身”、“齊家”、“治國”,一直到“平天下”,建構(gòu)出一整套價(jià)值準(zhǔn)則。而在西方社會(huì),起碼自羅馬帝國以來,就逐漸地形成了一套以法律(特別是其民法體系)為治世基礎(chǔ)的習(xí)慣,在其背后則受一套超越的信仰所支撐,是謂“高級(jí)法”。因此,學(xué)術(shù)界把具有“精神”品性的東西,稱之為“看不見的實(shí)在”(invisible reality),也有學(xué)者用“氣質(zhì)”(ethos)一詞予以表征。
這里所談的“公民性”也同樣具有這種“看不見之實(shí)在”的屬性,它也必須借助于其它的載體才能得以展現(xiàn),而“公民性”與其它各種類型的“社會(huì)力”不同的內(nèi)在氣質(zhì),就在于起碼在自己生存的共同體范圍內(nèi),實(shí)現(xiàn)公民之間的“充分尊重”。這樣的“內(nèi)在氣質(zhì)”要求任何一位公民,看待世界的眼界應(yīng)當(dāng)是多元的,不以某一固定的框架作為唯一準(zhǔn)則去刪改世界,也不僅僅強(qiáng)調(diào)一種局部意志和利益而強(qiáng)求其它局部跟隨改變。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希爾斯才說:“公民性”之特質(zhì)之所以一般地被解釋為公民個(gè)人所表現(xiàn)出來的某種處世態(tài)度和行為方式,“意味著禮貌、談吐優(yōu)雅、謙遜、尊重他人、自我克制、紳士風(fēng)度、文雅、高尚、良好的風(fēng)尚、斯文”等等,就是因?yàn)樵谶@些用詞和行為的背后,其更深的含義是摒棄“非違法的自我放縱”,“顧及他人的感受,特別是顧及他們要求受到尊重的欲望”。這樣,承認(rèn)他人至少具有與自己同等的尊嚴(yán),而決不貶低他人的尊嚴(yán),就成為衡量“公民性”的基礎(chǔ)原則和最后底線。
“公民性”表現(xiàn)為共同體成員自身所擁有的“良好風(fēng)尚”
如上所述,內(nèi)在氣質(zhì)之類的“看不見的實(shí)在”必須經(jīng)由物質(zhì)或行為載體才能得以展現(xiàn),那么,公民行為中體現(xiàn)出來的那些“良好風(fēng)尚”就成為“公民性”最重要的載體之一。與“公民性”的抽象屬性不同,這些“良好風(fēng)尚”則是實(shí)實(shí)在在可感可觸可聞可見的,而且隨時(shí)隨地地表現(xiàn)在社會(huì)生活的方方面面。
高丙中把“公民性”所體現(xiàn)出來的“良好風(fēng)尚”具體概括為7項(xiàng)內(nèi)容:禮貌成為普遍的社會(huì)行為;避免和排斥強(qiáng)制性暴力;對(duì)他人的容忍和寬容的心態(tài);對(duì)陌生人所持有的同情心;獨(dú)立自治的自愿精神;平等地尊重共同體中任何成員;對(duì)超出熟人世界以外之共同體抽象符號(hào)的認(rèn)同。
高丙中對(duì)這7項(xiàng)內(nèi)容已做過逐條闡述,此處不贅,這里所要稍加解釋的是上述概括中出現(xiàn)的“陌生人”和“熟人世界”這樣一種范疇。一般而言,尤其在中國文化環(huán)境之下,人們對(duì)待自己的所熟悉的親屬、朋友、師友等等,往往可能表現(xiàn)出一定程度的關(guān)愛、理解、尊重和寬容,但對(duì)于超出這個(gè)范圍以外的“陌生人”則可能呈現(xiàn)另外的一種行為。上面所表現(xiàn)出來的那些美德要素,會(huì)伴隨著陌生度加深而呈下降趨向。這種狀態(tài)稱之為“群族倫理”,而能稱得上“公民性”的品質(zhì)一定具有某種普遍性的特征。就是說,無論對(duì)方是什么人,一方面,我們都以同樣的一套原則相處;另一方面,別人也同樣以這樣的原則與你相處,于是在陌生人之間就達(dá)成了某種行為的共識(shí),這種共識(shí)之下任何一方在接觸對(duì)方之前,就可能判斷出他將以怎樣的方式與自己相處。顯然,這種彼此行為的“可預(yù)期性”就將成為彼此信任的基礎(chǔ)。所以有學(xué)者定義說:“‘公民性’的規(guī)范圈出一套行為準(zhǔn)則的范圍,以便于公民可以對(duì)陌生人產(chǎn)生正確的預(yù)期”。而上述規(guī)定的7個(gè)方面,就是被劃定的“公民性”的基本范圍。假如在共同體之中人人都認(rèn)同這樣一套行為標(biāo)準(zhǔn),那么就會(huì)由此形成一種相互默會(huì)的、毋庸論證的“共同感知”和“公共話語”系統(tǒng)。這是公民社會(huì)超越熟人世界的必要條件。
“公民性”是自我意識(shí)被集體性自我意識(shí)(collec-tive self―consciousness)部分取代時(shí)的一種行為
“集體性自我意識(shí)是將自我視為集體之一部分的認(rèn)知狀態(tài),它內(nèi)涵著一種將集體利益置于個(gè)人或地區(qū)與集團(tuán)利益之上的范圍。”在這里,希爾斯的意思是說,當(dāng)“公民性”被內(nèi)化為每一個(gè)成員的自覺價(jià)值的時(shí)候,就會(huì)生成某種被共同體成員所普遍認(rèn)同的“集體心性”。這樣自我個(gè)體德性的規(guī)范,就變成普遍的行為準(zhǔn)則,“公民社會(huì)”于是生成。當(dāng)一群公民成員自覺遵從共同認(rèn)可的良好風(fēng)尚并平等相處時(shí),他們彼此尊重各自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把對(duì)方視為具有同等尊嚴(yán)的公民,這就意味著將其他人,包括屬
于不同黨派、宗教團(tuán)體和種族群體,都應(yīng)被視為同一集體的成員,不因他們?cè)凇罢姟薄ⅰ靶叛觥被颉傲?xí)俗”的不同而加以排斥。特別重要的是,在這里,“公民性”是所有共同體成員,包含超出個(gè)人或社區(qū)以外的、以至于可囊括全體共同體成員的范圍,包括那些并不相識(shí)、彼此陌生的(即“不在場(chǎng)的”),甚至永世未必相見的共同體成員,共同建立起來的一套大家分享其權(quán)力與義務(wù)的“價(jià)值符號(hào)的空間”。而有資格共同分享價(jià)值的對(duì)象應(yīng)當(dāng)“包括自己的敵人”。“公民性不僅是良好的風(fēng)尚與和解的語調(diào),它同時(shí)也是一種政治行為模式。這種模式預(yù)設(shè)政敵亦是同一社會(huì)的成員、共享同樣的集體自我意識(shí)。”把他們也“視為同一集體的成員,亦即同一社會(huì)的成員,即使他們屬于不同的政黨、宗教團(tuán)體或種族群體。”“這一意義上的公民性包含了對(duì)政敵以及盟友福祉的關(guān)切”。
作為生活在半個(gè)多世紀(jì)以來所形成的政治認(rèn)知傳統(tǒng)中的中國人,理解“尊重?cái)橙恕睙o疑具有及其重要的意義。首先,“公民意識(shí)”所強(qiáng)調(diào)的“集體性自我意識(shí)”并不等同于中國人常說的“集體主義”,因?yàn)樵凇肮褚庾R(shí)”的本質(zhì)中沒有“階級(jí)斗爭(zhēng)”所釋放出來的那種“你死我活”的怨恨;其次,“公民意識(shí)”的本質(zhì)中注重“集體性自我意識(shí)”,并不構(gòu)成對(duì)個(gè)人意識(shí)的壓抑和扼殺,而是通過預(yù)期到別人同樣的感受而使自我行為自覺地受到克制,這種限制不是來自外力的約束,而是出于一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理推演;再次、“公民意識(shí)”的本質(zhì)中內(nèi)生著“當(dāng)社會(huì)之一部分可能從某一特定事件或政策中得到好處時(shí),任何設(shè)想或試圖減輕另一部分可能招致的損失的行動(dòng)都是一種實(shí)質(zhì)性公民品行的行動(dòng)”,由此形成謙讓、妥協(xié)、后退行為的可能性基礎(chǔ)。通過上述三點(diǎn),個(gè)人主義、地區(qū)或集團(tuán)性和“整體性”之間的一種動(dòng)態(tài)的平衡就能實(shí)現(xiàn)。
綜上所述,由于“公民性”不是“權(quán)力欲”,所以它是“非暴力”的;由于它的志趣不在于升值,因此它是“非營利”的;由于它的價(jià)值底蘊(yùn)出于“使命”之中,因此它是“志愿性”的;由于它“視人如己”,所以才能對(duì)“異己”給與寬容。一個(gè)公民社會(huì)就是其成員都具備公民美德的社會(huì);這樣的美德包涵了諸如“良知”、“獨(dú)立”、“志愿”、“慈善”、“互助”、“合作”、“責(zé)任”等等內(nèi)容;而當(dāng)這些公民美德內(nèi)化為共同體成員志愿遵循的價(jià)值準(zhǔn)則和日常行為時(shí),這就標(biāo)志著“公民社會(huì)”的成立;而“大愛無疆”和“彼此寬容”則又是其中最為抽象、也最為深刻的終極內(nèi)涵。
在這里,引用徐永光在談及慈善事業(yè)和慈善產(chǎn)品之性質(zhì)時(shí)所給出的具體解說,在一定意義上,他的意思表達(dá)了“公民性”抽象理念的核心內(nèi)涵:“做善事不光可以幫助別人,還能拯救自己的靈魂”。“公益慈善事業(yè)和志愿服務(wù),能夠撥亮人們心靈的明燈,推動(dòng)人和人之間建立平等、互助、互信、互利的社會(huì)關(guān)系,這是和諧社會(huì)建設(shè)不可缺少的社會(huì)資本。發(fā)展慈善事業(yè),就是讓中國人更加接近‘上帝’。這個(gè)‘上帝’不是別的,就是隱藏在每個(gè)人心中的慈善心、公德心、公益心、博愛心。……參與公益事業(yè),無論是捐款或是當(dāng)志愿者都是助人自助,有私奉獻(xiàn);贈(zèng)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為樂,施比受更有福。這是公益事業(yè)的市場(chǎng)需求。了解這種需求,以需求為導(dǎo)向來設(shè)計(jì)項(xiàng)目,推廣營銷,就找到了非營利組織的經(jīng)營之道。”強(qiáng)然他針對(duì)的是慈善事業(yè),但這其中韻律則留藏著“公民性”的久久芳香。
自上個(gè)世紀(jì)60年代以來,反思“現(xiàn)代性”(Modernitv)就成為一個(gè)嚴(yán)峻的國際性課題。學(xué)者們注意到,自西方近代啟蒙運(yùn)動(dòng)以來,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人類中心主義意識(shí)日益增強(qiáng),伴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日益發(fā)達(dá)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巨大成就,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良知,在人類整體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漸處于被關(guān)注的邊緣,人類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明顯地趨于淡化,物質(zhì)利益的獲取成為壓倒一切的“第一主題”。個(gè)人被從家庭、社群中剝離出來,而以專業(yè)和利益為原則被非有機(jī)地重新組織化,以至于個(gè)人在社群中角色失去了自然本性和連續(xù)性,以至于道德貶值、信念消逝、價(jià)值危機(jī)、世風(fēng)退敗,其突出的表征就是占有欲望的無限擴(kuò)張、窮奢極欲的消費(fèi)主義、冷漠功利的人際關(guān)系等等。顯然,這些征兆對(duì)完整社會(huì)有機(jī)體的健康和安全,構(gòu)成了嚴(yán)重的威脅。正如韋伯曾以其少有的激烈方式予以詛咒的那樣:“專家沒有靈魂,者沒有心肝;這個(gè)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dá)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人類所理解的“解放”,實(shí)際上是被再一次囚禁于“合理化鐵籠”。一句“德性能值幾個(gè)錢?”的亢奮質(zhì)疑,其實(shí)已全然揭示出了“現(xiàn)代性”狂躁的邏輯本性。
第3篇: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重要性范文
【關(guān)鍵詞】媒介使用;社會(huì)凝聚力;國家認(rèn)同;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地方主義
【中圖分類號(hào)】G206.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社會(huì)整合是大眾傳播媒介的重要功能,也是媒介研究的重要理論范疇(麥奎爾,2006),其中一個(gè)核心命題是大眾媒介與國家認(rèn)同的關(guān)系。由于“認(rèn)同”這個(gè)概念本身在政治、文化、歷史的不同層面,內(nèi)涵均十分豐富,“國家認(rèn)同”(national identity)[1]則不僅與民族/族群認(rèn)同相關(guān),也與社會(huì)凝聚力、愛國主義、民族主義(nationalism)等相互交織,因此圍繞該命題的學(xué)術(shù)資源不僅源流多元,而且路徑復(fù)雜、概念叢生,仍有許多理論關(guān)系值得梳理,在大眾傳播的經(jīng)驗(yàn)研究范疇內(nèi)更是如此。
在當(dāng)代社會(huì)理論看來(Trepte ,2006),社會(huì)認(rèn)同(social identity)籍由社會(huì)成員的資格來建構(gòu),是該社會(huì)類別全體成員的自我描述,由社會(huì)分類(social categorization)、社會(huì)比較(social comparison)和積極區(qū)分原則(positive distinctiveness)來建立。社會(huì)認(rèn)同包含了對(duì)自我身份地位、利益歸屬的一致性認(rèn)可,對(duì)周圍社會(huì)的信任和歸屬感,對(duì)權(quán)力和權(quán)威的遵從等等七個(gè)大類,國家認(rèn)同是其中之一(詹姆斯•S•科爾曼,2008)。在國家-社會(huì)高度統(tǒng)合的一體化結(jié)構(gòu)中,國家認(rèn)同不僅能夠用之詮釋形成社會(huì)凝聚力的個(gè)體間的心理聯(lián)系,也是社會(huì)凝聚力的實(shí)踐目標(biāo)之一。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一方面中國的經(jīng)濟(jì)成就和國際影響力極大地激發(fā)了國人的愛國主義情緒和民族自豪感,來自國際社會(huì)的“中國”和國內(nèi)以《中國可以說不》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浪潮交織在一起,加之汶川地震等重大災(zāi)害事件面前國人的高度凝結(jié),大眾媒介有關(guān)奧運(yùn)、國慶閱兵、世博報(bào)道有關(guān)中國國家形象、國家認(rèn)同的著力建構(gòu),都給人們帶來了新的有關(guān)國家認(rèn)同的想象;另一方面,在經(jīng)濟(jì)和文化日益全球化的場(chǎng)景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使得中國從一個(gè)國家高度統(tǒng)合的“總體性社會(huì)”產(chǎn)生裂變,形成了新的國家-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朱學(xué)勤,2006;朱學(xué)勤,2007),其中社會(huì)日益獲得相對(duì)獨(dú)立于國家的自主性(鄧正來,1999;鄧正來,2008),同時(shí)社會(huì)階層在得到重構(gòu)并日漸分化(陸學(xué)藝,2002;孫立平,2003;李路路,2003;李春玲,2005),為社會(huì)凝聚力和國家認(rèn)同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盡管在總體上,中國的大眾傳播媒介始終承擔(dān)著國家認(rèn)同和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建構(gòu)功能,但是有關(guān)社會(huì)信任缺失、歸屬感降低等媒介內(nèi)容也不在少數(shù)。
這樣的社會(huì)變遷提出了一系列理論問題,包括:在當(dāng)今中國復(fù)雜多變的社會(huì)發(fā)展格局下,國家認(rèn)同是否還能用社會(huì)凝聚力的動(dòng)力機(jī)制和實(shí)踐目標(biāo)來詮釋?大眾傳播媒介在這兩個(gè)概念及其關(guān)系的建構(gòu)上是否發(fā)揮不同的作用?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代表的新媒介技術(shù)是否在這些方面發(fā)揮出與傳統(tǒng)媒介不同的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討這些問題。通過在中國最大的國際化大都市――上海――進(jìn)行的實(shí)證調(diào)查,本文從經(jīng)驗(yàn)層面搭建起受眾的媒介使用、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和國家認(rèn)同之間的理論關(guān)系。
一、概念闡釋與研究問題
1、國家認(rèn)同: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地方主義及其新的特質(zhì)
社會(huì)學(xué)家Woodward(1997)認(rèn)為,認(rèn)同是通過象征資源和社會(huì)區(qū)分來建構(gòu)的,人們經(jīng)由話語選擇來感知認(rèn)同的內(nèi)涵,并且在差異性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中將其具體化,同時(shí)還需要心理層面的參與。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3)將民族界定為一種在本質(zhì)上有限的、享有的“想像的政治共同體”(頁5),那么,如果我們將“國家”這一概念同樣視為廣義上的想像的政治共同體,無論站在自由主義還是民族主義的立場(chǎng)上看,國家認(rèn)同的基本要素都包含三層含義,一是這個(gè)政治共同體的同一性和延續(xù)性,二是個(gè)體對(duì)自己歸屬于哪一個(gè)政治共同體的辨識(shí)和選擇,三是個(gè)體對(duì)自己歸屬的政治共同體的期待,這是與前一點(diǎn)對(duì)政治共同體的辨識(shí)和選擇相呼應(yīng)的關(guān)涉贊同、支持哪一個(gè)國家的心理期許(江宜樺,1998)。由于總體上中國社會(huì)在疆域、和歷史文化歸屬上具有基本的共識(shí),因此本研究用上述三層含義的后兩層來界定國家認(rèn)同的第一個(gè)維度:無條件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說,具有如此國家認(rèn)同的人,是那些辨識(shí)和選擇自己為中國人、并且在心理和情感上贊同與支持中國。在經(jīng)驗(yàn)研究層面,這個(gè)維度已經(jīng)在一些學(xué)者那里被提煉為對(duì)“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進(jìn)行測(cè)量的一個(gè)重要變量(Guo,Cheong & Chen,2007)。
然而,批判學(xué)者霍爾(Hall,1996a)認(rèn)為,所謂認(rèn)同并非靜止的存在,而是行動(dòng)者通過使用歷史、語言和文化等象征資源逐漸成為某個(gè)特定主體的過程,并且,行動(dòng)者和其實(shí)踐行為相互涉入、相互勾連,因此這個(gè)過程不僅是動(dòng)態(tài)的和互動(dòng)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效能(Hall, 1996b)。由此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在今天這個(gè)全球化的新的情景脈絡(luò)中,僅以民族主義作為考量國家認(rèn)同的單一維度,局限性是很大的。其中的一個(gè)重要影響因素就是全球化的人口流動(dòng)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傳統(tǒng)上個(gè)體對(duì)其國家-故土的一以貫之的穩(wěn)定的依附性(Lechner,2007)。這種情形會(huì)帶來有關(guān)國家認(rèn)同的兩方面變化。第一,對(duì)于那些進(jìn)入其它國家的新移民來說,一方面他們?cè)谇楦泻托睦砩先匀毁澇珊椭С肿约旱墓蕠?甚至更加強(qiáng)烈,另一方面從公民身份選擇上他們又會(huì)以實(shí)用主義的態(tài)度選擇轉(zhuǎn)換國籍。這一現(xiàn)實(shí)會(huì)從普遍意義上帶來個(gè)體在公民身份和心理情感上的國家歸屬變得比以往任何時(shí)候都要復(fù)雜和多元。2008年在奧運(yùn)圣火傳遞期間,國內(nèi)各大網(wǎng)絡(luò)論壇上有關(guān)海外華人能否愛國和如何愛國的討論便是一例[2]。戴維•莫利(2005)就曾在討論全球化時(shí)代的受眾時(shí),重申了霍爾有關(guān)移民經(jīng)驗(yàn)對(duì)理解當(dāng)代文化和傳播現(xiàn)象的重要性的論述,即便全球公民可以被劃分為自愿的和非自愿的兩類。第二,對(duì)于那些趨于全球化的國際大都市來說,越來越多的“本地人”并非“本國人”,在國家作為認(rèn)同之最終形式的政治支配功能之外,包括新的城市共同體在內(nèi)的多元次級(jí)形式的認(rèn)同也凸顯出來。近期的一項(xiàng)研究以上海開埠160年紀(jì)念的媒介報(bào)道為文本對(duì)象,探討上海報(bào)紙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下承接并轉(zhuǎn)換了傳統(tǒng)的民族國家認(rèn)同,重構(gòu)了新的城市共同體認(rèn)同(孫瑋,2009)。上海的“世界主義再造”(recosmopolitanization)是跨國文化身份抵抗從國家朝向全球化想象偏移的一部分(Yang,2002),也是全球化進(jìn)程中獲取身份表述的路徑之一(戴錦華,1999)。如此分析意味著“上海人”在這里并不一定都是“中國人”,而是所有那些對(duì)上海及上海的日常生活富有激情和心理依附的個(gè)體,無論他們種族和國籍如何。
鑒于此,我們?cè)诒狙芯恐性黾恿藝艺J(rèn)同的另外兩個(gè)維度,其一被我們稱作“世界主義”,內(nèi)涵強(qiáng)調(diào)的是個(gè)體公民身份選擇的全球化影響和獲取自身優(yōu)厚生活的便利性與實(shí)用性因素;其二是“地方主義”,在這里主要表達(dá)的是對(duì)城市共同體的心理和情感投入。盡管從理論上看,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和地方主義是國家認(rèn)同的三個(gè)維度,它們相互交織,在不同人那里以不同的形構(gòu)(configuration)體現(xiàn)他們的國家認(rèn)同。因此,在邏輯上對(duì)它們作出區(qū)別,有助于我們于將國家認(rèn)同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力圖呈現(xiàn)其當(dāng)下復(fù)雜和豐富的特質(zhì)。
2、媒介使用與國家認(rèn)同
大眾傳播媒介在傳遞主流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建構(gòu)國家認(rèn)同方面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在戴維•莫利(2005)看來,電視連接家庭、國家和國際,維持 “國家家庭”(National Family) 等各種共同體的形象和現(xiàn)實(shí)。Calabrese 和 Burke(1992)力圖從理論上厘清美國人的身份認(rèn)同是如何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在公共領(lǐng)域彰顯的民族主義來建構(gòu)的,為維系國家認(rèn)同,媒介把持著獨(dú)一無二的擷取國家注意力的強(qiáng)大能力,并被認(rèn)定為代表大多數(shù)美國人的需要和利益。Demertzis等(1999)通過希臘報(bào)紙如何報(bào)道馬其頓問題探討全球化時(shí)代的國家認(rèn)同問題,認(rèn)為當(dāng)代的民族主義與十九至二十世紀(jì)早期的最大區(qū)別在于,它始終被全球和地方之間的世界性的二律背反所影響,同時(shí)國家認(rèn)同又深深地根植于不同的政治文化當(dāng)中,民族主義者的偏見會(huì)作用于記者和媒介組織選擇和呈現(xiàn)國家認(rèn)同和“他者”的方式。不同國家的媒介如何報(bào)道在研究者看來也是媒介以國家作為多棱鏡報(bào)道全球事件的重要標(biāo)本(李金銓、陳韜文、潘忠黨、蘇鑰機(jī),2006)。大眾媒介和國家認(rèn)同在當(dāng)今全球化時(shí)代的結(jié)構(gòu)形態(tài)和影響路徑,在中國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歷史時(shí)期更顯現(xiàn)出其復(fù)雜態(tài)勢(shì)。有學(xué)者用“(跨)民族主義”((trans)nationalism)來闡述當(dāng)今中國大眾傳播媒介所實(shí)踐的國家想像,這一認(rèn)同是經(jīng)由民族主義話語和跨國進(jìn)程的共謀得以達(dá)成的(Sun,2001)。一方面,民族主義敘事始終是中國大眾媒介的主旋律(潘忠黨,2000;Pan,2010),另一方面,進(jìn)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并力圖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中國大眾媒介呈現(xiàn)和構(gòu)筑國家想象的重要方面(趙月枝,2005)。
那么,受眾的媒介使用行為是否會(huì)對(duì)他們?cè)趪艺J(rèn)同的不同維度上產(chǎn)生作用呢?已有的少量直接針對(duì)受眾的實(shí)證研究顯示,若是針對(duì)具體的熱門事件,受眾的媒介使用會(huì)對(duì)這種顯性表征的民族主義產(chǎn)生直接的影響。但是,對(duì)于辨識(shí)和選擇自己為中國人、并且從普遍意義的心理和情感上贊同與支持中國的隱性表征的民族主義,大眾媒介則需要通過個(gè)體的信息接受方式、頭腦復(fù)雜度、知識(shí)和人際溝通模式而產(chǎn)生間接的作用(Guo,Cheong & Chen,2007)。
然而,媒介再現(xiàn)的民族主義和國家想象,究竟如何影響于個(gè)體有關(guān)國家認(rèn)同的自我感知和情感依附?這方面的經(jīng)驗(yàn)觀察是十分貧乏和有限的。近年來,互聯(lián)網(wǎng)在中國政治和社會(huì)生活不同領(lǐng)域開始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比如網(wǎng)絡(luò)參與新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集體認(rèn)同感的建構(gòu)(孫瑋,2007),在公共事件當(dāng)中承擔(dān)社會(huì)動(dòng)員和組織功能,形成具有相對(duì)獨(dú)立性的新媒介事件(邱林川、陳韜文,2009),在鼓吹民族主義的同時(shí)也經(jīng)由網(wǎng)民代表公眾參與政府、商業(yè)機(jī)構(gòu)和傳統(tǒng)主流媒介之間的利益博弈并對(duì)集體行為模式產(chǎn)生影響(周裕瓊,2009),通過差異化意見表達(dá)和輿論監(jiān)督實(shí)踐體現(xiàn)出朝向公民社會(huì)的參與式特征(胡泳,2008;陸曄,2008)。這些新的變化與國家認(rèn)同之間的關(guān)系,也需要更多的經(jīng)驗(yàn)研究來驗(yàn)證。
鑒于此,本研究一方面力求拓展國家認(rèn)同的維度,將單純的個(gè)體對(duì)所屬國家的辨識(shí)、選擇和情感依附,擴(kuò)大到對(duì)國家、對(duì)城市共同體和對(duì)全球化三個(gè)維度的辨識(shí)、選擇和情感依附,另一方面,將公眾的媒介使用從傳統(tǒng)媒介拓展到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代表的新媒介,考察媒介使用所產(chǎn)生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gè)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1:公眾的媒介使用行為如何對(duì)他們對(duì)國家認(rèn)同的三維度發(fā)生作用?
3、公眾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向心力和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帶來的疏離感
作為社會(huì)群體構(gòu)成的要素之一,涂爾干(2000)認(rèn)為社會(huì)凝聚力是社會(huì)成員之間的依賴、忠誠和團(tuán)結(jié)程度,是社會(huì)的秩序特征,其中一個(gè)重要的衡量指標(biāo)是社會(huì)成員的共同價(jià)值觀、歸屬感和具有共同的社會(huì)發(fā)展目標(biāo)(江時(shí)學(xué),2008)。凝聚力是一個(gè)高度抽象的概念,其測(cè)量指標(biāo)非常復(fù)雜,但都大體包含從客觀的社會(huì)物質(zhì)差距到主觀的社會(huì)價(jià)值判斷等兩大不同相面的若干維度(Berger-Schimitt,2002)。這一部分涉及多個(gè)相面的社會(huì)資本,比如社會(huì)共同價(jià)值、公眾對(duì)政治的認(rèn)可和參與程度、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文化上的歸屬感等等,它們與大眾傳播媒介的建構(gòu)關(guān)系密切。在這里我們只考察主觀認(rèn)知的部分。
但是,在涂爾干的理論分析中,社會(huì)分化和社會(huì)凝聚被視為同一過程的兩個(gè)辯證的動(dòng)力機(jī)制,它們同屬一個(gè)過程,又相互有張力。與此一脈相承,Jenson(1998)、Berger(1998)等都將社會(huì)凝聚力看作由兩個(gè)指向相反的力量所構(gòu)成,正向的強(qiáng)化社會(huì)共同紐帶的緊密程度,如價(jià)值,文化,身份認(rèn)同,反向的則是導(dǎo)向社會(huì)的差異程度,即社會(huì)和經(jīng)濟(jì)差異,包括這些差異中的不平等。同時(shí),在大眾媒介與社會(huì)整合/分化之間,也被視為有兩種相輔相承又相互抵觸的關(guān)系(麥奎爾,2006),一是媒介被認(rèn)為具有顯著的個(gè)人主義和降低社會(huì)控制的特征,潛在地削弱傳統(tǒng)價(jià)值,強(qiáng)化離心趨勢(shì);一是媒介通過傳播共同規(guī)范和價(jià)值,凝聚零散的個(gè)體,整合差異性的現(xiàn)代社會(huì),強(qiáng)化向心趨勢(shì)。
沿襲這樣的理論脈絡(luò),我們?cè)诒狙芯恐袑⒐妼?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感知分為兩個(gè)不同維度的感知和判斷。表達(dá)向心和整合趨勢(shì)這一維度的是公眾對(duì)主流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和文化價(jià)值建構(gòu)的感知和認(rèn)可,這也是大眾傳播媒介長期以來不斷建構(gòu)的重要內(nèi)容,最典型的莫過于一年一度中央電視臺(tái)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huì)所建構(gòu)的家國一體的氛圍(Pan,2010),這種建構(gòu)同樣充滿奧運(yùn)會(huì)這樣的大型體育賽事報(bào)道、汶川地震這樣的災(zāi)難報(bào)道以及正在進(jìn)行中的世博會(huì)報(bào)道,它們激發(fā)的是全體中國人乃至全球華人同心同德的情感。表達(dá)離心和分化趨勢(shì)這一維度的是對(duì)由于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帶來的社會(huì)分化以及這個(gè)過程中的疏離感的呈現(xiàn)。在社會(huì)學(xué)家眼中,這種疏離感與斷裂社會(huì)、碎片化、社會(huì)階層、社會(huì)利益與意識(shí)的多元交叉緊密相關(guān)(孫立平,2003;李培林,李強(qiáng),孫立平等,2004;李春玲,2005);當(dāng)這種疏離感具體化為活生生的事例,就成為大眾媒介在市場(chǎng)上極利于賺取眼球的社會(huì)故事。都市報(bào)和電視民生新聞版面中有不少關(guān)涉這類呈現(xiàn),比如冷漠的人際關(guān)系和信任缺失、社會(huì)道義感下降、底層弱勢(shì)仇視社會(huì)的報(bào)復(fù)心理,等等。同時(shí),新媒介技術(shù)的擴(kuò)散和使用帶來的包括信息分配在內(nèi)的社會(huì)資源的分化及其中的權(quán)力沖突形態(tài)也已經(jīng)引起學(xué)者的關(guān)注(丁未,2009)。
那么,公眾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究竟是怎樣的呢?是不是會(huì)受到來自傳統(tǒng)媒介和新媒介的不同影響?這便是本研究關(guān)注的第二個(gè)問題。
研究問題2:公眾的傳統(tǒng)媒介和新媒介使用行為如何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產(chǎn)生作用?
由于國家認(rèn)同往往被視為社會(huì)凝聚力的動(dòng)力機(jī)制和實(shí)踐目標(biāo),就此延伸出第三個(gè)問題。
研究問題3:公眾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是否并如何影響他們的國家認(rèn)同的三個(gè)維度?
二、研究方法
1、樣本
本研究的數(shù)據(jù)來自2009年5-8月在上海完成《上海市城市居民與媒體使用調(diào)查》。本次調(diào)查采用了A、B兩個(gè)不同版本的問卷,調(diào)查的設(shè)計(jì)要求A、B卷各有1,500份完成問卷(抽樣誤差為2.6%)。由于B卷中包含了社會(huì)凝聚力和國家認(rèn)同的問題,因此本文分析的是采用B卷獲得的數(shù)據(jù)(n=1,421)。
2、測(cè)量
國家認(rèn)同:這組變量(參見表1)旨在考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認(rèn)同的復(fù)雜內(nèi)涵。我們?cè)趩柧懋?dāng)中測(cè)量了國家認(rèn)同的三個(gè)維度,每個(gè)由兩到三個(gè)采用5級(jí)量表(1表示非常不贊同,5表示非常贊同)的題項(xiàng)測(cè)量。因子分析的結(jié)果呈現(xiàn)了這樣三個(gè)因子:一是“無條件的民族主義者”(具體的測(cè)量分別為:每個(gè)中國人都應(yīng)該無條件支持自己的國家;就算可以隨便選擇世界上任何國家,我也更愿意做中國人。信度系數(shù)為0.68);二是“現(xiàn)實(shí)的世界主義者”(具體測(cè)量為:我有時(shí)覺得自己作為“世界公民”與作為中國人同等重要;全球視野比國家視野更適合當(dāng)今的全球化時(shí)代;我覺得做哪個(gè)國家的人都無所謂,關(guān)鍵是要生活過得好。信度系數(shù)為0.53);三是“感性的地方主義者”(具體測(cè)量: 不管別人怎么看上海這個(gè)城市,我都非常樂于做一個(gè)上海人;我對(duì)上海很有感情;我常常覺得跟上海這個(gè)城市格格不入。信度系數(shù)為0.67)(其中因子一和因子二的相關(guān)系數(shù)為0.094,p
公眾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這組題項(xiàng)經(jīng)由因子分析,呈現(xiàn)出兩個(gè)負(fù)相關(guān)的因子(參見表2,相關(guān)系數(shù)為-.116,p
媒介使用:在本研究中,我們重點(diǎn)討論三組有關(guān)媒介使用的變量,均用5級(jí)量表測(cè)量,1表示極少,5表示經(jīng)常。一是受眾對(duì)報(bào)紙新聞的閱讀,分別由對(duì)本地新聞、國內(nèi)新聞和國際新聞的閱讀頻率構(gòu)成(信度系數(shù)為0.704);第二組變量是受眾對(duì)電視新聞的收視行為,同樣由對(duì)本地新聞、國內(nèi)新聞、國際新聞的收視頻率構(gòu)成(信度系數(shù)為0.710);最后一組變量是受眾對(duì)網(wǎng)絡(luò)的使用行為,分別由瀏覽門戶網(wǎng)站(如新浪、搜狐)、瀏覽傳統(tǒng)媒介網(wǎng)站(如解放網(wǎng)、鳳凰網(wǎng))、閱讀報(bào)紙網(wǎng)絡(luò)版構(gòu)成(信度系數(shù)為0.698)。 這組變量是本研究的自變量,分別用來討論其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和對(duì)國家認(rèn)同的影響(其中從不讀報(bào)的樣本388人和從不上網(wǎng)的非網(wǎng)民樣本762人被處理為系統(tǒng)缺省值,排除在數(shù)據(jù)分析之外)。
人口變量:本研究的人口變量包括性別(男性編碼為1,女性編碼為2,比例為50.2:49.8),年齡(按升序排列,最小18歲,最大91歲,M=48.06歲),教育程度(標(biāo)準(zhǔn)化處理為0-20級(jí),缺省值用預(yù)測(cè)值代替,M=9.68),個(gè)人平均月收入(缺省值用預(yù)測(cè)值代替,M=2507.35元),并區(qū)分出生在上海(編碼為1,占64.5%)和外地遷來上海的被訪者(編碼為2)。
三、數(shù)據(jù)分析
1、媒介使用與公眾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
表3呈現(xiàn)的是是第一組OLS回歸分析結(jié)果,這些模式估測(cè)的是公眾的媒介使用行為和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這兩組概念間的關(guān)系。結(jié)果顯示,在人口學(xué)變量組中,只有性別、年齡和是否上海人這三個(gè)指標(biāo),是或多或少與社會(huì)凝聚力主觀感知相關(guān),其中年齡的預(yù)測(cè)強(qiáng)度比較高,年齡越大,越較多感受到大眾傳播媒介著力建構(gòu)的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向心力,也越少地感受到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帶來的疏離感,兩個(gè)方向的預(yù)測(cè)顯著性都比較突出。顯然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感受到社會(huì)凝聚力的向心趨勢(shì),而那些外地遷來上海的新移民,比上海出生的上海人要較少感受到社會(huì)的離心趨勢(shì),這一點(diǎn),應(yīng)該和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發(fā)展與新移民在上海所獲得的機(jī)會(huì)相關(guān)。教育程度的高低和個(gè)人收入的多寡則不能估測(cè)公眾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
在媒介使用變量組中,顯然相對(duì)于電視和網(wǎng)絡(luò),報(bào)紙?jiān)诠罍y(cè)公眾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正面向心作用的主觀感知上面,發(fā)揮著相對(duì)顯著的作用。越經(jīng)常性的閱讀報(bào)紙的本地新聞,就越顯著地感受到大眾媒介建構(gòu)的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向心力,但是越多閱讀報(bào)紙的其他國內(nèi)新聞,則相對(duì)越少地感受到這種主流建構(gòu)的向心作用,這一方面顯示出本地新聞在社會(huì)凝聚力向心建構(gòu)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與媒介在報(bào)道有關(guān)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帶來的社會(huì)疏離感的離心趨勢(shì)方面,所選擇的負(fù)面的社會(huì)新聞?shì)^少來自本地有關(guān),這種選擇既是媒介“異地監(jiān)督”的常用手法,也是近年來引起強(qiáng)烈社會(huì)關(guān)注的事故災(zāi)難、食品安全、醫(yī)療衛(wèi)生等新聞事件都發(fā)生在內(nèi)地所致。
在電視新聞收視行為變量組中,只有收看電視國際新聞反向預(yù)測(cè)對(duì)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帶來的疏離感的感知,也就是說,越多收看電視國際新聞,越少感受到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分化帶來的離心趨勢(shì)。
盡管互聯(lián)網(wǎng)的使用在估測(cè)公眾對(duì)于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方面幾乎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是那些經(jīng)常瀏覽傳統(tǒng)媒介網(wǎng)站(比如解放網(wǎng)、新民網(wǎng)、鳳凰網(wǎng))的網(wǎng)民,比其他人要更多地感受到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帶來的疏離感。這一結(jié)果令人深思,一方面盡管從日常的媒介使用經(jīng)驗(yàn)看,傳統(tǒng)媒介和其網(wǎng)站在大部分內(nèi)容上差異并沒有那么大,但是其網(wǎng)絡(luò)論壇可能會(huì)涉及一些傳統(tǒng)媒介較少涉及的具有一定爭(zhēng)議性的話題,比如人民網(wǎng)的強(qiáng)國論壇上有不少網(wǎng)民熱議的話題都是人民日?qǐng)?bào)本身并不涉及的;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進(jìn)一步考察那些愿意更多地在網(wǎng)絡(luò)上尋求多元信息的網(wǎng)民,是否具備對(duì)于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更強(qiáng)的反思和批判能力?這一點(diǎn)不僅提示我們要更進(jìn)一步關(guān)注網(wǎng)絡(luò)內(nèi)容與傳統(tǒng)媒介的差異性,對(duì)于網(wǎng)絡(luò)使用行為當(dāng)中更復(fù)雜的心理因素也非常值得我們?cè)诤罄m(xù)研究中進(jìn)一步探究。
2、媒介使用、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和國家認(rèn)同的三維度
表4呈現(xiàn)的是另一組OLS回歸模式的結(jié)果。這組回歸模式估測(cè)的是媒介使用變量組與國家認(rèn)同三個(gè)維度之間的關(guān)系,同時(shí)探究公眾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是否也影響到國家認(rèn)同。表4首先顯示了人口學(xué)變量之于公眾國家認(rèn)同的意義。從性別看,女性要比男性更認(rèn)同上海作為一個(gè)城市共同體的情感價(jià)值。年齡對(duì)于國家認(rèn)同的三個(gè)維度則都是十分顯著的影響因素,年長者比年輕人更傾向于成為無條件的民族主義者,對(duì)上海這座城市的感情也很深厚,但是年輕人卻更具備全球視野,傾向于成為世界公民的現(xiàn)實(shí)選擇。教育程度和個(gè)人收入對(duì)于國家認(rèn)同的三個(gè)維度都不具備估測(cè)的效果,但是那些從外地遷來上海的新移民,他們跟土生土長的上海人相比,顯然對(duì)上海這個(gè)城市的心理依附和情感傾向要低得多,不過盡管他們并不那么喜歡上海,卻也并不急于認(rèn)同世界公民,和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上海人相比,他們成為現(xiàn)實(shí)的世界主義者的可能性要更低。
從公眾的媒介使用行為來看,讀報(bào)和看電視在預(yù)測(cè)國家認(rèn)同的第一和第二個(gè)維度,也就是作為無條件的民族主義者和現(xiàn)實(shí)的世界主義者這兩點(diǎn)上,都沒有顯著的表現(xiàn),反而互聯(lián)網(wǎng)更有可能成為無條件的民族主義者的溫床,網(wǎng)絡(luò)使用行為當(dāng)中,在網(wǎng)上閱讀報(bào)紙的電子版正向顯著預(yù)測(cè)無條件的民族主義者這個(gè)維度。然而對(duì)于本地認(rèn)同來說,讀報(bào)和看電視多多少少具有一定的影響,其中收看電視本地新聞顯著正向預(yù)測(cè)感性的地方主義者這個(gè)維度,顯然收看本地新聞越多的人,他們對(duì)上海這個(gè)城市的熱愛和情感依附也是非常高的。而報(bào)紙的國際新聞反向預(yù)測(cè)這個(gè)地方認(rèn)同的維度,越喜歡閱讀報(bào)紙國際新聞版的人,在對(duì)上海這個(gè)城市共同體的認(rèn)同上要越淡漠。
在這一組變量關(guān)系中,我們必須注意到,相對(duì)于公眾媒介使用行為的影響力來說,有關(guān)公眾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這組兩維度的來自社會(huì)學(xué)領(lǐng)域的反向變量,顯而易見要比大眾媒介的直接影響強(qiáng)大得多,盡管這樣的主觀感知本身在個(gè)人的社會(huì)化過程中是無法脫離媒介這個(gè)擬態(tài)環(huán)境的作用的。被訪者對(duì)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建構(gòu)向心趨勢(shì)的感知,強(qiáng)烈顯著地正向預(yù)測(cè)國家認(rèn)同的三個(gè)維度――無論是民族主義、世界主義還是地方主義,公眾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在聚合方向的感知越強(qiáng)烈,國家認(rèn)同也越強(qiáng)烈。與此相反,那些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離散方向感知越強(qiáng)烈的人,盡管他們依然可能成為現(xiàn)實(shí)的世界主義者,但是卻不大可能成為無條件的民族主義者,也愈加無法認(rèn)同自己所生活的這種城市作為共同體的精神意義。
四、結(jié)論與討論
從總體上看,大眾傳播媒介無論在公眾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方面,還是對(duì)公眾的國家認(rèn)同,都可能產(chǎn)生一定的直接影響,同時(shí)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代表的新媒介也開始在一些維度上發(fā)揮作用。
針對(duì)本研究的第一個(gè)研究問題,在國家認(rèn)同的三個(gè)維度上,公眾直接的媒介使用行為,包括傳統(tǒng)媒介和互聯(lián)網(wǎng),對(duì)于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這兩個(gè)維度,按照傳統(tǒng)的刺激-反應(yīng)模式來進(jìn)行估測(cè),未能看出顯著的效果,但是卻對(duì)本地認(rèn)同產(chǎn)生影響。顯然,傳統(tǒng)媒介在建構(gòu)城市共同體方面,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收看電視本地新聞和公眾對(duì)上海這一城市共同體的情感依附之間,有著明顯的正向互動(dòng),而閱讀報(bào)紙國際新聞卻與這種本地情感依附之間形成反向的張力。對(duì)于無條件的民族主義的身份選擇,網(wǎng)絡(luò)要比傳統(tǒng)媒介的作用來得略顯著。對(duì)這個(gè)研究問題的考量提示我們,國家認(rèn)同的確是一個(gè)十分復(fù)雜的理論概念,目前的檢驗(yàn)只局限在媒介使用的最外在和表面層面,這種直接的測(cè)量較容易看到其對(duì)感性的本地認(rèn)同的作用,而在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個(gè)與人的政治社會(huì)化和理性視野相關(guān)的維度上,尚需要進(jìn)一步考察人們?cè)诿浇槭褂眯袨樯细鼮樯顚哟蔚幕?dòng)。
就本研究的第二個(gè)研究問題而言,報(bào)紙、電視和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行為都在公眾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主觀感知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其中最值得關(guān)注的是報(bào)紙國內(nèi)新聞閱讀行為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向心趨勢(shì)的反向預(yù)測(cè),和瀏覽傳統(tǒng)媒介網(wǎng)站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離心趨勢(shì)的正向預(yù)測(cè)。這對(duì)張力提醒我們更多地關(guān)注國內(nèi)新聞報(bào)道當(dāng)中有關(guān)社會(huì)疏離感的內(nèi)容對(duì)公眾的影響,以及網(wǎng)絡(luò)與傳統(tǒng)媒介在內(nèi)容和話題取向上可能存在的差異性。
本研究對(duì)第三個(gè)研究問題的回答是非常令人深思的。盡管大眾傳播媒介對(duì)國家認(rèn)同在不同的維度上產(chǎn)生了一定的正面的互動(dòng),但是公眾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離心趨勢(shì)的感知,會(huì)直接顯著地從負(fù)面影響到人們的民族主義認(rèn)同和對(duì)城市共同體的信心和情感依附,而國家認(rèn)同作為社會(huì)凝聚力的動(dòng)力機(jī)制和實(shí)踐目標(biāo),與大眾媒介著力建構(gòu)的主流意意識(shí)形態(tài)的向心力則有著積極的正向的預(yù)測(cè)關(guān)系。在這個(gè)意義上看,大眾傳播媒介有關(guān)家國一體和民族大家庭的政治共同體的想像建構(gòu),必須建立在社會(huì)整合和凝聚的現(xiàn)實(shí)感知之上,不然,當(dāng)社會(huì)分化導(dǎo)致的矛盾、沖突、疏離感到了一定的程度,國家認(rèn)同就會(huì)變成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
當(dāng)然,本研究只是有關(guān)媒介使用、社會(huì)凝聚力、國家認(rèn)同諸多復(fù)雜理論關(guān)系的初步的探索性經(jīng)驗(yàn)檢視,媒介使用作為自變量,和國家認(rèn)同這個(gè)多維度、內(nèi)涵深刻、外延廣泛的因變量之間,其理論關(guān)系不會(huì)是簡單的線性因果關(guān)系,人們的媒介實(shí)踐與其在國家、社區(qū)、與他者關(guān)系等諸多層面上的情感選擇本身,就有可能產(chǎn)生復(fù)雜的互動(dòng)。因此,對(duì)這其間理論關(guān)系的討論,還有待進(jìn)一步深化。
注:
1 由于Nation這一詞根具有多重涵義,使得National Identity在理論概念上既可對(duì)應(yīng)于民族認(rèn)同,也可對(duì)應(yīng)于民族國家認(rèn)同,而Nationalism則通常被認(rèn)為指代的是民族主義。我們面對(duì)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是,中國是一個(gè)由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漢族和五十五個(gè)少數(shù)民族共同組成的多民族國家,無論在普通百姓心目中,還是在媒介再現(xiàn)中,中華民族和作為政治共同體的中國,往往是合二為一的,民族認(rèn)同和國家認(rèn)同的統(tǒng)一被認(rèn)為是維護(hù)國家統(tǒng)一和社會(huì)穩(wěn)定的思想基礎(chǔ)。對(duì)于絕大多數(shù)老百姓來說國家認(rèn)同和民族認(rèn)同往往也是交織在一起,既沒有區(qū)別于國家的民族認(rèn)同,也沒有脫離民族的國家認(rèn)同。學(xué)者許紀(jì)霖(2006)在針對(duì)晚清以來中國思想家們對(duì)民族國家認(rèn)同的不同觀點(diǎn)進(jìn)行歷史述評(píng)時(shí)也指出,現(xiàn)代民族國家本身就是在民族基礎(chǔ)上形成的國家共同體,因此對(duì)這一政治共同體的認(rèn)同里面既包含了基于民族的文化認(rèn)同,也包含了對(duì)制度的政治認(rèn)同。由此,本研究沿襲臺(tái)灣學(xué)者江宜樺(1998)將中文的 “國家認(rèn)同”與英文的National Identity進(jìn)行概念對(duì)接的理論路徑。江站在政治哲學(xué)的立場(chǎng)指出,由于英文nation具有多種指涉,而“國家”并不只在狹義上指代近代才出現(xiàn)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也可以泛指廣義的各種政治共同體,因此研究者若能盡量以中文的“國家認(rèn)同”來思考問題,將有利于跳出將民族完全納入政治建構(gòu)以及“一個(gè)國家、一個(gè)民族”、“國家創(chuàng)造民族”等狹隘觀點(diǎn)的死胡同(頁7-8)。同時(shí),nationalism仍是遵從學(xué)術(shù)研究的慣例,在中文表達(dá)中對(duì)應(yīng)為民族主義。
2 比如天涯雜談:省略/publicforum/content/free/1/1663546.shtml。
參考文獻(xiàn):
[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3)。《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睿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戴錦華(1999)。《隱形書寫:九十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3]戴維•莫利(2005)。《電視、受眾與文化研究》(史安斌譯)。北京:新華出版社。
[4]鄧正來(1999)。導(dǎo)論:國家與市民社會(huì) ─ 一種社會(huì)理論的研究路徑。載鄧正來、J. C. 亞歷山大(編),《國家與市民社會(huì):一種社會(huì)理論的研究路徑》(頁121)。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5]鄧正來(2008)。《國家與社會(huì):中國市民社會(hu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6]丁未(2009)。一個(gè)城中村的互聯(lián)網(wǎng)實(shí)踐――社會(huì)資源分配與草根社會(huì)的傳播生態(tài)。《開放時(shí)代》第3期,頁137-153。
[7]胡泳(2008)。《眾聲喧嘩: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的個(gè)人表達(dá)與公共討論》。南寧: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8]江時(shí)學(xué)(2008)。拉美國家重視強(qiáng)化社會(huì)凝聚力。《求是》第23期,頁60-61。
[9]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rèn)同》。臺(tái)北:揚(yáng)智文化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
[10]李春玲(2005)。《斷裂與碎片――當(dāng)代中國社會(huì)階層分化實(shí)證分析》。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
[11]李金銓、陳韜文、潘忠黨、蘇鑰機(jī)(2006)。一起多國視野中的全球性“媒介事件”。載詹姆斯•庫蘭、米切爾•古爾維奇(編),《大眾媒介與社會(huì)》(楊擊譯)(頁286-295)。北京:華夏出版社。
[12]李路路(2003)。《再生產(chǎn)的延續(xù)――制度轉(zhuǎn)型與城市社會(huì)分層結(jié)構(gòu)》。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13]李培林,李強(qiáng),孫立平等(2004)。《中國社會(huì)分層》。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
[14]陸學(xué)藝(2002)。《當(dāng)代中國社會(huì)階層研究報(bào)告》。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
[15]陸曄(2008)。意見多元、差異化與公民社會(huì)之可能。載《財(cái)經(jīng)(年刊):“2009:預(yù)測(cè)與戰(zhàn)略”》(頁178-179)。
[16]麥奎爾(2006)。《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第4版)》(崔保國、李琨譯)。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
[17]潘忠黨(2000)。歷史敘事及其建構(gòu)中的秩序。載陶東風(fēng)、金元浦、高丙中(編)《文化研究》(第一輯,221-238頁),天津: 天津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
[18]邱林川、陳韜文(2009)。邁向新媒體事件研究。《傳播與社會(huì)學(xué)刊》,第9期,頁19-37。
[19]孫立平(2003)。《斷裂: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hu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
[20]孫瑋(2007)。“我們是誰”:大眾媒介對(duì)于新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的集體認(rèn)同感建構(gòu)――廈門PX項(xiàng)目事件大眾媒介報(bào)道的個(gè)案研究。《新聞 大學(xué)》,秋季號(hào),頁145-153。
[21]孫瑋、李美慧(2009)。制造上海:報(bào)紙中的"上海開埠"――以2003年為例。《新聞大學(xué)》冬季號(hào)。頁84+153-160。
[22]涂爾干(2000)。《社會(huì)分工論》(渠東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出版社。
[23]許紀(jì)霖(2006)。共和愛國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現(xiàn)代中國兩種民族國家認(rèn)同觀。取自“思與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網(wǎng) 站:省略/zwsx/002073.htm。上網(wǎng)日期:2010年4月30日。
[24]詹姆斯•S•科爾曼(2008)。《社會(huì)理論的基礎(chǔ)》(鄧方譯)。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
[25]趙月枝(2005)。中國傳播產(chǎn)業(yè)與入世:一種跨文化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視角。《中國傳媒報(bào)告》,第3期。取自中華傳媒學(xué)術(shù)網(wǎng): academic.省略/article.php?id=2105。上網(wǎng)日期:2010年4月19日。
[26]周裕瓊(2009)。真實(shí)的謊言:抵制家樂福事件中的新媒體謠言分析。《傳播與社會(huì)學(xué)刊》,第9期,頁95-120。
[27]朱學(xué)勤(2006)。“公民意識(shí)”:中國的困難與曲折。載朱學(xué)勤(著),《書齋里的革命》(頁328343)。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社。
[28]朱學(xué)勤(2007)。激蕩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廣州:嶺南大講壇(演講,12月21日)。取自:view.news.省略/ a/20071221/000049_1.htm。上網(wǎng)日期:2008年4月20日,
[29]Berger, P. L. (1998).The limits of social cohesion: Conflict and mediation in Pluralist societies: A report of the Bertelsmann Foundation to the club of Rom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30]Berger-Schimitt, R. (2002). Social cohesion betwee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Pas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for an enlarged union. 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 38(6): 721-748.
[31]Calabrese, A. & Burke, B. R. (1992). American identities: Nationalism,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Journal ofCommunication Inquiry, 16(2): 52-73.
[32]Demertzis, N., Papathanassopoulos, S. & Armenakis, A. (1999). Media and nationalism: The macedonian question.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4(3):26-50.
[33]Guo, Z,, Cheong, W. & Chen, H.(2007). Nationalism as public imagination: The media’s routine contribution tolatent and manifest nationalis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9(5): 467-480.
[34]Hall, S. (1996a).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In Hall, S. & du Gay, P.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pp. 108-127). London: Sage.
[35]Hall, S. (1996b). 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Morley, D. and Chen, K. (Eds.) (1996). Stuart Hall -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pp. 411-440). London: Routledge.
[36]Jenson, J. (1998). Mapping social cohesion: The state of Canadian research.省略cg.umontreal.ca/ pdf/CPRN/CPRN_F03.pdf。上網(wǎng)日期:2010年4月10日。
[37]Lechner, F., J. (2007).Redefining national identity: Dutch evidence on global patter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Comparative Sociology. 48(4):355-368.
[38]Pan, Z. (2010).Enacting the family-nation on a global stage: An analysis of the CCTV’s Spring Festival Gala. InM. Curtin & H. Shah (Eds.), Re-Orienting Global Communication: India and China beyond Borders (pp. 240-259).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39]Sun, W. (2001). Media events or media stories? Time, space and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Studies, 4(1): 25-43.
[40]Trepte, S. (2006). Social identity theory. From: uni-hamburg.de/fachbereiche-einrichtungen/medienpsychologie/ trepte_2006.pdf. 上網(wǎng)日期:2009年8月12日。
第4篇: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重要性范文
關(guān)鍵詞:經(jīng)典憲法概念;新憲法概念;憲法本質(zhì)
中圖分類號(hào):DF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9-0118(2012)-03-00-02
縱觀古今中外憲法的發(fā)展,憲法的概念歷來是學(xué)者談?wù)摵完P(guān)注的重點(diǎn)。目前,學(xué)界對(duì)憲法概念這一問題的探討多屬研究中的老問題新思路,筆者嘗試突破舊有憲法概念經(jīng)典定義的局限,以求得可以解釋當(dāng)下各種憲法困境的新的憲法概念。
一、經(jīng)典(傳統(tǒng))憲法概念及其局限性
(一)經(jīng)典(傳統(tǒng))憲法概念
1、從憲法的特殊地位上來定義。如日本《新法律學(xué)辭典》認(rèn)為憲法“指規(guī)定國家統(tǒng)治體制基礎(chǔ)的法的整體”,中國許多學(xué)者主張的“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也是以憲法在國家中的特殊地位來理解憲法的。
2、從政治民主上來給憲法下定義。如“憲法是規(guī)范民主施政規(guī)則的國家根本法,是有關(guān)國家權(quán)力及其民主運(yùn)行規(guī)則、國家基本政策以及公民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法律規(guī)范的總稱,是政治力量對(duì)比關(guān)系及現(xiàn)存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要求的集中反映”[2]等,都是從這個(gè)意義上理解憲法的。
3、從憲法的階級(jí)本質(zhì)上來界定。列寧曾經(jīng)說過,“憲法的實(shí)質(zhì)在于:國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關(guān)于選舉代議機(jī)關(guān)的選舉權(quán)以及代議機(jī)關(guān)的權(quán)限等的法律,都表現(xiàn)了階級(jí)斗爭(zhēng)中各種力量的實(shí)際對(duì)比關(guān)系。”[3]我國學(xué)者據(jù)此將憲法引伸和解釋成“憲法是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現(xiàn)”、“憲法是集中表現(xiàn)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的國家根本法”。典型的定義如“憲法是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的反映;憲法是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是統(tǒng)治階級(jí)的工具。”
4、從綜合的角度來定義。就大多說學(xué)者來講,其對(duì)憲法的定義往往是多方面的、綜合性的,實(shí)際上僅從某一個(gè)方面來給憲法下定義是很少見的,最典型的就是從階級(jí)本質(zhì)、地位、政治民主三個(gè)方面,將憲法定義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階級(jí)力量對(duì)比的表現(xiàn)”。
(二)經(jīng)典(傳統(tǒng))憲法概念的局限性
1、抽象程度的缺失。傳統(tǒng)憲法概念無法在必要的抽象程度上概括出不同歷史類型、不同國別的憲法所共同包含的最基本的內(nèi)容或所要解決的最根本的問題。這種局限性表現(xiàn)在找不到一條貫穿憲法學(xué)各個(gè)范疇的使它們形成內(nèi)在聯(lián)系并排列有序的基本線索。我國憲法學(xué)沒能找到它最根本的研究對(duì)象,沒有真正認(rèn)識(shí)憲法本身的落后狀況在學(xué)理上的集中反映,源于沒能給憲法下一個(gè)科學(xué)的定義。
2、本質(zhì)揭示的失當(dāng)。概念應(yīng)該揭示本質(zhì),本質(zhì)未能厘清,則憲法概念也無從界定。傳統(tǒng)憲法概念將憲法定義為“集中表現(xiàn)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的國家根本法。”這種觀點(diǎn)長期以來把對(duì)憲法的本質(zhì)理解定格于一種思維定式中來考察,而階級(jí)屬性則是指該事物與一定的階級(jí)利益之間的關(guān)系,它是各種社會(huì)政治事物的共同屬性,而不是憲法獨(dú)特的本質(zhì)屬性。
3、憲法概念的不周延性。憲法概念的不周延,可以從經(jīng)典憲法概念中“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這一特點(diǎn)而略見一斑,并非所有憲法都具備最高法律效力,比如不成文憲法。所以當(dāng)我們的“憲法”不僅僅是指“憲法典”時(shí),其他形式的憲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國憲法)將會(huì)被排除在其所謂的“憲法”之外,以此來定義憲法就會(huì)與現(xiàn)實(shí)相矛盾。
4、時(shí)代性與文化性的局限。經(jīng)典憲法將憲法定義為近現(xiàn)代特有的法現(xiàn)象,這不符合歷史的真實(shí)。在近代以前,人類社會(huì)不存在作為國家根本法的憲法,卻早有古典憲法的存在,國家消亡后憲法的命運(yùn)在經(jīng)典的憲法定義及其理論中也沒有直接論及。隨著現(xiàn)代憲法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憲法突破了西方文化圈的范圍,成為了世界性的文化現(xiàn)象。經(jīng)典的憲法定義不認(rèn)同甚至拒斥憲法的這種新的文化內(nèi)涵,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文化的局限性。
二、新憲法概念
(一)憲法的終極目標(biāo)――人的生存和發(fā)展
人類不斷地?cái)[脫自然、社會(huì)和自身的束縛,逐步走向平等和自由,這是一個(gè)形成、豐富和實(shí)現(xiàn)自身價(jià)值的過程,這一歷程是任何國家、社會(huì)和個(gè)人都不能逾越的,而人的生存和發(fā)展則是這一過程的主線。
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從哲學(xué)意義上說,也就是從其本原的意義上而言,憲法不僅是為著人的生活而存在,而且實(shí)在應(yīng)該是為著人的優(yōu)良的生活而存在。”憲法的這一終極目標(biāo),是站在歷史的角度去審視和揭示憲法的現(xiàn)象,它是一個(gè)更深層次的認(rèn)知,突破了憲法是“統(tǒng)治階級(jí)的重要工具”、“反映統(tǒng)治階級(jí)的意志和利益”等政治話語,讓我們意識(shí)到,“憲法是法律,但更是一種生活理念。在法律生長中,憲法是一根臍帶,一根連著‘母體’(文明)和‘嬰兒’(法律)的臍帶,它源源不斷地汲取著文明的成果,滋養(yǎng)著法律的完善。”既然生存和發(fā)展是人的本質(zhì)追求,憲法作為保障這種追求的最基本的法律,理應(yīng)以人的生存和發(fā)展作為其終極目標(biāo)。
(二)憲法的本質(zhì)――組織政治共同體的規(guī)則
國家并非這種政治共同體的唯一組織形式,當(dāng)然也不是憲法存在的必然空間,憲法與國家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在國家之前,還存在大量的共同體的組織形式,在國家消滅后,人類社會(huì)為了生存發(fā)展的需求,仍然會(huì)以“超國家”組織形式來制定、頒布和實(shí)施憲法,比如歐盟憲法的發(fā)展趨勢(shì)。我們把憲法定義為組織政治共同體的規(guī)則,考慮到了憲法的發(fā)展趨勢(shì),克服了近代憲法概念在認(rèn)識(shí)上的局限性,突破了“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的模式。這里所指稱的“規(guī)則”,并非一般的制度,具體涉及私人生活規(guī)則、“政治國家”的生活規(guī)則和“第三域”的生活規(guī)則,這比僅僅以“調(diào)整國家權(quán)力的運(yùn)行”、“以公民權(quán)利與國家權(quán)力為對(duì)象”等來界定憲法概念更具涵蓋性。
(三)憲法作為根本性的法規(guī)范體系的體現(xiàn)――憲法結(jié)構(gòu)
憲法作為組織政治共同體的規(guī)則,是一個(gè)根本性的法規(guī)范體系,主要體現(xiàn)在憲法結(jié)構(gòu)上。憲法結(jié)構(gòu)是指單一憲法文件的成文憲法在內(nèi)容上的體系和安排,其實(shí)質(zhì)是指憲法內(nèi)容的相互關(guān)系及其外在的表現(xiàn)形式。憲法結(jié)構(gòu)由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和外部結(jié)構(gòu)兩部分組成。
憲法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是指憲法由憲法規(guī)范、憲法的原則和憲法的指導(dǎo)思想三個(gè)不同層次的要素構(gòu)成的規(guī)范體系。這三個(gè)構(gòu)成要素存在于所有憲法之中。憲法規(guī)范(又稱憲法規(guī)則)是憲法結(jié)構(gòu)的實(shí)質(zhì)要素之一,也是憲法的核心和基礎(chǔ)內(nèi)容。憲法原則是憲法結(jié)構(gòu)另一實(shí)質(zhì)要素,它以憲法規(guī)范為前提,是指憲法在調(diào)整某一類社會(huì)關(guān)系時(shí)所持有的基本立場(chǎng)和傾向。憲法精神,以憲法規(guī)范和憲法原則為內(nèi)容,體現(xiàn)和反映一定的占統(tǒng)治地位的政治共同體的意識(shí)形態(tài)和特定時(shí)代的精神。憲法的外部結(jié)構(gòu)是指憲法與其他要素在組成更大社會(huì)系統(tǒng)中的相互關(guān)系,具體表現(xiàn)為由憲法典、憲法性法律、憲法慣例和判例等構(gòu)成的結(jié)構(gòu)體系。
(四)憲法的實(shí)現(xiàn)形式――憲法秩序
憲法是通過對(duì)共同體內(nèi)部以及共同體間的關(guān)系的調(diào)整,以形成憲法秩序,以此來使憲法得以實(shí)現(xiàn)。憲法秩序是將憲法上的(應(yīng)然)秩序變成實(shí)際的社會(huì)秩序,它是建構(gòu)現(xiàn)代法治社會(huì)的根本屬性和價(jià)值目標(biāo)之一。
憲法秩序是應(yīng)然憲法秩序和實(shí)然憲法秩序的統(tǒng)一體,是憲法規(guī)范指導(dǎo)、約束人們行為之后所形成的有序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狀態(tài),是成文憲法、現(xiàn)實(shí)憲法和觀念憲法的協(xié)調(diào)與和諧。憲法秩序作為一種憲法化的社會(huì)秩序,其實(shí)質(zhì)是成文憲法、現(xiàn)實(shí)憲法和觀念憲法相互協(xié)調(diào)的運(yùn)動(dòng)過程,是三者有機(jī)耦合的結(jié)果。在這一運(yùn)動(dòng)過程中,成文憲法是憲法秩序的保障,它是有大量的憲法規(guī)范存在其中并以法律文件和法律條文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憲法,以憲法典、憲法性法律等為存在方式;現(xiàn)實(shí)憲法是憲法秩序的基礎(chǔ)和核心,是“活”的憲法,它回應(yīng)了現(xiàn)實(shí)生活對(duì)憲法的追求,以憲法判例、憲法慣例、黨的政策等為存在方式;觀念憲法是憲法秩序的關(guān)鍵因素,是人類以某種標(biāo)準(zhǔn)來表達(dá)憲法的認(rèn)知和憲法需求,以及對(duì)憲法進(jìn)行的定性,以憲法知識(shí)、憲法要求、憲法評(píng)價(jià)等為存在方式。這一運(yùn)動(dòng)過程是一個(gè)成文憲法反映現(xiàn)實(shí)憲法和現(xiàn)實(shí)憲法適應(yīng)成文憲法的不斷循環(huán)上升的過程。
綜上,憲法是伴隨時(shí)代的變遷而不斷發(fā)展,伴隨人類對(duì)客觀世界的認(rèn)識(shí)而不斷深化,憲法概念呈現(xiàn)出由傳統(tǒng)的內(nèi)涵大、外延小到現(xiàn)代的內(nèi)涵小、外延大,由政治屬性、法律屬性到生活屬性的發(fā)展趨勢(shì)。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特定的社會(huì)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賦予了憲法概念特定的內(nèi)涵和外延;憲法的產(chǎn)生雖然起初不是基于民主與正義,但是憲法的概念又無時(shí)無刻不在談?wù)撝@些價(jià)值,以憲法判例、憲法慣例、政策等形式存在于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協(xié)調(diào)著觀念憲法和現(xiàn)實(shí)憲法;憲法與一個(gè)社會(huì)的有機(jī)體密不可分,憲法有其自身的本土性和民族性,憲法發(fā)展到了一定歷史階段必然孕育出自己的文化生活規(guī)則。這些要求我們?cè)诮缍☉椃ǜ拍顣r(shí),要用發(fā)展的眼光審視憲法,同時(shí)堅(jiān)持主客觀相統(tǒng)一,在界定憲法概念時(shí)必須反映一個(gè)國家或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社會(huì)歷史及現(xiàn)實(shí)。
參考文獻(xiàn):
[1]劉茂林.憲法究竟是什么[J].中國法學(xué),2002,(6):15-20.
第5篇: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重要性范文
論文摘要:民族認(rèn)同是民族的自覺行為,表現(xiàn)為一種歸屬感。跨界民族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認(rèn)同方面具有多重性,即民族認(rèn)同、政治認(rèn)同、文化認(rèn)同和社會(huì)認(rèn)同。歷史表明,在國際關(guān)系中,政治認(rèn)同和社會(huì)認(rèn)同的作用最為敏感。因此,要處理好跨界民族問題,必須解決好跨界民族的多重認(rèn)同問題。
冷戰(zhàn)結(jié)束以來,國際關(guān)系中存在著一種特別吸引世人眼球的國際社會(huì)現(xiàn)象,即圍繞著民族有關(guān)的表現(xiàn)為各種形態(tài)的地區(qū)爭(zhēng)端或沖突,而且隨著歷史的繼續(xù)演進(jìn),這些地區(qū)沖突有著進(jìn)一步加劇之趨勢(shì)。深入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沖突一方面涉及到“冷戰(zhàn)期間被認(rèn)為已經(jīng)或趨于消失而在冷戰(zhàn)結(jié)束后已成為國際政治畫屏的最重大焦點(diǎn)之一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還涉及到認(rèn)同這個(gè)十分復(fù)雜的問題,尤其在存在跨界民族或跨界民族問題的地方更是如此。
一、跨界民族的形成
提起跨界民族(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首先就包含了一個(gè)基本的理論前提即政治范疇中的“邊界或國界”。“邊界或國界”一方面包含了作為社會(huì)文化層面的民族的地理居住地,這種居住地具有一定的歷史性;另一方面包含了作為政治領(lǐng)域的民族的領(lǐng)土分界,這種分界具有相當(dāng)?shù)默F(xiàn)實(shí)性。為此,有學(xué)者將跨界民族定義為“那些原發(fā)民族和其傳統(tǒng)聚居地都被分割在不同國家而在地域相連并擁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由此可見,跨界民族的最初形成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就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產(chǎn)生和演變的歷史模式而言,“有的是歷史演變的自然結(jié)果,更多的國家民族的形成是非自然發(fā)展(如外國干涉或采取暴力的強(qiáng)迫手段)”。這是一個(gè)典型的悖論。“所謂民族國家,即國家的領(lǐng)土與某一民族所居住的疆域一致,是‘民族’從它的自然狀態(tài)轉(zhuǎn)變?yōu)椤畤摇恼涡螒B(tài)。”它暗示了國家和民族的一致性。
二、跨界民族的多重認(rèn)同
什么是認(rèn)同(Identity)?這是一個(gè)困擾學(xué)術(shù)界很久的難題,西方學(xué)者將它認(rèn)為是無所不在同時(shí)又含義模糊的重要概念。非常有意思的是,雖然大家都知道很難對(duì)其下一個(gè)科學(xué)和準(zhǔn)確的定義,但是大家卻一直都在高頻率地使用這個(gè)概念,而且學(xué)術(shù)界圍繞對(duì)認(rèn)同的研究興趣一直沒有減退。總結(jié)國內(nèi)外學(xué)者們的觀點(diǎn),盡管有著各種各樣的表述,但還是有這樣一些共同或共通的地方,即認(rèn)同“是一個(gè)人或一個(gè)群體的自我認(rèn)識(shí),它是自我意識(shí)的產(chǎn)物:我或我們有什么特別的素質(zhì)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們不同于他們”。在國際關(guān)系研究領(lǐng)域,著名學(xué)者俞正樑則認(rèn)為認(rèn)同是“建立在共同體成員共同特性基礎(chǔ)上的、區(qū)別于他者的共有身份與形象,以及對(duì)共同體的歸屬感”。“認(rèn)同有兩個(gè)向度,一是原生的或內(nèi)生的認(rèn)同,即自我因文化等因素所造就的認(rèn)同,二是社會(huì)建構(gòu)的認(rèn)同,即自我與他者通過互動(dòng)所造就的認(rèn)同。”
由此可見,可以這樣來對(duì)認(rèn)同進(jìn)行理論界定:(1)認(rèn)同的發(fā)生首先是基于自我和他者的比較,在某種條件下上升為一種認(rèn)識(shí),這種認(rèn)識(shí)認(rèn)為差異或差別是實(shí)際存在的,并且這種差異或差別也獲得他者的體認(rèn);(2)認(rèn)同涉及的內(nèi)容有形象、身份、符號(hào)、記憶、文化、傳說和歷史,并且表現(xiàn)為一種社會(huì)心理的認(rèn)同感和歸屬感;(3)認(rèn)同是一種心理意識(shí),其表現(xiàn)形態(tài)取決于自我和他者對(duì)具體情勢(shì)的認(rèn)知、比照和判斷,這種心理意識(shí)具有相當(dāng)?shù)姆€(wěn)定性和傳承性;(4)認(rèn)同并非是單一形態(tài),通常是以復(fù)合形態(tài)出現(xiàn)在各種問題領(lǐng)域中的,且復(fù)合形態(tài)下的各種因素交互作用互相影響。以上的界定為我們探討跨界民族的認(rèn)同提供基本的理論分析路徑。我們以跨界民族認(rèn)同的內(nèi)容為標(biāo)準(zhǔn),大致可以將其劃分為民族認(rèn)同、政治認(rèn)同、文化認(rèn)同和社會(huì)認(rèn)同等類型,顯然,深入探討這些認(rèn)同的屬性對(duì)深入理解和解決跨界民族問題提供必需的理論基礎(chǔ),是大有裨益的。
1 民族認(rèn)同
民族被認(rèn)為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是一種社會(huì)歷史現(xiàn)象。認(rèn)同在民族產(chǎn)生、發(fā)展和演變的過程中,始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認(rèn)為是構(gòu)成民族的六大要素之一。顧名思義,跨界民族首先是以民族的身份出現(xiàn)的,所以民族認(rèn)同即是民族成員在對(duì)民族整體的認(rèn)同心理和民族成員之間的認(rèn)同心理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一種高度自覺的民族歸屬感。這種歸屬感是隨著歷史的發(fā)展而不斷凝結(jié)和升華的,最后形成一種為所有成員共同認(rèn)同的復(fù)合體,比如中華民族形成的多元一體格局。
由于跨界民族本身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在相當(dāng)一段時(shí)期內(nèi),跨界民族的民族認(rèn)同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眾所周知,跨界民族是民族和民族國家并非完全疊合的表現(xiàn)形式。換言之,就是作為社會(huì)歷史中的民族和作為利益政治中的國家不一致而直接導(dǎo)致的。但是,從其產(chǎn)生的淵源、發(fā)展的過程、共有的風(fēng)俗習(xí)慣、共同的生產(chǎn)方式、共同的文化生活和共同的心理認(rèn)同等標(biāo)準(zhǔn)來看,只不過是同一族群或種族跨越兩個(gè)或兩個(gè)以上國家的政治邊界且連成一片居住狀態(tài)而已。所以,適用于社會(huì)層面的民族的認(rèn)同很大程度上也適用于國際關(guān)系層面的跨界民族的認(rèn)同。這是因?yàn)槊褡宓恼J(rèn)同具有多層次性,就像中華民族的56個(gè)兄弟民族的認(rèn)同也是如此,有對(duì)作為國族(na-tion)的集體認(rèn)同,也有對(duì)自己作為中華民族其中一分子的自我認(rèn)同——族群認(rèn)同。對(duì)此,概括得最為全面。他說,中華民族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rèn)同意識(shí),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yùn)的感情和道義。對(duì)中華民族的認(rèn)同是高層次認(rèn)同,對(duì)本民族的認(rèn)同是低層次認(rèn)同,不同層次的認(rèn)同可以并行不悖。
需要指出的是,跨界民族的民族認(rèn)同是一把雙刃劍,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影響。當(dāng)今世界上的國家90%以上是多民族國家,由于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交互作用,這些多民族國家有相當(dāng)一大部分又存在著跨界民族,如何理性認(rèn)識(shí)跨界民族的民族認(rèn)同現(xiàn)象,并在此基礎(chǔ)上采取合理的措施和執(zhí)行正確的政策就顯得格外重要了。鑒于民族認(rèn)同穩(wěn)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民族國家是積極面對(duì)還是消極回避,以及解決問題的手段和藝術(shù),在冷戰(zhàn)后民族分裂主義盛行的今天確實(shí)是考驗(yàn)民族國家的一大難題。事實(shí)一再表明,如果多民族國家能夠妥善處理最高層次的民族認(rèn)同和最低層次的民族認(rèn)同之間的關(guān)系,尊重事實(shí),尊重歷史,尊重意愿,尊重主流,跨界民族的民族認(rèn)同問題是不會(huì)成為民族和諧、社會(huì)進(jìn)步和國家發(fā)展的負(fù)擔(dān)的,相反倒是起到積極促進(jìn)作用,中國政府在這方面所采取的一貫政策就是最好的例證。
2 政治認(rèn)同
對(duì)于民族來說,政治訴求始終是一個(gè)重要的關(guān)切。相對(duì)于其他社會(huì)歷史現(xiàn)象,對(duì)權(quán)力和利益的關(guān)注是民族行事的最初出發(fā)點(diǎn)和最后的落腳點(diǎn),民族國家中的國族意義層面上的民族更是將其發(fā)揮到了極致。正如馬克斯·韋伯指出那樣:“在難以界定和把握的‘民族’之后,擁有一個(gè)共同目標(biāo),該目標(biāo)直接地植根于政治事務(wù)領(lǐng)域……我們可以從這個(gè)層面來理解民族這一概念,即民族是一個(gè)可以憑借自己方式來表達(dá)自己感情的共同體,并且一個(gè)民族常常傾向于自己最初發(fā)源的國家的共同體。”簡單地說,民族天生具有政治的本能。這種政治本能在認(rèn)同方面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效忠對(duì)象而且其效忠對(duì)象相對(duì)是穩(wěn)定的,這個(gè)效忠對(duì)象就是國家;再一方面就是效忠對(duì)象即國家需要為民族的產(chǎn)生、發(fā)展和演進(jìn)提供必須的生存空間、必要的物質(zhì)基礎(chǔ)和必備的制度保證。
然而,對(duì)于跨界民族而言,政治認(rèn)同就變成了一個(gè)令人困惑和犯難的大問題。跨界民族首先是民族,同時(shí)又是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民族。這是因?yàn)樽袁F(xiàn)代民族國家產(chǎn)生以來,通常意義上的民族都是在一定政治實(shí)體之內(nèi)即國家所屬范圍進(jìn)行效忠的,然而跨界民族是“一種特殊民族共同體”,其分布跨越了兩個(gè)或兩個(gè)以上的國家疆域,所以他們?cè)谛е覍?duì)象的選擇就顯得異常困難和引人注目,其可能性有:(1)對(duì)最初自己所發(fā)源的國家的效忠;(2)對(duì)現(xiàn)在自己所居住的國家效忠;(3)對(duì)兩個(gè)國家都效忠;(4)對(duì)兩個(gè)國家都不效忠,尋求新的的效忠對(duì)象,如另外建立自己的國家等。
可是,在戰(zhàn)后以來的國際關(guān)系中,跨界民族的以上選擇卻是異常的艱難。對(duì)于第一種情況,許多存在跨界民族阿國家主要是在戰(zhàn)后反帝反殖反霸的浪潮中建立起來的,由于西方殖民主義的擴(kuò)張,一些民族在權(quán)力政治的作用下變成了跨界民族,跨界民族本身在發(fā)展方面又存在著不平衡性,其中分布在邊界兩端的他們要實(shí)現(xiàn)對(duì)原來發(fā)源的國家效忠的時(shí)候,總有居住于兩國之內(nèi)的一方變得幾乎不可能,形成了“合法性危機(jī)”。對(duì)于第三種情況,要求跨界民族對(duì)所分布的兩個(gè)國家都要效忠,這種動(dòng)機(jī)一開始就遭到國家的反對(duì),尤其是在那些歷史上存在恩怨、隔閡和誤解而在現(xiàn)實(shí)中又沒有走出歷史陰影的兩個(gè)國家更是如此。對(duì)于跨界民族自身來說,他們也不愿意那樣,因?yàn)樘幚聿缓茫麄冊(cè)诂F(xiàn)實(shí)中有可能被當(dāng)成“第五縱隊(duì)”,尤其是在兩國關(guān)系不正常時(shí)往往遭到無端的懷疑、排擠、壓制或懲罰,所以這樣的想法通常被認(rèn)為極為不明智和不理性之舉。對(duì)于第四種情況,戰(zhàn)后以來的國際關(guān)系有一個(gè)顯著的特征,那就是現(xiàn)行國家邊界和疆域相對(duì)穩(wěn)定,跨界民族要建立自己的國家,往往受到國際關(guān)系的制約,特別是跨界民族本身所居住的相鄰國家更是一致的反對(duì)和制止,比如中東地區(qū)的庫爾德人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這種想法的可操作性無疑會(huì)遭到大多數(shù)人的質(zhì)疑。無奈之下,跨界民族最后只有選擇和接受第二種方案了,這種做法也為國際社會(huì)普遍認(rèn)可。問題是,由于一些國家對(duì)跨界民族采取不公正、不合理的政策和待遇,跨界民族在民族主義的作用下,再加上其他外部力量的支持,最后就形成了棘手的跨界民族問題,比如中亞地區(qū)的俄羅斯人問題、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巴斯克人問題、前南斯拉夫境內(nèi)諸族問題、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一泰米爾問題等。
3 文化認(rèn)同
文化被認(rèn)為是民族構(gòu)成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以復(fù)合體的形式存在和出現(xiàn)的。認(rèn)同則是民族對(duì)固有的習(xí)俗和傳統(tǒng)而產(chǎn)生的歸屬感,其主要?jiǎng)訖C(jī)就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間作出的區(qū)別。所以文化認(rèn)同被理解成民族對(duì)其本身的傳統(tǒng)而生發(fā)的一種內(nèi)在情結(jié)(complex)。對(duì)民族而言,“文化作為價(jià)值和意義體系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但它不能與衍生的結(jié)構(gòu)現(xiàn)象分離開來”,所以文化被視為限定一個(gè)族群區(qū)別于另一個(gè)族群的生活方式。
顯然,這種理論認(rèn)識(shí)就很難適用于跨界民族的認(rèn)同問題的討論。因?yàn)椤叭藗兤毡槌姓J(rèn),民族國家是一種現(xiàn)代西方建構(gòu)”。而跨界民族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衍生物,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亞、非、拉廣大地區(qū)。這些地區(qū)長期以來,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本身就存在了許多恩恩怨怨,跨界民族在文化認(rèn)同方面就面臨許多困惑,比如跨界民族究竟以哪一個(gè)文化主體作為其認(rèn)同的對(duì)象:是最初的母體文化還是現(xiàn)在所居住國家的主體文化?作為一種文化情結(jié),按理應(yīng)該是對(duì)最初母體文化的認(rèn)同,但問題是母體文化如果在現(xiàn)在國家不是作為主體文化而存在而是作為該國的文化支系而存在,或者該母體文化在內(nèi)力或外力的作用下,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的演變或者逐漸衰落了,那么對(duì)面居住的同根同族同文同血脈的族群將怎么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文化認(rèn)同呢?
當(dāng)今世界上的民族國家90%以上都是異質(zhì)民族國家,盡管這些異質(zhì)民族國家也公開承認(rèn)尊重和保護(hù)文化的多樣性,但隨著交流的增多,融合始終是大趨勢(shì),一體化則是最后歸宿。所以,最后的結(jié)局極有可能是“只要民族國家以為它可以通過多元主義或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把這些東西置于樊籬之中,它們就會(huì)被視作為某種更充分的一體化邁進(jìn)的道路上的一些加油站”。跨界民族由于分布在兩個(gè)或兩個(gè)以上的民族國家,作為這些國家民族構(gòu)成的一分子,其文化的異質(zhì)性的生存處境越來越艱難了,主要是這些國家一方面強(qiáng)調(diào)文化的多樣性,但對(duì)文化同質(zhì)性的追求在全球化的今天卻變得更加強(qiáng)烈。換言之,跨界民族在文化認(rèn)同方面變得更加模糊化。與此同時(shí),圍繞文化認(rèn)同而引發(fā)的跨界民族問題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了。
4 社會(huì)認(rèn)同
民族作為一種社會(huì)歷史現(xiàn)象,它的產(chǎn)生、發(fā)展和演進(jìn)總是同一定社會(huì)發(fā)展緊密聯(lián)系,同時(shí),社會(huì)運(yùn)行狀況和社會(huì)屬性也會(huì)體現(xiàn)在民族的發(fā)展過程中,從而形成民族的社會(huì)認(rèn)同。“社會(huì)認(rèn)同是一個(gè)社會(huì)群體的自我意識(shí),是對(duì)于‘我們’區(qū)別于‘他們’特質(zhì)的認(rèn)識(shí),是社會(huì)成員共同擁有的信仰、價(jià)值和行動(dòng)的集中體現(xiàn),它包含了群體中的個(gè)體對(duì)于所屬群體及其文化的歸屬感和內(nèi)心的承諾。”對(duì)于跨界民族而言,社會(huì)認(rèn)同除了具有作為民族所具有的歸屬感和自我體認(rèn)以外,還包括他們?cè)谒幼〉膰彝渌迦旱淖咫H關(guān)系究竟如何。簡言之,就是跨界民族的社會(huì)適應(yīng)性和民族融合程度同其發(fā)展?fàn)顩r是否協(xié)調(diào)。歷史證明,跨界民族的社會(huì)認(rèn)同常常受居住國的社會(huì)秩序、社會(huì)狀況和社會(huì)變遷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
總的來看,跨界民族的社會(huì)認(rèn)同有4種類型:(1)和而不同,一些多民族國家實(shí)行平等或?qū)捤傻拿褡逭撸菩卸嘣髁x,作為其國民構(gòu)成之一的、在數(shù)量上屬于非主體的跨界民族同其他族群關(guān)系和諧。在文化上,各族群之間的民族文化和傳統(tǒng)習(xí)俗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良好的發(fā)展;在社會(huì)融入程度方面,跨界民族同其他族群已經(jīng)相互適應(yīng),社會(huì)聯(lián)系緊密,社會(huì)心理成熟,以及在社會(huì)發(fā)展過程中互相關(guān)照,形成休戚與共,良性互動(dòng),呈現(xiàn)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局面,比如中國和越南之間的京族(越族)、苗族(赫蒙)和仡佬族達(dá)到“和而不同”的理想情形。(2)由和而同,在一些存在跨界民族的多民族國家里,盡管政治邊界把同一個(gè)族群分布在兩個(gè)國度里,跨界民族在與主體民族的族際關(guān)系總的來說是和諧的。隨著時(shí)代的變遷,跨界民族在文化上已經(jīng)相互適應(yīng);在社會(huì)觀念上,跨界民族經(jīng)由了“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巨大轉(zhuǎn)型,最后融入了該國的社會(hu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中國和老撾之間的瑤族就是最好的例證。(3)因同而和,跨界民族在發(fā)展和演進(jìn)的過程中,在文化上,跨界民族的民族文化已經(jīng)成為所居住國的文化的一個(gè)支系,同時(shí)與其他文化支系之間在經(jīng)歷過碰撞和交鋒之后,已經(jīng)相互借鑒,互相認(rèn)同,形成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社會(huì)心理方面,跨界民族的適應(yīng)性相對(duì)較高,實(shí)現(xiàn)了完全融入的狀態(tài),比如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56個(gè)兄弟民族之一的朝鮮族就是典型。(4)不和不同,在許多存在跨界民族問題的地區(qū),跨界民族與居住國之間的族際關(guān)系由于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原因顯得不是很正常,文化上相對(duì)封閉,心理上互相防范,社會(huì)融入度相對(duì)較差,社會(huì)適應(yīng)性明顯不夠。在這種情況下,跨界民族和居住國的主體民族相互不認(rèn)同,或者主體民族采取的強(qiáng)制措施和高壓政策不為跨界民族接受與認(rèn)可,族際關(guān)系通常顯得緊張,尤其是在對(duì)面同一民族的支持與鼓動(dòng)下,跨界民族的要求擺脫現(xiàn)狀,追求如自治等政治目標(biāo),離心傾向較大,從而引發(fā)相關(guān)國家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冷戰(zhàn)之后,前南斯拉夫境內(nèi)的科索沃問題、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的納卡問題、盧旺達(dá)的種族屠殺等跨界民族問題,就是由于跨界民族和主體民族之間“不和不同”的歷史因素同現(xiàn)實(shí)政治糾纏在一起共同引發(fā)的緊張局勢(shì)。
第6篇: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重要性范文
關(guān)鍵詞 common good public interest 公共 公眾
〔中圖分類號(hào)〕D03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0447-662X(2013)04-0029-11
黨的十報(bào)告強(qiáng)調(diào)“必須堅(jiān)持維護(hù)社會(huì)公平正義”,毫無疑問,政府應(yīng)當(dāng)在堅(jiān)持維護(hù)社會(huì)公平正義方面扮演著主要角色。因?yàn)椋鐣?huì)公平正義并不是能夠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自發(fā)產(chǎn)生的,而是需要通過政府的努力去獲得。政府在社會(huì)公平正義實(shí)現(xiàn)中的特殊角色決定了它的性質(zhì)以及存在狀況都是我們首先必須加以關(guān)注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回答什么樣的政府可以提供社會(huì)公平正義的問題。當(dāng)然,我國致力于建設(shè)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ì)主義,中國政府是中國人民從事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事業(yè)的政府,它有著自身獨(dú)具的性質(zhì),但是,近代以來所有政府都努力追求的公共性也必然是中國政府必須擁有的一項(xiàng)基本屬性。“公共”一詞有著清晰的現(xiàn)代特色,公共性也是現(xiàn)代政府應(yīng)當(dāng)擁有的屬性。正是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我們時(shí)時(shí)處處感受到了“公共”一詞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世界之中:幫助我們出行的是公共交通,保障我們健康的是公共醫(yī)療,甚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wù)也是社會(huì)正常運(yùn)轉(zhuǎn)須臾不可缺少的因素。我們也許難以想象,如果把所有這些用“公共”一詞加以定義的事項(xiàng)都改換了名稱的話,或者把它們統(tǒng)統(tǒng)用“私人”來加以定義的話,我們的社會(huì)將變成什么樣子?這表明,我們生活在一個(gè)具有“公共性”的時(shí)代,在哲學(xué)的意義上,正是具有“公共性”的事項(xiàng)維持著我們社會(huì)的健康運(yùn)行。所以,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社會(huì)治理體系及其過程都需要以維護(hù)具有公共性的社會(huì)事項(xiàng)為其基本內(nèi)容,而且,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社會(huì)治理體系也能夠在維護(hù)這些具有公共性的事項(xiàng)中使自己獲得公共性。我們看到,人們往往把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社會(huì)治理稱作為“公共治理”,把開展具體的社會(huì)治理活動(dòng)的行為及其過程稱作為公共行政,但是,我們也必須指出,所有這些與“公共”一詞相關(guān)的社會(huì)事項(xiàng)都是歷史建構(gòu)的結(jié)果,是在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歷史地建構(gòu)起來的。如果說“公共”一詞古已有之的話,那么,作為一種觀念,作為一個(gè)用來進(jìn)行學(xué)術(shù)敘事的概念,則是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發(fā)明的。我們的政府產(chǎn)生于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我們的行政改革以及所有的政府建構(gòu)行動(dòng),都必須走在公共性增長的道路上。只有當(dāng)政府有了公共性,我們的社會(huì)才會(huì)有公平正義,政府的公共性是我們的社會(huì)獲得公平正義的前提。
一、從common good到public interest
從詞源上看,英語中的public與古羅馬人所說的res publica(直譯“公共事務(wù)”,常作“共和國”)有著顯而易見的聯(lián)系;馬修斯(David Mathews)更是認(rèn)為,英語中的public與common直接起源于希臘語中的pubes與koinon。David Mathews, “The Public in Practice and Theo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44, Special Issue: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84, pp. 120-125.但是,這些詞源上的關(guān)系能否證明古代希臘人與羅馬人的頭腦中已經(jīng)具備了現(xiàn)代英國人的公共觀念?我們認(rèn)為,答案應(yīng)當(dāng)是否定的。無論是公共的概念還是公共的觀念,都不可能產(chǎn)生于古希臘和古羅馬,而且也不可能出現(xiàn)在中世紀(jì),公共的觀念是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逐步生成的,作為學(xué)術(shù)概念的“公共”一詞也是學(xué)者們用以進(jìn)行理論探索和學(xué)術(shù)研究的工具。
根據(jù)哈貝馬斯的考察,“在英國,從17世紀(jì)中葉開始使用‘公共’(Public)一詞,但到當(dāng)時(shí)為止,常用來代替‘公共’的一般是‘世界’或‘人類’。同樣,法語中的‘公共’(Le Public)一詞最早也是用來描繪格林詞典中所說的‘公眾’(Publikum),而‘公眾’一詞是18世紀(jì)在德國開始出現(xiàn),并從柏林傳播開來的;到這個(gè)時(shí)候?yàn)橹梗藗円话愣颊f‘閱讀世界’,或干脆就叫世界(今天來看就是指全世界)。阿德隆(Adelung)把在公共場(chǎng)所圍繞著一位演說家或表演家而形成的公眾和從事閱讀的公眾區(qū)別了開來;但無論是哪種公眾,都是在‘進(jìn)行批判’。公眾范圍內(nèi)的公斷,則具有‘公共性’(Publizitt)。17世紀(jì)末,法語中的‘publicité’一詞被借用到英語里,成了‘publicity’;德國直到18世紀(jì)才有這個(gè)詞。批判本身表現(xiàn)為‘公眾輿論’,而德語的‘公眾輿論’(ffentliche Meinung)一詞是模仿法語‘opinion publique’在18世紀(jì)下半葉造出來的。英語中的‘public opinion’大概也是在這個(gè)時(shí)候出現(xiàn)的。不過,在此之前,英語里早就有‘general opinion’這個(gè)說法了。”[德]哈貝馬斯:《公共領(lǐng)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等譯,學(xué)林出版社,1999年,第24-25頁。部分原文參照英文版進(jìn)行了補(bǔ)充,見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rederick Lawrenc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9, p. 26.根據(jù)這段描述,在英語、法語和德語這三種較為現(xiàn)代的歐洲語言中,“公共”與“公共性”的概念都是在17世紀(jì)以后產(chǎn)生的,當(dāng)它以名詞的形式出現(xiàn)時(shí)——如the public,則是指當(dāng)時(shí)正在形成之中的公眾。
梅爾頓(James Van Horn Melton)認(rèn)為,public在古羅馬時(shí)期和中世紀(jì)后期或近代早期有著不同的含義,在近代早期所具有的是“公眾”的含義,而在古羅馬時(shí)期則具有“公共”的含義。梅爾頓說,“Public在更加晚近的時(shí)候獲得了一種含義,使我們可以在受眾(audience)的含義上使用它,比如我們可以說一本書、一場(chǎng)音樂會(huì)、一幕戲劇或一場(chǎng)畫展的公眾。讀眾(reading public)、聽眾(music public)、觀眾(theater public)——這樣的用法從17世紀(jì)開始出現(xiàn),并在18世紀(jì)變得流行。不同于早前的含義,這些用法與國家權(quán)威的行使無關(guān)。它們所指的是由私人個(gè)體所構(gòu)成的公眾,在對(duì)他們所讀到、觀察到或體驗(yàn)到的事物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James Van Horn Melton, 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梅爾頓的這段話顯然暗示public在先前還有另一種含義,這種“早前的含義”所指的是古羅馬的“公共”概念。根據(jù)梅爾頓的考察,“‘public’擁有一段漫長的歷史。在古代羅馬,作為形容詞的publicus可以指稱一個(gè)由公民或臣民構(gòu)成的集體(像在res publica中一樣)及其財(cái)產(chǎn)。羅馬人還將publicus與私人家庭領(lǐng)域?qū)Ρ龋员硎局T如街道、廣場(chǎng)和劇場(chǎng)等公共空間。作為名詞的publicum帶有更為具體的政治含義,指稱國家的領(lǐng)土、財(cái)產(chǎn)或收入。公共與國家之間的這種聯(lián)系在近代早期的歐洲——王朝國家建設(shè)的古典時(shí)期——重新獲得流行,并一直延續(xù)到了今天:候選人為了公職而競(jìng)爭(zhēng),國家機(jī)構(gòu)坐落于公共建筑之中,國家公園是公共財(cái)產(chǎn)。”James Van Horn Melton, 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
比較梅爾頓與哈貝馬斯對(duì)public的不同認(rèn)識(shí),可以發(fā)現(xiàn),哈貝馬斯的理解更有歷史感,或者說,更加合乎歷史發(fā)展的實(shí)際情況。因?yàn)椋诠愸R斯那里,公共的概念是作為公眾興起的結(jié)果而被人們發(fā)明出來的,而這樣的公眾又是由“啟蒙運(yùn)動(dòng)”中大眾閱讀及其公眾輿論所造就的。如果把公眾輿論的出現(xiàn)看成資產(chǎn)階級(jí)革命的一項(xiàng)重要內(nèi)容的話,那么,公共概念的發(fā)明也應(yīng)當(dāng)被視作資產(chǎn)階級(jí)革命的成果。顯然,哈貝馬斯是了解羅馬人發(fā)明了res publica的概念的,事實(shí)上,在《公共領(lǐng)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中,哈貝馬斯對(duì)公共一詞在古代世界中的起源問題也作了必要的回顧,但他卻沒有像阿倫特那樣去到古希臘的集會(huì)廣場(chǎng)(agora)上去尋找公共領(lǐng)域的起源,更不把古典世界中的“公共”視作現(xiàn)代公共概念的前身。這表明,哈貝馬斯非常清楚地認(rèn)識(shí)到了羅馬人所使用的publica、publicus、publicum等概念是不同于現(xiàn)代人所理解的公共的,而是努力去把握中世紀(jì)后期以來的歷史賦予給公共概念的內(nèi)涵。事實(shí)上,從古羅馬語中的publicus到現(xiàn)代英語中的public的轉(zhuǎn)變,決不僅僅是一個(gè)語詞及其含義變遷的問題,而是反映了社會(huì)形態(tài)及其社會(huì)治理方式的根本性變革,即從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向工業(yè)社會(huì)、從共同生活向公共生活的轉(zhuǎn)變。在歷史演變的過程中去認(rèn)識(shí)公共的概念是一個(gè)可取的視角,因而,我們認(rèn)為,哈貝馬斯的觀點(diǎn)是更加合乎歷史實(shí)際的。盡管古代世界中也存在著許多類似于公共的詞匯,但其真實(shí)所指則是可以用現(xiàn)代詞匯中的“共同”一詞來加以概括的,也就是說,是可以歸入“共同”的范疇之中的。只是到了現(xiàn)代,我們才把公共一詞與社會(huì)治理方面的事務(wù)聯(lián)系在一起,才用來描述甚至定義社會(huì)治理方面的事務(wù)。我們認(rèn)為,在人類歷史上的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的歷史階段中,是不存在作為一個(gè)現(xiàn)代概念的公共一詞所指稱的東西的,當(dāng)人們用相關(guān)的詞語去描述或定義某些事務(wù)時(shí),其真實(shí)含義是指那些事務(wù)屬于“共同的”或“共有的”,而不是指領(lǐng)域分化條件下的特定領(lǐng)域中的存在物或事務(wù)。所以,在從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向工業(yè)社會(huì)的轉(zhuǎn)型過程中,也包含著一種從“共同”向“公共”轉(zhuǎn)型的內(nèi)容,具體地說,包含著從common good向public interest的轉(zhuǎn)型。
道格拉斯(Bruce Douglass)的研究發(fā)現(xiàn),common good是一個(gè)普遍使用于前現(xiàn)代世界的詞組,在整個(gè)前現(xiàn)代的時(shí)期中,common good “被視為國家的一個(gè)目的——事實(shí)上是國家的最高目的。它是全部政府活動(dòng)的一個(gè)象征。除了服務(wù)于common good以外,國家沒有其他目標(biāo)。一個(gè)好的統(tǒng)治者的全部所作所為大概都會(huì)被引向這一目的。”③④Bruce Douglass, “The Common Good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Political Theory, Vol. 8, No. 1, 1980, pp. 103-117.道格拉斯特別注意到,“common good包含許多特定的目標(biāo),它們旨在促進(jìn)普遍的人類福祉——比如和平、秩序、繁榮、正義以及共同體。因此,當(dāng)政府不僅增進(jìn)其自身的福祉,而且增進(jìn)了更廣大的社會(huì)福祉時(shí),就有效地促進(jìn)了common good。”③也就是說,common good是共同體的一種共同的善業(yè),而政府則是被用來促進(jìn)這一善業(yè)的工具。從common good的視角出發(fā),道格拉斯看到的是,“中世紀(jì)作家們寫到,當(dāng)政治社會(huì)是井然有序且運(yùn)行順暢的時(shí)候,它就像一個(gè)有機(jī)體,它的各個(gè)部分處在彼此多方交叉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中,不僅能夠促進(jìn)各自相互的福祉,而且對(duì)一個(gè)更大整體的維持做出了貢獻(xiàn)。”④common good向共同體成員所提出的要求是,如果共同的福祉與個(gè)體的福祉發(fā)生了沖突的話,那么,后者就需要為前者讓路。當(dāng)然,由于共同體本身對(duì)于它的成員也具有一種我們今天已經(jīng)無法感受到的無微不至的關(guān)懷(希臘語中的koinon來源于另一個(gè)詞kom-ois,即關(guān)懷David Mathews, “The Public in Practice and Theo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44, Special Issue: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84, pp. 120-125.),共同的福祉也就同時(shí)意味著共同體成員個(gè)人的福祉,一般情況下,并不需要共同體的成員隨時(shí)隨地做出無條件的犧牲,只有在共同體處于危機(jī)的狀態(tài)下,才可能出現(xiàn)這種情況。即使出現(xiàn)了這種狀況,也只能證明共同體成員的個(gè)人福祉是與共同的福祉密切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一種“傾巢之下無完卵”的狀況。也就是說,由于人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共同體意識(shí),當(dāng)他為共同福祉做出了犧牲時(shí),也往往不認(rèn)為自己是在犧牲。這是一種個(gè)體意識(shí)沒有萌芽的狀態(tài),是私人利益沒有覺醒的狀態(tài),在這樣的共同體生活中,當(dāng)一個(gè)人決定要做某事時(shí),影響他行為選擇的因素往往是這件事情是否能給共同體帶來好處,而不是因其符合他自己個(gè)人的利益。
然而,在絕對(duì)國家生成的過程中,“隨著中世紀(jì)封建主義的與民族君主國家的興起,common good越來越多地與君主利益以及該民族在國際政治中的名望與權(quán)力聯(lián)系到了一起。此外,它還開始被用來替王室因資助對(duì)外探險(xiǎn)而征召其臣民的生命與財(cái)產(chǎn)的行為辯護(hù)。”②③④Bruce Douglass, “The Common Good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Political Theory, Vol. 8, No. 1, 1980, pp. 103-117.也就是說,隨著君主及其王室攫取了共同體的,他們也隨之掌握了common good的解釋權(quán),并把它與王室的特定利益等同了起來,使common good變成了王室利益的代名詞。在這種情況下,新興的資產(chǎn)階級(jí)要實(shí)現(xiàn)自己的利益訴求,勢(shì)必要與王室所把持的common good話語相對(duì)抗,于是,他們就發(fā)明了新的概念武器,這就是反王室的public interest一詞的出現(xiàn)。“由此就產(chǎn)生了public interest的概念。特別是在17世紀(jì)中期英格蘭的動(dòng)蕩歷史中,這種語言和觀念上的轉(zhuǎn)變非常明顯。”②所以,public interest一詞有著不同于common good的內(nèi)涵,或者說,public interest所代表的是一種全新的觀念,在直接的意義上,是與王室所解釋的common good相對(duì)立的,而在其更為深層的含義中則反映了社會(huì)的轉(zhuǎn)型和歷史的變革,標(biāo)志著封建共同體的解體和個(gè)體意識(shí)的生成。毫無疑問,public interest一詞意味著人們開始在分散的、孤立的個(gè)體之間尋求一種具有public屬性的東西,而首當(dāng)其沖的就是interest,它不是可以由王室加以掌握和控制的good。
可見,與common good不同,public interest具有一種明顯的個(gè)體取向。“至少在最初的時(shí)候,那些言說著利益語言的人往往是根據(jù)個(gè)體公民的私人福祉來定義政府的目的的,他們尤其關(guān)心物質(zhì)上的幸福——也就是財(cái)產(chǎn)和財(cái)產(chǎn)權(quán)。與那些到處宣揚(yáng)國王特權(quán)和民族榮譽(yù)的人針鋒相對(duì),他們則宣揚(yáng)public interest——它的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含義是指通過培育私人財(cái)產(chǎn)而帶來的繁榮。”③也就是說,盡管帶有public的定語,但public interest則是以個(gè)體的利益為出發(fā)點(diǎn)的,是包含在個(gè)體利益之中的公共性因素。所以,在public interest一詞中是包含著個(gè)體利益覺醒的內(nèi)容的,從common good向public interest的轉(zhuǎn)變也就是共同體為個(gè)體所取代的過程。具體地說,西歐的客觀歷史進(jìn)程經(jīng)歷了這樣一個(gè)一波三折的過程:由于絕對(duì)國家的出現(xiàn),王室/君主攫取了,原有的政治共同體受到了破壞,從而使作為共同福祉的common good受到了王室利益的篡改,使大量無法在新的common good中得到體現(xiàn)的社會(huì)成員作為個(gè)體而被釋放了出來。當(dāng)這些個(gè)體聯(lián)合起來反抗王室/君主的時(shí)候,就形成了一種存在于個(gè)體之間的public interest。“由此,利益的觀念作為一場(chǎng)針對(duì)王室需求的自由的和民主的反抗運(yùn)動(dòng)的一部分而產(chǎn)生了影響。”④在利益觀念的影響下,原來共同體成員間以友愛形式出現(xiàn)的親密關(guān)系也就變成了個(gè)體間冷冰冰的利益關(guān)系,之所以這種冷冰冰的利益關(guān)系沒有使人們隔離開來,是因?yàn)樵谶@種利益關(guān)系之中又包含著一種public interest。
總的說來,public interest這個(gè)概念從一開始產(chǎn)生的時(shí)候就是根源于個(gè)體利益的,用這個(gè)概念去反對(duì)那種反映了王室利益的common good,實(shí)際上也包含了告別傳統(tǒng)的共同福祉的含義。當(dāng)然,在絕對(duì)國家形成之前的漫長歷史中,common good是否意味著一種共同福祉也是值得懷疑的。因?yàn)椋绻f在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的歷史階段中存在著奴隸社會(huì)和封建社會(huì)的話,那么,這兩種社會(huì)形態(tài)中的共同體盡管都是同質(zhì)性的共同體,卻是以等級(jí)制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形式出現(xiàn)的。在等級(jí)制的條件下,common good可能只在極少的情況下才意味著共同福祉。所以,在public interest出現(xiàn)之前,common good基本上是作為統(tǒng)治者的good而存在的,只是由于統(tǒng)治者往往是被看作共同體的化身的,而被統(tǒng)治者又是缺乏個(gè)體意識(shí)的,才使共同體成員誤以為統(tǒng)治者所把持的good是common good了。隨著個(gè)體意識(shí)的覺醒,這種同質(zhì)性狀態(tài)也就被打破了,common good概念也失去了意義,并在個(gè)體意識(shí)的理性化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public interest。所以,以interest定語形式出現(xiàn)的public本身就是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產(chǎn)生的,或者說,它的出現(xiàn)就標(biāo)志著人類歷史進(jìn)入了現(xiàn)代化的過程。
二、理論發(fā)展史上的公共概念
在每一次歷史轉(zhuǎn)型的時(shí)期,人們?cè)谑褂酶拍钌隙紩?huì)表現(xiàn)出極大的隨意性,雖然新的概念被建構(gòu)了起來,但是,更多的人卻習(xí)慣于使用舊的概念,即便是接受了新的概念,也會(huì)用新的概念去定義舊的事物。也就是說,不僅在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會(huì)有人去談?wù)撍^奴隸社會(huì)的公共行政、封建社會(huì)的公共行政,在歷史上的一些歷史轉(zhuǎn)型時(shí)期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當(dāng)public interest的概念被提出之后,很多人是不理解public與common之間的區(qū)別的,直到20世紀(jì)后期,一些不具備歷史意識(shí)的學(xué)者們也依然弄不清它們之間的區(qū)別。Bruce Douglass, “The Common Good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Political Theory, Vol. 8, No. 1, 1980, pp. 103-117.其實(shí),如果人們具有基本的歷史意識(shí)的話,common good與public interest的區(qū)別就變得非常清晰了。從字面上看,common good在通俗的意義上可以被理解為“對(duì)大家都好的事情”,是一種非常籠統(tǒng)的價(jià)值判斷,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家元共同體的成員往往就是根據(jù)這種籠統(tǒng)的價(jià)值判斷來決定他們的行為選擇的。隨著利益意識(shí)的覺醒,人們開始關(guān)注那些有益于個(gè)人利益實(shí)現(xiàn)的事情,這種事情不是存在于人的感覺之中的,而是在理性的分析和認(rèn)識(shí)過程中才能發(fā)現(xiàn)的事情,它就是存在于個(gè)人利益之中的具有普遍性的公共利益。
近代社會(huì)與此前的社會(huì)之間的根本區(qū)別就在于個(gè)體的人的出現(xiàn),由于個(gè)體的人的出現(xiàn)而使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的同質(zhì)性共同體瓦解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學(xué)者都具有歷史意識(shí),所以,他們并不理解近代社會(huì)與其之前的社會(huì)之間存在著這種區(qū)別,因而,也就不理解特殊與普遍、私人與公共之間的辯證法。結(jié)果,一些學(xué)者就把common good和public interest混同了,特別是在不同語言版本的文獻(xiàn)中,我們經(jīng)常發(fā)現(xiàn),一種語言版本中的good在另一種語言版本中往往被翻譯成了interest,而前者中另一個(gè)地方的interest在后者中又被翻譯成了good。同樣,隨著使用頻次的增多,common與public的區(qū)別也開始變得模糊了起來,學(xué)者們經(jīng)常會(huì)在同一個(gè)句子或段落中混同使用這兩個(gè)概念。這為我們判斷作者的意圖增加了難度,如果不能在前述理論范疇的意義上去區(qū)分common good和public interest,甚至?xí)屛覀儫o法正確地去理解歷史。其實(shí),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人是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在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的微觀生活中,這種社會(huì)關(guān)系主要就是共同體成員間的親緣關(guān)系,或者說,農(nóng)業(yè)社會(huì)中的人們生活在一種家元共同體之中,這種共同體阻礙了他們成長為獨(dú)立的個(gè)體,也阻礙了他們與其他共同體的相互承認(rèn)與相互接納。所以,家元共同體中的人們只能看到共同體自身的common good,而看不到個(gè)人與個(gè)人之間、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的public interest。但是,當(dāng)中世紀(jì)后期開始造就個(gè)體的人的時(shí)候,同質(zhì)性的家元共同體也就遭遇了一波又一波的挑戰(zhàn),并最終解體。在家元共同體解體之后,個(gè)體的人面對(duì)著全然陌生的環(huán)境,在個(gè)人的利益追求中與他人開展激烈的競(jìng)爭(zhēng),陷入了霍布斯所說的“自然狀態(tài)”之中。
“自然狀態(tài)”是人的一種不同于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的新型社會(huì)關(guān)系,“社會(huì)契約論”的歷史貢獻(xiàn)也就在于從理論上承認(rèn)了這種關(guān)系,并確認(rèn)了個(gè)體的人在這種關(guān)系中的先在性地位,從而為個(gè)人的利益與財(cái)產(chǎn)權(quán)爭(zhēng)取到了一種自然法上的價(jià)值,使它們獲得了相對(duì)于共同體——尤其是國家——需要的優(yōu)先性。在進(jìn)一步的邏輯延伸中,個(gè)體的人出于自我持存的需要而彼此訂約,自愿地將其所有的部分自然權(quán)利讓渡了出來,形成了一種“”。為了說明這種不是絕對(duì)君主所宣稱的那種,就需要強(qiáng)化這種的來源觀念,即指出這種是每一個(gè)個(gè)體的部分自然權(quán)利的讓渡出來后凝結(jié)而成的,屬于“人民”。但是,每一個(gè)人所讓渡出來的都不是其完整的權(quán)利,而是部分的權(quán)利,這種“部分的權(quán)利”又是無法形象地圖繪出來的,而是一種抽象意義上的權(quán)利,所以,由這些抽象的權(quán)利結(jié)成的“”也是一種抽象的存在。如果它僅僅是一種抽象性的存在的話,那是沒有什么意義的,所以,必須與一些被選的人結(jié)合起來。作為這種結(jié)合的結(jié)果,是被轉(zhuǎn)化為一種權(quán)力。如果說人民的概念中還包含著某些common的話,那么,當(dāng)轉(zhuǎn)化為權(quán)力后,就完全清除了common的內(nèi)涵,從而成為一種具有public屬性的權(quán)力,它就是公共權(quán)力。另一方面,個(gè)體的人也因其讓渡出了部分權(quán)利而實(shí)現(xiàn)了身份的轉(zhuǎn)換,即轉(zhuǎn)變?yōu)椤肮瘛薄>腿耸莻€(gè)體的人而言,他擁有屬于他個(gè)人的一切;就他是公民來看,則是“公共人”,必須參與到公共生活之中,必須在公共生活之中體現(xiàn)出他的“公共人格”。這樣一來,common一詞只有在描述一些微小的群體形態(tài)時(shí)才有著應(yīng)用的價(jià)值,而在公共生活的廣大空間中,則沒有可以放置的場(chǎng)所。然而,公民是平等的,盡管公民的另一種重份作為事實(shí)存在時(shí)必須承載著經(jīng)濟(jì)上的以及其他社會(huì)生活方面的地位不平等,但是,公民的身份則是平衡這種不平等而使其不至于擴(kuò)大的基軸。為了維護(hù)公民的平等權(quán)利,公共權(quán)力的功能就應(yīng)當(dāng)體現(xiàn)在對(duì)公平正義的維護(hù)。
在近代思想史上,霍布斯是較早努力從絕對(duì)國家中去發(fā)現(xiàn)“公共性”的思想家,他在區(qū)分“王室家臣”與“政府大臣”時(shí)提出了“公共大臣”的概念,“公共大臣(publique minister)是者(不論是君主還是議會(huì))用于任何事務(wù)并在該事務(wù)中有權(quán)代表國家人格的人。擁有的人或會(huì)議都代表著兩重人格(Persons),用更普通的話來說便是具有兩重身份(Capacities),一重是自然身份,另一重則是政治身份(比如君主不僅具有國家的人格,而且具有自然人的人格;一個(gè)會(huì)議也不僅具有國家人格,而且具有會(huì)議的人格);所以,為者的自然身份充當(dāng)臣仆的人便不是公共大臣,只有幫助者管理公共事務(wù)的人才是公共大臣。”②③④⑤⑥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4, p. 170、171、173、223、263、428.在這里,霍布斯是根據(jù)的應(yīng)用來定義“公共”的,只有根據(jù)的需要或要求去從事反映和代表的活動(dòng)時(shí),他的活動(dòng)才能被認(rèn)為是一種公共事務(wù),也只有服務(wù)于這種公共事務(wù)的大臣才能被視為公共大臣。分開來說,“其所以是大臣,是因?yàn)樗麄兯?wù)的是那一代表者人格(Person Representative),并且不能做出違抗他的命令或沒有他的權(quán)力為根據(jù)的事情;其所以是公共的,是因?yàn)樗麄兯?wù)的是他的政治身份。”②
顯然,霍布斯是把“公共”與“”這兩個(gè)概念聯(lián)系在一起進(jìn)行考察的,根據(jù)他的思想,這兩個(gè)概念是相互印證的。比如,霍布斯在對(duì)“訴訟”以及“罪行”的判斷中就作出了這樣的區(qū)分,“我所謂的民訴(Common Pleas)是指原告被告雙方都是臣民的訴訟,而在公訴(Publique Pleas)(也稱王室訴訟)中,原告則是者。”③當(dāng)一些罪行既可以引發(fā)民訟也可以引發(fā)公訴的時(shí)候,就以訴訟者的身份而定,根據(jù)霍布斯的意見,“由于幾乎所有罪行都不但對(duì)某些私人,而且對(duì)國家也造成了侵害,所以,當(dāng)同一罪行以國家的名義時(shí)就稱為公罪(Publique Crime),以私人名義時(shí)就稱為私罪(Private Crime)。相應(yīng)提出的訴訟則稱為公訴(Judicia Publica, Pleas of the Crown)或私訴(Private Pleas)。比如在一個(gè)謀殺案的訴訟中,如果控告者是私人,就稱為私訴;如果控告者是者,就稱為公訴。”④同樣,在談到“敬拜”的問題時(shí),霍布斯認(rèn)為,“敬拜也有公共的和私人的兩種。前者是國家作為一個(gè)人而進(jìn)行的敬拜,后者則是個(gè)人所表示的敬拜。”⑤不僅如此,甚至對(duì)于異端的“宗教裁判”也被納入了以為據(jù)的公私二分之中:“異端就是違反公共人格(Publique Person)——即國家代表者——下令教誨的學(xué)說而頑固堅(jiān)持私人見解者。”⑥霍布斯的這些意見是非常重要的,因?yàn)椋趩⒚傻臅r(shí)代,用公與私的視角去看問題是理論建構(gòu)的起點(diǎn),只有在公與私之間作出了區(qū)分,才有可能再去談?wù)撋鐣?huì)契約論的其他主題。在某種意義上,霍布斯的啟蒙先驅(qū)地位也恰恰是因?yàn)槠湓诠c私之間作出區(qū)分而奠定的。盡管今天看來他在公與私之間所作的區(qū)分并不準(zhǔn)確,但其思想的現(xiàn)代性特征已經(jīng)表露無遺,而且,難能可貴的是他已經(jīng)把“公共”一詞與國家——霍布斯與洛克都是用common wealth而不是state來指稱國家的——聯(lián)系在了一起,認(rèn)為“公共(Publique)一詞總是要么指稱國家人格本身,要么便是指稱由國家所有的事物,對(duì)此,任何私人都不能主張其所有權(quán)。”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4, p. 302.
在啟蒙思想家中,孟德斯鳩是最早明確地根據(jù)財(cái)產(chǎn)權(quán)來定義公共利益的。在討論共和國中的品德時(shí),孟德斯鳩使用了l'intérêt public的概念,他認(rèn)為,“我們可以給這種品德下一個(gè)定義,就是熱愛法律與祖國。這種愛要求人們不斷地在他個(gè)人的利益面前選擇l'intérêt public。它是一切私人品德的根源,所謂私德不過就是這種選擇本身。”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Esprit Des Lois, Paris: Librairie De Firmin Didot Frres, 1849, p. 31.但在具體定義公共利益的時(shí)候,孟德斯鳩則使用了bien public的概念:“政治法使人類獲得自由;民法使人類獲得財(cái)產(chǎn)。我們已經(jīng)說過,自由的法律是國家施政的法律;應(yīng)該僅僅依據(jù)關(guān)于財(cái)產(chǎn)的法律裁決的事項(xiàng),就不應(yīng)該依據(jù)自由的法律裁決。如果說,bien particulier應(yīng)該向bien public讓步,那就是荒謬背理之論。這僅僅在國家施政的問題上,也就是說,在公民自由的問題上,是如此;在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的問題上就不是如此,因?yàn)閎ien public永遠(yuǎn)是:每一個(gè)人永恒不變地保有民法所給予的財(cái)產(chǎn)。”⑤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Esprit Des Lois, Paris: Librairie De Firmin Didot Frres, 1849, p. 410. 譯文采自[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下冊(cè),張雁深譯,商務(wù)印書館,1995年,第189-190、182頁。在翻譯的時(shí)候,法語中的bien通常對(duì)應(yīng)的是英語中的good,就這段話而言,該書的第一個(gè)英譯本也將bien譯作good,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Translated by Thomas Nugent, Vol. 2, Fifth Edition, London: J. Nourse and P. Vaillant, 1773, p. 240.但中文本則將其譯為“利益”。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這兩種翻譯都是可以接受的,因?yàn)椋诿系滤锅F使用bien和intérêt的時(shí)候,并沒有要把它們嚴(yán)格區(qū)分開的意思。比如,在談到查士丁尼法典關(guān)于禁止解除婚姻的規(guī)定時(shí),孟德斯鳩寫道:“他使一個(gè)婦女不能結(jié)婚,從而損害了bien public;他使她受到無數(shù)危險(xiǎn)的威脅,從而又損害了l'intérêt particulier。”⑤可見,孟德斯鳩往往更多地是在行文的美學(xué)意義上來使用bien和intérêt的。顯然,由于孟德斯鳩的寫作主要是以古羅馬為參照對(duì)象的,以至于他受到感染而根據(jù)common good的傳統(tǒng)使用bien的概念。盡管如此,在他使用bien這個(gè)詞語時(shí),還是賦予了其public interest的內(nèi)容。所以,中文的翻譯要更為準(zhǔn)確。
盧梭提出了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的概念,也同樣對(duì)公共利益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盧梭所理解的公共利益(lintérêt public)不像是在權(quán)利讓渡過程中所形成的一個(gè)抽象概念,而更多地具有道格拉斯所說的那種對(duì)抗性的特征。比如,在談到法國的三級(jí)會(huì)議時(shí),盧梭寫道:“愛國心的冷卻、私人利益的活躍、國家的龐大、征服、政府的濫用權(quán)力,所有這些都可以使我們想像到國家議會(huì)中人民的議員或代表的來歷。他們也就是某些國家里人們所公然稱之為的第三等級(jí)。這樣竟把兩個(gè)等級(jí)的特殊利益(lintérêt particulier)擺在了第一位和第二位;而lintérêt public卻只占第三位。”Jean-Jacques Rousseau, Du Contract Social, Paris: Librairie Georges Bellais, 1903, p. 261. 譯文采自[法]盧梭:《社會(huì)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wù)印書館,2005年,第120頁。顯然,這里的lintérêt public是一個(gè)相對(duì)于此前作為王室利益的common good——在這里具體體現(xiàn)為前兩大等級(jí)的lintérêt particulier——的革命性概念,而不像是孟德斯鳩所描述的那樣一種治理意義上的概念。在盧梭這里,作為治理概念的公共利益反而是intérêt commun或bien commun:“以上所確立原則之首先而最重要的結(jié)果,便是唯有公意才能夠按照國家創(chuàng)制的目的——bien commun——來指導(dǎo)國家的各種力量;因?yàn)椋绻f個(gè)別利益的對(duì)立使得社會(huì)的建立成為必要,那末,就正是這些個(gè)別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會(huì)的建立成為可能。正是這些不同利益的共同之點(diǎn),才形成了社會(huì)的聯(lián)系;如果所有這些利益之間并不具有某些一致之點(diǎn)的話,那就沒有任何社會(huì)可以存在了。因此,治理社會(huì)就應(yīng)當(dāng)完全根據(jù)這種intérêt commun。”Jean-Jacques Rousseau, Du Contract Social, Paris: Librairie Georges Bellais, 1903, p. 145.從盧梭的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到,經(jīng)歷過市民社會(huì)與王室、貴族的持久較量之后,在啟蒙思想家們的視野中,所看到的是者業(yè)已形成的現(xiàn)實(shí),他們正是在這一前提下去進(jìn)行著述的,因此,他們所思考的對(duì)象都不再是“共同”問題,而是公共問題,都可以被納入public interest而不是common good的理論范疇之中。
三、公意、公共輿論與公眾
如前所述,公眾是在工業(yè)化的過程中出現(xiàn)的,它可以被看作是工業(yè)化的一項(xiàng)成果。然而,在早期啟蒙思想家們的理論敘述中,公眾的地位卻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體現(xiàn)。不過,對(duì)于公眾這一新的歷史現(xiàn)象,如果認(rèn)為啟蒙思想家完全沒有關(guān)注到,那是不合乎事實(shí)的。其實(shí)。在啟蒙思想家們的偉大作品中,公眾的概念(the public、le public)是隨處都可以看到的,這說明啟蒙思想家們雖然看到了公眾的存在,卻沒有意識(shí)到公眾的出現(xiàn)對(duì)于理論建構(gòu)的意義。另一方面,從邏輯上來看,霍布斯已經(jīng)在個(gè)體的人的基礎(chǔ)上設(shè)定了“自然狀態(tài)”,如果他再把公眾作為一個(gè)向量引入的話,就會(huì)對(duì)自然狀態(tài)的假定造成沖擊。因?yàn)椋娨呀?jīng)是個(gè)體的整合形態(tài)了,公眾中必然會(huì)包含著一些后來被康德所確認(rèn)的實(shí)踐理性,個(gè)體必然會(huì)在公眾中得到改造。所以,盡管公眾的形成已經(jīng)是不容否認(rèn)的現(xiàn)實(shí),而啟蒙思想家們出于理論推演的需要卻有意識(shí)地忽略了公眾的重要性,目的是為了使從自然狀態(tài)中推演出來的社會(huì)圖譜有著更為清晰的線條。如果我們這一推測(cè)是正確的話,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今天許多思想家把啟蒙思想歸入到機(jī)械論的范疇中去。也就是說,啟蒙思想家們?yōu)榱耸估碚撟兊帽M可能簡單一些而不得不舍棄某些因素,盡管他們關(guān)于公共概念的理論建構(gòu)極有可能是因現(xiàn)實(shí)中公眾的出現(xiàn)而催生的,但在理論敘述中,他們則必須把公眾置于一旁,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實(shí)現(xiàn)與過往理論的決裂。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我們也需要從其時(shí)代的需求中去加以認(rèn)識(shí),啟蒙思想家們所處的時(shí)代依然承擔(dān)著非常繁重的批判任務(wù),雖然后人較多地從建構(gòu)的方面來理解啟蒙思想們的貢獻(xiàn),而且,他們也確實(shí)努力去繪制新世界的圖景,但是,對(duì)舊世界的致命一擊依然是啟蒙思想家們放在首位的任務(wù)。顯然,在對(duì)舊世界的批判中,所面對(duì)的是一個(gè)同質(zhì)性的家元共同體,能夠?qū)以餐w造成毀滅性攻擊的,無疑是個(gè)體的人。相對(duì)而言,公眾的社會(huì)建構(gòu)意義要更大一些。正是由于這個(gè)原因,啟蒙思想家們給予了個(gè)體的人以更多的重視,把個(gè)體的人作為理論敘述的邏輯起點(diǎn),至于其他因素,要么受到排斥,要么被有意識(shí)地加以忽略,其中,公眾就成了他們有意忽略的因素。可是,在歷史演進(jìn)的實(shí)踐中,個(gè)體的人與公眾之間不僅不像在理論上那樣相互排斥,反而是共在的,社會(huì)朝著個(gè)體的人的方向分化得越是充分,公眾的成長也就越迅速,到了盧梭開始著述的時(shí)候,公眾已經(jīng)發(fā)育得非常巨大,以至于盧梭不得不對(duì)公眾作出理論思考。這段理論發(fā)展史對(duì)于我們的啟發(fā)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出于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要求,我們需要突出個(gè)體的人,而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已經(jīng)建立起來之后,當(dāng)我們關(guān)注協(xié)商民主的問題時(shí),就必須把公眾作為理論建構(gòu)的前提。
在契約論思想家中,盧梭可以說是第一個(gè)對(duì)公眾表達(dá)了公開承認(rèn)的思想家,他看到了lopinion publique的存在,并試圖從此出發(fā)去進(jìn)行他的制度構(gòu)想。在談到古羅馬掌管風(fēng)紀(jì)的監(jiān)察官制時(shí),盧梭寫道:“正如法律是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的宣告,監(jiān)察官則是公共判斷(jugement public)的宣告。”②③Jean-Jacques Rousseau, Du Contract Social, Paris: Librairie Georges Bellais, 1903, p. 312、314、314.這種判斷通過監(jiān)察官的宣告而成為了l'opinion publique。在盧梭看來,“l(fā)opinion publique是決不會(huì)屈服于強(qiáng)制力的,所以在為了代表它而設(shè)置的法庭里,并不需要有絲毫強(qiáng)制力的痕跡。”②也就是說,lopinion publique應(yīng)當(dāng)通過監(jiān)察官的制度而得到確認(rèn),而且,由于lopinion publique主要是一個(gè)風(fēng)紀(jì)的問題,監(jiān)察官制度也應(yīng)當(dāng)是一種柔性的制度,而不是強(qiáng)制性的制度。對(duì)于監(jiān)察官制度,盧梭著墨不多,他對(duì)lopinion publique概念使用得也較少,甚至還有一次是以lopinion commune的表達(dá)形式出現(xiàn)的。③但是,lopinion publique概念在理論發(fā)展史上的意義卻非常重大,特別是到了20世紀(jì),當(dāng)lopinion publique被作為公共輿論而得到人們的普遍關(guān)注后,甚至成了多學(xué)科研究的對(duì)象。
我們知道,在國家起源的問題上,盧梭與霍布斯的解釋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他們二人都是絕對(duì)論者。不同的是,在17世紀(jì),霍布斯只能觀察或者說想像國家的起源,而看不到常態(tài)的現(xiàn)代社會(huì)治理過程,所以,對(duì)他來說,意志的形成是一個(gè)一次性的過程,在這之后就再也不會(huì)發(fā)生改變。到了盧梭的時(shí)代,國家至少在英國已經(jīng)變成了現(xiàn)實(shí),所以盧梭得以觀察到了霍布斯所無法預(yù)見的常態(tài)社會(huì)治理過程,特別是看到了以選舉和投票活動(dòng)為基本內(nèi)容的國家運(yùn)行過程。所以,盧梭發(fā)現(xiàn),在國家形成之后,公意實(shí)際上是通過投票而得到表達(dá)的,而在投票的時(shí)候,選民們所表達(dá)的既是一種意志,也是一種意見,當(dāng)這些意見匯集到一起的時(shí)候,就形成了一種輿論,這就是lopinion publique。也就是說,到盧梭的時(shí)代,公意或者說意志的抽象概念已經(jīng)獲得了非常確定的內(nèi)涵,也有了明確的形式,它就是lopinion publique,而在今天,這一范疇甚至已經(jīng)具體到可以通過數(shù)字——支持率——來進(jìn)行衡量了。需要注意的是,在盧梭這里,lopinion publique并不是公共輿論,而是充滿了分歧的,只能說是不同公眾們的意見,這種意見以輿論的形式而對(duì)國家的政策施展影響。但是,由于盧梭注意到了公眾輿論這一現(xiàn)象,也就從中發(fā)現(xiàn)了“公眾”,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盧梭是從輿論的視角出發(fā)發(fā)現(xiàn)了公眾,并對(duì)公眾作出了理論上的確認(rèn)。也許正是因?yàn)榭吹搅斯娂捌湓谡紊钪械妮浾摶顒?dòng),盧梭才在進(jìn)一步的思考中提出了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的概念,并把公意與公眾輿論區(qū)別開來,以表明公意更加純潔和可靠,而不像公眾輿論那樣只是不同公眾的輿論。
在盧梭之后,黑格爾也對(duì)公眾輿論給予了關(guān)注,但是,由于黑格爾掌握了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法,這使他能夠?qū)ΡR梭的公眾輿論加以提升,從而上升為公共輿論。黑格爾認(rèn)為,“開放這種認(rèn)識(shí)的機(jī)會(huì)具有更普遍的一面,即公共輿論初次達(dá)到真實(shí)的思想并洞悉國家及其事務(wù)的情況和概念,從而初次具有能力來對(duì)它們作出更合乎理性的判斷。此外,它又因而獲悉并學(xué)會(huì)尊重國家當(dāng)局和官吏的業(yè)務(wù)、才能、操行和技能。”②③④[德]黑格爾:《法哲學(xué)原理》,范揚(yáng)、張企泰譯,商務(wù)印書館,1979年,第331、331-332、332、334頁。根據(jù)黑格爾的意見,司法公開有利于增強(qiáng)公共輿論(ffentliche Meinung)的理性,從而增強(qiáng)其與國家互動(dòng)的有效性,所以,司法公開可以成為特殊性通向普遍性的一個(gè)工具。不僅如此,黑格爾還對(duì)公共輿論的起源進(jìn)行了探究,認(rèn)為公共輿論是基于個(gè)體的言論自由而生成的:“個(gè)人所享有的形式的主觀自由在于,對(duì)普遍事務(wù)具有他特有的判斷、意見和建議,并予以表達(dá)。這種自由,集合地表現(xiàn)為我們所稱的公共輿論。在其中,絕對(duì)的普遍物、實(shí)體性的東西和真實(shí)的東西,跟它們的對(duì)立物即多數(shù)人獨(dú)特的和特殊的意見相聯(lián)系。因此這種實(shí)存是經(jīng)常存在的自相矛盾,知識(shí)成為現(xiàn)象,不論本質(zhì)的東西和非本質(zhì)的東西一同直接存在著。”②這樣一來,盧梭的公眾在黑格爾這里就被看成是個(gè)體之間的一種偶然的或者說自由的聯(lián)系,而存在于公眾之中的公共則是個(gè)體之間的一種必然聯(lián)系。所以,公共輿論是個(gè)體以及作為個(gè)體的集合形態(tài)的公眾通向普遍性的中介,在指向國家制度的時(shí)候,也就同時(shí)賦予了國家制度以公共性。如果說在啟蒙時(shí)期存在著個(gè)體與公眾兩個(gè)不相融合的視角和立場(chǎng),那么,到了黑格爾這里,由于有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法,個(gè)體與公眾則在公共的概念中得到了統(tǒng)一。
根據(jù)黑格爾的定義,“公共輿論是人民表達(dá)他們意志和意見的無機(jī)方式。在國家中現(xiàn)實(shí)地肯定自己的東西當(dāng)然須用有機(jī)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國家制度中的各個(gè)部分就是這樣的。”③作為一種無機(jī)(unorganische)的存在,公共輿論是不能代表真理的,“因此,公共輿論又值得重視,又不值一顧。不值一顧的是它的具體意識(shí)和具體表達(dá),值得重視的是在那具體表達(dá)中只是隱隱約約地映現(xiàn)著的本質(zhì)基礎(chǔ)。既然公共輿論本身不具有區(qū)別的標(biāo)準(zhǔn),也沒有能力把其自身中實(shí)體性的東西提高到確定的知識(shí),所以脫離公共輿論而獨(dú)立乃是取得某種偉大的和合乎理性的成就(不論在現(xiàn)實(shí)生活或科學(xué)方面)的第一個(gè)形式上條件。這種成就可以保得住事后將為公共輿論所嘉納和承認(rèn),而變成公共輿論本身的一種成見。”④所以,對(duì)于社會(huì)治理而言,既需要重視公共輿論,又必須實(shí)現(xiàn)對(duì)公共輿論的超越,要努力剔除公共輿論之中的那些特殊性的和非理性內(nèi)容,讓其中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有益于國家制度。如果對(duì)盧梭和黑格爾進(jìn)行比較的話,我們發(fā)現(xiàn),當(dāng)盧梭把“公意”與“公眾輿論”區(qū)別開來的時(shí)候,所看到的是公眾輿論包含著褊狹意見的一面,認(rèn)為公意可以成為社會(huì)治理的可靠資源。但是,公意在社會(huì)治理過程中的可靠性是由什么決定的,盧梭是沒有解決這個(gè)問題的。黑格爾有所不同,他是運(yùn)用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法來處理這個(gè)問題的。當(dāng)黑格爾把盧梭的公眾輿論表述為公共輿論的時(shí)候,實(shí)際上已經(jīng)賦予了公共輿論雙重內(nèi)容,即認(rèn)為它既包含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其普遍性的一面正是合乎國家的需要的。由此看來,“公共”一詞正是在黑格爾這位辯證法大師的筆下才有了自己確定的內(nèi)容,盧梭的“公意”也只有在黑格爾確認(rèn)了公共一詞的準(zhǔn)確含義之后,才能被解讀成“公共意志”或“公共意見”,而在盧梭那里,還是一個(gè)非常模糊的概念。
與黑格爾有所不同,在英國的思想家那里,并沒有把公眾提升為公共。這一點(diǎn)在密爾那里表現(xiàn)得尤為清晰。密爾在《論自由》中這樣寫到:“說句清醒的真話,不論對(duì)于實(shí)在的或設(shè)想的精神優(yōu)異性怎樣宣稱崇敬甚至實(shí)際予以崇敬,現(xiàn)在遍世界中事物的一般趨勢(shì)是把平凡性造成人類間占上風(fēng)的勢(shì)力。在古代歷史里,在中世紀(jì)間,以及以逐漸減弱的程度在由封建社會(huì)到當(dāng)前時(shí)代的漫長過渡中,個(gè)人自身就是一個(gè)勢(shì)力;如果他具有宏大的才智或者具有崇高的社會(huì)地位,他就更是一個(gè)可觀的勢(shì)力。到現(xiàn)在,個(gè)人卻消失在人群之中了。在政治中,若還說什么公眾意見現(xiàn)在統(tǒng)治著世界,那幾乎是多余的廢話了。唯一實(shí)稱其名的勢(shì)力,只是群眾的勢(shì)力,或者是作為表達(dá)群眾傾向或群眾本能的機(jī)關(guān)的政府的勢(shì)力。這一點(diǎn),在私人生活方面的道德關(guān)系及社會(huì)關(guān)系中和在公眾事務(wù)中是一樣真實(shí)的。有些人,其意見假公眾意見之名而行,卻并非總是同一類的公眾:在美國,他們所謂公眾只是全體白人;在英國,主要是中等階級(jí)。但他們卻永是一群,也就是說,永是集體的平凡的人們。”③[英]密爾:《論自由》,許寶骙譯,商務(wù)印書館,1998年,第77-78、99-100頁。密爾的著述是要為個(gè)體的人進(jìn)行辯護(hù),所以,他為個(gè)體的人所找到的對(duì)立面也就是公眾。因而,在密爾眼中,公眾輿論成為了實(shí)際的統(tǒng)治者,并對(duì)個(gè)體的自由造成了嚴(yán)重侵害。“近代公眾輿論的架構(gòu)實(shí)在等于中國那種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只不過后者采取了有組織的形式而前者采取了無組織的形式罷了。除非個(gè)性能夠成功地肯定自己,反對(duì)這個(gè)束縛,否則,歐洲縱然有其高貴的先祖和它所宣奉的基督精神,也將趨于變成另一個(gè)中國。”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Liberty;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10, p. 129.為了避免這種狀況的出現(xiàn),密爾極力反對(duì)公眾對(duì)個(gè)體的人的任何干預(yù):“在反對(duì)公眾干涉私人行為的一切論據(jù)當(dāng)中還有最有力的一點(diǎn),那就是說,如果公眾真去干涉,多數(shù)的情況是它作了錯(cuò)的干涉,干涉錯(cuò)了地方。在社會(huì)道德的問題上,在對(duì)他人的義務(wù)的問題上,公眾的意見也即壓制的多數(shù)的意見雖然常常會(huì)錯(cuò),大概更常常會(huì)是對(duì)的;因?yàn)樵谶@類問題上他們只需要判斷他們自己的利害,只需要判斷某種行為如任其實(shí)行出來將會(huì)怎樣影響到自己。但是在只關(guān)個(gè)人自身的行為的問題上,若把一個(gè)同樣多數(shù)的意見作為法律強(qiáng)加于少數(shù),會(huì)對(duì)會(huì)錯(cuò)大概各居一半;因?yàn)樵谶@類情事上,所謂公眾的意見至好也不過是某些人關(guān)于他人的善惡禍福的意見;甚至往往連這個(gè)都不是,而不過是公眾以完完全全的漠不關(guān)心掠過他們所非難的對(duì)象的快樂或便利而去考慮他們自己歡喜怎樣和不歡喜怎樣罷了。”③至此,可以看到,曾經(jīng)在霍布斯與盧梭那里被視為自由象征的公眾到了密爾的筆下卻變成了壓迫自由的公眾。
對(duì)于近代早期的社會(huì)變革而言,公眾的產(chǎn)生是最為重要的歷史事件,甚至可以說,整個(gè)現(xiàn)代史就是由公眾來書寫和推動(dòng)的。正是公眾通過輿論而進(jìn)行的自由探討,才使人類關(guān)于社會(huì)革命的走向獲得了一種明確的理論方案;也正是公眾通過輿論而對(duì)國家施予的巨大壓力,才使這場(chǎng)革命沒有變異為新興統(tǒng)治者的殘暴統(tǒng)治,而是帶來了民主制度的確立。在某種意義上,所有流傳下來的啟蒙著作以及其他無法計(jì)數(shù)的被遺忘了的小冊(cè)子,都是公眾輿論的一部分,因而,沒有公眾輿論,就不會(huì)有思想啟蒙,更不會(huì)有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的偉大成就。可以說,正是公眾輿論為個(gè)體爭(zhēng)得了自由。當(dāng)然,密爾的感受也是真切的,公眾輿論的確存在著壓制個(gè)體自由的問題。正是由于公眾輿論具有這種兩面性,致使啟蒙早期的思想家們有意忽略了公眾輿論,只是因?yàn)楣娂捌漭浾摰某砷L逐漸顯示出了其在社會(huì)治理過程中的力量時(shí),才使思想家們不得不對(duì)這一現(xiàn)象發(fā)表意見。隨著公眾進(jìn)入了啟蒙思想家們的視野,新世界的輪廓也就變得清晰了。具體地說,在近代之前的社會(huì)中,既沒有個(gè)體也沒有公眾,那是一個(gè)消融了個(gè)體和公眾的同質(zhì)性共同體,而在啟蒙思想家們所生活的世界中,個(gè)體與公眾相伴而生,并在其成長中為近代以來的國家及其社會(huì)治理體系的建構(gòu)提供了各種所需要的材料。當(dāng)然,在英法的啟蒙思想家那里,所感受到的和加以描述的都還是客觀事實(shí),并在這種事實(shí)的基礎(chǔ)上去提出國家及其社會(huì)治理體系建構(gòu)的方案,一旦這些事實(shí)進(jìn)入了德國哲學(xué)的視野,則通過抽象的方式來加以重新描述,結(jié)果,在個(gè)體與公眾之中發(fā)現(xiàn)了一種普遍性的因素,從而建構(gòu)起“公共”的概念。雖然公共的概念是在思維抽象中獲得的,但是,卻反過來對(duì)國家及其社會(huì)治理體系的建構(gòu)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在某種意義上,不僅是因?yàn)楣驳母拍顐鞑サ搅嗣绹a(chǎn)生了公共行政學(xué)這門科學(xué),而且,在公共行政實(shí)踐的每一新的進(jìn)展中,我們也同樣看到“公共”概念在發(fā)揮著向?qū)У淖饔谩?/p>
中國的改革開放并不是西方近代以來的這段歷史的復(fù)制,而是建設(shè)有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的偉大創(chuàng)舉。但是,近代以來的這段歷史將會(huì)在中國社會(huì)發(fā)展的道路上被壓縮到一個(gè)極其短暫的時(shí)間段中,這卻是一個(gè)無可爭(zhēng)議的事實(shí)。當(dāng)中國經(jīng)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在政治生活以及整個(gè)社會(huì)治理過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個(gè)體的人已經(jīng)成熟起來,有了自我意識(shí);公眾也是我們必須接受的現(xiàn)實(shí),頻繁發(fā)生的意味著公眾處于一種無序的狀態(tài),沒有得到必要的規(guī)范和引導(dǎo)。最為重要的是,公共的價(jià)值被寄托在了政府身上,而政府卻并沒有公共的觀念,所以,不能將公共行政轉(zhuǎn)化為有效維護(hù)社會(huì)公平正義的行動(dòng)。我們回顧近代以來公共概念的思想歷程,正是因?yàn)辄h十之后的中國社會(huì)可以用個(gè)體、公眾和公共這三個(gè)關(guān)鍵詞來加以描繪,這是我們開展社會(huì)治理和建構(gòu)和諧社會(huì)時(shí)須臾不能忘記的三個(gè)維度,特別是政府,在選擇和確認(rèn)一切社會(huì)治理事項(xiàng)時(shí),都必須以平衡這三維度為行動(dòng)的前提。
第7篇: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重要性范文
關(guān)鍵詞:文化翻譯;文化翻譯理論;翻譯技巧
一、序言
21世紀(jì)可以說是文化的時(shí)代,文化在現(xiàn)代人生活中占據(jù)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譯不再僅僅是語言之間的轉(zhuǎn)換,而且是涉及到文化層面的復(fù)雜情況。但是,即使在@樣的背景下,我們接觸原本的機(jī)會(huì)很少,大多數(shù)是通過翻譯來實(shí)現(xiàn),在這種情況下,翻譯的正確與否就顯得尤為重要,文化要素的傳達(dá)也被擺在重要的位置,因此,如何準(zhǔn)確進(jìn)行韓中翻譯,尤其是文化翻譯成為翻譯人員的重要課題。
中國和韓國因意識(shí)形態(tài)不同,在語言和文化方面存在很多差異,作為一名翻譯人員,要認(rèn)識(shí)到這種差異,并且研究解決方案。因此,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找出韓中文化翻譯的理論,減少或避免翻譯時(shí)因?qū)n國文化認(rèn)知的缺失導(dǎo)致的誤譯和誤會(huì)。
二、文化翻譯理論
巴斯奈特在《翻譯、歷史和文化》一書中提出了如下文化翻譯觀點(diǎn):第一,翻譯的單位應(yīng)該是文化而不是傳統(tǒng)的詞、句子、段落或是語篇;第二,翻譯并非單純的語言之間的轉(zhuǎn)換,實(shí)質(zhì)上是文化交流;第三,翻譯應(yīng)走出語義等值的局限,實(shí)現(xiàn)文化中的功能等值;第四,翻譯的原則和規(guī)范也是不斷變化的,翻譯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不同的需要。[1]巴斯奈特強(qiáng)調(diào)了文化翻譯的重要性,翻譯人員在翻譯時(shí)要充分考慮文化信息的翻譯和傳達(dá)。
Stolze強(qiáng)調(diào)了翻譯時(shí)文化差異的重要性,認(rèn)為這一觀點(diǎn)從哲學(xué)角度分析也是正確的,翻譯受目的影響,如果不與技能主義相關(guān)聯(lián),那么翻譯就不可能實(shí)現(xiàn)。
三、文化翻譯分析
本論文通過觀察韓國人的日常生活,選取反映韓國社會(huì)現(xiàn)象的“文化現(xiàn)象”,并將這些內(nèi)容按照相對(duì)應(yīng)的翻譯理論進(jìn)行了翻譯及分析。
(一)漢字詞的翻譯。
漢字詞在韓國語中所占比重最大,在翻譯時(shí)看似簡單,但因其與現(xiàn)代漢語詞匯不完全對(duì)應(yīng),出現(xiàn)錯(cuò)誤的概率也很大。中國與韓國同屬東亞文化圈,在文化翻譯時(shí),會(huì)遇到很多漢字詞,因此,漢字詞的翻譯應(yīng)引起足夠重視。
1.同型同義詞的翻譯。
同型同義詞指的是韓語中的漢字詞和漢語表達(dá)完全對(duì)應(yīng)的詞,適用于漢字詞與現(xiàn)代漢語意思完全對(duì)應(yīng)的情況。
[原文] ?????? ??.??.????? ?? ???? ? ??, ? ??, ? ??? ?????? ??? ???? ????? ? ? ??.
[譯文] 新村運(yùn)動(dòng)以勤勉、自助、合作為基本準(zhǔn)則,是由一個(gè)共同體(如一個(gè)村莊、一個(gè)地區(qū)、一個(gè)國家等)發(fā)起的一場(chǎng)以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為目標(biāo)的運(yùn)動(dòng)。
主席在各種會(huì)議和論壇上都提過“共同體”,因此,這種中韓表達(dá)完全一致的詞語就可以采用直譯的方法翻譯。
2.同型異義詞的翻譯。
[原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霍夫斯泰德把這種儒教價(jià)值觀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關(guān)系分析為: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復(fù)興的亞洲國家雖然對(duì)傳統(tǒng)有強(qiáng)烈的信念,但也不受傳統(tǒng)束縛,具有很大的靈活性。
“柔軟性”在現(xiàn)代韓語中的意思為“較軟,不堅(jiān)硬”,分析原文,這里的“柔軟性”指的是韓國人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過程中不拘泥于傳統(tǒng),審時(shí)度勢(shì),最終實(shí)現(xiàn)了經(jīng)濟(jì)復(fù)興,根據(jù)“等價(jià)理論”分析,此處翻譯成意為“思想、行為等具有融通性”的“靈活性”一詞最為恰切。
(二)添加與省略。
[原文] ????? ‘?? ????’? ?? ??? ?? ??? ?????? ?? ??? ?? ???? ?? ‘??? ??’? ???? ??.
[???] 在韓國,為了照顧因“教育遷徙”去國外的子女,媽媽隨孩子出去,只留下“大雁爸爸”孤獨(dú)一人的家庭急劇增多。(“大雁老爸”是韓國近年來的流行詞,意思是小孩去國外上學(xué),老婆陪讀,丈夫留在國內(nèi)掙錢,這個(gè)詞語頗有種“做男人不容易”的意味)
“大雁爸爸”是韓國一種特殊的社會(huì)文化現(xiàn)象,在沒有相關(guān)共同文化背景的情況下,需要對(duì)相關(guān)的文化現(xiàn)象添加注釋,以方便翻譯目標(biāo)讀者的理解。
(三)文化固有詞的翻譯。中韓兩國雖同屬儒教文化圈,但因民族文化存在差別,思考方式、文化心理等方面都有很多不同,因此,要重視文化翻譯時(shí)因文化差異導(dǎo)致的交流障礙。
1.異化翻譯法。異化翻譯法目的是保留原文中的異國情調(diào),讓目標(biāo)讀者向原文靠近,為了保護(hù)原文化的整體性。具體示例如下:
[原文] ????? ??? ? ?? ??? ??? 30??? ??? ?? ??? ??? ??? ??? ???? ????? ?? ??? ?? ?? ?? ????.
[譯文] 平時(shí)行駛一個(gè)小時(shí)的距離,“子彈出租車”(形容車速度很快)可以加速到在30分鐘走完,雖然這樣能節(jié)約時(shí)間和費(fèi)用,但卻是很容易出現(xiàn)事故的駕駛習(xí)慣。
????? ‘????’? ??? ??? ?? “飛車”?? ??? ??? “子彈出租車” ?? ??? ???? ?? ??? ???? ??? ??????? ??? ???? ???? ? ????.
在漢語中,與“子彈出租車”意思相近的詞是“飛車”,用子彈來形容出租車速度之快具有很強(qiáng)的韓國文化特點(diǎn),因此,此處采取異化翻譯法能夠讓讀者更好地理解韓國文化。
2.歸化翻譯法。歸化翻譯法旨在盡量減少譯文中的異國情調(diào)為目的語讀者提供一種自然流暢的譯文,適用于當(dāng)太過趨向原文的翻譯使讀者產(chǎn)生理解障礙時(shí)使用。
[原文] ??? ??? ???? ????? ??? ???? ?? ??? ???? ??? ???? ???? ??? ???? ???.
[譯文] 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西方近代化的副作用也導(dǎo)致了韓國傳統(tǒng)價(jià)值文化的消失和文化特征的弱化。
‘??? ???’對(duì)應(yīng)的漢字是“文化正體性”,但是在現(xiàn)代漢語中沒有類似的表達(dá),韓語國語辭典中對(duì)‘??? ???’的解釋是是指一個(gè)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這種情況下,需要根據(jù)規(guī)劃翻譯法將原文翻譯成易于目標(biāo)讀者理解的詞。
四、結(jié)論
在全球化時(shí)代背景下,如果文化翻譯出現(xiàn)錯(cuò)誤,會(huì)產(chǎn)生交流障礙,甚至可能會(huì)對(duì)兩國文化交流產(chǎn)生不利影響。因此,翻譯人員應(yīng)準(zhǔn)確把握翻譯文化圈的規(guī)則和慣例,對(duì)不同的環(huán)境使用何種翻譯方法做出正確的判斷。
在進(jìn)行文化翻譯時(shí),需要對(duì)翻譯規(guī)模、意識(shí)形態(tài)、文化特征等各方面進(jìn)行綜合考慮,翻譯人員也應(yīng)加強(qiáng)對(duì)翻譯對(duì)象國文化的學(xué)習(xí)和理解,從而減少翻譯時(shí)出現(xiàn)的誤譯和錯(cuò)誤。
參考文獻(xiàn)
[1]趙莉、何大順,《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譯觀》,《文學(xué)教育》,2009.06。
[2]馬漢蓉《中韓翻譯與文化》 《經(jīng)濟(jì)管理者》 2015.04上期。
[3]李民、宋立,《韓漢翻譯研究》,2014.07。
第8篇: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重要性范文
[關(guān)鍵詞]學(xué)習(xí);學(xué)習(xí)科學(xué);方法論;發(fā)展趨勢(shì)
[中圖分類號(hào)]G420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672―0008(2012)01―0026一11
一、前言
20世紀(jì)中葉,探究人類感知、思維信息處理過程及心智工作機(jī)制的認(rèn)知科學(xué),成為引起全世界科學(xué)家廣泛關(guān)注的新興研究門類,隨著計(jì)算機(jī)技術(shù)的發(fā)展,在70至80年代,為了更好地促進(jìn)人類的學(xué)習(xí),不少認(rèn)知科學(xué)領(lǐng)域的研究者開始利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設(shè)計(jì)開發(fā)學(xué)習(xí)軟件,并發(fā)起“人工智能與教育”大會(huì)。1978年,美國西北大學(xué)特聘請(qǐng)關(guān)注這一領(lǐng)域的耶魯大學(xué)的尚克(Roger C.Sehank)成立學(xué)習(xí)科學(xué)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the Learning Science,ILS),此時(shí),學(xué)習(xí)與技術(shù)的研究日漸深入。1991年1月,由尚克、柯林斯(Allan Collins)和奧托尼(Onony)等學(xué)者發(fā)起,《學(xué)習(xí)科學(xué)期刊》(the Journal《kamin Science)創(chuàng)刊,同年在西北大學(xué)的學(xué)習(xí)科學(xué)研究所召開了被尚克稱為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第一次國際會(huì)議Ⅲ,至此,經(jīng)過不斷醞釀的學(xué)習(xí)科學(xué)正式誕生了。2002年,國際學(xué)習(xí)科學(xué)協(xié)會(huì)(ISLS)創(chuàng)辦,使得學(xué)習(xí)科學(xué)這一學(xué)術(shù)共同體日趨成熟,國內(nèi)一些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研究機(jī)構(gòu)紛紛成立。
而今,伴隨著腦科學(xué)研究的深入進(jìn)展,特別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腦磁圖(MEG)、正電子發(fā)射斷層掃描fPET)等多種無創(chuàng)傷腦研究技術(shù)的問世,研究者可以對(duì)人腦高級(jí)功能進(jìn)行諸多實(shí)證性的研究,不斷揭示著大腦的學(xué)習(xí)機(jī)制,這促使人類對(duì)學(xué)習(xí)是如何發(fā)生的追問從猜想走向科學(xué)。
索耶(Keith Sawyer,2006)在《劍橋?qū)W習(xí)科學(xué)手冊(cè)》的序言中做出如下界定:“學(xué)習(xí)科學(xué)是一個(gè)研究教與學(xué)的跨學(xué)科領(lǐng)域,學(xué)習(xí)科學(xué)家研究多種場(chǎng)景中的學(xué)習(xí),不僅包括學(xué)校課堂中的正式學(xué)習(xí),也包括發(fā)生在家庭中、工作中和同伴間的非正式學(xué)習(xí)”,而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目標(biāo)則是“更好地理解學(xué)習(xí)的認(rèn)知,過程和社會(huì)化過程以產(chǎn)生更有效的學(xué)習(xí),并運(yùn)用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知識(shí)來重新設(shè)計(jì)課堂和其他學(xué)習(xí)環(huán)境,從而使學(xué)習(xí)者進(jìn)行深層學(xué)習(xí)”。本文就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緣起、發(fā)展、研究領(lǐng)域的重要問題及其方法論進(jìn)行探討。
二、“跨學(xué)科”的學(xué)習(xí)科學(xué)
20世紀(jì)40年代以來,科學(xué)的不斷分化被看做是科學(xué)發(fā)展綜合化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原有學(xué)科的鄰接區(qū)域紛紛成為新學(xué)科的生長點(diǎn),早期的學(xué)習(xí)科學(xué)與認(rèn)知科學(xué)息息相關(guān),或者如達(dá)菲(TDuffy,2004)所說的“是認(rèn)知科學(xué)的一部分”。然而,傳統(tǒng)的認(rèn)知科學(xué)所崇尚的事實(shí)規(guī)律,總是將人們身處的社會(huì)和自然情境抽離出去的結(jié)果,對(duì)當(dāng)時(shí)認(rèn)知科學(xué)狹隘視域進(jìn)行批判的一些研究者,逐漸成為后來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奠基人。
實(shí)際上。關(guān)于人類學(xué)習(xí)能力相關(guān)的研究涉及一個(gè)包括生物學(xué)、心理和社會(huì)學(xué)等機(jī)制在內(nèi)的寬廣頻譜,學(xué)習(xí)科學(xué)關(guān)注真實(shí)世界里的認(rèn)知,知識(shí)的理解和創(chuàng)新逐漸成為其研究重心,為此,“它吸收了有關(guān)人的科學(xué)的多種理論視野和研究范式,以便弄清學(xué)習(xí)、認(rèn)知和發(fā)展的本質(zhì)及其條件”,它涉及有關(guān)學(xué)習(xí)的科學(xué)(The Scienceso0fLearning)的不同領(lǐng)域,如認(rèn)知科學(xué)、神經(jīng)科學(xué)、腦科學(xué)、教育學(xué)、教育心理學(xué)、信息科學(xué)、計(jì)算機(jī)科學(xué)、人類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等,從多學(xué)科領(lǐng)域吸收成果并綜合了許多學(xué)科的方法,逐漸形成一個(gè)新的相對(duì)獨(dú)立的跨學(xué)科的研究領(lǐng)域,
最值得一提的是,眾多研究者對(duì)于將認(rèn)知神經(jīng)科學(xué)納入學(xué)習(xí)科學(xué)。有著較為一致的共識(shí),因?yàn)椋墒斓膶W(xué)習(xí)科學(xué)不僅要關(guān)注學(xué)習(xí)的發(fā)生,還應(yīng)了解學(xué)習(xí)為何發(fā)生,怎樣發(fā)生:而神經(jīng)科學(xué)的研究揭示了人類學(xué)習(xí)的內(nèi)在機(jī)制和生理基礎(chǔ),來自腦科學(xué)的微妙、靈敏的技術(shù)手段及與行為數(shù)據(jù)的結(jié)合還可能對(duì)理解學(xué)習(xí)的個(gè)體差異提供幫助(Gopnik。Meltzoff&Kuhl,1999)。
國際上,經(jīng)濟(jì)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啟動(dòng)了“學(xué)習(xí)科學(xué)與腦科學(xué)研究”項(xiàng)目(1999-2008),該項(xiàng)目召集了26個(gè)國家的相關(guān)研究者,在教育神經(jīng)科學(xué)的研究領(lǐng)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與此同時(shí),一些國家的學(xué)術(shù)組織也舉辦了相關(guān)論壇,如2000年美國的紐約論壇(主題為“大腦機(jī)制和早期學(xué)習(xí)”)、2001年西班牙的Granada論壇(主題為“大腦機(jī)制和青少年的學(xué)習(xí)”)、2001年日本的東京論壇(主題為“大腦機(jī)制和終身學(xué)習(xí)”)、2003年德國的烏爾姆大學(xué)論壇(主題為“情緒和學(xué)習(xí)”)等。世界一些著名大學(xué)也紛紛建立起跨學(xué)科、跨領(lǐng)域的認(rèn)知神經(jīng)科學(xué)研究機(jī)構(gòu),作為學(xué)習(xí)科學(xué)研究重要基礎(chǔ)的腦科學(xué)及認(rèn)知神經(jīng)科學(xué)的不斷發(fā)展,更新著對(duì)學(xué)習(xí)過程及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激發(fā)著學(xué)習(xí)科學(xué)領(lǐng)域中更有價(jià)值的研究和探索。
三、學(xué)習(xí)科學(xué)研究的重要問題
自上世紀(jì)90年代開始至今,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研究發(fā)展迅速,涉及人類學(xué)習(xí)的諸多方面,盡管學(xué)習(xí)科學(xué)成為一個(gè)日臻成熟的獨(dú)立的學(xué)科領(lǐng)域,但其研究領(lǐng)域的輪廓并不清晰,筆者認(rèn)為很有必要對(duì)其研究的重要問題進(jìn)行探討和闡述。
(一)知識(shí)的本質(zhì)
一般認(rèn)為,本質(zhì)即隱藏于事物背后的絕對(duì)不變的性質(zhì)、結(jié)構(gòu)與形式,被認(rèn)為是通過理性而得到的對(duì)事物的正確認(rèn)識(shí),因此,獨(dú)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觀知識(shí)也就具有普適性。知識(shí)的本質(zhì)觀對(duì)教與學(xué)有著長久的影響,也深刻影響著人們對(duì)知識(shí)價(jià)值和知識(shí)習(xí)得的看法。20世紀(jì)60年代以來,隨著后現(xiàn)代主義(尤其是反本質(zhì)主義知識(shí)本質(zhì)觀)對(duì)知識(shí)本質(zhì)主義的批判與解構(gòu),人們開始重新審視知識(shí)的本質(zhì),并且形成了一系列帶有濃厚后現(xiàn)代主義色彩的知識(shí)本質(zhì)觀。盡管人類對(duì)知識(shí)的探究總是在逐步地趨向某個(gè)“本質(zhì)”或“真理”,現(xiàn)代復(fù)雜性科學(xué)認(rèn)為。事物本身就是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統(tǒng)一體。這種不確定性也就決定了人類認(rèn)識(shí)事物的有限性、暫時(shí)性和不確定性(石健壯,2010)。同時(shí),人類的實(shí)踐及其創(chuàng)造的世界卻是不斷變化著、生成著的,生成性便是知識(shí)的基本屬性。
作為理性認(rèn)識(shí)結(jié)果的知識(shí)是人們對(duì)客觀世界的一種解釋,如果過分地強(qiáng)調(diào)知識(shí)的絕對(duì)性,會(huì)導(dǎo)致人們對(duì)客觀世界的誤讀,從而導(dǎo)致僵化的認(rèn)識(shí)和理解客觀世界的模式。后現(xiàn)代主義因此在對(duì)本質(zhì)主義的批判與解構(gòu)中逐漸壯大,確立知識(shí)本質(zhì)的多樣性、差異性以及不確定性。因此,知識(shí)在本質(zhì)上是對(duì)事物認(rèn)識(shí)的一種簡約化,是對(duì)客觀事物復(fù)雜性的一種理解與闡釋而學(xué)習(xí)科學(xué)關(guān)注知識(shí)的復(fù)雜性、情境性和社會(huì)性,
能夠幫助學(xué)習(xí)者在恰當(dāng)?shù)那榫持兄鸩嚼斫獠?shí)現(xiàn)對(duì)知識(shí)的完整建構(gòu),并不斷地探究問題情境隱含的深層知識(shí),得以解決復(fù)雜的實(shí)際問題。
當(dāng)人類社會(huì)經(jīng)由工業(yè)化社會(huì)、信息社會(huì)向知識(shí)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時(shí)候,強(qiáng)調(diào)知識(shí)的建構(gòu)性、社會(huì)性、情境性、復(fù)雜性和默會(huì)性等知識(shí)觀,成為創(chuàng)造知識(shí)生產(chǎn)和運(yùn)用新范式的主要?jiǎng)右颍耠S著自然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發(fā)展的日益深化,不斷沖擊著傳統(tǒng)的知識(shí)觀,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rèn)為,知識(shí)是人類在實(shí)踐的基礎(chǔ)上對(duì)無限發(fā)展著的客觀世界的動(dòng)態(tài)認(rèn)識(shí),是基于客觀世界的主觀構(gòu)建,是動(dòng)態(tài)發(fā)展的、開放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呈現(xiàn)出相對(duì)性、不確定性、動(dòng)態(tài)開放性、情境性、多樣性與差異性等特征,而日常生活的多樣化世界是文化和歷史中各種差異性和偶然性的基礎(chǔ),對(duì)現(xiàn)象學(xué)家而言,“世界的知識(shí)需要有作為世界的認(rèn)知者的自我(self-as-knower-of-the-world)的知識(shí)。
因此,有效的學(xué)習(xí)應(yīng)該關(guān)注在自然情境下學(xué)習(xí)者個(gè)體的認(rèn)知積儲(chǔ)過程,扎根于社會(huì)文化境脈,探究個(gè)體的、社會(huì)的認(rèn)知過程。在一系列的社會(huì)共同體內(nèi)存在的多樣性絕不僅僅是學(xué)習(xí)者學(xué)習(xí)的調(diào)為劑,由此而產(chǎn)生的差異更是深入學(xué)習(xí)的重要資源,在特定情境下的社會(huì)交互,尤其是隱含個(gè)體經(jīng)驗(yàn)的案例呈現(xiàn),使得緘默知識(shí)可視化,一定程度上促進(jìn)學(xué)習(xí)者之間的相互學(xué)習(xí)。
20世紀(jì)上半葉,哲學(xué)家們通常認(rèn)為科學(xué)知識(shí)來自于對(duì)世界的表述和應(yīng)用這些表述的邏輯操作(邏輯實(shí)證主義觀),而當(dāng)時(shí)行為主義支配下的學(xué)校教育以教授主義的方法實(shí)施教學(xué),即向?qū)W生傳播(“灌輸”)事實(shí)和程序。自20世紀(jì)60年代開始,一些人類學(xué)家、社會(huì)學(xué)家、心理學(xué)家開始研究科學(xué)家是如何工作的,他們逐漸發(fā)現(xiàn),科學(xué)知識(shí)并非簡單的對(duì)世界的表述及相關(guān)的邏輯操作,而是包括科學(xué)研究的方法和深層知識(shí)的模型,并且兩者通過解釋原理(explanatoi~DrinciDles)連接為一個(gè)整體性概念框架。他們認(rèn)可科學(xué)知識(shí)情境性、實(shí)踐性的特征,并強(qiáng)調(diào)協(xié)作在科學(xué)知識(shí)產(chǎn)生的重要性。因此,他們認(rèn)為傳統(tǒng)教室內(nèi)的教學(xué)無視科學(xué)知識(shí)的這些性質(zhì)。
傳統(tǒng)的學(xué)校教育以為學(xué)生提供顯性的確定的客觀知識(shí)為主,將考核的標(biāo)準(zhǔn)也界定為對(duì)這些客觀知識(shí)的保持和記憶的程度,但知識(shí)畢竟是有情境性的,杜威把知識(shí)界定為“通過操作把一個(gè)有問題的情境改變成一個(gè)解決了問題的情境的結(jié)果”。波蘭尼也在《隱性之維》(the Tacit 0f Dimension)一書中,探討知識(shí)不可言傳的另一特性,賦予知識(shí)的個(gè)人色彩和情境性,這都意味著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生在知識(shí)學(xué)習(xí)中親歷體驗(yàn)、探究的重要性,知識(shí)的“隱性之維”提醒我們,需要引導(dǎo)學(xué)生在不確定性的情境中探究某些確定性的結(jié)果。
不僅僅是學(xué)生,社會(huì)的從業(yè)者包括專家也需要不斷地學(xué)習(xí)新知識(shí),這些知識(shí)通常能夠幫助人們快速地在新情境中解決問題,筆者在此想強(qiáng)調(diào)的是適應(yīng)型專家知識(shí)(adaptive ex.oertise.有學(xué)者譯為“適應(yīng)性專長”),即支持持續(xù)學(xué)習(xí)、即興創(chuàng)作和自主擴(kuò)充的專業(yè)知識(shí)。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研究發(fā)現(xiàn),專家會(huì)注意到情境或問題的特征,而這常被新手所忽略。伯利納(Berliner.2001)已經(jīng)證實(shí)新手教師和專家教師在注意力上存在巨大的差異,而這又影響他們快速識(shí)別問題與時(shí)機(jī),并做出回應(yīng)的能力。對(duì)于“適應(yīng)性專長”的關(guān)注,成為2005年4月在加拿大舉辦的美國教育研究協(xié)會(huì)(AERA)年會(huì)的重要議題,研究者們將通過常規(guī)專家(routine expert)與適應(yīng)性專家的對(duì)比來界定適應(yīng)性專長,并大多聚焦在概念性理解、對(duì)新情境(問題,任務(wù))的反應(yīng)、對(duì)已知與未知的反應(yīng)、彈性或適應(yīng)性改變、革新或發(fā)明與創(chuàng)造、作為學(xué)習(xí)者的身份意識(shí)和信念、元認(rèn)知等多元維度,而以適應(yīng)性專長作為目標(biāo)的學(xué)習(xí)對(duì)知識(shí)的獲取與應(yīng)用有著不同于常規(guī)專長的理解。
(二)學(xué)習(xí)的實(shí)質(zhì)
1.真的學(xué)會(huì)了嗎
在課堂中,有些教師經(jīng)常感到迷茫,該講得都講了,該解釋的都解釋了,為什么學(xué)生還是不明白?為什么對(duì)一些司空見慣的“常識(shí)”學(xué)生們就是不能理解和應(yīng)用?在現(xiàn)實(shí)的教學(xué)中,教師與學(xué)生之間確實(shí)存在著理解的“鴻溝”,這一鴻溝經(jīng)常使得教師與學(xué)生的知識(shí)(觀念)難以共享。因此,教育者經(jīng)常面對(duì)一個(gè)困惑的現(xiàn)象就是:盡管教師們用心良苦地為了學(xué)生而授業(yè)解惑,但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效果卻往往與教師的期望有著明顯的差距。如,王光明(2005)的調(diào)查表明,我國基礎(chǔ)教育階段的師生對(duì)于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投入了很大精力,但對(duì)知識(shí)的理解水平遠(yuǎn)未達(dá)到深刻理解,多數(shù)學(xué)生對(duì)帶有識(shí)記性與操作步驟的問題解答表現(xiàn)較好,但在陌生的問題情境中卻常常不會(huì)應(yīng)用數(shù)學(xué)知識(shí),未能達(dá)到遷移性理解,意味著沒有真的學(xué)會(huì)。
沒有理解就沒有真正的學(xué)習(xí)。諸多的研究者認(rèn)為,面向理解的認(rèn)知發(fā)展的特點(diǎn)是概念轉(zhuǎn)變(Concepfion Change),即學(xué)習(xí)者掌握知識(shí)(或概念)的過程中,主要的是在原有知識(shí)(概念)的基礎(chǔ)上的發(fā)展或轉(zhuǎn)變,而非簡單的信息增疊。概念是異于個(gè)體的特殊主觀性中的共同因素,是反映在主觀性中的事物的客觀普遍性。概念轉(zhuǎn)變的意義,在于引發(fā)深層學(xué)習(xí),為知識(shí)的有效理解和遷移準(zhǔn)備了條件。杜威(John Dewey,1936)特別強(qiáng)調(diào)概念在人的理解過程中的作用,他認(rèn)為,首先,概念使我們能夠類化,使我們能夠把對(duì)某一事物的理解轉(zhuǎn)移于對(duì)其他事物的認(rèn)識(shí):其次,概念使知識(shí)標(biāo)準(zhǔn)化,它使流動(dòng)的化為凝固,易移的化為永恒;再次,概念幫助我們認(rèn)識(shí)未知、補(bǔ)充所知。
2.迷思概念
概念是構(gòu)成知識(shí)最基本的成分,也是科學(xué)思維的網(wǎng)結(jié),概念的獲得和理解是學(xué)習(xí)科學(xué)重要的關(guān)注點(diǎn)之一。學(xué)習(xí)科學(xué)研究的一項(xiàng)重要發(fā)現(xiàn)就是:學(xué)是在原有知識(shí)背景下發(fā)生的,進(jìn)入課堂的學(xué)生總是帶著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各種各樣的半成型的觀點(diǎn)或者前概念(Preconception) (有時(shí)被稱為“樸素科學(xué)”、“孩童的科學(xué)”),而課堂里“教師的科學(xué)”,是教師借由“課程的科學(xué)”轉(zhuǎn)化成包含自我理解的意義,盡管兒童的前概念未必都是錯(cuò)誤的,但往往是片面、模糊甚至是與科學(xué)概念對(duì)立的。在學(xué)習(xí)新知識(shí)時(shí),不少學(xué)生只注意到自己所理解的部分,所以,即便在學(xué)習(xí)后,學(xué)生通常不會(huì)放棄原有的概念(觀念),而是對(duì)新概念加以排斥,甚至扭曲對(duì)新概念的理解。這些在學(xué)生頭腦中存在的與科學(xué)概念不一致的認(rèn)識(shí),稱為“迷思概念(Misconception)”或“相異概念(Alter-nati’ve Conception)”。
相關(guān)的研究(Gilbert et a1.1982)證明,通常的課堂教學(xué)后,學(xué)生并未真正獲得對(duì)科學(xué)概念的理解,原因是他們習(xí)慣。性地將課堂中的知識(shí)與原有知識(shí)(概念)隔離,學(xué)習(xí)之后,他們?nèi)詴?huì)在真實(shí)的世界中應(yīng)用原有的知識(shí),而教師教授的知識(shí)則只用于學(xué)校的課堂中;或者學(xué)生獲得了對(duì)科學(xué)概念有限的認(rèn)知,卻不能達(dá)到有效的理解和內(nèi)化,因而,形成孩童的科學(xué)與教師的科學(xué)的混合物。
因此,從建構(gòu)主義的理論視域來看,學(xué)習(xí)是學(xué)習(xí)者在選擇知覺向度和從長時(shí)記憶中已經(jīng)存在的概念之間獲得聯(lián)結(jié),
并對(duì)獲得的意義進(jìn)行重構(gòu)(Gamett et a1.1995)。但面對(duì)新的知識(shí),他們并不喜歡轉(zhuǎn)變來自長時(shí)間的經(jīng)驗(yàn)和觀察的“前概念”,只有當(dāng)他們意識(shí)到原有概念無法進(jìn)行指導(dǎo)現(xiàn)實(shí)的問題解決,進(jìn)而對(duì)他們的概念不滿意,才會(huì)真的接納科學(xué)的概念,實(shí)現(xiàn)概念轉(zhuǎn)變(Posner.Strike.Hewson.1982)。
3.理解性學(xué)習(xí)
從行為主義的學(xué)習(xí)觀到建構(gòu)主義的學(xué)習(xí)觀,對(duì)于學(xué)習(xí)的界定發(fā)生著變化,越來越多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研究者開始關(guān)注“有效學(xué)習(xí)”、“深層學(xué)習(xí)”,來自腦科學(xué)和認(rèn)知科學(xué)的研究成果不斷推動(dòng)著該研究的進(jìn)展。Petitto和Dunbar等研究者(2004)曾利用FMRI技術(shù)對(duì)物理系大學(xué)生和非物理專業(yè)的成年人進(jìn)行“自由落體運(yùn)動(dòng)”概念的實(shí)驗(yàn)㈣,研究顯示,當(dāng)出現(xiàn)正確的運(yùn)動(dòng)圖像時(shí),物理系學(xué)生腦中的相應(yīng)區(qū)域(尾核和副海馬區(qū))激活,說明他們已經(jīng)接受了正確的科學(xué)概念:當(dāng)出現(xiàn)錯(cuò)誤的運(yùn)動(dòng)圖像時(shí),他們的前扣帶回激活增加,表示了概念上的沖突,普通成年人面對(duì)正確的和錯(cuò)誤的圖像時(shí),腦中激活的區(qū)域則相反,說明非物理專業(yè)的成年人仍然持有自由落體運(yùn)動(dòng)的錯(cuò)誤概念。
以技能訓(xùn)練、知識(shí)記憶為指向的傳統(tǒng)教學(xué)方式,容易造成學(xué)生對(duì)知識(shí)和概念的迷思,因此,與機(jī)械的記憶性學(xué)習(xí)相對(duì)的“理解性學(xué)習(xí)”備受關(guān)注。美國哈佛大學(xué)教育研究院主持的零點(diǎn)計(jì)劃(Project zero)中,已將理解性學(xué)習(xí)與教學(xué)(Learn.ing and Teaching For understanding,LTFU)作為其研究的重點(diǎn)之一。
那么,什么是學(xué)習(xí)中的理解?認(rèn)知心理學(xué)中將其闡述為學(xué)習(xí)者基于原有圖式的個(gè)體心智的意義建構(gòu)過程。從心智表征模型來看,理解是一種學(xué)習(xí)的程度和狀態(tài),表明了心理意義的獲得,也是個(gè)體內(nèi)隱的“意義生成”的心智活動(dòng),當(dāng)然這一活動(dòng)過程往往依賴于社會(huì)文化的中介作用。筆者認(rèn)為,心智模型@的建構(gòu)是理解的內(nèi)在心理學(xué)機(jī)制,基于心智建構(gòu)而在環(huán)境中表現(xiàn)出來的能力,即理解性實(shí)作(Understandin~Performance)也是理解的重要成分,因此:(1)理解是基于個(gè)體的已有知識(shí)和原有經(jīng)驗(yàn)來建構(gòu)意義:(2)理解是一個(gè)層次上深淺的問題(所謂的淺層理解與深層理解);(3)理解是有個(gè)體差異的、多樣的(因個(gè)體的心智結(jié)構(gòu)差異);(4)理解是基于心智建構(gòu)而在環(huán)境中表現(xiàn)出來的行動(dòng)和“實(shí)作能力”。
從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視角看待有效學(xué)習(xí),其實(shí)質(zhì)便是理解性學(xué)習(xí),即學(xué)習(xí)者對(duì)某主題知識(shí)的掌握,在量增加的基礎(chǔ)上,逐漸的精致化,圍繞專業(yè)知識(shí)的核心概念或原理形成知識(shí)結(jié)構(gòu)的內(nèi)在表征或心智模式,在事實(shí)和觀點(diǎn)之間直接建立關(guān)聯(lián),并能用不同的方式在真實(shí)情景中去運(yùn)用。學(xué)習(xí)科學(xué)強(qiáng)調(diào)的就是理解性學(xué)習(xí),為學(xué)生設(shè)定的目標(biāo)便是達(dá)到深層理解(deeo un.derstandin),即獲得專家用來完成有意義的任務(wù)時(shí)所用的那種知識(shí),這絕不是對(duì)事實(shí)或程序的機(jī)械記憶與再認(rèn),而是把概念和策略組織到一個(gè)層級(jí)框架(hierarchical framework)中,用于決定以怎樣的方式在何時(shí)把知識(shí)應(yīng)用于理解新材料并在特定環(huán)境中解決相關(guān)問題。
因此,理解性學(xué)習(xí)就是讓學(xué)習(xí)者將陳述性的有序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化,將程序性的知識(shí)整合原有經(jīng)驗(yàn)得以條件化,最終表現(xiàn)為環(huán)境中理解性實(shí)作能力的提升,這也體現(xiàn)出理解性學(xué)習(xí)的“遷移”本質(zhì),即學(xué)習(xí)者將已有知識(shí)和技能“遷入”新情境時(shí)的適應(yīng)性改變與調(diào)整,進(jìn)而能夠彈性的適應(yīng)新環(huán)境,“為新學(xué)習(xí)做準(zhǔn)備”。
最近的一些研究認(rèn)為,教師、教材是不能把知識(shí)傳遞給學(xué)習(xí)者的:相反,學(xué)習(xí)者通過探究周圍的世界、與環(huán)境交互、觀察現(xiàn)象、產(chǎn)生新想法、與他人討論,來積極建構(gòu)知識(shí),即學(xué)習(xí)者只有根據(jù)自己的經(jīng)驗(yàn)與外界交互并積極建構(gòu)意義的時(shí)候,深層理解才會(huì)發(fā)生吲。盡管在不同生活情境中的學(xué)習(xí)者有不同的描述生活情境的方式,以及因此所產(chǎn)生有差異的“意義”,但學(xué)習(xí)者在描述情境過程中,意義也就被建構(gòu)起來。而且他們對(duì)自己的表達(dá)和想法的反思,也會(huì)讓他們學(xué)到更多,也即他們自身想法(觀點(diǎn))的可視化有利于在新舊知識(shí)之間建立聯(lián)系。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方法和工具被用于支持這種有意義的學(xué)習(xí),如小組學(xué)習(xí)、類比策略、概念圖工具等;不僅如此,有研究者發(fā)現(xiàn)學(xué)生群體在學(xué)習(xí)科學(xué)概念時(shí),會(huì)隨意地與同伴使用“隱喻”(Joel J.Mintzes.2002)。隱喻具有對(duì)某一不熟悉概念的符號(hào)相似性(symbohc similarities),可以促進(jìn)學(xué)生在概念上的理解,學(xué)生使用的隱喻是依據(jù)他們的經(jīng)驗(yàn)而產(chǎn)生的,可以作為有效的認(rèn)知策略。
布蘭思福特(Bransford,2000)等研究者在《人是如何學(xué)習(xí)的》一書中總結(jié)出7個(gè)促進(jìn)理解性學(xué)習(xí)的策略,即:(1)圍繞學(xué)科的主要概念和原理形成結(jié)構(gòu);(2)運(yùn)用已有的知識(shí)建構(gòu)新理解:(3)運(yùn)用元認(rèn)知促進(jìn)學(xué)習(xí);(4)利用學(xué)習(xí)者之間存在的差異:(5)激發(fā)學(xué)習(xí)者的動(dòng)機(jī);(6)在實(shí)踐活動(dòng)的情境中學(xué)習(xí);(7)構(gòu)建社會(huì)交互的學(xué)習(xí)共同體。
值得注意的是,學(xué)習(xí)科學(xué)家還發(fā)現(xiàn),當(dāng)學(xué)習(xí)者外化并表達(dá)自己正在形成的知識(shí)時(shí),學(xué)習(xí)效果會(huì)更好(Bransford,Brown&Cocking,2000)。原因是表達(dá)引發(fā)了學(xué)習(xí)者思考的過程,產(chǎn)生了可能的反思,即自我啟發(fā)的學(xué)習(xí):最好的學(xué)習(xí)方式是在學(xué)習(xí)者知識(shí)尚未成形時(shí)就開始嘗試進(jìn)行表述,并一直貫穿于整個(gè)學(xué)習(xí)過程。因此,學(xué)習(xí)者之間的協(xié)作和對(duì)話是很關(guān)鍵的,可視化的社會(huì)交互,使學(xué)習(xí)者從清晰表達(dá)中獲益,而如何支持學(xué)習(xí)者的表達(dá)過程,也成為學(xué)習(xí)科學(xué)重要的研究主題。
4.從新手到專家:學(xué)習(xí)的過程
專家們是怎樣獲得那些專業(yè)知識(shí)的?從新手到專家的轉(zhuǎn)變,學(xué)習(xí)者經(jīng)歷了怎樣的心智階段?
一般認(rèn)為,專家是在特定領(lǐng)域具有專門技能、知識(shí)和經(jīng)驗(yàn)的個(gè)人,能夠有效地思考該領(lǐng)域的問題。與新手相比,至少在三個(gè)方面體現(xiàn)出專家知識(shí)的特征:第一,在知識(shí)的組織上,專家從理論發(fā)展與實(shí)踐應(yīng)用密切相連的縱橫維度,圍繞核心概念或“大觀點(diǎn)”構(gòu)成了開放穩(wěn)定、豐富內(nèi)涵的體系化知識(shí)網(wǎng)絡(luò)或圖式(sehema),專家能夠挖掘事物中隱含的條件和聯(lián)系,覺知有意義的信息模塊或組塊(chunk)。并據(jù)此進(jìn)行推理和評(píng)價(jià),因此,“知道得越多”意味著在記憶中擁有的彼此聯(lián)系的概念模塊或組塊就越多:第二,在面對(duì)問題解決時(shí),專家所運(yùn)用的科學(xué)方法隱含哲學(xué)的思想智慧,善于縱觀整個(gè)問題的背景和其中各成分間的關(guān)系并對(duì)問題進(jìn)行分類(新手往往只看到孤立的問題本身或表面特征對(duì)問題進(jìn)行歸類),然后結(jié)合自己的體驗(yàn)(或經(jīng)驗(yàn))自動(dòng)地調(diào)用大腦中的圖式應(yīng)對(duì)當(dāng)前的情境要求。提取相關(guān)信息以執(zhí)行一系列的認(rèn)知操作。因此,專家的知識(shí)是在經(jīng)久訓(xùn)練和具身體驗(yàn)中得到的相互連接、融合、組織化的體系,是“條件化”的。并且能做到“自動(dòng)化”的順暢提取。第三,與新手相比,專家更擅長規(guī)劃和檢查自己的工作,即進(jìn)行反思性(Reflective)的思維活動(dòng),如同作家,邊寫作邊出聲說出自己的思考過程,當(dāng)覺察到不
妥之處時(shí)進(jìn)行反省和調(diào)整,
由以上二者的差異看出,其實(shí)學(xué)習(xí)也就是“某領(lǐng)域的新手轉(zhuǎn)變?yōu)閷<业倪^程”,不過,從心智模型的相似性來衡量新手向?qū)<肄D(zhuǎn)變的程度值得推敲,因?yàn)槠淝疤嵴J(rèn)定專家們的心智模型是高度相似的。就簡單任務(wù)的完成而言,成功高效地完成者確實(shí)有著相似的任務(wù)技巧,相似性也體現(xiàn)在具體情境下運(yùn)用哪些關(guān)鍵概念和程序的信息,但環(huán)境因素的復(fù)雜及可變性,專家心智模型的唯一性也難以存在,而且不適應(yīng)環(huán)境變化的心智模型也會(huì)是僵化、低效的。因此,即使相同領(lǐng)域的專家也可能存在有差異的心智模型:同理,先前經(jīng)驗(yàn)在新手的學(xué)習(xí)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為準(zhǔn)確把握專業(yè)知識(shí)的內(nèi)涵屬性,僅僅通過觀察模仿專家間接經(jīng)驗(yàn)的學(xué)習(xí)是不夠的,而是要去經(jīng)歷體驗(yàn),讓新手沉浸在特定的情境中,通過參與特定領(lǐng)域真實(shí)的活動(dòng),在與專家的互動(dòng)交流中,逐漸形成自己對(duì)專業(yè)知識(shí)的理解(Lave&Wen~er,1991)。當(dāng)然這類活動(dòng)會(huì)對(duì)新手來說是有難度的,腳手架的搭建幫助他們更好的跨越因?qū)嵺`經(jīng)驗(yàn)差異造成的“專業(yè)鴻溝”。
5.學(xué)習(xí)的情感考察
學(xué)習(xí)作為人類重要的心智活動(dòng),個(gè)體心智模型的差異演繹著個(gè)體學(xué)習(xí)風(fēng)格的不同,而個(gè)體內(nèi)在的動(dòng)機(jī)、態(tài)度、興趣、自信、焦慮程度等與學(xué)習(xí)效果息息相關(guān),這已成為研究者們的共識(shí)并對(duì)此開展了諸多深入地研究。然而,直到20世紀(jì)末,情感作為認(rèn)知過程重要組成部分的身份才得到了學(xué)術(shù)界的普遍認(rèn)同。實(shí)際上,人們?cè)谡J(rèn)識(shí)客觀事物時(shí),總是帶有某種傾向性,表現(xiàn)出鮮明的態(tài)度體驗(yàn),充滿著感情的色彩,即內(nèi)心主觀體驗(yàn)的外部表征。認(rèn)知科學(xué)家們把情感與知覺、學(xué)習(xí)、記憶、言語等經(jīng)典認(rèn)知過程相提并論,重視學(xué)習(xí)者在學(xué)習(xí)過程中的非智力因素,認(rèn)為學(xué)習(xí)情感(即學(xué)習(xí)中所產(chǎn)生的情感過程)貫徹于學(xué)習(xí)過程的始終,正向的學(xué)習(xí)情感對(duì)學(xué)習(xí)者的認(rèn)知活動(dòng)將產(chǎn)生增效的作用。
人的學(xué)習(xí)本身就是一個(gè)復(fù)雜的認(rèn)知過程,情感參與和認(rèn)知投入是緊密地結(jié)合在一起的,而情感也是錯(cuò)綜復(fù)雜的心理現(xiàn)象,是各種心理因素的組合體。加之情感的易變性、不確定性和社會(huì)性特征,若與人們的愿望和期待相符合的情境則能夠引發(fā)積極的情感,反之則引起消極的情感。我們需要更多關(guān)注學(xué)習(xí)中情感、歸屬和交互的融合,探索學(xué)習(xí)中情感的多維心理特征的外在表征及其對(duì)學(xué)習(xí)的正向和反向的作用。如相關(guān)研究(焦彩珍,2008)表明,“學(xué)困生”在學(xué)習(xí)中情感的心理特征對(duì)數(shù)學(xué)成績就有著顯著的影響,而這些情感心理特征的各不同維度之間也密切聯(lián)系,相互作用。
如今,情感與其他認(rèn)知過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成為當(dāng)代認(rèn)知科學(xué)的研究熱點(diǎn),以至于由此產(chǎn)生的情感計(jì)算(AffectiveComouting)成為一個(gè)計(jì)算機(jī)科學(xué)中新興的研究領(lǐng)域,這是一個(gè)高度綜合化的研究和技術(shù)領(lǐng)域,通過計(jì)算科學(xué)與心理科學(xué)、認(rèn)知科學(xué)的結(jié)合,研究人與人交互、人與計(jì)算機(jī)交互過程中的情感特點(diǎn),設(shè)計(jì)具有情感反饋的人與計(jì)算機(jī)的交互環(huán)境,讓計(jì)算機(jī)通過對(duì)人類的情感進(jìn)行獲取、分類、識(shí)別和響應(yīng)。最終可能讓計(jì)算機(jī)像人一樣能進(jìn)行自然、親切和生動(dòng)的交互,即人與計(jì)算機(jī)的情感交互。
(三)學(xué)習(xí)的方式與形式
人類學(xué)習(xí)方式的演變體現(xiàn)出不同時(shí)代的人類學(xué)習(xí)活動(dòng)的特點(diǎn)與規(guī)律,傳統(tǒng)的學(xué)習(xí)研究,常常聚焦于個(gè)體如何主動(dòng)加工和建構(gòu)知識(shí),作為“完成學(xué)習(xí)任務(wù)時(shí)的基本行為和認(rèn)知策略與傾向總和”的學(xué)習(xí)方式。而今,在逐漸擺脫行為主義指導(dǎo)下以“教”為中心的教學(xué)理念后,隨著人類學(xué)習(xí)的認(rèn)知、心理、神經(jīng)學(xué)基礎(chǔ)的發(fā)展,特別是近十余年來產(chǎn)生的一些有關(guān)學(xué)習(xí)的新理論,如建構(gòu)主義學(xué)習(xí)理論、協(xié)作學(xué)習(xí)理論、情境學(xué)習(xí)理論以及泛在學(xué)習(xí)理論等等,推動(dòng)著教與學(xué)方式的變革,而學(xué)習(xí)的形式也趨于多樣化。
1.正式學(xué)習(xí)與非正式學(xué)習(xí)
從知識(shí)獲取角度看學(xué)習(xí)發(fā)生的方式,學(xué)習(xí)可以分為正式學(xué)習(xí)(Formal Learning)與非正式學(xué)習(xí)(I,fformaI Learning)兩種基本形式。非正式學(xué)習(xí)通常發(fā)生在學(xué)校以外,但與正式學(xué)習(xí)區(qū)分的主要依據(jù)卻不是學(xué)習(xí)發(fā)生的地理位置,而是是否發(fā)生于具有說教色彩的教學(xué)實(shí)踐。也就是說,在學(xué)校中也廣泛存在非正式學(xué)習(xí),而在非學(xué)校的環(huán)境中也可能有正式學(xué)習(xí)的發(fā)生(如社區(qū)教育中的培訓(xùn)活動(dòng))。作為正式學(xué)習(xí)的學(xué)校教育,提供的是與學(xué)習(xí)者日常生活并不連續(xù)相關(guān)的知識(shí)體系,密集的訓(xùn)練使得學(xué)習(xí)者的抽象推理能力得到提升,但人腦的發(fā)展不單純是教育的產(chǎn)物,兒童在日常生活中通過模仿學(xué)習(xí)獲得的經(jīng)驗(yàn)也有助于對(duì)其大腦的塑造,“鏡像神經(jīng)元”(mi‘rror neu,ronsl的發(fā)現(xiàn)驗(yàn)證了這一觀點(diǎn),凸現(xiàn)了“非正式”的模仿學(xué)習(xí)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學(xué)習(xí)者在沒有正規(guī)的教學(xué)(或?qū)W習(xí)意識(shí))參與的情況下,為適應(yīng)新環(huán)境而與周圍人或物的互動(dòng)(或觀察模仿)中,獲得了那些用言語難于表達(dá)的知識(shí),這也即內(nèi)隱學(xué)習(xí)的發(fā)生。
對(duì)非正式學(xué)習(xí)實(shí)質(zhì)的探究,也可以從正式學(xué)習(xí)的內(nèi)涵來推演。眾所周知,正式學(xué)習(xí)通常發(fā)生在學(xué)校,信奉普適的行為價(jià)值和標(biāo)準(zhǔn),以語言為主要媒介來傳遞常常脫離境脈的知識(shí),學(xué)習(xí)者也傾向于用語言來描述習(xí)得的知識(shí)或問題解決的過程。對(duì)比正式學(xué)習(xí),斯克里布納和科爾(Scfibner&Cole,1973)提出非正式學(xué)習(xí)三個(gè)特點(diǎn):(1)非正式學(xué)習(xí)是個(gè)人取向(person-onented)的,或者說是自我發(fā)起的,目標(biāo)的設(shè)定取決于個(gè)體本身的意愿而非掌握的知識(shí)基礎(chǔ):(2)非正式學(xué)習(xí)的過程融合了情感和智力,常常表現(xiàn)為包含著認(rèn)同和移情的“觀察學(xué)習(xí)”之中;(3)非正式學(xué)習(xí)中因個(gè)體身份的建構(gòu)而助長傳統(tǒng)主義,非教學(xué)性質(zhì)的社會(huì)交互形成“實(shí)踐共同體”,學(xué)習(xí)者身份及參與結(jié)構(gòu)把專家于核心位置,
現(xiàn)在,學(xué)習(xí)科學(xué)專家對(duì)非正式學(xué)習(xí)的關(guān)注體現(xiàn)在三條線索的研究:(1)內(nèi)隱學(xué)習(xí)與大腦;(2)非正式學(xué)習(xí);(3)正式學(xué)習(xí)與非正式學(xué)習(xí)的設(shè)計(jì)。研究者將他們的觀點(diǎn)和發(fā)現(xiàn)應(yīng)用于教育中,并提示學(xué)習(xí)科學(xué)家如何借鑒這些研究更加深入地理解學(xué)習(xí)㈣。
隨著通訊移動(dòng)設(shè)備的普及,非正式學(xué)習(xí)的形式和機(jī)會(huì)越來越多。需要注意的是,新手在非正式學(xué)習(xí)中僅僅觀察模仿專家的示范,尚不足以保證他們注意到所有相關(guān)細(xì)節(jié),如前文所述,專家的知識(shí)不是一張互不關(guān)聯(lián)的陳述性知識(shí)的清單,而是依據(jù)學(xué)科中的重要觀點(diǎn)(或核心概念)進(jìn)行有機(jī)連接和組織的知識(shí)網(wǎng)絡(luò),包括了應(yīng)用關(guān)鍵概念和程序的情境信息。因此,強(qiáng)調(diào)專業(yè)知識(shí)和注意力也暗示學(xué)習(xí)者不能簡單地從經(jīng)驗(yàn)中學(xué)習(xí),而是要學(xué)會(huì)去經(jīng)歷。
2.個(gè)別化學(xué)習(xí)與協(xié)作學(xué)習(xí)
個(gè)別化學(xué)習(xí)源于個(gè)別化教學(xué)的概念,是學(xué)習(xí)者高度自主性的學(xué)習(xí)方式,通過自我探索、自我思考實(shí)現(xiàn)知識(shí)的獲取或更新,適合于認(rèn)知領(lǐng)域和動(dòng)作技能中大多層次的學(xué)習(xí)目標(biāo),個(gè)別化學(xué)習(xí)體現(xiàn)以學(xué)習(xí)為中心,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理念。協(xié)作學(xué)習(xí)則是一種通過小組或團(tuán)隊(duì)的形式組織學(xué)生進(jìn)行學(xué)習(xí)的一種學(xué)習(xí)方式或策略,學(xué)習(xí)者個(gè)體之間通常采用對(duì)話、商討、爭(zhēng)論等形式在進(jìn)行問題解決的過程中獲得知識(shí)進(jìn)而達(dá)到學(xué)習(xí)的目標(biāo)。
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研究者將個(gè)體認(rèn)知延伸到群體認(rèn)知是相當(dāng)
有價(jià)值的,一系列的相關(guān)研究也證實(shí),小組合作的學(xué)習(xí)者較之個(gè)別化學(xué)習(xí)者更易在交互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更易得出有產(chǎn)出的推論(Simon,1997)。計(jì)算機(jī)技術(shù)和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快速發(fā)展為學(xué)習(xí)提供了良好的環(huán)境,如今,計(jì)算機(jī)支持的協(xié)作學(xué)習(xí)(Compu~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CSCL)成為研究和應(yīng)用的熱點(diǎn)。眾多學(xué)者認(rèn)為。CSCL是繼承計(jì)算機(jī)支持的協(xié)同工作(CSCW)理論和技術(shù)的基礎(chǔ)上將協(xié)作學(xué)習(xí)的教育理論融人其中發(fā)展演變而來的,考希曼(Kosehmann,2002)曾指出,CSCL的歷史發(fā)展軌跡為:計(jì)算機(jī)輔助教學(xué)一智能導(dǎo)師系統(tǒng)一學(xué)習(xí)LOGO程序語言CSCL。Gallaudent大學(xué)的ENH項(xiàng)目(讓聾人學(xué)生以新的文字媒介方式進(jìn)行寫作)、多倫多大學(xué)的CSILE項(xiàng)目以及加州圣地亞哥大學(xué)的“第五維度”項(xiàng)目(the Fifth Dimension Proiect),成為稍候出現(xiàn)的CSCL研究領(lǐng)域的先驅(qū),這三個(gè)研究都通過嘗試使用技術(shù)來促進(jìn)有關(guān)讀寫能力的學(xué)習(xí),
盡管小組合作學(xué)習(xí)的研究要比CSCL早得多,但CSCL的軟件環(huán)節(jié)提供不同形式的教學(xué)支持和腳手架支持,即通過設(shè)計(jì)技術(shù)(工具及人工制品)來支持學(xué)習(xí)者的意義建構(gòu),技術(shù)的社會(huì)性提供了更多地學(xué)習(xí)機(jī)會(huì),而技術(shù)本身也表現(xiàn)出在支持協(xié)作學(xué)習(xí)過程中的獨(dú)特性,如:(1)自由配置的計(jì)算機(jī)媒介實(shí)現(xiàn)了動(dòng)態(tài)表征,技術(shù)的潛能本身又促成了新的交互,(2)計(jì)算機(jī)為媒介的溝通“實(shí)體化”,使得學(xué)習(xí)活動(dòng)本身可以被記錄和重現(xiàn),成為新的學(xué)習(xí)資源。為此,考希曼在2002年CSCL的會(huì)議上做主題演講時(shí),對(duì)CSCL給出了一個(gè)概括性的描述:“CSCL著重研究在共同活動(dòng)環(huán)境下的意義和意義建構(gòu)的實(shí)踐活動(dòng),以及設(shè)計(jì)的人工制品被這些實(shí)踐活動(dòng)應(yīng)用為媒介的方式。
3.學(xué)習(xí)共同體
“共同體”是人類群體生活的表現(xiàn),從社會(huì)學(xué)的視角看待人類學(xué)習(xí),那些有價(jià)值的綜合的實(shí)踐性知識(shí)都隱含在特定的共同體中(趙健,2007),共同體內(nèi)部面向共同愿景的社會(huì)建構(gòu)和文化協(xié)商,促進(jìn)了成員的認(rèn)知成長。從這個(gè)意義上說,學(xué)習(xí)本質(zhì)上是對(duì)一定文化歷史背景下的特定實(shí)踐共同體的參與。
很多的研究者將學(xué)習(xí)置于共同體境脈中考察知識(shí)的社會(huì)建構(gòu)性。維果茨基認(rèn)為,每個(gè)學(xué)習(xí)者在協(xié)作的情境下發(fā)展的知識(shí)和能力和他們單獨(dú)學(xué)習(xí)時(shí)是不同的,他用“最鄰近發(fā)展區(qū)”的概念來衡量這兩者的差異,大多研究者也認(rèn)為“共同體”在促進(jìn)個(gè)體學(xué)習(xí)方面表現(xiàn)得很有效。群體認(rèn)知或主體間的學(xué)習(xí),存在于共同體內(nèi)面向知識(shí)建構(gòu)的互動(dòng),實(shí)際上,共同體內(nèi)部因成員差異而存在著客觀的異質(zhì)性。根據(jù)知識(shí)分布式的特點(diǎn),協(xié)作團(tuán)隊(duì)中的知識(shí)會(huì)呈現(xiàn)出異質(zhì)性和多元化,Jehn(1999)等研究者稱之為“信息異質(zhì)性”(另外還存在著“社會(huì)屬性異質(zhì)性”和“價(jià)值觀異質(zhì)性”),由此,協(xié)作中的會(huì)話(discourse)顯得尤為重要。貝克(Bake~2004)曾將其作用概括為:明確知識(shí)、通過差異化促進(jìn)概念轉(zhuǎn)變、闡述新知識(shí)及知識(shí)精致化等方面。
因差異而產(chǎn)生的認(rèn)知沖突在協(xié)商會(huì)話中起著中介的作用,成員之間能夠從不同的視角提供解釋來為自己的觀點(diǎn)辯護(hù),進(jìn)而能夠促使參與者在彼此思想的基礎(chǔ)上共同建構(gòu)新解。因此,共同體內(nèi)協(xié)商合作的過程也就是基于知識(shí)異質(zhì)性而進(jìn)行的心智模型共建共享的過程,而共同體內(nèi)的學(xué)習(xí)可以看做是協(xié)商不同觀點(diǎn)的行為,這種協(xié)商是基于真實(shí)的辯論而非等級(jí)觀念下的妥協(xié)。我們需要關(guān)注群體互動(dòng)中如何達(dá)成主體間性,需要了解學(xué)習(xí)本身如何在成員之間的互動(dòng)中發(fā)生。不僅如此,在協(xié)作學(xué)習(xí)的氛圍中,參與者會(huì)利用持續(xù)交談的方式進(jìn)行群體思考來建構(gòu)共同知識(shí)。輔助以手勢(shì)、圖板等進(jìn)行觀點(diǎn)(知識(shí))的可視化表達(dá),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相互理解或共同解決問題。而且即使同伴缺乏成熟的觀點(diǎn),仍然可以通過有意或無意的提示為其他學(xué)習(xí)者搭建腳手架,這種即興發(fā)生的同伴腳手架(peer scaffolding)是成員個(gè)體心智模型分布與認(rèn)同的聯(lián)結(jié),是增強(qiáng)團(tuán)隊(duì)效能的潛在動(dòng)力;當(dāng)然。協(xié)作活動(dòng)有時(shí)并不順暢,協(xié)調(diào)的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4.數(shù)字土著的“多任務(wù)”學(xué)習(xí)
信息技術(shù)的快速發(fā)展,不斷拓展用以呈現(xiàn)和信息加工的技術(shù)手段,由早期的多媒體通道呈現(xiàn)發(fā)展為以超媒體、計(jì)算機(jī)網(wǎng)絡(luò)等為支撐的新媒體技術(shù),支持著社會(huì)協(xié)商和意義建構(gòu),構(gòu)造出豐富的學(xué)習(xí)情境脈絡(luò)。而信息技術(shù)成為認(rèn)知工具、學(xué)習(xí)伙伴,這對(duì)學(xué)習(xí)者的心智模型產(chǎn)生著深刻的影響,學(xué)習(xí)的方式也悄然發(fā)生著變革。早年尼葛洛龐帝在面對(duì)數(shù)字時(shí)代的學(xué)習(xí)時(shí),認(rèn)為年輕的學(xué)習(xí)者是活躍的獨(dú)立學(xué)習(xí)者。當(dāng)時(shí),他試圖以其設(shè)計(jì)的百美元電腦實(shí)現(xiàn)“人人電腦”,讓孩子們的可以進(jìn)行直接探索、表達(dá)、體驗(yàn),直至跨語言和文化的無縫學(xué)習(xí)。今天看來,盡管尼葛洛龐帝認(rèn)為的只要借助于數(shù)字化技術(shù),學(xué)生就能自發(fā)實(shí)現(xiàn)有效的學(xué)習(xí)的理念確實(shí)是缺少說服力的,但是對(duì)于學(xué)習(xí)者來說,他們的主體性增強(qiáng)。而且教師的角色重新定位已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
而今,隨著智能手機(jī)、iPad等各種數(shù)碼產(chǎn)品的使用及其無線上網(wǎng)的普及,在學(xué)校里就讀的學(xué)生便成長在數(shù)字化的環(huán)境里,鐘情于“三屏”(手機(jī)、電視、電腦屏幕),生活在由網(wǎng)站、電子郵件、短信和移動(dòng)電話組成的數(shù)字世界里,(美國神經(jīng)學(xué)家蓋瑞?斯莫爾的著作《大腦革命》把從小接觸數(shù)字技術(shù)的年輕一代稱為“數(shù)字土著”,而把只在成年后才接觸計(jì)算機(jī)和網(wǎng)絡(luò)的人稱為“數(shù)字移民”),他們喜歡也擅長同時(shí)處理多種任務(wù),他們敏銳的快速的接收著各類信息,對(duì)于知識(shí)的學(xué)習(xí)習(xí)慣于“隨機(jī)進(jìn)入”,喜歡游戲而非“嚴(yán)肅”的有條理的工作。傳統(tǒng)的教育者堅(jiān)持認(rèn)為他們的學(xué)生在上網(wǎng)或者聽音樂的同時(shí)不能成功的學(xué)習(xí),因?yàn)檫@些教育者們自己不能做到(MarcPrenskv。2009):而且知識(shí)的獲取必須是個(gè)人參與的結(jié)果,離不開參與者的熱情、信念和理解,當(dāng)學(xué)習(xí)者的生活空間和信息空間融合的時(shí)候,在個(gè)別化學(xué)習(xí)、小組學(xué)習(xí)等正式的學(xué)習(xí)方式之外,泛在學(xué)習(xí)將與之并存。
基于數(shù)字土著的學(xué)習(xí)特點(diǎn),教育者們不僅關(guān)照諸多教育情境中具有的共同性與一致性要素,而且更專注于把握教育情境中知識(shí)本質(zhì)變化的復(fù)雜性與規(guī)律性,關(guān)注于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學(xué)習(xí)情境設(shè)計(jì):如今,特定情境與條件下知識(shí)變化與發(fā)展的多樣性與差異性備受關(guān)注,而多樣化和人本性的學(xué)習(xí)活動(dòng)設(shè)計(jì)和課程設(shè)計(jì)越來越得到重視,而學(xué)習(xí)方式變革的重點(diǎn)也放在了變“淺層學(xué)習(xí)”為“深層學(xué)習(xí)”上,要讓學(xué)習(xí)者變消極應(yīng)付為主動(dòng)加工,變機(jī)械記憶為探究思考。在學(xué)習(xí)方式“轉(zhuǎn)型”的十字路口,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發(fā)出倡議,他們不僅提倡與“他主”性、被動(dòng)性相對(duì)的自主學(xué)習(xí),還要求教師創(chuàng)設(shè)恰當(dāng)?shù)膯栴}情境,引導(dǎo)學(xué)生關(guān)注學(xué)習(xí)中的創(chuàng)意和深層的情感體驗(yàn),促成認(rèn)知深加工和行為卷入,而且還要關(guān)注學(xué)習(xí)者之間的協(xié)商合作、共享互補(bǔ),重視學(xué)習(xí)中的主體間性口硐。
(四)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設(shè)計(jì)
信息技術(shù)融入日常教學(xué)使得教學(xué)的手段和方式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然而一線的教師發(fā)現(xiàn),信息技術(shù)在教育教學(xué)中
帶來的效果有時(shí)并不如原來期望的那么大。庫班(Cuban,1986)探究了技術(shù)沒能成功支持學(xué)習(xí)的原因,Soloway、Guzdial及Hay等研究者(1994)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信息技術(shù)的應(yīng)用應(yīng)該圍繞學(xué)習(xí)者的(特殊)需求、目標(biāo)、活動(dòng)過程和教育情境來設(shè)計(jì)教育軟件,即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設(shè)計(jì)(Learner-CenteredDesign.LCD)。通過搭建基于軟件的腳手架(Scaffolding)構(gòu)建知識(shí)整合的環(huán)境來幫助學(xué)習(xí)者構(gòu)建新的理解。
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設(shè)計(jì),突出了“使知識(shí)更易于理解”,主要體現(xiàn)在:
首先,使得知識(shí)具有情境性(Situativity)。“情境”是一個(gè)現(xiàn)象學(xué)的概念,它是指通過個(gè)體或群體的“意向性”組織起來的環(huán)境因素。情境化觀點(diǎn)認(rèn)為,學(xué)習(xí)環(huán)境是活動(dòng)系統(tǒng),學(xué)習(xí)者在活動(dòng)系統(tǒng)中與環(huán)境中的其他人,以及物質(zhì)、信息與概念資源相互作用。傳統(tǒng)教學(xué)中的學(xué)生常常獲得不易激活和提取的僵化的“惰性知識(shí)”,即便所接受的結(jié)構(gòu)化組織的知識(shí),但這樣的結(jié)構(gòu)化也多依賴學(xué)科邏輯的鏈接,缺乏情境脈絡(luò)的支持,而導(dǎo)致學(xué)生在遇到問題時(shí)無法將知識(shí)和問題情境對(duì)接而不知所措。
后胡塞爾主義的現(xiàn)象學(xué)研究所產(chǎn)生的知識(shí)形式不是自然法則性的,而是情境化地理解和交流意義。因此,知識(shí)是情境化的,學(xué)習(xí)者需要在有同伴和專家的共同體中建構(gòu)他們自身的知識(shí)(Brown et aI.1989)。所以,獲得專業(yè)知識(shí)需要參與到專門的文化情境中,這樣可以使學(xué)習(xí)者明白共同的實(shí)踐、語言、工具和文化的價(jià)值所在。如Jasper系列給學(xué)生提出個(gè)性化的有意義的問題,激勵(lì)學(xué)習(xí)活動(dòng),將學(xué)習(xí)者當(dāng)前所學(xué)的材料與具有相似情境的或者先前的知識(shí)建立聯(lián)系。
其次,采用不同的方式為學(xué)習(xí)者提供“腳手架”。在維果茨基(Vy~otsky,1978)關(guān)于腳手架的理念之后,更多地研究者進(jìn)一步明確腳手架在為學(xué)習(xí)者提供協(xié)助的支撐本質(zhì),并在不同的情境中應(yīng)用,如提供輔導(dǎo)訓(xùn)練、建構(gòu)任務(wù)、提供建議或指導(dǎo)等。讓學(xué)生可以投入到真實(shí)的練習(xí)中。在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設(shè)計(jì)中,腳手架將整合知識(shí)建構(gòu)與應(yīng)用的方法,面向提升學(xué)習(xí)者的自主學(xué)習(xí)能力,而將知識(shí)更易理解,在情境中使得思維過程可視化,進(jìn)而加強(qiáng)了學(xué)習(xí)者知識(shí)的廣度和深度。
不過,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到課堂中對(duì)教與學(xué)的效果的促進(jìn)很多時(shí)候卻不盡如人意,尤其是早期的一些教育軟件的設(shè)計(jì)開發(fā),設(shè)計(jì)者一貫的思維是關(guān)注軟件的功能及可用性,而忽視了學(xué)習(xí)者的真實(shí)需要和教育情境的特殊要求,教育軟件本身也即學(xué)習(xí)情境的一部分。古茲德爾(Guzdial,1994)在傳統(tǒng)腳手架的理念基礎(chǔ)上,提出的“基于計(jì)算機(jī)軟件實(shí)現(xiàn)的腳手架”(software-realized scaffolding)受到關(guān)注,搭建起來的腳手架將學(xué)習(xí)者置身真實(shí)的實(shí)踐情境中(如軟件呈現(xiàn)的虛擬實(shí)驗(yàn)室),使學(xué)習(xí)者學(xué)習(xí)的各個(gè)方面可視化和直觀化而提供認(rèn)知支持(特別是類似科學(xué)、數(shù)學(xué)那些需要運(yùn)用軟件工具進(jìn)行練習(xí)的學(xué)科)。在特定方面給學(xué)生提供幫助,這些特定方面決定了軟件中腳手架特征的類型,設(shè)計(jì)者開發(fā)不同的搭建腳手架的方法,例如,制訂計(jì)劃是一項(xiàng)比較內(nèi)隱的活動(dòng),因?yàn)閷<宜坪鯌{先前經(jīng)驗(yàn)就可以自動(dòng)產(chǎn)生計(jì)劃,而不需要刻意思考:而學(xué)生由于經(jīng)驗(yàn)不足,未能認(rèn)識(shí)到制訂計(jì)劃在調(diào)查過程中的重要性。因此,給學(xué)生提供提示和引導(dǎo)成為支持學(xué)習(xí)者將操作步驟概念化的一項(xiàng)策略,以幫助學(xué)生制訂有效的計(jì)劃(Ouintanaet a1.2004)。在實(shí)踐中,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設(shè)計(jì)的效果評(píng)價(jià)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就是使用不同的基準(zhǔn)去判斷腳手架的可用性及其對(duì)學(xué)習(xí)者的支持活動(dòng)是否成功。
值得關(guān)注的是,有研究者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提出了促進(jìn)學(xué)習(xí)的新的教學(xué)方法――從設(shè)計(jì)中學(xué)(Learning bv Design,LBD),該方法采用基于項(xiàng)目的探究方法安排學(xué)習(xí)過程和課堂環(huán)境,如通過設(shè)計(jì)某島嶼侵蝕問題,來學(xué)習(xí)關(guān)于侵蝕、潮汐及水流方面的知識(shí),設(shè)計(jì)的具有挑戰(zhàn)的活動(dòng)為學(xué)生提供了參與并學(xué)習(xí)復(fù)雜認(rèn)知技能、社會(huì)技能和交流技能的機(jī)會(huì)。重要的是,這樣的學(xué)習(xí)能夠提供學(xué)生引發(fā)其深層學(xué)習(xí)的各種經(jīng)歷,促進(jìn)學(xué)生對(duì)學(xué)習(xí)經(jīng)驗(yàn)的反思(Kraicik&Blumefeld,2009)。LBD的學(xué)習(xí)活動(dòng)為實(shí)現(xiàn)挑戰(zhàn)目標(biāo)而從設(shè)計(jì)開始,利用調(diào)查手段,并以循環(huán)的形式整合了設(shè)計(jì)、合作、溝通等方面的技巧,如圖3所示,學(xué)習(xí)活動(dòng)從“設(shè)計(jì),再設(shè)計(jì)”循環(huán)開始,當(dāng)學(xué)生發(fā)現(xiàn)有新知識(shí)需要學(xué)習(xí)的時(shí)候就開始了“調(diào)查,探索”循環(huán)過程,而調(diào)查的結(jié)果又為設(shè)計(jì)過程提供了應(yīng)用的內(nèi)容。
在實(shí)際的教學(xué)過程中,LBD活動(dòng)的設(shè)計(jì)最終是為學(xué)生的深入思考提供腳手架,上述的循環(huán)通常呈現(xiàn)出兩類課堂腳本,一類是行動(dòng),一類是會(huì)話;前者融合了科學(xué)和設(shè)計(jì)的技能,后者則安排報(bào)告呈現(xiàn)及內(nèi)容討論的活動(dòng)。
(五)學(xué)習(xí)環(huán)境及其支持
威廉?格里諾和他的同事以“環(huán)境對(duì)大腦的影響”進(jìn)行了前沿研究,認(rèn)為人類的進(jìn)化已使其大腦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在特定時(shí)期對(duì)環(huán)境的信息輸融入產(chǎn)生“期待”(expect),大腦的發(fā)展是一種“受期待的經(jīng)驗(yàn)”(experience expectant),而豐富的環(huán)境資源提供大量的社會(huì)交互、直接接觸環(huán)境的機(jī)會(huì),增進(jìn)并加深了參與者的認(rèn)知體驗(yàn),構(gòu)建良好的學(xué)習(xí)情境將可能促進(jìn)更為有效的學(xué)習(xí)。而“情境化(situative)”的學(xué)習(xí)將焦點(diǎn)集中在促進(jìn)意義建構(gòu)與有效理解的活動(dòng)系統(tǒng)上面,讓參與者在活動(dòng)中進(jìn)行著經(jīng)驗(yàn)的積累與改變。
在使抽象知識(shí)具體化的過程中,計(jì)算機(jī)系統(tǒng)的支持不僅有助于概念的可視化和空間理解,還會(huì)在學(xué)生表達(dá)抽象概念知識(shí)時(shí)提供腳手架。計(jì)算機(jī)應(yīng)用于教育實(shí)踐,經(jīng)歷了上世紀(jì)60年代的計(jì)算機(jī)輔助教育(CBE)、70年代的智能教學(xué)系統(tǒng)(ITS)、80年代的學(xué)習(xí)環(huán)境建設(shè)和90年代開始的計(jì)算機(jī)支持的協(xié)作學(xué)習(xí)(CSCL)。CSCL的方法體現(xiàn)出網(wǎng)絡(luò)交互作用的優(yōu)勢(shì),支持更多社會(huì)層面的學(xué)習(xí)環(huán)境的創(chuàng)設(shè),具有支持有效辯論、引導(dǎo)深層理解的潛能,在這樣的學(xué)習(xí)環(huán)境中,個(gè)人可能通過參與學(xué)習(xí),也可能通過內(nèi)化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學(xué)習(xí),也促進(jìn)了小組內(nèi)知識(shí)的構(gòu)建。如CSILE軟件就是為了讓學(xué)生在幾周的時(shí)間中,異步合作地建構(gòu)科學(xué)概念和知識(shí)而設(shè)計(jì)的(Scardamali,a&Bereiter.1991)。
當(dāng)前,CSCL的研究突出了技術(shù)化、多元化的趨向,應(yīng)用計(jì)算機(jī)智能技術(shù)和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為支撐,促進(jìn)學(xué)習(xí)者的知識(shí)建構(gòu)、概念學(xué)習(xí)、問題解決和設(shè)計(jì)創(chuàng)作等等學(xué)習(xí)活動(dòng);這些研究的熱點(diǎn)如:CSCL中的協(xié)作交互(黃榮懷,劉黃玲子等。1998,2005;Henfi.F.1991)、CSCL促進(jìn)知識(shí)建構(gòu)(李克東,2007;王陸等,2009;Stahl.G.1999)、協(xié)作學(xué)習(xí)模式(趙東輪、黃榮懷等,2008;Wilfred Rubens等,2005)等等,也因此涌現(xiàn)出一批優(yōu)秀的學(xué)習(xí)平臺(tái),如國際教育資源網(wǎng)I'EARN(1988),Scardamalia等開發(fā)的CSILE平臺(tái)(1989),Berkeley大學(xué)(1998)開發(fā)的
WISE平臺(tái),斯里蘭卡國際中心(SRI)開發(fā)的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網(wǎng)絡(luò)學(xué)習(xí)平臺(tái)Tapped In(2005)、亞卓市(EduCities,陳德懷等,2005)、思摩特網(wǎng)(SCTNet,臺(tái)灣中山大學(xué))等。
計(jì)算機(jī)硬件和軟件性能的提高為將更多學(xué)生提供新的學(xué)習(xí)機(jī)會(huì),在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約翰.R.安德森(John R.Andemon)提出一種在智能導(dǎo)師系統(tǒng)發(fā)展和測(cè)試方面跨越更多學(xué)科的方法,即把認(rèn)知心理學(xué)的原則融ru 到人工智能中,這樣的智能導(dǎo)師系統(tǒng)將圍繞學(xué)生已有知識(shí)的認(rèn)知模型而建構(gòu),成為“認(rèn)知導(dǎo)師(Cognitive Tutors)”系統(tǒng),該系統(tǒng)監(jiān)控學(xué)習(xí)者完成預(yù)設(shè)任務(wù)的程度,并采用模型和知識(shí)跟蹤的算法來體現(xiàn)輔導(dǎo)和(共同體內(nèi)的)學(xué)徒制訓(xùn)練。大量的實(shí)踐證明,將認(rèn)知原則從個(gè)體延伸到群體活動(dòng)是很有價(jià)值的,因此而產(chǎn)生的“情境化視角”整合了個(gè)體認(rèn)知與交互研究這兩種取向,將學(xué)習(xí)環(huán)境界定為活動(dòng)系統(tǒng),關(guān)注個(gè)體的表征(即其信息結(jié)構(gòu)的呈示)符號(hào)與情境之間的聯(lián)系,即學(xué)習(xí)者在活動(dòng)系統(tǒng)中與環(huán)境中的其他人、物、信息等相互作用,與之周圍的存在物結(jié)成認(rèn)知伙伴關(guān)系(cognite partnership)(Nersessian et M.2003),個(gè)體的學(xué)習(xí)就是在這樣的交互中產(chǎn)生。
(六)學(xué)習(xí)效果的評(píng)價(jià)
學(xué)習(xí)的目的是內(nèi)化以熟練掌握相關(guān)知識(shí)并在真實(shí)的情境中得以應(yīng)用,學(xué)習(xí)效果的認(rèn)定不應(yīng)該像傳統(tǒng)的課堂測(cè)試和基于標(biāo)準(zhǔn)的評(píng)價(jià)測(cè)驗(yàn)?zāi)菢雨P(guān)注學(xué)生對(duì)所授課程內(nèi)容的辨認(rèn)和回憶,因?yàn)槟菢拥脑u(píng)價(jià)既不適合于探測(cè)學(xué)習(xí)者對(duì)知識(shí)的深層理解程度,也難以揭示學(xué)習(xí)者的真實(shí)思維過程和問題解決能力。瑞典的Marton和Salia最早進(jìn)行了對(duì)學(xué)習(xí)的“表層方式”和“深層方式”的研究(Thomas&Nelson,2005),在Ma~on的理論框架中,采用深層方式進(jìn)行學(xué)習(xí)的學(xué)生,對(duì)學(xué)習(xí)有內(nèi)在興趣,注重理解,強(qiáng)調(diào)意義,集中注意于學(xué)習(xí)內(nèi)容各部分之間的聯(lián)系,系統(tǒng)地陳述問題或概念的整體結(jié)構(gòu)的假設(shè)。
“真正的理解,只有當(dāng)學(xué)生在新的或者是未預(yù)料的情境中靈活而恰當(dāng)?shù)剡\(yùn)用知識(shí)和技能的時(shí)候才發(fā)生的”。也就是說,知識(shí)遷移是深層理解的一個(gè)重要特征,有效地運(yùn)用知識(shí)是深層理解的本質(zhì),按照建構(gòu)主義的觀點(diǎn),任何學(xué)習(xí)都是在學(xué)習(xí)者已經(jīng)具有的知識(shí)經(jīng)驗(yàn)和認(rèn)知結(jié)構(gòu)、已獲得的動(dòng)作技能、習(xí)得的態(tài)度等基礎(chǔ)上進(jìn)行的,而這種原有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對(duì)新的學(xué)習(xí)的影響就形成了知識(shí)的遷移。知識(shí)的深層理解意味著學(xué)習(xí)者能夠在不同的情境中順暢、靈活而有效的運(yùn)用習(xí)得的知識(shí),類似“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說法。從個(gè)人的角度來看,知識(shí)是指經(jīng)過檢驗(yàn)的確實(shí)可靠的信念。一般來說,對(duì)于知識(shí)的深層理解也一定與學(xué)習(xí)者的興趣、偏好及家庭背景、所受的教育等有關(guān),個(gè)體對(duì)外部世界的知覺形式、概念歸類及信息處理策略,形成路徑依賴(Dath-dependence)。深層理解的另一個(gè)重要特征是學(xué)習(xí)者能夠在個(gè)人所掌握的知識(shí)的基礎(chǔ)上經(jīng)過重構(gòu)或調(diào)整創(chuàng)造出新的知識(shí)。因此,對(duì)深層學(xué)習(xí)(Deep Learning)效果的評(píng)價(jià),應(yīng)在復(fù)雜情境中設(shè)置有層次的遞進(jìn)式問題間接評(píng)價(jià)、設(shè)置開放的、結(jié)構(gòu)不良的問題進(jìn)行對(duì)知識(shí)和技能要求的深入評(píng)估。
鑒于有效的學(xué)習(xí)通常發(fā)生在復(fù)雜的社會(huì)和技術(shù)環(huán)境中,那么評(píng)估的手法也不應(yīng)單一,考慮多種來自不同學(xué)科(如人類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發(fā)展心理學(xué)等)的評(píng)價(jià)方法的融合,如,民族志、對(duì)話分析、參與觀察等。
四、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方法論
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研究者認(rèn)為,深層學(xué)習(xí)通常發(fā)生在復(fù)雜的社會(huì)和技術(shù)環(huán)境中,為此,學(xué)習(xí)科學(xué)在多重理論基礎(chǔ)的指導(dǎo)下,發(fā)展了一系列新的方法論以及可操作性模式,采用各種方法論的組合來理解、探究學(xué)習(xí)的過程。如認(rèn)知心理學(xué)的實(shí)驗(yàn)研究、教育學(xué)領(lǐng)域的比較實(shí)驗(yàn)、采用社會(huì)學(xué)和人類學(xué)方法論進(jìn)行的社會(huì)交互研究以及一種稱為“設(shè)計(jì)研究”的混合方法論。根植于對(duì)理解“兒童如何思考”這個(gè)問題的持久興趣,在早期皮亞杰的發(fā)生認(rèn)識(shí)論和臨床訪談法、維果茨基的“發(fā)生歷史法”和單元分析方法、杜威實(shí)用主義探究思想的基礎(chǔ)上。基于設(shè)計(jì)的研究過程fDesign-Based Research Collective)已經(jīng)逐漸成為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研究方法,作為方法論的設(shè)計(jì)研究(De.siva Research),在繼承臨床訪談研究的基礎(chǔ)上延伸了教育領(lǐng)域的實(shí)驗(yàn)設(shè)計(jì),尤其是教學(xué)交互研究,旨在提供系統(tǒng)的、有根據(jù)的關(guān)于學(xué)習(xí)的知識(shí),并試圖運(yùn)用建構(gòu)理論來指導(dǎo)和促進(jìn)學(xué)習(xí)的教學(xué)決策(徐曉東,楊剛,2010)。
基于設(shè)計(jì)的研究(DBR)仍然是一種正在發(fā)展中的研究新范式,更多的學(xué)習(xí)科學(xué)家將其看做是“方法論工具箱”,以期通過有效的設(shè)計(jì)改變環(huán)境來研究該環(huán)境中的學(xué)習(xí),通常在自然情境中通過多次迭代循環(huán),采用民族志、會(huì)話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究學(xué)習(xí)者的學(xué)習(xí)過程,以此發(fā)展能推廣到其他學(xué)校和課堂中去的新理論、人工制品和實(shí)踐方案(Barab&Squire,2004)。也即是說,設(shè)計(jì)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滿足當(dāng)時(shí)的需求,重要的是形成一種理論框架,以及揭示、探索和辨別知識(shí)之間的聯(lián)系。
如在“探究亞特蘭蒂斯島”的項(xiàng)目中,根據(jù)角色扮演的在線游戲策略,糅合了商業(yè)游戲策略和教育研究中有關(guān)學(xué)習(xí)和動(dòng)機(jī)的課程,并圍繞教學(xué)中的復(fù)雜問題構(gòu)建“探索”(Ouests)、“使命”(Missions)和“單元”(Units)三種層級(jí)的任務(wù)體系,項(xiàng)目讓用戶在虛擬的環(huán)境參加教育活動(dòng),并與虛擬空間上的其他學(xué)員和教師進(jìn)行交流,建立個(gè)人的形象,逐步讓學(xué)生實(shí)現(xiàn)對(duì)相關(guān)知識(shí)和理念的意義建構(gòu)。“探究亞特蘭蒂斯島”項(xiàng)目最初的設(shè)計(jì),是基于“娛教理論”創(chuàng)設(shè)三維多用戶環(huán)境,結(jié)果當(dāng)時(shí)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大部分的學(xué)生都只是被華麗的在線學(xué)習(xí)環(huán)境吸引,對(duì)活動(dòng)的討論、學(xué)習(xí)及他們所參與的活動(dòng)的類型都知之甚少。后來,Barab等研究者通過實(shí)地走訪師生、分析與學(xué)習(xí)者互動(dòng)日志尋求需要改進(jìn)的因素,不斷嘗試改變?cè)O(shè)計(jì)路線,經(jīng)歷了螺旋上升的迭代修正,明晰了三位一體(教育、娛樂和社會(huì)責(zé)任)的設(shè)計(jì)方案,獲得了良好的社會(huì)反應(yīng)。而設(shè)計(jì)者的思想也經(jīng)歷了多次轉(zhuǎn)變,逐漸將最初的思想發(fā)展為設(shè)計(jì)實(shí)踐的…情境中的理論”,深刻理解了理論與情境的相互作用,以設(shè)計(jì)研究的方法完善了寓教于樂的理論框架。
在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方法論體系中,民族志和會(huì)話分析是最為常用的方法,
(一)民族志
民族志(Ethnographv)是20世紀(jì)初期由文化人類學(xué)家對(duì)其所研究的文化對(duì)象或目的做田野調(diào)查所創(chuàng)立的一種研究方法,需要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對(duì)象所在的特殊的社區(qū)生活中去,從其內(nèi)部著手,通過觀察和體驗(yàn),記錄客觀行為的民族學(xué)描寫,然后對(duì)這些記錄進(jìn)行分析,以期理解和解釋社會(huì)或文化現(xiàn)象,因此。“真實(shí)性”成為民族志研究的核心理念。
在對(duì)“學(xué)習(xí)共同體”進(jìn)行考察時(shí),民族志的方法在記錄一系列的描述性案例顯得很實(shí)用,研究者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與被觀察者進(jìn)行的復(fù)雜互動(dòng)中尋求不同層次的細(xì)節(jié),也可以采用共同體成員交談的影音或記錄來揭示小組成員完成學(xué)習(xí)的
情況。尋找出共同體內(nèi)意義建構(gòu)過程中的重要規(guī)律。從這個(gè)意義上說,民族志方法本身也是一個(gè)知識(shí)生產(chǎn)的過程,包含了長期參與的細(xì)致觀察以及民族志文本的撰寫和記錄,在必要的時(shí)候,民族志方法也可以采用設(shè)計(jì)研究的理念,或者一種混合的研究方法論(Johnson&Onwue uzie,2004)。
如今。互聯(lián)網(wǎng)已成為新的傳播媒介。將人類學(xué)領(lǐng)域的民族志法移植于Web中,基于其多元互動(dòng)及超文本的特點(diǎn),形成虛擬民族志法(Virtual Ethnographv)(孫建軍,2009),是民族志方法在網(wǎng)絡(luò)中的延伸。所以,網(wǎng)絡(luò)共同體內(nèi)部,來自不同地域的學(xué)習(xí)者進(jìn)行共同主題下的學(xué)習(xí),即使是兒童,他們也會(huì)通過觀察、提問或參與某些活動(dòng)來進(jìn)行主動(dòng)學(xué)習(xí),對(duì)學(xué)習(xí)者與他人日常交互進(jìn)行民族志研究,有助于了解學(xué)習(xí)者在共同體內(nèi)推進(jìn)自身發(fā)展的過程和方式,筆者在進(jìn)行的基于網(wǎng)絡(luò)的校際協(xié)作學(xué)習(xí)的實(shí)踐中,通過提供較為有效地技術(shù)環(huán)境支持,參與者逐漸構(gòu)建起具有共同性、建構(gòu)性為學(xué)習(xí)活動(dòng)特征的“網(wǎng)絡(luò)學(xué)習(xí)共同體”,采用虛擬民族志法參與觀察和交互活動(dòng),對(duì)成功的學(xué)習(xí)活動(dòng)進(jìn)行記錄、歸納和分析,發(fā)現(xiàn)學(xué)習(xí)主題共同性基礎(chǔ)上的“差異”(反映出社會(huì)和自然的屬性)是校際網(wǎng)上協(xié)作的重要資源和深層學(xué)習(xí)的出發(fā)點(diǎn),這樣“基于差異的學(xué)習(xí)”逐漸在網(wǎng)絡(luò)共同體內(nèi)清晰起來,成為開展校際學(xué)習(xí)活動(dòng)的重要指導(dǎo)策略。
(二)會(huì)話分析
始于20世紀(jì)60年代社會(huì)學(xué)領(lǐng)域的會(huì)話分析方法(con―versation analysis.CA).現(xiàn)已成為研究“互動(dòng)中的言談”常用的,實(shí)證研究分析方法。在教育領(lǐng)域,關(guān)于會(huì)話的早期研究關(guān)注在課堂中發(fā)生的師生會(huì)話,第一個(gè)對(duì)課堂會(huì)話進(jìn)行錄音并轉(zhuǎn)錄的研究出現(xiàn)在美國學(xué)者貝拉克(ABellack)在1966年出版的《課堂語言》一書中,該研究采用話輪轉(zhuǎn)換(interactional turns)來分析課堂會(huì)話,即首先把會(huì)話分割成話輪,然后對(duì)每個(gè)話輪進(jìn)行分析編碼。來分析課堂結(jié)構(gòu)和教學(xué)方式。
自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教育研究者開始研究協(xié)作學(xué)習(xí)中的會(huì)話交互(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出現(xiàn)了不同的研究流派,其中,社會(huì)文化流派最為重視協(xié)作中的會(huì)話研究,他們結(jié)合皮亞杰的認(rèn)知沖突理論及維果茨基的社會(huì)文化理論,強(qiáng)調(diào)“知識(shí)(意義)是在社會(huì)情境中通過話語交互共同建構(gòu)的”。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關(guān)注協(xié)作學(xué)習(xí)中發(fā)生的會(huì)話交互,會(huì)話分析研究的語料完全來自于自然發(fā)生的會(huì)談,研究者們采用錄音或錄像的方法如實(shí)記錄包含開端、發(fā)展及結(jié)尾的整體的會(huì)話過程,通過轉(zhuǎn)錄(transeription)捕捉文字所不能提供的信息,如在基于項(xiàng)目的協(xié)作學(xué)習(xí)中,成員之間在協(xié)商問題解決時(shí)的談話語氣、停頓、中斷以及重疊性的話語等現(xiàn)象所隱含的信息,可探測(cè)成員在共同體內(nèi)的角色地位、認(rèn)知程度及覺知(awareness)水平。
筆者在對(duì)基于網(wǎng)絡(luò)校際協(xié)作學(xué)習(xí)進(jìn)行知識(shí)建構(gòu)的效果分析的研究中,從共同體內(nèi)成員的參與程度、話題集中程度、交互程度、觀點(diǎn)多寡、協(xié)調(diào)結(jié)果,知識(shí)共享程度等方面進(jìn)行考察,在借鑒Robert Heckman和Hala Annabi(2002)的內(nèi)容分析表(Content Analytic Scheme)的基礎(chǔ)上,制作了一個(gè)“協(xié)作呈現(xiàn)(Collaboration Presence)”的標(biāo)示器(Marker),據(jù)此可以將對(duì)話分析得到的數(shù)據(jù)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較為客觀地把握成員在協(xié)作過程中知識(shí)理解和建構(gòu)的過程。
五、發(fā)展中的學(xué)習(xí)科學(xué)
(一)走向協(xié)同的學(xué)習(xí)科學(xué)
索耶在2006年主編的《劍橋?qū)W習(xí)科學(xué)手冊(cè)》中,列舉了跨學(xué)科的學(xué)習(xí)科學(xué)所關(guān)注的學(xué)習(xí)的基本問題,即概念理解、教與學(xué)并重、學(xué)習(xí)環(huán)境創(chuàng)設(shè)、原有知識(shí)及反思與學(xué)習(xí),對(duì)這些問題的研究分布在內(nèi)隱學(xué)習(xí)與大腦、非正式學(xué)習(xí)、正式與非正式學(xué)習(xí)的設(shè)計(jì)這三條相對(duì)獨(dú)立的研究主線中,并指出未來的學(xué)習(xí)科學(xué)將整合神經(jīng)和行為層面的學(xué)習(xí),自然促使內(nèi)隱的、非正式和正式學(xué)習(xí)活動(dòng)及其成果的整合。但并不意味著各自研究領(lǐng)域獨(dú)特觀點(diǎn)的消解,甚至所有這三條研究主線都試圖用各自獨(dú)特的研究工具探究并解決類似的問題,這些超越個(gè)人層面研究取向的不同觀點(diǎn)的彼此交叉和影響呈現(xiàn)出研究觸角多元兼及的狀態(tài),并在這樣的融合中,可能會(huì)形成更有用的理論來解釋人類的學(xué)習(xí)。
如前所述,走向協(xié)同的學(xué)習(xí)科學(xué),得益于其豐厚的學(xué)科基礎(chǔ),比如發(fā)展神經(jīng)學(xué)對(duì)于大腦的研究中,解釋“大腦如何在交互中發(fā)展”等相關(guān)成果,有助于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研究者們更好的理解學(xué)習(xí)的內(nèi)在機(jī)制,或者提出更為合理的學(xué)習(xí)策略。總之,學(xué)習(xí)科學(xué)越來越具有生態(tài)學(xué)的理念:“沒有孤立的存在”。
(二)從“如何學(xué)”到“學(xué)什么”
這個(gè)觀點(diǎn)的提出或許能引發(fā)一些批判的聲音,因?yàn)橥ǔ5目磥恚鐣?huì)及人類發(fā)展決定著其成員學(xué)習(xí)的內(nèi)容,而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工作應(yīng)該是促進(jìn)人們更好更快地掌握這些內(nèi)容,其研究的重點(diǎn)聚焦于“如何學(xué)”。比如在《人是如何學(xué)習(xí)的》一書中,從大腦、心理、經(jīng)驗(yàn)及學(xué)校等多個(gè)視角,探索采用更好的教學(xué)來讓學(xué)習(xí)者掌握盡可能多的知識(shí),被很多的研究者視為里程碑式的著作。即使如此,該書中仍不否認(rèn)“即使是嬰幼兒也可以進(jìn)行富有成效的學(xué)習(xí)”,而作者本身對(duì)當(dāng)前的學(xué)校教育狀況也并不樂觀。
教育者們常常將“素養(yǎng)”作為學(xué)習(xí)者知識(shí)獲得和增長的評(píng)價(jià)維度,在網(wǎng)絡(luò)和信息通信技術(shù)日益發(fā)展的今天,現(xiàn)代教育必將賦予素養(yǎng)新的內(nèi)涵,學(xué)習(xí)科學(xué)視域下的素養(yǎng)觀將更加關(guān)注特定社會(huì)文化境脈中的真實(shí)性實(shí)踐。一個(gè)典型的現(xiàn)象是:計(jì)算機(jī)已經(jīng)較為普遍的應(yīng)用到學(xué)校的教育中,但兒童們發(fā)現(xiàn)學(xué)校使用計(jì)算機(jī)的方式與越來越數(shù)字化的社會(huì)中的行事方式并不一樣:而且高校中越來越多的學(xué)生宣稱他們所學(xué)的知識(shí)與現(xiàn)實(shí)生活并不相關(guān),新的“讀書無用論”抬頭,“學(xué)無力”在學(xué)生中蔓延。然而與之對(duì)應(yīng)的事實(shí)是:他們?cè)趯W(xué)習(xí)復(fù)雜的電腦游戲時(shí)并不無力。因此,僅僅通過一些手段或策略教會(huì)學(xué)生如何正確理解知識(shí)是不夠的,還應(yīng)該通過變革教和學(xué)的內(nèi)容來改變這樣的現(xiàn)象。
俗話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學(xué)習(xí)者對(duì)某領(lǐng)域或?qū)W科的愛好可以轉(zhuǎn)化成令人吃驚的學(xué)習(xí)意愿,然而,太多的教育者將精力與金錢投入到膚淺的甚至是弄巧成拙的嘗試上,比如將兒童們不喜歡的內(nèi)容嵌入到游戲中以試圖吸引他們學(xué)習(xí),這種類似“愚弄”的手段真的不高明,教育者需要做的不是給學(xué)生們?cè)鲪旱膶W(xué)科知識(shí)裹上糖衣,而是要站在學(xué)生的角度,為他們提供他們喜愛的內(nèi)容。這肯定會(huì)有難度,但首先是一個(gè)認(rèn)識(shí)上的轉(zhuǎn)變,那就是“與其讓學(xué)生學(xué)習(xí)他們?cè)鲪旱臄?shù)學(xué),不如讓他們開發(fā)自己喜歡的數(shù)學(xué)”,可以設(shè)想交給學(xué)生方法,引導(dǎo)學(xué)生去創(chuàng)設(shè)自己喜歡的個(gè)性化的數(shù)學(xué)。或許,這是學(xué)習(xí)科學(xué)研究者不久的未來將非常關(guān)切的事情,試想在賦予學(xué)生自由的、無限開放的環(huán)境中用自己獨(dú)特的方法建構(gòu)自己的知識(shí),或與同伴或與團(tuán)隊(duì)進(jìn)行著自己的學(xué)習(xí),這將是多么讓人激動(dòng)的場(chǎng)景。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發(fā)展必將帶來學(xué)習(xí)新的革命,或許,不遠(yuǎn)的將來,學(xué)校不再扮演選拔學(xué)生的工具的角色,而,是面向知識(shí)社會(huì)的需求。在真實(shí)有意義的情境中重構(gòu)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知識(shí)體系、評(píng)估體系及組織方式。
第9篇: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重要性范文
關(guān)鍵詞:美國 民族政策 一體 多元
美國既是一個(gè)移民大國,也是一個(gè)多種族、多民族的國家。盡管有許多人基于美國的民族構(gòu)成與社會(huì)趨勢(shì)的變化而對(duì)美國能否保持國家特性不斷發(fā)出警告,但在因民族主義風(fēng)起云涌而導(dǎo)致世界民族問題叢生的后冷戰(zhàn)時(shí)期,美國卻沒有出現(xiàn)太大的民族問題。這種狀況在相當(dāng)大的程度上可以歸因于美國民族政策的成功。然而,對(duì)當(dāng)代美國民族政策的肯定并不能否認(rèn)歷史上美國在處理民族問題上出現(xiàn)的諸多錯(cuò)誤。
在美國的民族關(guān)系史上,充斥著移民群體、移民與印第安人、美國人與黑人奴隸及其后裔、美國主流社會(huì)與其他移民之間的沖突和斗爭(zhēng)。僅以美國政府處理印第安人問題的歷史為例,為了獲得印第安人的土地,確立起美國在這塊土地上的,美國政府曾通過屠殺、驅(qū)逐、隔離、同化、有限自治等方式對(duì)印第安人實(shí)施統(tǒng)治,使他們淪為自己土地上“最為悲慘的人群”。誠如有人所指出的:“美國歷史形成的經(jīng)驗(yàn)是,對(duì)土著美國人進(jìn)行長期戰(zhàn)爭(zhēng)。這一事實(shí)又繼而產(chǎn)生了美國人的形象,不是作為劊子手,而是一個(gè)‘新興的民族。這個(gè)民族沒有繼承人類的罪惡遺產(chǎn),而是作為獵手、開拓者、先驅(qū)與探索者尋求全新、有原創(chuàng)力的與純粹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對(duì)于其他非盎格魯一撒克遜民族或移民及其后裔,美國政府也長期沒有賦予他們美國憲法規(guī)定的“每個(gè)公民生而平等”的地位。這也是相當(dāng)長一段時(shí)間內(nèi)美國民族問題層出不窮的原因。
20世紀(jì)60-70年代,環(huán)境保護(hù)運(yùn)動(dòng)、同性戀運(yùn)動(dòng)、少數(shù)民族爭(zhēng)取權(quán)利運(yùn)動(dòng)與其他民眾運(yùn)動(dòng)一道,以巨大的能量沖擊了歐、美國家,使它們意識(shí)到本國弱勢(shì)群體維護(hù)自身權(quán)利與平等地位的強(qiáng)烈愿望和訴求。在美國,由馬丁?路德?金領(lǐng)導(dǎo)的黑人維權(quán)運(yùn)動(dòng)與印第安人發(fā)起的爭(zhēng)取“紅種人的權(quán)利”(Red Power)運(yùn)動(dòng)等形成了巨大的合力,共同推動(dòng)了美國民族政策的轉(zhuǎn)變。此后,美國歷屆政府被迫對(duì)其民族政策進(jìn)行了大幅度的調(diào)整,從而逐漸形成了目前以開放型、多元性、包容性為特征的民族政策。其核心原則是:美國國內(nèi)各民族享有基于憲法規(guī)定的平等的個(gè)人權(quán)利,但作為一個(gè)群體的少數(shù)民族不能要求特殊權(quán)利(印第安人除外);各民族文化可以在統(tǒng)一的美利堅(jiān)國家認(rèn)同下得到保護(hù),但各民族成員對(duì)其權(quán)利的要求不能違背構(gòu)建美國公民國家的目標(biāo)。在這種民族政策的大框架下,盡管在美國仍時(shí)有民族問題發(fā)生,有時(shí)甚至演變成極為激烈的社會(huì)矛盾,但總體上而言,20世紀(jì)60年代以來的美國政府在處理民族問題上還是較為成功的。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民族政策的形成和實(shí)施都是建立在該國歷史、人文、政治等國情基礎(chǔ)之上的。就此而言,對(duì)美國民族政策應(yīng)先重于研究、分析,后慎于借鑒。
一、美國的民族與民族政策概況
1997年美國管理與預(yù)算辦公室(OMB)確立了新的種族分類,將美國的種族分為5大類:白人、非洲裔美國人、亞洲裔美國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夏威夷及其他太平洋島民。另外,美國人口普查局還設(shè)立了一個(gè)特別的分類“其他種族”,2000年的人口普查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允許答卷者選擇一個(gè)以上的種族歸屬。
到2006年10月,美國的人口已經(jīng)突破3億,成為世界上第三人口大國。根據(jù)2000年人口普查的數(shù)據(jù),當(dāng)時(shí)美國的人口總數(shù)為2.814億,其種族構(gòu)成是:白人占75.1%,非洲裔美國人占12.3%,亞洲裔美國人占3.6%,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占0.9%,夏威夷及其他太平洋島民占0.1%,其他種族的人占5.5%;歸屬兩個(gè)以上種族的人占2.5%。談及美國的種族構(gòu)成,不可忽視西班牙語裔美國人,其又被稱為拉丁美洲裔美國人,主要指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古巴裔和其他中南美洲裔的美國人。雖然它并非美國聯(lián)邦種族標(biāo)準(zhǔn)中的一類,但美國人口普查局在統(tǒng)計(jì)中將其單列出來,可見該種族的重要性。
美國的民族政策是以聯(lián)邦憲法、聯(lián)邦法律、州法律、總統(tǒng)行政命令、法院判例為基礎(chǔ)組成的。美國的聯(lián)邦憲法規(guī)定了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則,憲法及其修正案具有最高的權(quán)威,任何具體的民族政策都不能與之相沖突,否則會(huì)因違憲而被取消。美國最高法院有解釋憲法的權(quán)力,作為判例法國家,美國最高法院的案例對(duì)其他同類案件都是適用的。美國是一個(gè)依法治國的國家,許多民族政策是由聯(lián)邦和各州的立法部門通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名義頒布和執(zhí)行的。由于美國的憲法僅是簡明地確立了核心原則,所以立法部門頒布的相關(guān)法律成為針對(duì)美國民族問題的具體而詳盡的政策。美國總統(tǒng)也可以根據(jù)形勢(shì)的需要,通過總統(tǒng)令的方式制定具體的民族政策。總統(tǒng)的行政命令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可以應(yīng)對(duì)隨時(shí)出現(xiàn)的民族問題。美國民族政策的穩(wěn)定性表現(xiàn)在其制定和實(shí)施始終保持延續(xù)性,不斷為自由、開放的民族格局的形成與發(fā)展提供法律根據(jù)。
應(yīng)該看到,美國的民族政策一直在不斷修訂和完善。美國雖然早在《獨(dú)立宣言》中就已宣稱“人生而平等”,但在較長的歷史時(shí)期里,該國一直奉行歧視性的民族政策。如對(duì)黑人實(shí)行奴隸制和種族隔離政策,對(duì)印第安人實(shí)行驅(qū)趕和屠殺政策,對(duì)亞裔和其他民族實(shí)行排斥政策,等等。針對(duì)美國政府的歧視性民族政策,美國人民,特別是少數(shù)民族掀起了不屈不撓的反對(duì)種族滅絕、種族隔離、種族歧視和種族偏見的斗爭(zhēng)。尤其是在20世紀(jì)60年代,美國少數(shù)民族掀起了大規(guī)模的民權(quán)運(yùn)動(dòng),強(qiáng)烈沖擊了美國的歧視性民族政策體系。在外部和內(nèi)部壓力下,美國政府或主動(dòng)或被動(dòng)地對(duì)民族政策進(jìn)行了調(diào)整和完善,使其從“白人至上”到“熔爐”同化,直至當(dāng)代的“一體”與“多元”的平衡。
當(dāng)然,當(dāng)代美國的民族政策并沒有解決其境內(nèi)的所有民族問題。久積成習(xí)的“白人至上”的歧視心理事實(shí)上仍在影響著美國的白人階層和上層精英,美國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痼疾仍根深蒂固,亞裔人、黑人、印第安人仍然處于被歧視的境地。但是,美國政府通過維護(hù)“一體”與“多元”平衡的民族政策,基本上保持了民族關(guān)系的相對(duì)平穩(wěn),這正是本文所要關(guān)注和分析的問題。
二、當(dāng)代美國民族政策的特征
(一)美國法律對(duì)少數(shù)民族成員平等權(quán)利的規(guī)定
雖然美國是一個(gè)多民族國家,但它只承認(rèn)和保護(hù)個(gè)人的權(quán)利而非民族的權(quán)利(惟一例外的是印第安人)。早在《獨(dú)立宣言》中,美國就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nèi)舾刹豢蓜儕Z的權(quán)利,其中包括生命權(quán)、自由權(quán)和追求幸福的權(quán)利”。盡管在美利堅(jiān)合眾國建立初期,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隸在當(dāng)時(shí)尚無享有公民權(quán)的資格,但在美國的實(shí)際生活中,已經(jīng)成為合眾國 公民的這些“不可剝奪”的權(quán)利還是得到了切實(shí)的維護(hù)與弘揚(yáng)。對(duì)個(gè)人權(quán)利的尊重成為“美國精神”的一個(gè)重要原則,并逐漸演變?yōu)橐詡€(gè)人至上主義為特征的美國文化。與對(duì)個(gè)人權(quán)利的強(qiáng)調(diào)相對(duì)比,那些以個(gè)人為基礎(chǔ)但又不同于個(gè)體的群體(包括民族)的權(quán)利并未得到美國法律的強(qiáng)調(diào)。所以,美國在法律上所宣稱的平等和其他權(quán)利只屬于個(gè)人,屬于個(gè)體的美國人,而不屬于各個(gè)民族。簡單地說,就是美國法律承認(rèn)作為“美國人”的權(quán)利,而不是“日裔美國人”、“德裔美國人”等作為民族群體的權(quán)利。“美國信條構(gòu)想的是一個(gè)由自己選擇并對(duì)自己負(fù)責(zé)的個(gè)人組成的國家,而不是一個(gè)以不可侵犯的民族社團(tuán)為基礎(chǔ)的國家。憲法保障的是個(gè)人的權(quán)利而不是群體的權(quán)利。”美國在議會(huì)中并不實(shí)行按民族配額的代表制。1787年憲法第一條明確規(guī)定:“眾議員人數(shù)及直接稅額,應(yīng)該按聯(lián)邦所轄各州的人口比例分配。”這一憲法條款否定了眾議員按民族配額的可能,各個(gè)民族要求的“民族權(quán)利”便沒有了法律依據(jù),這就保證了各個(gè)民族不會(huì)以“民族權(quán)利”而要求自治。
平等權(quán)。美國憲法第13修正案(1865年)、第14修正案(1866年)、第15修正案(1869年),都是美國南北戰(zhàn)爭(zhēng)后給黑人以公民權(quán)的憲法保障。美國憲法第13修正案規(guī)定,在合眾國境內(nèi)或受合眾國管轄的任何地區(qū)內(nèi),除了用以懲罰已正式定罪的罪犯外,不準(zhǔn)有奴隸制度或強(qiáng)迫勞役的存在。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第一款規(guī)定,凡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于合眾國而受其管轄的人,皆為合眾國及其所居住州的公民;眾議院議員人數(shù),按各州人口數(shù)量分配(黑人人口不再按3/5來計(jì)算;不納稅的印第安人除外)。這使得黑人也被包括在“出生或歸化”于美國的人之內(nèi),被賦予了公民權(quán)。美國憲法第15修正案規(guī)定,合眾國或任何一州對(duì)于合眾國公民的投票權(quán),不得因種族、膚色或曾為奴隸而拒絕或剝奪之。由此可見,這三個(gè)修正案使美國聯(lián)邦政府解放奴隸的政策憲法化,以憲法形式保障了黑人的平等公民權(quán)。
選舉權(quán)。20世紀(jì)50、60年代,美國政府通過《民權(quán)法》重點(diǎn)保護(hù)少數(shù)民族的選舉權(quán)。1957年美國國會(huì)通過了由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提出的20世紀(jì)“第一項(xiàng)全面的民權(quán)法案”,該法案授權(quán)聯(lián)邦政府可在公民選舉權(quán)被剝奪或受到威脅時(shí)以政府的名義提出訴訟。1960年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簽署了一部《民權(quán)法》,規(guī)定允許聯(lián)邦政府向一些有明顯種族歧視的地區(qū)派遣仲裁員,以監(jiān)督選民登記。1964年的《民權(quán)法》全面禁止法律上的種族歧視行為和種族隔離政策,并保證每個(gè)公民都享有選舉權(quán)。1965年,約翰遜總統(tǒng)簽署了20世紀(jì)的第四部《民權(quán)法》,該法又稱《選舉權(quán)法》,它廢除了在美國南方執(zhí)行了半個(gè)多世紀(jì)的投票前對(duì)少數(shù)民族特別是對(duì)黑人實(shí)行的文化知識(shí)測(cè)試制度,該法還禁止其他任何歧視黑人選舉權(quán)的行為。
就業(yè)權(quán)。經(jīng)過修訂后的1964年《民權(quán)法》涵蓋了聯(lián)邦、州和地方政府以及教育機(jī)構(gòu)、就業(yè)機(jī)構(gòu)和工會(huì),以及有15名以上雇員的雇主,禁止他們以種族、膚色、宗教、原國籍和性別為由在利用公共設(shè)施與服務(wù)(第二款)、聯(lián)邦政府資助項(xiàng)目(第六款)和雇工(第七款)時(shí)有歧視行為。根據(jù)該法還成立了美國平等就業(yè)委員會(huì)(EEOC),負(fù)責(zé)第七條款的實(shí)施。1965年,美國政府的11246號(hào)行政令亦禁止就業(yè)歧視,并在勞工部中成立了聯(lián)邦承包標(biāo)準(zhǔn)計(jì)劃辦公室(OFCCP)來實(shí)施該條款。1978年8月美國政府實(shí)施了《選拔雇員程序的統(tǒng)一指導(dǎo)方針》,其關(guān)鍵點(diǎn)是:“對(duì)受第七款制約的公司所實(shí)行的招聘考試來說,如果任何一種族、民族或性別群體的招聘率低于最成功群體招聘率的4/5,這一考試將被視為對(duì)該群體造成了有害的后果。”1984年美國民權(quán)委員會(huì)提出,反對(duì)在招工時(shí)實(shí)行配額制度。1987年美國最高法院裁決,支持優(yōu)先雇用少數(shù)民族成員,但反對(duì)率先解雇白人。
美國的民族問題主要涉及各民族的權(quán)利平等問題,尤其在教育、就業(yè)等方面。總體上而言,美國最高法院在平等權(quán)方面的判例中,維護(hù)了美國憲法所宣揚(yáng)的民族平等原則。
教育方面。在這方面最為著名的判例是1954年的“布朗案”。在該案中,美國最高法院了“隔離但公平”的普萊西原則,裁定種族隔離教育制度違憲,予以廢除。1957年,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公開抵制美國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所做的裁定,并引發(fā)嚴(yán)重沖突。最后,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下令派軍隊(duì)維持那里的秩序。這就是“小石城”事件。1964年的《民權(quán)法》被通過后,為加快種族合校的進(jìn)程,美國最高法院先后要求取消明顯帶有種族歧視傾向的“黑、白雙軌制”學(xué)校,并規(guī)定各學(xué)校中黑人學(xué)生須占一定的比例,以實(shí)現(xiàn)“黑、白”合校。1971年,美國最高法院還要求各學(xué)校使用交通工具,以解決“黑、白”合校中出現(xiàn)的學(xué)生上學(xué)困難的問題。
就業(yè)方面。1964年的《民權(quán)法》第七款特別說明,禁止給予任何個(gè)人或團(tuán)體以優(yōu)惠待遇。在1979年的“鋼鐵工會(huì)訴韋伯案”中,美國最高法院解釋了該法第七款的含義:如果以前不存在歧視,政府就不能要求有關(guān)機(jī)構(gòu)給予黑人以優(yōu)待。在1984年的“消防隊(duì)員訴斯考茨案”中,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在裁員問題上,黑人并不能得到照顧。
美國國會(huì)在20世紀(jì)70年代通過法律規(guī)定,如果白人所控公司在聯(lián)邦政府資助的工程項(xiàng)目招標(biāo)時(shí)中標(biāo),必須把工程總值的lO%部分轉(zhuǎn)包給少數(shù)民族所控公司。這一做法在1980年的“富利洛夫訴克盧茨尼克案”中,被最高法院裁定為合法,因?yàn)橛写罅康淖C據(jù)證明少數(shù)民族企業(yè)過去被取消了有效參與公共工程承包的機(jī)會(huì)。
婚姻方面。1958年,弗吉尼亞州的黑人杰特和白人洛芙英的婚姻被弗吉尼亞州認(rèn)為違反了該州禁止種族之間(白人同有色種人之間)通婚的法律。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弗吉尼亞州的做法違反了憲法第14修正案,并裁定:根據(jù)聯(lián)邦憲法,同一個(gè)與自己不同種族的人婚嫁與否,完全取決于個(gè)人意愿,州政府無權(quán)干涉。
住房方面。美國最高法院在1948年“謝利訴克萊莫案”的判決中宣布,禁止實(shí)行限制黑人購買某些街區(qū)地產(chǎn)的“住房買賣限制協(xié)議”,由此從法律上廢止了居住隔離制度。1968年,美國國會(huì)通過了20世紀(jì)的第五部《民權(quán)法》,規(guī)定在房屋出售和出租時(shí)實(shí)行種族歧視為非法。
公共場(chǎng)所。1950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在鐵路餐車中實(shí)行種族隔離違憲。1955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在公園、運(yùn)動(dòng)場(chǎng)、公共高爾夫球場(chǎng)中實(shí)行種族隔離為非法。1956年,美國最高法院判定阿拉巴馬州法律中在公交車上實(shí)行隔離的規(guī)定違憲。1964年的《民權(quán)法》規(guī)定,在公共場(chǎng)所廢除種族隔離制并禁止對(duì)黑人實(shí)行種族歧視。
從上述基于憲法的判例可以看到,美國以法律的手段逐步消除或減少了種族之間的權(quán)利不平等,使少數(shù)民族作為美國公民個(gè)體的權(quán)利逐漸趨同。當(dāng)然,美國在實(shí)現(xiàn)各民族權(quán)利平等方面并非一帆風(fēng)順,這和一些美國人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觀念有關(guān)。美國最高法院在涉及“肯定性行動(dòng)”(Affirmative Action,過去國內(nèi)譯作“反歧視積極行動(dòng)”或“平權(quán)措施”)中對(duì)少數(shù)民族的保護(hù)和一些白人提出的“反向歧視”問題時(shí),雖總體上維護(hù)了民族權(quán)利平等的原則,但其態(tài) 度的日趨軟化是顯而易見的。
(二)美國法律拒絕賦予少數(shù)民族以群體權(quán)利
根據(jù)哈貝馬斯的“新型歸屬感”理論,“新型歸屬感”不是基于共同體內(nèi)人們的族裔世系的一致性,而是通過對(duì)公民個(gè)人權(quán)利和自由的法理建構(gòu)而營造出公民對(duì)國家共同體的認(rèn)可。這種“公民國家”模式不是以族屬特征而是以公民資格作為對(duì)共同體成員角色定位的核心依據(jù)。在實(shí)現(xiàn)從“民族國家”向“公民國家”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換中,人們的“民族”意識(shí)逐步轉(zhuǎn)變,不再只注重血緣、文化屬性,而是強(qiáng)調(diào)公民共同實(shí)踐政治權(quán)利的公民意志。
在美國,由于缺乏界定傳統(tǒng)民族性的基礎(chǔ)(如共同的族裔世系、共同的歷史背景等),因而“民主式的政治體制便取而代之成為了界定國家整體特性的基礎(chǔ)”。美利堅(jiān)共同體的構(gòu)建經(jīng)驗(yàn)包括:民族聚落與政治構(gòu)建的分離、政治整合與民族同化的共進(jìn)。
第一,非民族聚居的聯(lián)邦制。美國聯(lián)邦制的特點(diǎn)是,聯(lián)邦單位的權(quán)利不以民族為單位,聯(lián)邦單位的自治權(quán)是建立在地域基礎(chǔ)之上的,而非建立在民族聚居原則基礎(chǔ)之上。蘇聯(lián)、南斯拉夫等以民族地域?yàn)閱挝坏穆?lián)邦制的解體說明,在民族矛盾尖銳的國家中實(shí)行民族聯(lián)邦制并不一定有利于多民族國家的統(tǒng)一和國家凝聚力的增強(qiáng)。由于整個(gè)政權(quán)體制(如眾議院、參議院議員的席位,總統(tǒng)選舉中的選舉人團(tuán)制度等)都與各地域單位(州)密切聯(lián)系,所以美國的這種聯(lián)邦制也從根本上否定了以民族地域?yàn)閱挝粚で竺褡鍣?quán)利的可能。美國的聯(lián)邦機(jī)制還成功地將多元化的地域利益納入一個(gè)具有包容性的規(guī)則體系中,不但成為地域利益政治表達(dá)均衡性的保障,也成為美利堅(jiān)共同體一體化進(jìn)程的動(dòng)力,更成為美國民族整合的重要制度基礎(chǔ)。而且,美國這一共同體并非由一個(gè)中央權(quán)威通過殘酷的武力征服來實(shí)現(xiàn)的,而是由不同的相對(duì)獨(dú)立的政治自治單位自愿合并而成的。這使得美國的聯(lián)邦制沒有某些國家內(nèi)部單位的那種歷史積怨,聯(lián)邦各單位的關(guān)系更容易協(xié)調(diào)。對(duì)于不同聯(lián)邦單位屬下的民族成員來說,美國的建國歷史并非像許多歐洲國家的原始擴(kuò)張那樣血腥殘忍,所以美國政府更容易構(gòu)建他們對(duì)國家的認(rèn)同感和歸屬感。而保證各地域單位的利益平等,成為維系美國聯(lián)邦制的制度框架。
第二,美國對(duì)于在大民族體下出現(xiàn)的小民族體的限制和防范是一向嚴(yán)于其他國家的。民族居住的地理分布情況是誘發(fā)民族問題的一個(gè)不可回避的因素。加拿大的魁北克民族問題就是因?yàn)榉ㄒ嵩诳笨说貐^(qū)的絕對(duì)集中而引發(fā)的。正如亨廷頓所言:“當(dāng)文化的差異和地理位置的差異重合時(shí),可能就會(huì)出現(xiàn)暴力、自治或分離運(yùn)動(dòng)。”從美國憲法到一般性的地方政策,都反對(duì)將民族聚落模式地域化,以及任何試圖以民族單位為基礎(chǔ)建立政治實(shí)體的努力。也就是說,美國不僅不允許各民族集團(tuán)在美國的土地上獨(dú)居一地以實(shí)行民族自治,而且任何民族集團(tuán)在政治上不被授予任何的認(rèn)可和正式的身份(因歷史原因,印第安人除外)。這是一種體現(xiàn)開放價(jià)值觀的民族政策,它基本上剔除了偏狹的民族主義以地域操縱人們思想、行為的可能性,讓各民族人民生活在開放的社會(huì)中,根據(jù)自己的競(jìng)爭(zhēng)能力來適應(yīng)美國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地域和社會(huì)流動(dòng)。
第三,對(duì)不同種族的經(jīng)濟(jì)、語言、文化整合與構(gòu)筑國族認(rèn)同。“從根本上講,文化的問題還需要從經(jīng)濟(jì)上來解決,美利堅(jiān)合眾國的合眾為一首先是經(jīng)濟(jì)上的一體。”國家的統(tǒng)一和高度發(fā)達(dá)的資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是美國民族同化和一體化的強(qiáng)勁推力。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機(jī)制沖垮了封閉的地域交換方式和死板的行會(huì)體制及社會(huì)升遷框架,形成了人員的地域混雜和社會(huì)流動(dòng),從而自然侵蝕著民族集團(tuán)的族體民族特性。同時(shí),經(jīng)濟(jì)因素對(duì)于一個(gè)國家內(nèi)各民族間聯(lián)系的加強(qiáng)和內(nèi)聚力的形成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現(xiàn)代社會(huì)維系國內(nèi)各個(gè)民族聯(lián)系的主要因素是經(jīng)濟(jì),只有建立在密不可分的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基礎(chǔ)上的民族關(guān)系才是最牢固的。”將不同的個(gè)體、民族和地區(qū)利益納入國族經(jīng)濟(jì)的主導(dǎo)框架,正是美國孕育人們共同體意識(shí)的關(guān)鍵所在。當(dāng)然,美國高度發(fā)達(dá)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和傲視全球的綜合國力,成為保障國內(nèi)民族關(guān)系穩(wěn)定的最重要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正如亨廷頓所言:“美國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和財(cái)富的成倍增長,造成了人們對(duì)自己國家的自豪。”
共同的語言能夠促進(jìn)人們之間觀念和情感的交流,它比純粹先天性的血緣紐帶更能強(qiáng)化人們?cè)谡J(rèn)識(shí)和道德方面的一致性。而在由不同族源的群體組成的現(xiàn)代國家中,語言的差異成為阻礙不同民族之間實(shí)現(xiàn)彼此認(rèn)同的主要障礙之一。考察美國的情況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雖然它擁有眾多的民族,但在語言方面卻有著高度的統(tǒng)一性:英語為通用語。人口的高流動(dòng)性推動(dòng)了美國地方方言的整合,而遍布美國各地的公共教育設(shè)施不僅促進(jìn)了英語作為通用語言本身的標(biāo)準(zhǔn)化,而且為外來移民的語言同化提供了保障。當(dāng)然,英語是美國的國語,其一致性并不意味著只有英語一種語言存在。
在一個(gè)多民族、多文化的國家中,營造一定程度的價(jià)值共識(shí)是凝聚人心、化解各種文化沖突的關(guān)鍵所在。這種共識(shí)不僅構(gòu)成一個(gè)社會(huì)中人們行為的共同理念基礎(chǔ),而且是一個(gè)政治共同體最根本的維系力量。美國通過“美國化”運(yùn)動(dòng)使移民逐漸融入了主流文化,但更重要的是把是否認(rèn)同普世性的美國自由主義政治原則和政治理想作為美國人身份的主要標(biāo)志。無疑,自由、平等、個(gè)人主義、平民主義等是美國建國以來奉行的一整套普世的思想和原則,利普塞特(Lipset)稱之為“美國信念”。“美國信念”使美國各民族集團(tuán)的基本價(jià)值體系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而這種高度同一的價(jià)值體系成為美國塑造國家民族認(rèn)同的最主要的內(nèi)核。對(duì)以“盎格魯一新教”(WASP)文化為傳統(tǒng)、以“平等、自由”為內(nèi)涵的“美國信條”的強(qiáng)調(diào)與鞏固,就成了美國政黨及政府塑造共同信念的一種手段。
當(dāng)然,美國文化基于科技實(shí)力的技術(shù)先進(jìn)性和基于體制基礎(chǔ)的創(chuàng)新性,為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發(fā)展動(dòng)力與對(duì)移民亞文化的吸引力。美國文化的普世性和對(duì)各民族群體的潛移默化,為統(tǒng)一的國家意識(shí)的構(gòu)建和維護(hù)提供了堅(jiān)實(shí)的文化基礎(chǔ)。而脫離母國本土的移民亞文化的弱勢(shì)性,在美國主流文化的強(qiáng)力影響、滲透下,難免被逐漸同化。
三、美國民族政策的實(shí)踐及其效果
當(dāng)代美國具體的民族政策是個(gè)金字塔型的多層分級(jí)體系:一是覆蓋面最寬的、保護(hù)和發(fā)展所有民族文化的政策;二是被稱為“肯定性行動(dòng)”的優(yōu)惠政策,這一政策一開始主要是針對(duì)黑人,后來覆蓋其他所有少數(shù)民族;三是針對(duì)印第安原住民的政策,即印第安人除了享受與其他少數(shù)民族同樣的權(quán)利以外,還享有保留地內(nèi)的自治權(quán)利。
第一,保護(hù)、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文化。美國政府通過建構(gòu)公民國家,逐漸實(shí)現(xiàn)了公民權(quán)利與民族權(quán)利的分離。1795年美國通過了第一部《歸化法》,規(guī)定移民必須放棄對(duì)原所屬籍貫國的效忠。隨之而來的便是一戰(zhàn)前后出現(xiàn)的“美國化”運(yùn)動(dòng)。但美國政府同時(shí)又允許任何一個(gè)民族集團(tuán)在忠于美國的前提下,保持自身獨(dú)特的,出版本民族語文報(bào)刊、書籍,創(chuàng)建本民族的學(xué)校,這在客觀上有利于外來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保持和延續(xù),從而使美國呈現(xiàn)“一體多元”的文化景象。美國構(gòu)筑統(tǒng)一的國族文化認(rèn)同并不是通過禁止或削弱各少數(shù)民族的內(nèi)部忠誠來實(shí)現(xiàn)的,而是將他們的訴求理性化、均等化,并將其納入一個(gè)具有包容性的整體之中。美國文化 并非英國文化模式的翻版,而是英國文化與其他外來移民的文化不斷互動(dòng)的產(chǎn)物。
通過保護(hù)、發(fā)展多元的民族文化,使得構(gòu)筑一體的美國文化得到了新的源泉。在這方面美國政府做得較多的工作是推行雙語教育。20世紀(jì)60年代,為了讓貧窮的墨西哥裔選民的子女能更好地受到教育,得克薩斯州的參議員亞伯勒提出了《雙語教育法案》,該法案于1967年獲國會(huì)通過。此后,非英語教育迅速遍及美國各地,甚至出現(xiàn)在已通過立法規(guī)定英語為惟一教學(xué)用語的7個(gè)州內(nèi)。2001年,美國國會(huì)為雙語教育撥款4.46億美元,各州也撥了大量經(jīng)費(fèi)。在推行雙語教育的過程中,各學(xué)校同時(shí)也對(duì)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進(jìn)行其來源國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1972年,一個(gè)聯(lián)邦地方法院裁決,根據(jù)法律上的平等保護(hù)條款,新墨西哥州的學(xué)生應(yīng)得到其母語和原有文化的教育。1974年,《雙語教育法》的修正案規(guī)定,允許在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順利完成學(xué)業(yè)的必要范圍之內(nèi)向他們提供母語和原有文化的教學(xué)。在具體的實(shí)踐中,少數(shù)民族學(xué)生原有文化的教學(xué)包括語文、藝術(shù)、音樂、文學(xué)和歷史等。雖然如今雙語教育在美國的一些州仍受到一定程度的非議,但是不可否認(rèn),它對(duì)于保護(hù)、發(fā)展多元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為一體的美國文化也正是因?yàn)槠涠嘣拿褡逦幕诺靡猿錆M活力。
自人類進(jìn)入文明社會(huì)以來,各個(gè)國家總是利用盡可能多的和先進(jìn)的手段,極力維護(hù)國內(nèi)各民族的統(tǒng)一,自覺不自覺地促進(jìn)著以國家為界限的國族認(rèn)同。各國調(diào)整民族關(guān)系的方式大致有兩類:一類是不承認(rèn)國內(nèi)某些民族的存在或其權(quán)利,極力消除建立在這些民族傳統(tǒng)文化基礎(chǔ)上的民族認(rèn)同,實(shí)行強(qiáng)制同化政策;另一類是在尊重和肯定這些民族及其認(rèn)同存在的基礎(chǔ)上,培植與國家認(rèn)同一致的國族認(rèn)同。前者因違背民族發(fā)展規(guī)律和被同化民族的意愿而受到抗拒,而后者則因順應(yīng)規(guī)律的引導(dǎo)而被各民族所接受。總體上而言,美國在20世紀(jì)60年代之后,逐步地采取了后一種做法。
第二,“肯定性行動(dòng)”。該政策是美國政府為了消除就業(yè)和教育等領(lǐng)域的種族和性別歧視,改善少數(shù)民族和婦女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狀況,自20世紀(jì)60年代中期以來所實(shí)施的各種政策和措施的總稱。它“主要是為那些在歷史上或?qū)嶋H生活中基于民族或性別等因素而被剝奪了發(fā)展機(jī)會(huì)、實(shí)際上完全有能力的人提供發(fā)展的機(jī)會(huì),并且制止將來歧視行為的再次發(fā)生”。
“肯定性行動(dòng)”萌芽于20世紀(jì)30、40年代。在二戰(zhàn)期間,羅斯福總統(tǒng)兩次總統(tǒng)令,禁止在聯(lián)邦公務(wù)員雇用和晉升方面及國防工業(yè)部門內(nèi)的歧視做法。1948年、1951年,杜魯門總統(tǒng)也先后了要求軍隊(duì)取消種族歧視,要求與政府簽訂合同的承包商和分包商遵守反歧視規(guī)定的命令。杜魯門總統(tǒng)還設(shè)立了民權(quán)委員會(huì),專門處理種族歧視問題。
20世紀(jì)50-60年代,美國爆發(fā)了由馬丁?路德?金領(lǐng)導(dǎo)的著名的黑人民權(quán)運(yùn)動(dòng),使美國的種族主義受到了沉重打擊,也迫使美國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民權(quán)法》以及總統(tǒng)的行政命令,采取了一系列“平權(quán)措施”。這些措施,也就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美國民族政策。
1961年,肯尼迪總統(tǒng)頒布了10925號(hào)行政命令,第一次使用“肯定性行動(dòng)”一詞。該行政命令宣布美國政府有明確的義務(wù),推動(dòng)和保證所有的人不分種族、信仰、膚色或民族血統(tǒng),在受雇于或申請(qǐng)聯(lián)邦政府的職位時(shí),在爭(zhēng)取聯(lián)邦政府的合同時(shí),享有平等的機(jī)會(huì)。1964年美國國會(huì)通過的《民權(quán)法》和《少數(shù)民族專門條款》明確規(guī)定,保障黑人的選舉權(quán),禁止在公共場(chǎng)所、學(xué)校、就業(yè)方面的種族歧視。1964年的《民權(quán)法》以法律形式強(qiáng)化了10925號(hào)行政命令中的“肯定性行動(dòng)”政策,并為以后該行動(dòng)計(jì)劃的實(shí)施提供了法律依據(jù)。
為了貫徹1964年的《民權(quán)法》,約翰遜總統(tǒng)、尼克松總統(tǒng)相繼總統(tǒng)令,保障少數(shù)民族在各類企業(yè)的就業(yè)、選舉方面的平等權(quán)利。為了確保“肯定性行動(dòng)”政策的實(shí)施,美國總統(tǒng)還授權(quán)勞工部聯(lián)邦合同管理辦公室(OFCCP)作為主管部門,該辦公室于1968年5月、1970年2月和1971年12月,先后多次相應(yīng)的實(shí)施條例,使“肯定性行動(dòng)”政策具體化。同時(shí),美國政府也逐步把該行動(dòng)的對(duì)象從黑人擴(kuò)大到西班牙語裔人、印第安人等弱勢(shì)群體。
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繼續(xù)在就業(yè)、教育、住房等領(lǐng)域推行“肯定性行動(dòng)”。雖然從90年代起美國社會(huì)對(duì)“肯定性行動(dòng)”提出了很多異議,“右翼”勢(shì)力甚至認(rèn)為這是對(duì)白人的歧視,但美國政府并未放棄這一政策的實(shí)施,因?yàn)檫@關(guān)系到美國民族關(guān)系的穩(wěn)定。
在一個(gè)民族身份決定個(gè)人在社會(huì)利益和機(jī)會(huì)分配中享有特權(quán)或遭受歧視的社會(huì)里,民族問在這方面的差別越大,民族之間的歧視程度越嚴(yán)重,優(yōu)勢(shì)民族捍衛(wèi)自身特權(quán)和劣勢(shì)民族力圖改善自身狀況的動(dòng)力也就越強(qiáng)烈。反之,如果各劣勢(shì)民族能夠在一種有利于自己的氛圍中通過正當(dāng)?shù)牧⒎ㄇ辣磉_(dá)他們的要求,而國家和優(yōu)勢(shì)民族也能夠用特別的扶助計(jì)劃來改變社會(huì)中通常存在的經(jīng)濟(jì)與政治資源的不公平分配狀況,那么各民族的和諧共處就有了可能。美國政府推行的“肯定性行動(dòng)”,在這方面起到了較好的作用。
第三,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制度。1975年,福特總統(tǒng)簽署了《印第安人自治法》,鼓勵(lì)保留地內(nèi)的印第安人實(shí)行自治,這是美國印第安人新的自治的開始。美國約有53.8萬印第安人居住在315塊保留地內(nèi)(但這些保留地大部分不是這些印第安人的世居地,而是政府劃定再將印第安人遷來而確立的)。美國共有560個(gè)被聯(lián)邦政府承認(rèn)的印第安人部落,部落政府是印第安人的自治機(jī)構(gòu)。
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通過美國聯(lián)邦政府的具體政策來規(guī)定和設(shè)計(jì)的,而是通過國會(huì)的立法工作,以及美國各級(jí)法院根據(jù)對(duì)國會(huì)的各種法律、法令所做出的解釋和裁定建構(gòu)起來的。因此,美國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的基本框架主要體現(xiàn)在相關(guān)的《印第安人法》之中。總體上而言,美國《印第安人法》具有四個(gè)較穩(wěn)定的根本特征:(1)在與聯(lián)邦政府的關(guān)系中,部落被視為擁有固有自治權(quán)的獨(dú)立實(shí)體;(2)部落的獨(dú)立地位不是絕對(duì)的,國會(huì)擁有管理和調(diào)整部落地位的權(quán)力;(3)處理與管制部落的權(quán)力專屬于聯(lián)邦政府,除非得到國會(huì)的授權(quán),否則各州政府不得介入印第安人事務(wù);(4)聯(lián)邦政府負(fù)有防止印第安人的部落和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遭到各州政府及其公民侵犯的責(zé)任。此外,聯(lián)邦法院在對(duì)《印第安人法》進(jìn)行司法解釋時(shí)所遵循的“條約解釋三準(zhǔn)則”也有利于維護(hù)印第安人的條約權(quán)利。這三個(gè)原則包括:由條約含混引起的爭(zhēng)議必須按照有利于印第安人的方式加以解決,對(duì)這些條約的解釋必須使印第安人能夠很好地理解之,在對(duì)條約進(jìn)行解釋時(shí)必須使其字面意義有利于印第安人。印第安人部落在保留地內(nèi)的自治權(quán)除了具備州政府所擁有的一切權(quán)力外,還包括:(1)在印第安人自己選擇的政府形式下開展工作權(quán);(2)成為部落成員的資格和條件確定權(quán);(3)內(nèi)部成員之間的關(guān)系管理權(quán);(4)繼承確定權(quán);(5)征稅權(quán);(6)在部落管轄范圍內(nèi)的財(cái)產(chǎn)管理權(quán);(7)通過自治地方的立法對(duì)部落成員行為行使約束權(quán);(8)行使審判權(quán)。正如一些法學(xué)家所評(píng)論的:“鑒于給各印第安部落政府帶來的內(nèi)部影響和給各州以及處于印第安人領(lǐng)地中的非印第安人個(gè)人及 其企業(yè)帶來的外部影響,印第安人的部落自治權(quán)仍不失為具有很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則。”但他們同時(shí)也承認(rèn):“聯(lián)邦政府在削減印第安人土地和部落自治權(quán)上所擁有的廣泛權(quán)力,使得印第安人部落很難避免依附于聯(lián)邦政府提供的指導(dǎo)和饋贈(zèng)。”
四、美國民族政策的啟示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從當(dāng)代美國的民族政策中得出許多有益的啟示:
第一,堅(jiān)持依法治國。美國的法律是政策的主體。美國關(guān)于民族方面的詳盡的法律規(guī)定,成為解決民族問題的權(quán)威闡述和剛性制度,這就避免了政府更迭帶來的政策反復(fù)性和人治狀況下政策的隨意性。各州、各民族群體的利益訴求與妥協(xié)下的美國民族問題的法治化過程,也基本上保障了各民族群體平等的利益表達(dá)和實(shí)現(xiàn),從而維護(hù)了美國民族關(guān)系的穩(wěn)定。而美國憲法―聯(lián)邦法律―州憲法―州法律這一完整的法律層級(jí)體系,既保持了美國民族政策一體性與地域性的統(tǒng)一,也在維護(hù)中央權(quán)威性的同時(shí),保護(hù)各州根據(jù)本地實(shí)際情況確立具體民族政策的靈活性。
當(dāng)民族間發(fā)生矛盾時(shí),雙方對(duì)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尊重,保障了民族關(guān)系可以在平等的基礎(chǔ)上以社會(huì)認(rèn)可的、代價(jià)最小的方式解決。200多年來,美國民族矛盾能夠在法律框架內(nèi)解決而不是運(yùn)用行政手段或其他手段解決,是美國政府能夠有效地處理民族問題、美國社會(huì)能夠有效地進(jìn)行自我調(diào)節(jié)的一個(gè)重要原因。
第二,在民族問題上堅(jiān)持“一體”與“多元”的平衡。能否消弭民族、宗教、文化的異質(zhì)性帶來的沖突甚至是離心傾向,是一個(gè)民族多元化國家的民族政策成功與否的關(guān)鍵。美國民族政策的成功之處,在于較好地維系了“一體”與“多元”的平衡。既尊重多元性,又將多元性加以整合以建構(gòu)一體性。美國的民族政策通過法律和政治制度將多元化的民族利益納入了一個(gè)具有包容性的規(guī)則體系中,并在此基礎(chǔ)上建構(gòu)國族的一體性。這種一體性又為民族的多元利益的競(jìng)爭(zhēng)與協(xié)調(diào)營造了較為寬松的政治空間。此外,多元主義因?yàn)榉掀降取⒐兔裰鞯脑瓌t,它也有利于一體化的創(chuàng)建和維持。因?yàn)槎嘣髁x更能造就國內(nèi)各民族的團(tuán)結(jié)與和睦的氛圍,更能加強(qiáng)各民族之間的文化聯(lián)系和交流,加速同質(zhì)性文化的發(fā)展和群體間共性的提高,這比刻意去追求和強(qiáng)制民族統(tǒng)一的民族同化政策更能促進(jìn)和鞏固國家認(rèn)同。正是多元利益與聯(lián)邦一體性之間動(dòng)態(tài)平衡的實(shí)現(xiàn),保持了美國民族關(guān)系的穩(wěn)定。
第三,積極構(gòu)建國族共同體和塑造國家認(rèn)同。現(xiàn)代國族共同體與傳統(tǒng)的以血緣世系為基礎(chǔ)的民族共同體不同,它是不同族源、不同地域的人們不斷交往、整合而形成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高度統(tǒng)一的共同體。美國民族關(guān)系的穩(wěn)定,與美國積極構(gòu)建美利堅(jiān)國族共同體不無關(guān)系。美國涵蓋全國、高度發(fā)達(dá)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系所強(qiáng)化的共同經(jīng)濟(jì)生活和共同經(jīng)濟(jì)利益,孕育了美國各地域、各民族的美利堅(jiān)共同體意識(shí);美國的聯(lián)邦制政治制度,成功地將多元化的地域(各州)利益納入了一個(gè)具有包容性和均衡性的規(guī)則體系中,它在保障各地域的獨(dú)特性的同時(shí),也為地域間通過政治體制營造利益共識(shí)提供了制度平臺(tái);同時(shí),美國通過突出、強(qiáng)調(diào)公民權(quán)利而非民族權(quán)利,完成了從民族國家向公民國家的轉(zhuǎn)變,也杜絕了以民族為單位因權(quán)利等因素破壞民族穩(wěn)定關(guān)系的可能。而且,美國政府通過對(duì)“盎格魯一新教”文化、“美國信念”等美國核心文化價(jià)值觀的強(qiáng)化,以及教育、語言方面的整合,完成了國民對(duì)國家的認(rèn)同和對(duì)新移民的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