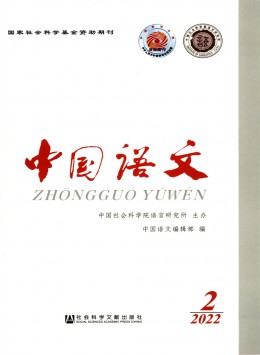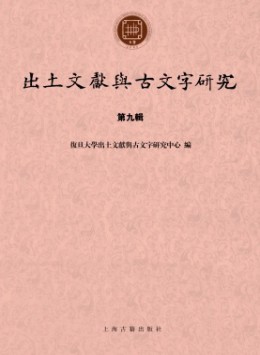文侯與虞人期獵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文侯與虞人期獵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文侯與虞人期獵范文
第2篇:文侯與虞人期獵范文
關鍵詞:觀化;放;豪;狂;萬象;李白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4)02-0083-10
豪放
觀化匪禁,吞吐大荒。
由道返氣,處得以狂。
天風浪浪,海山蒼蒼。
真力彌滿,萬象在旁。
前招三辰,后引鳳凰。
曉策六鰲,濯足扶桑。
《二十四詩品》(以下簡稱《詩品》)是中國古代詩學名著,它對中國古代詩歌中的多種藝術風格曾做過很好的甚至是很精彩的理論總結和升華,由此貢獻給中國古代美學很多理論概念明確內涵豐富飽滿的重要美學范疇。《詩品》中《豪放》一品所討論的“豪放”,就是這樣的范疇。《豪放》品說“豪放”風格,有四個要點,即:吞放不羈,豪情似狂,胸蓄真氣,萬象瑰偉。前三點主要從詩人的主觀氣質氣度胸襟著眼,后一點則主要就詩歌表現、意境、意象而言。前三者催生出后者并在后者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后者則以瑰麗的萬象展示著前三者的精神。下面順著《豪放》品的詩句和上述要點,做具體的討論。
一、“觀化匪禁,吞吐大荒”
“豪放”是古代習用的詞語,在文學藝術中,主要指一種特定的陽剛類型的藝術風格。“豪放”雖常聯言,但“豪”與“放”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是各有其含義的。楊廷芝《詩品淺解》說:“豪以內言,放以外言。豪則我有,可蓋乎世;放則物無,可羈乎哉!”楊氏此說,區分豪與放并指出二者的主要特點,大體不錯。比較而言,其說“豪”更準確些,其說“放”則似稍有不足。豪,確乎是指主體內心之蘊涵十分充盈,由是而自得自信自豪,其噴發而出遂有蓋世之勢。至于放,其主要特點固然如楊廷芝所說是在不可羈勒,但這不羈,不僅是不為物所羈,更主要是不為自我之“心”(自我所固執的欲望、利害、是非等等觀念)所羈,用楊氏的話說,即是不僅“物無”,而且是“物我俱無”。只有這樣,詩人的心才能真正地“放”得下,“放”得開。不難看出,“觀化匪禁,吞吐大荒”兩句,正是在強調詩人的心胸要不受物拘心滯,要推放得開,所以,這兩句主要說的是豪放之“放”。這兩句從文字到解說,歷來都有一些歧意歧說,需要做一些分析推敲。“觀化”,有的本子作“觀花”。無論作“觀化”或“觀花”,都有一些注本、學者曾加以解說。王潤華先生指出“孫聯奎在其《詩品臆說》中,把‘觀花匪禁’的‘花’解作‘化’,認為含有‘洞悉造化略無窒礙’之意。……郭紹虞則認為‘觀花匪禁’是‘看竹何須問主人’的另一種說法。……祖保泉則把它解成‘在都城看花,是豪放的行動’之意”。[1](P173)王潤華先生則根據其研究結果提出了一種很新的看法:從“追求其文字及意象之根源”的角度看,“觀花匪禁”這句詩,大概是出自一個有關劉禹錫及其玄都觀看花詩的典故。[1](P174~180)關于“觀化匪禁”或“觀花匪禁”的這幾種不同的解說,都各有其根據和道理,但推敲起來,我更贊成孫聯奎的解說,不大同意郭紹虞、祖保泉先生的解說,而尤不同意王潤華先生的新解。不同意王解的主要理由是:劉禹錫本人一生拘執少“放”,他參加永貞革新失敗遭貶,二十余年間對此耿耿在心從未釋懷,劉氏念茲在茲感慨難止之詩作,比比皆是。總體來看,劉禹錫及其詩作雖不乏豪情,卻殊少不羈之“放”,且其詩中也少有《豪放》品中那以“三辰”“鳳凰”“六鰲”“扶桑”為表征的神奇瑰麗的“萬象”,亦即二者在詩歌意象方面也頗不相合。顯然,《豪放》作者是不大可能“針對”劉氏詩風或說以玄都觀看花之典和劉氏詩風為“文字及意象之根源”而創作出《豪放》品的。所以,“觀花匪禁”乃至《豪放》一品,與劉禹錫詩作和典故并無多少關系。再說不大同意郭紹虞、祖保泉先生解說的理由。用“看竹何須問主人”和“在都城里看花”來解說“觀花”,置于《豪放》品中,似同樣與全品之義有所未愜。其原因,在所示境界大小之殊也。由這樣的“看竹”“看花”而得到的心靈解放,只能是一種很局限的區區之“放”,蓋因其所示之境具體而微,人之心胸實未能因不羈于此“竹”此“花”之“觀”而成其大放也。即使詩人能夠這樣地“看竹”“看花”,他也未必因此就能夠面對浩浩廣宇而“吞吐大荒”。事實上,這樣的“看竹”“看花”,也與《豪放》后文描繪的狂放瑰偉的詩風詩境明顯不類。所以,這樣的理解仍有未當。
竊以為,“觀花匪禁”語當作“觀化匪禁”,孫聯奎的說解基本是確當的,但沒有展開分析。這里且來做一點具體的分析論證。“觀化匪禁”,其意其境與《豪放》全篇甚為切合。“化”,即變化,在古代典籍中,又常指萬物的變化,自然的運化。《莊子》書中,此意多見,如其《大宗師》篇里,“化”“造化”“萬化”“一化”等等,頻頻出現,亦多有此意。又如《荀子?天論》云:“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陶淵明《形影神》詩中名句“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其大化亦指天地宇宙中無時或息的偉大的自然運化。至于“觀化”一語,也已多見于前人載籍。如《莊子?至樂》篇云:“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此“觀化”即觀察萬物的變化之意。又如六朝佛學大家僧肇在《不真空論》中說:“審一氣以觀化”,任繼愈先生譯為“從統一的原則觀察萬物的變化”[2~3](P288;31)。再如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有“窮神觀化,坐影揣神”之語。總的看,“觀化”一語習用已久,且大體為觀察萬物的變化自然的運化之意。《豪放》品放眼宇宙而談“道”談“氣”談“吞吐大荒”,在此背景下按習用的語意來采用“觀化”一詞,是比較自然的。進一步,不僅“觀化”一語,甚至“觀化匪禁”的整個意旨,都仍來自前人,尤直接從《莊子》書中來。試看如下兩段文字:
俄而字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于齊,肩高于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診,其心閑而無事, 而鑒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灸;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于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啻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之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铘’,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大宗師》)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于冥伯之丘,昆侖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至樂》)
這兩段話,講的同一個意思,即在自然運化面前,人應當去除物羈與心滯,委運任化,這不僅符合自然運化的規律,也使人的心靈、精神得到解放。具體說,天地宇宙、自然萬有都在自然地運化著,人在“觀化”,其實人也是“化”中的一分子。對自然運化中的事事物物乃至人自身的存在狀態或狀態改變,人若是此非彼,惡此好彼,固執己見,就都是不符合運化規律的、不正確的態度,人的心靈也因受到物拘我禁而難以開放自由。既不拘于物也不囿于我,一切委任運化的流行,這才是符合自然運化規律的、正確的態度,心靈因此亦將獲得解放與自由。對運化中的物或我的任何存在狀態或狀態改變的固守(如曰“人耳人耳”,曰“我必為鏌铘”等等)或拒絕(如對人之奇形怪狀的病態以及對死亡的“惡”),都是人在運化中的一種拘執,是橫亙在處于自然運化之中的人的心靈、精神面前的一種“禁”限,它既不符合自然運化的規律,也阻礙了心靈的開放與精神的自由。反之,去除拘禁,安時處順,委運任化,既符合規律,也能使心靈、精神獲得真正的徹底的解放。所謂“今一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由此而“成然寐,蘧然覺”,就都是解脫禁限后心靈開放精神自由愉悅的寫照。從這兩段話,我們看到了莊子“觀化匪禁”的大致思想風貌。由此,我們似乎可以說,“觀化匪禁”一語正是對上述莊子思想側面的一個相當準確的濃縮和概括,而孫聯奎對此語的解說(“能洞悉造化,而略無滯窒”)也是得當的。
再進一步,我們看到,不僅是“觀化匪禁”而且是“觀化匪禁,吞吐大荒”二句的整個意趣,也與莊子密切相關。“大荒”,或釋曠野,或說大地,或釋曠遠之地,或說極遠之地,總之,是極廣極遠之境。此二句是說,觀察萬物的變化而無拘束與禁制,人的胸襟就很闊大心靈就很解放,精神就能從閉鎖拘禁之中超而遨游于無限廣遠之境,自由來往,吞吐無限。而這種情形,在莊子那里正有最充分最突出的體現。在《莊子》書中,基于“觀化匪禁”之上的解放了的心靈和自由的精神,其終極指向,正是那極為廣遠空闊之境,請看:“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逍遙游》);“乘云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齊物論》);“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游無何有之鄉”,(《應帝王》)“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吸風飲露,不食五谷,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遙游》)等等,不一而足。在如此這般廣遠無限的境域里,然而來然而往,沒有了一切拘禁滯窒,精神無比自由。顯然,“觀化匪禁,吞吐大荒”的主要精神旨趣、思想路數,是與莊子精神相近的,它完全有可能受到過莊子上述思想精神的啟示。當然,它也與莊子思想有所不同,主要在于:莊子思想,求其精神的自由快適而已,并無涉乎將此種自由的精神、廣遠的境界以及“吸風飲露”似的修為轉化為某種藝術創造的偉力,莊子對于藝術品之完成并無絲毫的興趣;“觀化匪禁,吞吐大荒”則顯然正是談藝術創造的實際問題,它要求創造主體經由“觀化匪禁”的宇宙認識、人生態度而舒展其自由寬廣的胸襟,形成吐納宇宙揮灑萬物的氣勢和偉力,獲得廣闊無限的創造空間,并最終將所有這些都轉化為藝術創造之偉力,落實于藝術作品之中。
總上而言,化、觀化、觀化匪禁,觀化匪禁吞吐大荒,其語言意蘊皆有所本,而與莊子關系尤密。“觀化匪禁,吞吐大荒”二句,側重言“放”,以近乎極限的說辭(觀萬化而不禁,吞吐宇宙)對不羈之“放”做了形容或申說。這一形容申說,其語詞意蘊雖多取自前哲,卻又結合“豪放”藝術風格的創造實際進行了濃縮、概括與改造,既深含哲理,又頗合于藝術創造實際,且非常凝練形象。
二、“由道返氣,處得以狂”
這兩句主要說“豪”。對這兩句的含義,解說者們的看法比較相近一些,但我以為,對這兩句的句意和解說者們的相關看法,仍有再檢討的必要。
先討論“由道返氣”。有較多的學者聯系儒家思想尤其是孟子學說來理解這句詩。孫聯奎說:“返,追回也。追回其氣而以道范之。‘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詩品臆說》)楊廷芝說:“由道返氣,言氣集義而生,豪之所由來也。”(《詩品淺解》)郭紹虞先生說:“由道返氣,言豪氣是集義所生,根于道,故不餒。”(《詩品集解》)這些解釋,都將豪“氣”與“義”“集義”聯系起來,具體說法顯然源自《孟子》。這類看法影響很大,在晚出的相關書籍中也常可見到。但我覺得,這樣的解說其實是很值得商榷的。首先,在中國古代哲學中,作為宇宙本體,“道”與“氣”相比,是具有更為根本之意義的概念。在中國傳統哲學思想背景下,“由道返氣”應當指的是,從具有根本意義之“道”返回而落實到“氣”。那么,在中國古代思想中,究竟有哪一家在對待“道”與“氣”的關系時曾持有或表露過類似的態度或主張呢?先來看諸位解說者提出的儒家。儒家鼻祖孔子也談論過“道”(主要是倫理之道),卻似未曾將“道”與“氣”相聯系,更沒有類似“由道返氣”的說法或主張。孟子談“道”,且確曾將“道”與“氣”放到一塊兒說過,他說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孟子?公孫丑》上)浩然之氣作為一種“氣”,必須要配合上“義”與“道”才能真正成為至大至剛之氣,否則就不能成其為“浩然之氣”了。這里,出現了“道―氣”關系。但仔細推敲,這里的“道―氣”關系似與“由道返氣”的“道―氣”關系并不相同。在孟子這里,對于與浩然之氣相配合的“義”和“道”,重視的或強調的是“義”而非道。這從后面“是集義所生也,非義襲而取之也”一句可清楚看出,浩然之氣確切是由“集義”而生的。所以在孟子這段話里,主要表現出的是一種“義(道)―氣”關系。孟子的“義”是倫理正義,其“道”也是倫理之道,其配義與道而成的浩然之氣同樣是一種充滿倫理色彩的主體之氣,顯然,孟子的“義(道)―氣”關系論整個是在倫理領域展開的,并沒有涉及宇宙本體論或發生論的問題。然而,如果我們不帶任何先見而細品《豪放》全品的話,則顯然《豪放》全品是沒有多少倫理道德色彩的,其“道―氣”關系論應該是涉及了宇宙本體論和發生論的問題的。這也就是說,《豪放》的“由道返氣”從語言形式到思想意蘊,都并非從儒家或孔子、孟子來。以往的不少注解,引孟子語解之,不僅坐實了“由道返氣”與儒家的關系,而且使《豪放》品染上了濃厚的道德倫理色彩,這是不大妥當的。
我以為,“由道返氣”的提法更可能從道家而來。道家老莊,視“道”為宇宙的本體、本原,也都很強調“氣”,莊子更說過“通天下一氣”。(《莊子?知北游》)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老子》四十二章的說法,其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據一般解說,此句中的“一”就是氣;“二”就是陰陽二氣;“三”就是由陰陽二氣沖合而來之和氣。“道生一”就是“道”生“氣”,就是由宇宙本體之“道”向物質世界(“氣”的世界)落實。如果站在物質世界的角度看問題,那么這樣的一個落實過程,不就正是一個“由道返氣”的過程嗎?而從這里我們看到,在語句的形式層面,《豪放》的“由道返氣”與道家的上述說法是很相近的,它完全有可能是從后者中化出的或曰提煉出的。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由道返氣”雖然更可能源自道家的某些觀點和提法,但它對待“道”與“氣”的態度,卻不與道家盡同。《豪放》并不真正要像道家一樣去推崇“道”,它只是把“道”作為某種最高存在、最后根據、最高意義的象征而加以推尊,此“道”的存在,使“氣”的地位穩固可信而不被動搖。它強調的重點,是“氣”,更是詩人充盈于胸的元氣,而強調“氣”,就要借重于“道”。“由道返氣”一語,將“氣”置于作為宇宙本根的“道”之上,就使“氣”獲得了至極至固的根基和不會窮竭的源泉。在這個意義上,郭紹虞先生“根于道,故不餒”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總之,《豪放》“由道返氣”之說乃取徑老莊,托“道”論“氣”,其要在于給“氣”以一個終極的根據和最為有力的肯定。
再討論“處得以狂”。先分說“處得”和“以狂”,后再合起來說。先看幾種關于“處得”的解說,“人處得意之時”(孫聯奎《詩品臆說》);“言其實有所得”(楊廷芝《詩品淺解》);“處得,此處意謂偶然獲得,輕易獲得”(喬力《二十四詩品探微》)。顯然,這些說法都將“處得”的“得”,解為通常的“獲得”,至于“獲得”什么或怎樣“獲得”,則各說不一。我以為,將“處得”之“得”做普通意義上的“獲得”解,雖無大錯,卻也有著明顯的不足之處,主要是沒有傳達出“得”的更深層含義來。對于處于“由道返氣,處得以狂”之語境中的“得”和“處得”的理解,應當扣緊整個語境尤其是“由道返氣”來進行。據此,我認為這里的“得”并不只是普通意義上的“獲得”,而是針對“道”與“氣”而言的“獲得”,簡言之,即“得道”“得氣”之謂也。而“處得”,也就指的是處于“得道”“得氣”的狀態。這樣來理解,比較順乎語句的邏輯發展,上下句間的語義也顯得更連貫自然。不僅如此,這樣的理解,在中國古代思想中,也是有據可依的。中國古代思想尤其是道家一路的思想中,常有把握大道之說亦即“得道”之說。例如《老子》三十九章說:“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林希逸、嚴靈、陳鼓應等不少古今學者都認為,這里的“一”即是“道”,“得一”即是“得道”。[4](P218)其實主張“體道”“握道”“得道”的種種具體說法,在古代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中是很常見的,不必多舉。將“得”作為“得道”之意來理解,其可行性還可從“得”與“德”之關系這一獨特角度來再做考察。古籍中,常用“得”來釋“德”,“德者,得也”的說法很常見。而有時,“得”甚至也徑直可通于“德”,如《荀子?成相》篇“尚得推賢不失序”,此“得”即通于“德”。那么,什么是“德”呢?從本文的角度出發,我們看到,“德”與“道”有著特別密切的關系。《管子?心術》說:“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以。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德”是“道”的體現,而這個“德”也就是“得也”。《老子》二十一章有“孔德之容,惟道是從”一語,陳鼓應先生因之而闡論老子“道”與“德”的關系說:“一、‘道’是無形的,它必須作用于物,透過物的媒介,而得以顯現它的功能。‘道’所顯現于物的功能,稱為‘德’。二、一切事物都由‘道’所形成,內在于萬物的‘道’,在一切事物中表現它的屬性,亦即表現它的‘德’。三、形而上的‘道’落實到人生層面時,稱之為‘德’。即:‘道’本是幽隱而未形的,它的顯現,就是‘德’。”[4](P152)據此說,則“德”即是幽隱未形的“道”在萬物、人生中的某種顯現。“德”既然為“道”的體現,則它當然是“得”了“道”的。由此,亦由“德”與“得”的密切關系(“德者,得也”;“得”“德”有時相通),我們將“處得”之“得”做近于“德”的“得道”來理解,將“處得”即作為“處于得道之狀態”來理解,應該說是有根據的。竊以為,對“處得”“得”做如上理解,似更切合原句的語境義脈,也更能與中國古代哲學中的相關思想相切合。
此外,“得”又是“得氣”。中國古代思想中有一類重要的觀點,認為“氣”是萬物的始基,人與萬物都是稟受著“氣”或“元氣”而生而成的。例如漢代的王充在其《論衡》中說:“人稟氣于天,氣成而形立”(《無形》);“萬物之生,皆稟元氣”(《言毒》)。站在人與萬物的立場上說,“稟氣”當然也就是“得氣”了。按這樣的思想路數看,則緊接“由道返氣”而來的“得”,就非常可能是“得氣”之“得”,或說指的就是“得氣”。然而這樣一來,卻又出現了一個問題:既然人與萬物皆稟氣而生,則凡一切既生之人與物,都當然稟賦有氣或元氣,那么,《豪放》又為什么要強調“得”氣呢?“得”氣對于豪放風格又有什么意義呢?這同樣得從中國古代思想中尋找答案。原來,古人有一種看法:天之元氣化施固均,而人的受性卻各自不同。試觀王充《論衡?幸偶》中的一段話:“俱稟元氣,或獨為人,或為禽獸。并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可見,天施元氣雖不左此右彼,但人(物、禽、獸)之受性,人之實際上的氣稟卻千差萬別。《豪放》之“得”氣,就顯然并非對得氣的一般性要求或說明,而是對能夠保證豪放風格充分實現的那一種“氣”的強調,是強調詩人們必得此“氣”其詩方能逞其豪。那么,此“氣”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氣”呢?細尋“由道返氣,處得以狂”二句,細味《豪放》全品,豪放詩人所“得”之“氣”,當為一種最為淳厚的、飽滿無缺的陽剛之氣。此“氣”根源于“道”,自然不餒,用而不竭。此“氣”內充于人,令豪放之詩人真力充滿,自足自信,昂然向上,豪情似狂。而由此我們看到,詩之豪,乃源于人之豪;而人之豪首先在于其頗具先天性質的氣稟。就是說,《豪放》立足于詩人的氣質講風格,但這氣質,更強調了它的先天性,強調其先天氣稟的飽滿充盈,而似無涉或少涉乎后天的培育養成。而這也就是說,此種豪氣,既不類孟子的浩然正氣,也與“集義所生”無關。而同時,此種豪氣就其來源看,雖然形式上(“由道返氣”“處得”)與道家之說有關聯,但實質上與中國古代的稟氣、氣稟之說(如上舉王充之論)關系似更密切。因為,道家固然有“道生一”“通天下一氣”之類的說法,但老子貴雌尚柔,莊子法天貴真尚逍遙,都未深入討論氣與人之風格等等問題,也不主張人的豪邁雄強,更不曾也不會關注“氣”與人之豪邁雄強的關系。所以,《豪放》這里論豪氣之所自所來,是借用道家的語言形式(當然也包括其基本的部分意蘊)而又以古代稟氣、氣稟之說做了意涵方面的充實和改造的。
“處得以狂”,有的本子作“處得易狂”。有的注家據“易狂”而對“狂”作了否定性的說解,如:“人處得意之時,便易于狂。‘酒闊思吞海,詩狂欲上天’,語義未免太狂。品中每以反筆透題,如《自然》篇‘真與不奪,強得易貧’,筆法與此一律,妙在俱是先正后反,筆致跳躍”。(孫聯奎《詩品臆說》)喬力對《二十四詩品》的解說,也大體仿此。而有的注家則據“以狂”而對“狂”做了肯定性的說解,如:“狂有豪放之意”;(曹冷泉《詩品通釋》)“狂,放肆縱恣無拘束。……《莊子?山木》:‘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不知義之所適,禮之所將,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言不受禮義的拘檢束縛,率性而行,放縱恣肆、逍遙而自得,其行為自然合乎大道”。(劉禹昌《司空圖〈詩品〉義證及其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11月)我以為,無論做“易狂”或“以狂”,《詩品》作者都對“狂”持有肯定的態度。因為就《豪放》品后面用以展現“豪放”精神的那些詩歌意象看,其間洋溢著的那種揮斥萬象吞吐天地的氣勢情懷,正是無比的狂放!若對“狂”稍抱有警惕或批評的態度,是斷然不會以如此這般的意象來喻說其所謂“豪放”之詩風的。因此,若語做“易狂”,則是說因為“處得”,所以就自然易于發為狂放。全句只是一種事實的陳述,并不含有貶義。若語做“以狂”,則似可做兩種理解,都是褒義:一是說因為“處得”,自然有一種狂放的傾向;二是進一層言“狂”,意即“處得”本身并不一定就導致“狂”,然為“豪放”計,是應該要再進之以“狂”的。其實,“處得以狂”在語句上和意思上似乎都和穆夜解說莊子的說法存在淵源關系。成玄英《莊子序》引穆夜對“逍遙游”的解說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無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遙游。”很顯然,“至德內充”就是“自得”亦就是“處得”,“放狂”亦就是“以狂”,穆氏對莊子的“放狂”持肯定態度。這一解說是很能得“逍遙游”之精髓的,對于我們理解《豪放》開首四句詩,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據此看來,“狂”還不僅僅是“處得”(“至德內充”)的自然表現,而且也是“觀化匪禁”(“忘懷應物”)的正常結果。
總之,“狂”是《豪放》所謂“豪放”的一個必備的正面要素。這樣的“狂”,是置根于大道之上的昂揚,而非失根者的輕狂;是元氣充盈于內的自信與勃發,而非氣餒者的虛矯;是因忘懷物我而來的胸襟的自然大解放,而非拘拘者難得一見的偶然放膽。這是詩人氣質性情的最真實地表達:豪氣萬丈,不得不狂!
三、“真力彌滿,萬象在旁”
前人說此二句,語多精彩。孫聯奎《詩品臆說》云:“有真力以充之,上下四旁,任我所之,傍日月而摘星辰,何所不可。……凡所應有,無不俱有,鬼斧神工,奔赴腕下,是之謂萬象在旁。”楊廷芝《詩品淺解》云:“真力彌滿,則塞于天地之間。萬象在旁,舉凡天地間之所有者,亦祗視為左右之陳列而已。”那么,這樣一種真實的偉力,何所自而來呢?劉禹昌先生以為來自“道”,他說“真力,本為大鈞造物者神化之力,得道之人,在精神境界上,其思想與道(真)同體,則真力自然充滿于胸中”。(《司空圖〈詩品〉義證及其他》,33頁)姑且不論這真力是否即是造物者神化之力,我們知道,最宣揚體道的莊子,對他筆下種種得道之人,更強調的是因體道得道而來的精神自由、愉悅和無傷,卻似乎很少提到過因體道得道而來的巨大力量。所以,道雖是萬物(包括力量)的終極來源,但這里的真力卻并不一定直接來自人之體道得道。我以為,這真力比較直接地源自“由道返氣”之“氣”,即詩人因“處得”而蘊蓄于胸的飽滿元氣。在中國人看來,“氣”與“力”是有著緊密關系的,所以“氣力”“力氣”早已為習見之詞。古人又認為,氣的飽滿盛大會帶來巨大的力量。韓愈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氣猶水,水大則內蘊巨力,可使能浮之物盡數浮起,氣盛亦復如是,同樣內蘊巨力。真力源于盛氣,而盛氣又可以有不同的來源。在儒家尤其是孟子,其盛氣(浩然之氣)乃經由正義的不斷培養聚集而獲得。在道家,則氣自道來(“道生一”),無關乎倫理道德,亦似不特別強調氣之“盛”。在《豪放》,則采道家說法而以后來之氣稟說充實之,強調盛氣乃是一種根源于道的元氣充盈狀態。徑直說來,《豪放》之“真力”,即源自詩人因“處得”而內蘊之充盈元氣,由于此氣更多來自先天稟賦,亦即得自本真,故其顯而為力,亦稱“真力”。
浩浩真力, 彌漫于詩人胸中,遂使宇宙萬象,奔涌于其眼前或腦際,任其驅遣揮灑。既已驅遣揮灑,則浩浩真力,宇宙萬象,又復彌漫奔涌于詩人所創造的藝術世界中。這就是豪放之詩人,豪放之詩作。《豪放》用了全品一半的篇幅,來展示其所謂“萬象”之情狀,來形象地喻說豪放詩風。“天風浪浪,海山蒼蒼”,景象闊大,內盈巨力,格調平正,乃一般雄闊大境之描狀。此境與《雄渾》所造詩境相似,都是典型的陽剛風格的藝術體現。而“前招三辰,后引鳳凰。曉策六,濯足扶桑”四句,則顯出極鮮明的“豪放”的個性特色。楊廷芝說曰:“前招三辰,玩一‘招’字,則聲撼霄漢,手摘星辰。……鳳凰,不與群鳥伍,而今且無不可引,則進退維我,不可方物矣。策六,豪之至,濯扶桑,放之至。亦其胸懷不啻云開日出,海闊天空,故曉策六,濯足扶桑。”(《詩品淺解》)的確,這四句顯出了“豪放”詩風極為鮮明的個性特色:豪情萬丈,狂放不羈,天地星辰可驅,神鳥異木可遣,宇宙萬物,一切的一切,盡為所用,悉聽揮斥。這真是何其豪放之至也!由這四句,我們看到了伴隨胸襟的開放無羈而來的解放了的想象力,伴隨豪氣奔涌而霞光四射似的想象噴發,正是這種開放四射的藝術想象,導致了那瑰偉奇幻的“萬象”奔赴而來,陳列左右。
概括說來,《豪放》指出了豪放詩風應具備的四個要素:開放不羈的心胸(這是“放”的內在根基,由此,乃有“吞吐大荒”的藝術表現);充盈浩蕩的元氣與真力(這是“豪”的不竭源泉與內在動力,由此,乃有在廣闊藝術空間中展開的豪氣萬丈的藝術表現);由真實本性勃發而出的“豪”乃至于“狂”(這是豪放者之一種必然傾向,由此,乃有狂放、豪情似狂之類的藝術表現);瑰麗奇偉的“萬象”(這是由“豪放”而來的解放了的想象力亦即開放無羈的藝術想象的產物,這是“豪放”在詩歌世界中的展現,是前面三者之綜合的藝術顯現)。前三者多就創作主體言而映帶著藝術表現,后者就藝術表現言而又根系于創作主體。必具四者,豪放詩風乃能完滿而真實地展現于藝術世界,而“浪浪”于讀者眼前。這四個要素,也可以說就是《豪放》作者賦予“豪放”概念的四點理論內涵。這樣一來,“豪放”也就成了一個概念明確、內涵豐富飽滿的重要美學范疇。在中國藝術史美學史上,“豪放”本是一個習用的風格概念,豪放本是一種重要而有特色的藝術風格,然而,“豪放”概念究竟有哪些理論內涵?豪放風格究竟有什么樣的風格特色?對這樣的問題,淺談者多,深論者少,而能有特出透徹之論且有重大理論建樹者,惟《豪放》品而已。完全可以說,對豪放范疇所做的杰出的理論建構,是《詩品》作者對中國美學史做出的又一重要貢獻。其對“豪放”的看法和解說,除了基于中國詩歌的創作實際以外,還深深地植根于中國古代的尤其是道家一路的思想哲理,其思想意蘊與語言形式都多從此中提煉而出,又結合豪放詩風的創造實際進行了精彩的概括、改造與重鑄。于是《豪放》品短短十二句詩,不僅將豪放風格的基本特征較為飽滿、清晰地概括了出來,而且既深含哲理,又頗合藝術創造實際,且非常地凝煉形象。作者對中國古代思想,藝術之通曉深諳,尤其是對它們的化用自如以及其理論方面的概括、提煉、融鑄之精深功力,實在是令人贊佩!
四、《豪放》與李白
豪放屬于壯美、陽剛美,是陽剛類風格中的一種極具個性特色的藝術風格。盡管《豪放》概括出了豪放風格的諸多特征,而且也許別的理論家還可以列出豪放風格的另外一些特征,但豪放風格最根本的特征主要還是在“豪”與“放”二端。 由此又帶來了一系列的重要特征,如:闊大的境界,遒勁的風力,豐富的想象,某種狂情狂態,等等。“豪”與“放”各有自己的個性特色和風格含義,但二者又有一種互傾性,故又常融為一種風格。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它們有時各不相勝互相因依融而為一,而常常又是以一方為主而映帶著另一方。從理論上說,除了“豪”與“放”之外,豪放風格還可能具有很多具體特征,但在文學實踐中就具體作品來看,并非具備了其全部特征才能成為豪放之作,只要大體具備了其基本特征和部分重要特征,就可稱為豪放之作了。中國文學史上,豪放風格曾有出色的表演和顯赫的地位,具有豪放風格的詩人作家很多,一方面其豪放作品對于豪放的上述特征多少都有所具備,另方面其具體創作又各具特色,各有風采。將《豪放》與眾多豪放詩人詩作相對照,筆者有一個突出的感覺:《豪放》之“豪放”,既概括出了豪放風格的一般性特征,又似乎是有所特指的,即它可能是作者在參考諸家的基礎上而以某位詩家及其作品為主要范本而提煉出來的,所以最終在概括一般性特征的同時又較為明顯地指向了這位詩家的人品詩風。這位詩家,就是天才豪放的詩仙李白。下面,先簡單看一下與豪放相關的幾位文學大家的情況,再較為詳細地考察《豪放》與李白的關系,由此來看一看《豪放》與豪放名家們的實際關系,貼近地了解一下《豪放》在文學實踐方面的基礎或根源。
莊子是大哲學家,也是大文學家。《豪放》與莊子思想的甚深淵源關系,前文已多談及。總體來看,莊子極為放達,莊文元氣充盈,恣肆,境界闊大,想象豐富瑰麗……這都極顯豪放之精神。但在“豪”這一方面,莊子似與《豪放》略異,且莊子似亦不“狂”。蓋豪而至狂,主要有一種自得自信甚至因此而自以為很了不起的勁頭,有一種“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氣概。所以楊廷芝說:“豪則我有,氣蓋乎世。”然而莊子恰恰是以“喪我”“忘我”“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等等為其思想主旨的,他拒絕有為,拒絕現實世界中的一切積極創造實際功業以及由此而來的名譽功利,因而也就沒有了往往由此而生的種種現實的豪情(非但如此,莊子思想的一個重要側面正是強調“無心無情”,故其確難具豪情)。莊文中展開的境界雖然極其闊大,但一般都不是供豪氣豪情奔涌的空間,而是為主體放松了的心靈自在來往、悠然愉悅而專設的逍遙之地。總之,莊子甚少豪狂,這與《豪放》之說是明顯不同的。
屈原的詩歌意象,最為奇幻壯麗,與《豪放》所示之意象極為近似。然而,屈子精神卻與《豪放》之精神存在明顯差異:他殊少不羈之放;他一腔熱血,忠君愛國,“雖九死其猶未悔”,其道德的執著固然感天動地內蘊偉力,然卻與“觀化匪禁”恰成兩端。
曹操的詩作也頗雄豪。其四言名作《龜雖壽》何等豪放,《觀滄海》何等雄闊。但曹操畢竟是一個深系于時的政治家軍事家,雖亦偶發游仙之語,然卻終乏不羈之放。其詩風雖時顯豪放,但更多的卻是緣于時世人生的慷慨悲涼,按之《豪放》品,總體風格亦頗為異趣。
陶淵明詩素以平淡自然著稱,但也有豪放的一面,朱熹即認為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朱子語類》)話雖如此,但豪放之于淵明詩,確非主導風格,何況所謂淵明之“豪放”,與《豪放》所論差異明顯,此一望可知,毋庸細說。
劉禹錫詩風頗豪,但二十余年拘執一事耿耿于心而始終不放,此與《豪放》顯異其趣(此說已見前文)。
宋詞豪放派代表坡辛棄疾,其人品詩風雖以豪放著稱,但亦與《豪放》所言出入明顯,因其已晚于唐代,故姑不予評說。雖然近年對于《二十四詩品》的作者問題有爭論,但筆者認為,就目前掌握的情況看,晚唐司空圖仍是此書作者的第一可能人選。詳見拙文《與的關聯》,載《文化中國》(加拿大)2002年1期,收入拙著《儒道美學與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9月);又收入拙著《詩歌美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2月)。讀者可自味之。
通過以上簡單巡禮,可見上述中國文學史上有豪放色彩的文學大家們,其藝術風格或人之品格都與《豪放》有著多少不等的差異。他們雖然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曾作為《豪放》提煉“豪放”范疇時的參考對象,但卻顯然都不是《豪放》所謂“豪放”詩風的典型代表。比較起來,李白的人品詩風與《豪放》之“豪放”,有著更多的相合之處。《皋蘭課業本原解》正確地指出,《豪放》一品“正得青蓮之妙處”。不少學者也有類似看法。雖然如此,對于《豪放》與李白詩風人品的關系的較為深入具體的考察和說明,事實上卻很少見。有鑒于此,筆者就來對二者的關系做一些具體的考察。下面就《豪放》所談“豪放”的一些特征,先看一看前人對李白人品詩風的相關評說,之后筆者再做進一步討論。
放,不羈之放。方孝孺《李太白贊》:“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秕糠萬物,甕盎乾坤。狂怒呼叱,日月為奔。”本文所引關于李白及其詩作的評論,都據《李白集校注》(瞿蛻園、朱金城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曾《代人祭李白文》“子之文章,杰立人上。……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一瀉,末世猶壯。大馳厥詞,至于如此。意氣飄然,發揚俊偉。飛黃,軼群絕類。擺棄羈,脫遺轍軌。捷出橫步,志狹四裔。側睨駑駘,與無物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麒麟鳳凰,世豈能拘?”齊召南《李太白集輯注齊序》:“輕富貴如塵土,樂山水以逍遙。嗜酒慕仙,浩然自放,即遭危困,未見其憂,豈非天際真人之邈不可攀者耶?”“不可控制”“浩浩奔放”“擺脫羈,脫遺撤軌。……世豈能拘”“秕糠萬物,甕盎乾坤。狂怒呼叱,日月為奔”……云云,不就是李白“觀化匪禁,吞吐大荒”,心胸不羈而大放的精彩突出的寫照嗎?
豪,豪放。鄭日奎《讀李青蓮集》:“青蓮詩負一代豪,橫掃六宇無前茅。英雄心魄神仙骨,溟渤為闊天為高。興酣染翰恣狂態,獨任天機摧格律。筆鋒縹緲生云煙,墨跡縱橫飛霹靂。……冥心一往搜微茫,乾端坤倪失伏藏。”薩天錫《過池陽有懷唐李翰林》:“我思李太白,有如云中龍。……神光走霹靂,水底鞭雷公。”丘《過采石吊李謫仙》:“諸君看此李謫仙,掀揭宇宙聲轟然。”王士《論詩絕句》:“青蓮才筆九州橫,六代哇總廢聲。”又,《唐詩記事》引張碧語:“李太白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鯤觸巨海,瀾濤怒翻。”觀此數語,李白那無與倫比的豪情豪氣已可盡見,筆者于此,實不能再贅一詞。
元氣,天才,真性,真力。馬光祖《李太白贊》:“天地英靈之氣,曠千載而幾人?”魏裔介《讀李太白詩》:“太白更絕塵,汗血如飛兔。擲筆振金石,有文懸瀑布。萬象羅胸中,百代生指顧。是氣曰浩然,不祗為章句。”方孝孺《李太白贊》:“心觸化機,噴珠涌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悶于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于扶桑,飛騰帝鄉。”鄭谷《讀李白集》:“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鐘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明月。”皮日休《李翰林 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為真放焉》:“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植。蓬湖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岳為辭鋒,四海作胸臆。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李綱《讀四家詩選》:“謫仙乃仙人,薄游人世間。”李白詩仙,元氣充盈,性真力真,天才絕塵。
狂,狂放,豪狂。杜甫《飲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昔年有狂客,號為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杜甚知李,所言不虛。
真力,闊境,瑰偉奇幻之萬象。李商隱《漫成》:“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徐《李太白雜言》:“開口動舌生云風,當時大醉騎游龍。開口向天吐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后吐出光焰萬丈凌虛空。蓋自有詩人以來,我未嘗見太澤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千變萬化,雷轟電掣,花葩玉潔,青天白云,秋江曉月,有如此之人,如此之詩。”齊己《讀李白集》:“竭云濤,刳巨,搜括造化空牢牢。冥心入海海神怖,驪龍不敢為珠主。人間物象不供取,飽飲游神向玄圃。”諸語俱形容至極,不容筆者再饒舌。
上舉諸多評論,固有形容夸張之詞,但所指李詩諸特點,確鑿不虛,證諸李詩,要皆相合。囿于篇幅,也由于讀者對李詩一般較為熟悉,姑不再細析李詩,讀者若有興趣,可試做一對照印證。關于《豪放》與李白的特殊關系,茲再做如下申論。
首先,《豪放》“觀化匪禁”的“放”,較通常“放達”之放更加大放其胸襟視野,而“吞吐大荒”更將其“放”引向了更廣闊的宇宙空間,吐納天地,揮斥六合,冥搜微茫,驅駕神幻。考之文學實際,其所提倡的不羈之“放”,固然常為豪放作品所共有,但其具體渲染的這種“吞吐大荒”似的色彩,卻并非一般豪放作品所必須共同具備。試看蘇軾的《江城子?密州出獵》:“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此詞雖結尾處稍涉“大荒”,但總的看,寫的是實際生活,甚少“觀化匪禁,吞吐大荒”的具體色彩,卻依然顯得豪邁放達,成為千古豪放名作。對比來看,同是豪放之作,但李詩總體上顯然比蘇詞與《豪放》之所敘更為相似。如果將李詩與陶淵明那首被朱熹稱為露出豪放“本相者”的《詠荊軻》對照,同樣可以清楚看出,同為豪放之作,李詩比陶詩與《豪放》之所敘更為相近。就是說,雖然“吞吐大荒”的具體色彩并非為豪放詩作所必須具備,但李白詩歌是的確有著這樣的濃郁色彩的。
其次,豪氣真力等等,本來是也可以經由其他路徑而獲得而具備的,例如也可以經由倫理正義、浩然正氣的培養化成的儒家路數而獲得。寫下千古豪放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的文天祥,其人其詩所體現的豪氣與真力,不正是來自于凝聚著儒家精神的浩浩然倫理正氣嗎?然而,《豪放》顯然無取于此,它強調的是那種近乎道家而又加以了改造的、吸取了后來氣稟說的那樣一種路數:天地肇始,元氣充盈,天才本真,稟氣處得,豪情似狂,真力彌滿。這顯然與李白的人品詩風極為相近。這表明,《豪放》對豪氣真力之來源是做了有選擇的敘說的,其選擇和敘說,明顯與李白有關。
再次,豪情而至于“狂”,“萬象”而多瑰麗奇偉,同樣并非一般豪放風格所必備。這一點,只要看一看曹操、劉禹錫特別是蘇辛兩大家之作品就可以知道。然而,《豪放》卻對之很強調。這也顯然與李白其人其詩密切相關,因為這都正是李白李詩的顯著特點。
最后,《豪放》中一些有特色的詞語或意象,也為李詩所使用甚至是喜用。“前招三辰”中的三辰亦即日月星,古詩常用,李詩中亦多用,此不必細說。“后引鳳凰”中的“鳳凰”,李詩中極多見,如“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登金陵鳳凰臺》)“仙人騎彩鳳,昨下閬風岑”;(《擬古十二首》之十)“蓬湖雖冥絕,鸞鳳心悠然”;(《安陵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曉策六”的“”,同樣為李詩常用,“未夸觀濤作,空郁釣心”;(《贈薛校書》)“釣水路非遠,連意何深”;(《贈臨縣令皓弟》)“木落海水清,背睹方蓬”,(《贈盧征君昆弟》)……“濯足扶桑”的“扶桑”,李詩中亦很常見,如“余風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石袂”;(《臨路歌》)“月兔空藥,扶桑已成薪”。(《擬古十二首》之九)李詩又曾將“六鰲”與“扶桑”連用,“六鰲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登高丘而望遠海》)有的學者認為,《豪放》中的“六”“似又與‘日乘車,駕以六龍’的神話有關”。(劉禹昌《司空圖〈詩品〉義證及其他》)李白也曾將“六龍”與“扶桑”連用,“吾欲攬六龍,回車掛扶桑”。(《短歌行》)此外,到某廣遠奇幻之處“濯足”,也曾出現在李白的想象中。如《酬崔五郎中》:“舉身憩蓬壺,濯足弄滄海”;《郢門秋懷》:“終當游五湖,濯足滄浪泉”。李詩還曾直接用過“觀化”一詞,《贈盧征君昆弟》有云“滄州即此地,觀化游無窮”。其“觀化游無窮”與“觀化匪禁, 吞吐大荒”,從用詞到語意都顯然很近似。《豪放》品中這些極有特色的語匯和意象,在一般豪放詩人們如曹操、陶淵明、劉禹錫、蘇軾、辛棄疾等等的詩作中,是并不多見的,但它們的確為李白詩歌所常常使用,甚至成了李白詩歌的一種特色,很可能,李白詩歌就是《豪放》品“文字及意象的根源”。
綜上所論,很顯然,《豪放》所倡言的“吞吐大荒”似的不羈之放,來自本真天賦的元氣真力,由此而來的“豪”乃至于“狂”,瑰偉奇幻的“萬象”,以及《豪放》所使用的詞匯和意象,無不與李白及其詩作的特色若合符契。這充分說明,《豪放》品概括中國文學史上豪放類文學作品的基本特征和諸多相關特點,雖兼采眾家,但實與李白人品詩風關系尤為密切,其所謂“豪放”,完全可能更多的是從李白人品詩風中提煉而出復又更為明顯地指向了李氏李詩。從某種角度上甚至可以說,《豪放》實際上就是李白人品詩風的一曲頌歌!
[參考文獻]
[1]王潤華.司空圖新論[M].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9.
[2]漢唐佛教思想論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涂光社.原創在氣[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
[4]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M].北京:中華書局,1984.
On the Bold Beauty in the Twenty-Four Poetry, Boldness
ZHANG Guo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