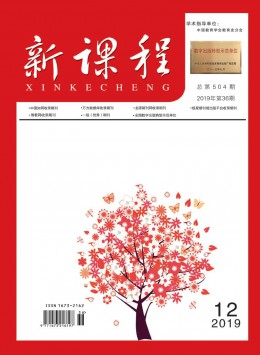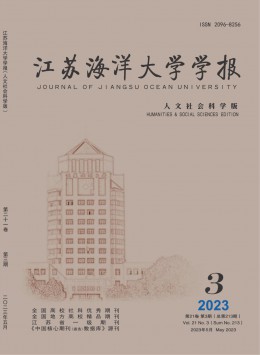表觀遺傳學意義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表觀遺傳學意義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表觀遺傳學意義范文
中圖分類號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高素質、高層次人才的重要手段。今天的社會對研究生的全面素質和創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專業課教學是研究生教育的最基本部分,是提高研究生專業素質和創新能力的直接途徑,因此,提高專業課教學水平對研究生的培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隨著生物技術和醫學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知識更新速度加快,學科之間相互交叉、相互滲透,邊緣學科和新興學科不斷涌現。表觀遺傳學是近幾年來生命科學迅速發展的前沿學科之一,其理論與技術已經廣泛滲透至生物學、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及預防醫學的各個學科。表觀遺傳學是我們學院學術型碩士研究生專業課程和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專業知識模塊的主干課程。如何適應新形勢下研究生培養的需要,筆者主要針對研究生表觀遺傳學教學談一些自己的看法及建議。
1 教師業務素質的提高
生物醫學模式的轉變對教師的業務素質和能力提出了相應的更高要求。不僅要求教師有生命科學、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的專業知識,而且還要有生物醫學理論方面的知識,同時要求教師的技術知識層次能跟上生物醫學實驗技術推廣周期不斷縮短的趨勢。我們在研究生的表觀遺傳學教學中,隨時進行文獻調研,密切關注最新高水平期刊和學術會議的相關信息,不斷補充傳達的最新知識。引導學生關注當前研究活躍的腫瘤、衰老、心血管疾病、感染性疾病與表觀遺傳學的最新研究進展情況,著重介紹營養、環境、應激、細胞代謝在表觀遺傳變化中的重要作用機制。這些新知識非常受研究生的歡迎,引起他們濃厚的興趣。通過這些新知識的學習,不僅開闊了研究生的學習視野,啟發了他們的創新思維,同時使他們形成良好的文獻調研和學術研討的習慣,逐步形成和掌握正確的科研方法,為即將開展的課題研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教學過程中反過來能進一步促進教師知識結構的不斷更新,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
2 改革教學內容,形成完整的表觀遺傳學知識結構體系
與經典遺傳學以研究基因序列決定生物學功能為核心相比,表觀遺傳學主要研究基于染色質事件對于這些“表觀遺傳密碼”的建立和維持的機制,及其如何決定細胞的表型和個體的發育。在表觀遺傳學研究生課堂教學過程中必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引導研究生關注表觀遺傳學學科的發展動態,密切注意學科的交叉和延伸,緊跟表觀遺傳學的發展方向和學科發展的突破點。課堂教學過程中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表觀遺傳學學科領域發展最活躍最富潛力的研究方向上,例如表觀遺傳機制在癌癥等疾病中的作用機制,細胞代謝與表觀遺傳變化的關系等。表觀遺傳學是生命科學中一個普遍而又十分重要的新研究領域。它不僅對基因表達、調控、遺傳有重要作用,而且在腫瘤、免疫、病毒感染復制等許多疾病的發生和防治中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教學過程中主要內容包括:表觀遺傳學概論,DNA甲基化,組蛋白修飾,染色質重塑,基因組印記,X染色體失活,siRNA與miRNA介導的調控,表觀遺傳學與疾病,表觀遺傳學與癌癥,天然產物及中草藥的發展對表觀遺傳學的展望,表觀遺傳學的治療進展。上述內容形成完整的表觀遺傳學知識結構體系。在教學過程中,通過有選擇地插入一些小型專題講座及相關的研究歷史背景資料的方式,介紹和強調學習和掌握表觀遺傳學的重要性,既活躍了課堂,又把課程從枯燥的理論講解中解放出來,同時激發了研究生的學習積極性,拓寬相關的知識面[2]。同時在教學過程中注重前沿進展內容的加入,如代謝、營養、環境等影響因素與表觀遺傳學的相關進展。
3 改革教學方法,培養研究生的創新能力
本課程所授課的對象是已具備一定自學能力和學習主動性的研究生,最重要的是培養他們科學地發現并解決問題的能力、準確表達個人思想見解的能力以及科研創新能力。本課堂選課人數一般在十人左右,因此課堂教學的特點在于小班授課。由于是小班教學,增加了教學的靈活性和增強了師生之間互動的可能性,師生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增多。因此在教學過程中采用教師課堂授課、學生參與研討、學生講授等多種教學方式,強調講授、研論、文獻調研、學術講座、論文報告、文獻綜述等多種方式并重的原則。在教學過程中,合理安排時間,讓研究生充分參與到教學的研討,結合自己的研究方向發表自己獨特的見解,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這種教學方式為研究生迅速進入科研工作的角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增強了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培養。發揮現代多媒體技術在教學中的重要作用,電子課件與板書相結合,同時采用圖片、視頻播放、動畫等多種方式的應用。倡導啟發式教育,摒棄灌輸式教學方法,講授基本理論知識的同時注意結合科研最新進展情況拓寬學生知識面,加強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使學生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應用能力同步得到提高,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對由于受學時限制而不能在課堂上詳細介紹的前沿內容可使用討論法,安排學生課后自學,啟發學生提出問題,通過課堂討論得到解決。還可以在部分單元結束后,要求研究生根據自己的專業方向,結合查閱最新的文獻資料,撰寫小專題報告,組織交流討論,以便鞏固學生所學知識,并進一步拓寬知識面。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他們有強烈的求知欲孥,有較高的學習熱情,有較強的自學能力,所以在教學中倡導自學,組織討論,是因材施教、培養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好方法。
4 多種考核方式結合,檢驗教學效果。
在研究生的考核方面,不僅僅局限于對課內授課內容的掌握程度,還可以采用綜述、專題小報告、PPT匯報、模擬課題設計等綜合考核方式,注重知識的活學活用和創新意識的培養,這樣才有利于研究生即打好廣博、堅實的理論基礎,又能其重組知識框架,只有這樣,研究生的創新意識才能夠得到增強。
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是受多因素復雜交錯影響的,要提升研究生的創新能力,既要保證培養研究生的客觀條件充足,又要發揮研究生的主觀能動性。研究生教育只有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才能不斷培養出符合社會需要的高層次創新型人才。表觀遺傳學既是目前迅速發展的學科和熱點領域,在生物醫學各種學科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也是我們學院研究生重要的專業基礎課,對于培養研究生的創新意識,培養研究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在教學實踐中不斷地提高教師自身素質,調整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才能達到預期目的。
參考文獻
第2篇:表觀遺傳學意義范文
關鍵詞:DNA的可逆化學修飾;胞嘧啶的甲基化;5mC去甲基化;哺乳動物;細胞分化
一、導言
細胞是生命體最基本的單位,其能組成頭發、眼睛、心臟等各種各樣的器官,并最終組成一個完整的生物個體。細胞核是細胞的“司令部”,而在細胞核中的“司令”們則是脫氧核糖核酸(DNA)。DNA由四種基本的單位腺嘌呤(A)、鳥嘌呤(G)、胸腺嘧啶(G)以及胞嘧啶(C)組成(圖1),其序列信息編碼了生物個體及種群的整個生命周期,因此其必須在整個周期中保持高度穩定。另一方面,DNA需要編碼多細胞生物中多種多樣的細胞活動,使其具有不同的形態、發揮不同的功能。這一看起來矛盾的兩個方面是由DNA的可逆化學修飾來調和的:DNA可以發生化學修飾,從而在不影響序列穩定性的基礎上擴充其生物學功能。這種具有調控功能的修飾被稱為表觀遺傳學修飾。
二、胞嘧啶的甲基化
多細胞生物中不同種類細胞的差異是由于其不一樣的基因表達情況決定的,細胞中不同的基因表達情況可以由多種化學修飾調控。哺乳動物細胞中存在最廣泛的修飾是5-甲基胞嘧啶(5mC)(圖2),它在生物個體的發育與疾病發生過程中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5mC主要出現在胞嘧啶-鳥嘌呤二核苷酸位點(CpG)上,哺乳動物基因組中大約60%~80%的CpG位點會出現5mC修飾。5mC的主要功能包括X染色體失活、抑制逆轉座元件的活性以及基因表達調控。
圖2胞嘧啶的可逆化學修飾
5mC在化學上是穩定的:甲基通過一個穩定的碳-碳共價鍵連接到胞嘧啶的5號位(圖2),因此具有很高的鍵能,若想要直接破壞這種結構不是那么容易。5mC在遺傳學上也是穩定的:DNA甲基轉移酶(DNMT3A、DNMT3B)能夠直接將甲基連接到胞嘧啶上,DNA甲基轉移酶1(DNMT1)也可以識別雙鏈DNA中只有一條鏈含有5mC的位點并將其互補鏈進行甲基化修飾;這種甲基化維持的機制可以保證DNA復制過程中新合成的鏈上帶有同樣的表觀遺傳學修飾。
三、5mC的去甲基化
盡管5mC是很穩定的,其需要通過多種途徑進行去修飾,從而發揮其在細胞分化與個體發育中的調控作用。如在胚胎發育過程中,5mC會發生劇烈的重編程。最重要的三個表觀遺傳學重編程過程發生在:(1)受精卵的著床前發育過程;(2)著床后胚胎發育過程;(3)精、卵子前體細胞發育過程。
5mC可以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去除:(1)被動稀釋甲基化:在一些情況下維持甲基化狀態的酶是不工作的,因此在發生DNA復制后,新合成的鏈上不帶有5mC修飾。隨著細胞分裂的進行,這種胞嘧啶的共價修飾就逐漸被稀釋了;(2)主動去甲基化:TET家族蛋白可以將5mC氧化并生成5-羥甲基胞嘧啶(5hmC)、5-醛基胞嘧啶(5fC)以及5-羧基胞嘧啶(5caC)(圖2)。氧化后的5mC可以通過不同途徑進行去修飾作用,一是通過細胞分裂過程中的DNA復制進行被動稀釋去修飾,二是通過TDG酶介導的堿基切除修復(BER)通路將其主動的還原成一個普通的胞嘧啶堿基(圖2)。
5mC的主動去甲基化過程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也受到了多層次的嚴格調控。(1)TET酶接觸到底物的難易程度是一種最直接的調控主動去甲基化過程的方式:細胞核中的DNA會被不同種類以及修飾狀態的蛋白結合并包裹起來,因此被TET酶結合并識別的概率是不一樣的。(2)TET酶發揮氧化作用時本身也需要多種不同的輔助因子:如α-酮戊二酸以及二價鐵離子,這些因素濃度的變化會影響TET酶的活力;此外,維生素C也能直接與TET酶的催化位點結合以及通過促進輔助因子二價鐵的生成從而增強TET酶的活性。(3)參與到主動去甲基化過程中的所有的酶本身的表達水平也可以受到上游機制的調控。(4)一些輔助蛋白可以幫助參與主動去甲基化的蛋白到達基因組上的特定位點從而實現特異性的去甲基化。
四、主動去甲基化的功能
在人以及鼠的卵子受精后的很短時間內,受精卵會發生劇烈的表觀遺傳學重編程,其中包括父源以及母源的全基因組水平的DNA去甲基化。在這個過程中,來自母方的基因組主要通過被動稀釋來完成去甲基化,而來自父方的基因組則會受到主動去甲基化與被動稀釋去甲基化的雙重影響。受精卵在這個過程能夠擦除絕大部分來自父母的表觀遺傳學印記,并在后續的胚胎發育過程中重新建立新的表觀遺傳學印記。
由于神經細胞中存在很高含量的5hmC,因此主動去甲基化如何幫助神經細胞發揮正常功能是一個熱點問題。TET1蛋白對于小鼠大腦的正常記憶與學習功能是必需的,TET1含量的變化能夠影響神經細胞中的基因表達情況。此外,TET3也在小鼠的嗅覺神經細胞以及視覺神經細胞中發揮重要作用,其功能的異常會影響神經細胞中的5mC以及5hmC的含量,進而會影響基因的正常表達情況以及神經組織的發育。
異常的DNA去甲基化也會導致癌癥。在小鼠模型中,TET2催化功能的缺失會影響造血干細胞的自我更新能力,從而導致惡性血癌的發生。TET1以及TET3的功能突變也與多種其他類型的癌癥相關。因此,DNA主動去甲基化能否正常發揮功能,關系到5mC修飾以及細胞中的基因表達情況;這個過程如果出現異常,則可能導致包括癌癥等疾病在內的細胞功能異常。
五、總結與展望
哺乳動物個體每個細胞中的基因組均包含完全一致的DNA序列信息,但是不同種類的組織中的細胞卻能夠具有完全不一樣的基因表達情況從而發揮不同的功能。包括5mC在內的多種不同類型與層次的化學修飾能夠在不影響DNA序列穩定性的基礎上實現基因表達的差異化調控。
胞嘧啶的甲基化修飾狀態能決定細胞的種類與命運,因此在胚胎與個體發育過程中每個不同的細胞需要逐漸獲得不同的表觀遺傳學修飾狀態。另一方面,受精卵需要擦除來自父母雙方的表觀遺傳學信息,從而重新建立新的表觀遺傳學印記,DNA的主動去甲基化在這一表觀遺傳學重編程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細胞中的表觀遺傳學狀態的異常可能會導致包括癌癥在內的多種疾病。
第3篇:表觀遺傳學意義范文
1 DNA甲基化和組蛋白乙酰化
1.1 DNA甲基化 DNA甲基化是指在DNA復制以后,在DNA甲基化酶的作用下,將S-腺苷甲硫氨酸分子上的甲基轉移到DNA分子中胞嘧啶殘基的第5位碳原子上,隨著甲基向DNA分子的引入,改變了DNA分子的構象,直接或通過序列特異性甲基化蛋白、甲基化結合蛋白間接影響轉錄因子與基因調控區的結合。目前發現的DNA甲基化酶有兩種:一種是維持甲基轉移酶;另一種是重新甲基轉移酶。
1.2 組蛋白乙酰化 染色質的基本單位為核小體,核小體是由組蛋白八聚體和DNA纏繞而成。組蛋白乙酰化是表觀遺傳學修飾的另一主要方式,它屬于一種可逆的動態過程。
1.3 DNA甲基化與組蛋白乙酰化的關系 由于組蛋白去乙酰化和DNA甲基化一樣,可以導致基因沉默,學者們認為兩者之間存在串擾現象。
2 表觀遺傳學修飾與惡性腫瘤耐藥
2.1 基因下調導致耐藥 在惡性腫瘤中有一些抑癌基因和凋亡信號通路的基因通過表觀遺傳學修飾的機制下調,并與化療耐藥有關。其中研究比較確切的一個基因是hMLH1,它編碼DNA錯配修復酶。此外,由于表觀遺傳學修飾造成下調的基因,均可導致惡性腫瘤耐藥。
2.2 基因上調導致耐藥 在惡性腫瘤中,表觀遺傳學修飾的改變也可導致一些基因的上調,包括與細胞增殖和存活相關的基因。上調基因FANCF編碼一種相對分子質量為42000的蛋白質,與腫瘤的易感性相關。2003年,Taniguchi等證實在卵巢惡性腫瘤獲得耐藥的過程中,FANCF基因發生DNA去甲基化和重新表達。另一個上調基因Synuclein-γ與腫瘤轉移密切相關。同樣,由表觀遺傳學修飾導致的MDR-1基因的上調也參與卵巢惡性腫瘤耐藥的形成。
3 表觀遺傳學修飾機制在腫瘤治療中的應用
3.1 DNA甲基化抑制劑 目前了解最深入的甲基化抑制劑是5-氮雜脫氧胞苷(5-aza-dc)。較5-氮雜胞苷(5-aza-C)相比,5-aza-dc首先插入DNA,細胞毒性比較低,并且能夠逆轉組蛋白八聚體中H3的第9位賴氨酸的甲基化。有關5-aza-dc治療卵巢惡性腫瘤的體外實驗研究結果表明,它能夠恢復一些沉默基因的表達,并且可以恢復對順柏的敏感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hMLH1基因。有關地西他濱(DAC)治療的臨床試驗,研究結果顯示,結果顯示:DAC是一種有效的治療耐藥性復發性惡性腫瘤的藥物。 3.2 HDAC抑制劑 由于組蛋白去乙酰化是基因沉默的另一機制,使用HDAC抑制劑(HDACI)是使表觀遺傳學修飾的基因重新表達的又一策略。根據化學結構,可將HDACI分為短鏈脂肪酸類、氯肟酸類、環形肽類、苯酸胺類等4類。丁酸苯酯(PB)和丙戊酸(VPA)屬短鏈脂肪酸類。PB是臨床前研究最深入的一種HDACI,在包括卵巢惡性腫瘤在內的實體腫瘤(21例)Ⅰ期臨床試驗中有3例患者分別有4~7個月的腫瘤無進展期,其不良反應是短期記憶缺失、意識障礙、眩暈、嘔吐。因此,其臨床有效性仍有待于進一步在Ⅰ、Ⅱ期臨床試驗中確定。在VPA的臨床試驗中,Kuendgen等在對不同類型血液系統腫瘤中使用VPA進行了Ⅱ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不同的患者有效率差異甚遠。辛二酰苯胺異羥肟酸(SAHA)是氯肟酸類中研究較深入的一種HDACI。其研究表明,體內使用安全劑量SAHA時,可有效抑制生物靶點,發揮抗腫瘤活性。大量體外研究結果顯示,聯合使用DNA甲基化抑制劑和HDACI會起到更明顯的協同作用。
3.3 逆轉耐藥的治療 Balch等使用甲基化抑制劑—5-aza-dc或zebularine處理卵巢惡性腫瘤順柏耐藥細胞后給予順柏治療,發現此細胞對順柏的敏感性分別增加5、16倍。在臨床試驗中,Oki等將DAC和伊馬替尼(imatinib)聯合使用治療白血病耐藥患者,結果說明,應用表觀遺傳學機制治療惡性腫瘤確實可以對化療藥物起到增敏作用,并且在一定范圍內其療效與體內表觀遺傳學的改變呈正比。Kuendgen和Pilatrino等對HDACI和化療藥物的給藥順序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在使用VPA達到一定血清濃度時加用全反式維甲酸可增加復發性髓性白血病和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患者的臨床緩解率,這可能與VPA引起的表觀遺傳學改變增加患者對藥物的敏感性有關。
第4篇:表觀遺傳學意義范文
自從1957年Waddington提出表觀遺傳學的概念后,表觀遺傳學和表觀基因組學有了相當大的發展。表觀基因組學是在全基因組水平上研究表觀遺傳學標志及其與基因表達的相互關系。這一新興領域已對毒理學研究與實踐產生重大的影響。國內,表觀遺傳學在毒理學研究已較深入地開展了一些研究,并發表了綜述。
1外源化學物的表觀遺傳毒性
基因表達的表觀遺傳調控是通過DNA甲基化,組蛋白編碼和相關的非編碼RNA(如miRNA)來完成的。3種機制各自的貢獻取決于特定基因及其環境,如物種,細胞類型,機體的發育階段和年齡,此外,每個因素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因此,表觀基因組的調控是一個強大的和動態的綜合過程,在發育和維持分化狀態中起關鍵作用。雖然表觀基因組不是所有的改變預期都是有害的,但有些可能產生有害結果(如發育異常,增加疾病易感性等)。在體外,動物和人類的研究已經確定了幾類環境化學物,可以修飾表觀遺傳標志,包括金屬、過氧化物酶體增殖劑、空氣污染物、毒物和內分泌干擾物/生殖毒物。目前環境化學物表觀遺傳標志的研究大多數集中在DNA甲基化,只有少數研究涉及組蛋白修飾和miRNA(表1~3)。外源化學物引起表觀遺傳學改變可影響細胞應激,并是潛在可逆的;也可能是可遺傳的。表觀遺傳毒性(epigenotoxicity)是指脫離外源化學物暴露后,可遺傳的有害改變。廣義的表觀遺傳毒性也可以包括外源化學物引起非遺傳的表觀遺傳學改變中介的外源化學物毒效應。可遺傳的表觀遺傳毒性和表觀遺傳改變中介的毒效應是有區別的。表觀遺傳毒性可以被分為有絲分裂的,減數分裂的或跨代遺傳的3類。表觀遺傳毒性這一新興研究領域對毒理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下文主要討論目前表觀遺傳毒性測試的主要發現及國際生命科學研究所(ILSI)“評估表觀遺傳變化”的研討會的意見。
2表觀遺傳毒性的主要發現
2.1化學致癌近年來在多種腫瘤細胞觀察到表觀遺傳事件。表觀遺傳事件可能引起基因表達的變化通過DNA甲基化,組蛋白修飾和/或染色質重構。并估計,在腫瘤細胞中檢測到甲基化變化的數目遠遠多于遺傳改變的數目。研究發現表觀遺傳事件參與環境與職業因子誘發癌變進程的引發和進展。DNA甲基化異常對腫瘤發生有因果關系作用,甲基胞嘧啶增加突變可能性,增加致癌物結合,腫瘤抑制基因沉默,DNA修復基因沉默,癌的DNA低甲基化和遺傳學改變。組蛋白修飾可能通過影響DNA修復和細胞周期關卡,引起遺傳學改變。傳統的致癌性試驗可確定表觀遺傳修飾誘導腫瘤的可能性。許多不同的嚙齒類致肝癌物已被確定,而研究發現這些化合物的作用模式并無遺傳毒性,與人類也無關聯性。例如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α(PPAR-A)介導的和構成性雄甾烷受體(CAR)介導的嚙齒類動物癌變。肝腫瘤促長劑苯巴比妥(PB),其與CAR的激活和隨后的效果相關。PB誘導的嚙齒類表觀遺傳學改變包括甲基化改變的區域,基因表達的特殊改變和外源性及內源性化合物的代謝。持續的核受體介導的肝臟致癌物的分子分析,將更加明確地表征每個受試化合物的作用模式。表觀基因組正常變異性的表征和與處理相關的表觀遺傳學影響的理解,將是研究致癌作用模式的巨大挑戰。
2.2遺傳毒理學評價化學物引起遺傳損傷的能力是風險評定的重要內容。表觀遺傳學影響基因表達的可遺傳的變化可能構成遺傳毒性。表觀遺傳導致基因改變的機制包括:錯配修復基因表觀遺傳缺陷,增加DNA修復基因表觀遺傳缺陷與癌癥特定突變譜相關,參與雙鏈斷裂修復的基因的表觀遺傳失活,有絲分裂關卡基因表觀遺傳缺陷,致癌物解毒基因與甲基胞嘧啶突變可能性增加,DNA全面低甲基化和染色體不穩定等。已經確定表觀遺傳學改變在腫瘤形成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在腫瘤發展過程中DNA甲基化模式的改變往往是最早觀察到的分子事件。甲基胞嘧啶(5meC)已知是C∶G至T∶A轉換突變的熱點,起因于胞嘧啶自發性水解和酶脫氨基率的增加和DNA修復降低。增加的5meC脫氨基率和T堿基修復受限可解釋在CpG位點突變頻率的增加。人類腫瘤p53基因突變的1/4和腫瘤抑制基因p16的C-T轉換的1/3已知會發生在CpG位點上。突變的增加也可能來自于飲食中甲基供體的不足。已證明葉酸補充劑能減少潰瘍性結腸炎患者發生結腸癌的風險和和預防結腸癌細胞p53突變。參與葉酸代謝的酶遺傳多態性影響表觀遺傳標志,改變SAM水平,并能調節結腸癌的風險。也已提出DNA氧化性損傷在癌癥的發生、心血管疾病和衰老中所起的作用。8-羥基鳥嘌呤(8oxoG)改變了CpG二核苷酸相鄰的C的甲基轉移酶活性,可能改變DNA甲基化。在CpG內C5-位的損傷影響DNA甲基化。在體外,5meC和5-氯C因啟動子甲基化引起次黃嘌呤-鳥嘌呤磷酸核糖基轉移酶(Hgprt)基因的沉默。此外,CpG內的8oxoG和HmC或顯著減少結合于DNA的MeCP2,并直接導致染色質結構改變。光二聚物,烷基化堿基,脫堿基位點,以及鏈斷裂也會誘導DNA的甲基化變化。對性細胞的致突變性將于下文討論。體外哺乳動物細胞基因突變試驗能夠篩選表觀遺傳學介導的危害。例如,在不同嚙齒類細胞系經5-氮胞苷處理TK基因可恢復活性。此外,DNA合成抑制劑3-疊氮基-3-脫氧胸苷(AZT)可引起TK位點超甲基化。應進一步開發篩選試驗以確定表觀遺傳學中介的遺傳毒性。
2.3發育與生殖的表觀遺傳毒理學完全分化的體細胞,在正常情況下,將有相對穩定的表觀基因組傳遞到子代細胞。但在哺乳動物的發育過程中,早期胚胎發育過程(著床前),以及在子宮內原始生殖細胞的發育過程中,有兩個表觀遺傳學的重編程階段,重新設置DNA的甲基化模式。這兩個發育的表觀遺傳重編程事件有可能是破壞表觀遺傳編程的敏感窗口。發育和生殖毒理學家特別感興趣的是毒物暴露是否可以直接改變發育的表觀基因組,有害的表型是否可跨代遺傳,及因此存在的潛在危害。表觀遺傳編程紊亂可能有助于對表型的跨代遺傳。使用Avy小鼠(黃色刺小鼠)模型,飲食暴露雙酚A,使Avy和CabpIAP亞穩外延等位基因低甲基化。甲基供體膳食補充劑或染料木素可抵消此低甲基化效應。這些結果與造成表觀遺傳影響的其他內分泌干擾物報告一致。在環境相關水平低濃度的雙酚A(1.2和2.4μg/kg體重)對大鼠可誘導跨代遺傳表型異常。暴露于雙酚A圍生期雄性后代的計數和活力降低,并在F3代持續這些表型。甲氧滴滴涕和乙烯菌核利在子宮中暴露也會導致跨代生殖遺傳表型異常。雖然甲氧氯和乙烯菌核利在高于人類接觸的劑量觀察到病理學改變,但此研究提供了一個模型來研究表觀遺傳跨代的機制。已證明,乙烯菌核利暴露后破壞了多達3代的小鼠一些印跡基因甲基化模式,這表明跨代遺傳異常的表型也有表觀遺傳的基礎。
2.4免疫毒理學已發現,表觀遺傳調控多能幼稚輔T細胞(Th)分化的啟動和其效應亞群的成熟。啟動后不久,幼稚T細胞同時轉錄低水平的Th1(CD4)和Th2(CD8)細胞因子,包括IL-2。在選擇性轉錄成為Ifng(Th1細胞因子標記)或Th2細胞因子基因(IL-4和IL-5,IL-13)之前需要幾次復制。在體外用5-aza誘導T細胞,導致由早先不產生這些細胞因子的T細胞系產生IL-2和IFN-g。在用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劑處理的CD4T細胞研究證實干擾素IFN-G和Th2型細胞因子的表達增強。上述研究結果表明,表觀遺傳機制是Th細胞分化和功能的關鍵因素。盡管與小鼠相比,人類IFNG基因缺乏脫甲基化,分化的人類Th細胞CpG甲基化分析顯示出與小鼠類似的結果。將化學物誘導的小鼠T細胞分化的表觀遺傳學改變數據外推到人應要謹慎。
2.5其他終點從鼠類模型或單一基因的表觀遺傳學的某些成果已被外推于人類疾病原因。表觀遺傳學基礎的表型被認為是人類疾病的起源有待進一步的研究,特別是確定表觀遺傳的正常變異和評價表觀遺傳影響需要適當的實驗設計和對照。已經提出,內分泌干擾物的表觀遺傳毒性可能導致暴露人群的許多發育,代謝和行為障礙。對其他靶器官或終點的表觀遺傳毒性還有待研究。
2.6檢測流程和模型Szyf2007年對檢測表觀遺傳毒性提出的研究思路為:①在生命一個時間點的環境暴露可能會改變表觀遺傳編程,導致穩定改變表型和反應性,②毒物暴露可能導致表觀遺傳重編程,導致生命后期表型的變異。Reamon-Buettner和Borlak提出使用動物模型(如鼠類)環境暴露后分析表觀遺傳機制的研究方案,見圖1。已推薦了檢測表觀遺傳毒性的動物模型,特別是Avy小鼠和Axin1融合(Axin1Fu)小鼠能用于研究表觀遺傳學和發育畸形之間的聯系,因為在特定的DNA甲基化模式的改變可以與小鼠遺傳疾病廣泛鏈接。
3ILSI的“評估表觀遺傳變化”研討會
2009年10月ILSI的健康與環境科學研究所(IL-SI/HESI)主辦“評估表觀遺傳變化”研討會,評估和提高表觀遺傳學方面的科學知識基礎及其在疾病中的作用,包括跨代的表觀遺傳變化的影響,還討論了將表觀遺傳納入安全性評價的幾個問題。
3.1可能用于評價化學物產生表觀遺傳毒性的模型系統大鼠和/或兔可能是評價外源化學物產生表觀遺傳變化影響F1和/或F2和F3代的適當的模型。小鼠可能是更易于處理的模型,因為小鼠基因組有更多的數據,并已有用于檢測表觀遺傳變化的工具。已建議Avy小鼠模型作為潛在的篩查工具,其毛色受亞穩Avy等位基因IAP隱蔽啟動子附近CpGs甲基化狀態的影響。然而,Avy小鼠模型用于篩選可能過于敏感。其他可能的模型包括斑馬魚和秀麗隱桿線蟲,以及蜜蜂和果蠅。體外模型是使用哺乳動物細胞或利用干細胞。干細胞包括其他物種不存在的印跡基因。印跡基因有可能作為確定表觀遺傳改變的感應器。以上討論的模型有可能用于潛在危害識別,并提供機制基礎。然而,將很難直接解釋這些數據對整體動物和人類的意義。在表觀遺傳模型轉化為管理決策測試之前,需要進行大量的基礎工作和驗證研究。
3.2可能評價的終點/靶對于表觀遺傳變化的指標,應確定適應反應還是有害反應。確定表觀遺傳修飾與可能提示特定有害影響的疾病相關基因表達改變之間的因果關系或強的關聯需要表型錨定。在發現受影響的表觀遺傳效應的基因與某種疾病相關的基礎上,應建立由表觀遺傳機制調控的基因數據庫。表觀遺傳效應很可能有物種,組織,暴露和時間特異性。目前,在研究中實驗對照組是化合物反應表觀遺傳變化的最適當的參照,建立表觀遺傳印跡的參考對照范圍可能是有意義的,因為這些區域甲基化模式可能更趨于穩定和遺傳。
3.3可能應用的技術關于DNA甲基化和miRNA,以陣列為基礎的平臺,針對人類和小鼠樣品已優化。針對大鼠可用的工具有限,但可用根據大鼠基因組序列基于陣列的高通量方法。雖然硫酸氫鹽為基礎的測序評價DNA甲基化方法可用于所有物種,但需要發展高通量測序方法。區分異常信號和背景信號并不容易,最大的挑戰將是數據分析和解釋,應發展信息學。
3.4管理機構的觀點為了將表觀遺傳毒性納入風險評定,有很多的考慮。必須明確的問題,理解環境、營養和/或藥物暴露對個人,群體及跨代水平的公共健康的潛在長期影響,界定希望解決的問題,確定模型系統。這就需要努力使與有害結局和基線改變相聯系的研究設計、方法和模型標準化。以適當的參考化合物、途徑和劑量驗證該模型。模型試驗檢測的任何變化必須以合理的方式鏈接到表型或臨床結局。對于法規測試,方法必須標準化,具有重復性和重現性。為了將表觀遺傳數據有效地納入人類風險評定,最好與管理機構共同努力,確定一個正常基線范圍,并與有害結局關聯,界定公共衛生關注的適當水平。管理機構將需要開發分析工具,以對公共健康方面的數據進行解釋,并將此類數據應用于風險評定模式和慢性健康結局。
第5篇:表觀遺傳學意義范文
【摘要】
目的RAS相關結構域蛋白1A基因(RASassociateddomainfamily1Agene,RASSF1A)啟動子區超甲基化介導的基因轉錄失活在卵巢癌中頻見,可作為卵巢癌診治過程中有意義的分子生物學指標,RAS相關結構域蛋白2A基因(RASassociateddomainfamily2Agene,RASSF2A)與RASSF1A同源,其基因異常甲基化在多種腫瘤發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本研究探討上皮性卵巢癌組織RASSF2A甲基化水平,并分析其臨床意義及高甲基化與mRNA表達情況的相關性。方法選擇2013-10-01-2014-12-31聊城市人民醫院手術治療的50例上皮性卵巢癌、27例交界性上皮性卵巢腫瘤和20例良性上皮性卵巢腫瘤患者,應用甲基化特異性PCR(MSP)檢測卵巢腫瘤組織中RASSF2A基因啟動子甲基化狀態,采用RT-PCR檢測其mRNA表達水平。采用5-氮雜2′-脫氧胞苷(5-aza-dC)對人卵巢癌細胞株SKOV3、3AO進行去甲基化干預實驗,并檢測藥物作用前后RASSF2A基因啟動子甲基化及其mRNA的表達情況。結果RASSF2A基因mRNA在良性上皮性卵巢腫瘤中的表達陽性率為95.00%(19/20),交界性上皮性卵巢腫瘤為59.26%(16/27),上皮性卵巢癌組織為34.00%(17/50),表達強度依次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1.855,P<0.001。RASSF2A基因啟動子在良性上皮性卵巢腫瘤組織中的甲基化率為0(0/20),交界性上皮性卵巢腫瘤為22.22%(6/27),上皮性卵巢癌組織為46.00%(23/5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5.474,P<0.001。RASSF2A甲基化水平與卵巢癌患者的年齡、病理類型、臨床分期、組織分化程度及淋巴結轉移無明顯相關性。RASSF2A基因甲基化與其mRNA的表達呈負相關,甲基化陽性組織的mRNA表達水平明顯低于甲基化陰性組織。5-aza-dC藥物作用后,卵巢癌細胞株中RASSF2A基因甲基化被逆轉,而其基因表達明顯升高。結論RASSF2A啟動子區高甲基化導致的基因表達沉默與上皮性卵巢癌的發生發展有關。
【關鍵詞】
上皮性卵巢癌;甲基化;RAS相關結構域蛋白2A基因;基因檢測
上皮性卵巢癌是女性生殖系統中惡性程度最高和預后最差的腫瘤,其病死率居婦科惡性腫瘤首位[1]。大量研究已證實,RAS相關結構域蛋白1A基因(RASassociateddomainfamily1Agene,RASSF1A)啟動子區超甲基化介導的基因轉錄失活是卵巢癌中的頻發事件,可作為卵巢癌診治過程中有意義的分子生物學指標[2-4]。與RASSF1A具有高度同源性的RAS相關結構域蛋白1A基因(RASassociateddomainfamily2Agene,RASSF2A)異常甲基化在多種腫瘤的發生和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本研究通過RT-PCR和MSP方法檢測良性上皮性卵巢腫瘤、交界性上皮性卵巢腫瘤和上皮性卵巢癌組織及卵巢癌細胞株中RASSF2AmRNA的表達及其啟動子甲基化狀態,分析RASSF2A啟動子甲基化與其mRNA的表達以及卵巢癌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探討RASSF2A啟動子區甲基化在卵巢癌發生發展中的作用。
1材料與方法
1.1標本來源收集2013-10-01-2014-12-31聊城市人民醫院婦產科收治的上皮性卵巢癌患者50例,交界性上皮性卵巢腫瘤27例,良性上皮性卵巢腫瘤20例。所有組織標本均經病理學確診,所有患者術前均未接受任何放化療或激素治療。標本采集在離體后10min內進行,并迅速放入液氮罐保存,后轉移至-80℃冰箱保存。上皮性卵巢癌病例中,依據2006年FIGO分期標準,Ⅰ~Ⅱ期19例,Ⅲ~Ⅳ期31例;依據2003年WHO組織學分類標準,漿液性腺癌24例,黏液性腺癌16例,子宮內膜樣癌10例;高分化10例,中分化15例,低分化25例;有淋巴轉移27例,無淋巴轉移23例;年齡<50歲者19例,≥50歲者31例。
1.2細胞株卵巢癌細胞株SKOV3和3AO由聊城市人民醫院中心實驗室提供。
1.3主要試劑Trizol試劑購自美國Invitrogen公司,DNA甲基化試劑盒購自德國Qiagen公司,引物均由上海生工設計合成。
1.4實驗方法
1.4.1細胞培養及藥物處理在37℃、5%CO2及飽和濕度的孵育箱中靜置培養卵巢癌細胞株,用含10%胎牛血清的RPMI1640細胞培養基及時換液。用終濃度為10μmol/L的5-aza-dC處理卵巢癌細胞株,常規換液,保持上述藥物濃度。于藥物連續作用72h后收集細胞。
1.4.2RT-PCR檢測參照Trizol試劑說明書提取組織及細胞總RNA。測得其濃度及純度符合實驗要求后,取2μL總RNA進行逆轉錄。所得cDNA經半定量PCR擴增。RASSF2A基因上游序列為5′-GCG-CCTAGAACGTGTTTTTC-3′,下游序列為5′-ACT-AGGCGTCCTCACATTGC-3′,擴增產物長度為563bp。以GAPDH作為內參基因,上游為5′-CAA-CGGATTTGGTCGTATT-3′,下游為5′-CACAGTC-TTCTGGGTGGC-3′,擴增片段長度為166bp。PCR反應條件為95℃10min,95℃30s,58℃30s,72℃30s,30個循環,最后72℃延伸10min。擴增產物在2%瓊脂糖凝膠電泳,紫外線下觀察實驗結果。
1.4.3DNA的提取及亞硫酸鹽修飾采用酚氯仿法提取組織及細胞總DNA,并對基因組DNA進行亞硫酸鹽修飾,按照甲基化特異性PCR試劑盒說明書進行。所得產物直接用于PCR擴增或保持在-20℃冰箱保存備用。
1.4.4甲基化特異性PCR使用2對引物檢測RASSF2A基因啟動子甲基化狀態。甲基化引物正義鏈為5′-GTTCGTCGTCGTTTTTTAGGCG-3′,反義鏈為5′-AAAAACCAACGACCCCCGCG-3′,非甲基化引物正義鏈為5′-AGTTTGTTGTTGTTTTTTA-GGTGG-3′,反義鏈為5′-AAAAAACCAACAACCC-CCACA-3′,擴增產物長度均為108bp。反應條件為95℃預變性10min,95℃變性30s,58℃復性30s(甲基化);54℃復性30s(非甲基化),72℃延伸30s,35個循環,最后72℃延伸10min。所得產物電泳后攝像,分析結果。
1.4.5甲基化結果判定標準若僅甲基化引物擴增出陽性條帶,為完全甲基化;若僅非甲基化引物擴增出陽性條帶,為非甲基化;若兩者均擴增出陽性條帶,為部分甲基化。
1.5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13.0分析數據。RASSF2A甲基化、mRNA表達在卵巢腫瘤組織間的差異以及基因甲基化與臨床病理特征等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或Fishier確切概率法。RASSF2A甲基化及其表達之間的關系采用Spearman相關性分析法。卵巢癌細胞系中RASSF2AmRNA表達量比較采用t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結果
2.1卵巢腫瘤組織RASSF2AmRNA的表達表1和圖1所示,卵巢良性腫瘤、交界性腫瘤及卵巢癌組織中RASSF2AmRNA表達率依次降低,分別為95.00%(19/20)、59.26%(16/27)和34.00%(17/5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1.855,P<0.001。兩兩比較結果顯示,卵巢癌組與交界性腫瘤組比較,χ2=4.568,P=0.033;卵巢癌組與良性腫瘤組比較,χ2=21.280,P<0.001;交界性腫瘤組與良性腫瘤組比較,χ2=7.719,P=0.005;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2.2卵巢腫瘤組織RASSF2A基因甲基化水平表1和圖2所示,97例卵巢組織標本均成功進行了MSP實驗。50例卵巢癌組織標本中有13例發生了部分甲基化,10例完全甲基化,甲基化頻率為46.00%(23/50);27例交界性卵巢腫瘤中甲基化陽性率為22.22%(6/27),其中2例為完全甲基化。而20例良性卵巢腫瘤組織均未擴增出甲基化陽性條帶,甲基化頻率為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5.474,P<0.001。
2.3RASSF2A基因甲基化與其表達的相關性表2所示,RASSF2A基因甲基化狀態與其mR-NA表達水平呈負相關。在RASSF2A基因發生甲基化的組織中,RASSF2A基因表達明顯降低,提示RASSF2A基因高甲基化可能是該基因表達沉默的原因之一。
2.4甲基化狀態與卵巢癌臨床病理特征相關性表3所示,RASSF2A甲基化程度與卵巢癌患者的年齡、病理類型、臨床分期、分化程度及淋巴結轉移之間無明顯的相關性。
2.55-aza-dC作用結果圖3所示,卵巢癌細胞株SKOV3和3AO中均檢測到RASSF2A基因甲基化,經去甲基化藥物5-aza-dC作用后,SKOV3細胞由完全甲基化轉變為非甲基化,而3AO細胞甲基化狀態被部分逆轉。SKOV3和3AO中RASSF2AmRNA表達水平較低,經藥物干預后,SKOV3(t=-5.258,P=0.006)和3AO細胞株(t=-3.060,P=0.038)RASSF2AmRNA表達水平明顯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3討論
近年來,隨著腫瘤分子生物學及表觀遺傳學的發展,腫瘤抑制基因失活在癌癥發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總的來說,其機制可概括為遺傳學機制及表觀遺傳學機制,換言之,腫瘤抑制基因功能的失活既可以是不可逆的,即遺傳學機制,如基因的突變或染色體的缺失,也可以是可逆的,即表觀遺傳學機制,如基因甲基化或組蛋白修飾。與遺傳學不同,表觀遺傳學主要研究內容不涉及DNA序列的改變,且在細胞分裂過程中具有可遺傳的、可逆性的基因組修飾作用[5]。DNA甲基化是哺乳動物基因組中最普遍的表觀遺傳學事件。相對于Knudson’s的二次打擊學說,基因甲基化僅靠一次打擊就可導致基因失活,腫瘤易感性增加[6]。RASSF2是新近發現的RASSF家族成員之一,生物信息學分析顯示,RASSF2與其他成員一樣,也含有RAS相關域[7]。RASSF2位于人類常染色體20p13,有329個氨基酸的開放閱讀框,11個外顯子。根據不同的啟動子和外顯子選擇剪接,可形成RASSF2A、RASSF2B和RASSF2C3個不同的轉錄本,其中,RASSF2A是最長的轉錄本,也是唯一一個含有5′CpG島的轉錄本。RASSF2A在卵巢癌組織中發揮抑癌基因的作用,如抑制細胞生長,阻滯細胞周期,促進細胞凋亡等,是一個腫瘤抑制基因。本研究分析了RASSF2A基因在上皮性卵巢癌組織中的轉錄表達及其甲基化水平。RT-PC檢測結果顯示,RASSF2A基因表達水平在良性卵巢腫瘤、交界性腫瘤及卵巢癌組織中依次降低,提示RASSF2A的轉錄失活,可能參與了卵巢癌的惡性演進過程,RASSF2A在上皮性卵巢癌中也起到抑癌基因的作用。張嫻等[8]研究結果顯示,RASSF2A基因甲基化可能參與了宮頸癌的發生,與宮頸癌的惡性進展密切相關。本研究結果顯示,良性卵巢腫瘤組織中未發生RASSF2A啟動子區甲基化,而基因異常甲基化從交界性腫瘤到癌呈逐漸上升的趨勢,RASSF2A基因甲基化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現象,說明了RASSF2A基因啟動子區甲基化從卵巢上皮增殖階段就開始起作用,與卵巢癌發生密切相關。多項研究表明,RASSF2A啟動子區高甲基化與基因表達沉默有關[9-11]。本研究結果表明,在發生RASSF2A甲基化的組織中,其基因表達水平明顯下降,兩者呈負相關。結果提示,在卵巢癌中RASSF2A啟動子甲基化是導致其低表達或者表達缺失的重要原因,這在細胞試驗中也得到驗證。應用甲基轉移酶抑制劑5-aza-dC對卵巢癌細胞株進行去甲基化處理后,卵巢癌細胞株的基因啟動子甲基化被逆轉,而其mR-NA的表達水平明顯升高,從而進一步證實了RASSF2A啟動子CpG島的異常甲基化在調節RASSF2A基因的表達中發揮重要作用。研究顯示,RASSF2A基因甲基化程度與宮頸癌、胃癌的淋巴結轉移有關[8,12],而與胰腺癌和結直腸癌[9,13]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無關。另有研究表明,基因啟動子甲基化水平與癌癥患者年齡密切相關[14]。在子宮內膜癌的研究中顯示,>45歲的患者更容易發生RASSF2A甲基化(P=0.041)[15]。在結腸癌和口腔鱗癌中也發現,RASSF2A基因甲基化程度與年齡相關[13,16]。在生物個體發育過程中,伴隨著時間的進程,DNA甲基化異常會不斷呈現,由此認為,表觀遺傳學疾病是一種與年齡相關性疾病。這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腫瘤多發生在老年人。檢測DNA甲基化程度可作為細胞衰老的標志之一。本研究結果顯示,RASSF2A基因甲基化水平與卵巢癌患者的臨床病理參數之間無明顯的相關性,是上皮性卵巢癌中的早期頻發事件,隨著患者年齡的增加,RASSF2A基因甲基化有增高的趨勢,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可能上皮性卵巢癌中RASSF2A基因甲基化不是年齡相關的表觀遺傳學改變。
綜上所述,RASSF2A啟動子區的高甲基化是卵巢癌發生和發展過程中的頻發事件,是導致卵巢癌中RASSF2A低表達或表達缺失的重要原因,其參與了卵巢癌的發病過程,并在卵巢癌的發生和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監測RASSF2A基因啟動子CpG島甲基化水平可作為表觀遺傳學的分子靶標,指導卵巢癌的診斷及其預后判定。
參考文獻
[1]SiegelR,NaishadhamD,JemalA.Cancerstatistics[J].CACancerJClin,2012,62(1):10-29.
[2]ShiH,LiY,WangX,etal.AssociationbetweenRASSF1Apro-motermethylationandovariancancer:ameta-analysis[J].PLoSOne,2013,8(10):e76787.
[3]李其榮,劉培淑,馮進波.卵巢腫瘤組織和血清中RASSF1A基因甲基化檢測及臨床意義的研究[J].中華腫瘤防治雜志,2008,15(5):374-377.
[4]FuLJ,ZhangSL.ExpressionofRASSF1Ainepithelialovariancancers[J].EurRevMedPharmacolSci,2015,19(5):813-817.
[5]MannJR.Epigeneticsandmemigenetics[J].CellMolLifeSci,2014,71(7):1117-1122.
[6]JoungJG,KimD,KimKH,etal.Extractingcoordinatedpat-terntsofdnamethylationandgeneexpressioninovariancancer[J].JAmMedInformAssoc,2013,20(4):637-642.
[7]AkinoK,ToyotaM,SuzukiH,etal.TheRaseffectorRASSF2isanoveltumor-suppressorgeneinhumancolorectalcancer[J].Gastroenterology,2005,129(1):156-169.
[8]張嫻,張友忠.宮頸癌RASSF2A基因啟動子甲基化與其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J].現代婦產科進展,2014,23(7):524-526.
[9]ZhaoL,CuiQ,LuZ,etal.AberrantmethylationofRASSF2Ainhumanpancreaticductaladenocarcinomaanditsrelationtoclini-copathologicfeatures[J].Pancreas,2012,41(2):206-211.
[10]Guerrero-SetasD,Perez-JanicesN,Blanco-FernandezL,etal.RASSF2Ahypermethylationispresentandrelatedtoshortersurvivalinsquamouscervicalancer[J].ModPathol,2013,26(8):1111-1122.
[11]任芳,波.RASSF2基因甲基化與卵巢透明細胞癌的相關性[J].中國醫科大學學報,2014,43(11):969-972.
[12]MaruyumaR,AkinoK,toyataM,etal.CytopalsmicRASSF2Aisaproapoptoticmediatorwhoseexpressionisepigeneticallysi-lencedingastriccancer[J].Carcinogenesis,2008,29(7):1312-1318.
[13]ParkHW,KangHC,KimIJ,etal.Correlationbetweenhyperm-ethylationoftheRASSF2ApromoterandK-ras/BRAFmuta-tionsinmicrosatellite-stablecolorectalcancers[J].IntJCancer,2007,120(1):7-12.
[14]HorvathS.DNAmethylationageofhumantissuesandcelltypes[J].GenomeBiol,2013,14(10):R115.
[15]LiaoX,SiuMK,ChanKY,etal.HypermethylationofRASef-fectorrelatedgenesandDNAmethyltransferase1expressioninendometrialcarciongenesis[J].IntJCancer,2008,123(2):296-302.
第6篇:表觀遺傳學意義范文
【關鍵詞】同性戀;基因;表觀遺傳
【Abstract】The reasons of homosexuality are complex.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easons of homosexuality are increasingly clearly understood, which mainly involve in physiological factors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asons of homosexuality, like genetic factor, biological factor, endocrine factor,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as well as the recent research achievement of epigenetic factors.
【Key words】Homosexuality; Genetic; Epigenetic
【中圖分類號】C913.14【文獻標志碼】A
自同性戀產生以來人們就沒有停止對其成因的探究,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生物醫學和分子流行病學的不斷進步,以及生理學和心理學的發展都對探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理論依據,人們對同性戀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男男者已成為我國艾滋病流行的三大高危人群之一,同時也是性病的高危人群。其形成原因是十分復雜的,涉及生物、遺傳、心理、社會文化等多重因素。本文就針對男性同性戀成因的研究進行綜述。
同性戀又稱同,是人際間性取向的一種。性取向指個體或群體的持續地指向何方。同性戀現象自古就有, 并一直存在, 在任何歷史時期,任何文化背景下,不管社會主流支持還是反對,它都在人類社會中保持相當的比例。同性戀 ( homosexuality) 一詞最早是由一名德國醫生Benkert Kertbeny于1869年提出的。這個詞的意思是指對異性不能做出性反應,卻被同性別的人所吸引[1,2]。《生命倫理學百科全書》對同性戀的描述為:同性戀者是一個有著持久、顯著、唯一的受同性性別吸引,對同性有性渴望和性反應,尋求同性并從中得到性滿足的人。我國有學者將同性戀定義為:這種關系可存在于內在的心理上或外在的行為之中,如果某個人一生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和同性別的人建立心理或者行為上的這種關系,就可稱為同性戀者。男性同性戀或稱男男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指性取向為男性,且生理性別為男性者。
近年來,對于男男者的形成有先天說(生物因素)和后天說(環境因素)兩種說法,前者稱為素質性同性戀,后者稱為境遇性同性戀[3]。但更普遍認為是由生物因素和環境因素共同決定的。其中生物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與遺傳學、神經生物學及性激素水平的相關范疇。環境因素主要在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兩方面。最近,有學者還提出了同性戀的表觀遺傳學說,研究顯示表觀遺傳學可能是導致同性戀的一個關鍵因素,從而擴大了同性戀成因的研究范圍。
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進化遺傳學家William Rice[4,5]認為,同性戀會隨后代遺傳,這必然存在某種原因。研究估計有8%的人群是同性戀,且眾所周知同性戀在家族中流行。如果一對雙胞胎中有一人是同性戀者,另一個有20%的概率也是同性戀。
Mustanski等[6]利用10cm距離上的403個微衛星標記測定其基因型,分別計算母系的、父系的和聯合遺傳的最大可能連鎖值,發現了連鎖值最高的3個區域:7q36、8p12和母源的10q26。而另一項針對男同性戀全基因組掃描的分析也發現這3個區域與性取向的聯系,并且發現了1個新的可能與MSM行為發生相關的14q32區[7]。
Camperio-Ciani等[8]比較了男性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的家系,結果顯示同性戀者母系女性親屬的生育能力顯著偏高,平均多生育33%的子女,父系女性親屬卻沒有,提示人類性取向相關的遺傳因素有可能位于X染色體上,這些遺傳因素未被逐步消除的原因在于攜帶該基因的女性生育能力較強。此外,男性同性戀的母系親屬中同性戀數目多于父系親屬,而且男性同性戀者多不是長子,有較多的哥哥或姐姐。其他幾位學者的研究也報道多項家族性研究均證實男性同性戀具有遺傳特征,且其相關影響因素可能位于X染色體上[9-11]。攜帶有同性戀基因的個體細胞,在適宜的條件下,易于發展成同性戀細胞。這就說明,同性戀的性取向有70% 是遺傳基因所產生的結果[12]。Hamer等[13]對114個家庭中男性同性戀者的舅舅和表兄弟的性取向進行家系和連鎖分析,并通過DNA連鎖分析了兄弟均為同性戀的40個家庭的X染色體的基因多態性,發現Xq28區域可能有決定性取向的基因。
“男性基因”SRY(性別決定基因)的發現也從另外一個角度佐證了男性同性戀和變性者的生物醫學基礎。SRY基因在哺乳動物性別決定中起關鍵作用,它是決定因子( TDF),啟動分化, 是發育負調節的抑制因子[13]。表現為XY的男性核型卻在性染色體中查不到SRY,或SRY發生了突變, 因此可能表現為女性化,即所謂“性反轉”[14]。迄今為止還沒有明確證據證實染色體上某一區域或基因與男性性取向相關,但似乎可以推測遺傳基因在性取向的決定上具有重要的作用,這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
澳大利亞學者對112 名男性同性戀和258 名男性異性戀的基因進行了比對,發現554%的男性同性戀的雄激素受體基因較長,476%的男性異性戀雄激素受體基因較長。研究人員說,雄激素受體基因較長可能導致激素信號傳輸弱,而激素是決定早期發育過程中大腦性別認知雄性化的關鍵因素。該研究認為,激素水平較低可能導致男性在大腦發育期時雄性化的過程不完整,造成性別認知方面傾向于女性[15]。
瑞典研究人員發現,男性同性戀者和女性異性戀者的大腦結構上存在某些相似特點,他們對一些志愿者進行了對比試驗,腦部核磁共振成像顯示,女性同性戀者和男性異性戀者都擁有不對稱的大腦,左側腦半球比右側腦半球略小;而男性同性戀者和女性異性戀者的左右腦半球是對稱的。研究人員還應用相關檢測設備對志愿者腦部杏仁核區域做了分析,結果顯示,男性同性戀者和女性異性戀者的杏仁核結構存在著相似性,而男性異性戀者和女性同性戀者的杏仁核結構更為相似。
科學家從腦和內分泌的研究出發,認為下丘腦是大腦負責調節包括性活動在內的身體功能的器官,同性戀可能與下丘腦有關。發現同性戀男性的下丘腦前部神經元的密度只是異性戀男性的一半,而下丘腦前角是大腦中能影響的部分,提出同性戀男性下丘腦前核神經元解剖學的差異可能導致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釋放頻率的改變,這可能會成為性傾向起因的生物學基礎。另外,Levay等比較了同性戀男性和異性戀男性的4種下丘腦前部間質核(interstitial nuclei of the anterior hypothalamus,INAH)的數量,其中INAHl-3是決定人類性別二態性的主要區域,結果顯示異性戀男性INAH-3的數量是男性同性戀者的兩倍。人體解剖發現男性同性戀INAH-3的體積與男性異性戀相比較小,但女性中卻未顯示出這種差異,提示了INAH-3與男性性取向的關系[16]。但目前尚未找到造成同性戀者大腦具有獨特性的原因,要深入了解與同性戀相關的神經生物學機制需要進行更大規模的研究。
一些研究者考慮到激素可能會導致同性戀。胎兒的大腦受何種性激素的影響,決定了個體細胞未來的性取向。如果男性胎兒未得到激素的影響,而是受到母親卵巢的雌激素影響,男性胎兒大腦就會女性化;女性胎兒如果受到激素的影響,女性胎兒大腦就會雄性化[13]。有學者推測異性性取向的男性的雄激素暴露水平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不足或超過此范圍都可能增加男性成為同性戀的可能性 [17]。也有學者研究發現孕期暴露于乙醇與壓力應激的聯合作用引發導致雄性后代的性取向的改變[18]。
一直以來也沒有任何的“同性戀基因”(gay genes)被確定。根據最新的一種假說,答案或許并不在于DNA本身,而是,隨著胚胎發育,子宮中母親和胎兒兩者生成的激素水平發生波動,性相關基因對此做出了反應性開啟和關閉。這樣的調節機制可使未出生的胎兒受益,即便是在激素處于頂峰時,也可以維持穩定的雄性或雌性發育。然而如果到孩子出生或孩子擁有自己的表觀遺傳學標記時,這些所謂的表觀遺傳改變仍然存留,那些后代其中的一些人就可能變成同性戀。在Rice[4,5]的研究中,顯示男性和女性胎兒對于它們周圍的激素反應并不相同,甚至當一種激素暫時性增高時,這種差異并非是基因的結構,而是基因激活的程度,以及蛋白修飾的方式及程度,如DNA甲基化與剪切、多聚尾修飾等。如在睪酮對胎兒發揮作用的信號通路中,幾個關鍵點的表觀遺傳改變有可能根據需要鈍化或增進了激素的活性。研究中還提到,這些表觀遺傳學變化在父母處于早期發育時保護了他們,而早期對父母有利的表觀遺傳改變可解釋同性戀在進化中遺留下來。Rice等[19]最近還建立并發表了針對同性戀發展的表觀模型,該模型是基于胚胎干細胞的XX與XY核型的表觀遺傳標記。這些標記提高了XY胎兒中睪酮的靈敏度,降低了XX胎兒睪酮的靈敏度,從而性發展得以進行。該模型預測,這些表觀遺傳標記的子集進行了跨代遺傳,建立了同性戀的表型。Ngun TC等[20]綜合相關證據認為性取向是生物學的基礎并且認為涉及表觀遺傳學機制,最近的研究表明,性傾向在同卵雙胞胎中比在異卵雙胞胎中更為一致,因此認為,男性的性傾向與基因組中的一些區域相關聯,該研究驚喜的發現性取向與表觀遺傳機制有著重要的聯系。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先天性腎上腺增生的女性病例中,由于其子宮內高水平的睪酮激素以至于其后代中非異性戀的比例高于哪些非先天性腎上腺增生的女性。同時動物模型研究有力的證明,激素暴露的長期效應是由表觀遺傳機制介導的,該文章通過描述的假說框架得出結論,遺傳和表觀遺傳共同解釋了性取向的有關成因問題并愈發的接近事實,但有關性取向的研究還仍然面臨很多挑戰。
到目前還沒有有力的證據能說明同性戀是由于生理因素導致的,而對于同性戀的形成機制的第二方面,主要包括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觀點主要有精神分析學說和行為主義學說。
關于童年早期性心理發展,弗洛伊德認為個體在幼兒時都具有兩性素質及雙性戀特性,到底發展成同性戀還是異性戀是與個體在成長中的個人經歷有關的。他認為在人的個體發展過程當中,4 至6 歲是兒童性別認同、性別角色發展的關鍵時期,在此期間兒童有著強烈的“戀父情結”或“戀母情結”,對異性的父母有著本能、強烈的依戀情感,而對同性別的父母則產生敵對情緒。父母如果在此期間對兒童的這種性本能不過分刺激也不過分抑制,兒童就會順利通過這一時期而隨后逐漸對同性父母認同。反之,如果在此期間兒童遭受心理創傷,就可能隱藏在潛意識里,并且在青春期時表現出來,可能發展為同性戀[21]。家庭環境對MSM的影響很大,1962 年,貝博提出的“家庭動力是同性戀主因”認為同性戀根源于早期家庭經驗。他們大多數來自單親家庭,從小缺乏父母一方的關愛;或是父母關系很差,經常爭吵,長期分居兩地;還有的是個體所處的家庭結構是由他/她和多個異性姐妹組成的,或者個體從小被父母當女兒養,從小和女孩子一起玩,產生了性倒錯[21,22],將會導致個體對其性別的自我認同產生影響, 并影響以后所形成的性取向。在家庭關系中,通常是母親的形象和影響遠遠大過父親,所以兒子在青春期后會尋找一個具有父親身上沒有的“男性力量”的人作為伴侶。
行為主義者認為,同性戀由環境影響形成。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如果在與異往中受挫或有過不快的經歷,異性情感沒得到正常的發展而與此同時又受到了同性方面的引誘,就可能產生同性戀傾向[23,24],特別的,第一次性經歷對個體性取向的影響很大,許多同性戀者第一次受人引誘或者在其他情況下發生同性,從而“欲罷不能”。有學者認為同性戀的形成是極度壓抑的結果,如果一個人對性的需求無法通過正常的異性途徑獲得滿足,便會壓抑它,壓抑的結果便是性需求更大,而為了消除性需求所帶來的壓抑,個體就會另尋出路去放松這種壓抑,一旦個體以同性的方式緩解了壓力,就有可能經過多次該行為的強化而形成同性戀。
學校是兒童接受教育的地方,同時也是孩子的主要活動場所,孩子的大部分時間都要在學校這個微縮型社會環境中度過,尤其是初中和高中正值學生性心理迅速發展成熟的時期,其間發生的任何事情如學校和老師對學生的性教育方式和力度、關切程度,以及同伴之間的相互影響等都會給孩子造成很大的影響。
李玉玲等[25]提出同性戀發生的原因在于性情緒的作用,男女同性戀的發生原因是相同的,同性戀與異性戀發生的原因也是相同的,都是由于性情緒的作用。當個體在中體驗到喜歡、興奮、沖動、渴望等積極情緒時,則將帶來這些體驗的人當戀對象。若此人為同性,則產生同性戀;反之則為異性戀。此外,戀母情結對同性戀者的情緒的產生也有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同性戀者的父母不鼓勵男孩表現出男性特征,有統治欲的母親不允許兒子對除她自己之外的異性產生興趣[26],因此產生變得膽小,甚至產生恐懼、偏執的心態,從而影響其未來性取向。
此外,從中醫的陰陽角度來看,人體內陰陽互藏,陰陽轉化。若男子,陽火不生,或陽剛之氣受挫,眾陰聚合,則易變主動為主靜。陽中陰氣愈聚,陰陽失調,則為男子中的女性。相對而言,男子中的女性,為陰,而男子為陽,陰陽的相吸作用,促使他們的自然吸引從而在一起,使得他們相互補足依靠,相互需要,從對方身上獲得快樂,實現陰陽的互根交感作用[27]。
社會學的研究個案表明,同性戀個體之間在成因上是不完全相同的,單純從一種理論出發分析他們的成因是不科學的。比如說素質性的同性戀即絕對同性戀和境遇性同性戀的成因有可能不同。境遇性同性戀更多地受環境的影響,如單性性環境的軍隊、監獄等,他們中有些人在改變了環境之后,又恢復到異性戀的狀態。
綜上所述,目前研究男性同性戀成因的領域主要包括社會學、心理學、醫學、法學、哲學等多個不同的學科,男性同性戀成因十分復雜,主要涉及遺傳因素、表觀遺傳學、神經生物因素、發育及內分泌因素、社會及心理因素等諸多方面,彼此之間的因果關系不明,盡管相關方面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尚待解決。探索男性同性戀形成原因的道路還很長,但是意義重大。
參考文獻
[1]伍傳仁.中國男男同性戀的研究現狀. 實用預防醫學, 2009, 16(3): 985-987.
[2]余放爭,楊國綱,余翔.同性戀國內研究概述. 醫學信息, 2006, 18(12): 1758-1761.
[3]熊明洲,韓雪,劉愛忠,等.男同性戀性取向成因影響因素Delphi法分析. http:///kcms/detail/211234R.201402081036007html.
[4]Rice WR, Friberg U, Gavrilets S. Homosexuality as a consequence of epigenetically canalized sexual development.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2012, 87(4): 343-368.
[5]Bailey JM, Dunne MP, Martin NG.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its correlates in an Australian twin sam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8(3): 52-54.
[6]Mustanski BS, DuPree MG, Nievergelt CM, et al. A genomewide scan of male sexual orientation. Human genetics, 2005, 116(4): 272-278.
[7]Ramagopalan SV, Dyment DA, Handunnetthi L, et a1 genome-wide scan of male sexoal orientation. J Hum Genet, 2010(55): 131-132.
[8]Camperio-Ciani A, Corna F, Capiluppi C. Evidence for maternally inherited factors favouring male homosexuality and promoting female fecundit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04, 271(1554): 2217-2221.
[9]Blanchard R. Quantitative and theoretical analyse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lder brothers and homosexuality in me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004, 230(2): 173-187.
[10]Ciani AC, Iemmola F, Blecher SR. Genetic factors increase fecundity in female maternal relatives of bisexual men as in homosexuals. 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2009, 6(2): 449-455.
[11]Iemmola F, Ciani AC. New evidence of genetic factors influencing sexual orientation in men: Female fecundity increase in the maternal line.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2009, 38(3): 393-399.
[12]佚名. 同性戀是怎樣形成的. 科學大觀園, 2007 (23): 47.
[13]Hamer DH, Hu S, Magnuson VL, et al. A linkage 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male sexual orientation. Science, 1993, 261(5119): 321-327.
[14]姜明子. SRY 基因的研究進展. 中國優生與遺傳雜志, 2007, 15(5): 119-120.
[15]研究認為同性戀可能與基因有關. 中華中醫藥學刊, 2011, 29(5): 1124.
[16]于微, 馮鐵建. 男性同性戀生物學成因的研究進展. 中華醫學遺傳學雜志, 2012, 29(002): 172-175.
[17]Rahman Q. The neurodevelopment of 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2005, 29(7): 1057-1066.
[18]Popova NK, Morozova MV, Naumenko VS. Ameliorative effect of BDNF on prenatal ethanol and stress exposure-induced behavioral disorders. Neuroscience Letters,2011,505(2):82-86.
[19]Rice WR, Friberg U, Gavrilets S. Homosexuality via canalized sexual development: a testing protocol for a new epigenetic model. Bioessays,2013,35(9):764-770.
[20]Ngun TC, Vilain E.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human sexual orientation: is there a role for epigenetics. Advances in Genetics,2014,86(1):167-184.
[21]李陽, 張延華, 張海霞. 同性戀形成機制探析. 醫學與哲學: 人文社會醫學版, 2007, 28(6): 50-51.
[22]吳天亮, 張健, 陳國永, 等. 男男同性戀常見精神健康問題及成因探析. 中國性科學, 2013,22(9): 85-87.
[23]馬文靖. 淺析同性戀成因中的心理、社會因素. 科技信息 (學術研究), 2008(11): 156-157.
[24]高淑艷, 賈曉明. 近15年來國內同性戀的研究概況. 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 2008 ,16(4):461-463.
[25]李玉玲. 同性戀是怎樣發生的. 中國性科學, 2006, 15(3): 32-35.
[26]楊揚, 岳文靜, 朱振菁. 同性戀的心理社會成因. 學理論, 2012 (15): 63-64.
第7篇:表觀遺傳學意義范文
【關鍵詞】胃癌;分型;進展
胃癌是消化系統的常見惡性腫瘤,為全世界范圍內發病率最高的癌癥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癌癥研究中心2002年的統計,我國胃癌發病率僅次于日本,位于全球第2位。2007年中國腫瘤登記提示:我國胃癌的發病居第二位,僅次于肺癌,死亡據第三位,僅次于肺癌、肝癌。胃癌在演進過程中隨著附加的基因突變會產生不同的亞克隆,使其不斷異質化導致其侵襲和轉移能力不斷加強,而這是胃癌治療困難和致死的主要原因。國內外學者都在尋求能指導臨床方案選擇及判斷預后的胃癌分型,傳統的癌癥診斷對病理學依賴性較大,有時會因為腫瘤的不典型或臨床信息的不完整而造成診斷困難。應用基因分析技術所產生的信息,特別是應用高通量芯片技術所產生的信息可以為胃癌分型提供更多的參考,因此對目前胃癌相關的分型予以綜述。
1 胃癌的傳統分型
胃癌病理分型是以組織形態結構和細胞生物學特性為基礎,不同類型的胃癌,其形態結構和生物學行為各異,流行病學和分子機制亦不同,以致現有的胃癌分型系統眾多。目前,常用的是WHO型、Lauren分型,大體分型主要使用Borrmann分型。
1.1 WHO胃癌包括以下常見組織學類型
狀腺癌、管狀腺癌、黏液腺癌、印戒細胞癌、腺鱗癌、鱗癌、小細胞癌、未分化癌。此外,胃內還可以發生類癌。WHO分型將Lauren分型的腸型、彌漫型納入腺癌之下。其管狀腺癌還可進一步分成高分化、中分化與低分化腺癌。少見類型或特殊類型胃癌有:實體型變異、肉瘤樣變異等。
1.2 1923年德國病理學家Borrmann提出的一種胃癌大體形態分型方法,此分型主要根據癌瘤在黏膜面的形態特征和在胃壁內的浸潤方式進行分類,將胃癌分為4型:Ⅰ型(結節型),II型(潰瘍局限型),III型(浸潤潰瘍型),是最常見的類型,約占50%。Ⅳ型(彌漫浸潤型),由于癌細胞彌漫浸潤及纖維組織增生,胃壁呈廣泛增厚變硬,稱“革囊胃”。Borrmann分型是胃癌經典的分型方法,既能反映胃癌的生物學行為,又簡潔實用,國際上廣泛采用。
1.3 Lauren分型將胃癌分成兩大主要類型,即腸型與彌漫型,當腫瘤內兩種類型成分相當時就稱為混合型。胃癌發生是一個多步驟的過程,彌漫型和腸型在腫瘤發生各個階段會產生多種基因及表觀遺傳學方面的變異。常見的包括抑癌基因的點突變和雜合性丟失,常見的表觀遺傳學異常包括CPG島的甲基化引起的腫瘤抑制基因沉默和腫瘤促進基因轉錄水平的增高。
2 胃癌分型與分子病理學
胃癌分型研究的意義在于探索其是否對判斷預后有價值或者對于今后的治療有指導意義。當前,國內張樹華采用組織病理與組織化學和免疫組織化學技術相結合的方法,兼顧宿主的免疫防御反應,把胃癌分為兩型:限制生長型和促進生長型。限制生長型預后較促進生長型好。
根據黏蛋白標記的差異,胃癌組織被分為4型:1)胃型:胃型黏蛋白標記的胃癌細胞>10%;2)胃腸型:胃型黏蛋白標記的胃癌細胞> 10%且腸型黏蛋白標記的胃癌細胞>10%;3)腸型:腸型黏蛋白標記的胃癌細胞>10%;4)未分類:胃腸黏蛋白標記的細胃癌細胞
Solcia等對對294例平均隨訪時間長達150個月的胃癌進行研究顯示,如果將胃癌的組織學結構、細胞異型性程度、p53基因突變、18q雜合性缺失、微衛星不穩定性以及有無脈管神經浸潤等因素與預后綜合分析,可以將胃癌惡性程度分成三級。胃癌I級(預后良好型)包括:大量腫瘤內/旁淋巴樣細胞反應型、高分化管狀腺癌、黏液結節型和促纖維結締組織增生性彌漫型胃癌,I級胃癌約占全部胃癌病例的37%。胃癌III級(預后不良型)包括:高度異型性胃癌、浸潤型黏液腺癌、腫瘤細胞異型性中等但具有p53基因的第7或第8外顯子突變、伴有血管淋巴管浸潤以及神經浸潤者,III級胃癌占全部胃癌病例的19%。其他胃癌則歸屬于預后中等的胃癌Ⅱ級,占全部胃癌的44%。這一關于胃癌惡性程度評價體系雖然是不依賴于臨床分期的胃癌預后判斷新標準,但實際操作中涉及到微衛星不穩定性的分子遺傳學檢測、p53基因突變檢測以及EB病毒原位雜交檢測等實驗技術,在臨床普及以及操作流程標準化控制等方面均有待統一。
3 微衛星不穩定性與胃癌分型
微衛星不穩定性[MSI]是胃癌發生過程中的一個常見事件,反應了腫瘤潛在DNA錯配修復缺陷,常常由Hmlh1啟動子區甲基化引起,胃癌合并MSI者其臨床病理因素特別,預后相對良好,胃腸道腫瘤中MSI的測定是最先被廣泛利用的預后分子檢測之一。MSI的檢測常采用熒光定量多重PCR進行,費用相對低,適用性廣。以往的很多觀察表明,胃癌中MSI的存在不僅僅是與已知的與組織病理特征強關聯的分子分型標志,同時MSI能能區分預后良好好亞組。因此Simpson等建議將MSI作為一個有效的分子分型工具。葡萄牙的一項研究表明,胃癌患者并低度MSI五年生產率為30%相比,而高度MSI者則為70%。韓國的一項大型研究也表明在胃癌分期為II、III期的患者MSI與預后良好有關。
4 胃癌的分子分型
以分子特征為基礎的新型分類體系即分子分型。高通量的基因分析可以是DNA水平的基因多態性分析、DNA甲基化分析和基因拷貝數分析.也可以是RNA水平的基因表達譜分析、微小RNA表達譜分析和蛋白表達水平的蛋白芯片分析等。
腫瘤分子分型的基礎:目前可以在DNA、RNA和蛋白質水平上進行腫瘤分子分型的研究。在DNA水平,可以依據基因突變、基因組的細胞遺傳學改變或甲基化差異進行分型。根據基因表達譜(RNA水平)的差異實施分型,是目前分子分型的研究主體,以表達譜芯片為基礎的分子分型研究數據處理分二類:一是,unsupervised analysis;二是,supervised analysis。在蛋白質水平,可以根據蛋白質表達譜的差異,亞細胞結構蛋白組成的不同或蛋白質翻譯后修飾的改變來進行分型。
分子分型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基因表達譜芯片技術:它可以同時觀察成千上萬個基因在不同個體、不同組織、不同發育階段的表達狀況。它的原理是在已建立的cDNA或寡核苷酸組成的芯片或微陳列上,用不同顏色熒光標記的cDNA制備的探針與之雜交,掃描及計算機處理所得的信號就代表了樣品中基因的轉錄表達情況。基因芯片技術在腫瘤的分子分型、基因功能、信號通路及代謝與調控途徑研究等方面有顯著的優勢;比較基因組雜交(CGH)技術:是在染色體熒光原位雜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分子細胞遺傳學研究技術。它主要是用不同的熒光體系來標記腫瘤組織DNA和正常對照DNA,與正常中期分裂象染色體進行競爭性抑制雜交,熒光信號攝取及軟件分析所得的比值可判斷染色體區段的擴增、缺失還是正常。它僅需少量腫瘤組織DNA即可在整個基因組水平研究不同基因組間DNA拷貝數差異,并將這些異常定位在染色體上。CGH與微芯片技術結合的芯片CGH,以cDNA作為雜交靶,可使得基因組水平遺傳物質異常的分辨率達到幾十個kb,并可對關鍵基因改變進行精細定位;蛋白芯片技術:基因突變和基因表達差異不一定導致相應的蛋白表達,而且蛋白質還存在磷酸化,乙酰化等復雜的翻譯后修飾過程,這些改變在轉錄水平上是無法檢測的。以高通量結合生物信息學為特點的蛋白質組學分析技術可以從細胞整體水平上檢測到這種變化,為腫瘤分子分型以及治療標志物的篩選帶來巨大的便利與可能。蛋白芯片技術主要包括雙向凝膠電泳技術、質譜技術以及生物信息學技術。
第8篇:表觀遺傳學意義范文
1資料與方法
1.2治療方案地西他濱聯合CAG方案:20mg/m2,qd×5d,維持1h以上。阿克拉霉素10mg,qd×7d,阿糖胞苷10/m2,q12h×14d,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300μg,qd×14d。
1.3療效評價完全緩解(CR)定義:ANC≥15×109/L,血小板計數≥100×109/L,骨髓中原始細胞≤5%。部分緩解(PR)定義:骨髓中原始細胞為5%,外周血標準同CR。未緩解(NR)定義:骨髓中原始細胞≥20%。
1.4不良反應評價按WHO急性及亞急性化療藥物不良反應分度標準判定不良反應。
2結果
接受一療程地西他濱聯合CAG化療后,行骨髓穿刺術,結果CR3例(42.8%),PR(28.5%),OR為71.4%。不良反應主要為骨髓抑制及繼發感染。Ⅳ度血液學不良反應71.4%(5/7),外周血白細胞計數最低值的中位值為0.54(0.03~2.32)×109/L,外周血血小板計數最低值的中位值為8(4~37)×109/L,Ⅲ-Ⅳ級感染發生率5例,Ⅱ度胃腸道毒副作用1例,無Ⅲ-Ⅳ級出血、惡心、嘔吐和肝功能損害。早期死亡1例,死因為疾病進展至終末期。
3討論
DNA甲基化是真核細胞正常的修飾方式,在維持正常細胞功能、遺傳印記和胚胎發育中呈現表觀遺傳改變[1-3]。在大多數惡性腫瘤中,表觀遺傳學表現為全基因組的低甲基化與局部CpG島的高甲基化共存的局面。這種甲基化作用影響了基因啟動子CpG島,使基因的穩定性降低和逆轉座子轉錄活性增強等,從而促使癌基因活化、抑癌基因失活而致腫瘤發生。在白血病和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myeIodysplasticsyndrome,MDS)中,同時具有高甲基化和多種基因沉默的特征[4,5]。地西他濱是一種2-脫氧胞苷類似物,在胞苷類似物5位嘧啶環上進行修飾,形成特異的DNA甲基化轉移酶抑制劑,可逆轉DNA的甲基化過程,激活沉默失活的抑癌基因,抑制腫瘤細胞生長,從而達到治療腫瘤的目的。2006年,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批準了其用于治療MDS,并取得了滿意的療效。MDS和AML均為造血干細胞異質性、惡性克隆性疾病,低劑量的去甲基化藥物地西他濱在MDS治療中的積極成果給治療AML的探索奠定了基礎。在一項Ⅲ期臨床試驗中,地西他濱治療170例MDS患者的總體有效率為30%,而地西他濱治療AML的有效率只有23%。1995年日本學者Yamada等首次報道預激化療方案(CAG方案)治療復發、難治和繼發性白血病患者,CR率達83%,大于60歲的3例AML患者全部獲得CR,而且化療并發癥少,治療相關死亡率明顯降低。國內2012年陳偉豐[6]等研究結果顯示地西他濱單藥治療MDS/AML2個療程,CR率達30.0%,總緩解率達60.0%。讓人振奮的是此項研究發現地西他濱對MDS/AML患者外周血細胞的改善有較好的療效。為了提高復發難治性白血病患者的療效,改善生存質量,減少輸血依賴,有必要探索在互補或者協同作用基礎上的聯合方案。作者的研究結果顯示地西他濱單藥治療1個療程,CR率達42.8%,OR為71.4%,初步結果表明地西他濱聯合CAG方案治療復發難治性AML患者安全有效,無嚴重不良事件發生,因此可作為此類患者治療方式的一種選擇,但仍需大樣本、多中心、雙盲、對照和隨機臨床實驗進一步探討其最佳給藥方式、藥物劑量,以達到最佳的療效。
參考文獻
[1]ValeriaSantini.Noveltherapeuticstrategies:hypomethylatingagentsandbeyond.HematologyAmSocHematolEducProgram,2012:65-73.
[2]KanaiY,HirohashiS.AIterationsofDNAmethylationassociatedwithabnormalitiesofDNAmethyltransferasesinhumancancersduringtransitionfromaprecanceroustoamalignantstate.Carcinogenesls,2007,28(12):2434-2442.
[3]LomberkG.Epigeneticsf.Pancreatology,2007,7(5-6):396-397.
[4]DavidP.Steensma.Canhypomethylatingagentsprovideaplatformforcurativetherapyinmyelodysplasticsyndromes?BestPractice&ResearchClinicalHaematology,2012,25(4):443-451.
第9篇:表觀遺傳學意義范文
[關鍵詞] 胚胎;培養液;培養發育;妊娠結局
[中圖分類號] R3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6)09(b)-0072-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influence of two commercially sequential media Cook and Vitrolife on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human embryos and the clinical pregnancy outcome.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398 patients conceived through IVF or ICSI from August 2014 to May 2015 in the Reproductive Medicine Center of the Affiliated Drum Tower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according to fertilization methods and embryo culture media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ok group (103 cases) and Vitrolife group (196 cases) in IVF; while Cook group (40 cases) and Vitrolife group (59 cases) in ICSI. In the same fertilization mode, the rate of fertilization, normal fertilization, cleavage, avaiable embryo, blastocyst formation, avaiable blastocyst, clinical pregnancy, embryo implantation and early abortion in the Vitrolife group and Cook group were compared. Results In IVF and ICSI cycles, the available embryo rate of the 3 days after fertilization in Cook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Vitrolife group (31.22% vs 40.61%, 33.43% vs 42.34%, P < 0.05). While, the available blastocyst rate in the Cook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Vitrolife group (55.42% vs 37.82%, 46.39% vs 30.58%, P < 0.05). 3 days after fertilization, the proportion of 5-7 cells of the embryo in the Cook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Vitrolife group (34.32% vs 24.23%, P < 0.05); and the proportion of 8-10 cells of the embryo in the Vitrolif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ok group (52.22% vs 42.07%, P < 0.05). Conclus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egnancy outcome either in Vitrolife culture medium or Cook culture medium, but the Cook culture medium may be bet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lastocyst stage.
[Key words] Embryo; Culture media; Embryonic development; Pregnancy outcome
人類胚胎培養液經歷了30多年的發展,如今市場上已出現多種有效的商品化培養液用于胚胎培養。不同品牌的培養液有不同類型及不同濃度的營養成分,同時由于人類配子的稀缺性、珍貴性,商品化培養液的配制更多是基于動物實驗結果驗證。而人類配子對營養成分的需求和體外微環境的適應性與動物配子又有一定差距[1],因此不同培養體系可能會對植入前胚胎的發育潛能以及種植能力產生一定影響,進而導致新生兒早產、低體重以及先天性畸形等子代健康問題[2-7]。造成差異的原因尚未明確,如何選擇更適用于人類胚胎的商品化培養液已成為很多生殖中心工作人員需要考慮的問題。目前,很少有研究比較這些商品化培養液對種植前人類胚胎的發育潛能及妊娠結局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就Vitrolife和Cook兩種商品化培養液對胚胎的發育速度等發育潛能相關指標及妊娠結局的影響進行深入探討。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回顧性分析2014年8月~2015年5月在南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鼓樓醫院(以下簡稱“我院”)生殖科行常規體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或卵胞漿內單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治療并新鮮周期移植的398例患者的臨床資料。納入標準:①女方年齡≤35歲;②不孕年限< 10年;③第1周期患者;④采用長方案治療;⑤體重指數(BMI)18~25kg/m2;⑥內膜厚度8~12 mm;⑦月經第3天卯泡刺激素(FSH)≤12 U/mL;⑧獲卵數8~15枚。排除標準:①種植前遺傳學診斷/篩查(PGD/PGS)周期;②供精;③受精失敗行早期補救ICSI周期。根據受精方式與胚胎培養液的不同進行分組:IVF周期分為Cook組(n = 103例)和Vitrolife組(n = 196例),ICSI周期分為Cook組(n = 40例)和Vitrolife組(n = 59例)
1.2 控制性超促排卵方案
采用促性腺激素(Gn)釋放激素激動劑(GnRh-a,曲普瑞林,德國Ferring公司)/基因重組促卵泡激素(Gonal F,果納芬,瑞士雪蘭諾公司)/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CG)長方案進行控制性超排卵[8]。當主導卵泡直徑≥18 mm,給予HCG。當主導卵泡直徑≥18 mm,給予HCG。
1.3 卵子采集及胚胎培養
取卵當日,卵泡穿刺獲得卵子-放射冠-卵丘復合物(OCCCs),置于受精培養液(IVF(Vitrolife,Sweden;FM,COOK,Sydney)中培養3 h,卵母細胞經IVF或ICSI進行受精,受精后轉移至卵裂培養液(G1,Vitrolife,Sweden;CM,COOK,Sydney)。受精后第3天除移植與冷凍胚胎外,剩余胚胎轉移至囊胚培養液(G2,Vitrolife,Sweden;BM,COOK,Sydney)繼續培養,于第5~6天分別觀察囊胚發育情況。
1.4 胚胎評估
根據ALPHA/ESHRE指南對胚胎質量進行分級評估[9],其中分裂期胚胎根據細胞數、卵裂球均一程度、碎片等形態學參數進行質量評估,分裂胚細胞數7~12個,碎片小于20%,均一或輕度不均為可利用胚胎;囊胚質量根據囊胚的擴張和孵出程度將其分為Ⅰ~Ⅵ級,并依據內細胞團(inner cell mass,ICM)和滋養層(trophectoderm,TE)的質量分為A~C級,ⅣCB和ⅣBC以上評分者為可利用囊胚[10]。
1.5 移植與妊娠
受精后第3天于B超引導下進行宮腔內雙分裂期胚胎移植。胚胎移植后2周留晨尿行尿HCG檢測,陽性結果確定為生化妊娠。移植后4周行B超檢查,見妊娠囊者確診為臨床妊娠。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的一般資料
IVF組與ICSI組中,患者的周期數、年齡、不孕年限、體重指數、內膜厚度、基礎FSH、黃體生成素(LH)用量、平均獲卵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2 IVF/ICSI周期中Cook與Vitrolife培養液對胚胎發育及妊娠結局的影響
IVF/ICSI周期中,Cook組的第3天可利用胚胎率顯著低于Vitrolife組,而囊胚形成率及可利用囊胚率顯著高于Vitrolife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受精率、正常受精率、異常受精率、卵裂率、正常卵裂率、可利用胚胎率、臨床妊娠率、種植率及早期流產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2.3 不同培養液對取卵后第3天胚胎發育速度的影響
對取卵后第3天胚胎的發育速度進行分析(Cook組共1716枚分裂胚,Vitrolife組共2922枚分裂胚)。Cook組5~7個細胞的胚胎所占比例顯著高于Vitrolife組,而Vitrolife組8~10細胞的胚胎所占比例顯著高于Cook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Vitrolife組≥11個細胞和Compacting的胚胎所占比例均略高于Cook組,≤4個細胞略低于Cook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3。
3 討論
國際輔助生殖技術監督委員會(ICMART)和歐洲人類生殖與胚胎學會(ESHRE)的統計數據顯示,通過輔助生殖技術受孕的孩子逐年增多,但其安全性還需進一步驗證[11-12]。植入前胚胎在體外培養過程中將經歷從受精至內細胞團和滋養外胚層等不同細胞譜系的派生等過程,體外培養液可能會導致這些關鍵性事件發生改變進而可能會影響胚胎的后續發育[13-14]。基于我院中心實驗室的培養體系,本研究結果顯示:Cook和Vitrolife兩種商品化培養液均可獲得較為理想的可利用胚胎和妊娠結局,但Cook組的第3天可利用胚胎率顯著低于Vitrolife組,而囊胚形成率及可利用囊胚率顯著高于Vitrolife組。
不同品牌的培養液其營養成分及含量均會有差異,Morbeck等[15]利用小鼠凍融后的一細胞胚胎分別在七種商品化序貫培養液中進行培養,其結果表明:7種培養液的營養成分各有差異,其中Vitrolife培養液的G1和G2中的乳酸含量為10.8和6.0 mmol/L,明顯高于Cook培養液(1.8 mmol/L);Vitrolife分裂期培養液G1不含必需氨基酸,而Cook分裂期培養液CM中含有一定量的必需氨基酸。此外,7種培養基在不同的氧氣濃度和蛋白含量下,鼠胚發育速度和囊胚形成率也有差別。
本研究結果提示,分裂期培養階段,Vitrolife培養液優于Cook培養液,而進入囊胚培養階段,Cook培養液呈現出了明顯優勢。于是本研究對第3天胚胎的發育速度進行了比對,結果顯示,Cook組中≤7個細胞的胚胎所占比例較Vitrolife組高,而≥8個細胞的胚胎Cook組所占比例較Vitrolife組少,說明Cook于分裂期發育速度慢于Vitrolife,而7個細胞以下的胚胎于第3天不會作為可利用胚胎,因此Cook組第3天可利用胚胎率會低于Vitrolife組。這一結論是否能說明G1優于CM,BM優于G2,仍需進一步研究。此外,Vitrolife組異常受精率(13.96%)略高于Cook組(11.00%),其原因可能由于過高的多精受精率會降低可利用胚胎率[16-17],因此Cook培養液的正常受精率比例有所提高,使正常胚胎數略有增加。
在輔助生殖治療過程中,胚胎培養液是種植前胚胎最直接的接觸環境,胚胎可能通過表觀遺傳學修飾做出一些適應性改變,產生長期持續性影響[18-21]。Rinaudo等[22]發現鼠胚在Whitten′s medium中有114個基因表達被影響,在KSOM/AA中有29個基因表達被影響。而與在體內培養的鼠胚相比,5種不同培養液培養的鼠胚為了維持基因印記會做出不同的表觀遺傳學改變[23]。鑒于以上動物實驗結果及試管嬰兒逐年增加的趨勢,應優化胚胎培養液的選擇,以降低胚胎的短期風險,保障母嬰安全。
本次研究對象均是35周歲以下,使用長方案促排的患者,其卵巢功能較好,獲卵數適中,因此研究對象范圍有局限性。在今后的臨床工作中,本研究將比較不同培養液對年齡較大、卵巢功能較差的患者,以及對獲卵數過多或過少的患者的胚胎發育狀況的影響。同時,本研究還將對新生兒出身狀況及長期健康情況進行隨訪,以確保商品化培養液的安全可靠。
[參考文獻]
[1] Bloise E,Feuer SK,Rinaudo PF. Comparative intrauterine development and placental function of ART concepti: implications for human reproductive medicine and animal breeding [J]. Hum Reprod Update,2014,20(6):822-839.
[2] Schieve LA,Meikle SF,Ferre C,et al. Low and verylow birth weight in infants conceived with use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J]. N Engl J Med,2002,346(10):731-737.
[3] Pinborg A,Wennerholm UB,Romundstad LB,et al. Why do singletons conceived after assisted reproductiontechnology have adverse perinatal outcom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Hum Reprod Update,2013,19(2):87-104.
[4] Yeung EH,Druschel C. Cardiometabolic health of children conceived by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J]. FertilSteril,2013,99(2):318-326.
[5] Zhu J,Lin S,Li M,et al. Effect of in vitro culture period on birthweight of singleton newborns [J]. Hum Reprod,2014, 29(3):448-454.
[6] Wunder D,Ballabeni P,Roth-Kleiner M,et al. Effect of embryo culture media on birthweight and length in singleton term infants after IVF-ICSI [J]. Swiss Med Wkly,2014, 144:w14038.
[7] Kleijkers SH,van Montfoort AP,Smits LJ,et al. IVF culture medium affects post-natal weight in humans during the first 2 years of life [J]. Hum Reprod,2014,29(4):661-669.
[8] 孔娜,劉景瑜,陳華,等.子宮內膜厚度和形態對體外受精/單注射-胚胎移植結果的預測[J].臨床和實驗醫學雜志,2013,5(12):696-698.
[9] Embryology E S I G. Istanbul consensus workshop on embryo assessment: proceedings of an expert meeting [J]. Reproductive Biomedicine Online,2011,22(6):632-646.
[10] Gardner DK,Lane M,Stevens J,et al. Blastocyst score affects implantation and pregnancy outcome: towards a single blastocyst transfer [J]. FertilSteril,2000,73(6):1155-1158.
[11] Zandstra H,Van Montfoort AP,Dumoulin JC. Does the type of culture medium used influence birthweight of children born after IVF?[J].Human Reproduction,2015, 30(3):530-542.
[12] Harper J,Magli MC,Lundin K,et al. When and how should new technology be introduced into the IVF laboratory? [J]. Hum Reprod,2012,27(2):303-313.
[13] Bolton VN,Cutting R,Clarke H,et al. ACE consensus meeting report:Culture systems [J]. Hum Fertil,2014,17(4):239-251.
[14] Chronopoulou E,Harper JC. IVF culture media: past,present and future [J]. Hum Reprod Update,2015,21(1):39-55
[15] Morbeck DE,Krisher RL,Herrick JR,et al. Composition of commercial media used for human embryo culture [J]. Fertil Steril,2014,102(3):759-766.
[16] 秦小娥,張波,馮貴雪,等.多精受精對體外受精-胚胎移植臨床結局的影響[J].中國優生與遺傳雜志,2011, 19(1):108-109.
[17] 徐志鵬,孫海翔,張寧媛,等.短時受精周期中多原核合子發生率與妊娠結局的關系[J].中華男科學雜志,2012, 18(9):807-810.
[18] Khosla S,Dean W,Reik W,et al. Culture of preimplantation embryos and its long-term effects on gene expression and phenotype [J]. Hum Reprod Update,2001,7(4):419-427.
[19] van Montfoort AP,Hanssen LL,de Sutter P,et al. Assisted reproduction treatment and epigenetic inheritance [J]. Hum Reprod Update,2012,18(2):171-197.
[20] 秦文松,劉英,秦輝靈,等.人卵母細胞玻璃化冷凍技術在輔助生殖中的應用[J].中國性科學,2015,24(2):93-95.
[21] 顧軍.兩種培養基對胚胎質量和IVF-ET妊娠率的影響[J].中外醫學研究,2014,12(27):37-38.
[22] Rinaudo P,Schultz RM. Effects of embryo culture on global pattern of gene expression inpreimplantation mouse embryos [J]. Reproduction,2004,128(3):3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