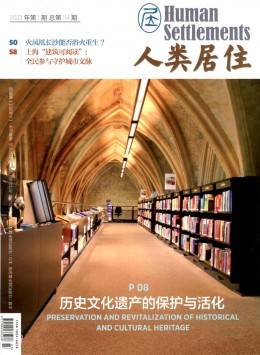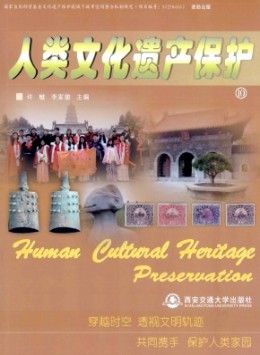人類學研究方法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人類學研究方法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民俗方法學;會話分析;田野研究
會話作為一種社會交往,是在會話參與者的相互協作下而產生的。人們對會話的科學研究始于上世紀60年代。會話分析起源于美國民俗方法學,因此也被稱作“基于民俗方法學的會話分析”,以下簡稱“會話分析”。
會話分析的基本目標是重建會話參與者以其各自的方式構建會話的動態過程,研究對象為所有在真實社會交際場景中自然發生的篇章(Deppermann,2008:20)。由于采集日常真實會話的諸多困難,目前絕大多數的會話分析研究以機構會話或媒體會話為研究對象。因此,如何研究真正的自然語料,成為會話分析研究者面臨的一道門檻。
一、會話分析與田野研究相結合的研究范式
德國民俗方法學會話分析學者(Kallmeyer,2005;Deppermann,2008)主張,從人類學角度研究會話,即采用田野調查的方法獲取真實語料。田野調查,是一種實地研究方法,指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對象的生活中,以參與觀察和非結構訪談的方式收集資料,并通過對這些資料的定性分析來解釋現象(風笑天,2001:238)。
Kallmeyer(2005:1214)認為,作為研究者并非一個被動的觀察者,只是不加反應地重構現實,而是無論在選材、轉寫以及分析的過程中都會用到自身所具有的基本分析資源。研究者本人的錄制、取材方式都帶有人類學工作方法的特點,分析過程中也會代入研究者本人的社會經驗和世界知識。在田野調查中,研究者可以直接感知客觀對象,特別是參與觀察能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鄭欣,2003:52)。
二、會話分析與人類學田野研究相結合的工作步驟
會話分析與人類學田野研究相結合的研究范式主要由收集語料、組織加工語料、經驗性范例和檢驗視角四個階段組成。下面分別進行介紹。
(一)收集語料
第一階段主要是收集和錄制語料。如使用現有的語料庫或媒體語料,則可直接獲取。如要自行錄制,則需嚴格遵守學術倫理,按照田野研究的工作步驟進行:一、培育研究網絡,與研究對象建立友好的關系,以期能夠獲得最接近真實狀態的日常對話;二、在朋友的身份下,向其說明研究意圖和目的,并獲得對方正式的許可,嚴禁在未告知的情況下私自錄音;三、進行田野初探,研究者本人以參與式觀察者的方式、錄制音頻或視頻,不可干預會話的進程。也就是說,經驗性研究要基于真實的交際場景,在此基礎上提出假設,而不是在已有假設的前提下“搜尋”適用于此假設的語料。四、語料錄制結束后,研究者考察取得的語料是否可以用于本研究,據此調整或繼續研究方式;五、進一步擴大語料錄制范圍,建成研究可用的語料庫。
(二)組織加工語料
轉寫是指研究者將語音或視頻,根據一定的規則書面化(Deppermann,2008:40),目的是把會話過程的語言細節記錄下來、加以再現,并認為所有語言細節都對社會現實的重現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視頻轉寫是在音頻轉寫的基礎上,對語言之外的其他模態加以描述。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也有越來越多的轉寫軟件可以用于實踐。
(三)經驗性范例分析
經驗性范例分析是指選取一段典型語料,首先對其進行轉寫及序列性分析,通過分析范例語料得出一定的假設和初步結論,目的是在前期^察的基礎上進行實驗性的分析。通過這一分析,研究者可以對研究問題的答案建立一些初步的假定,并通過后面的研究進行檢驗(段麗杰,2011:47)。
(四)檢驗視角
分析者在已有經驗性范例分析的基礎上,需要不斷地反思和檢驗,以規避因為主觀性而帶來的對某個語言現象以及研究工作本身做出客觀判斷的危險(Kallmeyer,2005:1220)。在這一階段中,主要通過補充新語料來驗證之前的初步結論是否成立,應該補充哪些新的視角,以得出最終結論。
三、小結
綜上所述,本文介紹了基于民俗方法學的會話分析與人類學田野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與工作步驟,回答了如何獲取和研究真正的自然語料這一問題。研究者需嚴格遵循經驗性的工作方法,一切從語料出發,根據語料的特點制定后續的分析方案。
參考文獻:
[1]風笑天.社會學研究方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2]段麗杰.德國企業新聞會的會話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3]鄭欣.田野調查與現場進入[J].南京大學學報,2003 (3):52-61.
第2篇: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學科建設;洛秦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172(2013)04006209
緣起
2005年初冬,人類學家莊孔韶教授到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學,內容是介紹使其蜚聲海內外的關于四川小涼山彝族宗族祭祖儀式戒毒的民族志電影《虎日》[1]的建構。席間筆者詢其編著的在國內很有影響力的《人類學通論》[2](2002)中音樂人類學章節缺失的緣由,莊教授只說再版時請洛秦教授補寫。但是一直到2011年洛秦教授編《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導論》[3](以下簡稱《導論》)出版,還是沒有見到忝列“音樂人類學”章節的《人類學通論》修訂版。缺失的緣由是人類學家囿于音樂研究的專業技能望而生畏的習慣性放棄,還是國內民族音樂學研究缺乏與人類學界必要的學術溝通與交流?音樂學者去做人類學家的研究很是鮮見,而人類學家說說音樂的事兒還真有如彭兆榮[4]等鳳毛麟角的代表。對于人類學知識的缺失或說渴求已使當下一些音樂學專業的碩士和博士到人類學院所讀博士和做博士后等,這屢見不鮮的事實昭示人類學對音樂研究的影響在逐漸加強。
《人類學通論》沒有“音樂人類學”章節,使號稱研究“人類文化”的人類學在實踐中繞道音樂而露出了人類學(者)研究文化的“軟肋”。但《人類學通論》的出版,體現了20世紀初以來近百年間從林惠祥、吳文藻、許烺光,到、林耀華先生等學者前赴后繼的學科貢獻,并吸收借鑒了國內外最新的人類學研究成果,將許多新興的、成長的人類學領域如歷史人類學、影視人類學、醫學人類學、都市人類學等分支學派納入書中,召集全國學界三十余名中青年精英參與編寫,反映了學科成熟的團體風貌和后勁迅猛的學術勢頭。洛秦教授編的《導論》出版對于民族音樂研究領域的影響與莊孔韶教授主編的《人類學通論》出版對于人類學界的影響,有異曲同工之妙,并因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特殊發展背景而彰顯重要的學科品格。
一、《導論》主要內容及結構
《導論》“編者前言”相當于簡短的“序”,是一個謙和的編輯動機言說。在以Ethnomusicology即音樂人類學(或稱民族音樂學)的中國實踐的低調敘述中,凸顯了一種務實和樸實的、和風細雨的學術品格。面對國內音樂學術界對音樂人類學認識的褒貶不一的現實,“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表明了一種務實研究的實踐作風而不是空談,有著“實干興邦,清談誤國”的當下旨趣,也力圖避免空談論爭的浮泛。“編者前言”斷判王光祈將比較音樂學引入開啟音樂人類學中國實踐的萌芽,改革開放后的1980年南京民族音樂學術會議是音樂人類學正式登陸中國的“標志”,由此至今的三十年間基本實現與國際學術界的同步對話和交流,完成了基本的學科建設框架、積累了中國初步實踐經驗。輕描淡寫之間,掠過多少學科成長的步履維艱。隨后是同類少有的“學術及編寫凡例”,以及洛秦、蕭梅、薛藝兵、楊民康、宋瑾、管建華、湯亞汀、齊琨、胡斌、黃婉、吳燕、徐欣、莊曉慶和張延莉等14位作者簡介及生活近照,表明編寫規范和對合作者的尊重及推崇,增強讀者對書著的感知和把握。
全書主體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學科發展歷程”是本書歷史性素描,以單一的章節“第一章,音樂人類學的歷史與發展綱要”為題,分別從19世紀前,19世紀,20世紀初、中、晚的西方音樂人類學的發展歷程描述以及中國人前后的跟進與實踐,這個線性素描勾勒了音樂人類學的昨天、今天以及對明天的展望,特別是清晰敘述西方音樂人類學的歷史脈絡后,作者巧妙地處理與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和民族音樂研究的關系,使用“人類學的中國實踐”一詞,如同使用“中國特色”一樣,消解和包容了學術上不必要的排外和內耗的可能。可以說,“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的提法是洛秦教授獨具匠心的創作,是在多年游歷西學之后結合中國本土經驗的智慧結晶。他兼顧當前中國音樂學術界對Ethnomusicology或稱民族音樂學(傳統音樂或學問或學科)或稱音樂人類學(人類學之音樂研究)的認知和考量。
主體之第二部分“理論與方法”共有六個章節。第二章“音樂人類學的性質和學科名稱”在介紹Ethnomusicology譯名的多種論爭之后,對于這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采取兼容并蓄的思路,化解了糾結著三十年來學術界因對民族音樂研究之熱愛的、觀念史問題之貢獻。而這種貢獻和熱愛有學術路徑“民族”化的文化標簽式的情結,也有趨于構建中西合璧的良苦心智使然,亦有人文大學科構建的抱負頂真。見仁見智,諸多的名號逐漸歸為“民族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之別。作者在談音樂人類學“學科”的話題中觸及到了學科的硬傷,在闡明音樂人類學主要研究活態音樂事件和口傳音樂以及音樂作為文化的研究的性質后,坦然說了“音樂人類學”是一種非學科的“觀念、思維和思想”(46頁),這的確需要勇氣和智慧。而我們的音樂人類學在邊界膨脹之后如何重新建構洗牌?作者留下一個緩沖帶——加了一個附錄:《稱民族音樂學,還是音樂人類學——論學科認識中的譯名問題及其“解決”與選擇》,既然是“學科認識中……”,自然暫時可以沒有定論。
第三章“音樂人類學的實地考察”開宗明義,馬林諾夫斯基在對特羅布里恩德群島田野調查模式及其《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成為科學民族志誕生的標桿,彰顯著音樂民族志學習人類學文化民族志范本的風向。不過,鑒于國內音樂學術界解讀Fieldwork的現實,人類學界習以為常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s)變成了被音樂學界些許認同或從眾理解的“實地考察”,以求國內音樂界對非“田間野外”的風雨橋、游方場、堂屋唱等民族尊重的語言性規避,畢竟國內的傳統音樂研究不是建立在迥然各異的他文化的基礎上,而是深深扎根于情同手足的民間情誼的血肉文本書寫。而第四章“音樂民族志寫作”從人類學“民族志”(ethnography)說到“音樂民族志”(Music Ethnography),雖說廣泛意義上任何記錄族群文化的材料都是民族志,但具有學科方法品格的民族志是居于個體田野工作經歷的個人著述,其學理淵源是西方人類學的田野書寫,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官方修志的“地方志”“民族志”“音樂志”“民族音樂志”的集體性志書以及個人游記大相徑庭。而作者在打開“音樂民族志”與“民族音樂志”的糾結后,用人類學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與“闡釋”利器,再度闡明“音樂民族志”所應有的人類學底蘊,也體現由音樂記寫(“淺描”)向音樂闡釋的“深描”的強調。
第五章“音樂人類學的觀察與參與”在“主位-客位”和“局外-局內”的方法與視角的敘述中,讓我們感覺到音樂領域研究如同馬林諾夫斯基“庫拉”交換研究形同“經濟人類學”(經濟的人類學研究)、格爾茲研究巴里島人的斗雞看到法律人類學(法律的人類學研究),音樂研究有作為人類學部類意識之感(在這里我們不必論爭Ethnomusicology前世今生的異同,只是此地共時性的“音樂人類學”認知)。作為類同于人類學的部類研究,第六章“音樂人類學的記譜與分析”和第七章“樂器文化學與樂器分類”使我們頓時明白了為什么從事人類學研究的一群人,面對包打天下“文化”研究抱負的人類學理想,卻不得不舍去這塊蛋糕。因為涉及音樂本體的研究,需要非常專業的音樂知識和技能,而這些知識和技能不僅僅是符號闡釋,而且也是個人音樂技能的考驗。作為音樂的民族志,音樂本體是躲繞不開的攔路虎,記譜就是一個基本研究的試金石。記譜不僅需要知道記譜的符號,明白表達什么意思,還要會讀譜,知道寫的是什么,最后,還要有音樂的理論水平,根據記譜和臨場體驗,分析音樂本體,這就必須是音樂的專業表達,[美]彼得·基維(Peter Kivy)在《純音樂:音樂體驗的哲學思考》一書的《導言》中非常精辟地說道:“在所有美的藝術中,音樂是唯一一門擁有了專業知識和專業詞匯才能跟‘學者對話’的一門藝術”[5]。由于需要較為專業的知識,就把這種人類學的音樂研究獨立出來,起了“音樂人類學”的名稱,而很多不以關注音樂為己任的人類學著作,遇到歌舞也就一帶而過,不做仔細的研究。事實上,一個社區,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音樂的存在,至于人類學家是否研究音樂本體(能否研究是另一個話題),就由課題的需要決定了。作為音樂人類學者即便是研究音樂文化事項,最后的落腳點也不一定是音樂本體,也可能是音樂作為藝術門類或作為文化門類體現出來的特點或啟示。
主體之第三部分分為九章。這一部分主要編寫了當前音樂人類學研究的新方法和論域,體現了《導論》并非重復“概論”的與時俱進思想,讓我們及時跟進音樂人類學的學術前沿,而不僅僅是“音樂人類學概論”式的基本概念普及。
第八章“‘新史學’視野下的音樂人類學與歷史研究”介紹了西方音樂人類學研究中的“新史學”傾向,并以“附錄”的文本佐證音樂人類學研究中的歷史經驗參與。傳統的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以研究無文字民族和口傳文化為旨趣,其歷史維度先天貧血,沒有記載或缺少文獻,使得共時研究成為必然的選擇,因此遭遇了歷時性缺失的譴責。時過境遷,今天的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研究,不僅蒂莫西·賴斯(Timothy Rice)在《關于重塑民族音樂學的模式》[6](1987)中借用格爾茲針對儀式研究提出的“歷史構成、社會維護和個體適應經驗”分析觀念對梅里亞姆(Alan P. Merriam)的“概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進行改造,理論化地對音樂人類學提出了歷史維度的研究要求;而且要求共時性與歷時性并重,這意味著音樂人類學研究從無文字族群向高文化研究的拓展和邁進。只有這樣,無文字族群文化的泛歷史或口傳歷史的研究在文明社會中才有了根本性的轉型,“附錄”的昆劇研究成功例證就是漢族文獻豐富的注腳。人類學化的歷史學互文性研究使歷史研究部有了當代的烙印,凸顯了個體對歷史的感性認知,如作為“新史學”代表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7],[美]柯文把發生在中國晚清時期的“”在歷史不同時空中的認識和解讀進行挖掘,體現了歷史學與人類學結合的巨大人文價值。歷史學化的人類學研究彰顯了人類文化的時空底蘊,全球化的時空沒有了“異樣”的他者,音樂人類學的研究沒有理由置之度外,而更應跟進當下,走向更加立體化的歷史視角。
第九章“城市音樂人類學”不是音樂研究的中國式“農村包圍城市”宣言,而是從農村到城市的研究視閾的擴展。城市音樂人類學也不是作為一個學科的添設,而是學科歷史轉型的一個論域。誠如上文所說,現代化過程中“全球化的時空沒有了‘異樣’的他者”,封閉的社區已經不復存在,不管是對于現實中國的研究者難以作實際居住式的參與觀察而變通作“家門口的田野”,還是學科跟進現代社會社區多樣化音樂活態的現實,拓展學科邊界包容日新月異的城市音樂如搖滾等非藝術音樂的即興表演活動,失去了藝術審美尊貴地位的城市音樂生活在不同價值指向的牽引下進行著平俗的展演,或服務于政治的布道,或歌頌于企業的投機,或從眾于市民的戲虐,或認同于紈绔的宣泄,換言之,與主流話語大相徑庭的社會音樂活動層出不窮,并因城市巨大的人力資源而甚于鄉村的變化,內特爾1978年寫的《八城市音樂文化:傳統與變遷》“前言”[8]說,財富、權力、教育、職業分化、人群整合、民族交融、文字傳媒、貧富差距等問題以及生活樣式的繁雜使得城市化過程中來自各地不同的音樂風格和體裁匯集導致的文化變遷吸引了學者將目光從鄉村城鎮轉向城市音樂文化生活,同時城市音樂人類學的研究也可以更好地借鑒和實踐“新史學”的研究方法。
第十章“象征主義和音樂符號學”和十一章“儀式音樂研究”,前者主要是一種研究觀念和方法,后者主要是一個研究領域和論題。它們都因音樂語言的關聯而分別與象征、符號、結構及儀式搭上不同的關系。作者不辭辛苦,在仔細梳理這些理論的來龍去脈后,最后落腳在中國的實踐現實上。第十章說明了象征理論和符號學在音樂人類學研究前景以及中國實踐,而第十一章則從宗教儀式的角度敘述了儀式音樂研究的理論視野和中國經驗的創新拓展和豐碩成果,全面地介紹我國儀式(宗教)音樂研究的不菲成績。
十二章“文化相對主義與音樂人類學”追述了“文化相對主義”產生的歷史過程,并對其應有的學理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梳理,對于初入人類學門檻的研習者,具有很好的引導作用。“文化相對主義”是一個聚訟不已、欲說還休的話題,其產生本身就是“歐洲文化中心論”流布的悖論(副產品),也是人類學(音樂人類學)洗心革面的產物。對于西方學術界,服務于殖民時期的文化中心論(源于進化論)在二戰后紛紛獨立的民族國家和地區沒有了市場,文化相對主義恰好成為了人類學學者反思性研究的方法和利器,既解決了與作為田野工作對象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相互關系,又成為發展中國家和人類學者民族文化自我認同的理論根據。問題在于,強調文化相主義的人類學在取得重要研究進展的同時,卻留下一個難以釋懷的癥結,即作為進化結果的人類族群,自從殖民時期以來打破族群邊界躋身共時性世界空間,人類社會文化能否回歸歷時性的坐標體認?同智力文化的個體差異是可以相對而論,而不同智力的文化是否還是必須有一個普同性價值判斷?既然唯物(生物進化與社會進化)進化必然快慢有異,又何以判斷非同智力及其文化?無論如何,“文化相對主義”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價值觀,對于推動西方學術界和非西方學術界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的發展找到了共同的價值支點,極大地推動了學術的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
十三章“社會性別與音樂”和十四章“音樂人類學新研究,‘離散’音樂文化”是一種新研究視角和論域,也是我國音樂研究的薄弱環節。“社會性別與音樂”的問題是隨著20世紀70年代女權主義的興起而出現的研究視角,實際上作為文化的音樂在被研究時,往往忽略性別角色的問題。“樂者為和,和則相親”(《樂記》),享樂向來是男子的特權,也因此音樂研究中的性別視角會因為男權社會思想的影響而簡化為忽略女性聲音的單一呈示,女性操演音樂文化的把控又往往附屬于男性權力的需要,難有獨立話語權去拒絕男性知曉甚至是參與。只有個別的音樂可以從社會性別文化去關注,往往也是那些作為非主流文化而活躍在女性邊緣話語圈中的亞敘事,如中國婦女的“哭喪”“哭咒”和“哭嫁”三哭等音樂文化,值得從性別的角度去加以解讀。女權主義在音樂人類學中的應用在于提示我們從女性角色的角度詮釋音樂,為傳統的音樂研究拓展新的研究路徑和視角。“離散音樂”研究也是近年來逐漸為人們關注,其中“飛地”音樂文化現象在中國為人們關注是因為1979年至2009年《中國民族民間十部文藝集成志書》編撰中大規模地毯式的音樂調查,但由于集成編撰工作的艱巨和離散文化缺少理論指導,所以沒有很好取得“離散音樂”研究的成果。但隨著21世紀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城市里聚集某地某些“離散”族(人)群和“離散”文化的存在,使“離散音樂”文化研究成為一個與時俱進的現實。上海音樂學院已開研究風氣之先,取得了“離散音樂”文化研究的初步成效,不管是拓展音樂人類學研究的領域還是佐證國家文化策略的建設,“離散音樂”文化研究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
十五章“音樂人類學視野下的多元文化教育”介紹了北美人類學家參與音樂教育合作的源流,并在多屆國際音樂教育學會會議上發表了影響深遠的發言,使多元文化教育價值得到世界范圍內認同,特別是1994年著名音樂人類學家內特爾(B. Nettl,1930~)參與起草和主稿的國際音樂教育學會《為世界范圍音樂教育倡議的信仰宣言》和《關于世界音樂文化的政策》兩個政策性文件,佐證列舉了1996年出版的由[美]杰·托德·提頓(Jeff Todd Titon)主編的《音樂世界》、1999年出版的由眾多音樂人類學家參與的遠程電視教材《探索音樂世界》和2003年出版由內特爾主編的《世界音樂概覽》等三本多元文化的音樂教材。為音樂人類學的多元文化教育價值在世界范圍內的推行,增添了新的出路,而且也為和諧世界程序的建立提供了豐富的教育資源和人文給養。
第十六章“后現代思想與音樂人類學”把音樂人類學放到后現代文化語境中,從后現代文化哲學思潮的角度,對音樂人類學遭遇的可能性影響做了廣泛的關注和大膽的預測,在學科邊界和特定情境的悖論中審視音樂人類學,提出了中性化研究的走向。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研究現存文化,并與民族民間的傳統活態文化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的非后現代性是否可以移植后現代人文思潮的方法和觀點?作為《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9]和《寫文化》[10]之后的人類學特別是音樂人類學,很難與“—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接軌并繼續,當下主體敘事的傳統性使然,后現代思潮對音樂人類學的影響依然猶抱琵琶半遮面。遭遇敘事危機擠兌的人類學,是否能夠在對音樂的描述敘事中輕松地采用浪漫的筆調和奇特的結構整合田野的材料?走進日常生活的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與后現代思想有多遠距離,本章促使我們思考。
該書主體部分的十六章之后有長達78頁的三個附錄:附錄一是《西方音樂人類學家簡介》英文原文,有37位西方音樂人類學家的簡介;附錄二是375篇西方音樂人類學英文原著的參考書目及推薦閱讀書目;附錄三是中文類音樂人類學的276篇論文、57部著作和13部譯著等參考文獻及推薦閱讀書目。
二、《導論》的編寫特點
《導論》不是一個概論性的教材,而是引導年輕學人入門現代音樂人類學的專業向導,其所涉獵的學術思想和理論譜系極其豐富。此書編寫站在音樂人類學學科建設的高度,高屋建瓴,嫻熟駕馭中外音樂人類學學科發展的理論和方法,旁征博引,從學科歷史、理論與方法、研究新論域等方面作了宏觀、系統的介紹,體現了以下幾個鮮明的編寫理念和特點:
(一)系統梳理和介紹音樂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來龍去脈
目前國內音樂學術界對音樂人類學的認識還處在仁智不一的階段,而系統介紹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的著作并不多見。不僅僅是出于普及和掃盲音樂人類學學科知識的需要,而且對于初入音樂人類學門檻的青年才俊,也有必要有一本系統而仔細介紹音樂人類學學科理論和方法的導引著作,更何況對于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認知,還必須有一個系統的介紹和宣傳,《導論》的產生就是居于這個思想的產物。撰寫者在廣泛認真而細致地查閱大量相關音樂人類學研究文獻及其相關學科理論的基礎上,不厭其煩地梳理介紹學科術語理論,對于重要的術語人類學家及音樂人類學對于重要的理論與方法,認真謹慎地梳理其源起、發展脈絡,其代表學者和著作,附有英文原名、生卒年限、出版年限等,使人閱讀后能夠清楚地了解理論與方法的來龍去脈,而不是使人如墜云里霧里的空降的術語和理論。
如第一章“音樂人類學的歷史與發展綱要”講到“比較音樂學”(Comparative Musicology)的產生時,追溯到音樂記載在早期殖民主義對殖民地文化做全景式描述時作為附帶品和點綴,采取“科學性”的中立態度,產生歐洲中心論的萌芽和歐洲標準的觀念,發展了“社會文化進化論”及對“和諧的普遍性”的推崇。啟蒙運動倡議批評“歐洲中心主義”和更為嚴謹研究“非歐洲文化”,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出版《音樂辭典》(1768)對非西方音樂文化多樣性的認可。“和諧的普遍性”推崇是自然法則和數學的魅力所致,17世紀美爾瑟尼(Mersenne)用數學規范音樂的企圖得到赫爾姆霍爾茨(Helmholtz,1821~1894)發明實驗測音儀器的支持(P.9),受普理查德(Prichard)民族學派研究方法的影響,依然是“搖椅式”研究的卡爾·恩格爾(Carl Engel)用比較的方法建立了“民族音樂”理論,而英國語言學家A.J.埃利斯(Alexander John Ellis,1814~1890)則在其基礎上建立比較音樂學學派,使埃利斯成為“比較音樂學”的創始人。1885年埃利斯《論各民族的音階》提出的“音分法”和1877年愛迪生留聲機的發明推進了音樂的實驗室研究,以施通普夫(Carl Stumpf,1848~1936)和霍恩博斯特爾(Erich Moritz von Hornbostel,1877~1935)為代表人物的“柏林學派”成了比較音樂學的大本營。至此,我們厘清作為音樂人類學前身的比較音樂學的產生及其與人類學民族學(派)的歷史淵源。
又如第十章“象征主義與音樂符號學”講述“象征”(Symbol)理論來源,不是空降術語,而是從涂爾干(Emile Durkheim,1912)群體研究和象征表達,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950)精神現象的象征表現研究,馬林諾夫斯基語言象征研究,列維斯特勞斯(ClaudeLeviStrauss,1963)文化象征體系研究,克利福德·格爾茨把文化活動作為象征符號研究,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儀式的結構象征研究以及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日常生活的儀式象征研究等,按照理論發生和影響的時間順序,娓娓道來,清楚而明白。講到符號學時,從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和美國哲學家皮爾士(Charles Sanders,1839~1914)的符號學理論講起,索緒爾語言學中的“能指”和“所指”、“語言”與“言語”,皮爾士的“符號”與“對象”、“象征”與“意義”都具有二元結構的特點。認為文化類同語言,可以作為符號體系觀察,從而構成音樂人類學的符號學和象征理論的來源。如此等等,這樣的溯源,使讀者特別是音樂學的讀者容易找到入門的路徑,對于需要進一步深入的人,提供了一個學習的向導,而不至于被共時性話語呈現而遮蔽了理論和方法應有的歷時性特征,使讀者成了摸象的盲人。
(二)引介音樂人類學新的學科前沿
《導論》雖然敘述音樂人類學的歷史只有一百多年,卻經過了“比較”“民族”和“文化”三個階段;從“搖椅式”研究到“田野觀察”,再到“新史學”視野,音樂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不斷地更新;從“非歐音樂”研究到“全部音樂”,關注、研究對象不斷擴大,學科邊界不斷擴展。一方面,19世紀學科林立的分門別類劃分研究的需要,沒有獨特學科方法和固定對象,使得借鑒方法和泛化對象的音樂人類學不斷招致非議,是學科還是方法觀念的論爭不絕于耳,但追隨者卻不斷增多,逐成氣候。不管是音樂學的人類學研究,還是人類學的音樂研究,音樂的人類學研究卻一刻沒有被人們放棄。而至于叫什么學科名稱,中外均有論爭,但跟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觀念沒有什么大的改變。受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在經過傳統的小社區研究之后,音樂人類學的研究在不斷擴展邊界的同時,也在尋找新的研究視角。《導論》放棄一般概論的基本敘述路徑,不再面面俱到講述田野工作的相關事宜,而是直接切入音樂人類學新研究,重點引領好學之人進入學科研究的學術前沿。居于學科研究的歷史與現實,《導論》中“‘新史學’視野下的音樂人類學與歷史研究”是歷時性維度缺失的矯正導引,是對歷史語境的一種研究關顧;“城市音樂人類學”是從鄉村社區口傳音樂研究轉向城市社會音樂研究的新領域,是簡單社區向復雜社區音樂文化研究的現代轉向;“象征主義與音樂符號學”是音樂人類學學科理論與方法的新拓展,也是人類學敘事危機在音樂人類學中闡釋突圍的路徑尋找;“儀式音樂研究”是音樂研究的儀式學觀照,賦予了音樂研究中儀式音樂本體研究的文化意義和深層解讀;“社會性別與音樂”一反音樂研究中的無性研究慣習,以女性主義的理論和視角深入挖掘音樂文化中女性角色意識和女性亞文化特色;“音樂人類學新研究:‘離散’音樂文化”是對居于傳統飛地文化(或孤島文化)的解讀和現代移民群體文化的漂移關注,是極度擴張的現代社會亞群體文化的研究引領;“音樂人類學視野下的多元教育”引入音樂教育有些唐突,但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解決了音樂人類學知識生產“向何處去”的終極問題,賦予了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而十六章“后現代思想與音樂人類學”則是人文學科“表述危機”在音樂人類學中的思辨體現,也讓我們在關注社會日常生活音樂文化地位的同時,有一種關懷象牙塔文化思潮的情懷。這幾個方面,無一不是傳統音樂人類學的新突破和新拓展,體現出《導論》引領音樂人類學學科前沿的抱負和雄心。
音樂人類學是舶來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于我們這個亟需音樂人類學學科史論與方法滋潤的中國音樂人類學實踐,作者羅列了西方音樂人類學發展史上重要的學者和重要的代表文獻,使執著于音樂人類學學習的學人能夠查閱原文和找到進一步深入學習的方向和路徑。
(三)學科團隊的集體編撰及中國實踐的展現
《導論》是洛秦教授及其合作者的力作,建立在大量“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吸收了國內外的最新研究成果,顯示了非同一般的、嚴謹的學術態度和寬廣的學術視野。一反個人編著的慣習,組織了我國主要從事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中青年學者,對“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采用了較為獨特、新穎的敘述方法,體現了其較為前沿的學術觀點,為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中國實踐打開了一扇嶄新之門。特別是召集全國學界14名中青年學者參與編寫,反映了音樂人類學學科中國實踐“篳路藍縷”走向壯大的團體風貌和后繼有人的學術勢頭。
音樂人類學在中國實踐遭遇了較多的尷尬和難堪,第一個問題是民族音樂學會改弦易轍,使襁褓中的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成了“無媽的孩子”(見下文“學科重建標志”);第二個問題是學科名稱是民族音樂學、音樂文化學還是音樂人類學等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11];第三個問題是舶來品的民族音樂學(即Ethnomusicology)傳入的標志性事件“南京會議”的發起人是否是高厚永先生[12]?第四個問題是音樂的文化研究(即音樂人類學)是學科還是思想方法?蒲亨強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見解[13],洛秦教授表達了許多情況下不得不把“音樂人類學”尷尬的作為“學科”(P45~46)。我們在想,有哪一種思想和觀念對音樂研究的影響如此巨大,以致追隨者前赴后繼?是傳統的科學規范過于苛刻,還是音樂人類學邊界的自我膨脹坍塌了本身的學科大廈?如何看待這個“不是學科又是學科”的奇特研究范式,值得我們思考。第五個問題是“音樂人類學”研究存在的所謂“去音樂化”現象,是有回避本體還是本體過于簡單亦或是課題需要使然?李方元教授做了很好的探討[14]。
不管是第一個問題學科“少年喪母”的先天不足,還是第二個問題學科“正名”之爭的無奈,對于這個本身就是“槲寄生式”的殖民成果的學科(或學問),面臨著學科合法性的追問,亦或是第四個問題音樂人類學是學科或是觀念思想?我們的困惑是“槲寄生”于殖民時代的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隨著二戰后民族國家的紛紛獨立,提供殖民統治資治的動力和市場已不復存在,“他者”已不是殖民對象,異文化研究不再只是[美]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研究《菊與刀》(1946)[15]的殖民需要,也有[美]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研究《薩摩亞人的成年》(1928)[16]以觀照自身的目的。研究的動力,有的是得到某一機構的資助而為其提供資鑒服務,有的是為了學科學術的發展而樂此不疲。緣起于殖民需要(或說槲寄生式)的人類學由于有了特別的研究方法(田野作業)和研究對象(他者文化)而躋身于學科之林,而同樣緣起于殖民時期(或說槲寄生式)的比較音樂學如果不嫁接于人類學陣營——代表事件是喬治·赫爾佐格(Herzog George,1901~1983)1925年投奔到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門下——還會有怎樣的發展?比較音樂學獨特的研究方法將會是什么?學術空間還有多大?音律的比較?音階的比較?換言之,比較音樂學向民族音樂學的轉換是偶然的事件還是必然的選擇?
從1885年“比較音樂學”(埃利斯:Comparative Musicology)到1950年民族音樂學(孔斯特:Ethno-musicology)再到1964年音樂人類學(梅里亞姆: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關注族群、關注文化成為一種趨勢,并且沿襲應用人類學經世致用的價值取向進行研究,如約翰·布萊金《人的音樂性》、安東尼·西格爾的《蘇雅人為何歌唱》等等,通過音樂的研究最后落腳到文化的啟示上,唯有此,通過個案的研究提升研究的視角和品格,達到與大學科對話的目的。可以說,比較音樂學與人類學的嫁接后的Ethnomusicology,在失去殖民需要推動的支配后,處于更加“寄生”的狀況,田野作業的方法是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是音樂學的,達不到構成傳統學科的標準。因方法論而不能歸屬音樂學被責備為“去音樂化”傾向,歸屬人類學又因人類學者難以駕馭“音樂本體”而困難重重。如果我們囿于學科的歸屬而浪費了時間和精力,不妨我們把這個稱為觀念的“音樂研究”歸屬“人類學”學科,作為下屬部類研究,名正言順。至于在研究中強調是本體還是文化,那根據課題需要而定,不必固執己見。竊以為梅里亞姆用“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音樂人類學)強調Ethnomusicology研究的人類學路徑后,雖然學科名稱沿用“Ethnomusicology”沒有用“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或“Music Anthropology”,但是后繼者多用了梅里亞姆關于音樂研究人類學方法的“概念、行為、音聲”三重認知模式,換言之,梅里亞姆之后的名稱沒有變,但是研究方法的梅里亞姆模式已廣為接受。
音樂人類學與中國“民族音樂學”是有區別的,所以,洛秦教授稱為“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在編著《導論》前,洛秦教授就主編了一套五卷本的“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文庫”[17],較為全面地收集了國內具有音樂人類學思想和觀念的文獻,成為編著《導論》的文獻基礎;又組織團隊進行了城市音樂人類學-上海城市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離散文化的音樂飛地研究”等新研究,提出了“音樂文化詩學”的研究方法[18]等,成為編著《導論》的實踐經驗基礎。《導論》是十多位作者的集體心血,也是三十年來音樂人類學的中國集體實踐經驗的成果展現。
三、《導論》的學術貢獻及價值
該書是國內第一部以人類學視角撰寫的“音樂人類學理論與方法導論”,反映了作者的學術取向,對我國音樂學學科及民族音樂研究發展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中國“民族音樂學”學會分化后的學科重建標志
眾所周知,雖說有王光祈、蕭友梅在20世紀初將比較音樂學(Comparative musicology)引入,但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真正進入大陸音樂學界卻是以1980年南京藝術學舉辦首屆“民族音樂學學術討論會”為標志。由于“民族”一詞在中國的多義讀解,既可以泛指“中華民族”,也可以特指“少數民族”。因而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民族民間音樂研究以及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都可以皈依“民族音樂學”旗下,使之可以囊括民族音樂之學科或民族音樂之學問的含義,并且由于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具有“民族音樂學”的譯名而被包容進去。這一個兼容并包研究的名號,匯集了一群從事民族音樂研究的學者和音樂集成編撰的工作者,為中國民族音樂研究轟轟烈烈地工作著。
可是好景不長,伴隨著“為民族音樂學”名號的論爭,經過1982年中國音樂學院舉辦“全國民族音樂學第二屆年會”,1984年分化為“全國民族音樂學第三屆年會”(少數民族音樂專題)貴陽會議和“全國民族音樂學第三屆年會”(民族音樂形態研究)沈陽會議,貴陽會議倡議成立“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或者過于厚重的歷史使漢族音樂必然成為專門的領域,過于寬廣的族群使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必須設定專門的旗號,進而到1986年在齊齊哈爾市召開的民族音樂研究學術討論會就直接成第二屆“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年會,并追認“全國民族音樂學第三屆年會”(少數民族音樂專題)貴陽會議為第一屆年會;而時隔一月之后在中央音樂學院召開的第四屆民族音樂學學術討論會也改弦易轍,成立“中國傳統音樂學會”取代“民族音樂學會議”,新成立的兩個學會每兩年召開一次學會年會。至此,“民族音樂學會議”已不復存在。
這個輕描淡寫的學會歷史敘述背后有一個巨大的學科傷痛,就是以“民族音樂學”名義起家的研討會(學會)最后拋棄了“民族音樂學”,使Ethnomusicology成了無家可歸的棄兒。1980年的“民族音樂學會議”囊括了“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或研究)”“(漢族)傳統音樂學(或研究)”和Ethnomusicology(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1984年開始分化出“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剩下的“民族音樂學會議”理應還有“(漢族)傳統音樂學(或研究)”和Ethnomusicology,可是1986年成立“中國傳統音樂學會”取代“民族音樂學會議”(高厚永語)[19]后,主要以研究漢族傳統音樂為目的的“中國傳統音樂學會”已經不能涵蓋“民族音樂學”含義,Ethnomusicology只能游離出來,沒有了安身之所,開始了從1986年至今長達二十多年的漂泊。
俗話說“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不管人們是否承認,以洛秦教授為代表的學人群體,以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以及上海音樂學院研究生專業建設為學科平臺,以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和《音樂藝術》為學術陣地,彰顯音樂研究方法的事實選擇,結出豐碩成果——即是這本洛秦主編《導論》的出版,使之成為中國“民族音樂學”學會分化后的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學科重建標志,成為一面旗幟,其過程有些慘淡經營的悲壯色彩。
(二)音樂人類學“中國實踐經驗”的明證
Ethnomusicology直譯為“民族音樂學”或意譯(或另用)為“音樂人類學”等名稱,區別在哪呢?是空穴來風嗎?“Ethnomusicology”分明是個舶來品,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學科,而實際上歐洲啟蒙運動以來熱衷于學科分門別類的研究時,我國的學科意識也不是十分的強烈。從構詞法譯“Ethnomusicology”為“民族音樂學”可以兼容我們習慣的“民族音樂之學”,難道改弦易轍的“傳統音樂學會”成立時就沒有意識到是對“民族音樂之學”某種意義的揚棄或說放棄?學會更名行動時不去論爭稱“民族音樂學會”或是稱“傳統音樂學會”是否有利中國民族音樂研究,而是囿于“民族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稱謂的辨析,對“民族音樂學”有些“抽象的肯定(名稱之辮),具體的否定(學會嘩變)”的意味,這個“羊頭”還要不要掛?基于中國的現實,又何必要“民族音樂學”的噓頭?因有“傳統音樂研究”使得“民族音樂學會”有了“民族音樂之學”的底氣,而失去“傳統音樂研究”之后的Ethnomusicology(以學會為標志,即民族音樂學會)還有多少中國的“民族音樂之學”的維度?
音樂人類學,愛之則趨之若鶩,恨之棄之如敝屣。這也正如《4′33″》,如果約翰·凱奇(John Milton Cage,1912~1992)不是音樂大師,有誰會把《4′33″》當音樂看?因為凱奇是音樂大師,我們難以望其項背,所以我們沒有懷疑過《4′33″》的音樂性!音樂人類學,這個擾亂我們音樂研究傳統思維慣習的“怪物”,究竟要如何理解,如何貼上標簽,才能讓我們跟上大師們的思路?人類學傳入國內沒有跟民族學打架,接受了!數學傳入后取代了“算術”,也為國人接受了!可是,這個“音樂人類學”怎么就會招人另眼相看?
時來運轉,2005年1月1日成立的由上海市教委主辦、以上海音樂學院為依托、以音樂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為主題的研究機構——“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研究院以洛秦教授為首席研究員,特聘研究員有楊燕迪、韓鍾恩、蕭梅、湯亞汀、薛藝兵、宋瑾、楊民康、管建華,以及臺灣大學沈冬、美國威斯利安鄭蘇、美國巴德學院Mercedes M. Dujunco、美國加州大學Helen Rees等著名專家學者組成,分別來自上海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美國大學等。“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的成立,使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在中國有了安身立命的居所,結束了近二十年(1986~2005)處于散兵游勇的研究狀況。在E-研究院的倡導下,從國際語境中的音樂人類學觀念和方法、中國視野中的傳統音樂聲像行為、上海地域中的城市音樂文化三個方面進行研究。在與國際學界廣泛交流的學術環境中,建立現代信息化工作平臺,與國內外大學和研究機構聯手,整合和優化研究資源和人才,圍繞“中國視野的音樂人類學建設”為目標,開展扎實且具有創新意義的基礎研究。
正像《導論》“編者前言”所說,“30年后的今天,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已經基本實現了與國際學界的同步對話和互動,并且已經獲得了不少成果和新的認識,不僅完成了重要而基本的學科建設框架,而且‘中國經驗’探索進程也已逐漸開啟,并獲得了初步的積累。”回想三十年前(1980年)在南京藝術學院登陸的“民族音樂學”在學會改制(1986年,如同釜底抽薪)失“陸”(失學會依托)之后,好不容易經過二十多年的艱苦奮斗,才有了今天的以洛秦教授為首席研究員的“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為音樂人類學的學科發展做出了巨大的成績:一是從2010年開始以音樂人類學方向(原為民族音樂學)招收了博士研究生及碩士研究生,并開設了音樂人類學博士后工作站,其畢業生已經逐漸成為當前音樂研究的骨干;二是E-研究院研究員居于音樂人類學的研究領軍地位,其研究如城市音樂文化研究等引領和輻射了國內音樂人類學研究的前沿;三是以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和上海音樂學院學報《音樂藝術》為陣地,出版和發表了國內外大量的音樂人類學研究著作,諸如“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文庫”(三輯)、《啟示、啟示、覺悟與反思——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與經驗三十年》(5卷)、“上海城市音樂文化研究叢書”“西方音樂人類學名著譯叢”“音樂人文地理叢書”“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文庫”“西方文化視角中的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系列”“中國音樂學經典文獻導讀系列”、《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文集》《藝術人類學文集》等,以及《音樂藝術》連續多年刊登年度“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專欄”(教育部社科“名欄”)。當然,音樂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是諸多學者付出了心血,是那些默默無聞辛勤耕耘的學者的貢獻為學科的建設注入了活水源頭,由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資助、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如梅里亞姆《音樂人類學》、約翰·布萊金《人的音樂性》等著作推動了為音樂人類學的學科建設,等等。因此,我們說,建立在中國實踐基礎之上的《導論》的出版是“中國經驗”的明證,也是褒貶不一之下的音樂學術研究的事實選擇的宣言。
當然,《導論》無疑還有些不太完滿,一是是否可以把撰寫者的范圍擴大一些,請一些旅居海外的學者介紹當前海外音樂人類學現狀;二是是否對傳統的音樂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也有必要增添介紹的章節,以便讀者較為全面知曉音樂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三是如作為非主流話語的后現代文化思潮對音樂人類學發展的影響是否真的這么大?等等。期待《導論》在再版之時可以斟酌考慮。
結語
《導論》編撰者殫精竭慮,集團隊功力而作,為中國音樂人類學的實踐經驗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其成績必定會對中國音樂人類學的學科建設大有裨益。1986年中國民族音樂學會議分化為“中國傳統音樂學”和“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兩個學會,而不能歸屬或不全歸屬于這兩個陣營學術路徑的個人和群伙堅守和追求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學術旨趣和學科理念,以一種篳路藍縷的悲壯操守,經過二十多年的摸爬滾打,以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及上海音樂學院為龍頭,逐漸形成了旗幟鮮明的“音樂人類學”研究群體,取得了不菲的業績,成為當前音樂文化研究的第三支重要力量。洛秦編《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導論》的出版,是音樂人類學中國實踐的標志性成果,是音樂研究中音樂人類學事實選擇的寫照,表明音樂人類學在中國音樂研究實踐取得了不可忽略的地位。
注釋:
①洛秦編:《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導論》,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
參考文獻:
[1]莊孔韶.“虎日”的人類學發現與實踐——兼論《虎日》影視人類學片的應用新方向[J].廣西民族研究,2005(2).
[2]莊孔韶.人類學通論[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3]洛秦.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導論[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
[4]彭兆榮.人類學視野中儀式音樂的原型結構——以瑤族“還盤王愿”儀式為例[J].音樂研究,2008(1).
[5][美]彼得·基維.純音樂:音樂體驗的哲學思考[M].徐紅媛,王少明,劉天石,張妹佳,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0(4).
[6][加]賴斯.關于重塑民族音樂學的模式[J].湯亞汀,譯.中國音樂學,1991(4).
[7][美]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M].杜繼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8][美]內特爾.《八個城市的音樂文化:傳統與變遷》前言[J].洛秦,黃琬,譯.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09(4).
[9]喬治·馬爾庫斯,米開爾·M·M·費徹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M].北京:三聯書店,1998.
[10]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M].北京:三聯書店,2006.
[11]洛秦.稱民族音樂學,還是音樂人類學——論學科認識中的譯名問題及其“解決”與選擇[J].音樂研究,2010(3).
[12]杜亞雄.民族音樂學傳入我國的途徑和過程[J].音樂藝術,2012(2).
[13]蒲亨強.音樂人類學:學科或方法?[J].藝術百家,2012(3).
[14]李方元.對梅里亞姆研究理論“三步驟”的思考與解讀——民族音樂學人類學取向與“兩張皮”困境[J].音樂探索,2011(2).
[15][美]露絲·本尼迪克特.菊與刀[M].田偉華,譯.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1.
[16][美]瑪格麗特.米德.薩摩亞人的成年[M].周曉虹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17]洛秦.啟示、覺悟與反思—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與經驗三十年》(1980~2010)1-5卷[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
第3篇: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語言人類學;文化;學科建設
一、語言人類學的學科發展
語言人類學(linguisticanthropology)是人類學的分支學科,同時也是人類學與語言學的一個交叉學科。但由于世界各國的學科淵源不盡相同,語言人類學的學科界定以及學科歸屬不盡相同。在前蘇聯所體現的歐洲大陸體系中,人類學主要指體質人類學,它與考古學、語言學、民族學構成關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學科。在以美國為代表的北美體系中,語言人類學與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學)、考古人類學等一起構成人類學的學科體系。現在學術界一般認為,語言人類學是人類學研究語言與文化關系的一個學科,有時也可當作人類語言學。不管是人類語言學還是語言人類學,都涉及到“傳統的歷史比較、親屬關系構擬,到‘認知語言學’(cognitiveanthropology)、‘說話民族志’(ethnographyofspeaking)、語用學和語言規劃”。①語言人類學旨在通過語言的研究或借助語言學的研究成果達到深化認識人類文化的目的,同時也使不同的語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語言人類學的學科淵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語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紀末,德國學者海德爾(G.Herder,1744-1803)指出語言與民族之間存在著同一關系。他認為,一種民族的語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語言。語言學家馮堡特(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進一步發展了海德爾的觀點,他認為語言是全部靈魂的總和,語言是按照精神的規律發展的。“語言的所有最為纖細的根莖生長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對語言的影響越恰當,語言的發展也就越合乎規律,越豐富多彩。”②語言相對論認為,語言有比較完善的和比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蠻部落的語言也不應該受到譴責或輕視,因為每一種語言都是人類原有的創造語言能力的表現。”海德爾和馮堡特都認為民族的語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觀和語言才能的體現。”③在這些觀點中,語言作為“中間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語言作為特殊的民族文化,語言等同于民族精神這些思想,讓人們逐漸認識到語言的文化性質和文化價值。語言是人們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這就是語言的文化性質;語言的文化價值主要指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各民族都會把自己的各種文化放在用語言作為標識的貯聚庫里,通過語言可以來透視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質。
索緒爾(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類學與語言學結合起來研究的第一人。為了回答語言對于人類學、民族學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闡述,索緒爾從語言與種族、民族統一體、語言古生物學、語言的類型和社會集團的心理素質等幾個方面進行了論證。索氏樹立了從語言的角度來探索人類歷史上文化現象的典范,為以后語言與民族,語言與文化相互關系的研究開了先河。④同時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過“回顧法(retrospectivemethod)”進行語言重建的方法為人類學開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鑒。20世紀初期,索緒爾的追隨者即社會心理語言學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較注重語言與民族以及文化之間的密切關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類學功能學派的代表人物馬林諾夫斯基(B.K.Malinnowski1884-1942)早年從事人類學研究,出版大量的人類學著作,為功能學派的開創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他晚年卻轉向語言學研究。馬氏的學科轉向加強了人類學與語言學的結合,強化了語言研究對于了解和揭示人類文化研究的重要意義。
作為一門學科,語言人類學是在美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摩爾根(L.H.Morgan,1818-1881)在對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調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礎上,在1851年發表了《易洛魁聯盟》一書。該書追溯了易洛魁人數百年的歷史,詳細的記錄了他們的生活環境、經濟活動、習俗、宗教和語言。1871年他又發表了《人類家族的血親和姻親制度》,該著作從語言學的角度討論了印第安人的奇特親屬稱謂和族源問題,開始了對人類早期社會組織原則及其普遍發展規律的探索。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人類學家在對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進行深入研究時,發現印第安人的語言不同于印歐語系諸語言。人類學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認為人類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類發展的歷史,他強調人類學的基本任務就是研究語言、習俗、遷徙、身體特征等的全部總和。覺得要獲得有關印第安人的資料就必須學習他們的語言。他對語言學極為重視,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語言問題,他本人就懂得多種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過程種發現,每一種語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語音、形態的意義和結構、詞匯的特點。描寫一種語言只能根據它自己的結構來描寫。他的這一主張被稱為“描寫語言學”或“結構主義”理論,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種方法對于研究無文字民族的語言尤其有效,對研究那些鮮為人知的語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還組織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語言手冊》(AHandbookofAmericanIndianLangguage),搜集了幾十種語言資料,他為該書所寫的序言一直被列為語言學的經典著作。博厄斯還于1920年創辦了美國最早的語言學刊物《國際語言學雜志》,該雜志對語言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1940年博厄斯寫成《種族、語言和文化》、1941年寫成《達利他人的語法》。博厄斯的“描寫”方法為語言人類學的學科方法奠定了基礎。⑤
薩丕爾(EdwardSapir,1884-1939)是美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晚年開始轉向人類學研究。薩氏重視語言與民族文化的密切關系。他說,“語言的內容,不用說,是和文化有密切關系的。不懂得神通論的社會,用不著神通論這個名稱;從來沒有見過或聽說過馬的土人遇見了馬,不得不為這個動物創造或借用一個名詞。語言的詞匯多多少少忠實地反映出它所服務的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語言史和文化史沿著平行的路線前進,是完全正確的。”⑥沃爾夫(BenjaminLeeWhorf,1897-1941)發展了薩丕爾的觀點,認為語言形式決定著語言使用者對宇宙的看法;語言怎樣描寫世界,我們就怎樣觀察世界;世界上的語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對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們的觀點濃縮為薩丕爾-沃爾夫假說(theSapir-WhorfHypothesis)。雖然“薩丕爾-沃爾夫假說”遭到了許多人的質疑,但是,語言與文化、世界觀之間的相互關系卻一直成為人們長期討論的主題。
20世紀中葉以來,語言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日臻完善。這一階段出現了大量的語言人類學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Philipson)、薩斯曼(ZdenekSalzmann)等人為代表,菲力普森從語言人類學視角對英語進行了個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語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語帝國主義,實際上是間接反映了一種盎格魯文化中心觀。⑧薩斯曼同樣從語言人類學的視角對語言、文化和社會的相互關系進行了論述,指出不同的語言結構與其所反映的思維方式具有協同性;同時還對當今的語言人類學“實用性”展開了論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語言人類學學科理論與方法的發展。⑨
二、中國的語言人類學研究
中國傳統語言學比較注重語言事實研究。先秦以文字訓詁為主;隋唐以音韻為主;清代是文字訓詁全面發展的時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洋為中用時期。⑩但我們也看到,語言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由來已久。如前文所述,語言學思想有時是時代思潮的延伸,它離不開自己的時代社會背景。如先秦諸子百家關于名與實的討論雖然屬于語言學問題,但更是哲學問題。中國語言學后來的發展都是與經學分不開的。在西方,由于現實需要以及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19世紀誕生了人類學這門學科,在西方人類學理論與方法引進到中國之后,中國的語言學研究就在搭建語言學與人類學之間的橋梁。
在國內,羅常培先生當屬于從事語言人類學研究的第一人。上個世紀30年代,羅氏研究語言就已經不把研究的視角局限在語言本身的范圍內了。羅氏通過對山東臨川音系的調查研究,并結合方志、史籍、族譜和已有論著,寫出方言與社會歷史移民關系的論述《從客家遷徙的蹤跡論客贛方言的關系》;期間,受先生的《關于功能派文化論》的影響,于是把研究方向從音韻學和方言研究轉向少數民族語言田野調查研究方面,并調查了多種少數民族語言。由于人類學歷來比較重視后進民族的田野調查和研究,所以羅氏所作的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研究已經表明中國傳統語言學正在朝著語言學與人類學的結合方面發展。1943年以后,羅氏的治學道路從語言學轉向了語言與文化關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圍涉及到了從地名研究民族遷徙的蹤跡;從人名研究民族來源和;從造詞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別是從詞的來源和演變研究古代文化的遺跡等等。羅氏對于語言人類學的貢獻,正如他本人所說,“假如我這一次嘗試能夠有些許貢獻,那就可以給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搭起一個橋梁來。”其著作《語言與文化》尤其側重國內少數民族和國外文化比較落后的口語,從語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來透視該民族文化的特點。可謂是中國語言人類學的先聲。[11]
20世紀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熱潮的興起,民族自覺意識得到顯著增強,文化語言人類學在國內重新被認識。從事語言研究的學者運用田野工作方法從事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關系的研究,達到深化認識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時來達到不同語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諧對話。關于此方面的論述,人類學家納日碧力戈已有專門論述。如傅懋勛運用永寧納西族的親屬稱謂來探討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練銘志運用田野調查材料,對現行土家語與古代土家語中的親屬稱謂進行比較后認為,認為古老親屬制有如下一些特點:父系和母系的親屬稱謂區分不明顯,從親屬稱謂大體可以區分出性別和輩分,親屬稱謂是類分式和專門稱謂相結合。湘西土家族古老親屬制的材料,不僅證明了摩爾根關于親屬制理論的主要觀點是正確的,同時也反映了土家族歷史上婚姻制度的演變過程。[13]羅美珍從語言角度闡述了傣、泰民族的發展脈絡及其文化上的淵源關系。[14]周慶生根據傣族親屬稱謂以及人名構建傣族社會歷史和社會結構,力求把語言和文化結合起來進行研究。[15]納日碧力戈運用結構主義理論,分析了藍靛瑤親屬稱謂的一些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語言學與人類學之間的對話。[16]吳東海運用傣族詩歌、諺語等語言材料闡釋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進行民族語言個案研究的同時,國內學者從宏觀角度對語言與文化、語言與人類進行了理論上的闡述,為語言人類學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馬學良和戴慶廈二位先生從語言在民族諸特征中的地位、語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關系、從語言研究民族等幾個方面論述了語言與民族的關系,提出從語言特點可以映射出民族特點。[18]陳保亞提出語言決定思維軌跡的觀點,認為“思維軌跡是思維能力在語言系統中的實現。思維軌跡的差異是語言系統決定的,語言澆筑了思維軌跡。”[19]武鐵平等人對陳保亞的觀點進行了批評,認為人的思維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語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會。[20]張公瑾把混沌理論引入語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開闊了語言和文化研究的視野,同時也為語言人類學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慶生從古今文獻資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調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屬于自己的理論框架,對語言與文化、語言交際與傳播、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等多個方面的關系進行了闡釋。[22]
除了對語言與文化、語言與人類相互關系的研究外,學者們將人類學與語言學有機地結合起來,從理論和實踐等方面對語言人類學學科進行了闡釋。李如龍是國內界定語言人類學的第一人,他認為語言人類學就是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研究語言,用語言材料來研究人類,它是語言學與人類學相互為用的邊緣學科。同時還明確指出了語言人類學的研究論題,即:語言起源;語言與思維;人類群體與語言社區之間的關系;從不同語言的借用看民族間的接觸;從語言材料看人類社會的發展;語言與精神文化之間的關系。[23]鄧曉華綜合運用語言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從語言結構以及與社會文化結構的關系諸方面來研究語言為何在廣闊的社會文化行為環境中運行其職能。同時,還對語言人類學的對象、范疇、理論和方法進行了界定。指出了語言人類學的特點在于強調語言的文化價值以及強調語言與社會、文化的雙向互動研究。語言人類學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在語言與文化的內部聯系上、從民族語言的結構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層文化的特點。[24]
中國的語言人類學的學科建設以及學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廈門大學就設置了語言人類學課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學、云南民族學院等民族院校也開設了該課程。現在一般的民族學科研以及教學機構,都把語言人類學與文化人類學放在同一個平面上對待。2003年,中國在申辦2008年世界民族學人類學大會時,將語言人類學向國外人類學專家和學者進行了重點介紹。[25]
三、語言人類學研究在中國的現實意義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語言人類學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其主要表現在學科建設以及科研成果兩個方面。該學科畢竟是一門交叉邊緣學科,在中國起步比較晚,基礎也表現得比較薄弱,但從學科角度看,這顯然是滯后的。我們認為,有必要加強中國的語言人類學研究,因為它既是學科建設的需要,同時又具有重要社會現實意義。
1.加強語言人類學研究是學科建設的需要。嚴格說來,中國語言人類學的學科淵源有文化人類學、中國傳統文化史、文化語言學以及社會語言學等,雖然這些學科的歷史并不很長,但它們有自己獨到的學科理論與方法,語言人類學要達到與這些學科“平行”,還需要從理論與方法上做一些開創性的工作。中國人類學是從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類學的分支學科文化人類學、語言人類學、體質人類學、考古人類學并駕齊驅,中國人類學特別強調文化人類學,似乎文化人類學可以代表中國人類學的全貌,雖然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類學學科的成熟,但同時也顯示出人類學其他學科發展的滯后狀況。所以加強語言人類學的學科建設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國的語言人類學要不斷吸收和借鑒中外文化人類學以及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文化,這是中國語言人類學發展的比然選擇。
2.加強語言人類學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種的國家,中國至少有80多種語言,而在當今現代化背景下,文化變遷日益迅速,許多民族的母語危機現象越來越突出。中國如此豐富的語言資源如何保護每一種語言所蘊涵的信息特別是傳統文化如何得到傳承這些都是人們非常關心的問題,人們對母語危機現象的“焦慮”以及對中國很多瀕危語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語言人類學學科的發展;中國豐富的語言資源也表明中國語言人類學具有十分廣闊的前景。
語言是民族的標識,語言人類學研究有利于民族內聚力的增強。一般說來,不同的民族都擁有自己的語言,由于民族成員對自己民族語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語言往往成為民族的象征。如,猶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國家在長達2000年的時間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員由于對自己民族的熱愛,在如此漫長的時間里卻不約而同地保留著自己的民族語言——意第緒語(Yiddish)。歷史發展到現在,中國境內一些少數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語言,一些少數民族語言的瀕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數民族有語言無文字,所以開展民族語言的保護和搶救工作對于民族內聚力的增強,對于語言以及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尤其重要。從這方面看,加強語言人類學研究,建設有中國自己特色的語言人類學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①納日碧力戈.關于語言人類學.民族語文[J],2002年第5期.
②(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譯.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③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
④(瑞士)索緒爾著.高明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⑤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
⑥(美)薩丕爾著.陸卓元譯.語言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⑦劉潤清編著.西方語言學流派[M].北京: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2002.
⑧RobertPhilipson.LinguisticImperialis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M].1992.
⑨ZdenekSalzmann.LanguageCulture&Society--AnIntroductiontoLinguisticAnthropology[M].WestviewPress.1993.
⑩王力.王力論學新著[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
[11]羅常培.語言與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傅懋勛永寧納西族的母系家庭和親屬稱謂.民族研究[J],1980年第3期
[13]練銘志.湘西土家族古老親屬制述論。土家族歷史討論會論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務委員會主編,1981.
[14]羅美珍.從語言角度傣、泰民族的發展脈絡及其文化上的淵源關系.民族語文[J],1992年第6期.
[15]周慶生.傣族人命的等級結構與社會功能.民族語文[J],1998年第2期.
[16]納日碧力戈.從結構主義看藍靛瑤親屬稱謂的一些特點.民族語文[J],2000年第5期.
[17]吳東海.傣語中的水文化.湖北民族學院學報[J],2005年第1期.
[18]戴慶廈.語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4.
[19]陳保亞.語言文化論[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3.
[20]武鐵平,潘紹典.語言。思維。客觀世界——評陳保亞《語言影響文化精神的兩種方式》,民族語文[J],2000年第2期.
[21]張公瑾.文化語言學發凡[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
[22]周慶生.語言與人類[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
[23]李如龍.略論語言人類學的一些課題.人類學研究[J],1985.
第4篇: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學內部逐漸出現了一股“歷史化”(historicization)的思潮,即:人類學日漸注重歷史研究的視角,開始關注“他者”的歷史,由此產生了新的理論洞見和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揭示了“他者”是有歷史的,并在歷史建構中具有重要的能動作用,以此為基礎提出了“文化界定歷史”的創新性理論架構,沖擊了傳統的“客觀歷史”說,根本性地突破了人類學中長期存在的“文化”與“歷史”、“結構”與“歷史”、“結構”與“事件”等基本矛盾的對立。另一方面,傳統民族志也得到了更新改造,人類學研究方法從單一的田野調查中解脫出來,走進了歷史的“田野”之中,融文獻史料、田野調查于一體,人類學文化撰寫方式日漸呈現綜合性、多元化的發展態勢;同時,這種方法論意義上的發展與更新還相應帶來了認識論上的深刻變革,凸顯了“他者”與世界共享著同一時間和空間的歷史,對隱藏于人類學知識生產過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思想進行了解構。總之,人類學的“歷史化”,正如弗賓(James D.Fauhion)所言,“已經成為一種多變的社會和文化現象,它并不僅僅代表一種純知識體系上的更新變革,也標志著倫理、道德和政治上的轉型”。除了上述社會環境的影響之外,筆者認為,有利的學術環境是促動西方人類學“歷史化”的不容忽視的深層次因素。本文將對西方人類學“歷史化”的學術環境進行系統梳理,以期能對全面、深入理解西方人類學的“歷史化”有所裨益。
一、西方新史學對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關注
德國蘭克史學作為西方傳統史學(政治史階段)的代表,在進入20世紀尤其是在二戰后,遭到了法國年鑒學派、英國史學和美國社會科學史學的批判。這些后起學派主張跨學科,提倡總體史,注重底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關注經濟社會史,由此引發了戰后以經濟社會史為主要標志的西方新史學(社會史階段)的到來。在稍后的70-80年代,以后現代主義文化批評、歷史敘述主義和文化人類學為理論源泉,新文化史應運而生,即西方史學又出現了由經濟社會史向文化史過渡的新趨勢。在實現這兩次轉型的過程中,西方史學對人類學理論與方法表現出極大關注,或者說人類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第一次轉型過程中(社會史階段),西方史學開始對人類學傳統主題和方法產生興趣。法國年鑒學派主要開創者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創造奇跡的國王》(1923年),從那時的宗教禮儀、風俗習慣、醫療狀況等為傳統史學家所忽視的史料人手,研究了法國民眾的風俗與信仰,揭示了當時的普遍社會心態;另一位開創者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沒有像傳統史學那樣以拉伯雷的書為史料去探討拉伯雷的思想,而是著力考察拉伯雷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化和風俗,剖析該時代的各種社會文化因素和社會心態結構。法國年鑒學派的第二代領軍人物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強調了長時段中的結構,認為傳統史學所關注的事件并不是重要的。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年),利用宗教法庭的審訊記錄,吸收了民族志撰寫中的一些表現手法,生動地描繪了蒙塔尤這個14世紀法國小村莊普通村民的家庭生活狀況。英國史學家愛德華?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年)中,把19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的態度和意識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其文化的構成,認為工人階級身份的真正形成不僅僅是社會經濟意義上的,還包括工人階級對自身地位的文化認同。
在第二次轉型過程中(文化史階段),人類學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新方法被借鑒到史學領域中來,對史學的影響更為直接和強烈。被視為“宏觀意義上”的歷史學家的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將文化比喻為尋找解釋意義的文本(text),倡導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寫作方法。這些見解和方法受到了許多新文化史家的青睞。戴維斯(Natalie Z.Davis)的《馬丁?蓋赫返鄉記》(1984年),以16世紀法國農村中的一個冒充農婦丈夫的陌生人如何被接受和被拒絕為題材,指出通過深入研究該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兩性關系的史料,史學家可以重構該農婦的思想歷程,即歷史學家可以通過一個朝著史料定向但又超越于它以外的想象力來填補史料中的漏缺。在戴維斯看來,事實與虛構之間并元明顯的界線,但首先要承認來源于解釋學的、存在一個諸如農民文化之類的更大的整體性聯系,這樣的重構才能成為可能。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的《屠貓記》(1999年),從解釋18世紀的一群印刷工人集體屠貓這樣一個事件出發,用人類學家研究異文化的方式來處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志觀察入微的方式來洞察歷史,揭示了當時法國人心態中對貓的種種象征意義以及屠貓行為所具有的儀式性和文化解釋,深入探討了18世紀法國人的思考方式。
自結構功能學派產生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人類學在整體上多是拒斥歷史的,這使得人類學“主動疏遠”了歷史學,它們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涇渭分明。而西方史學在二戰后的兩次轉型,對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關注和借重,使兩個學科之間的關系重新密切起來,達到了更高層次上的“合流”(convergence)和“復交”(reapprochement),從而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學的“歷史化”傾向營造了良好的學科外部環境。
二、在西方人類學中的興起和影響
20世紀70年代的人類學是人類學的時代,孕育了法國結構和英、美政治經濟學等新的人類學理論流派。這些新流派試圖對的某些方面加以應用、修正和新的詮釋,從不同角度體現人類學對“歷史”的“關懷”,為70年代以來西方人類學“歷史化”潮流的發生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學科內部氛圍。
西方人類學發端于法國,英、美等國的人類學界也受到影響。二戰后,法國人類學界出現了列維一斯特勞斯(Levi-Strauss)的結構主義人類學,列維-斯特勞斯相信支 配歷史進程的是一種無意識的潛在因素,這種潛在因素只有通過理論上的分析才能揭示出來,而的“唯物史觀”(historical materialism)相信歷史是由寓于生產方式運動之中的內在矛盾決定的,矛盾又是人們經過精心的研究之后才發現的。因此,在列維-斯特勞斯看來,他的“結構”概念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內在一致的。在上述思想的影響下,以葛德利爾(Maurice Godelier)為代表、試圖對馬克思的生產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論進行修正的法國結構學派應運而生。1966年,葛德利爾出版了代表作《經濟上的理性與非理性》。該書強調文化中非經濟性制度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中所發揮的經濟,并以功能性的階序觀來取代生產模式觀。葛德利爾主張把生產模式看成一個系統,而內部各個結構分別為小的系統,小系統在整體中發揮不同功能,若超越了相互之間的約束力即功能相容性的范圍時,則發生社會組成和歷史的變遷。這與把系統內部的矛盾尤其是階級斗爭視為歷史發展的動力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區別。葛德利爾對歷史發生興趣的目的在于修改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使之在的基本構架下適用于前資本主義社會演變的研究,所以他所研究的歷史其實是在“靜態”的結構理論的架構上建立起的社會進化史,盡管其材料來自人類學家的實地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擺脫了早期進化論者的臆測。“歷史在葛德利爾那里,既不是年代學的重擬,也不是人類學合作主體借以建構他們的世界的過程,正確地說,歷史是把社會現象的起源看作從社會制度的邏輯中推演出來的派生物。”因此,雖然葛德利爾聲稱人類學是人類學與歷史學差別消失的地方,但真正的歷史研究卻被他忽略了。盡管法國結構學派受到了種種批評,但它以其特有的方式關注了歷史分析,為發展出一種具有“批判性”的解釋理論做出了貢獻。
二戰后,美國人類學界出現了懷特(Leslie Alvin White)的新進化論和斯圖爾德(Juliar Haynes Steward)的多線進化論。與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早期進化論相比,懷特的進化論體現的是一種更為系統化的技術決定論,強調進化過程的不可分割的整體性;斯圖爾德則更注重進化路線的復合性和多樣性。他們都企圖對的歷史發展階段理論進行修正。哈里斯(Marvin Harris)把斯圖爾德和懷特的理論統合起來,提出了文化生態學和文化唯物論的觀點,尋求環境需求與社會制度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尋求支配歷史發展的新法則。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抨擊哈里斯的基礎上,提出社會文化決定生產過程的新觀點――因為文化既決定人們要生產什么,又決定人們怎樣去生產。此外,薩林斯還對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認識性質的觀點做了新的詮釋。在薩林斯看來,人類創造了自身的歷史,但人類只能根據自身的意識來創造歷史,因為認識總要受制于文化。斯圖爾德的學生沃爾夫(Eric R.Wolf)和敏茲(Sidney W.Mintz)則著重應用世界體系理論以及中資本主義制度下有關農民社會的有關理論,研究了農民社區內外的階級關系,研究了地方性、小規模農民社區與其所處的廣闊政治經濟過程之間的關系,將地方史置于世界史的范疇和視野之中。
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的英國人類學界,功能論、平衡論占據統治地位,因此往往忽略了強調階級沖突和矛盾的,對研究中的殖民情境(colonial situation)幾乎視而不見。英國曼城學派的代表人物格拉克曼(Glackman)強調社會沖突,但從整體上講他從沒有采納過的理論。他的弟子沃斯利(Peter Worsley)在題為《號角即將吹響》(1957年)的一項研究中,強調被研究的那些部族正在受到廣大地域中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剝削和利用,才日漸顯示了觀點的影響。1973年,由阿薩德(Talal Asad)編輯的論文集《人類學與殖民遭遇》已經明顯受到了的影響,開始對以往英國人類學靜態的、和諧的、無歷史的功能論展開嚴厲批判,揭示了人類學與殖民主義之間的深層次關聯:功能論者用“原始人”來代替“被殖民化的人”,缺乏一個對殖民情境的整體性概念,沒有把殖民形式整合到他們的分析中去;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應用人類學更是與“間接統”、“殖民地管理”密切聯系在一起,將作為政治和歷史問題的殖民制度與人類學之間的聯系掩蓋起來,他們既是非歷史的(a-history,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為代表),也是反歷史的(anti-history,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自此,以功能論、平衡論為特色的英國人類學逐漸改觀,開始注意“他者”的歷史,關注隱藏在研究者與“他者”之間的矛盾和斗爭。
三、西方人類學的反思
西方社會科學的整體反思(reflexivity)或解構(deconstmction),建立在西方20世紀60年代以來蓬勃開展的各種社會反省運動的基礎之上。這種反思,來自對“殖民情境”的檢討,源自對西方政治權威、學術霸權的解構。當知識創新的批評精神在現象學哲學、解釋學、后現代主義思潮滲入實地調查的經驗研究以后,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催生了人類學的反思意識。以往的“無歷史”的田園詩般的“現實主義”民族志描述方式成為反思和批判的對象,歷史人文主義成為新的實驗民族志的主要追尋目標之一。
由后現代主義等新思潮武裝起來的新一代人類學家,試圖使人類學帶有敏銳的政治和歷史感,力求使人們對文化多樣性的方式有新的洞察。他們在對傳統的文化撰寫方式進行反思、對寫作的文本本身進行解構的同時,開始嘗試和實驗新的表述方式:一是涉及對描述困境的新感受性,即在文化全球均質化觀念下表述文化差異所存在困難的感受;二是涉及對歷史和政治經濟現實的再認識。在后一種實驗策略中,又有兩個不同的走向:其一,受到政治經濟學、世界體系理論的強烈影響,試圖克服以往人類學將自己局限于地方社會、相對缺少歷史觀點的局面,將大規模政治經濟體系與地方文化狀況聯系起來。這種走向還對民族志美學化、詩學化提出了批評,認為要把民族志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去理解,結合社會、政治和物質去理解。其二,受到解釋學的影響,探討民族志敘述中歷史時間與場合的恰當的表述方式,對傳統民族志或者將敘述置于歷時背景之下或者將歷史一并放棄的種種做法提出批評。這種新的實驗策略就是要使民族志富有歷史感,在民族志敘述框架中展示時間和歷史的視野。
美國人類學家哈里斯認為,后現代主義在人類學中最有代表性的體現之一就是后過程主義(postproeessualism),即:不存在客觀的過去,我們對過去的呈現只是源自個人社會文化視角所制造的文本,是我們自己的一種“創造”。他指出,考古學等研究進化的科學忽視了社會行動的意義建構以及人類文化的歷史特殊性,科學思想根深蒂固的早期人類學家試圖客觀地描 述現在,但實際上與寫小說無異。后現代主義等思潮對科學、技術負面影響的批判,對被科學扭曲的人性的關注和推崇,使20世紀70年代的人類學逐漸從“科學”人類學的影子中走出來,“人文歷史主義”成為新一代人類學家深切關注和反思的時代主題。有學者認為,這會從整體上對人類學造成危機;但也有學者認為,這是人類學激動人心的新時代的開始。
人類學自身的反思,既是時代整體反思的產物,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學在自身反思與實驗過程中所體現的對人文歷史主義的推崇、對民族志描述歷史化的訴求,加速了人類學研究方法的轉換、更新,促進了人類學“歷史化”思潮的醞釀與形成。
四、美國民族歷史學的特殊貢獻
民族歷史學(ethnohistory)的概念,最初可能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的學生威斯勒(Clark Wissler)于1909年率先提出來的。在他看來,民族歷史學就是依靠結合民族史和考古學的數據來重建史前文化,就是紀實檔案(documentary)的同義語。當然,這種檔案并不是由當地土著來提供的。1915年,博厄斯的另一個弟子羅維(R.H.Lowie)對民族史研究中口述史的真實性做出了負面評價,進一步擴大了民族史研究的影響。當時的民族史方法論,無論對人類學家還是對史學家而言,都是一樣的,即主要利用檔案資源來討論“他者”的過去。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民族歷史學基本上以北美、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小規模族群社會為研究對象。這一時期,無論是人類學家還是歷史學家,對此都不太關注,因為小規模族群社會并不是當時史學研究所關注的重點,而人類學的研究目光也主要聚焦于尚與歷史有嚴重隔閡的現在時民族志上。因此,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民族歷史學作品數量不多、影響有限,其主要作用在于最初填補了人類學與歷史學之間的空白領域。
20世紀30-40年代,以博厄斯的學生克魯伯(A.L.Kroeber)、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形成的所謂心理結構學派(文化與人格學派),幾乎背離了博厄斯所開創的歷史主義傳統。隨著心理結構學派的興起,美國民族歷史學在二戰前的作用和影響更為微弱。二戰后尤其是50年代,歷史主義重新在美國民族學、人類學界抬頭,1954年創刊的Ethnohistory則突出體現了這種情緒。這一時期,美國民族歷史學主要有兩大方面的特征:利用文字檔案材料探討印第安各部落的傳統邊疆問題,以幫助他們維護自己的土地所有權;出現了所謂的“經濟人類學”,即從歷史主義的觀點、用現代的經濟概念去研究原始社會。其方法論依然如故,以有文化的非土著所提供的檔案等為主,而不是本土的口述資源。自此,美國民族歷史學作為一種獨特的學術思潮和新的研究范式,才登上了西方學術舞臺,并日漸繁盛。
20世紀上半葉,人類學與歷史學之間的劃分是明確的,但從70年代以來,這兩個學科明顯匯合了。人類學家使用歷史材料和歷史學方法,史學家也使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由此,原初作為在人類學與歷史學問起聯系和溝通作用的民族歷史學,隨著時代的變遷,其內涵的界定也就變得越來越困難。有學者猶豫地仍稱之為民族歷史學;有學者簡單地將之視為歷史學;有學者認為,民族歷史學不再是一門學科,而是一種方法;有學者認為民族歷史學是重建無文字民族的歷史;有學者則將之界定為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研究;還有學者則戲稱民族歷史學為“歷史學與人類學的雜種兒子”。
在凱奇(Shepard Krech Ⅲ)看來,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們已經對民族歷史學本身的界定持有懷疑態度,很難對“ethnohisto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抑或“anthropological history”進行明確區分。有些學者拒絕使用“ethnohistory”這個名稱,而代之以“anthrohistory”或者其他術語。民族歷史學已經逐漸失去了“民族”(ethnos,ethnicity,ethnic)的味道,不再像原來那樣帶有某些歧視色彩地用來專指部落少數民族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而變為歷史人類學(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人類學史學(anthropological history),成為人類學理論方法與史學理論方法互換、混合的產物,成為人類學“歷史化”的產物。“Ethnohistory”這個名稱,也逐漸為“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anthropological history”所取代。無論哪種取代,都合乎邏輯,都不會辱其名,因為人類學學者應該關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正如歷史學者應該關注“historical anthropology”一樣。凱奇認為,使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更為合適,“anthropologieal history”能表征時下“ethnohistory”所代表的真正內涵,能大致消除用語上的混亂局面。
席費林(Edward Schiefflin)和耶韋特(Deborah Gewertz)的討論主要在于揭示民族歷史學的本質特征。在他們看來,“在過去,民族歷史學指的是利用文獻或考古材料建構民族史。對歷史學家(及許多人類學家)來說,傳統上民族歷史學指的是替沒有文字歷史的民族重建歷史,……對我們來說,這種民族史的觀念即使不能說不對,也是不適當的……民族歷史學……最根本的是要考慮到當地人自己對事件是怎么構成的看法,以及他們從文化角度建構過去的方式”。這種見解,與之后以薩林斯為代表的西方人類學“歷史化”思想的主旨是一脈相承的。
第5篇: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
審美人類學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是近年來在國內當代美學、文藝學以及人類學領域中值得關注的動態之一。從現代知識體系不斷互滲和融通的學術背景來看,審美人類學作為一門復合型交叉性學科,是在新的文化語境中有效整合美學與人類學并超越其各自的局限性,激揚學科新質的有力嘗試,同時也是深入探討審美與現實生活以及歷史進步之間關系的必然要求。
在學理上,審美人類學嘗試理清審美現象與其他文化現象之間錯綜復雜的聯系,將對審美和藝術進行考察的重點聚集在特定的審美感知和活動得以形成的社會文化機制上,亦即探討人們在關于“什么是美”以及“如何審美”方面所形成的觀念和實踐是如何被建構和規范起來的,“美”又是如何在這種建構中被遮蔽和顯現的。這就必然要求在尋找美學與人類學之間深層契合點的基礎上,研究當今的文化事實,探討“美”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的不同表現形態、特征、功能以及造成“美”的復雜性和特殊性的深層原因,并將關于異質文化或“他者”的研究與當代文化危機的思考結合起來,從而建構一種更加富于平衡感的審美文化觀念。
從嚴格意義上說,審美人類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國外大約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逐步形成和發展。在西方,關于美學與人類學交叉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人類學美學”、“美學人類學”、“審美人類學”名稱出現的研究群體,一些圍繞以人類學研究方法開拓新的研究藝術的方向以及關注非西方族群的審美偏好等問題的相關著述相繼問世,并引發了一系列關于人類學與美學交叉研究的前沿論題。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國內學者在深入理解國內外美學與人類學著述,了解并反思當代美學與人類學前沿問題的基礎上,努力發掘這兩門學科的深層契合點,并通過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激發其生長性,審美人類學在國內才得以形成。
近年來,國內審美人類學建構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深入開展:一是研究美學與人類學的關系問題,整合二者的思想資源和研究成果;二是在學理上對審美人類學的學術淵源、學科定位、主要任務、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學科意義及其發展向度等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探討;三是發掘和闡釋國內外人類學與美學著述中的審美人類學思想;關注過去被忽略的或未被充分重視的文化現象和審美經驗,激活其理論生長空間,并通過選擇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區域族群文化以及能夠充分體現當代審美文化新質的個案,運用田野調查和理論闡釋的方法探討審美現象的復雜性及其深層的社會根源;四是在一些院系開設“審美人類學研究”課程,初步形成大學本科、碩士、博士三個層次的審美人類學人才培養序列,并將“審美人類學”切實納入學科形態的現代轉型之中。從國內近幾年發表的著述來看,審美人類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其學術理念和田野實踐在國內學術界已獲得了較廣泛的支持和響應,充分顯現了審美人類學可觀的學術發展前景。
第6篇: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 教育人類學 后現代 特征
中圖分類號:G40-0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x.2015.10.030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Post Modernity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WU Chuangang, WANG Lei, QU Jiaojiao
(School of Teachers' Education, Mudanjiang Normal College, Mudanjiang, Heilongjiang 157012)
Abstract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about the knowledge of anthropology, but the knowledge hadn’t become a subject until modern time, and the use of concept is usually confused. In the period of World War Two, many branches came out of anthropology, including the subject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It is useful for us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I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 more deeply. And the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 can be gradually seen clearly.
Key words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
1 人類學的歷史演進
人類學是近代產生的,但人類學的相關知識卻由來已久。古埃及金字塔中有許多不同種族的圖像,希羅多德的《歷史》中,記載了許多不同民族、種族的形體特征、生活環境、風俗習慣等。我國的人類學資料中甲骨文中就有對殷商時期西部居住的氏羌部落的記載。周代能以語言、服飾、禮儀等標志區分華夏與四方的蠻夷。《山海經》記述了先秦以前的古國古族。《史記》中有匈奴、西南夷、東越、南越等列傳。
15世紀西方大規模殖民拓張,東南亞、非洲、澳大利亞、大洋洲島嶼上的土著,南、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進入了歐洲人的視野。引發了對于異于歐洲的民族、種族的人體質與文化的不斷研究。
“人類學”一詞是1501年德國學者洪德最早使用的,指人體解剖和人的生理研究。而后法國、德國、奧地利等國家使用人類學、民族學等概念。但至今在德、奧等歐洲大陸國家,始終用人類學一詞指體質人類學,研究人類的體質形態,民族學則研究人類的社會文化。
19世紀30年代,法國物理學家讓?雅克?昂佩勒制訂科學分類表時,引入民族學Ethnology(意思是族的研究)這一概念把它劃為一個單獨學科。
英國1863年成立倫敦人類學會,人類學包括體質和文化的研究,1871年兩會合并為人類學學院,1908年由人類學家弗雷澤(J?Frazer)提出將研究文化的部分稱為社會人類學。
美國于1842年在紐約成立民族學學會,1879年建立華盛頓人類學協會,1501年把人類學分為體質和文化兩個部分,創立了文化人類學這個名稱,1902年成立美國人類學協會。
20世紀20年代初,民族學引入我國,那時我國既用“民族學”也用“人類學”來稱呼這一學科。解放初,人類學、社會學被視作資產階級學科受到批判,文化人類學作為學科名稱已不見使用。蘇聯一向使用民族學名稱,在學習蘇聯的形勢下,便沿用民族學作為學科名稱,人類學則作為專指體質人類學的課程名稱而存在著。現今我們所使用的人類學概念借鑒指英美,指體質人類學和社會(文化)人類學。
2 教育人類學的產生發展
二戰期間,美國政府為“更詳盡地認識自己和對手”組織人類學家開展了對敵國、同盟國的國民性研究。二戰后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民族意識增強,研究殖民地民族的園地縮小了,人類學家被迫轉向國內社會問題的研究,研究本國的鄉村社會和都市社會。人類學迅速發展出許多分支,諸如都市人類學、鄉村人類學、政治人類學、經濟人類學,工業人類學、醫學人類學、教育人類學等。
20世紀50年代,一些人類學家開始研究學校教育。代表人物是斯坦福大學的斯賓德勒(Spindler),1954年6月,斯賓德勒主持教育與人類學學術會議,主題是研究教育與人類學的交叉及教育中的跨文化問題。美國學者科米塔斯評價這次會議是“第一次公開宣布教育人類學的誕生”,會議出版了《教育與人類學》一書。
作為一門系統的、有理論的學科,教育人類學是在20世紀70年代年以后發展起來的。
我國的教育人類學在20世紀80年代逐步發展起來,代表人物有馮增俊、莊孔韶、滕星等他們在引入、比較西方教育人類學,構建本土化教育人類學,探討教育人類學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
3 教育人類學先天的后現代氣質
教育人類學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不同于傳統的科學研究,與后現代的思想不謀而合。
3.1 反思“科學”
科學是人類現代化的理論和技術基石。而后現代卻是對“現代”的反思,其實就是對現代背后的“科學”的反思。在科學統治世界的時期人類學的研究被科學視為沒有可靠依據的只言片語。馬林諾夫斯基堅持了科學實證主義,為人類學研究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他的實證性研究規范包括:在進入田野研究前要有問題和理論準備,就如科學家帶著理論假設進入實驗室一樣;要遵循標準化的田野研究方法,包括一系列的程序和步驟;要對研究對象有全面的考察,而不是沉浸在個別之中。研究者要有客觀的眼光,并客觀地闡述事實;要對研究對象中的文化等現象做結構、功能的梳理;要選取并典型化研究的人物;要用專業術語對相關概念加以說明。正是這樣一套實證性的規范符合了“科學”世界的基本要求才使得人類學的地位得以確立。然而問題也就出現在這里――人類學的研究天生具有的是對科學基礎的質疑和反思。正如馬林諾夫斯基,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馬林諾夫斯基逐漸清楚意識到田野調查和民族志寫作中的問題。在其死后出版的日記中,他曾寫道:“寫作的經驗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即使觀察者是相同的――更不用說有不同的觀察者了!因此,我們不可能講述客觀存在的事實:理論創造事實。”
科學的客觀性在人類學的研究中不斷暴露出缺陷和不足。而在人類學的研究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卻越來越顯現出與后現代的思想的契合。
3.2 去宏大
教育人類學對于教育的研究要求我們深入到微觀的社會群體中,以微觀而深入的視角審視其內在世界。不再將研究定位在形成宏觀、統一的宏大理論,以此來解釋世界,揭示本質。后現代拋開本質,剔除宏大的研究范式和思維角度正好與人類學研究相一致。教育人類學以人類學的視角和方法透視教育現象和發現問題。但人類學對于教育的研究卻并不是為了探尋其普遍的規律和大統一的解釋,而是關注教育事件存在的本身,理解其本身的感受和體驗,哪怕這感受是微小的和個性的。這種理解和探究往往被“現代”所否定,而后現代的觀念卻對這樣的研究意義和價值給予了理論的說明和肯定。
3.3 求“異”
教育人類學關注“異”群體中的“異”文化及“異”情感。使得被求同思維所邊緣的少數民族文化教育、個體情感重新受到關注。從“異”中理解世界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理解教育中曾被忽視的群體的情感和文化。這也是后現代對于“現代”思維的轉向。從德里達的“延異”到利奧塔的“異識”后現代主義者反對確定性和本質性,高揚“異”的價值。使得“異”不再是“同”的附庸。要求在教育研究中要尊重異于主流的“他者”的“異”文化,不將自己的思想意識強加于本地的教育問題及研究。學會以“他者”的眼光去審視、研究“異”教育,體會“他者”的情感。當研究“異”教育時要更換現代性的參照標準和體系,以后現代的眼光去發現“現代”所未曾發現的事情。
3.4 多主體交互
現代思想引導的教育人類學,在價值認識上強調的是價值無涉,以中立、客觀的視角去看待事物。但現代的思想與教育人類學的矛盾就在于,要深入、真切地理解、體會研究對象的思想和情感就不能置身事外,而要參與其中。而一旦參與其中,便使得研究者本身不再可能如機器般機械地記錄,而必然在體會情感中滲透情感。甚至使得觀察者與被觀察者融為一體。這種融入性觀察研究直接引起了交互的活動。活動中也逐漸模糊了主體與客體的界限,觀察者與被觀察者都成為活動的主體,整個活動就是多主體的互動過程。觀察者帶著慎思明辨的理性走入其中,在融入性深度交互活動中帶著真切的情感走出來。活動中話語與認識上的交流溝通成為研究的重要關節。
以上這些特點使得教育人類學與生俱來地帶有明顯的后現代特征,此外后現代所倡導的復雜性、多元性及建設性后現代所倡導的有機性、整體性等在教育人類學中也都有體現。隨著教育人類學的不斷發展,必將以深度的后現代思想和學術范式規范和指導研究。
參考文獻
[l] 吳曉蓉.中國教育人類學研究述評[J].民族研究,2010(3):90-92.
[2] 王川.教育人類學[J].外國教育研究,1987(5):59-62.
第7篇: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
人類學是近代產生的,但人類學的相關知識卻由來已久。古埃及金字塔中有許多不同種族的圖像,希羅多德的《歷史》中,記載了許多不同民族、種族的形體特征、生活環境、風俗習慣等。我國的人類學資料中甲骨文中就有對殷商時期西部居住的氏羌部落的記載。周代能以語言、服飾、禮儀等標志區分華夏與四方的蠻夷。《山海經》記述了先秦以前的古國古族。《史記》中有匈奴、西南夷、東越、南越等列傳。15世紀西方大規模殖民拓張,東南亞、非洲、澳大利亞、大洋洲島嶼上的土著,南、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進入了歐洲人的視野。引發了對于異于歐洲的民族、種族的人體質與文化的不斷研究。“人類學”一詞是1501年德國學者洪德最早使用的,指人體解剖和人的生理研究。而后法國、德國、奧地利等國家使用人類學、民族學等概念。但至今在德、奧等歐洲大陸國家,始終用人類學一詞指體質人類學,研究人類的體質形態,民族學則研究人類的社會文化。19世紀30年代,法國物理學家讓•雅克•昂佩勒制訂科學分類表時,引入民族學Ethnology(意思是族的研究)這一概念把它劃為一個單獨學科。英國1863年成立倫敦人類學會,人類學包括體質和文化的研究,1871年兩會合并為人類學學院,1908年由人類學家弗雷澤(J•Frazer)提出將研究文化的部分稱為社會人類學。美國于1842年在紐約成立民族學學會,1879年建立華盛頓人類學協會,1501年把人類學分為體質和文化兩個部分,創立了文化人類學這個名稱,1902年成立美國人類學協會。20世紀20年代初,民族學引入我國,那時我國既用“民族學”也用“人類學”來稱呼這一學科。解放初,人類學、社會學被視作資產階級學科受到批判,文化人類學作為學科名稱已不見使用。蘇聯一向使用民族學名稱,在學習蘇聯的形勢下,便沿用民族學作為學科名稱,人類學則作為專指體質人類學的課程名稱而存在著。現今我們所使用的人類學概念借鑒指英美,指體質人類學和社會(文化)人類學。
2教育人類學的產生發展
二戰期間,美國政府為“更詳盡地認識自己和對手”組織人類學家開展了對敵國、同盟國的國民性研究。二戰后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民族意識增強,研究殖民地民族的園地縮小了,人類學家被迫轉向國內社會問題的研究,研究本國的鄉村社會和都市社會。人類學迅速發展出許多分支,諸如都市人類學、鄉村人類學、政治人類學、經濟人類學,工業人類學、醫學人類學、教育人類學等。20世紀50年代,一些人類學家開始研究學校教育。代表人物是斯坦福大學的斯賓德勒(Spindler),1954年6月,斯賓德勒主持教育與人類學學術會議,主題是研究教育與人類學的交叉及教育中的跨文化問題。美國學者科米塔斯評價這次會議是“第一次公開宣布教育人類學的誕生”,會議出版了《教育與人類學》一書。作為一門系統的、有理論的學科,教育人類學是在20世紀70年代年以后發展起來的。我國的教育人類學在20世紀80年代逐步發展起來,代表人物有馮增俊、莊孔韶、滕星等他們在引入、比較西方教育人類學,構建本土化教育人類學,探討教育人類學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
3教育人類學先天的后現代氣質
教育人類學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不同于傳統的科學研究,與后現代的思想不謀而合。
3.1反思“科學”科學是人類現代化的理論和技術基石。而后現代卻是對“現代”的反思,其實就是對現代背后的“科學”的反思。在科學統治世界的時期人類學的研究被科學視為沒有可靠依據的只言片語。馬林諾夫斯基堅持了科學實證主義,為人類學研究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他的實證性研究規范包括:在進入田野研究前要有問題和理論準備,就如科學家帶著理論假設進入實驗室一樣;要遵循標準化的田野研究方法,包括一系列的程序和步驟;要對研究對象有全面的考察,而不是沉浸在個別之中。研究者要有客觀的眼光,并客觀地闡述事實;要對研究對象中的文化等現象做結構、功能的梳理;要選取并典型化研究的人物;要用專業術語對相關概念加以說明。正是這樣一套實證性的規范符合了“科學”世界的基本要求才使得人類學的地位得以確立。然而問題也就出現在這里——人類學的研究天生具有的是對科學基礎的質疑和反思。正如馬林諾夫斯基,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馬林諾夫斯基逐漸清楚意識到田野調查和民族志寫作中的問題。在其死后出版的日記中,他曾寫道:“寫作的經驗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即使觀察者是相同的——更不用說有不同的觀察者了!因此,我們不可能講述客觀存在的事實:理論創造事實。”科學的客觀性在人類學的研究中不斷暴露出缺陷和不足。而在人類學的研究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卻越來越顯現出與后現代的思想的契合。
3.2去宏大教育人類學對于教育的研究要求我們深入到微觀的社會群體中,以微觀而深入的視角審視其內在世界。不再將研究定位在形成宏觀、統一的宏大理論,以此來解釋世界,揭示本質。后現代拋開本質,剔除宏大的研究范式和思維角度正好與人類學研究相一致。教育人類學以人類學的視角和方法透視教育現象和發現問題。但人類學對于教育的研究卻并不是為了探尋其普遍的規律和大統一的解釋,而是關注教育事件存在的本身,理解其本身的感受和體驗,哪怕這感受是微小的和個性的。這種理解和探究往往被“現代”所否定,而后現代的觀念卻對這樣的研究意義和價值給予了理論的說明和肯定。
3.3求“異”教育人類學關注“異”群體中的“異”文化及“異”情感。使得被求同思維所邊緣的少數民族文化教育、個體情感重新受到關注。從“異”中理解世界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理解教育中曾被忽視的群體的情感和文化。這也是后現代對于“現代”思維的轉向。從德里達的“延異”到利奧塔的“異識”后現代主義者反對確定性和本質性,高揚“異”的價值。使得“異”不再是“同”的附庸。要求在教育研究中要尊重異于主流的“他者”的“異”文化,不將自己的思想意識強加于本地的教育問題及研究。學會以“他者”的眼光去審視、研究“異”教育,體會“他者”的情感。當研究“異”教育時要更換現代性的參照標準和體系,以后現代的眼光去發現“現代”所未曾發現的事情。
第8篇: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
誰人不曉特納的《金枝》繪畫?
浸于想象中的燦爛金色,
帶著作者的情思移駐致美的自然神韻,
哦,夢幻般的尼米小林地湖呀,
祖先傳揚的榮耀——“狄安娜之鏡”。
……狄安娜是否還徘徊在那荒涼的林中?
——J.G.弗雷澤[①]
這不是詩人的夜下歌唱,不是頹廢文人的無病,而是人類學家在執著尋索。伴著由祖上而來口耳相聞的“金枝”傳說,伴著年年相隨的“狄安娜祭儀”,先民在自然壓抑之下的恐懼,以及在儀典中娛神虔敬的靜穆所揮發出特有的人文精神楚楚動人、拳拳可掬。
那儀式中人為的真實和由此蒸騰的人文情致是怎樣的共生共攜?人類祖先們是怎樣地在他們的特有行為中巢筑起自己的精神家園?那浮現于外的巫術行為與深納于內的情愫是怎樣地“交感”(sympathetic)作為?這,便是弗雷澤所要尋找的“金枝”;這,便是被T.S.艾略特強調的“一部深刻影響我們這一代的著作”。[②]
這位孜孜不倦的學者,劍橋大學的知名教授,人類學公認的開山祖之一也許到死也沒能明白,為什么自己的著述對后來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影響如此巨大;而在人類學領域卻倍受責難和奚落,后生們送給他許多諸如“書齋里的學者”、“太師椅上的人類學家”等渾名綽號。
弗雷澤等人所開辟的畛域正是文學的人類學。歲月仿佛信滄桑洗禮,滌去了塵埃,留下了真金。這就是為什么及至20世紀90年代,在人類學的“自省”(anthropology in anthropology)中又悄然地將那久久遺下的“弗雷澤情結”搬了出來。弗雷澤式比較文本的方法重新在獲得“尊重”的前提下被加以討論并使得這種討論具有著鮮明的現代性。因為“現代人類學和現代主義文學之間的關系強烈地互動,而這種強大的撞擊力正是來自諸如艾略特的《荒原》和喬伊斯的《尤里西斯》等對弗雷澤《金枝》借用的提示。”[③]
莊嚴的學術殿堂有時不免摻和著一些游戲的色調。不論人們怎樣絞盡腦汁地試圖變換花樣使自己的穿著能夠超越世俗,并為此百般困苦,而一旦省悟,才發現褲子原來總還是“兩筒圓管”!不論對弗雷澤的評說“沉浮”幾何,他還是他!
一“金枝”情結
弗雷澤的粘附力在人類學界其所以遠不及于文學領域,并不是早期的“弗雷澤們”所開創的領域與今日人類學“疆界”有多大出入;也不是弗雷澤研究的對象已今非昔比。他當年所潛心的儀式、巫術研究迄今仍被視作標準的人類學研究內容。弗雷澤的“問題”在于他當年沒能完成“田野作業”。過去五十年人類學在“強調”(emphasis)上的不同演繹出了所謂的“弗雷澤問題”。“毫無疑問,弗雷澤的《金枝》之于人類學是以一個純學術化的追求而著名,然而,諸如美國的弗朗茲·鮑亞士(Franz Boas),英國的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法國的莫斯(Marcel Mauss)等人對田野方法的強調,使之成為人類學作為一種科學和學術上的圭臬。”[④]這樣,“弗雷澤方法”在人類學領域受到長時間的冷凍也就不足為怪了。
如果田野方法果然能夠成為一把利刃將人類學與文學切出個涇渭分明;如果田野的調查技巧果然是一柄“風月寶鑒”,將人類的麗質與污質正反截然區分;如果就作為個體的研究者而言,參與觀察能夠將文化精神的“質”與“量”一成不變地娓娓道來,那么,文學與人類學或許就永遠消失了湊合在一起的機緣。其實,早期的人類學尚在其雛型時期確曾出現過一種將人類學定位自然科學范疇的努力,一些人類學家試圖從體質人類學、考古人類學出發,把人類學取名為“物理學的一支”、“生物學的一種”、是解剖學、數學、化學等等。[⑤]從現在的文化人類學發展來看,這種說法顯然與其學科定位相去甚遠。而人們不再沿襲“舊說”的事實就足以說明一切了。 轉貼于
人是社會的動物,文化的載體。人類學與人類本身一樣從誕生之日起就在尋找著它的“人話/神話”。這種一語雙義形同人類的人性/獸性(Humanity/Animality)構造出一個永恒精神家園的“迷思”(Myth)。[⑥]對于它的“天問”式求索,簡單的“田野作業”永遠無法窮盡。如果說那正是弗雷澤所欲尋覓的“金枝”妙諦的話,人類學只是發展到了今天,才在文學的人類學那里拾得了某種體驗與歡娛。“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兩千年前中國詩人屈子著實地為當代的人類學家們好好地上了一課;千萬莫把人類對精神考古的癡醉建筑于“田野”中用那些圖表、數據般“技術化”的企望之上,尋求本身比“求得”崇高百倍。浮士德博士那震撼人心的呼喊:“哦,你真美呀!”——“找到”恰好成為他的死期!這,方為文化之謎底。
弗雷澤倒是真正循著“金枝”神話遺跡,在它的“積存庫”——儀式里步履蹣跚。對于神話和相關儀式的比較研究,要求研究者像對待現實中的一個可確認單位社區那樣進行數據調查,顯而易見其荒唐!威克利(J.B.Vickery)就尖銳地指出:“現在人類學家們責難(其實并無可指責)《金枝》,說弗雷澤除了給人們一芽‘鍍金的細枝條’(a gilded twig)外,余者就所剩無幾……而弗雷澤偉大工作的貢獻在于他以一種特殊的表現方式將現代神話詩學的想象傳達出來。”[⑦]更重要的是,“《金枝》提供充足的文本資料讓讀者相信原始人的生活深深地為春天以及生命律動儀式所浸潤,這些生命、生長和生產的儀式成為了后來神話學研究的濫觴和中心活動。”[⑧]即使在今天,我們從所謂的生命的“通過儀式”(the passage of life)和再生儀式(rebirth ritual)中清晰地洞見弗雷澤的影子和原型的力量。它與文學家筆下的生命體何其相似。讓我們再品味一下莎士比亞的不朽劇作吧:《配力克里斯》里的隱士薩利蒙使泰莎復活;《冬天的故事》里阿波羅命運的神讖,那料峭的激情和悲劇與一年一度動植物的再生及儀式;《辛白林》中的太陽崇拜和預言;《李爾王》頭戴的野草帽在暴風雨的曠野中再生出“另一個李爾”與耶穌頭頂棘刺之冠死而復活如出一轍。
這種對生命景觀的描繪和對生命循環強烈的潛意識的企盼指示出人類文化的另一種“實在”——精神實在。有葉芝(W.B.Yeats)《基督重臨》的著名詩句為證:
Surely some revelation is at hand,
Surely the Second Coming is at hand,
The Second Coming!
無疑神的啟示就要顯靈,
無疑基督就要重臨,
基督重臨!
有的學者根據自己悉心研究和統計,把神話和史詩中的英雄生命分解為八個部分,形成一個完整的“生命圈”。它們是:生、入世、退縮、探索或考驗、死、地獄生涯、再生、最后達到非自覺的神化或新生。[⑨]但丁的《神曲》正好是一個完型圖解。對于人類在神話儀式里的認知規則,人類學家與詩人其實認識得一樣透徹。誠如杜爾凱姆(E.Durkheim)所言:“世上的一切事物全都在信仰中分成兩類,即現實的和理想的。人們把萬事萬物分成這樣的兩大類或兩個對立的群體。它們一般是用兩個相互有別的術語來標志的,而這兩個術語大多可以轉譯為‘世俗’和‘神圣’……信仰、神話、教義和傳奇,或是表象或是表象的體系,它們表達了神圣事物的本質,表現了它們所具有的美德和力量,表現出它們相互之間的聯系以及同世俗事物的聯系。”[⑩]有意思的是,貼上“功能主義”標簽的人類學家杜爾凱姆早在1885年,當他還是個不名一文的師范學院的學生時,一個叫赫爾的圖書管理員向他推薦了弗雷澤的關于圖騰崇拜和神話儀式等方面的論著,從此他被引進了人類學的神圣殿堂。
如果說,導致后來很長一段時間(大約五十年)人類學界對弗雷澤的不屑一顧,是因為他不曾在“田野”里留下兩個腳印,只依靠文本的比較或聽人口述而生產出的“產品”與從田野歸來的人類學們的民族志有著天壤之別,倒也有情可原。問題是,人們從那些涂上了現代人類學色彩的“作者”們的許多作品中卻同樣看到了“金枝”那種東西。歷史本身宛若一個故事,盡管由于敘事(narrative)的單一要求,拂去了本來可以說明更深刻內涵的豐富軼事,卻并不妨礙讀者將它們作同一類看待的歸納。馬林諾夫斯基“功能主義”的價值首先得益于他本人長期生活在特羅布里安島(Trobriand);同時,他的一系列著作不啻對民族志(ethnography)寫作的一種規范。雖然他的有關神話、巫術、儀式、宗教等方面的研究無不被嵌入在以“具體個人的基本需求上”,對此他還嚴厲地批評了杜爾凱姆以集體表象面目出現的“社會功能”說。[①①]可是馬氏本人的不少著述如《西太平洋上的探險隊》、《野蠻社會的犯罪與風俗》等與“弗雷澤們”的作品卻并無本質差異。這一點亦已得到學界的共識。鮑亞士、薩皮爾(Sapir)、赫默斯(Hymes)等在語言和宗教上的論述與弗雷澤以及劍橋學派,即“神話—儀式學派”(Myth-Ritual School)的風格完全一致。[①②]就是到了利奇、列維—斯特勞斯(Levi-Strauss)那里,人們還能看見由泰勒(E.B.Tylor)、弗雷澤等人壘筑起的傳統。
本世紀初葉,因《金枝》的出現引起了文學與人類學一次極有聲勢的聚合,在比較文化的大前提下,文學家、人類學家對神話儀式中所呈現出的“原型”,諸如“十字架與復活”、“替罪羊”、“弒圣殺老”等研究趨之若鶩。加之艾略特、葉芝、喬伊斯等大文豪筆下的文學人類學特征一時演為時尚,《金枝》成了文學寫法的時髦和規范。[①③]可悲的是,“弗雷澤”的名字在人類學的學科內反愈發顯得蒼白、蒼老和蒼涼。
二 兩個“F/F”:事實/虛構
老柏拉圖的文藝思想中有一個極著名的觀點:“影子的影子”。他認為作品中所描寫的與“真實”隔著三層:第一層是詩人頭腦中的“理念”,第二層是現實中具體的東西,第三層才是文藝作品中所描繪的。這樣,現實是理念的影子,作品中反映的則又是現實的影子。柏拉圖將理念視作一切真實的策源地也就把他推到唯心一疇。不過,老柏拉圖倒是慧眼識得“真實”永遠具有其不同層面和不同意義的性質。而對真實的認知也構成了文學人類學的首要問題,只是其視線與柏拉圖完全相反。
作者理念——自然真實——文本作品(柏拉圖模式)
自然真實——作者理性——文本作品(文學人類學模式)
誠然,兩種模式在認識方向和邏輯上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差別,但從根本上都不妨礙“文本作品”的同一性——即制作和接受上的相同和相似。
不過,在很長的時間里,文學家與人類學家在看待文本上很難統一。前者認定文藝作品的生產過程是從“fact”(事實)到“Fiction”(虛構);也就是說文學的創作支持作者主體意識的放縱。后者則認為其民族志的生產過程是從“Fact”(事實)到“Fact”(事實),反對人類學研究對主體意識的放縱。特別是美國歷史學派的鮑亞士對人類學方法的全面規定(包括要求人類學家學會調查對象的語言,深入土著人的生活,忠實地對社會進行記錄等)[①④],和英國功能學派的馬林諾夫斯基民族志寫作的典范作用,很快在學界形成了一種認識上的錯覺,即民族志所描述的事實=現實中的事實。
不幸,鮑亞士和馬林諾夫斯基都“出了一點事”。前者涉及到現代人類學界的一樁最大的“訴訟”——他的女弟子米德(Mead)與弗里曼(Freeman)對薩摩亞青春期的調查與結果的根本性沖突。[①⑤]馬氏則因自己的那篇長期秘而不宣的日記被披露,讓讀者猛然在他的標準化民族志和日記兩種文本之間找不到原先心目中那種不改的“真實”。于是,人們開始懷疑田野調查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劃清人類學與文學間的界限。與此同時,人類學家的“知識”也受到了拷問。“人類學家的知識總是帶有偏見的,因為人們不可能告訴你每一件事情。某些文化中最優秀的東西對你來說正是最難捕捉的。給你提供信息的人的知識無論如何總是不完全的,在某種意義上總是‘錯的’”,因此,“民族志與文學作品一樣需要詮釋。”[①⑥]而像福斯特(E.M.Forster)的文學作品《印度之行》不是也很“人類學味”嗎?在寫作之前,他親自去了印度;在印度,有他在劍橋讀書時期的同窗好友印度籍學生馬蘇德的陪同和向導;福斯特本人也就民族沖突等問題在當地進行了尋訪;其中的“山洞游覽”極具異族情調;受害者穆斯林醫生阿齊茲的官司又具有強烈的種族背景認同下的沖突等等……只不過《印度之行》沒有打上“人類學作品”名稱而已,否則,它與中國著名人類學家林耀華的《金翼》在質量上有什么差異呢?
無獨有偶,一些人類學家也開始對民族志中的“事實”產生了懷疑。格爾茲(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釋》中認為,人類學家在田野作業過程中的那些先期建立聯系、尋找提供信息者、謄寫文書、梳理譜系、制作地圖、做日記等技術性環節并非最關鍵因素,重要的是與人類學家的知識體系有關。因為它決定著人類學家在田野調查中對“事實”的選擇,理解,分析和解釋。[①⑦]他甚至公然宣稱,人類學家在其完成的民族志當中,使人信服的并不是經過田野調查得來的東西,而是經過作者“寫”出來的。他干脆把作為“作者”的人類學家與文學家放到一起去強調“作者功能”(author function)。[①⑧]比較文學家弗克瑪(Douwe Fokkema)也說出了幾乎與人類學家相同的話:“在科學研究中,研究者——作為決定研究資料和決定被當作研究‘事實’的資料間的結合權威——和研究對象同樣地重要甚至比后者更重要。”[①⑨]在文化的比較研究作為學界強勢的今天,文學的人類學化傾向不僅為文學與人類學提供了“聯姻”的契機,更重要的是,人們已經愈來愈相信,兩個“F/F”之間并不是不可逾越的。
轉貼于
事實/虛構的可交換性或曰“互文”性的邏輯依據可以從以下三個層次的關系和演繹中獲得:
(A) 自然(Nature)文化(Culture)
“自然/文化”在西文中是一對相關的概念。前者指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未經過人文雕飾的存在。后者原指經過人類的“栽培”、“養育”,致使生物脫離野性的狀態。“文明”則強調外在的人文法則,提倡“人文自然”(human nature)——人性。中文雖與西文在指喻上有所不同,精神卻完全一致,指人文繪飾,與“野”(自然狀態)相對。“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論語·雍也》)。文明亦有同義,指與野蠻相對的文化狀態。李漁的《閑情偶寄》作如是說:“若因好句不來,遂以俚詞塞責,則走入荒蕪一路,求辟草昧而致文明,不可得矣。”簡單的考釋,徒欲使自然/文化二元對峙單元中的品質差異凸現。這樣,就又把我們帶回到了利奇的分類,得到了在“自然/文化”的人類學基本命題“野性/人性”。[②⑩]既然文化附麗著豐富的人類精神,也就宣告其人文品質。任何絕對的純粹計量化追求和刻板只能是一廂情愿。
(B) 歷史(History)故事(Story)
這是一對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首先,二者的詞根相同,但敘事角色有所不同。后者雖未顯示人稱代詞,實則昭示著確定的“某述”;前者,不言而喻,“他的故事”(His-story)。表面上,后者更接近于“事實”的本身,前者則浸染著第三者色彩。本質上恰恰相反。故事的講述可以人言言殊,歷史的他述包含了在“它的”(It’s)上有“他的”(His)——即本來那樣的敘述。其次,歷史是掠越時空的故事貯存和記錄。所以,早期的文字敘述很難用今天的學科分類來看待。希羅多德因為留下了一本《歷史》而被冠于“歷史之父”;盲詩人荷馬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被看作神話史詩;赫西俄德的《農作與日子》——一部典型的農作教科書,卻不妨礙他用詩化筆觸來講述“潘多拉之甕”的神話故事。他還是對人類五個階段劃分(the Five Ages of Man)的第一人。[②①]一千多年以后的人類學進化學派也只不過提出了與之相類似的貨色。然而,《農作與日子》卻被視作文學作品。可誰又能想到,考古人類學家施里曼、伊文思偏偏就是根據荷馬史詩所提供的線索挖掘出了震撼世界的特洛伊和麥錫尼遺墟。更令人詫異的是,史詩中許多神、半人半神(英雄)用過的器具描述(比如酒具、胄甲等)竟與考古學家從墓穴中挖出來的一模一樣。[②②]這說明文學的發生原本就是很人類學的。文學中的“虛構”隱匿著歷史上曾經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事實,無怪乎在神話學研究中,“神話即歷史”學派(Euhemerism)極具強勢了。[②③]
(C) 進程(Course)話語(Discourse)
歷史是時空的進程和人文話語的雙重疊加。文化的不可復制性緣自于它的歷時性。所謂“文化的復原”永遠是一個有條件的限制性概念。科學的追求只能在有限的條件下盡其所能。“文獻/地下/田野”所體現的正是這種努力。對于逝去了的事件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歷史的文獻記錄。但是,文獻是文人記述的,其中必然充滿了文人話語。所以,任何“記錄都不能成為單一的歷史部分,即真正發生的遺留物……歷史的記錄本身充斥著人的主觀性——視野、視角和‘事實’的文化漂移。”[②④]有些學者基于對歷史進程中人文話語的認識,提出了所謂“虛構的存在”或曰“非真實的真實”(fictitious entities)。[②⑤]從本質上看,“虛構的存在”就包含著現行時髦“話語”——“說”的歷史化明確意喻。葉舒憲教授在他的《詩經的文化闡釋——中國詩歌的發生研究》一書中從“詩”、“頌”、“言”的考掘入手,極為精致地將個中關系道出:“詩和禮一樣,原本是王者統治權即神權的確證,王者的衰敗自然使詩和禮由官方向民間轉移,這也是由神圣向世俗的轉移。”[②⑥]這樣,《詩經》既交織著一個時期社會多層面的敘事:“風”、“雅”、“頌”,也呈現了歷史進程演變所導致文學話語的轉變。當然,也導致兩個“F/F”的互滲。
三 從田野到文本
按一般的說法和理解,“田野”和“文本”仿佛成了人類學家與文學家各自研究對象和手段的分水嶺。“田野/文本”在品質上似乎也就成了絕然不同的東西。其實,是大誤大謬也!
具有現代意識的人類學家絕對不會因田野而棄文本。因為他們知道,二者并非構成“實踐/理論”——有人引伸為另一種關系:“田野研究/書齋研究”的簡單排中律。文本中可以有“田野”,書齋也可以有“田野”。“為了使我們對一些旅行者的人類學式觀察更加準確,確認這些非人類學家所提供的信息更加精確,書齋里的人類學研究是需要的。”[②⑦]英國的社會人類學在研究宗族與家庭時,傳統的做法是從收集譜系開始,以便保證研究者建立一個縱向的視野。譜系多為文本。倘若人類學家需要進行橫向的比較研究,書齋式的文本研究就更不可缺少。沒有人相信世界上的人類學家擁有“孫行者”的本領,上天入地,跨越時空,事事身體力行。何況,歷史上的許多類型的文本原就有民族志的性質,就是“田野”里生長出來的果實。
具有現代意識的人類學家很清楚地知道,他們并不是田野中的“照像機”,他們必須對田野中的事實進行解釋。“對于田野工作者所提供的事實,社會學家和民族學家會在他們比較的框架結構中綴入自己的解釋。”[②⑧]在格爾茲之后,人類學界出現了一種越來越在比較文化的大趨勢下對文學理論的借鑒,具體表現在對文本性質的關照和在民族志撰寫中對個性化解釋行為的認可。正如泰特羅所云:“人類學也改變了它的視角,從追求純客觀化的對某一事物的描述,到現在意識到這只是一種關于某物的寫作,同時,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它也總是一種自我建構的行為。”[②⑨]田野中的“事實”邏輯與某一個人類學家對待這些“事實”的邏輯原本不是一碼事。他把現實中無數排列零亂的東西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解釋寫進民族志(文本),同一個“事實”已經產生距離。后來的民族學家在參閱某人的民族志過程中又必然產生出“誤讀行為”——參與了自己的解釋行為;隨之又產生出了新的“事實”。文化變遷即是這樣一種過程,文化的研究也是這樣一種過程。這就是文學人類學的精神,推而廣之,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精神。因為,它本身就是顛撲不破的事實!
具有現代意識的文學家絕對應該重視“田野”的現實作用。文學的“人學”性(高爾基語)決定了其研究對象——人的社會化與文化變遷進程。比較文學家弗克瑪指出:“一種文化變化理論需要一門人類學,一個關于人的概念,或者是一種關于人類能夠做什么或能夠學做什么的觀念。”[③⑩]如果文學家筆下的人物完全沒有社會生活中的指標,或者說,沒有“田野”的氣味,那么,白紙上的黑色字符只能停留在“文本”(text)的層面上,沒有或者少有轉化到“作品”(works)的層面。“接受理論”認為,作者用筆墨書寫的或由鉛字排印出的文字組合,在未經讀者閱讀之前只能稱為文本;只有經過讀者閱讀之后它方產生效益,才能最終稱得上是作品。這樣,讀者無形之中成了“文本/作品”轉化機制的“上帝”。而讀者選擇文本的第一依據不是其他,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真實,是濃郁的“田野氣息”。因此,廣義的田野作業對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具有絕對的必要性。對此,人類學與文學在此的追求完全一致。“田野作業遠比因技術性操作所引出的事實要多。”[③①]如果人們只追求由技術性操作的數據事實,他根本犯不著歷盡艱辛地到“田野”中去,他本人就是一個真正的實體。那樣,文學也就淪落為記錄陰私的雕蟲小技。在文化人類學眼中,人的價值有以下基本指標:(a)人的本性;(b)人與自然的關系;(c)時間;(d)人類的追求和目標;(e)人與人的關系。[③②]而要獲取這些,有效的途徑是:田野與文本的融合。
具有現代意識的文學家很清楚地知道,不同的文本的價值是不一樣的。文學人類學對文本的研究首先要確認哪些文本具有“人類學性質”,即“田野潛質”。列維—斯特勞斯在南美的巴西做過田野調查,卻沒有妨礙他對古代希臘、羅馬等許多民族的神話傳說和文本一并收羅起來進行參照,也沒有妨礙在比較文化的背景下做他的結構主義營造。人們不會將其中他做過調查的和沒有做過調查的材料區分開來,進而去褒揚前者,貶抑后者。其實,斯特勞斯常用的神話材料恰恰并非是他“實地”考察得來的。[③③]這一點,原本很“弗雷澤式”。人們之所以對他的神話研究不作苛責,是因為相信他選擇的文本材料擁有豐富的人類學品質。并且更相信他能夠用人類學的方法將文本中的潛質抽取出來。這樣,文本人類學研究的兩個必要條件被揭示出來:1.文本中的人類學品質。2.研究中的人類學方法。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當代中國的文學人類學研究,以蕭兵、葉舒憲、王建輝主持的《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系列為例,若按上面兩個必備條件來看,筆者認為是合格的,甚至是高規格的。自然,這并不能阻止筆者對其中的某些解釋和某些結論持置疑的態度。
誠然,我們的耳邊不斷地回蕩著雷納·韋勒克的話語:“文學的人類學批評是當今文學批評中最富生命力的一翼。”[③④]我們也同樣真誠地期待著文學人類學批評春天的到來,但是,文學和人類學畢竟是兩個各自有著不同的研究對象、范疇、方法的學科;二者無論是“聯袂演出”也好,“學科對接”也罷,都不能漠視兩個學科的本質差別。“聯袂”、“對接”是跨學科的互補,是兩個學科間的相互提示。以“我者”對“他者”的簡單消化或粗暴解構都是有害的。[③⑤]重要的是一種方法,一種視野。正如哈姆雷特無疑是一個相當陳舊的故事,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取材于古老的民間傳說,與浮士德一樣,它同樣為人類學家們所稔熟。“特別是文化人類學家,他探究哈姆雷特傳說的來源,從莎士比亞以前的戲劇追溯到撒克遜文學,從撒克遜文學追溯到有關自然界的神話傳說,卻沒有因此遠離了莎士比亞;相反,他愈來愈接近莎士比亞所創造的那個原型。”[③⑥]同時,人類學家對文本的關注點與文學家亦呈迥異。1966年,一位人類學家在西非的特夫(Tiv)人中進行調查時,就以莎士比亞悲劇《哈姆雷特》中的親族關系(Kinship)為話題,向當地土著首領講述歐洲的親族制度的古老傳統,并通過親族關系來解釋為什么王子會“憂郁”,原因在于父親死后不久母親就嫁給了叔叔。根據傳統,女人只能在丈夫后死后兩年才可再嫁。人類學家的故事立即遭到土著首領的激烈反對:“兩年太長了,在她沒有丈夫期間誰來為她鋤地?”[③⑦]于是,人類學家很容易地通過對哈姆雷特的故事講述得到了對特夫人親族制度的了解。
尋找文本中的“田野”,除了吸吮其中的生活滋養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改善作者的知識結構。學者們經院理論的學習、文字知識的訓練作為進行研究的必需,恰好在另外一個方面——對鄉土知識和民間智慧了解和掌握的疏遠;而無論是人類學抑或是文學研究,尤其在當代,對后者的學習、了解和掌握都必不可少。“講述老百姓的故事”已不再是中央電視臺的一個“欄目”,事實上它已經構成了社會、文化的焦點。對此,民俗學(Folklore)悄悄地“成為聯接人文科學之間的渠道。”社會科學家們無不爭先恐后地加入到對那“共有文化”(co
【作者簡介】on culture)的資源開發中去。[③⑧]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田野/文本”便成了一個有機的維系體,對它的擷英采蜜總是自然的、美好的。
哦,神秘的“金枝”,你在哪里?
——那是老弗雷澤的呼聲。
“生活你真美好!”
——那是浮士德博士的絕命詞。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那是屈子的衷情。
……
或許,人類永遠得不到那枚“金枝”,它總是恍惚于前卻令人遙不可及。然而,人類難道不正是在這種永無止歇的尋索中瞥見生活的美麗,發現人文精神的絢爛么?!
① 弗雷澤(J.G.Frazer)《金枝》,麥克米蘭出版公司,1922年版,第1頁(譯時作詩化處理)。
② 參見《外國現代文藝批評方法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頁。
③ ④ ①⑧ 馬克·曼加納羅(M.Manganaro)主編《現代主義人類學:從田野到文本》,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頁。
⑤ 參見A.C.哈登《人類學史》,第一章“體質人類學的先驅”,廖泗友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⑥ ②⑩ 人類學家利奇(E.Leach)曾就此問題作過專門討論。參見他的《社會人類學》“人性與獸性”部分。1986年英文版,第86—89頁。
⑦ 見威克利《羅伯特墓葬與白神》,林柯恩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12頁。
⑧ ②③ 洛斯文(K.K.Ruthven)《神話》,梅索恩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36、5—10頁。
⑨ 參見利明(David Leeming)《神話學》,紐約1976年版,第96—97頁。
⑩ 杜爾凱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見史宗主編《20世紀西方宗教人類學文選》,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61頁。
①① 馬林諾夫斯基《巫術、科學與宗教》,紐約1948年版,第55—59頁。
①② 參見拙作“對話:在‘詩性王國’與‘世事王國’之間”,《人類學與民俗研究通訊》第28—29期。
①③ 見威克利《“金枝”的文學沖擊力》,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138頁。
①④ 參見鮑亞士《總體人類學》,第15章“研究的方法”,D.C.赫爾斯出版公司1938年版。
①⑤ 二十年代初美國學術界開始對紐約青少年因青春期騷動而引起犯罪的原因展開討論。絕大多數學者認為,青春期騷動和由此引起的危機是生理和心理在一定時期的表現。人類學家鮑亞士則認定其為文化的作用。為了求證,他讓他的學生米德去完成。米德在薩摩亞作了一年多的調查后,完成了她的成名作《薩摩亞人的青春期》,書中用“事實”講述了在另一種文化氛圍里,青春期是平穩的。據此,她和她的老師在這場論辯中成了贏家。后來,另一位名叫弗里曼的人類學家也到了薩摩亞,并長期居住在島上,對米德書中的論據進行核實;最后他得到的結論與米德完全相反,并完成了《米德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一書。
①⑥ ②⑨ 泰特羅《文本人類學》,王宇根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6頁。
①⑦ 參見格爾茲《文化的解釋》,紐約1973年版,第5—6頁。
①⑨ ③⑩ 見弗克瑪等《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俞國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7頁。
②① 博拉(Maurice Bowra)《古代希臘文學》,牛津大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41—42頁。
②② 參見拙文《痛苦的宣泄:從酒神、模仿的關系看希臘悲劇的本體意義》,載《外國文學評論》1988年第2期。
②④ ②⑤ 迪爾內(Emiko Ohnuki-Tierney)主編《跨越時間的文化:人類學方法》,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279頁。
②⑥ 葉舒憲《詩經的文化闡釋——中國詩歌的發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159頁。
②⑦ 參見優里(James Urry)《英國人類學田野方法的發展和人類學評述與質疑》,載《皇家人類學院進程》1972年版,第45—57頁。
②⑧ 庫柏(Adam Kuper)《人類學與人類學家——現代英國學派》,路特里奇和凱根·保羅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193頁。
③① ③⑧ 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社會和文化人類學主潮》,紐約1979年版,第23、64—65頁。
③② 參見羅伊·雷諾等主編《文化人類學的主要流派》,紐約1973年版,第233頁。
③③ 參見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巫術與宗教”部分,謝維揚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
③④ 雷納·韋勒克《二十世紀文學批評主潮》,載《中外文學》1987年第3期。
③⑤ 參見拙作《文學人類學解析》,載《當代文壇》1993年第4期。
第9篇:人類學研究方法范文
民族志概念及方法引入
民族志的英文為Ethnography,其中ethno意指“一個民族”、“一群人”或“一個文化群體”,graphy是“繪圖”、“畫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類畫像”,是同一族群當中人們“方向或生活”的畫像。民族志(Ethnography)是一種寫作文本,它運用田野工作來提供對人類社會的描述研究 。Ethnography原為社會人類學者以參與觀察的方法,對特定文化及社會搜集資料,紀錄,評價,并以社會或人類學的理論,來解釋此類觀察結果的一種研究方法(劉仲冬,2001)。在質化研究中,民族志研究成為社會研究的一種普遍的途徑,它被許多學科及應用領域采用,如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社會學,人類地理學,組織研究,教育研究與文化研究等。民族志研究普遍上又被稱為“人種志研究”或“俗民志研究”。
民族志內容主要為相關人的訪問內容、檔案記錄,從此內容,可找出特定團體與組織之間的關聯,并為關心大眾以及專業的同行撰寫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而民族志學家則記錄人們的日常生活,研究的焦點放在人類思想和行為中較可預測的型態上。民族志的產生通常需要相當長時間的實際體驗,如吉爾茲所說的,在人類學界,即社會人類學界從業的人所作的工作就是民族志。在結束實地參與回到自己的家園之后,人類學者以一定的敘述框架論說這種參與的體驗與發現。其中包括確定報道人,訪談報道人,民族志記錄,描述性問題,結構性總問題,對照性問題,文化主題分析,民族志寫作等內容。
民族志方法科學性闡釋
在科學史的發展過程中,民族志作為一種科學研究路徑也有它自身的發展歷程,依據科學性標準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傳統民族志、現代民族志、反思民族志或實驗民族志。
在傳統民族志發展階段,主要是以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志為主,如中國的《山海經》、二十四史中的“蠻夷”部分、古希臘作家希羅多德的《歷史》。中世紀以后,出現了由探險者、旅游者、殖民地官員和傳教士觀察所寫成的民族志。這一階段出現的人類學家們,如:摩爾根、巴斯蒂安、馬雷特、弗雷澤等,研究者們談論著各種人群的行為和儀式,他們卻從來沒有見過這些人;他們引用別人的資料,可是并不知道這些資料是怎么得來的,受到了人們的廣泛質疑和批判。傳統民族志方法運用階段,也正是世界格局中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殖民擴張剛剛開始等一系列背景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這時的科學性標準是以對異文化的基礎描寫而成的,也是一種宏觀的“風物志”,而所具有的描寫目的多是因為探險、旅游、殖民擴張、傳教等。
人類學的原本主旨是對“他文化”的探索。在20世紀之前,來自西方社會的人類學者廣泛收集非西方文化的資料,試圖理解人類的本性與人性的起源及進化過程。傳統民族志所用的材料是來自殖民官、旅行者和傳教士的記錄,這些記錄帶有很重的殖民主義價值傾向。現代民族志的研究目的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時已經是以科學為原則,強調人類學家的參與觀察,材料的獲取必須是科學的、客觀的。
20世紀初,歐洲社會民族矛盾積累到不可和平解決的程度,爆發了世界大戰。處在這種情景下的人類學者體驗到“本文化”的內在困境,社會學家必須致力于理解宗教行為對于其他領域,諸如:倫理的、經濟的、政治的或藝術等領域活動的影響,并且明白確認出各個領域所秉持的各種異質性的價值之間可能產生的沖突。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思曾說過:社會人類學是從發現中發展出來的。這一發現就是指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這些方面構成了一個有意義的復合體,如果沒有被放在與其他方面的關系中考察,任何一方也無法被理解。
現代民族志寫作將自己的描述和分析規定在單一的社會和時空,它的優點在于使人類學研究注意到文化元素所處的社會場合和時空的重要性,以及人類學者能采用被研究者的觀念分析他文化。在馬林諾夫斯基之前的人類學家,除去摩爾根親自調查過易洛魁族之外,著名的人類學家們從未離開過書齋,他們都以傳教士,殖民地官員和商人提供的資料為依據,或進行比較研究,或構筑宏大的理論體系。20世紀之后,馬林諾夫斯基的老師塞利格曼曾到新幾內亞和錫蘭調查,里弗斯則實地調查托達族的情況并據此寫了詳細報告。馬林諾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遠洋航海者》和布朗的《安達曼島民》都出版于1921年,學說史將這一年看做“功能主義人類學”或者“近代人類學”誕生的年份 。馬林諾夫斯基和布朗的很多重要啟示來自于涂爾干,即強調對社會事實的把握是學術的基礎,注重社會科學的使命首先是呈現社會事實,然后以此為據建立理解社會的角度,建立進入“社會”范疇的思想方式,并在這個過程之中不斷磨礪有效呈現社會事實并加以解釋的方法。馬林諾夫斯基和布朗的工作方法有三個區別于前人的特點:第一,他反對把社會文化現象割裂為支離破碎、各自孤立的考察法,主張應該竭力把握人類文化生活的整體,在完整的文化體系背景中對各個文化事實及其相互關系加以考察和研究,以求最終把握住它們的本質;第二,主張參與式的局內觀察法,即人類學家應該深入到土著居民中去,和他們融為一體,觀察他們生活中包含的真實觀念、情感,從而能夠像土著居民一樣體驗、思考,得出正確的結論;第三,主體自覺介入原則,即“以功能眼光來解釋人類學事實”。現代民族志的這樣一種現實關切也導致了不真實性,那就是利奇(E.Leach)說的:“研究與人類學者本身沒有距離的本土文化,必然導致人類學描述的不真實性,因為研究者必然是帶著一定的價值觀去談論其所熟悉的文化,而且對自己的文化司空見慣而無法進行客觀分析。”
此后現代民族志有了更為精細的劃分:“巨觀民族志”(研究復雜社會、多樣社區、多樣社會機構或含有多樣生活型態“單一社區”);“微觀民族志”:(單單描繪某個異國小部落、中產階級社區中一小群人的單一社會情境,或單一社會制度卻含有多樣社會情境者)。這樣的劃分是考慮到各文化事實相互關聯的動態整體中的相互作用,并通過這種作用來體現相對于文化整體而言的各文化事實的價值、意義以及總體。但是任何文化功能都必須以某種文化事實及其相互間的客觀的乃至于物質的社會關系或稱之為客觀的社會結構為基礎,否則就不可能有現實的文化功能的存在。
20世紀全球化帶來的文化變遷、世界格局變化帶來的歐美文化霸權的東移、社會變遷所引起的族群關系與文化沖突、民族-國家與現代性的不斷強化對社區生活的沖擊等等客觀事實的出現,無不給民族志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思想界出現了一個質疑權威、質疑科學主義、質疑結構的思潮。這個內容龐雜、主張繁多的思潮被統稱為后現代主義。20世紀以來數代人類學者逐步積累下來的跨文化理解論、文化相對論等都需重新評估與思考,包括博厄斯、馬林諾夫斯基和后來的人類學家反思現代民族志把“主觀性”都放在了很次要的位置上,去強調“客觀性”,而事實上做不到,他們要求重新來解放民族志在現場的解釋權利和主觀性,出現了當代的反思人類學。一種建立在后現代哲學、人類學基礎上,強調反思思想的民族志產生了,被稱為“實驗民族志”。其實,反思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民族志“科學性”重新確認和重新討論。“實驗民族志”包括三種大類型:第一,為了克服整體論,實驗民族志主張文化中的個人與人觀;第二,為了避免把文化當成“異族”和殖民對象,實驗民族志主張在描寫中給予全球化重要地位;第三,為了揭開民族志的“客觀科學”的面具,實驗民族志主張人類學者應主動把自己當成“意義的創造者”,利用人類學知識,展開對權力和霸權的批評 。這也就是保爾?利科所說的“通過對他者的理解,繞道來理解自我” 的問題。現代的民族志研究者更多的是從事文化研究的“科學家”,而反思民族志研究者則更多的充當了不同文化之間的“翻譯者”。20世紀之前的“前殖民時期”,以西方世界(含日本)為主的民族志研究活動及內容多少都有先入為主的觀念或偏見。事實上,研究的問題、地區或人群的選擇本身就是含有偏見的。后殖民世界中的民族志工作除了控制偏見,還有經由多方驗證,脈絡化及非主觀的方法等等來降低偏見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結語
現代“民族志”方法是一種較為微觀的社會文化整體描寫方法,它的出現及發展也引出了社會人類學家反思民族志更長遠的目標:解釋及翻譯世界的所有文明,使人們了解不熟悉的信仰與風俗成為可能,從而沖淡民族中心主義的限制,進行所有社會的比較研究。自馬林諾夫斯基以來,西方社會人類學者所采用的用當地人的眼光理解當地社會的民族志方法(也可以稱為“主位法”),還有著其他的隱含意義。用的話說,他們并沒有真的走進非西方社會,而是走進去不久又很快地“出來了”。他們進去的地方是他們的文化不斷沖擊著的對象,因為人類學者的跨文化行動反映西方近代以來的“殖民遭遇”和世界經濟體制與文化接觸的變遷。
民族志文本的科學性問題,伴隨著民族志的產生就存在了,不存在所謂的絕對的“真實性”與“科學性”,一切都是相對的。民族志方法也不會具有超然的“科學性”,而應當是一種具體場景中的具體表現和具體表述研究。從傳統民族志到重視實踐理性的現代民族志到后現論影響下的實驗民族志方法,以及它對人類環境、政治、經濟、文化整體大環境的關照,以及反思民族志的出現,都是“關于在急劇變遷世界中的社會現實的表述”,無不顯示出科學性標準的漸變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時代科學技術發展演變的過程,政治、經濟、文化等的背景給予了這一變化過程更多的參照標準。科學性的過程是一個“猜想與反駁”的過程,并不是生成理論的方法。理論是得到信息和經過訓練的大腦的創造。而科學性過程只是一種減少謬誤的理性方法。正如弗蘭克爾所說,理解和可理解性本質上都是一些心理過程,它們因人而異。我們通過民族志研究路徑尋找或應該尋找的,則是關于社會文化現象的可靠的公共知識。
民族志作為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多民族地區的使用應注意以下幾點:一,多民族地區的復雜性。這里的復雜性不僅是指多民族地區語言,風俗習慣等的復雜性,更多的指多民族地區民族心理的特殊性及復雜性。這些都是由于文化身份的不同而造成的不同,在使用民族志方法中極大的困難會體現在“進入”這一問題上。不能很好的融入當地的人文環境是無法進行調查研究的,甚至可能引發民族矛盾和沖突。二,注重農業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文化身份問題,應作為考察的大背景來把握。民族志方法的使用是帶有一定的理論系統,不管用到什么樣的理論系統,我們應該更多的關注多民族地區是否存在游牧文化或者漁獵文化所造成的文化身份的不同。比如,在對新疆錫伯族進行調研的過程中,在新疆境內的這個民族是由當時的漁獵轉為農耕的民族,這時的文化身份,文化心理是與地地道道的農耕文化里的人們不同的。三,邊疆多民族地區與內地經濟發達地區有著不同的發展思路。各民族共同繁榮是多民族地區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目標。綜上所述,對于在多民族地區使用民族志方法,還有其特殊性的一面,在具體的民族志研究中如能運用好此方法,對于展示中國多民族地區社會各層面的問題有著積極的意義。
參考資料:
[1]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2]科塔克:《文化人類學:文化多樣性的探索》,徐雨村譯,巨流出版公司,2008年版
[3]Spradley, J. P. (1980).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4]《韋伯作品集? 中國的宗教:宗教與世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版
[5]張沁潔:《對功能理論基本概況的闡釋》,省略/xueshu/others/shijiao/200210/20022021//24.htm.
[6]王銘銘:《文化格局與人的表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Scholte, Bob?Toward a Reflexive and Critical Anthropology, in Dell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1969.
[8]王銘銘:《西方人類學思潮十講》,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版
[9]Paul Ricoeur?Existence at Hermeneutique, inLe Conflit des Interpretations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9, P20
[10]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徹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王銘銘等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