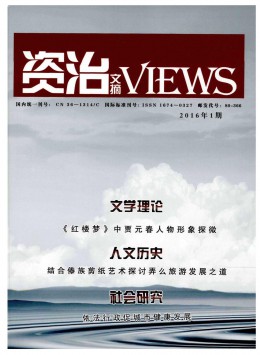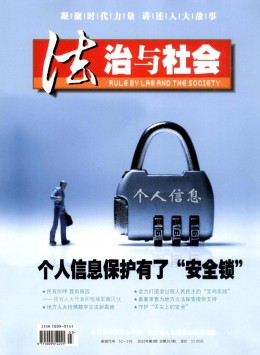資治通鑒白話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資治通鑒白話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資治通鑒白話文范文
一、相信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重視引導學生自主學習理念的培養。過去的課堂教學中,許多教師總是擔心讓學生自主學習無法從課本中攝取有效的知識信息,那種以教師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方式扼殺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對作為課堂教學中主體的學生沒有足夠的信心,于是,教師不厭其煩地講呀講,學生對課堂如何能夠產生興趣呢?當我們根據學生的認知規律進行引導,放手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角,他們對基本的知識信息領悟就會增加信心,其能力也能得到鍛煉提高。
如在學習《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時,筆者指導學生識讀“春秋形勢圖”和“戰國形勢圖”,使學生掌握了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的名稱及具體的地理位置,這就為后面分析爭霸勝負時,學生能獲得“地理位置決定國家經濟發展”這一知識信息奠定了基礎。由于本課爭霸斗爭的史實具有較大的趣味性,為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可展開搜集成語典故資料比賽,拓展學生的視野。這樣,在解決“齊桓公為什么能首先稱霸”這一問題時學生就猶如囊中探物,能很快講述“管鮑之交”、“老馬識途”等成語典故的意義和當時所起到的歷史作用。
二、把課堂中的大量時間交給學生,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人。初中學生具有較強的自我表現欲望,但注意力集中的時間持續得不長。把課堂時間交給學生,可避免學生因為缺少活動而出現昏昏欲睡的現象。在教學中,教師發揮引導作用,通過學生的表演、討論、對話,較好地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能夠較為有效地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
在歷史學習中,編演歷史劇是學生比較喜歡的一種形式。如《絲綢之路》的部分內容適合用這種方式來處理,所以筆者安排一些同學自編、自導、自演了歷史劇《絲路上的貿易》。這樣既可以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又可以鍛煉他們的文字、語言表達、表演等多方面的能力。為了激發大家的學習熱情,使得更多的同學參與到今后類似的活動中來,筆者在學生的表演和發言結束后,對所有參與的同學予以點名表揚,特別是一些幕后英雄,如劇本的編寫者等,同時也對課上踴躍回答問題的同學提出了表揚。為了將本節課的內容做一拓展升華,筆者設計了三個問題供學生討論:①我們應該向古人學習哪些可貴的精神呢?②從樓蘭古國的消亡我們可以得到什么啟示呢?③現在我們應該如何保護和開發絲綢之路呢?這樣學生能感受到古人開辟絲綢之路的艱辛,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也可讓學生思考絲綢之路是否還能重視昔日的輝煌,在現在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機遇面前,應當如何開發絲綢之路。
第2篇:資治通鑒白話文范文
[關鍵詞]漢文小說;創作宗旨;文體
日本漢文小說創作最早出現于奈良(710-794)、平安時代(794-1192),至江戶(1600-1868)、明治(1868-1912)時代達到。毋庸置疑,要寫作漢文小說,必須具有較高的漢語表達能力及中國文學、文化素養。那么在日本,漢文小說這一文學奇葩的創作主體屬于怎樣的社會階層?他們又是抱著怎樣的宗旨來從事這些創作的?他們所采用的小說文體與中國古代小說有著怎樣的關聯?這些都將是本文關注的主要問題。
一、日本漢文小說的作者構成
在江戶時代以前,漢文主要掌握在皇室、公卿貴族、高級僧侶及上層文人手中。能用漢文寫作,不僅是一種有文化教養的象征,更是一種有地位的象征。日本文學史上最早的漢詩集“敕撰三集”的主要編撰者,就都是當時的官居要職者。一些詩集的編排標準,不是看作品藝術水平的高低或所詠事物的類別,而是看詩人爵位的高低。與此相關,詩集所收作品,也大都是天皇或達官貴人之作。平安時期的高級僧侶如空海(774-835),曾經作為遣唐僧在中國留學,精通中國文學文化,回國后,編纂了六朝唐代詩論集《文鏡秘府》等,深得嵯峨天皇的喜愛。下至鐮倉(1185-1333)、室町(1338-1573)時代,在高級禪僧中出現了一批漢學問僧和能夠創作漢詩文的文學僧,后者尤以五山文學的著名人物夢窗疏石(1275-1351)、義堂周信(1325-1388)為代表。這些五山僧侶的佼佼者,也大都活躍于社會的上層,身份顯貴。夢窗疏石被后醍醐天皇之后的七代天皇尊為國師,其弟子義堂周信則經常出入幕府,五山官寺制度正是在他的建議下創設的。由此可見,在江戶時代以前,漢文的掌握以及能否用漢文書寫和表達情感,確實與當時人們的社會地位有著某種強烈的關聯。
日本漢文小說的作者構成,也以江戶時代為界,呈現出兩種不同情形。在江戶時代以前,其作者與詩文作者一樣多為出身顯貴者。江戶中期的著名學者兼詩人木下順庵(1621-1698)在論及平安時代的漢文小說《浦島子傳》時,曾謂其“奇文華靡,無檢束,想夫古之紳家學白香山而失于俗者”。在此,木下順明確將《浦島子傳》的作者與“古之紳家”聯系了起來。不過,雖然《浦島子傳》寫得“奇文華靡”,但由于這類帶有志怪色彩的小說在那個時代屬于“失于俗”者而不被人看重,故作者還是不愿署上自己的真實姓名。同樣成書于平安時代的漢文佛教故事集《靈異記》,其作者景戒雖為僧人,但他的出身卻是紀伊國名草郡的豪族。景戒在《靈異記》序文言及自己寫作的初衷:“昔漢地造《冥報記》,大唐國作《般若驗記》,何唯慎他國傳錄,弗信恐自土奇事?粵起自矚之,不得忍寢,居心思之,不能默然。故聊注側聞,號日日本國現報善惡靈異記。”景戒提到的《冥報記》,為初唐唐臨撰述的宣揚佛教因果報應的故事集,《般若驗記》為盛唐孟獻忠撰述的宣揚佛教靈驗的《金剛般若經集驗記》,二書可能為當時遣唐僧人學成歸來時所帶回。景戒能閱讀到這些作品并能讀懂這些作品,說明他不是地位低下的普通僧人。而在《靈異記》中,有不少內容是關于大僧正行基的談話輯錄,雖然從《靈異記》的成書年代推算,景戒似不會與行基同時,但能接觸到大僧正的談話資料文獻,至少間接說明了景戒的身份絕非一般。
大江匡房(1041-1111)的《江談抄》是一部關乎日本平安時代的朝野典故以及當時流傳的中日詩歌逸聞的談話輯錄,在中國傳統目錄學中,這樣的著作屬于可以羽翼信史的“史之余”。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其《史通?雜述篇》中別史氏為十流,其中就有逸事、瑣言、雜記這些屬于小說范疇的類別。在文化深刻接受中國影響的平安時代,這樣的文學觀念自然也會影響著日本人。所以《江談抄》與《浦島子傳》雖然在今天看來都屬于日本漢文古小說一類,但是在遙遠的古代,它們所遭遇的命運卻是不相同的。也正因此,以記瑣言、逸事為主的《江談抄》,才堂而皇之留下了它的作者的真實姓名。大江匡房,出身文章世家,其曾祖父大江匡衡,是平安中期的著名學者兼文學家,官至一條天皇侍讀、文章博士。大江匡房本人知識淵博,歷仕后冷泉、后三條、白河、堀河、鳥羽五代天皇,是日本院政時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大江匡房在文學上除了擅長寫作漢詩,還擅長寫作極具小說意味的漢文體散文,有《游女記》、《傀儡子記》、《狐媚記》等作品傳世。
江戶時代,隨著漢文教育的普及,對于漢語言文化的掌握,不再是一種特權,而是普通民眾亦有可能掌握的一種知識與技能。這種變化直接帶來的是漢文學創作主體的改變――雖然仍有達官貴人寫作漢詩文,但更多的作者可能僅是一介文人學者而已,漢文學創作隊伍的構成呈現出多元與平民化的趨勢。這種情況又以漢文小說作者表現得尤為明顯。
大體而言,江戶時代及之后的漢文小說作者主要由普通文人知識分子構成。其中,社會地位相對較高者多以儒學學者及藩侯儒官的身份出現,是漢文小說作者的主體,如服部元喬(1683-1759)、岡田白駒(1692-1767)、菊池純(1819-1891)、石川英(1833-1918)等。服部元喬師從古文辭學派先驅荻生徂徠(1666-1728),為當世鴻儒與詩文泰斗。其早年出仕江戶柳澤侯吉保儒官,后致仕,在江戶收徒講學,晚年為肥后侯賓師。服部一生著作極豐,除《大東世語》外,尚有《南郭先生文集》等十余部著作傳世。岡田白駒與服部同時,早年行醫,后棄醫習儒,晚年應肥前蓮池侯之召,擔任藩儒,執掌文教。岡田的著述計有《(詩經)毛傳補義》、《(世說新語)崩》等多部著作。盡管岡田的儒學造詣在后人眼中不算深湛,但在時賢們看來,他仍可稱得上是自成一家之人物,當時有評論云:“平安文學,由來尚矣。然以今觀之,東都之盛不及遠甚,乃名下果非虛士而足稱者,唯見岡千里(按:千里為岡田之字)一人,其他言過其實。”可見其影響甚大。菊池純師承名儒林檉宇,曾任江戶赤阪邸學明教館授讀、幕府將軍昭德公侍講及儒官等職。菊池純夙有修史之志,著有《國史略》、《近事紀略》等。石川英曾任儒學教官,與當時中國駐日使團往來密切,常與何如璋、黃遵憲、黎庶昌、楊守敬等人詩酒酬唱、談文論道。
這一時期漢文小說作者中社會地位較低的文人,他們或為翻譯兼漢語教師,或為報刊雜志的普通撰稿人,職業不定,岡島冠山(1674-1728)、三木愛花(1861-1933)是這一類作者的代表。岡島冠山早年曾擔任長崎通事(即翻譯),后至江戶、大阪等地從事唐話(指漢語白話)教學工作。著名學者荻生徂徠成立研究并教授唐話的組織“譯社”,岡島冠山被聘為講師。岡島冠山著有影響較大的白話漢語教材《唐話纂要》,此外還著有多種漢語辭書。其在漢文小說方面的最大貢獻是將日本戰記物語《太平記》翻譯為章回演義小說《太平記演義》,開創了日本演義體小說的先河。著有《東都仙洞綺話》等多部愛情小說的作者三木愛花,從二十一、二歲起,即擔任《東京新志》、《吾妻新志》等雜志的編輯,并因所編《吾妻新志》多以風花雪月為主題,而自號“愛花”。《東京新志》、《吾妻新志》停刊后,三木又先后在《朝野新聞》、《東京公論》等報刊雜志任職。
有一些文人雖然也曾擔任過高級儒官職務,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但在幕末、明治維新的特殊年代,他們的生活已經陷入了潦倒境地。《柳橋新志》的作者成島柳北(1837-1884),其祖、父輩皆為幕府儒官,其本人也在23歲繼承父職,擔任幕府將軍侍讀,但在幕府滅亡后,他的生活競幾近“赤貧”,關于這一點,他在《(柳橋新志初編)序》中有所流露,其云:“余也狂愚一書生,凹硯禿筆,僅糊其口者,無居士之才,無居士之學,加之赤貧如流,未曾一日游其境而驗其實,焉足記之?然喜聞蕩子之說話,睹市街之圖冊,得窺其概略,遂偷一夕之閑而記。”這里的“赤貧如流”或許有夸大之嫌,但生活陷入困窘卻是可以肯定的。
江戶、明治時期日本漢文小說作者隊伍的變化,直接影響到了作品的創作,尤其是影響到了作者對題材和描寫對象的選擇。由于這一時期的小說作者基本上為普通文人知識分子,他們雖為儒者,但出身低微,官階不高,甚而只是一介私塾教師,故與社會底層的生活有著某種天然的聯系。換言之,社會底層的生活因為有了這一聯系而受到了作者更多的關注。有研究者曾對《譚海》的題材類型做過研究,以為可以區分為三類:畸人寒士之事行、才女名妓之事行、儒者文士及藩府官吏之事行等,并以前兩類為主。這種題材下移的特點,該研究者總結為“新時代精神和價值觀念”所致,但筆者以為,其最根本的當是作者身份的下移,這是觀察視角得以確立的基礎。《啜茗談柄》的作者藍澤祗(1792-1860),開設私塾三余堂講授漢學,小說是他在授課之余,與學生講談“詭怪可喜之事”,并在此基礎上整理創作而成的作品。作者在《自序》中談及了自己的創作過程:“自余開館于此,于今十年。七郡之髦士,挾策操觚,相從游者幾滿門。論道講書之余,恐其或于圍棋諸戲,于是乎每五日洗沐,使各話詭怪可喜之事,以攪其情。或辭以寡聞,余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皆曰:‘喏。’乃各舉其于鄉里嘗所聞見而話之,頗可喜者,吾從旁筆記之,題曰:《啜茗談柄》。”可見,藍澤祗如果沒有私塾教師的經歷,是斷然寫不出這部充滿日本民間傳說意味的漢文作品的。
二、日本漢文小說的創作宗旨
從時間上看,日本漢文小說創作涉及的時間跨度極大,前后約有千年之久;從小說題材上看,日本漢文小說創作涉及世情、神怪、歷史、英雄傳奇、笑話等各種題材,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小說創作主體看,日本漢文小說作者如上所言,他們有著不同的出身和社會地位,與此相應,他們也有著不同的審美趣味和創作期待。面對這樣一個相對復雜的研究對象,要籠統地談他們的創作宗旨,顯然有掛一漏萬之嫌。但筆者也認為,作為異邦的小說作者,當他們運用不屬于自己本國的文字進行創作時,由于受到與該文字體系相聯系的他國文化的影響,一定會在某些方面表現出他們的共同性。本節所致力探討的正是這種具有共同性的問題。
第一,“備修史之料、補史傳之闕”,是不少漢文小說作者所標舉的創作宗旨。關于這一點,在許多作品的序或凡例中皆有反映,如佐藤一齋(1772-1859)在《(先哲叢談)序》中云:(原念齋)“嘗纂集天文已降,文臣武將,暨名一技藝者,行狀碑志,家乘譜牒凡一百卷,名曰《史氏備考》,以俟他日修史者采掇焉。別撮其要,成若干卷,名之日《先哲叢談》。……蓋當時儒流固未止此,然于國家崇文之化,彌隆彌溥,猶將有所就考焉。”(參佐藤一齋認為,原念齋的《史氏備考》和《先哲叢談》,其最大貢獻就是他為后來的修史者留下了大量可供“采掇”和“就考”的資料。
這種把寫小說當成“備修史之料、補史傳之闕”的觀念,源于中國古代的影響。早在唐代,對于小說材料能否入史,曾產生過不小的爭論。贊成者以史家李延壽為代表,反對者以史學家劉知幾為代表,他直斥援小說入史為“厚顏”。宋代司馬光《資治通鑒進書表》追隨李延壽,不避諱自己修史旁采小說的做法:“遍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撾幽隱,校計毫厘。”而為司馬光所“旁采”的小說中就有不失“諧謔荒怪”的《朝野僉載》。在古代中國,經史子集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目錄先后的排序,更是意味著主流社會對于它們的價值高低的認定。小說進入史的范疇,雖然有可能模糊了它作為一個獨立文學門類的特性,但是卻有助于提高它的社會地位。所以中國古代文人評小說寫小說,多把小說是否接近于史、有補于史看成是其成功與否的標志。唐李肇《唐國史補序》評價沈既濟的《枕中記》、韓愈的《毛穎傳》,認為“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才也。”在此,李肇把司馬遷當做了小說家的最高典范,把“良史才”看成是對小說家才能的最高贊譽。正因為中國古代文人對于小說與史的關系持有這樣一種態度,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深受中國古代文化影響的日本漢文小說家在這個問題上的取擇和傾向。
第二,為治世者提供“守文施治之術”,為大眾提供“修身處世之方”,也是日本漢文小說作者給自己確立的創作宗旨。蒲生重章(1833-1903)是明治時代前期重要的漢文小說作者,其編撰的軼事小說《近世偉人傳》十卷刊行后獲得極高評價。蒲生重章在為松村操(1843?-1884)的《續近世先哲叢談》作序時,談及了他們編撰這類書籍的初衷:“今節卿(按:松村操字)之專取于道德文章,其意最善,可以諷世矣。夫儒學之士見用,則邪說暴行不興,泰平之化可致。……嗚乎!憂世道者,執節卿是編,及賤著《偉人傳》讀之,則于守文施治之術、修身處世之方,豈鮮乎哉!”蒲生重章們所處的明治時代,學風大變,儒學已經不是唯一的學問主流,甚至不再是學問主流,即所謂“霸府末年,歐學大開,文物一轉,以入明治”。洋學的入主和打擊,使曾有的國民儒學精神變得式微和黯淡。為“偉人”立傳,為“先哲”留名,其目的就是希望以此喚醒國民,為世人提供“治世”和“修身”的榜樣。
日本漢文小說作者的這一創作宗旨,深受儒家文以載道、重視教化的文藝思想的影響。日本江戶時代,在德川幕府的倡導推行下,以朱子學為代表的新儒學逐漸取代了中世以來占主導地位的佛教,而成為近世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并成為國民生活的指導原則和規范。同時,新儒學也對當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影響直接表現為對于文學道德要素的強調。具體言之,即為對于載道和勸懲的要求,這是一股彌漫于整個江戶時代的文學思潮。時至明治,盡管儒學已經風光不再,但是新儒學的文學觀念卻仍為這一時期的漢文小說作者所秉持,個中的原因甚為復雜。
首先,這與漢文小說作者大多為儒學學者出身有關。作為儒學學者,他們的價值觀和美學觀基本來自儒家,即使處在歐化主義盛行的社會大變革時代,他們也很難從根本上去除儒家的影響。以主要文學創作時期在明治時代的依田百川(1833-1909)為例,雖然有研究者注意到他也曾贊揚過一些在西洋小說影響下從事創作的當代作者,但筆者認為這并不能完全改變他對于明治時代在歐化主義影響下的文壇風氣和創作現狀的排斥和厭惡。在附載于《談叢》后的《依田百川自傳》中,他抨擊道:“時文學盛行,少年才子,著稗史小說,根據洋說,多鄙俚語。百川一以勸懲為主,人毀其陳腐,乃毅然日:‘洋人富于才,而慳于德,使今少年稍加齒,寧不后悔乎?’”依田百川卒于1909年,而《談叢》正式刊行于1900年,也就是說,依田百川即使已步入晚年,他也仍然堅持著文學主勸懲的觀點,而他認為這恰恰是西洋小說所欠缺的,也是“時文學”所欠缺的。
其次,歐化熱在明治十七、十八年達到頂點之后,隨之慢慢有所冷卻,代之而起的是所謂國粹主義。這里的國粹,不是限于國學者眼中狹隘的國粹(按:即日本的國文、國史、神道),而是指“與新輸入的西方文化相對而言的整個日本固有文化”,包括佛教、儒學等。國粹主義抬頭的標志性事件,是明治二十三年(1890)頒布的《教育敕語》,它是以天皇教誨的方式,對國民進行以儒家忠孝倫理為主體的道德訓誡。國粹主義抬頭的原因復雜,非本文所能涵括和探討,筆者所要指出的是,或許正是在這股強大的復古思潮的背景之下,才會有這一時期漢文小說家期冀通過作品為治世者提供“守文施治之術”、為大眾提供“修身處世之方”的熱切和堅持。
第三,出于與眾同樂、彰顯風雅的目的。角田九華在《近世叢語(自序)》中云:
余嘗罹病屏處書室。俯仰寂寞,門無來人。于是湯藥之暇,自近時文集,旁及稗乘,一一頌讀,尚論其人。諸名家而至于旁枝委流,標望雅尚,風韻氣象,各有精神面目矣。……旦暮遭遇,妙諦奇晤,使人不覺擰躍。竊謂余獨樂之,不若與眾。且也今不排纂而標著之,則天下后世,孰得窺名賢堂壺者乎。
相比較于前一點,角田九華的編撰目的或許不算崇高,他只是期望在“樂”中引人向善――這種善非儒家的道德,而僅是風雅一類的“雅尚”和“風韻”而已。
第四,漢文小說家編撰小說還有一個更為實用的目的,那就是將之作為漢語學習的教科書。關于這一點,在清田絢為岡田白駒的《譯準開口新語》(1751)所作的序言、佐伯仲為菊池純的《譯準綺語》所作的跋文中皆有所揭示。前者以為岡田之作是為了給“從學之士”示以作文準則;后者則強調菊池之作是“舉苦心所存,以示作文之法”。
三、日本漢文小說的文體運用
從文體上看,日本漢文小說基本承襲了中國古代小說的所有樣式。從其作品產生的實際情況看,最早為日本作者所采用的文體是雜傳體式,其代表作品即《浦島子傳》。中國古代小說的雜傳體式由史著的紀傳體發展而來,它在記敘一人之事跡時,務求詳備,首尾貫通。由于有相對完整的故事情節,所以其篇幅較長,有初步的人物形象描寫。《浦島子傳》敘事的開端云:“當雄略天皇二十二年,丹后國水江浦島子,獨乘船釣靈龜。”此后進入敘事的主體,寫靈龜變為仙女,浦島子隨仙女來到蓬萊仙宮,成為夫婦,過起了“朝服金丹石髓、暮飲玉酒瓊漿”的神仙生活。但是不久浦島子“魂浮故鄉”,向仙女提出了“暫歸故里”的請求。臨別時,仙女送與島子玉匣,并告誡“若欲見再逢之期,莫開玉匣之緘”。結局部分寫回到故鄉的浦島子,所遇“不值七世之孫”,“至不堪”,遂忘仙女所誡,“披玉匣見底”,但見“紫煙升天無其賜”,遂不能再往仙宮云云。如果把《浦島子傳》的敘事模式與漢魏六朝的雜傳體小說比較,不難發現它們的相似之處。而經改寫后的《續浦島子傳記》,雖然主要情節沒有改變,但語言華麗典雅,且多用駢儷和詩句,其文體形式已經脫離雜傳而接近傳奇。
雜記體是日本漢文小說運用最多的文類樣式。中國古代的雜記體小說,所敘之事多為“里巷閑談辭章細故”(《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之類,題材的細小瑣屑決定了其體制的短書性質,故大多數雜記體小說的篇幅都比較短小,不追求敘事的完整和長度,但因作者能力所致,也有可能通過這些片段或素描,從一個側面表現了人物的性格或神情風貌。日本漢文小說中,從最早平安時代的《江談抄》,到江戶、明治時代的《大東世語》、《啜茗談柄》、《當世新語》、《談叢》等,都是較好運用雜記體進行創作的作品。如《大東世語》關于嵯峨天皇(786-842)的一則記載:
弘仁帝時,《白氏文集》一部,獨藏秘府,世未有睹者。帝幸河陽館,賦詩云:“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本白氏一聯也,試視野篁。篁曰:“圣制改‘遙’作‘空’更妙。”帝驚曰:“此樂天句也,本已作‘空’,聊試卿而,乃卿詩情,已至與白氏同邪!”(《大東世語?文學1》)
白居易的詩歌曾對日本平安朝的文學產生過重大影響,上引的這則小故事,說的正是嵯峨天皇與他的文學近臣小野篁學白居易詩的一段軼事。這則小故事,僅僅是對事情本身進行客觀的記錄,并沒有對人物作更多的渲染――雖然我們盡可懷疑它的真實性,但從文本的角度,我們仍可以透過它的簡練敘寫,感受到了平安時代天皇和貴族們對于白居易詩歌的熱愛以及他們極高的漢詩造詣。
當然,在中國古代的雜記體小說中也有一些篇幅相對較長的作品,它通常是通過人物將若干相互間沒有關聯的事件勾連起來,帶有以短章連綴成篇的特點,這類小說的缺憾是情節缺少細膩的描寫和鋪墊。日本漢文小說《啜茗談柄》的部分篇章繼承了雜記體小說的這一敘事技巧,但它卻在一定程度克服了這類小說的弊病。以其中的《獵夫多四郎話》為例,該篇小說由三段情節組成:殺蛇、遇山僧、遇大蜘蛛,三段情節問沒有因果聯系,敘述者在引入新情節時,用的是程式化語言“又嘗……”作為勾連。全篇小說以概述為主,講述的是主人公山獵活動的片斷,情節剛開始,很快就奔向結局,缺乏對人物活動的詳細描寫。但是,如果和我國六朝雜記小說相比,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它的發展之處。以殺蛇一節為例,情節的敘述重心無疑是在多四郎如何殺蛇的方面,所以從多四郎看見大蟒蛇,到如何將蟒蛇殺死,只要把這個過程敘述清楚,小說就可視為完成。然而我們細看文本,卻發現它有許多溢出的筆墨,如對被蟒蛇所逐之鹿逃跑時的描寫,對蟒蛇猙獰的描寫,以及蛇被殺時聲震山谷的描寫。這些描寫采用的是夸張的文學手法,它雖然也與主要人物和事件相關,但卻不是情節本身所必需的,它的存在僅是起到渲染多四郎殺蛇時的緊張氣氛,以及加深讀者對描寫對象的直觀感受的作用。這種不甚合乎雜記文體的筆法,給文本帶來了類似于唐傳奇“施之藻繪,擴其波瀾”的效果。
傳奇體也是為日本漢文小說家們所嫻熟運用的一種體式。從文體上看,傳奇體小說采取紀傳體的基本構架,而敘事寫人更加細膩,情節更加曲折,更富于想象和虛構。日本漢文小說中的傳奇體小說最具代表性的是《譚海》、《奇聞觀止本朝虞初新志》等。《譚海》記述的是“近古文豪武杰、佳人吉士之傳,與夫俳優名妓、俠客武夫之事行”。這種寫人物事行、給人物立傳的敘事目的,正與傳奇體的敘事架構相吻合,而作者對于人物的細致描寫、對于情節的匠心安排、對于語言的富有文采的使用,以及大多于結尾處綴有“野史氏日”、“百川曰”的議論等,都使這部作品具備了傳奇體的神韻。如《譚海》的《巨杯》,寫的是一次平凡的宴飲活動,但作者卻把它寫得波瀾四起,很好地表現了人物的性格。德川氏勛臣井伊直孝能飲,“一斗不亂”。內藤忠興宴請井伊,“以一巨觴容一斗者進之”,不料井伊卻要主人先飲,這便難倒了“無涓滴之量”的內藤,此乃第一折;井伊網開一面,以為“主人不能,請陪客代之;陪客不能,請仆從代之”,但內藤遍問陪客和仆從,居然皆“無應命者”,此乃第二折。至此,故事似已陷入僵局,不料井伊又提出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建議:“即廁養卒亦可矣。”廁養卒者,為地位低下之從人。當老臣們“盡召邸中士議之”時,便有一人出列,這便是次要人物馬場三郎。僅從小說的開篇,讀者已經可以感受到作者在敘事構思上的縝密以及高超的文學表現手法。作者一筆而寫多面,就井伊直孝而言,這里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無應命者”的描寫,不僅凸現了這個人物飲而無敵的特點,更凸現了這個人物以飲會友、不以身份壓人的率真豪爽;就馬場三郎而言,不難看出這是作者運用烘托手法來為這個人物的出場造勢,從而使人物未出場就已在讀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在人物肖像描寫上,《譚海》同樣精彩。如《巨杯》透過井伊之眼寫馬場:“直孝諦視之,面黑身長,寡發多髯,額有三創,狀貌奇偉。”寥寥幾筆,人物如繪。菊池純在此文下評點說:“‘寡發多髯’,飲伯面目,繪畫逼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