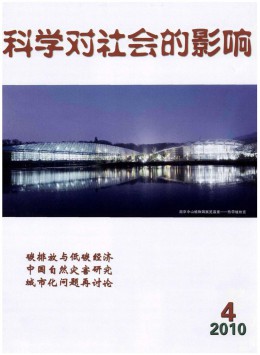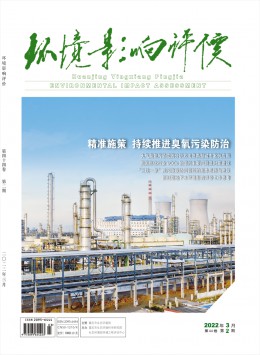影響生育率的原因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影響生育率的原因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生育文化;生育率;新型
生育率的變動不僅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生育文化的直接影響。相較于經濟發展水平這一影響生育率高低的最終因素,生育文化對生育行為有更直接的影響,生育率的變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育文化的作用。
一、生育文化的內涵
學術界對生育文化的定義和內涵闡述較多,共同贊同的定義是生育文化是人類生育活動中表現出來的一些文化特征,是指人類在一定的生產條件下所形成的對待生育活動的一套觀念、信仰、風俗習慣、價值標準以及行為規范等。
這個定義包含了三層很重要的思想,首先,把文化界定為一種觀念形態,把文化看做人類精神活動的產物,生育文化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屬于上層建筑。其次,生育文化是在生育活動中所形成的意識形態和相應的規范制度,這就將生育文化和其他文化區別開來。最后,指出觀念、信仰、風俗習慣、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等都屬于生育文化的范疇,確定了生育文化的范圍。
二、生育文化對生育率的影響
在影響生育率的諸多因素中,生育文化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考察生育文化對生育率的作用可以采取多種指標,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數據的可靠性,我們采用貧困帶各縣生育率和超生罰款情況的指標,并與張家口的10個貧困縣縣域數據進行比較,從而凸顯不同縣域不同的生育文化對本地區生育率的影響。根據六普數據可知,河北省縣域生育水平為38.81‰,張家口這10個貧困縣的婦女生育率為28.122‰,明顯低于河北省縣域的平均水平。張家口貧困縣的生育率普遍較低,其中蔚縣相交于其他縣來說生育水平最高為37.376‰。張家口10貧困縣均屬于農村二胎政策覆蓋范圍,生育率的差異主要體現在這些地區政策內和政策外生育的差異,生育文化的不同也是影響這個地區生育率差異的重要原因。
根據張家口市各縣調查數據統計我們發現,此地區農村出現超生情況的家庭很少,不僅如此,許多符合國家生育政策,滿足生育間隔條件可以生育二胎的家庭也不再生育,甚至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也放棄生育二胎。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來自經濟的壓力,壩上貧困縣的家庭收入水平低,養育子女的花費大;另一方面是壩上縣的生育文化,在壩上一些地方人們普遍認為生孩子會影響到他們原本較清閑的生活,人們早已形成了這種生男生女都一樣的生育文化。
生育率高的縣,計劃外生育情況也多。我們對貧困縣超生情況進行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超生罰款比例較高的縣和生育率較高的縣具有一致性,生育率高的縣罰款比例也高。張家口10個貧困縣中,蔚縣的生育率最高為37.376‰,罰款比例也是最高的為17.33%。根據調研,蔚縣地區生育二孩的現象比較普遍,大多數家庭的生育意愿為兒女雙全。這種生育文化的影響深刻,甚至是不在生育二胎政策范圍內的公職人員,同樣受本地區兒女雙全等傳統生育觀念的影響,生育二胎。還有部分人們對兒女雙全的生育文化產生從眾心理和示范效應,也是本地區生育率和超生罰款率高的原因。在生育問題上,人們受本地區生育文化的影響,內部的生育文化氛圍就決定了人們的生育行為。同一地區中的人們,在生育意愿、對孩子的性別偏好等方面往往是一致的。因此,有什么樣的生育文化,就有什么樣的生育行為,生育文化對生育率的影響比經濟水平更直接。
三、加速實現新型生育文化
針對以上表述,我們可以看出張家口10貧困縣受生育文化的影響生育率較其他地區來說較低,這和本地區人們“生男生女都一樣”的生育觀念密不可分。然而10貧困縣中蔚縣的生育率和超生罰款率和其他9縣相比都比較高,本地區的生育觀念仍受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從而可以看出不同的生育文化影響不同地域的生育率水平,生育文化比經濟發展水平對生育率的影響更直接。雖然說傳統生育文化已基本轉變為新型生育文化,但是我們仍不可低估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在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傳統生育文化觀念仍然頑強的存在人們的意識中。
對于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間還有一定距離,因此,我們應全方位的營造適宜生育文化變遷的環境,采取一些當地人容易接受的方法,努力挖掘傳統習俗中積極的因素,使之與生育政策相結合,建立符合現代社會人們生育觀念的新習俗。
第2篇: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社會保障水平;社會保障替代率;結婚概率;總和生育率
中圖分類號:C9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5)06-0114-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6.012
一、引言
社會保障與人口結構是我國人口和社會福利最為基礎的指標之一,它們將對我國未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社會保障繳費率和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是社會保障研究領域中非常重要的兩個部分。社會保障繳費率反映了社會保障給人們帶來的經濟壓力,社會保障支出水映了社會保障給人們帶來的福利水平。本文主要研究在社會保障變化的過程中社會保障水平對于人口結構的影響,這里所指的人口結構包括總和生育率和結婚人數。雖然人口結構的變化主要取決于經濟收入的提高以及人口政策的導向,但是這兩個主要因素的變化并不能完全解釋人口結構的改變。例如從我國總和生育率的角度來看,在剔除由經濟收入變好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控影響以外,有研究者重新估算了我國近些年的總和生育率應該是多少,其得到的結論是估算的總和生育率水平要高于我國政府所公布的實際總和生育率水平。與此同時,該研究按照重新估算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實際模擬了我國1972-2008年的人口估算總量,發現中國實際的人口總量比估計的人口總量還減少了約4.58億人[1]。因此,單以經濟收入和政策因素作為人口結構的變化的解釋因素仍略顯不足。本文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社會保障的變化對人口結構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社會保障的變化會降低總和生育率的水平,同時也使得結婚人數產生了下降的趨勢。
二、文獻綜述
貝克爾(Becker)正式建立了人力資本和生育決策之間關系的微觀理論模型,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單向利他模型和雙向利他模型,開啟了社會保障對生育決策的影響研究。其研究主要分析了二者的效用關系。這種效用研究體現了兩個方面:一是社會保障對總和生育率的收入效應,但由于缺少有效的數據而難以對該理論進行有效的檢驗[2]。二是社會保障對總和生育率的替代效應。萊恩特(Lainter)將父母的遺產動機同子女對父母的利他性結合起來考查,證明了如果加入年輕人對父母的利他性,特別是子女對父母贍養和贈予要大于父母給予子女的遺產時,社會保障制度更有利于私人儲蓄和物資資本積累,從而降低了生育水平[3]。埃斯瓦蘭(Eswaran)通過納什博弈分析了生育決策過程中夫妻雙方談判力量的作用,男女雙方的不同力量決定了不同的生育水平,亦即決定不同的總和生育率[4]。博爾德林(Boldrin)分析了社會保障繳費率與總和生育率之間的關系,發現社會保障繳費率的提高降低了總和生育率[5]。霍爾姆奎斯特(Holmqvist)針對撒哈拉以南地區的非洲國家1960-2007年的數據作了研究,發現帶補貼養老金制度的引入使得每個婦女少生0.5-1.5個孩子[6]。納蒂亞(Nadia)等人分析了社會保障替代率和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將會降低女性的總和生育率[7]。
社會保障對人們婚姻影響的研究分析指出,社會保障的變化將降低人們的結婚意愿。埃爾利希(Ehrlich)指出“在充足的社會保障基金支付能力和適度社會保障繳費率條件下,人們通常就不會選擇利用結婚形式作為維系生存的重要因素”,并且通過對OECD國家的研究發現,社會保障基金支出增加將會降低OECD國家的總和生育率以及結婚人數,并且這種降低的影響不會通過代際轉移而消失[8]。斯蒂芬(Steven)發現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多少對于家庭中的女性更為重要,特別是對低收入的女性更是如此,一旦這些女性選擇離婚將不再能夠獲得丈夫的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從而導致離婚女性變得更為貧困,而且增加男性的社會保障基金收入不利于維系家庭的穩定[9]。席妮池(Shinichi)在對社會保障和勞動供給研究中發現,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并且使得女性的勞動工作時間至少增加了4.3%-4.9%,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以及工作時間的增加將降低女性結婚的意愿[10]。安德魯(Andrew)分析了社會保障繳費率和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對于男女收入的影響,進而研究發現以上兩者對結婚選擇產生了不同影響,社會保障繳費率的提高會增加女性結婚的意愿,但是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會同時降低男性和女性共同的結婚意愿[11]。王云多分析了家庭組成、生育決策和社會保障之間的理論關系,認為社會保障的變化會降低家庭組成的概率,并降低人們的生育意愿[12]。斯蒂芬也分析了結婚導致社會保障基金收入所帶來的效用的降低,社會保障增加并不能很好地維系婚姻,同時分析了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能夠提高喪偶女性的收入與福利[13]。
三、模型建立
1.前提假設和基本模型
社會保障與人口結構的變化過程中存在著撫養子女的代際交疊、勞動供給的代際交疊,以及退休人口的代際交疊這三種代際交疊形式。因此,本文把代蒙德的代際交疊模型作為社會保障和人口結構變化動態分析的基礎模型并擴展該模型。假定在具有同質工作能力的工人和固定的勞動供給的經濟體系中,假定婚姻選擇除已婚外,其他都作為未婚(包括未婚、離婚以及喪偶)。該模型假定只有已婚的家庭才會理性選擇孩子數量和質量,因此,代蒙德模型的擴展從孩子的人力資本開始,人力資本模型為Ht+1=A(H-+Ht)ht,H-作為初始人力資本,ht∈[0,1],代表父母在孩子身上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所使用的物資資本并假定H0=0,A代表提高知識代際傳遞的環境因素。所有人工作的目的都在于使其能夠獲得最大的效用U,并且每個人都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數。pt代表結婚概率,U*m(t)和U*s(t)分別代表已婚和未婚的最大期望效用函數,效用函數為:
四、實證分析
1.主要概念界定和計算方法
對關鍵概念界定不清容易造成誤導,因而有必要予以詳細介紹。
(1)主要變量說明。影響人口結構變化的社會保障主要沿用了納蒂亞所指的社會保障替代率SSR(Social Security Replacement Rates),社會保障替代率=社會保障年收入÷年收入[14]。
社會保障替代率需要進行分層計算,普賽爾(Purcell)介紹了具體的計算辦法[15]。社會保障替代率的計算需要分為以下兩步。第一,計算不同人群年收入。區分了工作期間的個人收入和退休人口的個人收入。工作人口的年收入用人均工資年收入表示,所選取的數據名稱為就業人口的人均 GDP(1990 年不變價購買力,來源:世界銀行)。退休人口的年工資收入按照退休前的最后一年的工資計算(計算方法來源: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例如,如果個人在1995年退休那么其年收入標準為1994年的年工資收入,由于在退休以后沒有工資收入,而社會保障替代率事實上反映了對于收入的一種替代關系。
第二,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計算方法。個人(家庭)所獲得的社會保障收入從國家角度看實際上是國家對于社會保障的支出。因此,個人(家庭)獲得的社會保障收入應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社會保險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工傷保險基金、失業保險基金收入和生育保險基金。由于本文選擇的國家除中國外,還涉及東盟各國(不包括文萊),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方面的數據無法獲得,為計量實證分析指標的一致性,本文僅選擇了社會保險基金收入作為個人(家庭)社會保障收入。因此,本文的社會保障替代率在計量中所反映的是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年收入。
(2)[JP+2]其他變量說明。第一,結婚概率(MARRY)是作為結婚人口的比例,即用已婚人數除以成年人口總量。第二,選擇不同階段的生存概率(π1和π2),π1和π2的上升能夠增加n和h的回報率,n和h又涉及消費的跨期替代率,因此會對結婚概率和總和生育率產生影響。 第三,人均GDP和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作用類似,對結婚概率和總和生育率也會產生替代效應。第四,女性人數與男性人數的比例(SEX),該變量影響結婚的搜索效率,因此影響了結婚概率,進而影響了總和生育率。第五,女性勞動參與率(FLFP),勞動參與率的提高會增加女性的收入,將會降低女性結婚概率,影響總和生育率。第六,
女性與男性教育水平比例的均值(FSCH)。女性教育的提高能夠促進女性的就業,使得女性收入增加,這會降低女性的結婚率,并且影響總和生育率。第七,政府購買占GDP的比重(G),以便于區分開社會保障替代率和其他政府支出對婚姻結構以及總和生育率的影響。
本文主要選擇中國和東盟國家(未包括文萊)作為樣本,統計了上述的主要變量,并且對變量進行無綱量化處理,對所有變量的數據取自然對數。
2.主要統計描述
中國和東盟國家在社會保障替代率和人口結構的變化上主要表現在:從中國數據的特點來看,社會保障替代率的年增長率的總體趨勢在不斷遞增,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結婚概率出現小幅波動但整體趨勢在不斷下降。從東盟國家數據的特點來看,首先各國的社會保障替代率從1995年開始都在不斷地增長,其中增長最快的國家是泰國;其次各國的總和生育率都在下降,下降最多的國家為老撾;最后各國的結婚概率也出現了不斷下降的趨勢,變化最大的國家為柬埔寨。并通過Stata統計軟件統計分析了主要變量的數據特征(見表1)。
從表2可以發現較高的社會保障替代率降低了結婚概率的值。確實社會保障替代率和結婚概率呈現著一種負相關關系,這與事實一致,對于沒有穩定工作的人,特別是在有權獲得配偶的社會保障收入時,更有動機和激勵去結婚并且很好地穩定家庭婚姻。較高的π1和π2有助于結婚的形成,其原因可能在于較高的生存概率更能夠增加青年個體組成家庭的概率。LGDP與LMARRY負相關,反映了跨期替代的家庭婚姻的選擇行為,也反映了收入與婚姻的替代關系。政府購買支出(G)增加對于維系婚姻具有積極的意義,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購買支出增加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稅收負擔,降低了人們的收入,因此人們愿意維護婚姻的穩定。女性與男性人數的比例(SEX)越接近1,說明男女比例越均衡,這將使得男女在搜索伴侶的成本方面會降低,使得結婚的成功率會提高。較高的女性勞動參與率(FLFP)降低了結婚意愿,女性參與工作的概率大,使得女性推遲了結婚,因此降低了結婚概率。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比率的均值(FSCH)越小,說明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差距越大,那么配偶之間潛在收入的互補性就越大,這能夠提高和穩定家庭結構。
(2)總和生育率實證回歸結果。表2的后4列是對LTFR回歸的結果,模型1和模型2代表了方程(14)的OLS回歸,作為第一階段回歸結果,模型3和模型4代表了方程(14)的GMM回歸,作為第二階段回歸。在模型2和模型4中LMARRY(被視為內生變量)與LSEX、LFLFR和LFSCH一起加入模型中進行內生回歸。
分析的結果發現社會保障替代率與總和生育率是負相關的,這說明社會保障費率的提高將會降低總和生育率,這符合上述的分析。結婚概率與總和生育率呈現了正相關關系,說明結婚人數的增加提高了組成家庭的數量,孩子是已婚家庭的選擇,已婚家庭數量的增加提高了總和生育率。π1和π2的提高通常有利于總和生育率的提高,生存概率對總和生育率的影響也是非常顯著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生存概率的提高使得家庭婚姻結構的增加,進一步刺激了家庭撫養孩子的可能性也隨之提高。人均GDP的提高卻使得總和生育率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在不斷上升,撫養孩子將會降低收入所帶來的效用,因此降低了總和生育率。政府購買支出(G)的提高通常也會降低總和生育率,其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增加將導致人們稅收負擔的加重,這將增加撫養孩子的成本,因此降低了人們的生育意愿,降低了總和生育率。女性和男性人數的比例(SEX)增加促進了總和生育率的提高,由于女性人口的增加會使得結婚的人數增加,撫養孩子是家庭的選擇,因此會提高總和生育率。較高的女性勞動參與率(FLFP)反映了較高的市場工資,增加了撫養子女的機會成本,所以降低了總和生育率。女性與男性教育水平比率(FSCH)的提高使得夫妻在撫養孩子的問題上能夠更好地進行溝通,因此使得總和生育率上升。
五、結論與建議
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社會保障水平對人口結構的影響符合理論預測,社會保障替代率的提高降低了結婚概率和總和生育率。進一步分析,社會保障替代率彈性的提高將會導致結婚概率和總和生育率彈性的提高。結合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實證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適時根據我國國情調整人口政策,雖然減少人口數量會帶來人口質量的提高,但人口質量的提高能否補償人口數量減少所帶來的人口紅利損失還有待商榷。適度放寬生育政策,以此調節總和生育率,使人口結構能夠均衡發展,這才是未來我國人口發展的核心目標。
當前我國已經明確提出全面二孩政策,但仍需相關法律支持,為保證我國的人口均衡發展,需要相關法律盡快完成以保證全面二孩政策的順利實施。
第二,結婚和生育是未來人口發展和社會保障財政收入的主要支撐點,因此降低結婚成本和生育成本有利于社會保障政策良性運行和改善人口結構。結婚與生育是相互影響的,結婚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婚姻的形成,結婚人數的提高才能夠改善我國目前不斷降低的總和生育率;與此同時,目前的生育數量將決定未來結婚搜索成本能否降低,能否促進結婚概率的提高。為此相關政策措施應一起配合來降低結婚成本和生育成本,從而促進社會保障和人口結構均衡發展。
參考文獻:
[1]陶濤,楊凡.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應 [J].人口研究,2011(1):103-112.
[2] 王天宇,彭曉博.社會保障對生育意愿的影響:來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證據 [J].經濟研究,2015(2):103-116.
[3] LAINTER J. Household bequest behavior and the 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9, 46:467-483.
[4] ESWARAN M.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fertility, and child mortality: toward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2(15): 433-454.
[5] BOLDRIN M, NARDI M, JONES L. Fertility and social security [EB/OL]. [2005-03-16].http:///sol3/papers.cfm?abstract_id=669445.
[6] HOLMQVIST G. Fertility impact of highcoverage public pens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J]. Global Social Polity, 2011(11):152-174.
[7] NADIA S, ALICIA H, PATRICK J. How do trends in women’s labor force activity and marriage patterns affect social security replacement rates? [J].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2013, 73(4):1-24.
[8] EHRLICH I,JINYOUNG KIM. Social security and demographic trend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06,10(1):55-77.
[9] STEVEN A S, WEI SUN, ANTHONY W. Why do married men claim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so early? ignorance or caddishness? [R].Center for Retirement Research at Boston College, 2007:1-46.
[10] SHINICHI N. The joint labor supply decision of married couples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system [R]. Retirement Research Center, Michigan (MRRC), 2010:1-46.
[11] ANDREW G, GAYLE L, NADA O. The treatment of married women by the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program[R].Center for Retirement Research at Boston College, 2010:1-27.
[12] 王云多.家庭組成、生育決策和社會保障 [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11(1):56-62.
[13] STEVEN A S, SUN Wei, ANTHONY W. Social security claiming decision of married men and widow poverty [J]. Economics Letters,2013,119:20-23.
第3篇: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生育意愿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行為。長期以來,“多子多福”的傳統生育文化影響著我國農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導致農村的多生行為,“多孩”成為家庭的普遍選擇。然而在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人口流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傳統“多子多福”生育觀念遭受巨大的挑戰。以工業化、市場化為特征的現代經濟侵蝕傳統的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強勢的計劃生育政策從制度上嚴格約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選擇的空間;大規模的“鄉城”人口流動對農村多孩生育觀念帶來巨大的沖擊,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在不斷弱化,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經由多生、早生,轉變為自愿少生、晚生;從重視孩子數量逐漸轉為重視孩子的質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數量”的變化是這種轉變的直接體現。2006-2007年,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顯示[11],在無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數為1.45,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遠。以現行的1.5個子女作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斷標準①,江蘇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農村家庭對孩子數量的選擇空間極為有限。相關學者估算,我國農村地區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體上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選擇空間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與孩子數量之間進行的艱難抉擇。從政策生育水平來看,農村政策生育水平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轉變增長勢能消退后,負增長的人口政策將累積人口負增長慣性。
近年來,受城市發展的推動以及人口流動阻力的減小等因素的影響,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西方學者在研究生育率轉變過程中,就提出現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轉變的基本決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方面[14]。而針對我國的實證研究也證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觀點、生育文化對常年居住于城市的農村青壯年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城市化顯著減緩了我國人口的增加[15],有過外出流動經歷的農村婦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沒有外出經歷的農村婦女[16]。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將推動農村生育模式轉變。從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狀態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與實際生育水平存在差異。事實上,由于經濟、政策、流動等條件的限制,人口的實際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生育的城鄉二元結構,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農村地區低。不過近年來,農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斷下降,因而城鄉生育水平正逐漸趨同。“六普”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44,遠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鄉生育水平的趨同態勢較為明顯。這也表明,農村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不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許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許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無法克服因生育帶來的巨大成本而放棄生育,進而造成實際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現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實際生育水平的梯級遞減特征。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也顯示,擁有二孩生育權的婦女中,沒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過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個孩子比例不足4%。放棄二胎現象表明,在農村地區,一胎化已有內化為個人自覺生育選擇的趨勢。這種自覺的超低的實際生育水平已經在人口內部累積起巨大的人口負增長慣性,這一現象值得警惕。
在這種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下,農村地區實際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積巨大的負增長慣性。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規模由2000年的934萬人減少至2010年的841萬人,年均減少近10萬人。如果按照這一變動趨勢,2022年,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將不足400萬人;由于出生人口的減少,農村少兒人口(0-14歲)規模由2001年的2.06億人減少至2010年的1.17億人(圖1),減少0.89億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處于“少子化”狀態,并處于“嚴重少子化”①的邊緣。這種長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實際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內部累積了巨大的負增長的慣性,農村人口未來將遭遇負增長已成定局。同時,少兒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動整個農村人口結構的老化(圖2、圖3)。假設以2010年農村各年齡人口規模為基礎,0歲組人口規模以2000-2010年間變化趨勢為準,并假設年齡死亡率不變,2030年,農村人口年齡金字塔將如圖5所示。金字塔圖表明,2030年,中國農村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別達到15.7%和26.3%,屬嚴重的“少子老齡化”狀態。
二、農村人口勞動力虧損
城鄉二元體制下,我國缺乏明確且有效的城鄉均衡發展的政策和途徑。相反,國家政策長期傾斜于城市的發展。我國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節節攀升,而與之相對應的農村,種地不賺錢成為一種普遍狀態(參見表1),我國城鄉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失衡的城鄉發展,也帶來了城市社會對農民身份的偏見與歧視,農民對自己的身份也容易產生較強的自卑感,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厭離農業,“跳出農門”、“遷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強烈。由于推拉合力產生了城鄉之間巨大的勞動力遷移勢能,農村勞動力轉移順勢而出。
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不完善、勞動力市場尚不完全,農村勞動力轉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很難形成有序、合理的城鄉勞動力流動。這種失靈的勞動力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與沖動性,并造成農村人口虧損。據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2011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58%(參見圖6)。其中,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59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36.4%。相關學者研究也顯示,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已經結束,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①已經出現[19]。據估計,2006-2010年間,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在0.3~1.8億人之間(參見表2)。而2011年我國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08年起,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億人以上,其規模均超出學者們所推算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即農村勞動力凈剩余規模由正轉為負,出現城市、農村爭奪勞動力現象。近年來東部發達省區出現的“民工荒”、農民工工資上升等現象則是對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直接佐證。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②調查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2011年6月,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發現,河北、山西、湖南、內蒙古等其他省(區)的情況,大致情況類似,本來是農業大省的中部廣大農村地區,年輕人變得越來越少,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將越來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勵加快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另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為城鎮的發展提供了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資金流。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每年農民工為城鎮發展帶回的資金流高達數千億元。農民工外出務工帶回的資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鎮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城鎮發展資金不足的狀態。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政府鼓勵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熱情。國家出臺的很多政策弱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中間障礙,甚至鼓勵有能力的勞動力出國打工。這種單向的政策鼓勵導致能進城的都進了城,農村真正全職的“種養”勞動力幾乎沒有,這也成了一種普遍狀態。這種“只推不拉”的單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農村凋敝的步伐。
能夠保障村莊安全、發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輕人口的缺乏,農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經出現③。這樣的景象絕非個別,甚至在鄉土中國不斷蔓延。據《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字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從2005年至2009年逐年減少,分別為62.9萬、62.4萬、61.3萬、60.4萬、60萬。平均計算,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說明,在中國這個曾以農業文明興盛的廣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國土資源部調查發現,我國每年撂荒耕地達到3000萬畝,10年則達到3億畝,數量驚人。由于勞動力短缺、種糧效益較低等原因,農民對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興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積達40%以上,并且還存在“隱性撂荒”現象,本來可以種植雙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種了單季稻③。種糧農民不足的問題已經出現,再過5~10年,這些老人無法勞作之時,種糧主產區的勞動力將后繼無人①。
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們認為中國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現在卻出現了“供給缺口”。即便總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穩定,我國也將長期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26]。“六普”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僅有海南、新疆、貴州、廣西四省的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間,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遼寧、黑龍江、吉林六省市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1,已進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雖然我國生育率長期存在二元城鄉結構差異,但生育率相對偏高的農村地區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這是發人深省的事實。同時,“六普”數據顯示,我國城市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0.882,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438,比世界發達國家水平還要低0.262②,反彈乏力,這也是造成勞動力后備資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城鎮失業報告》③稱,未來我國農村從事農業的年輕一代(16-25歲)勞動力,其在農村戶籍勞動力中的比重已不足兩成。造成農村人口無法維系“無限供給”的狀態,并出現勞動力“供給缺口”。
人口城鎮化一方面通過轉移農村過剩人口,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城鎮化吸走的農村人口不一定是過剩勞動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勞動力和精英勞動力。因為遷移行為是具有選擇性的,那些處于青壯年時期的人口以及擁有較高學歷的人口更有可能選擇遷移。這樣過度而且具有選擇性特征的人口轉移所帶來的就不是“人口適度”和“人口紅利”,而是農村“人口虧損”和“人口負債”。這也告訴我們,人口城鄉、區域間的合理分布,是實現城鄉、區域均衡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農村無農民不穩,無農民不旺,農村勞動力轉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發展,也要推進農村的進步,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長期以來,城市與農村發展密不可分。沒有穩定的農村,城市將很難實現持續發展。沒有興旺的農村,城市將很難有持續的繁榮。沒有新的農民人口補給進來,農業發展將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將因為沒有興旺的農業、農村作為后盾而失去發展的基礎,這也是當前“無農不穩”的新含義。
第4篇: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內容摘要 “單獨二孩”作為一個壓力測試和政策試驗,有助于對未來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和策略提供決策支持。研究發現,鑒于“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效果的類似性,我國育齡婦女的終身生育率仍然將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的現實,從現在開始實行“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調整是可行的。從充分滿足民眾的生育需求和維持宏觀人口發展均衡可持續的目標來看,建議從2019—2020年開始,在“全面放開二胎”以后逐步落實向、“家庭自主生育”轉變,以及實現計劃生育向家庭計劃的轉變。
關鍵詞 單獨二孩 全面放開二胎 新生兒-母親-代人口比 家庭自主生育 家庭計劃
作 者任遠,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上海200433)
一
五普以來,人口發展完成了人口轉變,而我國生育政策調整一直滯后于人口狀況和中長期人口變動的態勢。六普數據表明,我國人口生育率水平實際上低于本世紀初國家人口戰略預測的結果,而人口內在萎縮的速度比預想更嚴重。近年來,雖然較多學者論證應該可以實行“全面放開二胎”的改革,而2014年以來我國開始實施的是“單獨二孩”的生育政策。該政策到目前為止的實施效果是,全國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萬,到同年8月底,只有70萬對申請生育二胎。全國不同地區“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以后新增加生育的情況都遠低于預期的水平,符合“單獨二孩”政策家庭的實際生育水平不高,職能部門所擔心的“單獨二孩”政策所帶來的補償性生育的人口反彈并沒有出現。
“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生育效應產生一定預判失誤的原因有:一是政策變動效果的跨年度效應,政策影響行為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現出來。二是利用2005年人口小普查數據進行生育預測,在數據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不少生育預測往往是以生育意愿來代替實際生育行為,而社會生活和經濟約束下的生育行為決策往往顯著低于生育意愿。我們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后獨生子女一代年輕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經顯著降低,在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人口群體中選擇生育的比例相當低,一些研究論證這個比例大約在20%—30%。
“單獨二孩”的生育政策調整,整體上說是一個相對滯后的政策調整。如果我們換一種思路,將“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作為“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壓力測試和政策試驗,據此對“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后果進行預判,目前進行的單獨二孩政策及其實施結果,可以對未來生育政策改革的方向和策略提供新的研究發現和政策文持。對于“全面放開二胎”,國家仍然持謹慎態度和“沒有時間表”。前不久,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新聞會上表示, “目前我們國家的生育勢能還是很大,現在有一個孩子的家庭全國測算有1.5億左右,有近80%的家庭有生育意愿,就有將近9000萬的家庭準備再生育孩子”。他指出,如果現在普遍實施二孩政策,就會使中國的生育水平有一個很大的反彈,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影響,也會使國家制定的人口發展目標受到影響。他強調,中國人口多這個基本國情目前還不會改變,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還不會改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系還不會改變。 為此,筆者擬利用已有的數據,估算“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究竟會對新增加的生育帶來多大影響,從而為生育政策改革提供依據。
二
本文的研究假設是,假如所有家庭夫婦在“全面放開二胎”下的生育行為和單獨家庭在“單獨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為是類似的,那么,按照目前1100萬“單獨家庭”在“單獨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為,可以推斷出所有家庭在“全面放開二胎”下的生育行為和生育結果。
為了估計這種生育行為的影響,筆者設計了“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 (NM)的分析工具,這是指當年新生兒人口和平均生育年齡之前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的比值。“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類似一種倒推上去的隊列總和生育率,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衡量生育水平的指標。當然,這個指標也沒有考慮移民效應、母親一代人口的死亡等。我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衡量這種生育率水平和時期總和生育率(TFR)究竟誰高誰低,而是以此為工具來衡量生育政策調整對生育水平變化的影響,以及估算生育政策變化對新增加的生育人口數量變化的影響。
對國家人口和生育來說,存在一個基本能夠反映當下生育政策約束的“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 (NMl)。例如,我國的女性平均生育年齡是28歲,可將2013年新生兒人口數1640萬人,與1985年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983萬的比值1.67,作為“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前計劃生育政策約束下的基線生育水平。其中, “單獨二孩”家庭中申請生育二孩而新增加生育的新生兒數,與平均生育年齡前母親一代人中符合單獨政策人口數的比值,構成第二個“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 (NM2),這是所有單獨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水平。而單獨二孩家庭的新增補償性生育,與平均生育年齡前國家所有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數的比值,則構成第三個“新生兒一母親一代人口比”(NM3)。NM3和NM1兩相比較,基本能夠反映“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對于人口生育水平的影響。 (詳見表1)
假設2013年和2014年的生育水平無顯著差異,我們用“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可以估算“單獨二孩”政策調整對于生育水平的影響。“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是類似于隊列的終身生育率,不適合直接和時期指標計算的總和生育率進行類比。參考郭志剛從時期生育行為對終身生育水平的去進度效應的估計,1990年代末婦女終身生育率TFR’約為1.7(近期的育齡婦女終身生育率水平應該更低)。即使用這個較高的終身生育率水平來推算, “單獨二孩”可能使得我國育齡婦女的終身生育率上升到1.8;而“全面放開二胎”會使我國育齡婦女的終身生育率水平上升到1.83,但這個結果依然是較低水平的生育率,仍然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
從生育政策調整來看育齡婦女的終身生育水平,這也說明我國的生育率下降已經進入了“低生育陷阱”,即和東亞諸多國家和地區類似,出現了“生育率下降了就很難反彈”的風險。就此而言,對生育政策調整會帶來顯著的生育反彈的擔心是不必要的。從長遠來看,人口與發展的主要風險不是生育水平過高的問題,而是生育水平過低的問題,為此,需要進一步放開二胎的限制,解除生育行為背后的政策枷鎖。
圖1描繪了我國1980年代以來的年出生人口數。1980年代,我國年出生人口數基本都在2000萬以上,特別是1986~1990年受到1962~1970年出生高峰推移的影響,形成了出生堆積的高峰,每年新出生人口數達到2500萬以上。而1990年以后總體上出生人口數是快速下降的,基本穩定在1600萬左右的年出生人口。
如果所有家庭都“全面放開二胎”,也就是說按照NM2來生育,那么通過“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結合過去各個年份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數,可以近似推斷出在平均生育年齡以后的未來各個時期“全面放開二胎”新增加的生育人口。 (詳見表2)
研究表明, “單獨二孩”政策下,2014年大約年出生人口數會達到1983萬。“單獨二孩”政策使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實施以前增加6.3%左右,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生育效應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實施以前增加7.8%左右。即使立刻實施“全面放開二胎”政策,2014—2030年新增加的生育人口也就是1932萬左右。如果說中國總人口在2025—2030年將到達頂峰,我國峰值人口數量僅比現在高出2000萬人口。就此而言,“全面放開二胎”會增加9000萬人口,不太可能出現。
四
我們將“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效果作為政策試驗,來預判“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生育影響,結果表明,對于生育政策調整帶來的生育反彈實際上不必過分擔憂。值得擔憂的倒是,即使放開生育控制,婦女的終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即我國可能已經進入生育率下降很難反彈的“低生育率陷阱”。實施“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不會帶來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長。
實施“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所帶來的補償性生育反彈,大約會增加6%—8%的新增生育人口。同時, “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比“單獨二孩”多增加的人口實際是有限的,或者說“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效果并沒有顯著差別。 (圖2)這也再次說明,從“單獨二孩”到“全面放開二胎”的漸進改革有些“過于碎片化”的謹慎,實行“單獨二孩”或許僅僅在政策調整試驗上具有意義。鑒于“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實施效果的類似性,實際上我們可以從現在起實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 “全面放開二胎”對于生育反彈的影響不大,人口生育水平仍將維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值得提醒的是,相對于2013年出生人口1640萬,2014年出生人口預期會達到1980萬, “十三五”前四年即2015~2018年年出生人口都將相對較高,在2000萬以上甚至達到2200萬。但是我們并不用過分擔憂,因為即使沒有生育政策的調整,也會出現年出生人口數增加,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應。我們千萬不要將這段時間人口出生的顯著增長歸因于(或者怪罪到)生育政策的調整,避免將因為人口慣性帶來的生育反彈歸咎于政策調整造成了政策波動。同時,我們要看到即使2014—2018年人口生育數量將有較大增長,仍然顯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階段的出生人口數;而且,2019年以后,隨著上一波生育高峰開始下降,我國的出生人口數量也會隨之快速下降。
上述研究再次表明,從現在開始實施“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的調整是可行的。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即使我們實行“全面放開二胎”,我國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務還沒有完成,因為“全面放開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口群體的生育意愿, “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生育率水平仍將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在人口上依然是長期不可持續的。從充分滿足民眾的生育需求和維持宏觀人口發展均衡可持續的目標來看,我們需要在“全面放開二胎”后逐步落實向“家庭自主生育”的轉變,以及實現“計劃生育”向“家庭計劃”的轉變。此時,我國自1980年開始的計劃生育政策就完成了過渡期任務,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實現自主生育”的時間點建議放在“十三五”期間最后一年,大概在2019—2020年。因為如前已述,2014—2018年的年出生人口會在1986—1989年出生高峰推移效應下維持較高水平,從而增加政策決策的不確定性。但是,2019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數就會顯著下降,如果利用這一年開始推動實施全面自主生育,能夠抵消生育下降的缺口,并幫助穩定人口的波動性。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節點,2021年是建黨100年,用實現自主生育的民眾民主來作為全面小康的歷史里程碑,并為第一個100年獻禮,將使中國開啟一個全新的生育政策時代,標志著國家新人口政策的開端。
參考文獻:
[1]衛計委回應普遍放開二胎:現在還不是時候.中國網,2014.7.10.
第5篇: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如今,藥吃多了,世界還好嗎?
1993年開始,上海市戶籍人口就進入了負增長,作為中國富裕化的代表樣板,它尷尬地告訴中國人:中國已經悄然邁入了“低生育率”時代。2009年,上海市重申了2004年起施行的“符合再生育條件夫妻可生二胎”政策,這樣的鼓勵與當年轟轟烈烈的計劃生育,對比效果頗值得玩味――因為低生育率已經不再只是德國、日本等一些人口負增長國家的頭等大敵,人口學研究表明,中國可能正在走上與歐洲和日本相似的道路。
究竟是哪些原因,讓世界上的新生兒越來越少?
明年復明年,明年何其多?國外的研究已經證明,生育年齡推遲是生育率的重要抑制因素。比如,近年來歐盟人口由于生育年齡不斷推遲導致其生育率降低了30%;北大教授用同樣方法對中國數據的分析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由于推遲生育降低生育率的幅度為11%,而在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其降低幅度則高達23%――在愈加發達的中國,生育年齡推遲這個抑制因素的影響已經變得相當大。
相信你一定遇見過“職場白骨精小A”這樣的朋友:“公司倒沒有規定不能生小孩,但是這意味著我要離開崗位將近半年甚至更久,等我再回來恐怕早被人占了座!生孩子這事兒,能等就再等等吧!”也應該不缺少“完美主義者小B”這樣的閨蜜:“我只是花了太多的時間尋找理想的另一半……”
――當自我意識開始蘇醒,生兒育女這類的傳統事務,放下爸媽的電話就能被忘得干凈。
一不小心就成了沒運氣的“不孕族”。在這個冰川融化、地溝油出沒的時代,環境惡化正在大范圍地發生,加之社會節奏加快、競爭加劇,人們面臨前所未有的生理和心理壓力:野心的膨脹正令我們失去本以為理所應當的健康。
這一代人中的不少人,經歷了這樣的軌跡:在健康蓬勃的青春年代無知無畏,終于混到“人上人”的境界買了別墅有了草地,卻再不能有自己的小孩在其中打鬧嬉戲。不孕,早已成為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據報道,現在美國不孕率為10%~15%,而歐洲的不孕率則達到20%,我國的最新研究結果同樣顯示,新一代已婚婦女的不孕風險明顯提高。
與高質量生活競爭后的走低生育率。西方國家曾經流行一個口號:發展,就是最好的避孕藥――因為忙于其他生活追求而減少甚至抹掉了生育的必要,實在比任何措施都立竿見影。
這種競爭有時來自宏觀層面。比如2009年美國眾議院73名議員力促奧巴馬在2011年中為國際計劃生育增加10億美元,因為“較低的人口增長率將使得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更容易達到”。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同樣認為:為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我們可以在疫苗、醫保方面做得很好的條件下,把人口降低 10 至 15 個百分點――來自強勢話語權的信息告訴我們:讓現有的人口過得更好,似乎比人口增長繁衍更有意義。
這種競爭也可以微觀到個體。密歇根大學的Ron Lesthaeghe曾經提出“第二次人口轉型”的概念:它是工業社會從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發展到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時,人口生育狀況發生變化。它的出現是由微觀個體的集體行為帶來的:人們更愿意推遲或者拒絕生育,從而可以更專注于教育和事業發展,花更長的時間尋找理想配偶,追求更加靈活有趣的生活。因為富裕社會的這些趨勢,教授們猜測再過50多年,美國將為人口的減少而擔心,就像現在的歐洲和日本一樣。
第6篇: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楊成鋼(西南財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國經濟增長能夠“消化”新增人口,應該全面放開“二胎”政策
為什么要調整?用人口指標說話
一是四川人口出現負增長。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以下簡稱“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以下簡稱“五普”),全國常住人口增長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現負增長,2010年人口總量較2000年減少193.08萬人。
二是四川婦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數據顯示,四川婦女總和生育率遠遠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樣調查顯示,除甘孜、阿壩、涼山“三州”地區之外,四川省婦女總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區,其也只有1.72,遠遠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來越少。“六普”數據顯示,四川省0~14歲兒童人口比重為16.97%,比“五普”下降5.6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未來四川勞動力人口會減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來越多。“六普”數據顯示,四川省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為10.95%,比“五普”上升3.2個百分點。國際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7%就是老齡社會,全省老齡化已經來臨,獨生子女負擔加重。
五是城鎮化加快發展改變居民的生育觀點。“六普”數據顯示,全國城鎮化率為50%,四川38.7%,雖然四川城鎮化水平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近幾年四川城鎮化的發展速度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發展趨勢加快。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城市人口比重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持有“晚婚、晚育、少生、優生”觀念的人數增加,直接影響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會進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還有2個特別顯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萬獨生子女戶,占全國1/3;二是“失獨戶”四川占全國比重最高。這些人口指標顯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調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調整。
為什么能調整?處于有利時機
全國人民的呼聲很強烈。對于放開“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村居民;不管是廣大干部,還是一般群眾,都有比較強烈的意愿,學術界也基本達成共識,生育調整已有輿論氛圍。
我國經濟增長還會持續,能夠“消化”新增人口。從總體上說,現階段我國經濟狀況良好,未來保持較快增長是有保證的。經濟增長一方面有勞動力資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夠承受人口增加帶來的負擔。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的轉型期。在經濟社會的轉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開,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個,因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轉化為生育行為有一個滯后期。因此,很多人不會馬上選擇生第二胎,這種滯后對政策效應有一個緩沖期,新增人口在我們的承受期之內。
總體來看,現階段生育政策調整處于有利時期。
兩個誤區需避免
第一個誤區: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為
大樣本調查顯示,87%的夫婦生育意愿是2個,而且最好兒女雙全,一男一女。很多媒體據此得出放開二胎總人口就會翻番的結論,于是,他們反對放開二胎。放開二胎總人口就會翻番,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為。
第二個誤區:人口增長降低了資源、環境的承載力
資源、環境的承載力需聯系經濟增長來思考。真正影響資源、環境承載力的是經濟增長速度、規模、方式。過快的城市化規模,不適度的經濟增長節奏和不恰當的發展方式才是造成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們既要找到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在增強資源、環境承載力方面積極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四川放開二胎生育的時機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國家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四川作為一個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來,四川的總和生育率從過去的4.0以上下降到現在(全省抽樣調查的)1.6左右,實際情況可能比這個還要低。30多年來全省共計少生了4000多萬人口,為全國計劃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根據四川省當前的人口形勢,應該及時放開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長期少子老齡化使目前人口結構性問題十分突出。一般來講,一個國家如果總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實現正常的人口代際更替。四川的生育率遠遠低于2.1。被撫養的少兒人口減少,老齡人口增加:目前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4%,65歲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社會負擔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紅利不可能持續下去,未來會缺乏有活力的創新型人才。過去多年,四川大量勞動力到外地打工,為全國經濟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貢獻,但是人口紅利不可能持續下去,因為少兒人口越來越少了。四川勞動力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老化,15~30歲人口在下降,45~65歲人口比例在上升,這樣的人口內部結構,其創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勞動力年齡結構中45~65歲人口的比例會高達48%,勞動力都是些中老年人,會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勞動力,特別是高端的年輕創新型人才,這樣更不利于四川經濟發展。
原因三:緩解四川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個人口結構會達到最老化。退一步講,即使現在放開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緩解,因此,現階段必須及時調整二胎政策,時間不等人,在我看來,現在調整已經遲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調整生育政策,如果當時調整,四川也許會早一點緩解人口結構帶來的各種問題。
原因四:不會出現社會不穩定。放開后,短期內生育率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反彈;但是從長期看,人口數量不會有太大的波動,更不會出現社會不穩定。
原因五:獨生子女問題多。獨生子女責任重、壓力大;獨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對整個社會影響大;失獨家庭不能再生育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大;獨生子女增多對征兵和國防建設也有一定影響。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鄉不平等,應逐步統一。當年城市實施計劃生育政策非常嚴格,城鎮企事業單位職工若生第二胎,會開除公職和黨籍,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實際上為計劃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農村生育政策條件相對寬松。城鄉生育權利不平等,應該逐步統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該有回報。當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積極響應,做出的成績有目共睹,為全國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2008年四川發生大地震,傷亡慘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兒女。我覺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現在是該回報他們的時候了。
如果放開二胎政策,建議分兩步走:第一步:分步實施,平穩過渡。雙獨家庭早已放開,現在應該考慮放開單獨家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有殘疾兒童的家庭、再婚夫婦家庭。第二步:完全放開城鄉育齡婦女的二胎生育。
借這個平臺我再次呼吁:四川放開二胎生育的時機早已成熟,希望盡快調整相關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人口學碩士生導師):
放開“單獨”二胎,協調人口數量控制和結構優化的矛盾
人口年齡結構出現嚴重失調抑制物質資料的再生產
從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視角來看,實行人口計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協調人口再生產與物質資料再生產的關系,通過人口的數量控制和結構優化有機結合的綜合措施,使兩個“再生產”的關系處于一個合理、科學的均衡區間。
上世紀50年代初以來,由于我國人口發展政策發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無節制生育,使人口增長超過了物質資料再生產增長的能力,帶來以高出生率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問題。
上世紀70年代后,我國開始執行嚴格的以數量控制為主要特征的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億多人,使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進入“人口紅利”時期。
但是,當我國人口數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達到一定程度后,又產生了新的不協調問題,即人口年齡結構出現嚴重失調的發展態勢,人口的深度老齡化反過來會降低積累率,抑制物質資料的再生產,使經濟發展進入以老齡化為特征的“人口陷阱”狀況。目前人們考慮采取適度提高出生率以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樣在于協調兩個“再生產”。
科學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能夠增加資源的人口承載力
人口數量控制的另一個目的在于協調人口與自然資源承載能力的關系。目前不少人擔心人口數量控制放松,會導致土地等資源難以承載過多的人口。但是我們不難看出,我國過去在制定計劃生育政策所依據的人口承載力的理論是設定在一個封閉的自給自足經濟社會體系,尤其是基于我國耕地、糧食等資源的生產能力來確定的所謂“最佳人口規模”和“人口數量極限”。然而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建立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糧食生產能力等資源約束不再是人口數量控制目標的基本判定標準。日本、韓國、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國,卻能夠養活那么多人,并且順利成為世界上的高收入國家。所以,現在再看我國實行的以數量控制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國際環境下是正確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反映人口承載能力的科學依據越來越顯得不足。因為科學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都能夠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從而增加資源的人口承載力。
人口再生產具有長周期的特征,調整生育政策才能夠滿足2030年后勞動力要素的需求
相對物質資料的再生產過程,人口再生產具有長周期的特征。一個國家只有通過“未雨綢繆”行動和高瞻遠矚的超前決策,才能夠免除人口結構失調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與挑戰。目前,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已經長達30多年后,在人口結構已經進入全面轉型階段,在普遍實行“雙獨”二胎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實行“單獨”二胎的政策,明顯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國在2020年前仍處于“人口紅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適度增長可擴大居民消費與就業的規模,從而拉動經濟穩定增長。
第7篇: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需求學派;供給學派;生育經濟學
1)生育行為:需求方面的解釋
首先,從靜態的角度看,人類的生育行為建基于家庭靜態效用函數和靜態預算約束函數。Becker(1960)認為,人是在理性地考量個人生育行為成本和收益的基礎上,做出生育決策。子女對于父母來說,是一種消費品,同時也可以作為生產品在未來為父母提供收入。父母對子女的需求分別為數量上的需求和質量上的需求,它取決于如下因素:父母對子女的偏好;子女的質量;父母的收入;子女的成本。在此基礎上,Becker & Tomes(1976)引入“子女稟賦”這一概念,著重探討了子女由遺傳和運氣得到的能力等因素對孩子需求的影響。他們認為,在“子女稟賦”不變的情況下,父母收入的提升會使其對單個子女的開銷大幅度提升,這有助于提升每個子女的質量,也有助于降低父母對子女數量的需求。因此,我們所觀測到的質量收入彈性較高,而數量需求彈性較低,甚至為負數。在此基礎上,Schultz(1969)進行了拓展,他認為,家庭的生育行為取決于如下三點:家庭規模目標;死亡率;不確定性。其中,與子女出生率、死亡率相關聯的生育不確定性會促使家庭多生育或者少生育。
但是,靜態分析是遠遠不夠的。Nerlove(1974)認為,這一分析范式主要有兩大問題:第一,家庭欲最大化的效用函數為靜態的,違背了先前出生的子女也是家庭生育決策參與人這一基本事實;第二,子女在未來所帶來的收益值是靜態的,這也不符合家庭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會對子女生產能力產生影響這一事實。而Leibenstein(1981)則對“需求學派”靜態分析范式的新古典基礎進行了批評,他認為人們在生育決策中,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最大化一個目標函數,我們無法從他們的生育行為中倒推出人類的最優化決策過程。同時,人類完成最優化決策的諸多條件也不可能滿足。為彌補這兩方面的不足,我們需要從如下兩個方面拓展分析視角。
第一,我們需要考慮人類生育決策的動態性,將Becker建立的基礎生育決策模型動態化。Becker & Barro(1986)在構建具有利他特點的家庭效用函數基礎上,將家庭預算約束函數和家庭效用函數動態化,他們發現代表性家庭各代生育數量與真實利率、父母的利他程度成正比,與各期的消費增長率成反比,將上述基礎模型拓展后,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代表性家庭的生育行為,他們認為,生育率與世界的長期真實利率、父母的利他程度以及孩子的存活概率正相關,生育率與世界的技術進步速率和社會保障體系完善速率負相關。
第二,我們需要拓展生育行為的理性假設。Leibenstein(1981)在其本人對新古典生育經濟理論批評的基礎上,提出新的思路。他認為,在分析人類的生育行為時,需要用“過程理性”假設來取代“真實理性”假設,需要將經濟學的分析范圍由“決策結果分析”轉變為“決策過程分析”。這一分析范式認為,人做決策的過程是理性的,但由于諸多原因,人的決策結果卻不一定是理性的,因此,他認為對人類生育行為的分析應該著眼于人類的生育決策過程。人類總會衡量不同決策方式的成本和收益,進而最大化自己所做決策的收益。具體說來,人類的生育決策過程經歷如下四個模式:(1)基于道德原則的生育決策;(2)基于一系列傳統行為的生育決策;(3)基于些許算計的生育決策;(4)基于縝密邏輯演繹和全面計算的生育決策。這四種決策模式的成本越來越高,且其結果也越來越接近于“理性經濟人”的決策結果。Leibenstein認為,人類的生育決策無非是在上述四種模式中做出的,但很少有人通過第四種模式來進行生育的決策。
2)人類生育行為:供給方面的解釋
我們也可以從供給方面來解釋人類的生育行為。在對上世紀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美國人口生育率、收入、勞動參與率等數據進行分析的基礎上,Easterlin(1966)發現,不同年齡組的女性的生育率與“代際相對收入”指數呈現正相關關系,這一發現顛覆了“需求學派”的“人類偏好穩定性”假設。從供給的角度解釋,他認為,人類生育行為由如下三大因素決定:家庭對孩子的需求;家庭潛在生育率;節育成本。其中,家庭對孩子的需求取決于自身對孩子的偏好,同時也取決于家庭收入、撫養孩子的成本等經濟因素;家庭的潛在生育率主要取決于父母的生育能力和其所處社會對生育行為的規范;節育成本則取決于節育帶來的心理不適成本和實際開銷。在這三大因素下,家庭進行生育決策。若家庭的潛在生育率低于家庭對孩子的需求,則會出現生育需求過剩,此時,家庭不需要進行節育措施,他們會通過收養子女或者加大對已有子女的花費,以滿足其生育需求。若家庭潛在生育率高于其對子女的需求,那么該家庭便出現生育供給過剩,此時,家庭會采取相應的節育措施,以保證實際子女數與其期望相吻合。(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參考文獻:
[1]Gary S. Becker, Nigel Tomes,1976, 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23
第8篇: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中國的鄰邦日本正在遭受“人口少子化”的困擾。1989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57,被稱為“1.57危機”。2005年,這一數字下挫到1.08,日本媒體驚呼“少子化已達危害國家興衰的地步”。與此同時,在人口眾多的中國,少子化問題也日漸浮現。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的總生育率僅僅為1.18。另據統計,今年高考報名人數900萬人,是2008年以來連續下降的第四個年頭。報考人數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出生率下降。數據表明,2008年是18歲適齡人口的拐點,隨后快速下降。
從人口學理論分析,適度、理想的低生育率被稱為“更替水平”,也就是總和生育率在2.0左右。這一數字在1.5以下的為“很低生育率”,1.3以下的為“超低生育率”,1.0以下的為“災難性低生育率”。“目前我國一些超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的生育率都在1.0以下。”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說。專家分析,中國的少子化呈現出三大特點:一是發展速度極快,而且不存在城鄉差異。二是“未富先老、未富先少”。三是少子化問題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說:“如果不采取措施及時應對‘少子化’,真的等到十幾、二十年后風險集中凸現時,局面將難以挽回。”(見《瞭望》,楊琳/文)
學問學問,學本乎問
凡是教過幾天書的人都知道,現在的學生真是不會問問題——別說主動問老師問題了,就是老師提問,愿意主動回答的都沒有幾個。學問學問,學本乎問,非問無以成學。可惜現在的教學,往往只顧“學”而置“問”于不顧。原因很簡單:所謂應試教育,只需要把考題答準答對即可,而考題的標準答案都在教科書與老師講義之中,學生需要做的只是將其記下背熟,哪需要“問”的環節?
超級中學:一將功成萬骨枯?
每一個地方都有這樣一所神一樣的中學,它們壟斷了當地最優質的師資和生源,是重點大學甚至北大清華的保障,用流水線的模式輸出流水線型的大學生,滾雪球般積累名氣,使之處在教育資源“食物鏈”的頂端。它們是:廣東華師附中、河北衡水中學、重慶巴蜀中學……
這些被媒體和網民稱為超級中學的學校,其生源一部分是本市戶口的考生,另一部分則從周邊地區吸引而來。這類中學的數量不多,卻幾乎壟斷了其所在地區的優秀生源和教師,加之高昂的教育經費和政策支持,以及連年優異的高考成績,在當地往往擁有極大的影響力。
新浪微博之上,有網友總結超級中學的三個基本特征:人數以萬計,壟斷尖子生,比拼升學率。
在一些教育工作者眼中,這三樣特征已經形成了一個馬太效應。“因為升學率高,自然能吸引越來越多的學生擠破頭想進校,學生多了,尖子生就多,升學率穩步上升,名氣越來越大。”遼寧省實驗中學一位高級教師向記者解析道。
在名氣與光環的背后,超級中學開始暴露出一系列弊端。對于同區域的其他學校而言,超級中學的存在,正在不斷壓榨它們的發展空間。
“好老師我們學校也有過,但留不住,那些名校隨便開一個條件,我們都給不起。”北京市密云區一所中學的校長說,學校的一名年輕教師,剛剛得獎有了些名氣,便很快被挖走,“這些年走了不下十名好老師,幾乎每年都有走的。”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云杉認為,農村孩子很難進入這些猶如航空母艦的超級中學,“馬太效應導致強校越來越強,匯集優秀生源、師資與教學條件,且重心上移,向省會等大中城市聚集。這導致在考分上具有競爭力的農村生源減少了,在中小學教育中,能獲得優異學業成就的農村學生減少了”。
超級中學引發的種種弊端已經引發人們的反思。今年兩會上,聲討超級中學的聲音不絕于耳。著名學者楊東平更是撰文總結了超級中學的五宗罪過:一家獨大、損害公平、助長應試教育和升學率評價、收取高額擇校費、存在教育隱患。楊東平認為,超級中學是違反教育規律、有害無益的。它高揚的是應試教育的價值,延續的是“效率優先”的“教育產業化”路線。
第9篇:影響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學齡人口;農村教育;影響;對策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2-0037-03
學齡人口是指符合入學年齡6~7歲到青春期即十四五歲左右前的所有人口。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農村學齡人口開始逐漸減少,在校生減少,各地大量撤并小學。據教育部公布的統計數據,從2000―2010年,中國農村小學數量十年內減少了52.1%,統計各省區市教育主管部門公布的數據,從2001―2011年,初中數量下降26.19%。這種現象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反映了學齡人口的變動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沖擊,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
一、近年農村學齡人口的變動及原因
(一)近年來農村學齡人口變動的狀況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發展,中國的人口實現了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的傳統模式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現代模式轉變,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連續多年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進入了低生育率時代。中國的生育率由1970年的5.80‰,下降到1980年的2.24‰。進入90年代以后,1990年中國進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時發現生育率僅為2.11‰,而到2001年則為2.01‰,已經降到了人口更替水平以下,以后歷年的生育率也都逐年下降。很顯然中國的生育水平已經進入了低生育水平的行列。
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必然導致農村學齡兒童的大幅減少。從近年來的數據統計可以看出,近年來中國學齡兒童在逐步減少,2005年達到高峰,此后開始大范圍下降,農村學齡兒童的減少應是一種普遍趨勢,
(二)農村學齡人口變動的原因
1.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前中國人口以驚人的速度增長,給經濟、資源和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迫于人口的壓力,從70年代起,中央提出了“晚、稀、少”的具體政策,在全國城鄉普遍推行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有效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有統計稱,1971―2005年間,由于實行計劃生育,全國少生了約4億人,出生率下降到1.8%。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中國農村人口的生育率開始下降,學齡人口逐步減少。
2.農村人口流動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的家庭承包制極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農業生產邊際效益開始遞減,農村出現了大量剩余勞動力。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勞動力開始大規模向效益更好的城鎮轉移,形成了持續不斷的農村人口流動潮流。到2010年流動人口比例已達到16.53%。9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人口流動在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其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最顯著的結構變化是由分散的、跑單幫式的流動向家庭化轉變。農村的學齡兒童有相當一部分已在流入地即城鎮就近入學,這加劇了在農村接受基礎教育學齡人口的減少。
3.教育水平提高的影響。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婦女接受了教育,農村婦女的教育水平越來越高。一般而言,教育水平的高低因素會直接影響婦女的生育觀念,進而影響生育率,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教育水平越高的婦女,越有可能走出家庭參與工作,這樣挑起生兒育女和工作賺錢這一雙重負擔的可能性將降低;二是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婦女,更容易理解政府或其他機構計劃生育的呼吁;三是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更高,對孩子期望值更高的家庭,往往也是婦女教育水平較高的家庭,他們對孩子的成本―收益比率計算將會轉變,孩子成本成為影響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很多研究表明婦女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會越低。值得注意的是,丈夫的教育水平對妻子的生育水平有間接的影響。丈夫的教育水平越高,生育觀點會轉變得更快,也越能理解和接受計劃生育。因此,中國農村的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學齡人口因此而減少。
二、對農村基礎基礎教育的負面影響
(一)直接導致學校生源減少
農村學齡人口減少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學校生源的大幅度減少,特別是人口稀少的偏遠山區農村。一個班幾個學生,一個學校幾十名學生、不到10名的教師的現象在農村小學已司空見慣,更有甚者,校園荒草萋萋,教室屋檐群鳥棲息,眾多中小學呈空巢之象。相比城鎮,農村的教學資源明顯不足,在生源減少之前,一些地區教學所需要的基本設備,破舊落后甚至沒有,更別奢談圖書館、實驗樓、遠程教育等設設施,嚴重影響了農村教學質量的提高,到了更新換代的時候,但是由于在校學生的大幅度減少,學校規模變小,本來就緊張的教育資源和資金向規模小的這些學校投入可能性更小了,鄉村學校教學設備的建設和完善變得更加困難重重。與此同時,農村的教師缺乏,而且現有教師偏向老齡化,知識結構已不能滿足當代教育的要求,師資水平亟待提高。隨著學生的急劇減少,農村學校更招不到老師,師資嚴重不足,許多學校出現一個老師兼任全科,帶各個年級的現象,造成了農村少兒教育的先天性貧血。老師負擔重、身心疲憊,而且能力有限,制約教學水平的提高。這些問題加劇了教育的不平等性,影響了農村教學質量的提高,阻礙了學生的全面發展。
(二)影響了學生身心健康和正常的教學管理
學齡人口減少直接導致了學校生源不足,為了合理配置教學資源,增強教學的規模效益,客觀上要求對農村的學校重新布局調整,這也是符合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的。但在實際調整中,許多地方將調整簡單地理解為“撤并”,撤并過程中帶來了很多問題。
1.影響學生身心健康和學習。由于學齡人口減少,幾個學校撤并為一個服務半徑較大的學校,一些學生被迫轉入另一所學校,這使許多原本就近入學的學生增加了家校之間的距離。在這樣的情況下,部分學生選擇寄宿,另一部分由于種種原因未寄宿。對于寄宿的學生來說,他們年齡偏小,生活自理能力及自我約束能力較差,同時長期遠離父母,缺少父母的日常關愛和家庭教育,還要適應陌生的生活環境和人際圈的壓力,這是他們容易產生自卑、害怕、膽怯、孤獨等心理問題,甚至成為“問題學生”,從而影響了學生的學業。對走讀生來說,由于家校距離變遠,他們花在路上的時間和風險增加了,尤其是那些地處偏遠山區或交通極不便利的學生。由于每天花在路上的時間較長,學生的睡眠嚴重不足,長期以往,不僅影響了他們的身心健康,同時也對學習造成了很大的困擾。同時,在缺乏安全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的情況下,路途的增加會使學生的安全事故更容易發生。另外,由于家校距離太遠,中午不能回家,學生只能每天從家里帶午飯,或從學校附近小攤點買些廉價食品對付一頓,部分住宿生甚至要帶足一周的干糧。長此以往,很多學生患有營養不良或腸胃病,正常發育受到很大影響。
2.教學條件不達標,學校管理難度加大。幾個規模小的學校合并為中心學校后,學校規模變大,師生人數變多,班額增大。這就客觀上要求學校改善教學條件,加強學校的公共建設包括校舍、宿舍、食堂、浴室和活動場所等,但是教育經費卻跟不上。農村稅費改革以后,取消了農村教育集資和教育附加費,這兩項的減少直接導致了農村教育經費的短缺。農村學校公用經費普遍短缺,無法支付學校建設資金,致使硬件建設不達標,從而導致了寄宿條件質量低。同時,寄宿學生增多,而大多數學校專職管理人員偏少,現有管理人員缺乏必要的培訓和經驗,再加上校后勤配套設施滯后,無形中加大了管理的難度。另一方面,由于寄宿學生年齡偏小,轉校后心理問題突出,需要對他們進行心理輔導,但絕大多數學校缺乏心理輔導老師或心理老師太少,致使“問題學生”突出。
(三)增加了農民的教育負擔
伴隨著學校的撤并,農民的教育費用也隨之增加。這些費用主要來自學生到較遠的學校上學中所需要的交通費、伙食費,住宿的學生還有住宿費以及購置被褥、餐具的費用,這些花銷加起來每學期要800多元。這對一般的農民家長來說,相當于一家人全年日常生活所有花銷的1~2倍。另外,孩子因為到較遠的學校上學而不能幫助家里做農活,對農民的家庭勞動收入也構成損失。除此之外,家長還要承擔由于家校距離遠導致的孩子安全問題的心理負擔,同時還要付出接送孩子上學放學的時間成本和體力成本。農民的教育負擔加重,會影響對學生的教育投資,對學生的長遠發展不利,加大了貧困家庭學生的輟學概率。
(四)農村教學點教育資源浪費,生均教育成本提高
由于教育設施具有穩定性和滯后性,在短時期內某一地區某一學校很難在教育硬件(如校舍)軟件(如人力)及學校規模和容量上有較大變動,但學齡人口變動特別是在數量上在短時期內變化較為明顯和劇烈。一方面,在學齡人口不斷減少的趨勢下,校均規模和人均班額也會不斷變小,而原有的學校規模及布局是在以前學齡人口較多的情況下建設的,當學齡人口波峰過去,波谷來臨時,就會出現教育資源的過剩,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有多余的教師和閑置的教室。當原有的學校被撤并之后,這些學校就直接被棄置,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損失。另一方面,學齡人口的減少,使得教師、學校各類資源相對過剩,導致生均教育成本提高,無法實現教育資源的濃縮效應。所謂濃縮效應,學者認為,出生人數減少,無論是從家庭還是社會的角度看,教育投資更加集中,生均教育經費增加,這就是人口轉變的教育投資的“濃縮效應”。就教學點學齡人口數量來講,無疑應是發揮教育投資濃縮效應的最佳條件因為就讀人數少了,分攤在每一學生身上的投資應多了。但是,教學點的資源特別是硬件設施卻是閑置在那里,無法利用在學生身上,實際上是一種嚴重的浪費,農村生均教育成本無以提高。
三、對策
(一)堅持以人為本,合理布局教學點
由于學齡人口減少導致了農村學校“撤并”之風,造成了許多問題,損害了學生和家長的利益,違背了就近入學的原則。為了提高農村的教育質量,農村學校布局調整要科學規劃、因地制宜,避免在調整中的“一刀切”現象。在布局教學點時在偏遠山區或交通極不便捷的地方適量保留教學點。同時新學校的服務半徑確定要合理,結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充分考慮財力支付、校舍建設、食宿配置建設等狀況,不能因為生源不足多少就硬性撤并,不具備條件的,應該適當延緩撤并。
(二)保障教育投入,改善辦學條件
政府應該安排農村學校布局調整專項資金,對農村基礎教育進行特殊照顧,在制定布局調整和政策安排資金方面要有所傾斜,保證合并后的學校教育經費能及時跟得上。同時,原有的教學點也要適當地投入資金,特別是在教師方面,適當提高農村教師的工資,在偏遠山區要加大遠程教育的投入。另外,應加大對貧困學生的教育補助,不應把改革的成本轉移到弱勢群體身上。
(三)加強監管,合理利用撤并后的校產
農村中小學撤并后閑置的校園校舍要首先考慮改建成規范化的幼兒園或學前班,也可將閑置的校園校舍改建成向農民宣傳國家方針政策和傳播科學知識、實用技術、致富信息的場所,成為開展農村文化娛樂活動和政府部門組織科技培訓的基地,繼續發揮其農村文化陣地的優勢。有些地方還可考慮將校舍變賣后買校車,用來接送孩子到中心小學上學。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后,對撤并學校的教職員工要統籌考慮,統一調配,符合條件的及時安置,不符合條件的要通過培訓、轉崗等辦法,及時給予妥善安排,盡全力保證教師資源的充分利用。
參考文獻:
[1] 田家盛.教育人口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17.
[2] 田寶宏.學齡人口變動對基礎教育的沖擊與應對[J].中州學刊,2009,(5).
[3] 蒯鵬州.學齡人口減少及其對教育發展的影響[J].西北人口,2012,(5).
[4] 王穎,楊潤勇.新一輪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后的負面效應:調查反思與對策分析[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8,(34).
- 上一篇:實施雙減政策的意義范文
- 下一篇:醫療衛生發展前景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