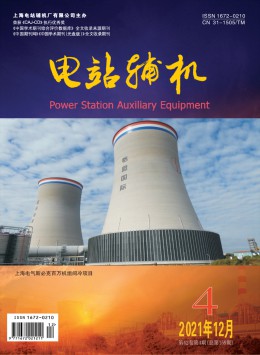關于醉駕的處罰規定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關于醉駕的處罰規定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關于醉駕的處罰規定范文
法律與政策精神
袁彬(以下簡稱“袁”):醉駕入刑是我國為有效維護道路交通安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而進行的重要刑事立法。觀察醉駕入刑一年來的法律實踐發現,各地對醉駕入刑的精神理解不一,進而導致司法尺度的較大差異。請問趙秉志教授,您如何看待醉駕入刑的法律與政策精神?
趙秉志教授(以下簡稱“趙”):醉駕入刑是我國在酒駕、醉駕肇事案件多發頻發背景下采取的重要立法舉措,既體現了我國嚴懲醉駕的法律精神,也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精神。
首先,醉駕入刑體現了我國嚴懲醉駕的法律精神。嚴懲醉駕是《刑法修正案(八)》的重要立法精神:一方面,《刑法修正案(八)》將原本作為行政違法行為處理的醉駕升格規定為犯罪,擴大了犯罪圈,表明了我國從嚴懲治醉駕的法治立場。另一方面,《刑法修正案(八)》對醉駕入刑的設定體現了嚴懲醉駕的精神。對比《刑法修正案(八)》第22條的規定可知,我國對醉駕行為人罪和飆車行為入罪采取的是不同的標準。其中,飆車行為必須“情節惡劣”才能入罪,而醉駕行為入罪則無此要求。
其次,醉駕入刑貫徹了我國寬嚴相濟的基本刑事政策。雖然從總體上看,我國對醉駕行為采取的是從嚴懲治的態度,但這并不意味著對醉駕的懲處要一味從嚴。事實上,作為《刑法修正案(八)》的基本政策指導,醉駕行為的入罪標準和刑罰設置都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司法實踐中,對于那些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醉駕行為,可依照《刑法》第13條“但書”的規定作無罪處理;對于那些構成犯罪但沒有必要予以刑罰處罰的醉駕行為,可依照《刑法》第37條的規定,作定罪免刑處理;對于那些構成犯罪應予處罰但存在從寬情節的醉駕行為,則可作緩刑或輕刑化處理。而對于那些構成犯罪并且情節嚴重的醉駕行為,應依法處以較重的刑罰;對于醉駕犯罪案件中構成其他嚴重犯罪的,則應注意以重罪論處或數罪并罰。
二、醉駕應否一律入罪
袁:關于醉駕應否一律入刑,我國刑法理論界與實務界一直都存在較大爭議。醉駕入刑一年來,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不少對情節顯著輕微的醉駕案件不入罪的做法,于是乎在理論上和實務中又出現了強烈的對醉駕行為應一律入刑的主張。對此,您怎么看?
趙:一年來的實踐表明,醉駕的情形多種多樣。不同情形的醉駕,其社會危害性也各不相同。對醉駕應根據其情節的不同區別對待,而不應一律入罪。從理論上講,對醉駕行為不應一律入罪也是有充分根據的。
第一,《刑法》第13條的“但書”決定了醉駕不應一律入罪。《刑法》第13條的“但書”規定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就要求司法機關在判斷醉駕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時,除了根據犯罪構成要件加以認定外,還必須考慮包括犯罪情節在內的所有要素對相關法益所造成的侵害或威脅是否屬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而不能因為《刑法修正案(八)》第22條沒有為醉駕入罪設定情節限制,就突破《刑法(總則)》第13條“但書”的規定一律人罪。
第二,危險駕駛罪的公共安全客體決定了醉駕不應一律入刑。按照我國犯罪構成理論,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須以侵害或威脅《刑法》所保護的法益為前提,不具有法益侵害性或威脅的行為是不能被認定為犯罪的。醉駕行為要構成危險駕駛罪,就必須在客觀上對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了威脅。
第三,刑法的威懾性決定了醉駕不能一律入刑。刑法的威懾性是在《刑法》的實施過程中,社會公眾所表現出來的因懼怕犯罪及其懲罰后果而產生的威嚇、震懾作用。醉駕入罪的威懾性取決兩個因素:一是有罪必罰,即對威脅公共安全的醉駕行為,要及時、準確地予以懲治,不能使任何具備危險的醉駕行為逃脫法律的制裁,打消醉駕避刑的僥幸心理;二是罰當其罪,即只能對已經造成公共安全危險的行為予以懲治,區分一般行為的危險性與具體行為對法益的抽象威脅,正確打擊犯罪,使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不被認定為犯罪,以保證《刑法》的公正性。唯有如此,借助刑法手段打擊醉駕行為才能實現良性治理的目的;否則,就有可能陷入“嚴打”的怪圈,失去刑罰懲治的可持續性。
第四,對醉駕行為不一律入罪并不會導致醉駕的刑事處罰與行政處罰的脫節。我國2011年4月22日通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調整了對醉駕的行政處罰,取消了拘留和罰款,僅規定了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但是,該法對酒后駕駛則保留有拘留和罰款的行政處罰。不過,考慮到醉酒駕駛的標準高于酒后駕駛,只要行為人的行為達到醉酒駕駛的標準,自然也達到酒后駕駛的標準,而且醉酒駕駛的危害性要大于酒后駕駛,因此對酒后駕駛可以予以拘留、罰款的處罰,對醉酒駕駛當然更可以予以拘留、罰款的處罰。對醉駕行為不一律入罪并不會導致醉駕的刑事處罰與行政處罰的脫節。
袁:醉駕入刑一年來。各地對醉駕入罪的具體標準掌握不一。您覺得應如何理解醉駕入刑的情節和正確運用醉駕入刑的追訴標準?
趙:對醉駕行為不應一律入刑,但這并不意味著大量醉駕行為可以不入罪。醉駕入刑一年來的實踐表明,不入刑的醉駕行為應當是少數,大量醉駕行為均已入刑。
首先,要正確理解醉駕人刑的情節規定,將大量醉駕行為入刑。根據犯罪情節的嚴重程度和我國《刑法》分則的具體規定,我國一般將犯罪的入罪情節區分為“情節惡劣”(或稱“情節嚴重”)、“情節一般”和“情節顯著輕微”三個層次。其中,《刑法修正案(八)》第22條規定,飆車入罪必須達到“情節惡劣”的程度,“情節一般”和“情節顯著輕微”的飆車行為當然不應入罪。但該條對醉駕入刑則沒有明確的情節限制。據此,除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醉駕可依照《刑法》第13條“但書”的規定不入罪,“情節一般”和“情節惡劣”的醉駕行為則均應入刑。醉駕應入罪的范圍要明顯大于飆車。
事實上,現實中發生的大量醉駕都是屬于“情節一般”的醉駕。如從醉酒程度上看,有統計發現,78.43%的醉駕者的血液酒精濃度是在100-200mg/100ml,只有20%多的人是處于這一區間之外。在機動車的類型上,有統計發現,兩輪摩托車占到了醉駕案件的60%。單純從醉酒程度、機動車類型因素上看,這些醉駕都屬于情節一般的醉駕,是醉駕的主要類型。而根據社會經驗法則,在“情節顯著輕微”、“情節一般”和“情節惡劣”三個層次中,“情節一般”作為中間層次所占的比例通常會比較大。司法機關應當將大量醉駕行為入刑,只有少量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醉駕行為依法才不入刑。
其次,要正確運用醉駕人刑的追訴標準。一是公安機關在相關執法活動中應當將大量醉駕行為(包括情節嚴重的和情節一般的)都納入刑事立案的范圍,只有少量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醉駕行為才不予刑事立案。二是在追訴過程中,根據犯罪的具體情節和案件的證據,可對少量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醉駕行為不或者不定罪,但大量的醉駕行為都應當被、被定罪。即便是被告人已經死亡的醉駕案件,從保護被害人利益的角度,也可對醉駕行為做一定的定性處理,以方便被害人行使民事賠償權。三是對需要定罪的醉駕行為,亦可根據案件的情節和被告人的悔罪表現等,對少量危害不大的醉駕行為人適用緩刑或者免刑。不過,對醉駕行為適用緩刑或者免刑應當慎用,適用的數量不應過多、幅度不宜過大。據有關報道稱,在安徽某地法院判決的25起醉駕案件中,被告人均被適用緩刑,比例為100%。廣東、安徽、重慶、云南適用緩刑的比例超過40%,部分城市人民法院判決緩刑的比例高達73%。這種做法顯然不妥。醉駕本來就屬于輕罪,刑罰很輕,如果再大量適用緩刑或者免刑,將會極大地削弱《刑法》的威懾力,影響其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因此,對醉駕案件應當慎用緩刑,更要慎用免刑。
三、醉駕的標準及其適用
袁:根據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2011年7月1日實施的《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我國對醉酒主要是采取血液、呼氣酒精含量檢驗,即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屬于醉酒駕駛。此外,對于血液中酒精含量沒有達到飲酒駕車血液酒精含量值的車輛駕駛人員,或者不具備呼氣、血液酒精含量檢驗條件的,應進行唾液酒精定性檢驗或者人體平衡的步行回轉試驗或者單腿直立試驗,以評價駕駛員的駕駛能力。對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趙:我國現行的醉酒標準是在大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參考了一般國民對酒精的耐受狀況而作出的,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對于該標準的適用,在實踐中應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是醉酒的形式標準,同時也是一個絕對標準。客觀地看,受生理因素的影響,不同人對酒精的耐受性并不完全相同。同樣是血液酒精含量達80mg/100ml以上,對有的人的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可能并無多大影響;但對其他人則可能導致嚴重的行為失調。因此,單純以血液酒精含量作為醉酒的標準,并不能真實地反映飲酒量對人的影響情況。不過,醉酒的形式標準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和普遍適用性,因而為許多國家和地區所采用。我國亦不例外。
第二,血液酒精含量的計算時間應以檢驗時為準,不必考慮酒精的清除情況。一般而言,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會因時間的延長而逐漸消除。實踐中,醉酒駕駛從飲酒結束到其危險駕駛行為被查獲及至酒精檢驗,通常都要經歷一段時間,有的要經過好幾個小時(甚至有隔夜被查的)。在此情況下,檢驗時的血液酒精含量與駕駛時的血液酒精含量可能會有較大的差異。在實踐中可能出現行為人駕駛時處于醉酒狀態,但被查獲時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經降至醉酒標準以下了。不過,由于我國目前的酒精檢驗標準并沒有要求考慮酒精的清除情況,對此不能認定為醉駕。
第三,對駕駛人員進行步行回轉試驗或者單腿直立試驗的前提是駕駛人員的血液酒精含量檢驗沒有達到飲酒駕車血液酒精含量值或者所在地方不具備呼氣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這是人體平衡試驗在駕駛能力測試中適用的限制,其根本在于該測試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在證據固定上容易產生系列問題。目前我國很少采取這種方法檢驗駕駛人員的駕駛能力。不過,既然我國規定了這種人體平衡實驗,在一定條件下,我國仍可對駕駛者進行該試驗,以認定其駕駛能力。
袁:當前我國交警部門在處理醉駕時通常要對駕駛人員進行兩次酒精檢測,即先進行呼氣酒精含量檢驗,如果呼氣檢驗結果達到或者接近醉酒標準,再對駕駛人員進行血液酒精含量檢驗。由于兩種檢驗在方法上存在一定差異、在時間上存在一定間隔,因此實踐中有時會出現呼氣酒精檢驗與血液酒精檢驗結果相沖突的情況。對此,您覺得該如何處理?
趙:一般而言,呼氣酒精含量檢驗結果與血液酒精含量檢驗結果的沖突主要有三種表現:一是兩種檢驗結果均達到了醉駕的程度,但呼氣酒精檢驗值與血液酒精檢驗值存在較大差異;二是呼氣酒精檢驗結果達到了醉酒的程度,但血液酒精檢驗結果沒有達到醉酒的程度;三是呼氣酒精檢驗結果沒有達到醉酒的程度(如僅為飲酒后駕駛),但血液酒精檢驗結果達到了醉酒的程度。在這三種情況下,采用何種檢驗結果作為認定行為人醉酒的依據,會直接影響醉駕的認定與量刑。對此,司法實踐中尚無統一的標準,我認為,應當以血液酒精含量檢驗結果為準。這是因為:
第一,血液酒精含量檢驗結果比呼氣酒精含量檢驗結果更準確。按照我國《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的規定,血液酒精含量檢驗是直接檢驗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而呼氣酒精含量是檢驗駕駛人員呼氣中的酒精含量,然后按照1:2200的比例將其換算成血液酒精含量。對此,有觀點認為,“呼氣”檢驗的準確性不如血液檢驗。而在涉及違法者將面臨刑事處罰的嚴重問題時,做不到絕對準確的“呼氣”檢驗結果不能成為法庭定案的關鍵證據。我認為,這一觀點有道理。從準確確定行為人責任的角度,應當以血液酒精檢驗的結果作為認定醉酒的最終標準。
第二,血液酒精含量檢驗更契合我國《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的規定精神。關于醉酒的標準,《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規定的是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該標準明確了血液酒精含量是確認醉駕的標準。雖然呼氣酒精含量標準可轉換為血液酒精含量標準,但從對應關系上看,血液酒精含量檢驗結果與《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的醉酒標準具有更直接的對應關系。
第三,血液酒精含量檢驗的程序要求更嚴格,證據效力更高。《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明確規定了血液酒精含量檢驗必須出具書面報告,但對呼氣酒精含量檢驗則沒有這一要求。此外,血液酒精含量檢驗的要求更為嚴格。需要有專業的采血人員、采血器具,也有專門的檢驗規程。血液酒精含量檢驗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其證據效力較之于呼氣酒精含量檢驗更高,自然應當以血液酒精含量檢驗結果為準。
袁:一年來的實踐發現,我國一些地方存在著駕駛人員逃避酒精檢驗的情況,如有的駕駛人員逃避任何酒精含量檢驗,也有的駕駛人員在呼氣酒精含量檢驗后逃避血液酒精含量檢驗。對此,您覺得該如何處理?
趙:對于你說的上述第一種情況,由于我國沒有像有的國家或者地區將逃避酒精含量檢驗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因此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只要駕駛者沒有采取暴力、威脅等方法逃避酒精檢驗并因而構成妨害公務罪,就無法追究駕駛者逃避酒精含量檢驗行為的刑事責任,并且一般情況下也難以追究其醉駕的責任。但如果駕駛者歸案后作了醉駕的如實供述,如供認喝了大量的酒,足以達到醉酒的標準,或者有其他的人證、物證等證明其大量飲酒并酒后駕車,整個證據能夠相互印證,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則也可以審慎地以危險駕駛罪追究其醉駕的刑事責任。
對于你說的上述第二種情況,由于已經對駕駛者進行了呼氣酒精含量檢驗,因此雖然駕駛者逃避了之后的血液酒精含量檢驗,但也可對其按照現場呼氣酒精含量檢驗的結果追究其醉駕的刑事責任。對此,我國一些地方司法機關已經形成了共識,即經呼氣酒精含量檢驗達到醉酒標準的犯罪嫌疑人,因逃脫而無法抽取其血樣進行血液酒精含量檢驗的,一律按照現場呼氣酒精含量檢驗的結果追究其刑事責任。這一做法是合理的。駕駛者的呼氣酒精含量檢驗結果達到了醉酒的標準,就符合醉酒駕駛的規定,當然可以追究其醉駕的刑事責任。
袁:一些駕駛者為逃避法律的制裁,在查處醉駕的現場故意喝酒,干擾交警人員的酒精檢驗。對此,能否因其酒精檢驗結果達到了醉酒標準而追究其刑事責任?您如何看待此種情況?
趙:顧名思義,醉駕是指行為人在醉酒的狀態下駕駛機動車。如果行為人駕駛時沒有醉酒,但在駕駛之后、酒精檢測之間喝酒,進而導致酒精檢測時達到醉酒程度,通常情況下是不能據此追究駕駛者危險駕駛罪刑事責任的。但在實踐中,一些駕駛者為逃避法律的制裁而在查處醉駕的現場故意喝酒。對此,我國有的地方司法機關為了防止駕駛者逃避法律制約,明確規定:司機如果故意現場喝酒,根據呼氣酒精含量檢驗和血液酒精含量檢驗結果,達到醉酒標準的,一律按醉酒駕駛機動車追究其刑事責任。
對此,我認為是恰當的:一方面,駕駛者在查處醉駕的現場當場喝酒,可以直接推定其駕駛行為屬于飲酒后駕駛或者醉酒駕駛;另一方面,既然現場的呼氣酒精含量檢驗和血液酒精含量檢驗的結果已經表明駕駛者達到了醉酒的程度,那么這表明駕駛人員的行為已經符合了醉酒駕駛的條件,且這種狀態是行為人自己造成的,當然可以追究其危險駕駛罪的刑事責任。反之,若對這類駕駛者的行為不以危險駕駛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的話,那么將導致危險駕駛罪規定的虛置,無法發揮其應有效果。
四、醉駕之刑罰處罰與行政處罰的合理協調
袁:為了完善醉駕的法律懲治,2011年4月22日修訂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加重了對醉駕者吊銷駕駛證的行政處罰,但也取消了醉駕的罰款和行政拘留。對此,您覺得應如何進一步加強醉駕的刑事處罰與行政處罰的銜接與協調?
趙:為了加強對醉駕的懲治力度,2011年4月22日修訂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調整了對醉駕的懲治力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加強了對醉駕者吊銷駕駛證的處罰。該法第91條規定:“醉酒駕駛機動車的,南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五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醉酒駕駛營運機動車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十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后,不得駕駛營運機動車。”“飲酒后或者醉酒駕駛機動車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并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吊銷機動車駕駛證,終生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
事實上,關于對醉駕者吊銷駕駛證,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審議過程中,曾有人主張對危險駕駛犯罪增設資格刑,在《刑法》中規定吊銷醉駕者一定期限的駕駛證甚至終生禁駕。這也是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普遍做法,如英國《1991年道路交通法》規定,因醉酒或吸毒陷于不適宜狀態而駕駛車輛的,剝奪駕駛的期限不少于2年。在我國香港地區,兩次或者多次實施醉酒駕駛犯罪的,一般要吊銷不少于2年期限的駕駛執照,并處罰金。不過,考慮到《刑法》內部的協調(主要是《刑法》總則與分則的關系協調)等問題,《刑法修正案(八)》仍然沒有對危險駕駛犯罪規定剝奪一定期限或終身駕駛資格的資格刑。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刑法》對包括醉駕在內的危險駕駛犯罪的打擊力度,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刑法》對危險駕駛犯罪的預防功能的實現。因此,修訂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專門針對醉駕規定了吊銷駕駛證,是對《刑法修正案(八)》關于危險駕駛犯罪規定的補充和配合,能夠彌補《刑法》關于危險駕駛犯罪資格刑缺失的缺陷,有利于促進《刑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在懲治和預防醉駕方面的配合,提高其防治醉酒駕駛的效果。為此,我國應當加強對醉駕刑罰處罰與行政處罰的配合與銜接。根據醉駕的車輛是否屬于營運車輛、駕駛行為是否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等情況,無論醉駕是否構成刑事犯罪都應當南交通行政管理部門吊銷醉駕者的機動車駕駛證,并限制其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以強化醉駕的法律治理。
五、改善醉駕入刑的司法適用
袁:一年來,醉駕入刑的法律適用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和法治效果,但也存在一定問題,影響了醉駕入刑規定的正確實施。您覺得應如何進一步完善我國醉駕的司法適用?
趙:自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醉駕入刑的規定實施至今,一年來,我國公安司法機關始終保持對醉駕整治的必要力度和聲勢,醉駕入刑的法治效果顯現,交通安全形勢明顯好轉。據公安機關統計,“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20日,全國公安機關共查處酒后駕駛35.4萬起,同比下降41.7%。其中,醉酒駕駛5.4萬起,同比下降44.1%。”“北京、上海等地查處的酒后駕駛和醉酒駕駛數量,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分別在50%、70%以上。”這是十分可喜的法治成效。不過,一年來的執法和司法實踐也發現,醉駕入刑的適用仍存在許多難題,有待于進一步改善相關司法。
一是要正確區分醉駕行為構成的不同犯罪的界限。合理區分犯罪的界限是正確定罪量刑的基礎。對醉駕行為的犯罪界限而言,一方面,要根據醉駕者的主觀心態和客觀危害,正確區分醉駕行為所可能構成的危險駕駛罪、交通肇事罪以及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尤其要避免僅根據行為的危害后果,不當地擴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適用范圍;另一方面則要正確運用罪數理論,合理區分醉駕行為和以醉駕方法或在醉駕被查處時實施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妨害公務等犯罪,正確衡量應從一重罪處斷的情形和應數罪并罰的情形,以免放縱犯罪或處罰不當。
二是要合理把握醉駕入刑的刑罰尺度。對醉駕的治理除了要準確認定醉駕的行為性質,還要根據案件的具體情節合理確定其刑罰尺度。對此,一方面,對某些具有特殊身份者的醉駕行為,如對公務員尤其是公安司法人員醉駕,可以適當從重處罰;另一方面,對多次醉駕、醉駕再犯亦應當適度從重處罰。目前,我國對危險駕駛罪規定的最高法定刑是拘役,單純的醉駕者一般無法構成累犯(除了醉駕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外)。但實踐中的確存在不少屢教不改、多次醉駕的情況,對這類醉駕,應考慮其所具有的較嚴重的人身危險性而對其適當從重處罰。
三是要正確看待醉駕入刑的法律效果。與其他許多犯罪相比,醉駕在行為的查處和防治上具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醉駕者一旦駕車上路,其行為是否被查處往往不受其控制,被查處的幾率很高。醉駕行為被查處的高風險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治理醉駕的執法效果,削弱了醉駕者的僥幸心理。也正因為如此,隨著醉駕治理的深入,“開車不飲酒、飲酒不開車”的觀念才會日益深入人心。因此,從提高醉駕行為防治法律效果的角度,我國應當繼續加大醉駕的執法與司法力度,尤其是針對醉駕行為高發的特定時期、特定時間段(有統計顯示,68.63%的醉駕是發生在晚上6點至11點之間),更要加大醉駕的執法力度,嚴格執法。
四是要正視醉駕入刑的地方差異。目前,我國大多數地方都較好地貫徹執行了醉駕的法律規定。不過,一些地方在醉駕的執法力度上還存在一定的差別。總體而言,大中城市的醉駕執法狀況相對較好,小城市、城鎮和農村的醉駕執法狀況則相對較差,存在一定程度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而同一地區不同時期的執法和司法狀況也存在一定的區別。醉駕入刑的這種地方差異極大地損害了醉駕入刑規定的實施和法律效果的實現,因而有必要對各地醉駕入刑的實施情況進行實證調查,并在此基礎上對小城市、城鎮和農村查處醉駕的情況從宏觀上進行引導、糾偏。
五是應及時制定相關司法解釋或規范性文件。為了更好地貫徹醉駕入刑的精神和法律規定,糾正偏差,實現醉駕入刑的公正、統一執法和司法,進一步提高醉駕入刑的法治效果,我國應當及時出臺醉駕入刑的司法解釋或者規范性文件,細化法律的操作規范,對各地醉駕入刑的做法進行引導。并促使不斷加大執法與司法力度,積極發揮醉駕入刑的威懾作用。六、醉駕入刑的立法完善
袁:在《刑法修正案(八)》的研擬過程中,曾有觀點主張將吸毒后駕駛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一年來的司法實踐也發現,現實中的確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吸毒后駕駛等危險駕駛行為現象。您覺得,將來我國應如何進一步完善醉駕入刑的立法?
趙:客觀地說,醉駕入刑是我國《刑法》應當前社會發展的需要,積極加強對醉駕懲治與防范的體現。目前來看,醉駕人刑已經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不過,醉駕入刑是在現行立法框架下的酌情選擇。結合醉駕入刑的司法實踐,從長遠的角度看,我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醉駕人刑的立法:
第一,在對象上,將駕駛的對象由機動車擴大至機動車、船只或者航空器等。目前,我國危險駕駛的對象僅限于機動車。其立法初衷是考慮到醉酒駕駛船只、航空器或者駕駛船只、航空器追逐竟駛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較少出現。但從立法的嚴謹性和司法實踐的角度看,我國應將危險駕駛(包括醉酒駕駛)的對象由機動車擴大至包括機動車、船只、火車和航空器在內等多種交通工具,以進一步嚴密我國刑事法網,提高醉駕人刑的法治效果。
第二,在情節上,將增加醉駕入刑的情節限制。對醉駕入罪應當增設一定的立法情節,一方面有利于從立法上區分道路交通管理違法行為與刑事犯罪行為的界限,防止醉酒駕駛的行為過度入罪,節約刑法資源;另一方面則有利于將醉酒駕駛的既遂形態由抽象危險犯轉變為具體危險犯,從而有利于更好地貫徹《刑法》的謙抑精神,對醉酒駕駛者予以合理的人權保障。因此,未來我國應對醉駕入刑增設情節的限制。
第三,在行為類型上,應增加與醉駕類似的危險駕駛行為。刑法立法既要考慮當前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也要保持適度的超前。除了醉酒駕駛、飆車之外,吸毒后駕駛、無證駕駛、駕駛不具備安全i生能的車輛、高速公路或單行道逆向行駛、單行道超速等行為的危害性并不亞于醉酒駕駛和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長遠地看,我國應將吸毒后駕駛等較為嚴重的危險駕駛行為入罪。
第2篇:關于醉駕的處罰規定范文
論文關鍵詞 醉駕犯罪 危險駕駛罪 量刑均衡 量刑標準
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各種人為的風險呈現快速上升及多樣化趨勢,從交通事故頻發、全民性食品安全問題到犯罪率攀升等,工業社會已經演變為風險社會。基于風險控制的考量,《刑法修正案(八)》增設了危險駕駛罪。實踐表明一年來醉駕入刑已初見成效。但也應看到,關于醉駕犯罪各種問題的討論一直沸沸揚揚,不難發現,醉駕入刑才一年多,司法實踐中關于醉駕犯罪的適用情況出現諸多問題,法律權威性受到了質疑。
一、問題呈現: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的量刑實況
盡管才歷經一年多,關于醉駕入罪后的司法現狀已經出現諸多問題。筆者經整理這一年醉駕案的司法裁判情況,發現主要存在如下問題:
(一)刑法對醉駕犯罪的法定量刑設置不盡合理
基于風險控制思想,為了有力遏制醉駕行為給整個社會帶來的潛在與已發生的危害性,具有謙抑性的刑法仍將危險駕駛行為納入刑法體系,可見立法的用心良苦。然而入罪一年來,關于醉駕犯罪的量刑設計過于單一而不符合此類犯罪情節多樣性的特征、法定量刑過輕導致法律效果不夠的質疑一直不斷。筆者經整理案例發現,現今醉駕量刑存在過輕問題,犯罪者的關于醉駕行為受到短短幾個月拘役的刑罰給其帶來影響不大的主觀認識大多存在,這樣的主觀認識意味著其再犯醉駕行為的可能性極大,當犯罪成本低于犯罪收益時,必將趨使犯罪者鋌而走險。
(二)相似案件犯罪人領刑結果不一甚至相差很大
如四川綿陽“醉駕第一人”王某某被判處拘役四個月、罰金2000元,檢測出的血液酒精含量為159mg/100ml;北京首例醉駕入刑的李某某則被判處拘役兩個月、罰金1000元,檢測出的血液酒精含量為159.6mg∕100ml。二人犯罪情節類似,血液酒精含量檢測結果也相差無幾,但兩人的領刑結果卻有較大相差(主刑相差兩個月,附加刑相差1000元)。
(三)各地法院對醉駕犯罪采納的量刑標準不統一
有的法院僅以血液酒精含量的高低為量刑標準,如四川富順縣首批醉駕入刑的李某、鄧某,被查獲時兩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檢測結果分別為168.65mg∕100ml和239.64mg∕100ml。法院則依據血液酒精濃度的高低確定量刑的高低。有的則不光考慮醉酒程度,還考慮其他情節。如天津“醉駕入刑”第一案的被告人李某某(血液酒精含量檢測結果為210.78mg∕100ml),東麗區法院鑒于其在歸案后能如實交代犯罪事實,認罪態度較好,且積極給予了民事賠償,故酌情從輕判處。
(四)各地法院對醉駕犯罪適用緩刑的情況各異
關于緩刑的適用,自醉駕入刑來各地法院一直做法不一。比如,北京、杭州等城市,已判決的醉駕犯罪案件實刑率分別達99%和95%以上,意味著這些地方被處以緩刑或者免刑的醉駕司機為極少數。而據報道,去年5月至今年2月,合肥市廬陽區檢察院共辦理27起醉駕案,在已判決的25起案件中,被告人均被適用緩刑;從去年5月1日至10月10日,廣州全市法院審結的50起醉駕案中,18人被判處緩刑,2人免于刑事處罰,適用緩刑案件占已判決案件的36%。去年第四季度,廣東全省醉駕案件的緩刑與實刑之比已超過1:1。各類法院對醉駕犯罪類似情節卻實刑不一,有違量刑均衡。
二、分析反思:醉駕型危險駕駛罪量刑不均的現實考量
“在一定社會歷史文化條件中同一罪名下的司法裁判活動,能否體現出時空上的一貫性、一致性,這是罪刑均衡的起碼條件。”而針對醉駕犯罪在實踐中量刑不一的情況,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
(一)立法不周密及司法解釋滯后
立法是量刑公平的基礎。我國刑法長期以來受到宜粗不宜細立法思想的影響,法條過于簡略、籠統、抽象,法官被賦予較大自由裁量權,而相應的司法解釋又存在不及時、不系統、不具體情況,“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沒有缺陷,因此,發現法律的缺陷并不是什么成就,將有缺陷的法條解釋得沒有缺陷才是智慧。”就醉駕犯罪案件來說,立法對危險駕駛罪法定刑的設置方面、與其他罪的量刑銜接方面、涉及從重、從輕等多個量刑情節的,什么情況算“情節顯著輕微”可不追究刑事責任,什么情況適用緩刑、免刑,沒有相對統一的司法解釋及指導性案例進行規范。我國沒有判例制度,若司法解釋再無法與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現實發展同步,就會給刑事量刑自由裁量權的不正當使用或濫用留存較大的空間。
(二)風險控制思想促使裁判規范隨意性
在風險控制思想的指導下,危險駕駛罪是在突破刑法謙抑性的基本底線情境中,對社會中出現的尚未發生危險的“危險行為”予以懲罰的產物。與傳統的風險相比,風險控制視野下的“風險”具有獨特的性質,其正逐漸超越自然風險成為風險結構中的主導力量,在空間上現代風險具有全球擴散性,在時間上既有延展性,且風險影響途徑不確定,比如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危險駕駛罪等,很難預測此類行為可能造成危害的深度和廣度。因為風險本身的認定標準尚不明確,具體到危險駕駛罪,在其影響下,構成犯罪所需的危險駕駛行為造成的風險狀態依舊不清晰、不明確,由于本罪的立法有情緒性立法的嫌疑,本身就欠缺全面論證及理性和科學性,再基于風險控制思想對刑法謙抑性突破的沖動本性,使得司法實踐對認定危險駕駛罪易出現較大的隨意性,也由此直接導致了關于危險駕駛罪裁判規范構建的隨意性。
(三)無統一的量刑標準和規則
由于沒有統一的量刑標準和規則,法官在法定刑幅度內行使量刑自由裁量權時會產生操作上的困擾,難免出現量刑偏差。同時,即使法院的量刑出現偏輕偏重情形,檢察機關也無準確依據對其量刑行使法律監督權,而公眾更無從評價。司法實踐中,審判機關對醉駕的基礎量刑標準都尚未達成一致意見,至于類似“情節惡劣”等字眼更是模糊的概念,舉例來說,在醉駕案件中,犯罪者被判處拘役的時間從一個月到六個月的都有,審判機關量刑的依據不一,有的以機動車的車型不同,來確定基準刑期,有的則以犯罪人血液酒精含量濃度的高低來確定,有的則綜合考慮醉駕者犯罪的各方面情節因素。對于具有相似犯罪情節的醉駕者,被判處一個月和被判處六個月的都是在法律規定量刑幅度內判決的,應該說是合法的,但是否合理呢?對此并沒有統一的標準可以評價。
三、解決進路:從立法與裁判規范兩層面進行補充完善
由于刑罰是一種必要的惡,所以量刑的程序和結果是否公正,不僅關系到人們對國家動用刑罰的正當性評價,也體現出一國立法和司法審判的技術程度。
(一)立法規范層面上醉駕型危險駕駛罪量刑的補充完善
關于危險駕駛罪的法定刑設置,一直備受關注,例如,周光權認為應當規定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任茂東委員則建議,“只要是醉酒和追逐行駛的,應當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筆者認為,基于以下幾方面考慮應當對其量刑進行補充細化。
1.從違法成本理論角度考慮
經濟學的“理性犯罪人”理論指出,“任何一個犯罪人都是一個‘理性’的計算者,在實施犯罪行為之前,會將犯罪的預期成本與預期犯罪收益進行比較,從而決定是否從事具有風險的犯罪行為。”醉酒駕駛之所以頻發,與犯罪成本較低是有關系的。刑罰的偏低和實踐中實際的處理情況,易使醉駕者對醉酒駕車的危險性認識不足,警惕性普遍較低。此外,由于自身的缺陷,拘役所起到的刑罰功能一直飽受爭議。拘役是短期自由刑的一種,由于其威懾力不大,難收改造效果,而且容易使被處刑者交叉感染犯罪惡習。且單處拘役刑伸縮性差,其期限較短,意味著即使行為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再多,構成醉駕罪的,也只能判處最高6個月的短期自由刑。刑法規定拘役也可以判處緩刑,這將導致即使再嚴重的危險駕駛,行為人實際服刑的期限可能很短,對行為人的改造也就很難取得效果,若對危險駕駛罪處以有期徒刑的話,不僅刑罰幅度擴大,并且還能對多次危險駕駛的累犯進行嚴厲打擊,也會使駕駛人員有所顧忌。
2.從與其他相關罪銜接角度看
危險駕駛罪是應現代風險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其與交通肇事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均旨在保護公共安全利益。危險駕駛罪入刑前,通常由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來規制交通安全領域的犯罪,由于二者無法完全涵蓋實踐中出現的各類犯罪,存在無法準確概括危險駕駛行為并用適度的刑罰加以處罰的空白地帶,因此對頻頻發生的因危險駕駛行為引發的惡性案件,經常會無論以二種罪的哪種定罪處罰都易引起巨大爭議。也正基于這一尷尬法律問題,危險駕駛罪才應運而生。至此,這三個罪名共同形成了一個保護體系,由淺入深逐步遞進地保護著交通安全方面的社會公共安全。但危險駕駛罪法定刑的設置與因危險駕駛行為引起的惡性案件所造成的實際危害結果不能很好相稱。根據條文規定,“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此條款是對于想象競合犯從一重罪處罰的規定,即將罪責更加嚴重的危險駕駛行為所引起的犯罪指引由較重的罪名進行規制。但此規定有將問題帶入另外一層矛盾關系的嫌疑,有可能再次引起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二者的爭議,不利于充分準確地對危險駕駛行為進行規制。
此外,危險駕駛罪法條的設計本身具有一定缺陷,醉駕行為的表現形態是多樣的,其表現出來的犯罪情節也因此具有不同的危害程度,如剛達到醉駕標準頭腦尚清楚的醉駕和酩酊大醉意識模糊仍堅持醉駕的行為,在人煙稀少的郊外醉駕的和在車水馬龍的鬧區醉駕的,醉駕未造成任何損害和醉駕造成人員、財產受損的,其犯罪的危害性大小明顯不同。而立法未能考慮到罪內危害性明顯不同的犯罪行為得到差別不大的法律評價,將有損刑罰的嚴肅性。
綜上所述,筆者建議在危險駕駛罪本身的框架內,做進一步更高法定刑的規定,提高對危險駕駛行為的處罰力度,應在現有立法基礎上,針對不同犯罪情節,并區分初犯、再犯,把現有法定刑定位于專門處罰剛達到醉駕標準且未造成任何損害的初犯,并進一步司法解釋,針對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的,分別處以不同的有期徒刑,以細分不同的犯罪情節所對應的刑罰。同時,還應借鑒日本等國關于資格刑的設置,剝奪駕駛資格將有效扼制再犯念頭。
(二)裁判規范層面醉駕型危險駕駛罪量刑的理性界定
針對上文所述的是否適用緩刑問題及定罪量刑的基礎標準為何等,筆者認為
有必要在裁判規范層面上進行理性界定。
1.確定量刑基礎標準
(1)各地法院對于醉駕量刑標準規范化的有益探索。以溫州中院為代表:其在全省率先制定出臺危險駕駛犯罪量刑細則。其中在界定醉駕犯罪基準刑期方面,是以區分不同車型為標準來區分犯罪基準刑期的。即針對不同車型危險駕駛的社會危害程度,將醉酒駕駛電動車、摩托車、自備車、營運車(出租車、貨車)、大客車(含專用或非專用校車)的基準刑期,分別確定為一、二、三、四、五個月。
以杭州、北京、廣州法院為代表:根據杭州市市級公安、檢察、法院形成的相關會議紀要,對于醉駕,審判機關也有相對統一的量刑標準,即規定血液酒精濃度的高低決定判處刑期的長短。而北京的一家法院與杭州一樣,規定了相同的量刑標準與幅度。類似的,廣州地區法院在審判案件的過程中也是以血液酒精濃度高低為標準進行量刑。
筆者發現,盡管醉駕量刑基礎標準不一,大多數法院醉駕量刑統一了標準,體現出量刑標準規范化成效。
(2)以醉駕者血液酒精含量作為基礎標準并結合其他情節確定量刑。針對上述的不同標準,筆者認為應當以醉駕者血液酒精含量作為量刑基礎標準。理由如下:
危險駕駛罪屬于抽象危險犯,入刑的前提條件是達到醉酒程度。根據《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規定,一般認為只要行為人體內酒精含量達到法定的醉酒標準,就構成危險駕駛罪。可見,血液酒精含量是此種罪的唯一界定因素。
從醫學上分析,就醉酒而言,在不同酒精濃度下行為人的具體表現也不相同,醉酒的程度會對造成危害結果的行為的主觀方面造成影響。當血液中酒精含量達到20-40mg/100ml時,行為人的自制能力會稍微降低,情緒不太穩定,容易激動;達到50mg/ 100ml時,行為人會出現飄飄然的感覺,此刻比較容易產生交通事故;達到100mg/100ml時,行為人會出現較為興奮,語無倫次,喜怒無常的情形,此刻交通事故發生的概率急速上升;達到150mg/100ml時,行為人將會變得激動,并會吵鬧;達到200mg/ 100ml時,行為人的動作協調性會大大下降,意識開始紊亂;達到300mg/100ml時,行為人處于麻痹狀態,并通常陷入昏迷。因此,隨著BAC(血液酒精濃度的簡稱)的上升,行為人駕駛機動車的危險性便隨之上升,并因此影響事故發生的幾率,在BAC達到50mg/100ml時,行為人駕駛機動車輛的行為明顯會對公共安全造成威脅,但達到80mg/100ml左右時這種威脅已無法為社會容忍,行為危險性倍數激增,事故發生的概率大幅度提升幾乎成為常態。
因此應以行為社會危險程度的大小為量刑基準刑期即以血液酒精濃度含量的高低為標準,含量低的基準刑期短(前提是血液中酒精濃度≥80mg/100ml),含量高的基準刑期長。當然還要考慮個別情節,即如果抓獲犯罪嫌疑人時,因故未能及時測量其血液酒精含量,這時若有其他足夠的言詞、視聽證據、證人能夠認定當時犯罪嫌疑人確實大量飲酒,也可以認定嫌疑人為醉酒駕駛。至于量刑精確到什么程度,筆者認為只要有個容易操作、普遍認可、相對合理的標準可以參照,量刑個案平衡與整體平衡基本上就能找到結合點,就不會出現量刑差距太大的狀況。
2.基于風險控制有條件地適用緩刑
《刑法》第72條規定了可以宣告緩刑的四個條件。對于危險駕駛罪,顯然符合這四個條件,因此從法律設計上看,危險駕駛罪可以適用緩刑制度。
第3篇:關于醉駕的處罰規定范文
關鍵詞 醉駕 犯罪構成 交通肇事罪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完善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識碼:A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第22條規定,“在刑法第132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133條之一:‘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正式將醉駕入罪。
醉駕入罪已成為事實,但我們仍需進一步探析其罪狀設定,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關系,以求更好地落實和完善,從而推進立法進程。
一、 犯罪構成若干問題探析
(一)“醉駕”構成的危險駕駛罪的主觀方面。
關于“醉駕”構成的危險駕駛罪的主觀罪過,學術上爭論很大,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觀點一:故意說。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 “醉駕”主觀方面都是故意。即醉酒駕駛人明知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從而放任這種狀態的發生。有的學者認為,“醉酒駕駛是明知故犯的行為,對危險情形的發生是持放任態度,因而構成間接故意犯罪。”
觀點二:過失說。該理論認為,行為人如果故意使自己的行為陷入危險狀態,應當對行為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因此本罪主觀方面應為過失而不是故意。
觀點三:嚴格責任說。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黎宏則提出,“80mg/100ml的醉駕標準本身已是客觀標準,該客觀標準已無須再被主觀評價。
由于立法者將本罪置于《刑法》第133條之后,而不是《刑法》第114條之后,所以,有學者主張本罪的主觀罪過是過失。也有學者提出,本罪的主觀構成要件是故意還是過失并不重要,只要證明了“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事實存在,犯罪即成立,可以免除罪責的情形幾乎不存在。對此筆者表示質疑:一個行為之所以會被刑法入罪,是因為本身嚴重危害了社會秩序,將要受到最嚴厲的懲罰,故在認定行為觸犯刑法之前必須對其犯罪構成方面進行分析,這樣才符合入罪的謹慎原則,犯罪的主觀方面是犯罪構成的基本組成四要件之一,如何脫離犯罪構成要件談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
依筆者之見,要認定“醉駕”的主觀是故意還是過失,關鍵是如何認定“危害社會的結果”這個標準,依據本罪的入刑出發點,應當把“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本身就理解為是對公共安全的危害,那么其醉酒駕駛本身已經產生了危害結果,即行為人明知自己醉酒仍然希望發生駕駛機動車這一結果,成立直接故意。
駕駛人必須認識到自己是在醉酒狀態下駕駛機動車。但是,對于醉酒狀態的認識不需要十分具體,即不需要認識到血液中的具體酒精含量,只要行為人知道自己喝了一定的酒,事實上又達到了醉酒狀態,并駕駛機動車的,就可以認定其具有醉酒駕駛的故意。當然,如果沒有主動飲酒,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飲酒的,應排除故意的成立。
(二)“醉駕”構成危險駕駛罪的客體。
立法者將該罪歸入刑法分則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可知“醉駕”構成的危險駕駛罪所侵犯的同類客體應該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人或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財產利益;直接客體,應當是道路交通安全。
(三)“醉駕”構成危險駕駛罪的客觀方面。
關于醉酒的定義,根據國家質監局的 《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規定: 駕駛員每 100 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在 20 -80 毫克之間為酒后駕駛,超過 80 毫克即為醉酒駕駛。可見醉酒的標準是十分明確的。當然,由于個體差異,每個人對酒精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樣的。于是在 “醉酒”標準的具體適用上,學者對此存在分歧。一種觀點是執行單一的標準,認為從法律上, “醉駕”的本質就是 “酒后駕車”,按照法律規定的尺度來認定行為人的意識清晰程度、控制能力。另一種觀點則是執行復合的標準,認為雖然酒精在客觀上對機體神經的麻痹有必然影響,但是每個人對酒精的反應不一樣,所以應當考慮各人對酒精的耐受程度,因此對于醉酒駕駛的認定還應當出臺更完善的檢驗標準。
筆者認為,衡量醉酒須堅單一的標準,將這一標準作為共同的量化準繩適用于所有人,才符合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符合現代法治的精神。生活中,我們并不排除不同的人攝入等量的酒精而表現不一樣。但是由于這種主觀醉酒狀態存在于行為人的內心,難以用客觀的標準衡量,司法實踐中也不可能對每一酒后駕車者制定單獨的醉酒標準,否則將導致認定標準的混亂,背離了公平正義的刑法理念。醉酒危險駕駛罪,在法理上屬行為犯,只要行為人達到刑法所規定的條件,就應當依法入罪。
二、醉駕是否應當一律入罪
2011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各地人民法院應當慎重穩妥地追究醉駕的刑事責任,不能僅從字面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即不能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而要與修正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相銜接,情節輕微的可以不入罪。在隨后進行的針對“醉酒不必一律入罪”論的大討論中,公安部發言人指出:“公安機關對經核實屬于醉酒駕駛機動車的一律刑事立案”。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醉駕案件只要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檢察院一律”。至此,公、檢、法三機關對醉駕的態度已基本明確: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持“醉駕一律入罪”的立場,而最高人民法院持“醉駕不必一律入罪”的立場。
筆者認為,醉酒駕駛不受情節嚴重限制,即“醉駕不必一律入罪”論不成立。
《刑法修正案 ( 八) 》的規定很明確:行為人只要醉酒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即構成醉酒危險駕駛罪,沒有其他犯罪情節要求,所以對該行為定罪不存在 “情節惡劣”要素的要求。醉酒危險駕駛罪侵害的客體是道路交通安全,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并不需要司法人員根據具體情況判斷行為是否存在具體危險性。在實踐中,多數醉酒駕駛案,其實并未發生實際可量化的緊迫危險,可如果任憑此種行為的發生,對公眾的安全和信賴感無疑造成巨大壓力,對公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潛在的巨大威脅和損益。故而,醉酒危險駕駛罪應當被設定為抽象危險犯,即只要實施醉酒危險駕駛行為,只要不具有其他無罪因素,如無故意或者緊急避險等情形,無論是否具備其他惡劣情節,即被推定為對社會、民眾公共安全的危險狀態已然存在,無論是否發生具體侵害結果,都認為侵害法益的危險而構成犯罪。具體理論如下:
抽象危險犯理論不允許“醉駕不必一律入罪”論的成立。
“醉駕”構成的危險駕駛罪是抽象危險犯已經被刑法學界公認。所謂抽象危險犯,是指立法者所規定的類型化的危險行為一旦出現,作為犯罪成立或者既遂根據的抽象危險狀態就產生犯罪形態。與抽象危險犯相對的是具體危險犯,從司法的意義上講,具體危險犯需要司法者根據個案的具體情況判斷危險行為是否具備現實化的危險狀態。抽象危險犯意味著只要有危險行為就具備抽象危險,無需司法者對是否具備危險性作個案性的具體判斷。因此,根據危險犯的理論,醉酒危險駕駛罪是抽象危險犯,意味著在立法層面只要醉駕就一律構成犯罪,在司法層面無需司法者對醉酒危險駕駛的是否具備危險性作個案的具體判斷。
三、“醉駕”構成的危險駕駛罪與交通肇事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
(一)“醉駕”構成的危險駕駛罪與交通肇事罪的界限。
“醉駕”構成的危險駕駛罪和交通肇事罪是一種補充關系而非排斥關系。醉酒駕車人對違章駕駛行為必定是明知故犯,而交通肇事行為人對違章行為多數是明知故犯,但也可能是誤犯;“醉駕”構成的危險駕駛罪是危險犯,以一定的危險狀態的存在作為構成犯罪的基本要件,而交通肇事罪是結果犯,以一定的實害結果存在作為構成犯罪的基本要件。當醉酒駕車尚未造成他人傷亡的實害結果時,認定為“醉駕”構成的危險駕駛罪而非交通肇事罪。但如果實施了醉酒駕車行為又發生了造成他人傷亡的實害結果的,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實施了醉酒駕車行為,已經構成了醉酒危險駕駛罪,但同時,該行為又造成了實害結果(行為人對實害結果是過失),因而又構成了交通肇事罪。但是行為人只實施了一個醉酒駕駛行為,因而屬于一個行為觸犯數罪名的情形,應當按照想象競合犯處理原則,以重罪即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
(二)“醉駕”構成的危險駕駛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
從犯罪形態分析,“醉駕”構成的危險駕駛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雖然都屬于危險犯,但前者是抽象危險犯,后者是具體危險犯:前者只要實施醉酒駕駛行為即被推定為危險狀態已經存在;后者不僅要實施特定的危險行為,而且必須引發現實的具體危險,才能認為構成要件該當,而具體危險狀態的有無,不能立法推定,必須由司法人員進行個案判斷。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兜底罪名,在司法實踐中要嚴格限制其范圍。要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必須產生等同于放火、決水、爆炸等引起公眾恐慌性級別的危險,醉酒危險駕駛產生這樣危險性的,是極其個別的案例。
四、醉駕入罪的立法完善——擬建立前科消滅制度
醉駕一旦入罪,對當事人來講影響巨大。執行后將留下犯罪記錄,如果是公務員等會因此被除名,進入事業單位、服兵役等很難通過政審;考學也將受到限制等等。普通的勞動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律師、注冊會計師、職業醫師、資產評估機構、驗證機構專業人員等,職業資格完全受影響。另一方面,醉駕者大多有工作,如最后拘役期滿很可能變成無業人員,如果其實家庭收入主要來源,則會增加家庭代價與社會成本。
筆者經過比較研究發現,在規定醉駕是犯罪的不少國家的法律制度中,都建立有“前科消滅制度”。 “前科消滅”是指曾被宣告有罪或被判處刑罰的人在具備一定的條件時,可以注銷其相關罪刑記錄的制度,它已被實踐檢驗是切實可行的并且為許多國家(地區)所普遍采納。我國刑法第一百條規定,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就業的時候,應當如實向有關部門報告受刑記錄,這就是所謂的前科報告制度,它的存在對犯罪人出獄以后的出國、就業和擔任公職等等諸方面都會有很大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犯罪的標簽效應。前科消滅制度具有的價值蘊含及其獨特功能,能最大程度地消除對犯罪人的標簽效應,使犯罪人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從而最終達到回歸社會、避免再重新走上犯罪道路的尷尬局面,而我國尚未確立該制度。筆者認為,前科消滅制度就目前來說可以很好地緩和醉酒駕車未肇事的輕行為與入刑后種種標簽惡果的矛盾。
(作者:賴燕娜,廣西大學法學院2010級刑法學專業研究生;唐思琴,廣西大學法學院2010級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專業研究生)
參考文獻:
[1]邵棟豪.危險駕駛罪的理解和適用.載人民院報,2011年5月18日第06 版.
[2]張明楷.危險駕駛罪及其相關犯罪的關系.
[3]王伶俐.醉駕入刑:應理性考量四個問題.檢察日報,2010 年11 月3 日第 003 版.
[4]陳嘉.刑法亟待增設“危險駕駛罪”. 載江蘇經濟報,2010年10月8日第03版.
[5]李曙明.如何看待“警方對醉駕一律刑事立案”.檢察日報.2011年5月19日.
[6]李樂平.醉駕入刑,執法莫犯迷糊.檢察日報.2011年6月14日.
[7]王秋實、劉薇.“醉駕非一律入刑”待司法解釋.京華時報.
[8]戴玉忠.醉酒駕車犯罪相關法律規定的理解與適用.檢察日報.2011年6月20 日第三版.
[9][日]大谷實.黎宏譯,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0][德]羅克辛.王世洲譯.德國刑法學總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第4篇:關于醉駕的處罰規定范文
關鍵詞:醉駕肇事原因自由行為主觀罪過合理量刑
一、引言
近兩年內,惡性醉酒駕駛肇事案件的接連發生,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各地司法實踐在定罪和量刑上作法不一、差距懸殊。強烈的社會反響以及實務操作中的不統一引發了學術界對于醉酒駕駛肇事行為的罪責評價問題的廣泛討論。最高人民法院在孫偉銘案宣判之后于2009年9月11日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然而各種理論爭議、意見分歧并未消餌。對于爭議焦點—刑法應當如何評價醉酒駕駛發生事故后再次撞人行為,有的學者支持法院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的做法:有的學者認為此類案件實質上仍是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酒后駕車,以致發生交通事故,因此應當只構成交通肇事罪;還有部分學者提出仿效日本的做法,在我國刑法中增設危險駕駛致人死傷罪。在這三種主流的聲音之外,有一種比較微弱的呼聲在主張應以原因自由行為理論來辨析醉酒肇事的行為性質。
筆者認為三種主流的觀點都不能從理論上周延地解決醉酒駕駛肇事行為的罪責評價問題,且對于我國刑法體系的完善也未有裨益。而運用以醉酒犯罪為藍本構建起來的原因自由行為理論,則可能為這個問題謀求一條妥善的解決之道。
二、以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為視角評價醉酒駕駛肇事行為之罪國責
在我國醉駕肇事行為的罪責評價問題之所以引起如此廣泛的爭議,其原因主要在于法院在評價此行為時忽略了行為人醉酒后辨認和控制能力均發生障礙的客觀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故意和過失的簡單判斷本身就是不科學的。現代醫學表明,輕度醉酒的人控制能力有所減弱,中度醉酒的人辨認和控制能力均有所減弱,高度醉酒的人有一定程度的意識障礙。衛也就是說,醉駕者在醉駕肇事時,并不具有完全的責任能力。根據現代刑法“責任與行為同在”的精神,我國目前對于醉酒駕駛肇事的罪責評價存在著嚴重的體系化問題。美國法學家胡薩克的一段描述與我國的刑事立法、司法現狀十分契合,“一個犯罪時處于醉酒狀態的被告以其行為缺乏一般犯意為由進行辯護。他膽怯地聲稱其判斷力受到了損害,他的控制力被降低,如果他更清醒,就不會實施這一犯罪行為。假如這些聲明是真實的,那么被告是否具有了一個有效的辯護,或者其行為是否含有犯意?法院幾乎是一致地認為被告的辯護是無效的。然而,他們是如何〔或者是否)使這一結果與正統刑法理論中的犯意要求保持一致的,卻不清楚。”胡薩克教授指出這個問題并非是否定此類案件的可罰性,事實上,鑒于此類醉酒駕駛肇事案件反映出的強烈性格,為了保護公共安全,“若法律以其自陷于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情形,任其主張不罰或減輕,將無以維持社會秩序,在刑事政策上自非所宜。”他在這里所要提示的信息是—理論上的空白或者說缺乏理論指導的刑事司法是危機四伏的。追究造成我國醉酒肇事罪責評價之困境的原因,首當其沖的正是我國刑法關于原因自由行為規定的不完善。
所謂原因自由行為,是指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而使自己陷入意識不清或行為失控的狀態,然后在此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態下實施了侵害刑法所保護的法益的行為。其中,使自己陷入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的行為稱為“原因行為”;在此狀態下實施的侵害刑法所保護的法益的行為稱為“結果行為”。那么,為何要求在實施危害行為時不具有完全責任能力的行為人承擔完全的刑事責任,原因自由行為的責任基礎試圖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
(一)原因自由行為的責任基礎
對于原因自由行為的責任基礎,各國學者提出了不同觀點,筆者以對責任主義原則的堅持程度將各國學者的立場劃分為三種:<1)堅持責任主義原則。利用原因前置說、統一行為說、間接正犯說等理論,調和原因自由行為與責任主義的沖突。(2)弱化責任主義原則。用嚴格責任來解決原因自由行為的責任基礎問題。(3)主張責任主義原則的例外。將原因自由行為作為“責任與行為同在”原則的一種例外。限于篇幅和考慮到國內外學者對于此問題的探討已經較為深入,筆者在此不贅述每種學說的具體內容,僅闡明本人所持觀點。
筆者支持例外說的觀點。該說認為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屬于“責任一行為時一合致一原則”的一項例外。原因自由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并非對責任主義的否定,而是責任主義存在著行為與責任暫時性分離。具體而言,對于原因自由行為,并不要求行為人實施危害行為時具有責任能力,只要是行為人由于自身罪過自陷于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的狀態中,而實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為,并且行為人對于危害結果的避免時具有期待可能性的,則可以追究行為人的完全刑事責任。筆者之所以認同例外說的觀點,具體理由如下:
其一,從責任的核心內涵分析,責任能力未必以與結果行為同時存在為必要。責任是指行為的非難可能性,責任能力、罪過,只不過是行為是否具有非難可能性的推斷依據,并非責任本身。因此,即便原因自由行為中的結果行為是在不完全的責任能力時所為,但是基于此結果行為取決于行為人在有責任能力時的意思態度,而刑法譴責行為人的主觀根據,正是行為人對其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所持的心理態度。故行為人在主觀方面是具有非難可能性的,因此當行為的其它方面同時符合犯罪構成要件時,追究行為人的完全刑事責任是有理論根據的。
其二,從責任主義原則的刑法價值選擇分析,責任能力亦未必以與結果行為同時存在為必要。“責任主義存在著一個從古典責任主義到現代責任主義的轉變。古典責任主義是一種與報應觀念相聯系的責任主義,而現代責任主義是一種與預防觀念相聯系的責任主義。“有效的預防應建立在造成危害結果背后的原因的基礎上。為了科處刑罰,除了責任之外還要考慮政策性要素,作為政策性要素,要重視一般預防,也要對特別預防加以注意。因此當行為的其它方面同時符合犯罪構成要件時,追究行為人的完全刑事責任是有現實價值的。
(二)運用原因自由行為理論分析醉駕肇事行為的主觀罪過
故意與過失的區分,關鍵在于行為人對于危害結果的主觀心態。落實到原因自由行為,則應當結合行為
人在原因行為時對危害結果的主觀心態和在結果行為時對危害結果的主觀心態具體分析。然而與單一行為類型不同,自陷于無責任能力狀態的原因自由行為和自陷于限制責任能力狀態的原因自由行為,基于前文筆者對于原因自由行為責任基礎的分析,其在主觀心態方面考察的側重點各有不同。前者故意或過失應以原因行為時對危害結果的主觀心態來確定,而后者則主要是以結果行為時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主觀心態來確定。
將這種理論具體到醉駕肇事行為,即對醉駕者是故意還是過失的判斷,應當區分兩種情況:(1)行為人故意或過失地自陷于無責任能力狀態,然后醉駕肇事。此時,故意或過失應以行為人醉酒行為時對最終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結果的主觀心態確定。(2)行為人故意或過失地自陷于限制責任能力狀態,然后醉駕肇事。此時,故意或過失應以行為人醉酒駕駛以及其后續行為時對最終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結果的主觀心態確定。
1.自陷于無責任能力狀態時醉駕肇事行為的罪責
既然此情況下的故意或過失,應以行為人在醉酒行為時對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結果的主觀心態確定,那么,除極少數行為人出于報復社會、泄憤等目的,故意用醉酒駕駛的方式危害社會的情形,絕大多數行為人在醉酒行為時,只會認識到其隨后的醉酒駕車行為是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但對于最終危害公共安全的結果在主觀上顯然是持否定態度的。從而,可以認為把無認識意志能力的醉駕肇事者視為主觀上的過失,而依交通肇事罪處罰,是合乎法理的,可以避免出現體系上的混論。
然而,盡管這種過失的認定合乎法理,但是如果其醉駕肇事行為的確造成了很嚴重的危害結果,而依我國交通肇事罪則量刑過輕,對于犯罪人來說起不到特別預防目的,對于社會民眾而言,不能滿足其正義感情和報應的基本要求。為了解決這個現實的問題,于志剛教授提出修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中第四條,在特別惡劣情形中加入醉酒駕駛機動車輛的情形,以此來實現對醉酒駕駛的嚴厲處罰。筆者比較贊成這個解決方案,將醉酒駕駛作為量刑情節處理,既可以不用打破我國二元化的體制將其作為一個新罪名予以處罰,又可以將其納入刑法評價的體系,滿足刑事政策的要求。
借鑒上述思路,針對醉酒肇事后的二次碰撞問題,筆者認為,可以修改《解釋》第五條中關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限制性解釋,將”在逃跑過程中過失致他人死亡”納入“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中。
2自陷于限制責任能力狀態時醉駕肇事行為的罪責
此情況下,故意或過失應以行為人醉酒駕駛以及其后續行為時對最終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結果的主觀心態確定,那么問題的討論則回歸到刑法中判定行為人主觀罪過的一般方法,即根據“主觀支配客觀,客觀反映主觀”的基本原理,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認定。就醉酒駕車犯罪而言,應結合行為人是否具有駕駛能力、是否正常行駛、行駛速度快慢、所駕車輛車況如何、路況和能見度如何、案發地點車輛及行人多少、肇事后的表現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認定。如果判定屬于間接故意,則成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為過失,則考慮如何在交通肇事罪項下進行合理的量刑。根據筆者在上文中提出的對《解釋》的修改,在此情形下對醉駕肇事行為科以恰當的刑罰,基本上是可以完成的。
(三)關于華總則中以原因自由行為的規定取代《刑法》第十八條第四款的規刃的探討
在探討醉駕肇事的罪責評價問題時,運用原因自由行為理論分析的學者大都提出,應當在我國刑法總則中規定“行為人因飲酒、服用麻醉劑、興奮劑等,故意或過失地陷于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態,并在此狀態下引起危害社會結果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不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事責任。”,取代現行《刑法》第十八條第四款的規定。
從應然層面來講,從完善刑事立法體系的考慮出發,在總則中對原因自由行為作出原則性規定是必要的。原因有二:其一,通過總則條款的規定,明確了處罰對象是原因自由行為,從而根據原因自由行為的一貫性、關聯性,那么筆者在前文中提出的原因自由行為主觀罪過的判斷標準則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盡管我國刑法界的主流觀點都是認可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但是畢竟它僅僅是一種理論學說,并未上升到立法高度,于爭議發生時援引之,總覺根基不深,底氣不足。其二,《刑法》第十八條第四款僅規定“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事實上,它是將非由于行為人主觀故意或過失而陷于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態的情形也包含在應負刑事責任的情況之中了,這顯然實質性地違背了責任主義的要求。因此,在總則中以原因自由行為的規定取代刑法第十八條第四款,從理論上說是應該的。
但是,從實然層面上看,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其一,目前是否己到了修改刑法總則的最佳時機?其二,在總則中對原因自由行為作出原則性規定的必要性是否十分迫切?關于第一個問題,我國首部《刑法》于1979年制定,其后經過了1997年的全面修訂,而97《刑法》也經過了多次修正,其修正的主要方式是修正案,迄今共通過了七個修正案,可以注意到七個刑法修正案中均為涉及對總則規定的修改。事實上,之所以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對《刑法》進行修改和完善,主要就是考慮到此方式能夠較好地保持刑法典基本原則和主體結構、內容的穩定性。1997年的修訂距今不到十三年,從刑法穩定性及立法成本的角度考慮,目前絕非修訂刑法總則的最佳時機。下面再來看第二個問題,盡管在應然層面上筆者論證了修改的必要性,但同時筆者認為這種必要性并不十分迫切。誠然,“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規定將非由于行為人主觀故意或過失而陷于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態的情形也包含在應負刑事責任的情況之中,但這種情形在現實生活中是極少數,司法實務中大量面對的都是由于自身罪過限于不完全責任能力狀態的情況。對于這種絕大多數的情況,第十八條第四款的規定在法理上是基本周延的。而且,正如筆者上文所說,我國刑法界的主流觀點都是認可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那么即使對于那種極少數情況,也可以通過責任主義原則的運用予以彌補。
因此,考慮目前并非進行刑法總則修訂的最佳時機,同時,《刑法》第十八條第四款的規定是基本能正當地解決實踐中的絕大多數案件,筆者并不主張于近一階段,在總則中以原因自由行為的規定取代《刑法》第十八條第四款的規定。
三、結語
第5篇:關于醉駕的處罰規定范文
在近3年時間里,全國各地司法機關在辦理危險駕駛犯罪案件的過程中,基本采取了零容忍態度,全國形成共識,統一量刑標準,且始終保持高壓態勢,有力打擊和遏制了醉駕、飚車等危險駕駛之違法犯罪行為。但隨著司法實踐的深入推進,不少問題顯現出來,尤其是醉駕上的疑難問題逐步形成司法困境,而且,初期的有些作法已明顯不適應形勢的發展,效應式司法必然要走向精細化司法。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本文試圖就相關醉駕入罪之疑難問題,以法律適用為視角,談點一孔之見,期望有助于問題之研究。
一、關于醉駕之強制措施適用難問題
醉駕入刑以來,各地司法機關在辦案中逐步發現,對醉駕行為人施以強制措施存在諸多困境,主要表現為:刑法第133條中對醉駕犯罪的法定刑為拘役并處罰金,這就自然排除了逮捕強制措施之適用,因為逮捕的必備條件之一是“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醉酒犯罪不符合逮捕條件。根據刑訴法第六章強制措施的規定,醉駕排除逮捕適用后,只有刑事拘留、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可供選擇。刑事拘留,法定期限一般為3日,情況復雜且經批準可延長1-4日,對結伙、流竄、多次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經批準延長至30日。而醉駕刑事拘留期限最長只能是7日。也就是說,司法機關必須在7日內完成醉駕案件的偵查、起訴和判決,無疑加重了司法機關的辦案壓力。取保候審,適用對象是管制、拘役或獨立附加刑者或有期徒刑取保不致于發生社會危險性者,以及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者或哺乳期中的婦女等。但醉駕案中一定比例的行為人來自外地,無法提供符合條件的保證人,采用保證金取保方式又難以確保行為人隨時到案。監視居住,多適用于嚴懲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者,懷孕或處于哺育期中的婦女,或屬于生活不能自理者的唯一扶養人等,且辦案中采用監視居住方式耗費人力物力,實際效果也不好,司法機關很少適用,這一強制措施基本形同虛設。
綜上比較,司法機關對醉駕犯罪嫌疑人采取的法定強制措施,基本上僅限于取保候審和刑事拘留兩種,這也是近三年來司法實踐的基本走向。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可以采取三種辦法走出強制措施之司法困境。其一,推行以取保候審為主,刑事拘留為輔的選擇適用原則。因為取保候審法定最長期限為12個月,既可以為司法辦案留足辦案時間,減輕辦案壓力,又可以節省人力物力,降低司法成本,更合于醉駕案件社會危險性較低之特點,這原本系刑訴法第70條的立法要求。其二,采用取保候審方便了各個司法機關的程序操作與辦案銜接,利于訴訟程序的快速運轉,而且一旦嫌疑人嚴重違反取保候審規定時,各辦案機關均可改變措施施行逮捕方式,且不受刑訴法第79條之限制。其三,根據國家立法機關近期已著手修改刑法的動態(法制日報2014年1月24日“人大立法”版《法工委已經著手進行調研論證》),建議增加規定“曾因醉駕判刑的,應當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追究刑事責任”,提高醉駕法定刑,從而解決強制措施適用等一系列程序性問題。
二、關于醉駕之證據收集難問題
目前,一些辦案單位反映,一方面,目前認定醉駕犯罪標準主要看犯罪嫌疑人酒精檢測結果,即呼氣酒精檢測結果和血液酒精檢測結果。問題在于,呼氣、血液兩種檢測存在時間間隔問題,但酒精卻是不斷揮發和被人體分解的,從而造成在呼氣檢測時達到醉駕標準,但送去專門機構進行血液檢測時卻沒能達到標準。另一方面,言詞證據存在極大的不穩定性,通常情況下交警最初查獲時嫌疑人一般都承認其有醉駕行為,但當案子移送檢察機關或審判機關時,卻對醉駕聲稱不清楚或矢口否認,甚至編造沒有開車的事實或證據。再一方面,證人證言也存在不穩定性,因為醉駕案件中,目擊證人往往是犯罪嫌疑人的親朋好友,證人很難作真實陳述,而且犯罪嫌疑人案發后多被取保候審,有充足時間和空間去活動,極大提高了串供和干擾證人的可能性(記者走訪海口市龍華區檢察院時劉枚副檢察長發表的看法,法制日報1月24日“視點”欄目)。
筆者認為,證據是定案之根據,事關醉駕犯罪的打擊力度問題,的確馬虎不得。根據司法實踐反映出的問題,筆者認為改進取證方法,完善規范化、標準化取證體系很重要。第一,在酒精含量的取證上,確保真實性和準確度。既然目前認定醉駕犯罪標準主要是看犯罪嫌疑人酒精檢測結果,亦即呼氣酒精檢測和血液酒精檢測定案,所以就應當在檢測上下功夫,在抽取血液樣本、測定電子違法數據時,謹慎實現證據獲取的真實性和準確度,提高取證質量。第二,為防止呼氣檢測與血液檢測因時間間隔發生的誤差,一方面,在檢測規則上應當確定比較科學的誤差值,既承認這種自然現象,又體現以事實為根據的司法原則;另一方面,強化檢測程序理念,力求準確、及時,實行血液備分封存,將時間間隔形成之誤差降到最低限度。再一方面,在制度和規則上堅持“首次檢測為主”的認證標準,之后的任何檢測只作為參考值。第三,在言辭證據的取證上,為防止翻供和串證行為,應當效仿看守所提審的方式,實行全程式錄音錄相監控,以證明辦案機關錄取口供和證言的文明辦案程度,程序合法公正程度,從根本上消除串供、翻供隱患。
三、關于改造與回歸社會問題
第6篇:關于醉駕的處罰規定范文
酒駕是指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毫克/100毫升,小于80毫克/100毫升的駕駛行為。
醉駕是指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毫克/100毫升的駕駛行為。
【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條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屬于醉酒駕駛機動車,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規定,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未達到醉酒駕駛機動車標準,也就是血液中酒精含量低于80毫克/100毫升的,按照《道路交通安全》的有關規定給予行政處罰。
(來源:文章屋網 )
第7篇:關于醉駕的處罰規定范文
關鍵詞:危險駕駛罪;醉酒駕車;故意;擬制的間接故意
中圖分類號:d924.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3)01?0093?07
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經過第三次審議并通過,醉駕正式入刑。修正案(八)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醉駕入刑以來,酒后駕駛行為數量同比大幅下降,治理成效明顯。據統計,2011年5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全國共查處酒后駕駛機動車201 153 起,較2010 年同期下降44.5%,其中,醉酒駕駛機動車33 183 起,較2010 年同期下降43.7%。[1]但是,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對醉駕構成的危險駕駛罪①的規定過于抽象、概括,司法實務對本罪的認定尤其是對主觀要件的認定存在諸多分歧,影響了本罪的準確適用和刑法實施效果。
一、問題的提出
“醉駕型”危險駕駛罪旨在處罰醉酒駕車的危險行為而非肇事的結果,即只要有侵害法益的危險性,本罪就成立,因而是危險犯。依據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危險犯既可以是故意犯罪,也可以是過失犯罪。那么,本罪之主觀要件究竟是故意還是過失,抑或兩者兼具,學界并未達成共識。
有論者認為本罪之主觀罪過為故意,且多為間接故意。如趙秉志教授認為:“在酒駕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下,行為人主觀心態多為間接故意,在性質上不同于交通肇事罪的過失。”[2]另有論者認為本罪之主觀罪過只能是過失,依據我國的罪過理論,行為人對危害公共安全的結果明顯持反對態度,不可能是故意。[3]有一種折中的觀點認為,本罪之主觀要件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于自信的過失,醉酒者一般情況下在醉酒前是不希望發生交通事故這一危害結果的,因為根據經驗其輕信可以避免。由此,在整個醉灑過程中以及醉酒前,醉酒者對危害結果的發生顯然是不希望的,其主觀罪過形式是過失。但是,也有一些醉酒者故意使自己陷入醉酒狀態,放任危害情況的發生,抱著一種無所謂的心態。這種情況可以直接認定為故意,且絕大部分是間接故意,當然也不排除直接故意。[4]還有論者認為,“醉駕型”危險駕駛罪既不是故意犯罪也不是過失犯罪,傳統刑法理論不能合理解釋醉駕犯罪在主觀上的可歸責性,其主觀罪過突破了傳統的罪過理論,應屬于嚴格責任。[5]
由此可見,學界對于本罪的主觀罪過主要集中在故意與過失之爭,折中說和嚴格責任的呼聲甚微。事實上,部分學者傾向于認為本罪為過失犯罪,而不是故意犯罪,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認為行為人醉駕,對法益侵害的結果持希望或放任態度的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罰,故意醉駕不存在危險駕駛罪適用的余地;二是刑法修正案(八)對危險駕駛罪處罰較輕,只規定了罰金、拘役,更符合過失犯罪的刑罰設置和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
筆者認為,前述觀點值得商榷。首先,“故意醉駕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這一觀點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其次,在“醉駕型”危險駕駛罪主觀罪過的認定中,存在間接故意與自信過失難以區分的一個中間狀態,即在考察行為人對危險結果的意欲因素時存在灰色地帶,究竟是故意、過失、第三種罪過抑或嚴格責任呢?②下面筆者將圍繞上述問題展開具體論述。
二、故意醉駕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個假命題
依據我國刑法第114條和115條的規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危險性相當的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6]分析可知,我國刑法并沒有明確列舉以危險方法
害公共安全罪的行為方式,對于“其他危險方法”的內容是什么?哪些行為方式可以成為這里的“其他危險方法”?刑法都缺乏明確、具體的規定,這給司法實踐留下了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由于本罪乃“小口袋”罪名,與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有一定偏差,學界都主張對“其他危險方法”應做嚴格限制解釋。一般認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其他危險方法”的認定應當受到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危險方法“相當性”的限制。[7]
醉酒駕車的特殊性就在于是在醉態下駕車,從行為性質來看,醉酒駕車不應歸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行為范疇。首先,醉酒駕車的社會危害性與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比不具有相當性。其次,從主觀惡性以及人身危險性來看,行為人一旦放火、爆炸或者投放危險物質,其報復、反社會動機顯而易見。醉駕之行為人除非確證有仇視社會的動機,一般來說行為人都是不希望,甚至是反對危險結果發生的,而且危險結果的造成與行為人的醉酒密切相關。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個口袋罪名,應當嚴格限制,除非行為人是故意醉酒借機報復社會,否則對于醉駕不能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罰。再次,刑法修正案(八)將醉駕獨立成罪表明醉駕不屬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安全罪之“其他危險方法”的范疇。對醉駕以危險駕駛罪處罰,而不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罰,就清楚表明在危險犯層次,醉駕不能跟放火等行為等價,不能歸于同一行為類型。最后,刑法修正案(八)對醉酒危險犯的刑罰僅僅判處拘役、罰金,明顯輕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醉酒駕車行為也不能與“其他危險方法”相提并論。
在危險犯的層次理解醉酒駕車行為不屬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其他危險方法”的范疇并不困難,但是當醉駕造成嚴重的實害后果或者醉駕肇事后又繼續肇事時依然要堅持這一結論卻不容易。對醉酒駕車造成嚴重實害后果,尤其是肇事后繼續肇事的,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觀點在理論與實務界均有市場。比如發生在成都的孫偉銘案③,最終判決行為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這一判決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維持與確認。2009年9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指導意見及相關典型案例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規定對醉酒駕車,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放任危害后果的發生,造成重大傷亡,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115條第1款的規定定罪處罰。對于該《通知》,司法機關傾向于認為醉酒駕車只有“造成重大傷亡”的,才能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醉酒駕車造成一般傷亡的,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8]《通知》將造成嚴重后果的醉駕行為列為“其他危險方法”的范疇,在實害犯的層次實現了醉酒駕車與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行為的相當性。類似孫偉銘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罰,實際上是承認了醉駕屬于“其他危險方法”,這一判決在無形中提升并確認了醉酒駕車行為的危險性。
筆者認為,即便承認結果犯層面的醉酒駕車屬于“其他危險方法”的范疇,也不能當然得出尚未造成任何實害的醉駕危險行為也屬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結論。實害行為的危害性與危險行為的危害性無需在“量”上等同,但必須在“質”上具有一致性。比如故意放火,其對法益的嚴重危害性都孕育在行為中,行為的危險性與實害結果的發生幾乎具有同時性、不可逆性。另外,行為人無法對放火行為進行持續管理,放火行為一旦實施,就脫離了行為人的控制,事態的發展完全取決于自然力。醉酒駕車行為則明顯不同。首先,醉酒駕車造成實害結果只是概率上的統計,相比放火等行為其造成實害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其次,“醉駕型”危險駕駛罪乃持續犯,其侵犯法益的狀態一直持續,行為人一直處于控制車輛的狀態,對行為的持續管理并沒有中斷。盡管行為人管理行為的能力由于醉酒減弱,但必須看到,由于人力的存在,實害結果的發生并非具有不可逆性。由此可見,醉駕危險行為與造成嚴重實害后果的醉駕行為在“質”上不具有一致性,刑法理應給予不同的評價。這也是刑法修正案(八)僅規定“醉駕型”危險駕駛罪,而未規定醉駕實害犯的原因。
綜上所述,我們應看到危險犯層次與實害犯層次醉酒駕車行為性質的不同,不能依據造成嚴重實害結
果的醉駕行為來反推醉駕危險行為的性質,這種邏輯倒推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以及實務中做出類似孫偉銘案判決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值得進一步研究。根據前述分析,一般意義上的醉駕與放火等行為相比不具有相當性,除非能夠確證行為人出于強烈的報復社會動機,故意駕車沖撞人群,否則即使醉酒肇事后繼續肇事的醉駕行為也難以歸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其他危險方法”的范疇。因此,一般意義上之醉酒駕車行為不屬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其他危險方法”,不管行為人是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醉酒駕車的都不成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醉駕型”危險駕駛罪主觀罪過的認定
既然“故意醉駕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個假命題,那么故意醉駕構成危險駕駛罪就是一種可能的選擇。明確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其掃清了“故意醉駕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這一觀點設置的邏輯障礙。換言之,“醉駕型”危險駕駛罪之主觀罪過可以是故意,這在邏輯上是成立的。基于前述判斷,接下來只需要確定“醉駕型”危險駕駛罪之主觀罪過究竟是故意、過失、第三種罪過還是嚴格責任即可。
(一)故意與過失區分的理論述評
刑法中的故意是一個錯綜復雜的法律概念,要準確界定故意的概念存在困難,間接故意的認定尤甚。大陸法系國家刑法理論有關故意的學說眾多,理論分歧巨大,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代表性觀點:
一是意志說、認識說、容認說。意志說又稱希望說,即具有希望實現構成要件內容的意欲即屬故意。認識說又稱表象說,即只要對構成要件的內容有認識即為故意。由此可見,前者強調故意的意志因素,后者強調故意的認識因素,無論堅持哪種觀點都不能準確界定故意的內涵。如果堅持意志說,沒有意欲的“放任”則不屬故意,縮小了故意的范圍;如果堅持認識說,則所有的有認識的過失都會全部歸入故意,這又擴大了故意的范圍。容認說以希望說為基礎,認為行為人對結果發生的可能性有認識時,應根據行為人的意志來區分故意與過失,容認結果發生的是故意,不容認結果發生的是過失。[9](216)所謂容認是指,并不需要具有希望或意欲那種程度的侵害法益的積極態度,只要行為人對結果的發生持一種不介意的態度,即侵害法益的結果發生與否都不違背行為人的意志。申言之,消極的容認也構成故意。容認說將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很好結合起來,因而得到了多數學者的支持,成為日本等國的通說。
二是以認識說為基礎的蓋然性說與可能性說。蓋然性說認為,行為人認識到結果發生的蓋然性 (較大的可能性)時是故意,只認識到結果發生的可能性時是過失。換句話說,行為人的認識程度對他的意欲具有征表意義,行為人認識到結果發生的蓋然性時,依舊作為或不作為,就表明行為人意欲結果的發生;行為人只認識到結果發生的可能性時,表明他不意欲結果的發生。分析可知,依據該標準不能有效區分故意與過失,行為人認識到結果發生的蓋然性時,也可能相信憑借自身的能力可以避免結果的發生或者僥幸逃脫。畢竟蓋然性不等同于必然性,所以不能據此推定行為人的主觀心態一定是意欲。行為人認識到結果發生的可能性時,也可能意欲結果的發生。上述情形在現實中是完全可能的,因而它們之間并非一一對應的關系,而是有可能出現不同的組合。認識說則主張,故意并不需要行為人認識到結果發生的蓋然性,只需要認識到結果發生的可能性即可成立。可能性說相比蓋然性說只是降低了認識的程度與標準問題,兩者并無實質差別,但可能性說完全排除了有認識的過失存在的余地。
故意是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統一體,這一點幾無爭議。問題的難點是如何確定行為人對所預見的符合構成要件結果的態度,即意志因素。容認說認為,故意就是對構成要件的知與欲,欲就是實現構成要件的意思,以預見結果會發生而認可或接受其發生作為故意的認定標準,對結果的認可則使用不同的說法,如同意、認可、接受、容忍。[10](229)但是司法實務中面對錯綜復雜的案件,尤其是在認定間接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問題上,容認說并不能提供讓人信服的判斷標準。對意欲的判斷,大陸刑法理論上有認真容認說、蓋然性說、決定說、可能性說、防果說、漠然說、風險說、客觀認真說等諸多學說。[11]這些學說可以分為意欲主觀說和欲意客觀說兩類,無一
外這些學說沒有能夠完美地解決意欲的確證,間接故意與有認識過失的界限并不明確。
(二)第三種罪過、嚴格責任使問題的解決回到原點
我國刑法理論對故意與過失的區別也采用容認說,實務中間接故意與自信過失的區別存在難題,刑法理論上對此也展開了諸多討論。依據我國罪過理論,間接故意與自信過失的區別主要在于意志因素的不同,前者為放任,表現為對法益的蔑視;后者為反對,表現為對法益的消極不保護。但是對于如何確認放任則沒有進一步的考證,多循此種方式說明:明知實施行為會發生侵害法益的結果,而依然決意實施行為,并沒有采取相關保護法益的行動,因而缺乏自信的基礎,所以行為人對法益侵害的結果持放任態度。這種論述很不明確,對于兩者的區別幾乎沒有提供任何具有實質性、可操作性的判斷標準。
事實上,間接故意與過于自信的過失兩者都對法益侵害或侵害的危險有認識,兩者在認識程度上只有量的差別,沒有質的不同,要據此認定行為人的意欲因素確實存在困難。不可否認,在間接故意與過于自信的過失之間有一個難以區分的模糊、中間地帶。因此,要對這一“灰色地帶”做出明確的區分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像德國學者提出的漠然說、蓋然性說、可能說等,都是一種積極的學術嘗試。我國學界對間接故意與自信過失的區分缺乏深入探討,由于確證 “灰色地帶”的意志因素存在困難,反而轉向不區分兩者的界限,對“同一法條規定的同一罪名包含了跨種的罪過形式”這一新現象進行積極的理論探索,以期突破現行的罪過理論。如有學者提出嚴格責任說[12]、客觀超過要 素[13]、復合罪過形式說[14]等。
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罪過理論來看,我國刑法僅確立故意和過失兩種罪過形式,既是理論的結構性缺陷,也不便于司法操作,而承認第三種罪過或者嚴格責任未嘗不是一種有效路徑。如法國刑法之“中間類型”、德國刑法之“第三種罪過形式”、英美刑法之“輕率”。但是,在現有罪過理論體系下,第三種罪過以及嚴格責任的提出并不能解決罪過形式中的間接故意與自信過失難以區分的理論困境,因為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中,間接故意與自信過失的區別都是不可避免的。況且,第三種罪過和嚴格責任也只是解決了“同一法條規定的同一罪名包含了跨種的罪過形式”不用區分,簡化司法操作的問題,無論如何不能說只要難以區分間接故意與自信過失,就認定為第三種罪過或者采取嚴格責任。可見,無論是第三種罪過還是嚴格責任實質都是回避了兩者的區分,對問題的解決并無實質性貢獻。
(三)擬制間接故意概念之提倡
1. 概念的提出
間接故意存在于兩種情形,一種是原目的行為是不違反法秩序的社會相當行為,一種是原目的行為本是法秩序所不容許的行為,不管哪一種情形,所要探討的都是附隨結果是否是行為人的故意造成的。[10](267)
間接故意與自信過失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難以截然區分開來,這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基本事實。因此,間接故意的認定需要法律的推定,筆者稱之為擬制的間接故意。不容否認的是,盡管理論上可以提出區分兩者的標準,但是在司法實務中由于這一標準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而難以操作,究竟是間接故意還是自信過失往往取決于司法裁判者的選擇。事實上,我國司法實務普遍存在依據事實推定間接故意的情形。因此,理論上提出擬制的間接故意概念剛好契合了司法實務的實際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筆者并非認為間接故意與自信過失之間的區分不可認知,也不贊同廣泛使用擬制的間接故意概念來簡化司法操作,而是在盡量區分兩者基礎上承認“灰色地帶”的存在事實,從法律上確認擬制間接故意的適用。這既是對司法實務中事實推定的理論肯定,也是在傳統罪過理論框架下對罪過形式的修正。
有論者可能會質疑,既然有擬制的間接故意,那為什么不提出擬制的自信過失概念呢?根據罪刑法定主義的要求,存疑時應堅持有利于被告的原則,當間接故意與自信過失難以區分時,如果結果是認定自信過失,原本就是法律的應有之義,所以并無必要強調擬制的自信過失這一概念。然而,擬制的間接故意概念卻大不相同。間接故意的推定在事實上對被告不利,本應杜絕這種推定,但是法律的適用客觀上需要這樣的制度設計。擬制的間接故意概念有其獨特價值與功能,其中最大的價值在于通過法律塑造國民的規范意識,在這一點上其相比自信過失具有
更大的效用。因為擬制的間接故意通過推定的形式提高了法律對國民的要求,加重了國民的危險預見義務和危險回避義務,而自信過失需要發生危害結果不利于規范意識的培養。
2. 擬制的間接故意適用于抽象危險犯
學界普遍認為,“醉駕”型危險駕駛罪乃抽象危險犯。危險犯是指行為人實施的行為足以造成某種危害結果發生的危險狀態,嚴重結果尚未發生,即構成既遂的犯 罪。[15]危險犯又分為具體危險犯和抽象危險犯,大陸法系國家刑法理論對于如何區分具體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主要有以下幾種學說:[9](112?113)
第一種觀點認為,具體危險犯中的危險是構成要件要素,需要具體判斷;抽象危險犯中的危險不是構成要件要素,因而不需要具體判斷。第二種觀點認為,具體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都是以對法益的侵害為處罰根據的,但前者的危險需要司法上具體認定,后者的危險是立法上推定的。[16]第三種觀點認為,具體的危險是“作為結果的危險”,抽象的危險是作為“行為的危險”。第四種觀點為,兩者的區別僅僅在于危險程度的不同,抽象的危險犯是具體危險犯的前一階段,即侵害意味著發生實害,具體危險犯的危險是高度的危險,抽象危險犯的危險是比較緩和的危險。
由以上爭議觀點可知,無論是擬制推定還是需要具體判斷,無論是“行為、結果之危險”還是“高度、緩和”的危險,無一例外都表明抽象危險犯之法益侵害的危險是動態游離的。對醉酒駕車這一抽象危險犯之“危險”性質的理解有利于間接故意與自信過失兩者的區分。抽象危險犯之法益侵害的危險在某種程度上變化莫測、難以把握,行為人在實施行為時對這樣一種不明晰但客觀存在的危險所造成的法益威脅狀態要認識就很困難,那么要把握行為人行為時的意欲因素就更為困難。
“醉駕型”危險駕駛罪之間接故意的認定與本罪之法益侵害的危險是密切相關的,因為危險犯的規制對象乃危險行為,而危險行為的實施一般都伴隨有對法益侵害的危險性,行為人對危險結果即法益侵害的危險性所持的心理態度就是故意的意志因素。如果行為人持希望態度,則為直接故意;如果行為人持放任態度,則為間接故意。法益侵害的危險性是屬于行為所造成結果的危險性,其與行為本身的危險性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問題在于,行為本身的危險性往往與行為結果的危險性在抽象危險犯中幾乎無法做出區分,它們共同使法益處于一種受侵害的危險性狀態。實踐中,要區分到底是行為的危險還是行為結果的危險造成法益侵害的危險狀態幾無可能。法益侵害危險性的高低大小以及緊迫程度能夠表明行為人的認識程度,但對意欲因素并不是非黑即白,既可能反映行為人對法益蔑視也可能是消極不保護的態度。對抽象危險犯而言,刑法保護的是法益免受侵害的危險性,由于客觀存在物——法益侵害危險性難以被準確界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集主觀、客觀于一體的意欲因素之認知。因此,抽象危險犯之“危險”推定與間接故意“意欲”因素的推定具有重合性、同步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擬制的間接故意在抽象危險犯中有適用的余地。
在抽象危險犯中,確立擬制的間接故意概念是一種較為務實的選擇。申言之,只要行為人對危險行為有認識(構成要件事實),且行為具有導致法益侵害的可能性時,依舊作為或者不作為,從而推定行為人對危險結果的發生持放任的態度構成間接故意。從邏輯上看,擬制間接故意之認定直接推定行為人意志因素,似乎脫離了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的統一,與通說所堅持的罪過理論背道而馳。有論者可能會擔心,擬制的間接故意過分強調法益保護而忽視對人權的保障,甚至以過分犧牲個體的人權作為代價。如果危害行為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實害后果,刑法基于法益保護的需要做出間接故意的推定,還有其合理性,那么對于僅僅造成法益侵害危險的危險犯做出這種推定,似有本末倒置之嫌。
上述質疑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完全杜絕這種推定既沒有道理,也不可能。任何一項刑事立法都是法益保護與人權保障機能之統一,同時也是法益衡量的結果。抽象危險犯之立法意旨在于對法益保護階段的提前,重在強調社會防衛,這是風險社會下刑事立法對人們安全渴求的積極應對。另外,“法律的生命在于經驗而非邏輯”,僅僅依靠邏輯并不能應對變化莫測的現實世界,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決定了立法只是相對明確。擬制的間接故意是
經過利益衡量后的一種特殊的立法選擇、司法選擇,其適用應受到嚴格限制,而不是一種常態,這種推定是法規范價值選擇和司法實務需要的結果,有其合理性。
3. 擬制的間接故意適用限制
刑法做出間接故意推定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允許的,但是這種推定應當進行嚴格的限制。那么如何限制以及限制的依據何在呢?
筆者認為,基于實證的考察和經驗的積累,對危險行為侵害法益危險性大小進行評估,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即憑借統計學上的概率論,評估出危險行為對法益侵害危險性的蓋然性和可能性。據臺灣學者的研究表明,人體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0.05%(呼氣中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時,駕駛人的駕駛能力變壞,肇事概率為一般人的兩倍;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11%(呼氣達0.55)時,平衡感與判斷力障礙迅速升高,肇事率為一般人的十倍;如果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17%(呼氣達0.85)時,則會感到惡心、步履蹣跚,肇事率則上升為一般人的五十倍。[17]臺灣學者尹章華試圖以坐標表現的方式將危險量化,來證明行為人的意欲。[18]雖然蓋然性、可能性的標準不好掌握,但至少是一種積極的嘗試。
一般生活經驗法則一旦得到法律的確認,就上升為一種規范意識,那么刑法據此推定行為人實施該危險行為時持“放任”的心理態度,具有內在的合理性。刑法所處罰的危險犯都是對法益侵害危險具有蓋然性或者可能性的行為,而且指向的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即為了保護重大法益,這就決定了行為人只要實施這些行為,危險性就有可能上升到需要刑法評價的程度。“法律是一條帶哨子的辮子”,在打人之前必須要有預警機制。刑法明確規定實施某種危險行為構成犯罪,行為人依舊實施這類極其危險的行為,“放任”的主觀心理態度顯露無疑,刑法做出這樣的推定并不違背公平、正義之理念。
四、“醉駕型”危險駕駛罪之故意內涵的確定
通過前面的論述,筆者解決了兩大問題:一是故意醉駕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應構成危險駕駛罪;二是筆者提出擬制的間接故意概念解決了抽象危險犯之間接故意與自信過失危險犯難以區分的難題。基于前述兩個結論,“醉駕型”危險駕駛罪之主觀罪過為故意而非過失已經顯而易見④,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界定本罪故意的內涵。
我國臺灣地區“刑法”針對醉駕規定了“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也采用抽象危險犯的立法例,理論與實務中對該罪的主觀要件究竟是故意還是過失也存有很大爭議。如林山田教授認為:“本罪之故意應為,行為人對其服用、麻醉藥品、酒類或者其他相似之物而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有所認識,但仍決意駕駛之主觀心態,即具本罪之構成要件故意,包括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19]至于行為人是故意抑或使用麻醉藥品而致不能安全駕駛,則非所 問。[20]分析可知,飲酒即原因行為是故意還是過失并不影響本罪故意的認定,其實質在于只要行為人對其飲酒或嗑藥后會導致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有認識即可認定故意。也就是說,只要行為人認識到可能無法安全駕車,卻又放任這個危險,就構成本罪之故意。
綜上,我國臺灣地區“刑法”對“醉駕型”危險駕駛罪之故意之認識因素是明知道飲酒后不能安全駕駛,有可能危及到公共安全,意志因素是希望或者放任自己在此種危險情形下駕車。臺灣學者關于“不能安全駕駛罪”之故意內涵的界定就是基于行為人對自身行為危險性的認識來推定其對法益的“意欲”,同樣未能確證行為人對法益的態度如何,間接故意的認定實質也是推定,法律擬制的。
筆者認為,臺灣學者對“不能安全駕駛罪”之故意內涵的界定具有一定的參考借鑒價值。“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為抽象危險犯,立法者設立本罪的意圖是采取“零容忍”的政策,提高打擊范圍和打擊力度,但并不重罰,以期通過刑法的實施來規范和引導人們的行為,充分發揮刑法的道德效應和社會影響。加之現代社會交通危險是一類很普遍、高發的危險,人們能夠預知并有一定的容忍義務,刑法規定“醉駕型”危險駕駛罪,提前介入規制以防止嚴重危害結果的發生,是為了最大限度滿足民眾的安全渴求。行為人認識自己行為的性質和法律后果,而醉酒情形下駕車侵害法益的危險性是顯而易見的,那么這種情形下行為人仍然決定駕駛就表明對法益侵害結果并不反對,立法基于法益衡量的結果做出推定具有
合理性。
另外,“醉駕型”危險駕駛罪故意的認定應當限于抽象危險犯所保護法益的“射程”之內,即本罪所保護的法益只是公共安全免受侵害的危險性,這種危險只是一種抽象的蓋然性或可能性,而不能根據醉駕造成實害結果后進行事后判斷或推定。因為,醉駕者對于不特定或多數人的生命、健康以及財產權益受侵害顯然不可能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態度,但是對于這種侵害的危險性持希望或者放任態度并不難理解。前者已經超出了“醉駕型”危險駕駛罪保護法益的“射程”,而后者正是本罪規范價值的應有之義。
醉酒駕車有侵害法益的蓋然性、可能性應成為全社會的規范意識和一般的經驗法則。因此,行為人應該認識到醉酒駕車會威脅到公共安全法益,同時醉酒駕車的行為本身伴隨對公共安全法益的抽象危險,因此只要實施醉酒行為,那么行為人對法益侵害的危險結果持希望或放任態度并不難理解。我國法律對“醉酒”的認定標準是客觀標準,是量的標準,而行為人本身不大可能明知自己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否超過了80毫克,因此,不需要行為人認識到自己在駕車時處于醉酒的狀態,只要行為人認識到自己是飲酒后駕車即可。
綜上,筆者認為“醉駕型”危險駕駛罪之故意應這樣界定:明知自己飲酒后不能安全駕駛機動車而依然駕駛,對公共安全法益受侵害的危險性持希望或放任的態度。
注釋:
① 本文只研究醉酒駕車構成的危險駕駛罪,飆車構成的危險駕駛罪不在本文研究之列,下文為表述方便,對醉駕構成的危險駕駛罪簡稱為“醉駕型”危險駕駛罪。
②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傳統理論下的罪過只有故意、過失兩種形式,近年來有學者提出第三種罪過即間接故意與自信過失的混合罪過形式,也有學者建議引入英美法系的嚴格責任來豐富我國現有的罪過理論,后兩種罪過形式并未得到立法的確認,但在理論上進行探討具有價值。
③ 2008年12月14日中午,肇事司機孫偉銘醉酒駕車途中,酒量不支,在撞上一輛轎車的尾部后,駕車高速逃逸,連撞四輛車,造成4死1重傷的嚴重后果。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定孫偉銘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節特別嚴重,后果特別嚴重,依法判處死刑。后經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改判為無期徒刑。
④ 過失醉駕是存在的,比如隔夜醉酒。德國刑法就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其在同一法條規定過失醉酒駕車與故意醉酒駕車同樣處罰。我國臺灣地區“刑法”未規定處罰過失醉駕行為,對此,臺灣學界也存在是否處罰過失醉駕行為的爭論。
參考文獻:
[1] 周詳.“醉駕不必一律入罪”論之思考[j]. 法商研究, 2012, (1): 137?143.
[2] 趙秉志, 趙遠. 危險駕駛罪研析與思考[j]. 政治與法律, 2011, (8): 14?25.
[3] 馮軍. 論<刑法>第133條之一的規范目的及其適用[j]. 中國法學, 2011, (5): 138?158.
[4] 魏唯. 危險駕駛罪的法律分析與完善建議[j]. 東方企業文化, 2011, (10): 260?262.
[5] 張紅粱, 錢學敏. 嚴格責任下的醉駕型危險駕駛罪[j]. 西南政法大學學報, 2012, (3): 38?44.
[6] 李希慧. 刑法各論[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 53.
[7] 張明楷. 刑法學(第二版)[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545.
[8] 李立眾. 刑法一本通(第八版)[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94.
[9] 張明楷. 外國刑法綱要(第二版)[m].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7.
[10] 許玉秀. 當代刑法思潮[m]. 北京: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
[11] 洪福增: 論故意與過失之界限[j]. (臺灣)刑事法雜志, 1975, (6): 1?21.
[12] 劉仁文. 刑法中的嚴格責任研究[j]. 比較法研究, 2001, (1): 44?59.
[13] 張明楷. “客觀的超過要素”概念之提倡[j]. 法學研究, 1999, (3): 22?31.
[14] 儲槐植, 楊書文. 復合罪過形式探析—刑法理論對現行刑法內含新法律現象之解讀[j]. 法學研究, 1999, (1): 49?56.
[15] 高銘暄. 中國刑法學[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9: 169.
[16] 張明楷. 法益初論[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 95.
[17] 蔡中志. 酒后駕駛對交通安全之影響[j]. 警光雜志, 2000,
(522): 18?23.
[18] 尹章華. 論故意與過失之法理結構[j]. 軍法專刊, 1990, 36(6): 7?12.
第8篇:關于醉駕的處罰規定范文
[論文關鍵詞]醉酒駕駛;行為;定性
一、“醉酒駕駛”行為入罪必要性分析
(一)“醉酒駕駛”行為是否應當單獨入罪
盡管《刑法修正案(八)》已經明確規定“醉酒駕駛”行為構成危險駕駛罪,但刑法學界對于其是否應當單獨入罪的爭論并沒有停止。
一部分學者主張“醉酒駕駛”行為應單獨入罪,主要理由有:第一,我國當前危險駕駛導致重大傷亡的交通事故的機率非常高,為了從根本上遏制危險駕駛機動車輛導致重大交通事故的發生,減少對公共安全的危害;第二,醉酒駕駛屢禁不止顯示了醉酒駕駛違法成本太低,行政處罰不足以遏制醉酒駕駛行為;第三,我國已步入了風險社會,刑法應該對危險駕駛這樣的高風險行為提前介入;第四,單獨設立危險駕駛罪,對人民的法益提前予以保護,復合國際形勢立法的潮流。
一些學者則認為,“醉酒駕駛”行為不應單獨入罪,主要有:首先,按照當前的刑法罪名(如交通肇事罪、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完全可以對“醉酒駕駛”行為予以定罪處罰,對于較為輕微的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行為,也完全可以用行政處罰予以規制;其次,即使當前不存在對“醉酒駕駛”行為處罰具有比較有針對性的罪名設置,仍然可以通過對刑法進行必要的解釋來對此類行為進行規制。
筆者贊同對“醉酒駕駛”行為采取高壓態勢,嚴厲打擊醉酒駕駛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這是刑法保護法益的功能所決定的。同時,“醉駕入刑”的積極性,主要表現為“宣示”其對“醉駕”行為的明確否定,正如刑法理論界指出的,危險駕駛行為除“飆車”和“醉駕”之外,還包括吸毒后駕駛機動車、無證駕駛機動車等。然而立法者僅選擇前兩種行為作為危險駕駛罪的行為方式,絕不是因為由于“飆車”和“醉駕”具有更大的社會危險性關鍵原因在于:同“飆車”行為一樣,根源于我國獨特的“酒文化”,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在現實社會中更具普遍性,民眾對其深惡痛絕。由此,立法者在刑法對“民憤”給予回應,顯示出國家層面對“醉酒駕駛”行為的否定,從而更加“醒目”的對“醉酒駕駛”行為敲響警鐘。
(二)是否一切“醉酒駕駛”行為都應當入罪
《刑法修正案(八)》規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基于此,“醉酒駕駛”行為成立危險駕駛罪只需行為人有在醉酒狀態下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即可。然而,理論界和實務界并為達成一致。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指出,對“醉酒駕駛”行為追究刑事責任不應僅從文義上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對這類行為處理應當慎重。此種表態引起了輿論的熱議,質疑這種表態有造成司法不公的可能。
根據刑法通論,犯罪是指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懲罰性的行為。據此,作為犯罪行為,必須具有嚴重的社會危險性,其他適用法律不足以對其進行恰當的處罰。不具有社會危害性或是社會危害性不大的行為,即使表面上符合犯罪的形式要件,仍然不能作為犯罪,不能納入刑事處罰的范圍,這是刑法補充性和謙抑性的要求,是保障公民自由的要求,《刑法》“但書”也將這類行為排除在犯罪圈以外。基于此,“醉酒駕駛”行為盡管在法律文本中并未對危害結果或情節等有具體要求,仍然不能將一切行為都以危險駕駛罪論處。認定“醉酒駕駛”行為為醉酒駕駛罪仍然要考慮具體案件中的醉駕行為是否確實具有社會危害性,詳言之,即該行為是否確實會置公共安全于現實危險。該行為確實會造成對公共安全的威脅,且符合危險駕駛罪的主客觀要件,理所應當的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刑;倘若行為人的“醉酒駕駛”行為確實不會對公共安全造成任何危害,則不應對其科以刑罰,比如行為人凌晨時分在公路上(行為人平時多日觀察該段路程凌晨時分幾乎無任何車輛行駛)醉酒駕駛機動車回家。此外,筆者認為對將一部分“醉酒駕駛”行為作非罪化處理并不會招致司法不公,理由在于:將“醉酒駕駛”行為中的一部分作非罪化處理只是將那些社會危害性不大或是根本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醉酒駕駛”行為出罪,即此種出罪是有一定的標準可依,而非人為的任意出罪;并且,這類出罪的標準——“是否確實會對公共安全造成威脅”是可以通過具體的案件事實來反映的,并非不可捉摸。因此,在司法認定的過程中,嚴格把握對“醉酒駕駛”行為認定的標準是不易導致司法不公的。
二、“醉酒駕駛”行為入罪方式分析
(一)造成危害結果“醉酒駕駛”行為主觀方面定性分析
要準確對造成危害結果“醉酒駕駛”行為進行定性,首要的問題是對該行為主觀方面有正確的認識和界定。目前刑法理論界就此行為在主觀方面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是認為屬于過于自信的過失;二是認為行為人的主觀方面是間接故意,認為過于自信的過失的成立,需以“根據”(作出能夠避免危害結果這一結論的“依據”)客觀存在為前提,如確實有通常能避免結果發生的技術、體力、外在環境等等。但若該賴以親信的“根據”不是客觀的,而是行為人臆想的,則這時行為人的主觀意志因素就不是“輕信能夠避免”,而是“放任”。筆者贊同后一種觀點,認為行為人在此種情形下主觀方面應為間接故意。不可否認,在間接故意的犯罪行為中,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當然也不是積極追求的。然而在任何間接故意犯罪的情況下,都是以追求某種目的結果為前提的,正是這種目的結果,導致了行為人原先的不希望意志狀態發生性質上的變化,一旦行為人在這種目的支配下決意實施預定行為,于是原有的不希望意志形態自行消滅,轉化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報聽之任之的放任意志形態。現實生活中,一般人應有這種認識:酒精的攝入會降低機動車駕駛人員對機動車的駕駛能力,人在醉酒狀態下駕駛機動車與在正常狀態下駕駛機動車是存在明顯的駕駛感覺偏差。在這種認識下,行為人仍然在公共交通道路上駕駛機動車,顯然是對造成公共安全遭到損害這一危害結果的發生持包容態度。
(二)造成危害結果“醉酒駕駛”行為具體罪名認定分析
1.造成危害結果“醉酒駕駛”行為與交通肇事罪,造成危害結果“醉酒駕駛”行為如果構成犯罪,其主觀方面為間接故意,故應當排除性地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為根據理論通說,交通肇事罪是我國刑法中典型的過失犯罪。然而筆者看來不然,交通肇事罪的主觀方面值得進一步分析。根據我國《刑法》規定,交通肇事罪是指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毫無疑問行為人在主觀方面是過失。然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一)酒后、吸食后駕駛機動車輛的;(二)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的;(三)明知是安全裝置不全或者安全機件失靈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四)明知是無牌證或者已報廢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五)嚴重超載駕駛的;(六)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在這幾種危險駕駛行為下的交通肇事構成犯罪的,實際上在主觀方面應當定性為間接故意。由此,在這些情形下也是一種間接故意的犯罪。因而在理論界也有關于“復合罪過形式”罪名的提法。”但筆者并不認同交通肇事罪是這種“復合罪過形式”罪名的觀點,因為復合罪過形式是指一個行為是在多種罪過形式的支配下實施的。筆者所提出的故意的交通肇事罪的情形下,其實交通肇事行為仍然是在間接故意的支配下實施的,并不存在多個罪過形式。綜上所訴,在醉酒的狀態下交通肇事的行為只要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仍然應當以交通肇事罪論處,只是這種情形下交通肇事罪的主觀方面和傳統的交通肇事罪有所不同,表現為間接故意。
2.造成危害結果“醉酒駕駛”行為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9篇:關于醉駕的處罰規定范文
內容提要: “酒駕肇事”是對當前發生的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的酒后、醉酒駕駛行為的統稱。酒駕肇事行為人負刑事責任的根據在于行為人酒后、醉酒犯罪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后果;行為人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為與酒后、醉酒犯罪的結果行為之間具有直接因果關系;行為人實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為時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行為人實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為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我國《刑法》懲治酒駕肇事案件存在法條設置和刑罰制裁均缺失等方面的問題。
一、酒后、醉酒犯罪負刑事責任的根據問題
(一)酒后、醉酒犯罪的刑事責任能力特點
酒精對人體神經的毒害作用簡稱酒精中毒,也稱醉酒。醉酒一般可分為生理性醉酒和病理性醉酒。由于病理性醉酒屬于精神病的范疇,因此刑法上通常所講的醉酒是指生理性醉酒。
關于生理醉酒,醫學上一般將其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為興奮期,又稱輕度醉酒,表現為脫抑制現象,如興奮話多、情緒欣快、易激惹、容易感情用事、招惹是非等,此期控制能力有所減弱。第二期為共濟失調期,又稱中度醉酒,此時醉者動作笨拙、步履蹣跚、舉止不穩、語無倫次、辨認和控制能力都有減弱。第三期為昏睡期,又稱高度醉酒,此時醉者面色蒼白、皮膚濕冷、口唇微紫、呼吸緩慢伴有鼾聲,此期可有一定程度的意識障礙。[1]
根據飲酒量和酒精發作周期的不同,酒后、醉酒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能力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第一,在興奮期,行為人雖然出現脫抑制現象,控制能力也有所減弱,但行為人的辨認能力完好,能辨認和控制自己的行為,其對自己酒后、醉酒時實施的行為仍然可能具有完全的刑事責任能力。第二,在共濟失調期,行為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都有所減弱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其對自己酒后、醉酒時實施的行為不能完全辨認和控制。第三,在昏睡期,行為人已經出現了意識障礙,其對自己的行為既無辨認能力也無控制能力,屬于無刑事責任能力人。
(二)酒后、醉酒犯罪的主觀心態特點
第一,根據醉酒原因的不同,醉酒可分為自愿醉酒和非自愿醉酒。在非自愿醉酒中,行為人醉酒系不得已而為,其主觀并未預見到醉酒的危險性。因此,在一般情況下,非自愿醉酒者主觀上對自己的行為既無故意也無過失。當然,對因非自愿醉酒陷入限制責任能力而犯罪,則可根據犯罪時的心態確定是否成立故意或者過失,并可依《刑法》第18條第3款的規定對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第二,根據醉酒前有無犯意的不同,自愿醉酒又可以分為事前無犯意的醉酒和事前有犯意的醉酒。事前有犯意的醉酒,是指行為人出于逃避懲罰,減輕罪責的動機或想借酒精對神經的興奮作用來增強其犯罪勇氣,故意醉酒使自己陷入限制責任能力或者無責任能力狀態,并利用此狀態實施犯罪行為。事前有犯意的醉酒并因此而實施犯罪行為的,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
第三,根據醉酒后的責任能力狀態不同,事前無犯意的醉酒又可區分為:一是因醉酒而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的事前無犯意醉酒;二是因醉酒而陷入限制責任能力狀態的事前無犯意醉酒。對于第一種情形,一般來說,行為人實施行為時無犯罪的故意、過失,但其對醉酒時具有故意或者過失。對此,可依其醉酒時對危害結果的心態而成立故意或者過失。對于第二種情形,行為人不僅對醉灑行為有故意或者過失,而且對犯罪行為的危害后果也有故意或者過失。對此,可依其犯罪時心態而成立故意或者過失。
(三)酒后、醉酒犯罪與原因自由行為
原因自由行為是指行為人由于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于限制責任能力或者無責任能力狀態,并在此狀態下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2]行為人使自己陷入無責任能力或者限制責任能力狀態的行為,稱為原因行為;在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態下實施的符合犯罪構成的行為,稱為結果行為。[3]結合有關學說,我們認為,酒后、醉酒犯罪負刑事責任的根據主要在于:
第一,行為人的酒后、醉酒犯罪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后果。我國《刑法典》第1條規定,刑法的目的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因此,盡管刑法既要保護人權也要保障人權,但是從社會政策的角度,刑法立法應當以社會公共利益為重,保護社會的根本利益,對于嚴重危害社會利益的行為予以懲處。這是行為人對其酒后、醉酒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的社會基礎。
第二,行為人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為與酒后、醉酒犯罪的結果行為之間具有直接因果關系。行為人酒后、醉后犯罪行為是行為人飲酒這一原因行為所引起的。行為人是整個飲酒行為、酒后或醉酒犯罪行為的發動者。行為人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為和結果行為是一個行為整體,共同導致了危害后果的出現。行為人對此應當承擔刑事責任。這是行為人對其酒后、醉酒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的行為基礎。
第三,行為人實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為時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雖然行為人在實施危害行為時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或者只具有部分刑事責任能力,但是行為人在飲酒的時候完全能夠辨認和控制自己的行為,是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他有義務和能力控制自己的醉酒行為以防止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但卻沒有控制。因此,行為人應當對此承擔刑事責任。這是行為人對其酒后、醉酒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的行為人基礎。
第四,行為人實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為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雖然行為人在醉酒狀態下實施犯罪行為的當時無責任能力或責任能力受到限制,因而在主觀上可能不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者過失,但這種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態的出現是行為人故意或過失造成的。行為人應當對其故意或者過失實施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這是行為人對其酒后、醉酒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的心理基礎。
因此,基于原因自由行為理論,行為人應當對其酒后、醉酒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并且不能從寬處罰。
二、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法條設置問題
(一)我國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法條設置及特點
在我國刑法中,可以規制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法條主要是《刑法》第115條關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規定和第133條關于交通肇事罪的規定。我國《刑法》第115條第1款規定:“放火、決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第133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從我國《刑法》關于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法條設置看,它的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在立法方式上,刑法沒有專門設置有關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法條,而是將酒后、醉酒駕駛與其他相關的不法行為放在一起統一規定。這種立法方式,在效果上,不利于有效發揮刑法有針對性地懲治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作用。
第二,嚴格區分了故意和過失犯罪。在法條設置上,我國《刑法》嚴格區分了故意的酒后、醉酒駕駛犯罪和過失的酒后、醉酒駕駛犯罪,并分別設置罪名。其中,對于故意的酒后、醉酒駕駛犯罪,依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對于過失的酒后、醉酒駕駛犯罪,則依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只有當先前的肇事行為必然會造成當事人的死亡時,其逃逸行為,即‘不作為’才能構成間接故意殺人罪。”[4]而交通肇事中過失的確立與認定與現代社會的信賴原則密不可分。[5]
第三,在犯罪的成立條件上,規定必須發生了嚴重危害后果才負刑事責任。根據我國《刑法》第115條和第133條的規定,酒后、醉酒駕駛,只有發生了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才負刑事責任。在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構成中,除要求以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為前提外,發生重大事故的結果是個非常重要的罪與非罪界線和適用不同量刑檔次的標準。[6]
(二)我國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法條設置缺失
第一,沒有將酒后、醉酒駕駛行為入罪。韓國2009年4月1日修訂的《道路交通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在醉酒狀態下駕駛車輛。對于違反者該項規定醉酒駕駛者,將被處以3年以下徒刑或者一千萬韓元以下罰金。[7]但是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在我國,酒后、醉酒駕駛只有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后果才成立犯罪,單純的酒后、醉酒駕駛行為不是犯罪。這使得對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懲治延后。
第二,沒有規定拒絕酒精檢測的刑事責任。酒精檢測是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酒后、醉酒駕駛的重要保證。在國外,有不少國家規定對拒絕酒精檢測的行為可追究刑事責任。如韓國《道路交通法》就規定,交通警察在有相當理由認為駕駛人員處于醉酒狀態而駕駛人員拒絕酒精呼吸檢測的,要被處以3年以下徒刑或一千萬韓元以下罰金。但我國目前沒有這方面的規定。
第三,沒有將酒后、醉酒駕駛的部分共犯行為人罪。關于酒后、醉酒駕駛的共犯,日本2007年9月19日生效的《道路交通法》對酒后駕車做出了嚴格的規定,除對酒后駕車者本人嚴加懲處之外,還設有“車輛提供罪”、“酒水提供罪”以及“同乘罪”等新罪種。[8]這實際上將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多種共犯行為分別入罪了。我國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通過的《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將部分指使、強令酒后、醉酒駕駛的行為納入了交通肇事罪的范圍,但并沒有規定提供車輛等幫助行為可以入罪。
三、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刑罰制裁問題
(一)我國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刑罰制裁檢視
關于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刑罰制裁,主要體現為我國《刑法》第115條第1款關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第133條關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規定。
在法定刑的設置上,我國《刑法》第115條第1款關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規定是“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我國《刑法》第133條關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則分為三檔,即“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國關于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刑罰制裁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對過失的酒后、醉酒駕駛犯罪,法定刑設置很輕。根據我國《刑法》第133條的規定,在過失的情況下,對酒后、醉酒駕駛犯罪,最高只能判處7年有期徒刑。而同樣的情況,在日本可以判處15年有期徒刑,在英國可以判處10年有期徒刑。相比而言,我國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設置非常輕。
第二,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的法定刑相差懸殊。根據我國《刑法》第115條、第133條和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在同樣是酒后、醉酒駕駛致1人重傷的情況下,對過失的酒后、醉酒駕駛致死的,最高只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而對故意的酒后、醉酒駕駛致死的,則最低可判處10年有期徒刑、最高可判處死刑。兩罪的法定刑相差幅度較大。這為司法中的定罪量刑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為了防止量刑的規范,有必要建立案例指導制度和量刑規劃化制度。[9]
第三,在法定刑的設置上,沒有體現出酒后駕駛與醉酒駕駛的區別。國外不少國家和地區在酒后、醉酒駕駛犯罪法定刑的設置上都區分了酒后駕駛和醉酒駕駛。一般情況下,醉酒駕駛犯罪的法定刑要高于酒后駕駛犯罪。如根據日本《道路交通法》規定,對于醉酒駕車者處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萬日元以下罰款;飲酒駕車者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萬日元以下罰款。[10]但是,我國刑法沒有酒后駕駛肇事和醉酒駕駛肇事的法定刑進行區分。
(二)我國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刑罰制裁缺失
第一,沒有規定罰金刑。對酒后、醉酒駕駛犯罪規定罰金刑,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通行做法。如韓國《道路交通法》關于醉酒駕駛罪和拒絕酒精檢測罪都規定了一千萬韓元以下的罰金。芬蘭《刑法典》關于迷醉狀態下駕駛、嚴重迷醉狀態下駕駛等犯罪中也都規定了罰金刑。對酒后、醉酒駕駛犯罪規定罰金刑,有利于剝奪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從加強對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懲治。我國《刑法》沒有在有關懲治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條文中規定罰金刑,是一個立法缺失。
第二,沒有規定資格刑。酒后、醉酒駕駛的資格刑主要是指吊銷駕駛執照和禁止駕駛。英國《1991年道路交通法》規定,醉酒或吸毒陷于不適宜狀態而駕駛車輛的,剝奪駕駛的期限不少于2年。在我國香港地區,兩次或者多次實施醉酒駕駛犯罪的,一般要吊銷不少于2年期限的駕駛執照,并處罰金。在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了暫扣、吊銷駕駛執照以及禁止駕駛。但是,我國刑法中并沒有相關規定,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處罰非常輕。因此,即便在對行為人判處刑罰的同時由公安交通部門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對酒后、醉酒駕駛者暫扣、吊銷駕駛執照或者禁駕,行為人仍然可以很快重新駕駛。這不利于對酒后、醉酒駕駛犯罪的懲治與預防,應當進一步加強刑法與《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相關行政法規的協調。[11]
四、結語
我國刑法在懲治“酒駕肇事”案件方面,既存在法條設置上的缺失也存在刑罰制裁上的缺陷。但是,基于原因自由行為理論,出于保護社會利益的需要,我們必須加大懲治“酒駕肇事”行為的力度,為此需要從刑事司法、刑法立法等多個方面尋找解決的方案,“在立法技術的層面,刑法立法要處理好立法簡明與立法細密的關系”[12]。事實上,只有進一步嚴密懲治“酒駕肇事”行為的法網,并進一步加大刑法對“酒駕肇事”行為的懲治力度,才能充分發揮刑法懲治“酒駕肇事”行為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參見湯濤、黃富穎:《原因上的自由行為與急性酒中毒的司法精神病鑒定》,載《法醫學雜志》2000年第4期。
[2]參見林山田:《刑法通論》,臺灣三民書局1984年版,第176頁。
[3]參見趙秉志:《論原因自由行為中實行行為的著手問題》,載《法學雜志》2008年第5期。
[4]參見龔昕炘、劉佳杰:《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適用分析》,載《法學雜志》2008年第6期。
[5]參見毛元學:《信賴原則在交通肇事罪中的適用》,載《法學雜志》2009年第6期。
[6]參見黃偉明:《交通肇事罪構成中結果標準的數量因素分析》,載《法學雜志》2005年第2期。
[7]參見《韓國:新增醉酒駕駛車輛罪》,載《法制日報》2009年9月1日。
[8]參見陳曦:《關注酒后駕車:日本嚴懲酒后駕車同乘供酒者并罰》,www.xinhuanet.com,訪問日期:2009年8月20日。
[9]參見王瑞君:《案例指導量刑與量刑規范化》,載《法學雜志》2009年第8期。
[10]參見陳曦:《關注酒后駕車:日本嚴懲酒后駕車?同乘供酒者并罰》,www.xinhuanet.com,訪問日期:2009年8月20日。
- 上一篇:安全教育的意義和重要性范文
- 下一篇:數字化學習的概念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