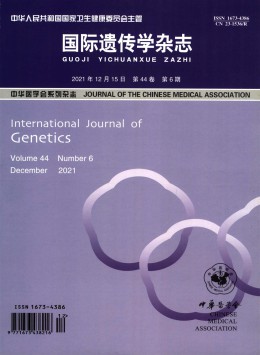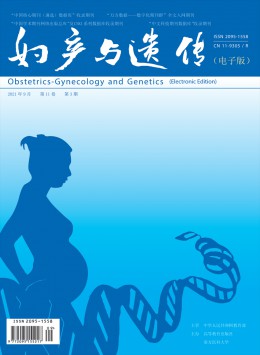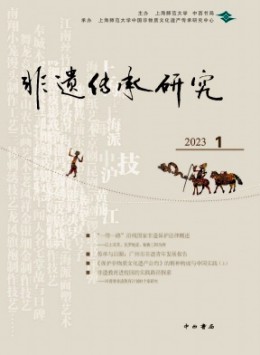遺傳學分離定律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遺傳學分離定律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遺傳學分離定律范文
關鍵詞:規律 生物學 歷史性 特異性
一、引言
規律或定律(law)觀念是傳統科學和哲學的基本信念。 這種觀念的本質就是亨普爾概括的“演繹—規律論”解釋模型。根據這一模型,科學的本質就是發現現象背后不變的聯系,并把它們建立成規律體系。對單個事件的解釋就是要把這個事件從這些規律和初始條件中演繹出來。這就是說,如果要對一個事件的發生做出科學的解釋,就必須把這一事件歸并到已經發現的一條或幾條定律之下。否則,這一事件就是不可理解的。
“演繹—規律論”解釋模型把規律看作是科學最本質的東西。那么什么是規律呢?一般人們認為一個陳述如果滿足如下條件就是一個規律或定律:(1)普遍性標準,即該陳述必須包含普遍限定詞, 不涉及任何具體的個體、時間和空間地點;(2)可檢驗性標準, 即該陳述必須具有經驗內容,并已得到確證;然而滿足這兩個條件還不能說是一條定律,它還必須滿足第三個往往被大多數人忽略的標準,即(3 )連貫性標準,就是說這個陳述必須能夠整合到一個更大的理論體系之內,或者說它必須從屬于一個更大的理論,因而有理論上的根據和保證。
“演繹—規律論”解釋模型既說明了科學的本質,又指出了科學結構及其運作過程。這種解釋模型,其主要依據是物理科學,不論是經典物理、經典化學還是現代物理和現代化學,都采取的是這種演繹規律論的方法或覆蓋定律的方法進行運作的。這種解釋模型適合與物理科學之外的其他學科嗎?或者說其他學科是否也要把它們的理論建立成規律性的理論體系?是否也要把它們要解釋的事件歸并到規律之下?
本世紀中期,生物學日益成為可以與物理科學相抗衡的新學科,生物科學因此成為檢驗傳統科學哲學普適性的一個新標本。所以從六十年代開始,大量的思想家開始從生物科學出發研究哲學,他們或者用生物科學檢驗已有的哲學理論,或者從生物科學中概括出新的哲學思想。這里,規律問題自然成為新的科學哲學家們重新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1963年,著名的科學哲學家斯瑪特(J.J.C.Smart )通過對生物科學的考察認為,嚴格意義上講,只有物理學和化學才具有規律,生物學中并不存在規律。因為物理學和化學中概括具有普遍性,“它們可以適合于時空中的任何地方,”“并且可以用非常完美的普遍概念來表達而不使用專有名詞或暗中提到專有名詞。”(〔1〕,p.53 )然而生物學就不同,生物學中的陳述,比如“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在斯瑪特看來就不是規律性的陳述。因為天鵝是根據它們在進化樹中的位置定義的。這樣的定義隱含著一個特殊的指稱——我們的地球。這個特殊的指稱使該命題不符合前述的標準(1)。當然, 人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定義天鵝,比如通過提到天鵝所擁有的特性來定義,但是,這樣做的話,我們就沒有理由認定那種陳述在整個宇宙中都是成立的,因為其他星球可能有不是白的天鵝,盡管它們有我們所定義的特性(即與標準(2 )不符)。另外,它也不符合標準(3)。 因為這樣的陳述并不能整合到更廣的生物學理論中去,也不能從其它生物學理論中推導出來。
為什么物理學和化學與生物學相比在規律上有較優越的地位呢?斯瑪特認為這與它們研究的客體的性質有關。物理學和化學研究的客體是相對簡單和均一的系統,其組成成分比如基本粒子被認為在宇宙中是無所不在的。而生物客體則不同,它們相對來說是復雜的,并且具有特異性,它們是自然史中一定階段的產物或客體,所以在宇宙中是受時空限制的。貝爾納也曾這樣說過:“我認為生物學和所謂精確的或無機的科學、特別是物理學之間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在無機科學里,我們假定宇宙結構所必須的基本粒子以及支配它們運動和轉化的定律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一般都適合于整個宇宙。另一方面,生物學則涉及對宇宙中那些極其特殊的部分,即對我們所謂生命的描述和有序化。當前,說得更具體些,就是地球上的生命。它象地理學一樣,主要是一門描述性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在特定的時間內、特定行星上一批特別有組織的實物的結構和作用。”所以,貝爾納說,目前的生物學不具有普遍性,但貝爾納認為應當有一門真正普遍的生物學。
著名的生物進化論專家恩斯特·邁爾進一步論證并發揮了斯瑪特等人的觀點,認為規律的觀念是物理主義、本質主義觀念的必然結果,在生物學中必須擯棄。([2],p.41)邁爾認為,生物學是19 世紀的產物。在19世紀以前,作為獨立的生物學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些零散的與生物學有關的研究傳統。但那時物理科學已經比較發達,所以當17世紀和18世紀科學哲學家們發展他們哲學思想時,完全是以物理科學為基礎的。物理科學的規律,特別是牛頓力學規律的解釋和預言作用給哲學家們以深刻的影響,以致于這個時代的哲學家都把建立規律作為科學的決定性標準。當時的生物學家也不例外。早期的生物學家象拉馬克、達爾文等就都以揭示生物界的規律為己任。然而100多年過去了, 生物科學獲得了長足的進展,在涉及生命現象的各個領域都建立起了生物學分支。然而,奇怪的是;各生物學分支中都很少提到“規律”二字。邁爾認為,這不是偶然的,因為生物學中并不存在普遍定律,生物學中的概括一律具有例外。他說:“生物學中只有一條規律,那就是所有的概括都有例外。”([2],p.41)與斯瑪特類似,邁爾認為生物學概括具有例外的原因是,生物學努力描述的事件是歷史的、特異的事件。任何生物都是長期進化的結果,都與歷史相關,都具有獨特性。這就要求我們,對生命現象的解釋不能象物理科學那樣是由規律提供的。事實上,邁爾把規律觀念看作是本質主義的錯誤結果。本質主義是由柏拉圖發展起來并一直支配西方思想界的哲學思潮。在本質主義看來,可變化的現象世界只不過是固定不變的本質的反映。世界上真實和重要的東西就是這些本質,現實世界的變異只是內在本質的不完備的表現。因此,不變性和不連續性是本質主義特別強調的論點。邁爾認為,這種思想在今天是有其局限性的,它必須被新的群體思想所代替。群體思想與本質主義相反,它認為,重要的東西不是本質而是個體。許多生命現象,特別是種群現象是以高度的變化為特征的,進化的速率或物種形成的速率彼此的差別有三到五個數量級,這種變化程度在物理現象中是很少有記錄的。物理世界的實體具有不變性的特征,而生物實體卻以可變性為特征。生物實體的這種特異性告訴我們,必須用與研究完全均一的無生命的東西完全不同的精神來研究生命現象。這種新精神就是要擺脫規律思想的影響,充分考慮到生物體的歷史特異性。
與斯瑪特、邁爾等人類似,著名科學哲學家波普爾也斷言進化生物學中沒有規律。他認為,由于地球上的生命進化或者人類社會的進化只是一個單獨的歷史進程,因此,對進化過程的描述就不是規律性的描述,而只是一個單純的歷史陳述。所以,波普爾認為,探索進化的“不變秩序”和“規律”是不可能的。([3],pp.85—86)
這么多的思想家否定生物學中存在規律,是不是生物學中真的沒有規律?這些思想家的觀點一經提出,就有其他思想家從不同側面提出自己的否定意見。
二、例外的出現與連貫性標準的作用
斯瑪特、邁爾等人的觀點,概括起來可以歸結為:(1 )生物學中的概括一律具有例外,不是全稱普遍陳述,原因是(2 )生物客體具有歷史性、特異性、非均一性。針對第一點,魯斯(M.Ruse)認為,生物學中的概括比如孟德爾定律有例外,但這不損壞它作為一條定律。事實上,它是一條真正的規律,因為例外可以由生物學家作出合理的闡釋。只要我們考慮到生物的較低水平及適當的邊界條件,發生在表型水平的例外可以根據細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上的變化得到說明。比如孟德爾自由組合定律的一些例外就可以根據亞細胞水平的基因連鎖與互換得到解釋。〔4〕魯斯的這種論證表明,連貫性(coherence)在討論“普遍性”時將起重要作用。在經典遺傳學中,對孟德爾定律的連貫論解釋采取的是縱向整合的形式(vertical integration),即對組織不同層次的整合。通過這種整合,宏觀層次(或表型層次)的規律及其例外,可由微觀層次(基因層次甚至分子層次)的規律推導出來。
哈爾(D.Hull)也認為,通過不同層次之間的理論整合,是建立生物學規律的唯一可能。在《生物學的哲學》一書中,哈爾曾舉出個體發育的例子。他認為,個體發育階段的順序性是受規律控制的,但在我們把描述這種發育順序的陳述看作規律之前,我們需要找到能把它們從中推導出來的有關系統的規律。這樣做,我們就不能局限在表型層次,而必須深入到生物體的基因型中,看這些基因型是如何起作用而控制這種特殊的發育過程的。對于系統發育,哈爾給出了相似的論證。他認為,生物表型特征關系的陳述可以被看作是規律,只要我們的認識已擴展到指出有機體的遺傳構造以及產生這些表型特征的生化反應。[5]不過, 哈爾不象魯斯那樣樂觀。魯斯認為經典遺傳學已經基本整合到分子遺傳學中,而哈爾認為這種整合仍存在許多障礙。
列旺汀(R.C.Lewontin)也有類似的思想,他認為,在群體遺傳學中有許多假定的一般規律,但很難檢驗它們。所以,群體遺傳學要想成為一門成熟的科學,人們必須建立起一種聯結基因型和表現型水平的整合理論,有了這種整合理論,群體遺傳學中規律才能真正成為規律。[6]
可以看出,魯斯、哈爾、列旺汀等人對生物學規律的連貫性辯護實際上就是要把高層次的概括還原到低層次的理論。由于這種辯護采取的是理論還原的策略,所以,關于這種辯護的反對意見自然也就從反駁理論還原的可能性入手。因為,如果理論還原或縱向整合存在困難或者是不可能,那么,采用這種方式為生物學規律辯護,說服力就會大大降低。魯斯曾竭力論證經典遺傳學可還原為分子遺傳學。哈爾承認這種縱向整合的可能性,但也看到這種整合的困難,看到目前人們還遠遠未做出這種整合。今天,雖然生物學的快速發展已使我們能從基因水平解釋越來越多的表型層次的特征及其關系,但畢竟我們尚不能解釋許多事情。所以,魯斯和哈爾等人的結論是建立在未經證實的哲學假設之上的。也許這種假設是正確的,但這畢竟是一個假說而已。
斯蒂因(W.J.Van der Steen)看到縱向整合的困難,所以, 他采取一種新的連貫論策略為生物學規律辯護—橫向整合或水平整合(horizonal integration)。他認為, 人們不應當把縱向整合看作是為生物學規律辯護的唯一途徑。同一組織層次上的理論整合也可以使我們在生物學中建立普遍規律。比如說,孟德爾的分離律具有例外,像透明金魚與不透明金魚雜交,子一代是半透明金魚,而不像顯性規則所說的那樣只呈現一種性狀,即顯性性狀。子一代的金魚互相,子二代不是呈現3:1的比例,而是1:2:1的性狀比,即透明金魚和不透明金魚各占一份,半透明金魚占兩份。對此,生物學家解釋說,顯性具有相對性,即對有些相對性狀來說,并沒有哪個性狀占絕對顯性,哪個性狀占絕對隱性,所以,透明金魚和不透明金魚雜交,子代有半透明金魚。另外,遺傳上的并顯性,互換等都可以通過引進補充性假設來解釋,而不必采取縱向整合的形式。這種解釋例外的方式,斯蒂因稱之為水平整合,即在同一組織層次上的整合。所以,斯蒂因說,連貫性不必采用縱向整合或還原論的形式,水平整合也是確保生物學規律存在的理論根據。(〔7〕,p.450)
三、物種特異性能否定規律的存在嗎?
斯瑪特和邁爾等人否定生物學規律的存在,一個重要的根據是生物客體的獨特性、變異性和歷史性。確實,與物理實體比如原子、分子相比,生物實體物種具有高度的變異性和獨特性,但變異性、獨特性能成為否定生物規律的可靠依據嗎?
哈爾和邁爾一樣反對本質主義,承認生物實體與物理實體的不同,但哈爾并沒有因此走上否定生物學規律的道路,而是努力尋求為生物學規律辯護的新的方法。
哈爾認為,對生物學沒有普遍規律的指責源于對種的類別的本體論地位的誤解。生物的物種是歷史進化的實體,這種歷史性使物種不具有某種特殊的本質。 所以, 哈爾認為, 物種不是某種自然類(naturalkinds)。物種不是自然類,那么物種是什么呢? 對物種獨特性的強調使哈爾提出了一條令西方思想界廣泛討論的命題:物種是自然個體(natural inpiduals)或自然特殊物(natural particulars)。在哈爾看來,物種類似于一個特殊的有機體。有機體由許多部分組成,但不包含成員,并且,特殊有機體的部分之所以是這個有機體的部分,是因為這些部分之間具有時空的和因果的聯系。這一點與類中的成員要求具有某類性質相反。金中的成員都具有共同的原子結構這一特性,這些成員并不依賴與其他金塊的特殊的時空關系和因果關系。物種的個體與個體之間就不同,它們彼此之間都有著特殊的時空關系和因果關系,因為物種是在一定區域內聚合在一起連續的聯合性實體(或歷史實體)。物種之所以是時空上連續性的實體是因為物種是進化的單位,即能夠通過自然選擇進化的實體。物種通過自然選擇進化,必須滿足三個條件:(1)變異,即有機體的性狀與親代相比具有差異性;(2)不同的適應力,即有機體性狀的變異使它們各自具有不同的適應能力;(3)遺傳, 即變異的性狀必須是可遺傳的。其中,條件(3)非常關鍵。 一個性狀當它通過繁殖被忠實地傳遞給下一代就是遺傳,而繁殖是一個時空上特化的過程一雙親和胚胎必須具有時空上的連續性。所以,性狀傳遞給物種的后代,條件是那些后代必須通過繁殖關系在時空上互相連接。因而,唯有形成時空上連續的實體,物種才可能通過自然選擇進化。由于物種的個體與個體之間具有時空上的連續性和因果關系,所以物種不是有機體的種類,它的成員不是它的特例;相反,每一個物種都是個體,一種時空上受限制的特殊客體,其成員是它的部分和組成,不是它的例子。
轉貼于 哈爾認為,如果物種是個體,進化生物學就不應當被指責沒有自然定律。考慮到氣象學和地理學中的一個類似情況。在氣象學和地理學中,沒有關于特殊氣象現象和特殊巖石的組成部分的規律,但并沒有人指責氣象學和地理學中沒有規律。氣象學和地理學的規律存在于不同的本體論水平之上,這些規律涉及是一般的氣象現象、一類巖石(比如大理石)、以及組成那些巖石的一類元素(比如金和鐵)。同樣的考慮也適用于進化理論和物種。也許并沒有涉及某一特殊物種所有成員的規律,但這并不表示進化理論沒有普遍規律。在進化理論中,物種是個體,不是類,所以,如果進化理論中有規律,這些規律將存在于其他本體論水平之上。哈爾認為存在關于一類物種的規律,比如群體生態學家談到的K—選擇物種和R—選擇物種——生活在穩定環境和非穩定環境中的物種,對它們的共同特性的概括就可以看成是規律。另外,也存在關于一類群體的規律。比如邁爾的地理成種概念詳述了弧立種群何時變為新種,哈代一溫伯格定律預言在一定種類的隨機群體中發現的基因的頻率。[8]
與哈爾類似,羅森伯格也認為,物種的個體性并不影響在生物學中建立規律,因為,“生物學中的一般發現并不建立在有關特殊物種的規則之上”,而是“建立在所有物種都與之適合的規則之上”的([9],p.205)。在羅森伯格看來, 生物學中關于所有物種的經驗概括有兩類:一類是最低水平的概括,比如:“非特化物種比特化物種趨于滅絕的時間要長”,“物種在進化過程中體形趨于增加”,“生活在相同環境中的現代物種趨于以相同的方式變化”等等。這類概括與其他經驗概括一樣有例外,但是這些例外可通過訴諸于第二類更普遍的經驗概括來解釋。這些較高水平的概括就是生命科學中的規律。羅森伯格認為,這種經驗概括與比如“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等陳述不同,如若其他條件保持不變,在其他有生命的星球上也是可以期望獲得的。這樣的規律有哪些呢?羅森伯格列出了以下五條:
(1)物種是在有機體中傳遞下來的宗譜分支(lineage of decent a-mong organisms)。
(2)任何一個物種后代的生物體數有一個上限。
(3)每一個有機體與它的環境之間都有一定程度的適應性。
(4)在一個物種中,如果D是一個在生理上和行為上都相似的亞族(subclass),且D 比該物種的其他成員在適應性上許多世代都足夠優越,那么在該物種中D的比例將增加。
(5)在一個不是處于滅絕邊緣的物種的每一個世代中, 都有一個亞族D,它比該物種的其他成員更優越,且有足夠長的時間確保D相對于該物種成比例增多,并將獲得充分的優越性繼續增加,直至在某一時間達到構成整個物種的活的成員。([9],p.212)
羅森伯格認為,這些定律與前面第一類經驗概括不同,它們沒有例外。這些生物學定律沒有提到特殊的物種,并且它們把物種看作是特殊進化的宗譜分支,而不是有機體的類型、集體或種類。
魯斯也捍衛生物學規律。但在處理物種的特異性問題上,他與哈爾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盡管在處理生物學概括例外問題上他們有著相同的思維方式(即他們都采取連貫論的思維)。哈爾和羅森伯格等人把物種看作是個體而不是自然類,魯斯等人則認為物種是自然類而不是個體;哈爾和羅森伯格等人把生物學規律看作是超越物種層次之上的普遍概括,否定關于個體物種規律的存在,魯斯等人則認為關于物種成員的規律是存在的。
魯斯指出,如果象哈爾所說的那樣沒有關于特殊物種規律的話,那么,任何關于人類自身的特有主張就都不是規律,因為它們都是關于單一物種—人類屬性的研究。因此,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科學、歷史科學、語言學等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事實上,由于物種不是個體,而是自然類—即同一物種之所以是同一物種,就是因為它們的成員共有某一性質,因此,關于某一特殊物種的所有成員的普遍陳述是可能的。([10],p.225)凱切爾(Kitcher,P.)也認為存在關于具體物種的生物學規律,因為我們能找到這樣的性質P,它們與物種S特有的遺傳組成的關系非常密切,以致于P的不存在就意味著這種遺傳組成的變化, 并導致新種的出現或不能存活的個體出現,這樣“凡S必有P”這類陳述就是可以得到的。([11],p.312)
四、歷史敘述可以代替規律解釋嗎?
“演繹—規律論”的科學解釋理論把科學看作是由各種互相關聯的定律組成的規律體系。如果生物學不存在規律,那么生物學還是不是科學,特別是與功能生物學相差較遠的進化生物學還是不是科學?一些人走得很遠,他們認為進化論不是科學的理論。斯瑪特、波普爾等人都是如此。邁爾也否認生物學定律的存在,但他并沒有因此否定進化理論的科學性,相反他認為,人們應當改變對科學的傳統觀念。他說:“有一些科學并沒有運用無可爭辯的被稱為定律的表達方式也運行得非常順利。”([12],p.20)邁爾所說的“有些學科”最主要指的就是生物學。
既然生物學中沒有定律,那么生物學中的解釋是如何進行的呢?邁爾認為,生物學的解釋方式采取的是不同于物理學的歷史敘述的方式。他說:“規律觀念遠遠沒有歷史敘述的觀念那樣有助于進化生物學。”([2],p.140)這就是說,在生物學中歷史敘述比規律解釋更重要。
岡奇(T.A.Gondge)也有類似思想。岡奇曾經指出:“在討論生命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單個事件的時候,敘述性解釋進入了進化生物學……敘述性解釋的建構一點也沒有提到一般規律,……進化過程中的事件不是某種事件的例子,而是單獨發生的事,是某種只發生一次,不能〔以同一方式〕再發生的事情,這時候要求敘述性解釋……歷史性解釋構成進化理論的基本部分。”([2],p.77)
在邁爾等人看來,歷史敘述具有解釋價值,是因為生物學的對象—生命客體是歷史客體,在歷史過程中,早先的生命事件通常對后來的事件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白堊紀末期恐龍的滅絕留下了許許多多的生態小生境,為哺乳動物在古新世和始新世向四面八方的驚人發展提供了空間,因此,歷史敘述的目標之一就是發現后繼事件的原因。然而,在邁爾看來,“那些由基本邏輯公理系統訓練出來的哲學家,看來是很難理解特異性和事件歷史序列的特殊性的。他們想要否認歷史敘述的重要性,并想用結構性法則把它們公理化,但他們的想法并沒有說服人。”([2],p.77)
確實有許多人指出,歷史敘述并不能否定規律解釋。比如魯斯就認為,敘述性解釋的推理過程或者總體上不能令人滿意,或者在解釋過程中或明或暗地運用到規律。舉例來說,描述到生物演化史上的歷史事件時,經常要運用“適應”、“優越性”等概念,然而這些概念只能在自然選擇和群體遺傳學的背景中才能被理解。所以,歷史敘述具有解釋價值,必須有理論上的保證。這些理論雖然在具體敘述時未提及,但它們卻在知識背景中起作用。所以,魯斯認為,不是贊成規律解釋的人的思想沒有說服人,而是否定規律解釋的人的觀點沒有說服人。
在我看來,魯斯說的不無道理,然而,我們也應看到,在生物學中,獨特性確實比物理學和化學更普遍,因為生物體在結構上是如此的復雜,以致于它們顯示出更多的變異和個性。邁爾等人希望人們關注到這一點,希望人們用特殊的詞恰當地描述生物事件,若不是走得太遠的話,是包含有合理因素的。因為在很多情況下,生物事件是如此的復雜,以致于完全的解釋需要訴諸于許許多多的規律和初始條件,這時,人們在實踐上就不得不滿足于描述性工作或者“大略解釋”工作。在作大略解釋時,人們可能要用到規律,但這些規律可以不表現出來,而只是停留在背景知識中。我們不必用非常精確的形式把它們表達出來。所以,在生物學中,歷史敘述的解釋形式很普遍,但我們應知道,歷史敘述并不否認規律解釋。
五、結論:走向新的解釋
規律觀念的本質涉及的是科學理論的結構及科學的運作方式。傳統科學哲學認為科學是通過建立越來越普遍的規律向前發展的,規律或定律的建立,既是科學理論成熟的標志,又是科學解釋和預言的依據。我國的科學哲學研究幾乎無例外地都認為科學是由規律經演繹形成的理論體系。如果我們忽視了科學的具體實際,這種觀點仿佛很是圓滿。但當我們面對具體的各門科學時,會發現這樣的理論圖景其實是依據物理科學得出的,并主要適合于物理科學。當代生命科學正如邁爾所說,幾乎很少用到規律或定律一詞(只有遺傳學中有所謂的三定律和哈代—溫伯格定律等少數例外)。達爾文進化論對生物學就象牛頓力學對經典物理一樣重要,然而達爾文進化論并不象牛頓力學那樣由幾條規律經數學演繹形成理論。生命科學理論在實踐上缺乏定律或規律!
生命科學在規律或定律上的缺乏說明了什么?是傳統的科學哲學有問題?還是生物學迄今還不是一門成熟的科學?如果生物學存在規律,生物學是否也應當建立成類似牛頓力學、愛因斯坦相對論那樣的規律體系?
依我看,傳統規律觀念有其深厚的理論基礎,從生物客體的歷史性、特異性出發,從概念上否定生物學中存在規律,尚缺乏較堅實的理論基礎,所以我們必須從另外的角度尋求生物學缺乏規律的原因。實際上,生物學理論在規律上的缺乏完全是由生物學所面對的問題與物理科學不同所造成的。物理學最關心的問題是物質本身所內涵的性質,所以必須借助大量抽象的符號來描述,因此,物理學很容易就走入數學的世界,建立數學的邏輯工具。但是,生物學的重心一開始就落在結構上面,諸如什么動物長什么樣子,擁有什么樣的器官,長在什么位置,構造和功能有什么關系等等。即使是最近的生物學進展,其重心依然在結構上面,從細胞的各種顯微構造到基因的構筑及表現,還有各種生物大分子的三維空間的立體結構等等,生物學家們一直致力的,是如何將各種生命現象在實體形象上求得解釋。所以,生物學家最常用的表達方式便是“看圖講故事”,亦即對于已知的構造經由類比聯想去闡釋其功能。在生物學中敘述性解釋成為主要的解釋方式,物理科學中那種從規律(由數學公式表示)出發,經由嚴格的數學推理的解釋方式很少出現在生物學里。從早期孟德爾的遺傳實驗,到摩爾根對染色體的解釋,直到近期分子生物學的發展,實際存在的構造成了理論好壞的依據。一個理論成功與否完全依賴其是否能將所觀察到的現象嵌附到已知的結構上去。于是,結構變成了所有解釋的出發點。染色體也好,DNA雙螺旋也好, 都是如此,在這里,數學形式的邏輯推理派不上用場,結構的合理性才是最好的解釋手段。另外,由于生物系統及其環境的復雜性,也必須限制在該領域建立一般視律或定律來解釋詳細細節,所以,生物學家在建立他們的理論體系時,通常更強調先在條件而不是一般規律。
從本世紀五十年代起,許多哲學家從不同方面對邏輯實證主義發起了進攻,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科學哲學思潮。然而,實際上邏輯實證主義思想仍然在背后支配著許多人的行動。許多人仍然認為一般定律的多少是“好科學”的標志就是一例。然而,我認為,在科學中,除了普遍性推理之外,人們也需要結構性描述,并且在一定的背景中,結構性描述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生物學中缺少定律而有更多的敘述性解釋,并不一定是生物學的消極特征。生物學不但是一門真正的科學,而且其成就及其思維方式必然要引起哲學的新的變革。
參考文獻
[1] J. J. C. Smart, Phibosophy and Scientific Realis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3.
[2]邁爾:《生物科學思想的發展》,劉jùn@①jùn@①等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3]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 杜汝楫譯, 華夏出版社,1987。
[4]Ruse,M.,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Hutchinson,1973.
[5]Hull,D.,Phiosophy of Biological Science, Pretice- Hall,1974.
[6]R.C.Lewontin,The Genetic Basis of Evolutionary Chan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7]Steen,W,J.Van der and Kamminga,Harmke:Laws and NaturalHistory in Biology,Brit.J.Phil.Sci.1991(42).
[8]Hull,D.,The Metaphysics of Evolution, 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1989.
[9]Rosenberg,A.,The Structure of Biological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10]Ruse,M.,Biological Species:Natural Kinds, Inpiduals or What?Bri.J.Phil.Sci,1987(38).
第2篇:遺傳學分離定律范文
【關鍵詞】 雙相障礙;認知功能;遺傳學;病例對照;數量性狀
中圖分類號:R749.4,B84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729(2011)004-0295-07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1.04.013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11,25(4):295-301.省略
【Abstract】Objective:To examine the relation of bipolar disorderⅠ and cognitive function to rs947267 polymorphism of G72 gene.Methods:Totally 202 patients with euthymic bipolar disorderⅠand 103 normal controls were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Edition (DSM-Ⅳ).The cognitive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 digit symbol,trail making test (TMT),digit span,visual reproduction,verbal fluency,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 and tower ofHanoi (TOH).And rs947267 polymorphism were tested.Analysis of covariance was used to compare cognitive function between patients and normal controls.Case-control and quantitative characters were used in genetic analysis.Results:(1)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s,BD patients were impaired in digit symbol,time of TMT-A,time of TMT-B,digit span,visual reproduction,verbal fluency,WCST and TOH (P0.05).(3) In patients group,the TMT-B time was shorter in those with genotype of AA than in those with genotype of AC (P
【Key words】 bipolar disorder;cognitive function;genetics;case-control;quantitative characters
(Chin Ment Health J,2011,25(4):295-301.)
雙相障礙的谷氨酸假說認為,谷氨酸能系統,尤其是N-甲基-D-天冬氨酸(N-methyl-aspartate,NMDA)受體的過度激活可引起情緒癥狀、神經毒性、神經元死亡等[1]。G72基因編碼的蛋白是D-氨基酸氧化酶(D-amino acid oxidase,DAO)激動劑,而DAO是NMDA受體的激動劑[2]。研究結果顯示G72基因可能是雙相障礙的易感基因之一[3]。此外,近年的研究提示認知功能損害可能是精神疾病的遺傳內表型。雙相障礙患者即使在穩定期也存在認知損害支持此觀點。精神分裂癥患者[4]和正常人群[5] 中的研究也顯示G72基因可能與認知損害關聯。目前國內尚未見G72基因與雙相障礙的相關研究報道,國內外未見進一步結合患者認知功能的相關研究。本課題小組前期研究已表明穩定期雙相障礙患者確實存在注意、記憶和執行功能面的認知損害[6-7],但目前國內外同類研究結果也不一致[8]。故本研究在繼續收集樣本的基礎上進一步檢驗前期對于穩定期雙相障礙認知功能的研究結果,并探討雙相障礙和認知功能與G72基因的關系。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收集2006年8月至2009年3月在廣州市精神病醫院門診和住院部的雙相障礙患者242例。入組標準:①符合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4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Ⅳ,DSM-Ⅳ)雙相障礙Ⅰ型診斷標準[9],診斷有分歧者則排除;②漢密頓抑郁量表(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10]評分<7分;③Young躁狂量表(Young Mania Rating Scale,YMRS)[11]評分<6分;④穩定期≥3個月。穩定期指末次發病后臨床癥狀控制,病情穩定。排除標準:①合并其他精神障礙;②認知功能評定前1年內接受電痙攣治療;③嚴重軀體疾病;④腦外傷后意識障礙史,或其他腦器質性疾病;⑤色盲、色弱、耳聾或口吃。正常對照組來自廣州市精神病醫院及其他單位員工、學生等,共162名。入組標準:①既往無精神障礙史;②二系三代無精神疾病家族史。排除標準同患者組③④⑤。
患者組有40例未抽取外周靜脈血,最后入組202例,男82例,女120例,年齡18~67歲,平均(30±10)歲,受教育年限0~17年,平均(11.4±3.0)年。病程4~492個月,中位數38個月(P2516個月,P7584個月)。穩定期3~60個月,平均(8.5±7.2)個月。發病年齡10~59歲,平均(24±9)歲。穩定期評定認知時患者組服藥情況:未服藥5例,服藥197例,其中1種藥物65例,2種藥物120例和3種藥物12例,主要是心境穩定劑單一使用(n=65)或合并抗精神病藥物(n=118),個別合并了苯二氮艸卓類藥物(n =2)、苯海索(n=2),合并新一代抗抑郁藥9例。碳酸鋰90例[(1011.1±217.5)mg/d],丙戊酸鈉91例[(1067.6±295.3)mg/d];抗精神病藥物:主要是喹硫平65例[(317.3±216.4)mg/d],利培酮23例[(3.1±1.0)mg/d],個別使用氯丙嗪和氯氮平(分別為3例和7例,均<300mg/d)。評定時藥物劑量穩定時間均在30d以上。 對照組59名未抽取外周靜脈血,最終入組103名,男47名,女56名,年齡18~58歲,平均(34±12)歲,受教育年限2~19年,平均(12.0±3.8)年。
所有受試者均為漢族,右利手,對研究知情同意。2組間的性別、受教育年限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但年齡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3)。
1.2 入組診斷與量表評估
入組時采用DSM-Ⅳ軸Ⅰ障礙臨床定式檢查(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 Axis I Disorders,SCID-Ⅰ)[12]評估受試者的精神狀況。本研究中的患者均為本院經過半年以上門診隨訪的患者,臨床診斷(高級職稱醫師負責)已明確為雙相障礙,而入組時統一由在讀研究生采用SCID-Ⅰ再評估,診斷無分歧者方納入本研究。所有受試者均進行HAMD、YMRS評分,評定者間一致性選取10例患者進行,Kappa值為0.79~0.83。
1.3 認知功能評定
參與認知功能評定者研究開始前進行培訓,由2名精神科在讀研究生及1名專職科研護士進行評定。測驗在安靜環境中連續進行。按實際測驗順序依次使用了以下工具。
①修訂韋氏成人智力量表手冊[13]中的數字符號和數字廣度[包括順背、倒背和總分(順背+倒背)]。②修訂韋氏記憶量表手冊[14]中的視覺再生(甲套)。上述3個測驗均采用粗分,得分越高成績越好。③連線測驗(Trail Making Test,TMT)[15]:包括A、B兩部分,評定完成時間,時間越短成績越好。④言語流暢性測驗(動物)[16]:記錄正確數。正確數越多越好。⑤威斯康星卡片分類測驗(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17],以分類數、總錯誤數、持續錯誤數作為評定指標。分類數越多成績越好,總錯誤數、持續錯誤數越少成績越好。⑥漢諾塔(Tower of Hanoi,TOH)[18]:選用3木塊及4木塊操作手工版,共12個測試。以計劃時間、執行時間和完成測驗所得總分作為主要評定指標。時間越短成績越好,總分越高成績越好。數字符號、連線測驗主要檢測受試者的注意功能,數字廣度、視覺再生主要檢測受試者的記憶功能,言語流暢性測驗、WCST和TOH測驗主要檢測受試者的執行功能。所有癥狀量表和認知功能評定在同一天內完成,后者耗時30~60 min。
1.4 G72基因rs947267多態性檢測
1.4.1 DNA提取
抽取受試者外周靜脈血10 mL,ACD2 mL抗凝。按酚-氯仿法常規提取DNA。
1.4.2 基因型檢測
①引物。采用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網站提供的DNA序列,利用Primer Premers 3在線軟件設計引物。L:5'-AGT TTC TGC CTT AAC ACA TTT AGG T-3',R:5'-GAA AAT ACC CGG AGT CTC ACA TA-3'。②PCR反應。反應體系:10×PCR緩沖液3.0 μL,Dntp 8mmol,正反向引物各6 pm,TaqDNA聚合酶0.3 U,基因組DNA100 ng,滅菌蒸餾水加至30 μL。反應參數:95 ℃預變性3 min,32個循環(95 ℃變性20 s,61 ℃退火30 s,72 ℃延伸30 s),72 ℃延伸5 min。
1.4.3 酶切及電泳
取PCR產物5 μL,加5U內切酶HaeⅢ,37 ℃下消化4~6 h,8 %的非變性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分離酶切產物,銀染并觀察結果。若為A等位基因,401bp的PCR產物不被酶切;若為C等位基因,PCR產物則被酶切成248bp和153bp。根據電泳帶型確定基因型。
1.5 統計方法
采用SPSS13.0處理數據。所有認知測驗結果采用粗分,未經轉換。符合正態分布的數據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或χ2檢驗(性別構成比)。由于認知功能可受年齡、性別、受教育年限的影響,故組間認知功能的比較采用以上述變量為協變量的協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LSD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數據采用中位數(25%位數,75%位數)即[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Kruskal-Wallis檢驗。遺傳學資料采用PLINK1.07[19](http:∥pngu.mgh.harvard.edu/purcell/plink/)軟件分析,包括Hardy-Weinberg平衡檢驗、病例-對照分析及以認知功能作為數量性狀的關聯分析。
2 結 果
2.1 病例組和對照組的認知功能比較
將年齡、性別和受教育年限作為協變量進行組間協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病例組的數字符號、TMT-A時間、TMT-B時間、數字廣度各項指標、視覺再生、言語流暢總數、WCST各項指標和TOH各項指標的成績均差于對照組(P
2.2 G72基因rs947267多態性與雙相障礙的關聯分析
病例組和對照組的基因型經Hardy-Weinberg平衡檢驗,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定律(χ2=2.81,0.323;P=0.094,0.556),表明本研究的各組樣本均來自隨機婚配的自然群體。病例組和對照組的rs947267多態性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頻率見表2,兩組間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頻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2.18,0.09;,P=0.336,0.769)。
2.3G72基因rs947267多態性不同基因型組的認知功能比較
按rs947267多態性的不同基因型分組比較認知功能。患者組中,不同基因型組的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病程、穩定期和發病年齡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正常對照組中,不同基因型組的性別、年齡和受教育年限差異也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3)。
協方差分析顯示,患者組中不同基因型組間的TMT-B時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3.67,P=0.027),兩兩比較顯示,AA基因型組成績好于AC基因型組(P
2.4 G72基因rs947267多態性和雙相障礙認知功能數量性狀的關聯分析
在控制了年齡、性別和受教育年限后,將所有認知測試分值作為定量遺傳指標,采用PLINK軟件的linear過程分析與等位基因A的關聯。結果顯示,在患者組中rs947267多態性與TMT-B時間存在關聯,攜帶等位基因A的患者TMT-B成績較未攜帶者好(r=-6.92,P=0.015);在正常對照組中rs947267多態性與TOH總分關聯,攜帶等位基因A者TOH成績較未攜帶者差(β=-3.05,P=0.019)。
3 討 論
為了提高樣本的同質性,本研究只納入了雙相障礙Ⅰ型患者。本課題小組前期研究結果顯示,患者組的多個注意、記憶和執行功能指標的成績均比正常對照組差[6-7]。此次在患者組樣本量增加的基礎上進一步比較,結果顯示,患者組的數字符號、TMT-A時間、TMT-B時間、數字廣度各項指標、視覺再生、言語流暢總數、WCST各項指標和TOH各項指標的成績均比對照組的差,驗證了前期研究結果,只是兩組有差異的指標增加了TOH的計劃時間,考慮是樣本量增加、統計效能提高所致。患者組TOH的計劃時間增長提示患者計劃調整能力差,是一種執行功能的損害。
G72基因在13q33上,有5個外顯子,4個內含子。Chumakov等[20]首次報道G72基因和分裂癥關聯。兩個來自美國的家系研究報道了雙相障礙和G72基因存在連鎖不平衡[21],Schumacher 等[22]和Chen等[23]對于雙相障礙的病例-對照研究也支持上述結果。rs947267位于第3內含子上,有研究結果顯示與分裂癥關聯[24],但目前尚未見該位點在雙相障礙中的相關報道。故本研究探討了G72基因rs947267多態性與雙相障礙的關系,但結果未發現二者存在關聯。不過,Zhang等[25]在中國漢族人群中的研究顯示,G72基因的另一個多態性rs778293位點與雙相障礙關聯。他們探討的SNP位點與本研究不同,這可能是兩個研究結果不同的原因之一。同時,也可能與本研究正常對照樣本量偏少有關。
既往研究顯示,G72基因可能與認知功能存在關聯[4,26]。認知功能可受年齡、性別和受教育年限的影響[27],故本研究以上述變量為協變量進行協方差分析以及數量性狀遺傳分析,進一步在患者組和正常對照組中分別探討了G72基因rs947267多態性與認知功能的關系。結果顯示,在兩組中該基因多態性對認知功能的影響不盡一致。在患者組中AA基因型的TMT-B成績較AC基因型的好,認知數量性狀分析也顯示,攜帶等位基因A的患者TMT-B成績較未攜帶者好;在正常對照組中,AA基因型的TOH總分成績較AC基因型差,數量性狀分析也顯示,攜帶等位基因A者TOH總分成績較未攜帶差。其中,上述不同基因型組間雖僅有AA組和AC組間比較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但從具體數據來看,AA、AC、CC基因型組間的成績都呈階梯趨勢,提示CC組與AA、AC組無差異可能是因CC組樣本量偏小的緣故,值得擴大樣本量后加以驗證。總之,本研究結果提示,雙相Ⅰ型患者中AA基因型和A等位基因可能與TMT-B反映的注意轉換認知維度有關;在正常對照組中,AA基因型和等位基因A可能與反映執行功能認知維度的TOH總分有關;總體提示G72基因可能對認知功能有一定影響。未見既往研究探討G72基因rs947267多態性與認知功能的關系,但可見該基因其他多態性的相關研究。Soronen等[26]對雙相障礙的研究結果表明,G72基因rs3916966和 rs2391191多態性與視覺空間記憶存在關聯。而在精神分裂癥患者中同類研究的陽性結果更多些,Goldberg等[4]的研究顯示G72基因多態性與操作記憶、注意損害關聯。Opgen-Rhein等[27]的研究顯示,G72基因與操作功能關聯。Goldberg等[4]的研究與本研究均提示G72基因與注意損害可能有關,只是患者的疾病診斷不同。不過,近年來遺傳研究等發現精神分裂癥和雙相障礙存在許多交叉。目前在患者中報道G72基因與認知功能關聯的研究較少,各研究檢測的認知維度也不盡一致,以致各研究結果的可比性受影響。目前,已見初步探討正常人群中認知功能遺傳的研究,有研究顯示G72基因rs3918342和rs1421292多態性與正常人群的言語、空間工作記憶關聯[5],其中工作記憶也是對執行功能認知維度的反映,故與本研究正常人群的結果有一致性。
4 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僅初步探討了G72基因的單個多態性,正常對照的樣本量也偏小。但本研究結果提示,在雙相障礙Ⅰ型患者或正常人群中,G72基因對認知功能均可能有影響。未來的研究可進一步探討G72基因與不同人群不同認知維度的關系,更進一步了解G72基因在雙相障礙及認知功能中的作用。本課題小組正在開展這方面的工作。
參考文獻
[1]Kugaya A,Sanacora G.Beyond monoamines:glutamatergic function in mood disorders[J].CNS Spectr,2005,10(10):808-819.
[2]洪武,方貽儒,汪作為.G72基因與抑郁癥的關聯研究[J].中華遺傳學雜志,2006,23(5):523-525.
[3]Kato T.Molecular genetics of bipolar disorder and depression[J].Psychiatry Clin Neurosci,2007,61(1):3-19.
[4]Goldberg TE,Straub RE,Callicott JH,et al.The G72/G30 gene complex and cognitive abnormalities in schizophrenia[J].Neuropsychopharmacology,2006,31(9):2022-2032.
[5]Jansen A,Krach S,Krug A,et al.A putative high risk diplotype of the G72 gene is in healthy individuals associated with better performance in working memory functions and altered brain activity in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J].Neuroimage,2009,45(3):1002-1008.
[6]林鄞,曹莉萍,溫光池,等.穩定期雙相障礙Ⅰ型患者執行功能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2008,34(11):641-644.
[7]曹莉萍,林鄞,李,等.穩定期雙相障礙Ⅰ型患者的認知功能及相關因素[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9,23(10):713-717.
[8]Robinson LJ,Thompson JM,Gallagher P,et al.A meta-analysis of cognitive deficits in euthymic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J].J Affect Disord,2006,93(1-3):105-115.
[9]美國精神病學會.DSM-Ⅳ分類與診斷標準[M].龐天鑒,譯.楊森文庫,2001:20~32.∥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M].4th Ed.Washington DC: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1994.
[10]Hamilton M.A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J].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1960,23(1):56-62.
[11]Young RC,Biggs JT,Ziegler VE,et al.A rating scale for mania:reliability,validity and sensitivity[J].Br J Psychiatry,1978,133(5):429-435.
[12]First MB,Spitzer RL,Gibbon M,et al.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 Axis I & Axis II Disorders [M].Version 2.0.New York:Biometrics Research,New York State Psychiatric Institute,1995.
[13]龔耀先.修訂韋氏成人智力量表手冊[M].長沙:湖南醫科大學,1989:4-16.
[14]龔耀先.修訂韋氏記憶量表手冊[M].長沙:湖南醫科大學,1989:15-16.
[15]Lu L,Bigler ED.Performance on original and a Chinese version of Trail Making Test Part B:a normative bilingual sample[J].Appl Neuropsychol,2000,7(4):243-246.
[16]郭啟浩,張明園,Simon D,等.一組評估認知功能的神經心理測驗在老人中的應用[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1994,2(3):155-157.
[17]Nelson HE.A modified card sorting test sensitive to frontal lobe defects[J].Cortex,1976,12(4):313-324.
[18]Simon HA.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of problem solving skills[J].Cognit Psychol,1975,7(2):268-288.
[19]Purcell S,Neale B,Todd-Brown K,et al.PLINK:a tool set for whole-genome association and population-based linkage analyses[J].Am J Hum Genet,2007,81(3):559-575.
[20]Chumakov I,Blumenfeld M,Guerassimenko O,et al.Genetic and physiological data implicating the new human gene G72 and the gene for D-amino acid oxidase in schizophrenia[J].Proc Natl Acad Sci U S A,2002,99(21):13675-13680.
[21]Hattori E,Liu C,Badner JA,et al.Polymorphisms at the G72/G30 gene locus,on 13q33,are associated with bipolar disorder in two independent pedigree series[J].Am J Hum Genet,2003,72(5):1131-1140.
[22]Schumacher J,Jamra RA,Freudenberg J,et al.Examination of G72 and D-amino-acid oxidase as genetic risk factors for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J].Mol Psychiatry,2004,9(2):203-207.
[23]Chen YS,Akula N,Detera-Wadleigh SD,et al.Findings in an independent sample support an association between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and the G72/G30 locus on chromosome 13q33[J].Mol Psychiatry,2004,9(1):87-92,image 85.
[24]Shi J,Badner JA,Gershon ES,et al.Allelic association of G72/G30 with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disorder:a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J].Schizophr Res,2008,98(1-3):89-97.
[25]Zhang Z,Li Y,Zhao Q,et al.First evidence of association between G72 and bipolar disorder in the Chinese Han population[J].Psychiatr Genet,2009,19(3):151-153.
[26]Soronen P,Silander K,Antila M,et al.Association of a nonsynonymous variant of DAOA with visuospatial ability in a bipolar family sample[J].Biol Psychiatry,2008,64(5):438-442.
相關熱門標簽
相關文章閱讀
相關期刊推薦
精選范文推薦
- 1遺傳病論文
- 2遺傳學顯性基因隱性基因
- 3遺傳學基因突變
- 4遺傳學的問題
- 5遺傳學在生活中的應用
- 6遺傳學在農業上的應用
- 7遺傳學和分子研究
- 8遺傳學分離定律
- 9遺傳學在育種中的應用
- 10遺傳學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