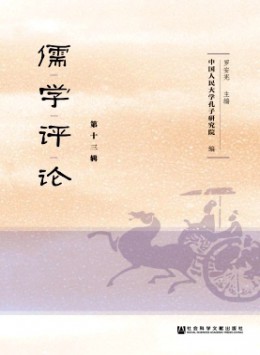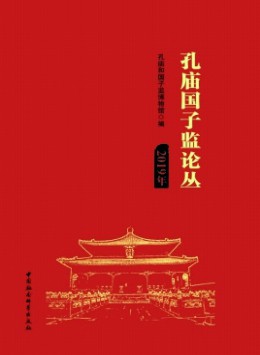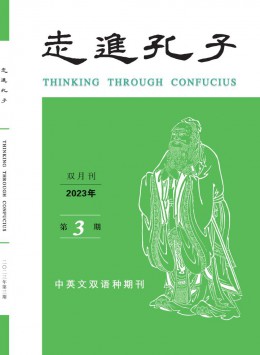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相同點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相同點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相同點范文
[關鍵詞]邵雍物理之學性命之學心學先天之學后天之學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
能知萬物備于我,肯把三才別立根。
天向一中分體用,人于心上起經綸。
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這首詩是北宋道學五子之一的邵雍寫的,題目叫《觀易吟》,詩中流露了作者參透天人、觀易見道的智慧,顯示了作者博大舒放的宇宙胸懷和洞明深湛的生命意識。
當代研究者一般偏重于研究其《觀物篇》中的“物理”之學,而比較忽略其“性命”之學。其實邵雍不僅是宋易之區別于漢易的開風氣的人物,而且還是宋明理學“心學派”的開拓人物,他不僅建構了一套縝密的宇宙論圖式,而且創立了獨具特色的性命學說、修養理論與價值系統,并最終完成了他的以“物理”推論“性命”的“先天易學”體系。唯其如此,才備受二程、朱子等理學大師的稱贊。邵雍的人文情懷、安樂精神和真善境界,不僅對后世易學家、理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當今的世俗人生仍然有著可資借鑒的意義。
一、天人相為表里,推天道以明人事
“天”和“人”的問題是邵雍象數哲學的基本問題。邵雍在《觀物外篇》中說:“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他把易學分為兩類,一類是研究物的,即“天學”,又稱“物理之學”;另一類是研究人的,即“人學”,又稱“性命之學”。合而言之即“天人之學”。邵雍還用了兩個概念:“先天之學”與“后天之學”,其中“先天之學”是研究天道自然的,相當于“天學”;“后天之學”是研究人道名教的,相當于“人學”。①
在對待天人的關系上,如果說儒家偏向于人道,道家偏向于天道;義理易學派偏向于人道,象數易學派偏向于天道,那么邵雍則是儒道互補(或內儒外道)、天人并重、象數與義理貫通的集大成者。天道與人道,天學與人學、先天與后天、物理之學與性命之學,被邵雍巧妙而自然地融進他的易學中。他在《觀物內篇》中說:
天與人相為表里。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系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
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天地人物則異矣,其于道則一也。
邵雍引用《易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的“天道”觀,將“天道”歸結為陰陽、剛柔;同時繼承并改造了《易傳》“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的“人道”觀,將人道歸結為“正邪”,“仁”與“義”都屬“正”的范疇,與之相對的應該是“邪”。在邵雍看來,人之正邪與天之陰陽、剛柔是互為表里的關系,雖然各自的表現千差萬別,但都統一于“道”上。邪正來源于君主的好德好佞,君主的好德好佞又是天道崇陽崇陰的折射。
就天道與人道的地位而言,表面上看,邵雍似乎更重天道,他不僅將自己的著作稱為“觀物篇”,以“觀物”為認識天道的重要思維方法,而且將人看成是“物”——“天”的一分子,認為“盈天地萬物者唯萬物。”然而實際上并不是這樣,從立論路徑上看邵雍是先論天道后論人道,先論先天后論后天,先論物理后論性命,而推天道、先天、物理是為了明人道、后天、性命,人道、后天、性命才是邵雍的立論目的,天道、先天、物理不過是邵雍的立論根據。用邵雍的話說,它們之間是“體用”關系,先天為體,后天為用,后天從屬于先天,后天闡發的人性、人道高于先天闡發的物性、天道。這里的“先天”與“后天”是相對關系,邵雍又把“先天”與“后天”統稱為“先天之學”。先后天是體用不離,相函相依的,體者言其對待,用者言其流行,是一個統一的天人之“道”的兩個不同方面,同時又是一個統一的“道”的變化過程的兩個不同階段。邵雍將宇宙演化的歷史過程以唐堯時期為界分為兩段,唐堯以前為先天,此時還是宇宙自然史時期,還沒有人文、社會、主觀等因素的參與,還沒有人事之“用”,只有天然之“體”;唐堯以后的后天“用”,進入到人類文明史時期。根據這種劃分,邵雍對儒家和道家作了評價,指出老子為得《易》之體,孟子為得《易》之用,今人余數康先生認為,道家的物理之學著重于研究宇宙的自然史,可稱之為“天學”,對先天之“體”有獨到的體會;儒家的性命之學著重于研究人類的文明史,可稱之為“人學”,對后天之“用”闡發得特別詳盡。老子有天學而無人學,孟子有人學而無天學。盡管老子和孟子學派門戶不同,分屬道儒兩家,仍是體用相依,并來分作兩截,道家的“天學”與儒家的“人學”會通整合而形成一種互補性的結構,統攝于《易》之體用而歸于一元。邵雍稱物理之學即自然科學為“天學”,性命之學即人文科學為“人學”。在物理之學上推崇道家,在性命之學上推崇儒家,超越了學派門戶之見,從儒道互補的角度來溝通天人,他的這個做法是和《周易》的精神相符合的。②
邵雍對“天”和“人”、“天道”和“人道”作了多角度的界說,其《觀物外篇》說:
自然而然者,天也;惟圣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也。
元亨利貞,交易不常,天道之變也;吉兇悔吝,變易不定,人道之應也……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兇悔吝,《易》之應也。
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濟未濟,以人事也。《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離,終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認為自然的、非人為的是“天”,效法天然之道、參與主觀意識的是“人”。就《周易》而言,上經言天道,下經言人事。元亨利貞四德配春夏秋冬四時,反映了在天道四時以及自然萬物的變易流行;吉兇悔吝反映了人事的變化規律。天道和人事相互對應,“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奉天時則吉,違天時則兇,元亨利貞四德各包含吉兇悔吝四事,吉兇悔吝四事又對應元亨利貞四德。邵雍在《觀物內篇》中從另一角度歸納天道人道:“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陰陽、剛柔是天道本然的現象和規律,而領悟并運用這種規律的卻是人。
邵雍將“人”看成是“萬物之靈”,天地宇宙之間充盈了萬物,人是萬物中有靈性的出類拔萃者,人靈于物;人中可分出一部分最優秀的人,就是圣人,圣靈于人。“人之所以靈于萬物者,謂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觀物內篇》)萬物的色、聲、氣、味能被人的目、耳、鼻、口所接受,具有其他事物(包括動物、植物)所達不到的靈性、智慧,遠遠超出其他事物接受宇宙的信息的能力,不僅如此,人還可以改造或適應宇宙的信息、事物的運動變化,“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觀物內篇》)而人中之“圣”又具有一般人所達不到的智慧,“然則人亦物也,圣亦人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邵雍對人中的至者——圣人作了界定:
人之至者,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音,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彌倫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里人物者也。(《觀物內篇》)
這樣的圣人不是隨便什么人都可以見到的,只有“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可以理知之也。”在邵雍看來,除了伏羲、黃帝、堯、舜、周文王、周武王、齊桓公、晉文公以外,只有孔子稱得上“圣人”。孔子整理修定了《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四部經典,邵雍將春夏秋冬稱為“昊天之四府”,將這四部經典稱為“圣人之四府”,兩者一一對應,《易》為春,為生民之府;《書》為夏,為長民之府;《詩》為秋,為收民之府;《春秋》為冬,為藏民之府。將四府交錯組合,則有四四一十六種,如《易》與《易》、《書》、《詩》、《春秋》組合,則有生生,生長、生收、生藏四種。其余類推。認為這四部經典是為了貫天人、通古今。
邵雍還將人類生理結構與物類形態結構作了比較,認為兩者雖有區別,但又有對應關系,《觀物外篇》說: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肢。
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何也?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干巨而葉繁,應天地數也。
人之四肢各有脈也,一脈之部,一部三候,以應天數也。
動者體橫,植者休縱,人宜橫而反縱也。
飛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兩手,翅也;兩足,趾也。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于萬物也。
不僅將人的四肢、十六象、一脈三部九候、形態特征等與天地之數相對應,而且將人與其他動物進行比較,從而說明人是稟天地之氣生,是天地萬物之中最聰明、最優秀的品種。此外,邵雍還對人的五臟、六腑、五官、七竅的來源作了分析,《觀物外篇》說:
體必交而后生,故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陽與柔交而生肝膽,柔與陰交而生腎與膀胱,剛與柔交而生脾胃。心生目,膽生耳,脾生鼻,腎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
心藏神,腎藏精,脾藏魂,膽藏魄,胃受物而化之,傳氣于肺,傳血于肝,而傳水谷于脬腸矣。
認為人的五藏六腑由陰陽、剛柔交合而生,人不僅與外部的天相對應,而且人體本身內在的臟腑與外在的器官、與精神意志一一對應,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對應與《黃帝內經》不同,《內經》主張心開竅于舌,肝開竅于目,腎開竅于耳與二陰,脾開竅于口,肺開竅于鼻;心藏神,腎藏意,脾藏志,肝藏魂,肺藏魄。邵雍可能另有所本,但這種將人視為宇宙天地的全息系統,以一身統貫三才之道,“神統于心,氣統于腎,形統于首,形氣交而神交乎中,三才之道也”,則可視為《易經》和《內經》天人合一思想的體現,是“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的分層描述。
二、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性命之學的建構
邵雍是一個由道入儒,由儒入道、儒道通貫的學者,早年師從李之才學習物理之學、性命之學(事載《宋史·道學傳》、《宋元學案·百源學案》),其后在明自然的物理之學上推崇道家,建構一套帶有厚重道家色彩的推衍宇宙萬物的物理學體系,從而獲得“觀物之樂”;在貴名教的性命之學上推薦儒家,建構了一套帶有濃厚儒家色彩的宣揚人文價值理念的性命學體系,從而獲得“名教之樂”。道家的物理之學與儒家的性命之學,被邵雍歸結為“易”中,邵雍認為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易》之體用兼綜道、儒,在邵雍那里并沒有象朱熹批評的那樣“體用自分作兩截”,而是在《易》的大道統帥下,儒道二家之旨、物理與性命之學(即天學與人學)、內圣與外王之功,被合理地、自然地統一起來,既沒有邏輯矛盾,又沒有斧鑿生硬之嫌。可以說:邵雍是以“易”貫通儒、道③的重要代表人物。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周易·說卦傳》對“易”所下的命題之一,邵雍對此作了解釋:
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觀物內篇》)
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者,天下之真知也。(《觀物內篇》)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理窮而后知性,性盡而后知命,命知而后知至。(《觀物外篇》)
“性命之學”即邵雍所稱的“人學”。所謂“性”指人性,所謂“命”指天命,所謂“理”指物理。這三者同歸之于“易”之大“道”——即陰陽變化之“道”、天人合一之“道”,太極一元之“道”……顯然邵雍是參合了《周易》與《中庸》而得出這個結論的,《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能致命于人,進而賦予人的本性,遵循本性的自然發展而行動就是“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是一個最高范疇,能夠統領“性”、“命”、“理”于一體,邵雍說“《易》之為書,將以順性命之理者,循自然也。”性命之理即是自然之“道”,也就是《周易》之“道”的體現。這個“道”是無處不在的,“道”在物則為“理”,在人則為“性”。“命”是由天決定并賦予人而為人所具有的。張行成對邵雍性命學作了闡釋:
命者,天之理也。物理即天理。異觀私,達觀則公矣,公則道也。(《皇極經世索隱》)
性命,天理、物理都歸結于“道”。所以邵雍說:“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天地萬物之道盡于人矣。”天地萬物之“道”通過人的性命之理而顯現。“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中的“我”,指有主體性自我意識的人。
由此可見,邵雍的“性命”有廣狹二義,廣義的“性命”包含天地萬物,狹義的“性命”則專指人。邵雍說:“萬物受性于天,而各為其性也。在人則為人之性,在禽獸則為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為草木之性。”(《觀物外篇》)“天下之物,莫不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觀物內篇》)這里的“性”、“命”以及“理”是廣義的。就狹義的“性命”而言,邵雍認為人之“性”有兩個特點:一是人性同于物性,“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惟人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二是人性高于物性,不僅表現為人有靈性、有智慧、有意識,所謂人為“萬
物之靈”,“無所不能者,人也。”而且表現為人有道德、有倫理、有價值理想,所謂“唯仁者真可謂之人矣”,“性有仁義禮智之善。”
人之“性”與“心”、“身”、“物”、“道”等范疇,有密切關系,邵雍在《伊川擊壤集序》中對比作了總結;
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
“性”是“道之形體”,“道”在于人則為“性”,在于物則為“理”,“道”是無形的,而人“性”和物“理”則是“道”的顯現,好比是“道”的形體,“道”的外延和內涵都大于“性”,④“道”包括了人“性”和物“理”,“道”既含有自然萬物的變易規律(“理”的內涵),又含有人的道德倫理、價值觀念(“性”的內涵)。“道”是一個最高范疇,在“道”的統領下,邵雍提出了四個命題:性是道的形體,心是性的郛郭(城堡),身是心的區宇,物是身的舟車,就這四個命題的外延看是:
性<心<身<物
“性”范圍小于“心”,因為性的本質為善,而心包涵了善與惡、正與邪,性居于心中卻不能該盡“心”;“心”小于“身”,因為心只是身中眾多器官中的一種,身是心的寓所,心居于身中卻不能該盡“身”;“身”小于“物”,因為人身只是萬物中的一種,身居于萬物之中卻不能該盡“物”。然而從內涵和地位上看,卻是恰恰相反:
性>心>身>物
“性”作為“心”中的善的本質,是最值得宏揚、修養的,其內涵最為豐富,其地位最為尊貴;“心”雖居于身中,但卻為身之“君主”,可以主宰身;“身”雖從屬于萬物,但萬物如果失去人“身”,沒有主體的參與,就變得毫無意義,因而身又是物的主宰。
邵雍表述這四個命題一環緊扣一環,一層更進一層,將性命之學置于宇宙大系統中,通過對彼此關系的分析,突出了人性既高于物性又源于物性,既高于自然又源于自然的人文主義精神。接著邵雍又從認識的角度對這幾個范疇作了進一步闡釋。
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者,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
邵雍所謂的“觀”是主體對客體的一種認識活動,“觀物”是邵氏認識客體世界的核心方法。這里邵氏強調的是要以本層面之道、性、心、身、物“觀”本層面的道、性、心、身、物,這樣才能不損害對認知對象的客觀、公正的理解,從而獲得“兩不相傷”、“情累都忘”的觀物之樂中。如果以上層面去“觀”下層面,則難免有情累之害。對道、性、心、身、物等概念,朱熹作了解釋:“以道觀性者,道是自然的道理,性則有剛柔善惡參差不齊處,是道不能以該盡此性也。性有仁義禮智之善,心卻千思萬慮,出入無時,是性不能以該盡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卻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檢其身處。以一身而觀物,亦有不能盡其情狀變態處,此則未離乎害之意也。”這段話從內涵和外延上對這幾個概念作了區分,雖然朱熹偏重于道德修養上解釋,與邵雍偏重于理性認識有所不同,但對這幾個概念的界說還是基本合理的。
在人性論上,邵雍綜合了道家的自然主義與儒家的人文主義,在中國哲學史上有重要意義。更值得一提的是,邵氏還從認識論上講人性問題,他在《觀物外篇》中將“性”與“情”
作了對比: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圣人之性也,茍不知而強知,非情而何?失性而情,則眾人矣。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性”是與“情”是相對的,這是繼承了李翱等人性情對立、性善情惡的觀念。“以物觀物”就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順應事物的自然本性去認識事物,不帶有自我的主觀好惡之情,
因而是公正,明白的;“以我觀物”就是按照自我的主觀意愿去認識事物,因為帶有個人的感彩,所以就偏頗而暗蔽。“以物觀物”既是事物的本性,又是人的本性。在認識活動中,能夠實事求是,知則知,不知則不知,這是圣人而非眾人的本性。
張行成發揮了邵雍“性”“情”對立說:“愛人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性也。”以《中庸》的“中和”說解釋人之“性”。
邵雍從認識論上認為只有主客合一、尊從客體本來面目又不摻雜主體的感彩,才是事物和人的本性,這種立論方式獨特而巧妙。
邵雍的“性命之學”與他的“心學”有著密切的關系。“心學”是邵雍對自己哲學體系的稱謂,“心學”包含了物理之學與性命之學。因為邵雍將“心”分成“天地之心”與“人之心”兩大類,其中“天地之心”講的是物理之學,“人之心”講的是性命之學。就“人心”而言,邵雍又將它分為兩大類,即“眾人之心”與“圣人之心”。
所謂“眾人之心”,邵雍稱為“人心”、“人之心”。《觀物外篇》說:“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心是人的君主之官,是思維的器官,是人之所以區別于動物的關鍵所在(此“心”不是生理之“心”),人之心具有認識物類性情形體的能力,具有主觀能動的靈性(人為“萬物之靈”)。《觀物內篇》說:“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人之心與天地之心有什么關系?《觀物內篇》作了比較:“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天地至妙者”即指天地之心,其特點是“一動一靜”的本然之理,不是受人的主觀意愿干預的客觀存在;“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就加上了人的主觀之“心”而言,人之心在于“一動一靜之間”,即人心非動非靜,但卻主宰動靜。人心是宇宙萬物的本源⑤。人體主觀感知自然,能動地改造并獨立于自然,是人心的本質特征。然而眾人之心是兼指正邪、性情、善惡而言的,有邪、有惡即亂世之源,有情、有欲亦昏蔽、不公之始。因而真正肇始自然萬物、能成為“天地之心”的本源者只有“圣人之心。”
所謂“圣人之心”則是一種無情無欲、無邪無惡的純凈之心,是眾人之心的精華,它源于眾人之心而高于眾人之心。《觀物外篇》說:“大哉用乎!吾于此見圣人之心矣。”這個“圣人之心”即“人性”——人的純潔、虛靜的本性。邵雍對“圣人之心”作了描述:“人心當如止水則定,定則靜,靜則明。”“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物。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觀物外篇》)說明圣人之心是靜止、澄明,不起念頭的。所謂“心一而不分”張行成解釋:“心之神,其體本虛,不可分也。隨物而起,泥物而著,心始實而分矣。”(《觀物外篇衍義》)因為心本體為虛,所以不可分,不可動。圣人之所以能達到本性境界,是因為無思無為、洗心、退藏。這種圣人之心就是不動的“太極”。
邵雍的“心”從功用上可區別為兩種:
一是作為本體的“心”。《觀物外篇》說:“心為太極。”“萬化萬事生乎心也。”說明“心”是生成萬事萬物的本源,然而這個“心”到底是指“天地之心”還是指“圣從之心”?邵雍曾說過“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觀物外篇》)可又說過“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余何足言?”(《擊壤集》)既然“心在天地前”,說明這個“心”不是天地之心,而是人心(圣人之心),“天地自我出”的“我”即人之心。可見這個宇宙本體的“心”即是人之心——圣人之心,然而天地之心與圣人之心實為一體關系,據邵雍之子邵伯溫解釋:“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天地之心,蓋于動靜之間,有以見之。夫天地之心,于此見之;圣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于此而見之。”(《宋元學案·百源學案》)可見本然存在的客觀之道(“天地之心”)即是通過圣人的主觀認識(“圣人之心”)才得以顯示的,人與天地自然的溝通也是通過“圣人之心”的中介才得以實現的,因而可以說圣人之心即反映了天地之心,從而成為宇宙的本體。
二是作為法則的“心”。《觀物外篇》說:“先天之學,心法也。”“先天之學,心也;后天之學,跡也;出入有無生死者,道也。”這是以涵括天地萬物之理的先天學法則為“心法”,邵雍認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的法則既是八卦、六十四卦次序和方位生成的法則,又是天地方圓、四時運行、人遷、萬物推移的法則,“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觀物外篇》)所謂“天向一中分體用,人于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是說天道變化與人心思維具有同一個法則。朱伯昆先生認為,邵雍以其先天圖及其變化的法則出于心的法則,此種觀點實際上是將易學的法則歸之于人心的產物,他所以得出這一結論,就其理論思維說,是將數學的法則,如他所說的一分為二、方圓之數的演算等等,看成是頭腦自生的、先驗的東西。總之,認為數的變化和演算的規律性,存在思維自身之中,是從思維自身的活動中引出來的⑥。
綜上所說,可以看出邵雍的性命之學——心學是一個以象數(先天學)為心法、以心性為本體、集本體與法則為一體、視天地之心(天道)與圣人之心(人性)為一理的龐大的哲學體系。儒家的道德修養與道家的宇宙精神、儒家的人道觀、價值觀與道家的天道觀、認識論被邵雍十分巧妙、圓融無礙地貫通在“易”理之中,在“北宋五子”中獨樹一幟。應該說,邵雍也是宋明理學中“心學派”的開創者,當然邵雍的心學與程顥的心學有同有異,其相同點是都視天理與人心為一體,都以圣人之心為天地之心,所不同點是邵雍偏向于冷眼觀物,偏向于從認識論方面觀照天人法則、體會圣人之心;而程顥則偏向于潛心識仁,偏向于從價值論方面修養道德、誠敬體物、擴充圣人之心。當然邵雍并沒有取消道德修養,而是從另一層面講“養心”、“修身”、“主誠”。
注釋:
余敦康認為:“邵雍稱自然科學為天學,人文科學為人學,并且以有無人文因素的參與作為區分先天與后天的標準。”(《內圣外王的貫通》,學林出版社,1997年1月,226頁)
余敦康:《內圣外王的貫通》,學林出版社,1997年,220-227頁。
“易貫儒道”的觀點,參見拙著《易道:中華文化的主干》,中國書店,1999年1月。
余敦康先生《內圣外王的貫通》第237頁認為:“就外延而言,道大而性小,性從屬于道;就內涵而言,則道小而性大,因為人之性除了同于自然的物之理外,還包涵著極為豐富的人文價值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