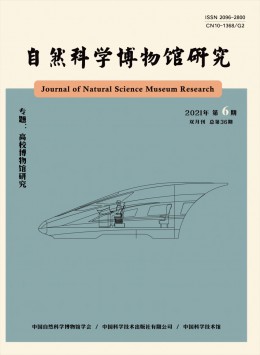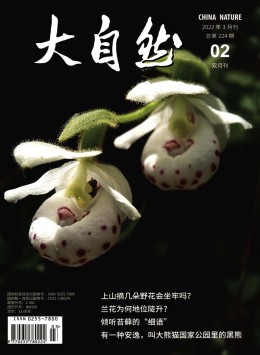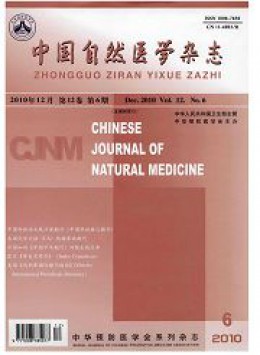自然科學的方法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自然科學的方法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范文
一、用實驗創設情境
實驗是一項興趣盎然的活動。創設實驗情境,自然課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善于采取靈活多變的實驗方法,巧妙地安排新異有趣的實驗,通過學生動手、動腦,創設寓教于樂情境,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產生動力,主動探索。例如教《氣體的熱脹冷縮》時,教師先演示一個“噴泉”實驗,即把一個帶有玻璃管的瓶塞塞到裝有少量冷水的燒瓶口上,玻璃管插入瓶底,用一杯熱水澆燒瓶,燒瓶內的冷水便會立即從玻璃管口噴出一米多高。學生被這一新奇的現象吸引住,激發了學習興趣和探索欲望,啟發了學生的創造思維,達到了最好的教學效果。
二、用科技史設置故事情境
曾經有一位教育家說過:“故事是兒童的第一大需要。”自然教材中一些著名實驗、發現事例,是情境教學的優質素材。在課堂教學中,根據授課內容,穿插講一些生動有趣的名人軼事、歷史故事,看一些科學家的照片或插圖,能夠使學生終身難忘,他們會追蹤科學家的思維,去體驗創造發明的境界。例如教《電流》時,結合課文講愛迪生發明電燈的故事;教《生物進化》時,講達爾文從小熱愛大自然,課余時間常到野外捕捉昆蟲,尋找礦石,揀拾貝殼和采集動植物標本的故事;教《水的壓力和浮力》時,講阿基米德從浴桶水溢出來的啟發而獲得一種“直覺的頓悟”,發現了物體的沉浮規律的故事……這些豐富的史料,扣人心弦,融知識性、趣味性、思想性為一體,能夠吸引學生進入教學情境,再現科學家們的忘我探索情境,激勵學生陶冶情操,鼓舞斗志,培養發現精神。
三、聯系舊知識,創設情境
巴甫洛夫說過:“任何一個新問題的解決,都要利用主體經驗中已有的同類題。”因此在課堂教學中,根據新舊知識之間的聯系,巧設懸念,創設多種新情境,讓學生把原有的知識、經驗遷移到新情境中,使學生有盡可能多的機會在新情境中運用所學知識、技能解決實際問題,有利于激發學生對新知識的探求。例如在《導體和絕緣體》一課教學中,教師先出示一電路板,緊接著設問“有什么方法使小燈泡亮,蜂鳴器變響 ?”學生答:“合上開關。”進一步追問“假如把電路開關斷開,有沒有辦法在不合開關的情況下,也能使燈泡變亮?”學生即答:“用一金屬接在開關兩端,就能使小燈泡變亮。”這時教師請他們試試,并讓他們說說,是什么物體使小燈泡變亮起來的,這樣讓學生在這種新情境中運用已有知識、經驗,動手操作,通過觀察小燈泡亮與不亮來證明該物體是導體,還是絕緣體。學生既學到了知識,又培養了能力。
四、猜謎語、唱兒歌創設情境
猜謎語、唱兒歌是學生喜愛的方式,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使淺顯平淡、枯燥無味的教學內容轉為妙趣橫生的學習活動,融知識教學于情趣之中,把課上得有聲有色,饒有趣味,使學生百上不厭。在課堂教學中,根據教材內容,把教科書中的知識編成謎語或兒歌讓學生學習,有利于概括知識,揭示規律,也有利于激發學生的興趣。例如教《空氣》一課時,教師課前編一個謎語:看不見摸不著,無顏色無味道,動植物一刻離不了。看誰猜得準、快?大家踴躍競賽猜謎語,好勝心激起了學生強烈的興趣。
五、聯系生產生活實際,觸境
人的認識過程的起步,是從感性認識開始的,自然課是把整個自然作為學生認識對象,與社會生產、生活密切相聯,有創設學習情境的豐富材料。對于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學生看得見,摸得著,有的親身經歷過。在課堂上,教師聯系客觀實際,用強烈、豐富的感性材料,使學生爆發思想的火花。例如講《雷電》一課時,提問:夏天下大雨時,看到閃電不久,就聽到雷聲,你們說說閃電、打雷是同時發生的還是非同時發生的?講到《能源礦產》時,聯系生活中燒的煤,汽車、飛機、輪船等燒的柴油、汽油是什么形成的?……用這些自然的、社會的生活實際,掀起學生心頭的層層浪花,推動思維的漣漪,引起無窮的遐想和追求,并獲得成功的快樂。
六、利用游戲創設情境
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說:“游戲是由愉快促動的,它是滿足的源泉。”游戲是兒童的天堂。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根據學生心理特點和教材內容,設計各種游戲、創設教學情境,以滿足學生愛動好玩的心理,產生一種愉快的學習氛圍。這種氛圍不但能增長學生的知識,還能發展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提高他們的觀察、記憶、注意和獨立思考能力,不斷挖掘學生的學習潛力,游戲活動一般有比賽、表演、角色扮演等方式。例如在教《怎樣認出它們》一課時,在學習了用摸的方法認識東西之后,設計一個摸袋子游戲,給每個小組準備一個牛皮紙袋,里面裝有鉛筆、橡皮、糖、小刀、硬幣、花生等東西,要求學生不準看,只能用手伸進去摸,比一比誰摸出的東西最多,最后把東西倒出來看,究竟摸對多少,摸對了的學生開心得不得了,在輕松愉快的游戲中,加深了對自然課的理解,在學中玩,玩中學,學得有勁,玩得開心,增強了學習自然的興趣。
七、運用想象構思情境
第2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范文
關鍵詞:自然科學;心理學發展;積極貢獻
心理學的自然科學傳統深遠流長。從19世紀后半期,在自然科學尤其是物理學、生理學和化學的的影響下,心理學蓬勃發展,最后終于以馮特(Wundt,1832—1920)在萊比錫大學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標志心理學正式獨立,到現在世界各地心理學越來越普及,并與其他學科相結合,派生出很多新學科,心理學一直在自然科學理論及研究方法的陪伴與影響下發展。
一、自然科學與心理學的成長相伴
(一)物理及數量方法對心理學的促進
古希臘時期哲學和自然科學混為一體,其中的心理學思想已經受到其他自然科學思想的影響。其實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到公元前三百多年期間,以德謨克利特為代表的原子論者即已奠定了以物質現象解釋心理活動的基礎。15世紀后一段時期科學研究風行一時,伽利略(Galilei,1564—1642)、開普勒(Kepler,1571—1630)、牛頓(Newton,1642—1727)等人在機械運動研究方面成績卓越,特別是牛頓力學理論得到普遍承認。笛卡爾(Descartes,1596—1650)的反射論中機械力學觀點更是徹底,他將人的身體看作一件自動機器,腦是控制中樞,肌肉是引擎,各種器官是活門和機件,生命現象歸結于機械運動,機體活動不是精神支配的結果而是對刺激的回應。19世紀生理學家韋伯(Weber,1795—1878)發現了“恰可辨認的差異”,用系統的實驗方法研究各種形式下的感覺閾,尋找心理量(感覺)與物理量(刺激)的關系,并用數量關系把它表示出來,創造了心理學史上第一個定量法則韋伯定律。物理學家費希納(Fecher,1801—1887)在韋伯的工作基礎上,進一步論述身心之間,或外界刺激與心理現象之間的數量關系,提出在心理學界人人皆知的韋伯—費希納定律,創造了心理物理學。
(二)生物學、生理學及化學對心理學的影響
心理活動是腦的高級機能,是生物體的生命現象,故心理學的發展進步必然與生物學、生理學的發展進步相聯系。達爾文(Darwin,1809—1882)的科學進化論影響深遠,對心理學的影響也甚為廣泛。19世紀,心理學的基礎學科—生理解剖學發展迅速。以貝爾(Bell,1774—1842)為代表的對神經沖動和傳導的研究,和弗盧郎(Flourens,1794—1867)關于腦生理的研究,為理解人的感受和運動過程打下了重要基礎。19世紀后期,生理學家發現了神經沖動的電性質,并測出了神經沖動的傳導速度,使心理學家認識到心理過程是可以進行實驗和測量的。顱相說及后來的大腦機能統一說,與布羅卡言語中樞、感覺和運動中樞的發現一起,使心理是腦的機能成為共識。
(三)計算機科學等現代科學技術及原理對心理學的促進
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尤其是計算機科學技術的巨大發展成就對認知心理學的產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信息論是一門用概率論和數理統計方法研究信息量度量和信息分析、信息編碼、信息處理、信息傳遞及信息變換規律的科學。認知心理學者借用信息論中信息輸入、過濾、衰減、存儲等過程模式。自動調節控制系統中反饋系統促進達成有效的控制的思想被心理學家所接受。而從系統理論來看,人處于物理,生物、社會三大系統的交叉處,具有開放性、動態性和主動性,決定了人心理活動的系統性和復雜性。
二、自然科學對現代心理學的促進及展望
我們看到心理學幾乎是從萌芽時期起,一路走來,離不開自然科學的一路相伴,自然科學的進步總是對心理學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總的來說,自然科學對心理學做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貢獻:
(一)促進心理學的獨立
一般把馮特在萊比錫大學建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作為心理學獨立的標志,把在這之后的心理學稱為現代心理學。心理學在獨立之前主要作為靈魂學說依附于哲學,受一些其他自然科學思想的影響,心理學逐漸擺脫泛靈論和宗教神學的束縛,有了實證研究思想,為心理學走上自然科學的道路埋下種子。馮特正是從物理、化學、生物中得到啟示,把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運用于心理學,建立了標志心理學獨立的實驗室。
(二)促進心理學研究方法的改進、研究工具的改良
心理學領域的眾多理論進步,都離不開研究方法的改進,研究工具的改良。而無論是歷史上有名的斯金納箱,還是當今的眼動儀、生物反饋系統等,包括心理學研究中最常見心理量表,都不開自然科學的支撐。從物理及數量方法被帶到心理學中,到現在以計算機科學技術、生物反饋技術等為支撐的各種越來越先進的研究工具,自然科學以其巨大的發展成就為心理學獨立和發展在研究方法、研究工具方面提供了技術支持。
(三)自然科學拓展心理學研究領域,并推動心理學研究不斷深化
隨著社會發展,心理學已與其他一些自然學科形成一種相互促進的局面。計算機信息、電子、分子生物技術、物理技術的革命性進步,導致心理學研究手段的現代化,促進心理結構的研究逐步深入,如閾下啟動效應、知覺的選擇模型等,使我們對心理現象實質的認識取得巨大進展。我們看到,自然科學不僅僅給心理學帶來了具體的科學知識,更是改善了心理學研究的思維模式,提供了先進的實驗條件、手段和工具,為心理學研究的突破提供了可能性。心理的自然屬性決定了心理學與自然科學的必然聯系,利用自然科學中對心理學有益的先進思想和方法,能夠提高心理學研究的準確性和有效性。
【參考文獻】
第3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范文
對此,有人大呼“墮落”,有人認為“無所謂”,有人覺得“很爽”,“冷眼旁觀”者也大有人在。可貴的是,真正的人文學者開始了痛定思痛的反省,試圖調整自家的心態、眼光和學術策略,以適應前所未有的人情世態之變故。確實地,回思歷史可能是看清現實和篤定未來的主要渠道,而對人文學本身之性質、價值以及它同身處其間的社會文化之間的學理關聯和現實糾葛所當有的恰切認知,則是歷史回思的基本前提。這兒,我們就按照這一思路,從“科學”內涵兩次“狹化”的角度,回恩人文學被邊緣化的“往事不堪回首”,進而揭出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二而一”實質。
這里所謂的“科學的兩次狹化”,主要發生在啟蒙之后的那幾個世紀里。具體說,18世紀末,人們完成了對“科學”內涵的第一次狹化。如眾所知,只有當某一套知識構成為一種系統或被體系化時,才可以被稱為“科學”。因此,科學既包含我們現在所謂的自然學、社會學,也包括人文學。在學科的系統中,即在系統知識的系統中,也是有等級層次的,最能代表科學之本義和理想者,當然非數理科學莫屬,其中數學(尤其是幾何學)、物理學(尤其是牛頓力學)又是其中的翹楚,并因而在英語世界“霸占”了“科學”這一名詞,后被狹化為“自然科學”的簡稱,終于成為一種正面的價值理想和判斷標準。這使得在近代直到眼下,“科學”成了“先進”和“敬意”的代名詞,科學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員,比如形而上學、道德學說、美學、詩學、心理學等,都應當向它們學習――這就是近代實際呈現出來的學科生態。笛卡爾、萊布尼茲、斯賓諾莎、康德,他們在形而上學、道德哲學和歷史學等這些狄爾泰意義上的“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學)必得向自然科學學習,以及一切科學皆應有的基本特性即科學性、客觀性即“確然性”這些方面,沒有根本性分歧。
本來秩序井然且只是統稱的“科學”一詞,完全被“自然科學”,尤其是理論物理學和數學所獨占,“科學”一詞本身也因此成了“進步”“理性”和“力量”的代稱,并進而使得“自然科學”成了所有人類知識系統和知識追求的“范本”和“榜樣”。一然科學獨占“科學”之名,并因其對自然世界和物理現象巨大的解釋效力――此時的自然科學還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并未產生如今所理解的那種現實效應和物質上的便利而成為各類學術研究仿效的標桿,其后果是非常顯著而嚴重的:一方面,自然科學因自身的偉大業績而變得“趾高氣揚”和“目中無人”,對自然科學之外的其他學科,無疑形成了巨大而沉重的壓抑;另一方面,“不甘落后”和“迎頭趕上”的心理訴求和創新動力,使得“后進者”心急如焚, “大力仿效”便成了“眾后進”走出陰影并開創未來的不二法門。關鍵的問題是,“仿效什么”和“如何仿效”,這當然取決于“先進”和“眾后進”對自然科學之取得卓著業績所主要依靠者的理解和認定。
在這一“歸功干”問題上,雙方的認證驚人地一致,不過,事實也確實如此――那就是“方法”。近代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主要得歸功于自培根、笛卡爾以來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對“方法”的窄前重視和精彩運用。不論是一般哲學史所謂的唯理論還是經驗論,沒有誰會認為“方法”不是第一位的,從培根的《新工具>到笛卡爾的《論方法》,莫不如是。笛卡爾為自己也為整個近代哲學確立了一個異常艱巨的哲學任務:找到一套方法,以確保人們獲致無可置疑的真理。這種對自然科學的艷羨和追慕,具體化到自家園地的耕耘,就變成了對“自然科學方法”的單方面推廣和模仿。或把解決“他域”問題的成功方法請進自家領域,或雄心勃勃地推廣“己域”之成功方法于“他域”之中――“這種企圖是人類思想史中一個持久的因素”。正如被譽為“人文領域中的牛頓”的狄爾泰所云:“啟蒙運動的本質就在于,將科學方法的這種結果運用生活的每一個部分。” (《精神科學中歷史世界的建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頁)
這就是科學的“第二次狹化”,即在把科學“狹化”為“自然科學”后,又把包含成果、性質、精神和方法等諸多面相和層次在內的“自然科學”,“狹化”為“科學方法”。而眾所周知的“科學方法”就是經驗歸納和量化處理,尤其是“量化”,也就是“通過化一切質為量來研究任何對象”,可謂是自然科學的方法的靈魂。就這樣,以“量化”為靈魂并以之為自豪的“科學方法”,成了“眾后進”想要“迎頭趕上”的唯一選擇。理解越來越狹,路就越走越窄,希望也就越來越渺茫,人文學因此就被毫無疑義地遺忘了,最終多少也是有些自我放逐的味道了。
然而,正如科學史家曾經確認的,如果僅僅把自然科學看作是一種探討的方法,那就如同把達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視為畫布顏料的組合一樣(克萊因《西方文化中的數學》導論)。無論是對于數學,還是自然科學,精神都是最重要的。
說起“精神”,有關的討論可謂多矣,且常把“精神”分為兩橛,一曰“科學精神”,再日“人文精神”。有關學術的精神只有一個,無論稱其為“科學精神”還是“人文精神”。把二者對立提出,很顯然是把這里的“科學”理解為狹義的“自然科學”,潛在的可能是對“人文學科”能否成為一般意義上之“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的懷疑和猶豫。這是個雖然太大但卻異常緊要的理論問題,一兩句斷難說清。我的總體看法是,兩種精神其實是一種精神,之所以被分而言之,究其根源,在西方自文藝復興,尤其是牛頓物理學大行以來,自然科學的如日中天和一統下,導致自然科學成了一切科學的典范和模板,一些深刻的人文學者,看到人文有不同于自然的根本特性和功能,奮而起來捍衛人文學科的獨立性和自律性,最早看出這一點的是帕斯卡(1623-1662)和維柯(1668-1744)。為r護守人文學的獨立性,歷代學者不得不在對象、方法、特性諸方面不斷地思考人文學之不同于自然科學的方方面面。與“科學精神”相對立的“人文精神”可能就是在這種理論語境中被大力宜揚的。可“人文精神”(Spirit of Humanism)這個術語在西方的相關著述中,并不常見――與它意思相當的是Humanistic Spirit一詞,其意思是人本主義或人本精神――倒是“科學精神” (ScientificSpirit或者Spirit of Sciencc)常常被學者們提及,也在一般的著述中經常出現。
西方知識界所遭遇的這一古今轉折的大變關頭,同樣在歐風美雨襲來的近代中國重現。民族、國家的不堪一擊,讓國人不得不“瞪”眼西方,從技術到制度再到思想,終于深入到了“西方”的“心臟”――哲學的層面,來為中華之崛起尋求出路。1920年代的“科玄論戰”正是西方知識界曾遭際的處境之中國化重演,看來也是必然的。玄學一派所提倡的無非就是那種關注人生價值和意義的人生哲學,后來的概括和發展就成了對“人文精神”的推介和高揚。這當然源于他們對西方近代世界自然科學之風大暢后帶來的諸多災難性后來的警惕和擔心,前車之鑒當警惕之。但深遠者常常都是超前者,這種警惕和機心與當時吾國之情勢并不相侔,故而,丁文江等人的看法也不無道理,因為那是最應時且流行的看法。
第4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范文
關鍵詞:自然界;辯正自然觀;自然科學;辯正本性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3-0228-02
收稿日期:2013-08-19
作者簡介:黃柳(1992-),女,安徽六安人,本科生,從事理論研究。
一、運用整體論的思維方式來研究自然觀的整體特性
恩格斯在《導言》中集中解決的問題是自然界的辯正本性,創立了辯正自然觀,辯正自然觀的整體性就表明了自然界的辯正本性。也就是說,恩格斯在提出辯正自然觀時,首要的是運用整體論的思維方式從整體上考察辯正自然觀的整體特性。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任何事物的整體性都標志著事物的根本特性、基本特性或主要特性的,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特性,也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質或實質。這對于辯正自然觀的考察也不例外,從整體論上思考就會抓住辯正自然觀的根本特性。
從整體論的思維方式出發,一方面要考察自然界,另一方面要考察辯證法。而要揭示自然界的辯正本性,最終歸結為實現自然界與辯證法的結合。也就是說如果把自然界與辯證法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就有可能揭示出自然界的辯正過程和辯正發展。在此之前自然界與辯證法是分離的,取代辯證法地位的是形而上學,不管是近代的形而上學自然觀,還是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自然哲學,最后都導致在自然界對辯證法的否定。這樣恩格斯要確立辯正自然觀,從方法論上看就是要實現自然界與辯證法的結合和統一。
二、以自然科學作為中介來達到自然界與辯證法的統一
要實現自然界與辯證法的結合和統一,恩格斯運用了以自然科學為中介的方法,這就是選取了一個中介因素——自然科學,它既跟自然界發生聯系,又跟辯證法發生聯系。或者說自然科學之所以能成為中介,是由于自然科學與自然界的關系以及自然科學與哲學的關系所決定。如果說自然科學尚在哲學的母體之中,哲學與自然界是直接發生關系,那么當自然科學獨立后并從哲學中分化出來,就產生了自然科學與自然界的關系,同時也產生了自然科學與哲學的關系。但是由于自然科學存在于這兩種關系中而形成兩個層次關系,即自然界與自然科學是一種層次關系,自然科學與哲學又是一種層次關系。而且哲學位于自然科學層次之上,自然科學處于自然界層次之上,于是哲學、自然科學、自然界三者之間形成以自然科學為中間層次的關系,哲學就通過自然科學這一中介與自然界發生關系。這樣,自然界與辯證法的關系,實際上是自然界與哲學的一種關系,并且要通過自然科學與自然界的關系來解決。換句話說,辯正自然觀的確立要通過自然科學對哲學的作用來解決,而這種作用就是作為中介的自然科學的運用。
自然科學的中介作用是由自然科學的性質和特點決定的。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但它不是研究整體自然界,而是研究自然界各個不同領域,它所獲得的成果是對自然界各個不同領域特殊規律的認識。辯正自然觀是研究整個自然界的,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規律。這樣無論從研究對象和研究成果來看,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都可以歸結為一般與特殊的關系。而自然界中實際存在的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而自然界中實際存在的是一般與特殊的統一,或一般與個別的統一,并且直接存在的形式是具體的、個別的所以說一般與特殊或一般與個別的統一,實際統一于特殊或個別之中。這樣自然科學對哲學的中介作用,就表現為如何從特殊上升為一般,通過特殊的自然科學規律來論證辯正自然觀的普遍規律、揭示自然界本身的辯證法。自然科學作為中介,把自然界與辯證法統一起來來揭示出自然界的辯正本性。
三、自然界的辯正本性及其論證
既然以自然科學為中介,把自然界與辯證法統一起來揭示出自然界的辯正本性,那自然界的辯正本性到底是什么呢?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自然界的辯正本性就是“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自然界是不是存在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呢?這就要使自然界與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統一起來。恩格斯就是運用自然科學的成果來論證自然界的辯正本性,揭示出自然界的各種物質存在的物體之間的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
(一)天文學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辯正本性
1755年,康德發表的《宇宙發展史概論》中就提出了天體形成的星云假說。指出太陽系及一切恒星都是由原始星云在引力和斥力的作用下逐漸凝聚而產生的。原始星云的細小物質微粒在引力作用下相互轉動著的扁的云狀物中較大的團塊就凝聚成行星。恩格斯從康德的星云假說中看出:“關于第一次推動的問題別取消了;地球和整個太陽系表現為某種在時間的進程中逐漸生成的東西。”[1]“是從哥白尼以來天文學取得的最大進步。認為自然界在時間上沒有任何歷史的那種觀念,第一次被動搖了。”[2]但是當時大多數自然科學家仍受形而上學觀念的影響,康德的著作并沒有引起注意,對自然科學和哲學也沒有產生直接影響。
直到1976年,法國天文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拉普拉斯出版了《宇宙系統論》,提出了灼熱星云假說,并從數學上作了論證。認為高溫旋轉的星云由于熱量輻射到宇宙空間而逐漸冷卻收縮,星云越來越成為一個圓盤的星云塊,生成一圈又一圈氣體環,由于相互吸引形成團塊,最后形成行星,星云的中心部分形成太陽。直到這時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說才引起人們的重視,并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間占統治地位。以后天文學家獲得的一些材料表明假說還不夠完善,但是生成和發展的思想卻由此在天文學中得到了公認。
(二)地質學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辯正本性
1830—1833年英國地質學家漸變論者賴爾的《地質學原理——參照現在起作用的各種原因來解釋地球表面過去發生的變化的嘗試》一書指出,通過風、雨、河流、海浪、潮汐、火山、地震等因素說明歷史上所發生的各種變化,認為地球的歷史在時間上是連續的,現狀是以前變遷的結果。變化的原因是由一系列微小的、緩慢的變化積累起來的,而不像災變論者居維葉所說的那樣是全球性的災變造成的。賴爾的地質學成就說明:“不僅整個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在其上的植物和動物,也都有時間上的歷史。”[1] 對此,恩格斯指出,盡管賴爾的觀點也有缺陷,但賴爾卻是“第一次把理性帶進地質學中,因為他以為地球緩慢的變化這樣一種漸進作用,代替了由造物主的一時興發所引起的突然革命。”[1]
(三)物理學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辯正本性
19世紀三四十年代,物理學的最高成就就是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的發現。恩格斯指出還有英國的焦耳和格羅夫也在這個期間提出。它表明“一切所謂物理力,即機械力、熱、光、電、磁,甚至所謂化學力,在一定的條件下都可以相互轉化,而不發生任何力的損耗”[1],自然界物質運動的“相互聯系和轉化已經被證明”,“運動著的物質的永遠循環是最終的結論”[1]。對于這一定律的哲學意義,恩格斯指出:“如果說,新的發現、偉大的運動基本規律,十年前還僅僅概括為能量守恒定律,僅僅概括為運動不生不滅這種表述,就是說,僅僅從量的方面概括它,那么,這種狹隘的、消極的表述日益被那種關于能的轉化的積極的表述所代替,在這里過程的質的內容第一次獲得了自己的權利,對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記憶也消除了。”[2] 現在“自然界中的一切運動都可以歸結為一種形式向另一種形式不斷轉化的過程”[3],而且“轉化過程是一個偉大的基本過程,對自然的全部認識都綜合于對這個過程的認識中”[2]。
因此,通過這些自然科學成就所揭示出來的自然界的辯證法的整體特性是自然界的一切東西都產生、消逝、運動、變化、發展、聯系、轉化、統一之中,進一步概括升華就會得出自然界的普遍聯系——永恒運動的辯證法特性。表明“整個自然界是作為至少在基本上已解釋清楚和了解清楚的種種過程的體系而展現在我們面前”。
恩格斯通過自然科學及其成就實現了自然界與辯證法的結合、統一,揭示了自然界的辯正本性:普遍聯系——永恒運動,并對辯正自然觀的“基本點”給出了完整表述:“一切僵硬的東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一切被當作永久存在的特殊東西變成了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恒的流動和循環中運動著。”[1] 恩格斯這一表述是就其辯正自然觀的“基本點”說的,這里的“基本點”實際指的是中心、核心,即辯正自然觀的中心、核心是永恒運動。從辯正自然觀的整體性質是關于自然界的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的見解中可以看出,辯正自然觀的基本點所強調的只是辯正自然觀關于自然界的辯正本性的一個方面——永恒運動。之所以要突出這一點,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恩格斯是針對形而上學自然觀“這個總觀點的中心是自然界絕對不變這樣一個見解”說的,辯正自然觀和形而上學自然觀截然相反,中心是自然界的永恒運動。第二,普遍聯系也是自然界的一個整體特性、辯正本性,但是自然界的這兩個辯正本性——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從邏輯關系看,普遍聯系應該是邏輯在先的,所以僅僅承認普遍聯系還不能最終使辯正自然觀與形而上學自然觀區別開來,還必須在承認普遍聯系的前提下,承認這些普遍聯系的東西之間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永恒運動。第三,自然界的永恒運動不僅僅以普遍聯系為前提,而且它本身就包含著普遍聯系,永恒的運動表現為各種運動形式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轉化,這本身就是一種相互依賴、普遍聯系的顯現。
參考文獻:
[1]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2-16.
第5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范文
關鍵詞: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分類;體系
中圖分類號:G8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1307-3612(2006)11-1453-04
1 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及分類研究沿革
20世紀90年代盡管國家已將體育科學歸屬于社會科學,但體育科學領域許多專家,還有科學學科研究的有些專家對于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及分類問題都提出了異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與研究成果。
田雨普認為體育科學是介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綜合科學,其學科體系由基礎科學(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技術科學(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專業技術3個學科體系組成(圖1)。
熊斗寅認為體育科!學隸屬于科學體系中的“技術科學”。學科體系分為體育自然科學類、體育管理科學類和體育社會科學類(圖2)。
胡曉風認為體育科學學科體系由體育社會學學科、基礎學科、運動學學科3大類學科群組成(圖3)。
1982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體育》卷中,體育科學分支學科共有12個,即體育學、運動學、運動形態學、運動解剖學、運動人體測量學、運動局部解剖學、運動生理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生物化學、運動心理學、運動醫學、運動訓練。對上述學科劃分為3個層次和3大類(圖4):第1層次是體育學,第1層次向第2層次過渡的學科是體育哲學和體育情報學,第2層次是體育基礎學科、運動技術學科和體育社會學科3大類,第3層次是下屬各門學科。
徐忠、屈世瓊認為,體育科學是屬于一門綜合性科學,與自然科學、人文、管理科學、交叉科學綜合融合而構成了體育科學學科群。從而提出體育科學體系結構為6個學科群:哲學方法學科群、人文社會學科群、自然生物學科群、運動科學學科群、管理信息學科群、交叉邊緣學科群(圖5)。
王續琨、劉永振認為:“體育科學現已發展成為一個包含眾多分支學科、邊緣學科,介于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交叉學科。”對體育科學分類提出了自己的構想,將體育科學的分支學科、邊緣學科區分為5個群組(圖6)。
邵偉德、馬楚紅在“體育學科分類體系的科學性探討”一文中認為體育科學簡單地歸為社會科學不夠合理,并指出了在體育學科分類時需注意的4個原則:科學性原則,發展性原則,實用、可行、方便性原則,統一性原則,由此而提出體育學科分類體系的構想圖(圖7)。
羅加冰對體育新學科進行了分類:體育自然科學類新學科,體育社會科學類新學科,體育管理科學類新學科,體育人文科學類新學科,體育綜合科學類新學科(圖8)。盡管是新學科分類,實際是他對體育科學學科的分類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與意義。 上述關于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及分類研究后繼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 科學學科分類研究
科學作為一種觀念形態和知識體系,是對整個世界的認識和反映。科學結構與它所反映的客體結構即整個客觀世界的結構是一致的。我國對科學學科體系的探索,有二元論、三元論和多元論之爭。二元論即認為科學學科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三元論認為科學學科分為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多元論認為科學學科分為許多學科體系。恩格斯早在1874年提出對科學分類的觀點:“每一門科學都是分析某一個別的運動形式或一系列互相關聯和互相轉化的運動形式的。因此,科學分類就是這些運動形式本身依據其內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類和排列,并將科學分為數學、力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及地理學6類。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根據系統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認為整個客觀世界從自然界發展到人類,同時出現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由此而提出科學大廈由自然科學、人體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數學科學、系統科學6大部分組成。陳文化等學者依據“自然一人一社會”的演化次序與科學本身的“固有發展次序”有內在的聯系,認為科學學科分為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三大門,并構建了現代科學體系――以人文科學為主體、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為兩翼的立體結構。由于當代跨學科的廣泛研究,出現了許多交叉性學科,如運籌學、環境學、人才學、管理學、信息學等,許多新學科的學科屬性屬于綜合性,難以隸屬于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這3大科學,更難以涵蓋如雨后春筍日益冒出的大量復雜性、綜合性的新學科,因此,必須有一門科學學科可以涵蓋不隸屬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外的一門學科――綜合學科。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學學科已發展成約有5550門學科,其中非交叉學科約有2 969門,而交叉學科總量已達2581門,占全部學科總數的46.58%。交叉學科僅在100年左右增加的學科數量就占總學科數量的一半,并繼續呈迅猛增長勢頭。有的學者將管理科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并列,并將交叉的綜合性學科歸屬至管理科學內,這是不妥的。追究管理科學,實際它介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是一門多學科融合的綜合性學科,理應隸屬于綜合科學。特別現有許多交叉新學科根本沒有管理的屬性,按科學邏輯性無論如何也不能隸屬于管理科學,只有將管理科學和許多交叉新學科隸屬于綜合科學才比較合理,而不能將交叉性綜合學科歸屬于管理科學。這一隸屬關系不能顛倒。本人認為,現代科學學科應分為4大類學科相對比較正確,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綜合科學(圖9、圖10)。
3 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及其分類研究
對于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劉仲林在《現代交叉科學》一書中指出,體育科學是一門由生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生物力學等20多門學科的滲透融合,廣泛應用電子計算機技術、聲像技術、遙控技術等現代技術的一門綜合學科。國外專家研究認為,一個運動員成績的提高是素質、體質、機能、心理、戰術、技術、智力等150多個因素綜合效應的結果。社會中的體育現象和運動中人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決定了體育科學的跨學科性和綜合性。但體育科學的綜合性又不是各個學科研究結論的簡單相加,而是運用各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手段取得各種參數進行綜合運算,以得出比較全面的結論。隨著體育科學的迅猛發展,其綜合性屬性越來越凸顯。俄羅斯體育科研的綜合試驗臺,可對人的運動能力進行學科問的綜合性基礎研究。遺傳學家、教育家、生物力學家、生理學家、生物化學家、心理學家、計算機專家可在統一的試驗對象身上進行分子的、亞細胞的、細胞的、各器官的、各系統的以及整個有機體的試驗研
究。在綜合監督訓練過程中可運用近300種檢測演技的方法,檢測出3000多種訓練水平參數,在總訓練時間中約25%的時間用于進行各種檢測。因此,有人稱之體育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窗口。體育的許多方面研究,都走到了科學的研究前沿,如檢測運動員興奮劑方面研究,運動生物力學方面研究,運動免疫學方面研究,運動康復研究等等,都與相關學科或母系學科的前沿科學研究并駕齊驅。可以說,在體育方面通過一系列實證,證實屬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綜合性科學方面的許多具體學科內容。體育科學學科有十足的理由分為4大類:體育自然科學、體育社會科學、體育人文科學和體育綜合科學。隸屬于體育自然科學類學科有:運動解剖學、人體生理學、運動生物化學、運動生物力學等;隸屬于體育社會科學類學科有:體育社會學、體育產業學、社會體育學、體育經濟學、體育法學、體育人口學、體育傳播學、體育教育學等;隸屬于體育人文科學類學科有:體育史、體育心理學、體育哲學、體育美學、體育科學學等;隸屬于體育綜合科學類學科有:體育控制論、體育信息論、體育系統論、體育決策學、體育運籌學、體育環境學、體育人才學等。因此.體育科學隸屬于科學學科體系中的綜合科學是非常正確的學科歸屬。
而國家將體育科學歸屬于社會科學,是否符合科學邏輯?首先要了解分析社會科學是一門什么學科?社會科學是一門以社會為研究的知識體系。我國的《辭海》中說:“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的任務是研究并闡述各種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由此可見,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社會,社會科學的性質與其研究對象本身的規定性是直接同一性的。社會科學的任務是揭示并闡明各種社會現象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等。從學科研究理論可以準確地告訴我們,科學的內在的直接同一性和邏輯辯證關系是學科分類的依據與方法:體育社會科學的母學科是社會科學,體育自然科學的母學科是自然科學,體育人文科學的母學科是人文科學,體育綜合科學的母學科是綜合科學。國家將體育科學歸屬于社會科學,依據科學學科的內在邏輯,體育科學是難以分化出體育自然科學、體育人文科學、體育社會科學和體育綜合科學的,而現實的體育科學恰恰能科學地梳理出體育自然科學、體育人文科學、體育社會科學和體育綜合科學,這些難道社會科學能包容得了嗎?即使硬包容著體育自然科學、體育人文科學等學科,這本身就違背了科學的內在邏輯性及其分類原則,產生了嚴重的自相矛盾和錯位現象。因此,硬將體育科學歸屬于社會科學是“牽強附會”的,是缺乏科學依據的,更是扭曲了體育科學的本質。隨著近幾年科學理論專家對科學學科分類研究的深入及其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積極影響著體育科學學科研究的深化,逐步取得明朗化的研究進展。
我們研究認為,體育科學學科屬性是綜合性科學,是隸屬于科學學科體系中的綜合科學;體育科學學科分類類似于科學學科分類,是“大科學”學科體系的“縮影”,同樣分為4大類:體育自然科學、體育社會科學、體育人文科學和體育綜合科學(圖11)。從圖12可清楚地看出4個方面的學科群,而且在不斷地發展和龐大。仔細研究體育科學下屬4大學科,各學科發展“勢均力敵”。本研究為什么將田徑運動(學)、球類運動(學)、體操運動(學)等運動技術學科隸屬于體育自然科學類,這是因為體育自然科學是涵蓋著體育的“自然世界”。這些運動技術學科的本質都是具有自然科學屬性。從田徑的跑、跳、投到劉翔奧運會得金牌的神速跨欄動作;從籃球、排球、足球的跑、跳、投到姚明的扣籃等以及俄羅斯名將涅莫夫單杠上6個空翻抓杠動作等等運動技術,無不顯示出運動生物力學、運動解剖學、運動生理學、運動營養學、運動生物化學等方面的知識特征,顯示出運動技術科學的前沿科學知識,都是顯示出自然科學知識的屬性,應該隸屬于體育自然科學中的分支學科。這些學科還夠不上資格與體育自然科學、體育社會科學、體育人文科學和體育綜合科學相提并論的一門學科。田徑運動(學)、球類運動(學)、體操運動(學)等運動技術學科,這些成熟學科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應該規范學科名稱,在后面加上“(學)”。
目前,國家頒發的許多文件和權威性雜志里都認為體育科學是一門綜合性科學。在2004年10月20日國家體育總局頒布的“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體育社會科學的意見”中指出,“體育科學是綜合性科學,實施科教興體戰略包括繁榮發展體育自然科學和體育社會科學兩個方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育事業,離不開體育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2005年《體育科學》雜志編輯部在第1期版2的序言“開拓創新任重道遠”中指出:“《體育科學》雜志記錄了這20多年來中國體育科學發展的成長歷程。記得在本刊創刊之初,學者們曾就‘體育’的科學屬性進行過熱烈的討論。而今,這種爭論也是不爭自明:因為隨著科技全球化的迅猛發展,體育科學研究的廣度、深度和研究的手段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體育既與信息技術、生命科學、基因納米技術等當今世界的熱點科學與技術有著不解之緣,又與國家的政治體制、經濟發展、人文地理環境等有著密切的聯系。體育科學,已發展成為一門集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于一體的綜合性應用性的交叉學科。”
4 結論
第6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范文
關鍵詞:技術科學;技術;技術哲學
前蘇聯以及現今俄羅斯的重工業技術和軍事技術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究其原因我們不能回避其發達的技術科學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實早在前蘇聯時期,學者們就對技術科學哲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關研究具有鮮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蘇聯技術哲學的主要成就,也極大豐富了當今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技術哲學體系。
一、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背景
前蘇聯和俄羅斯的科學技術哲學是世界技術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指導思想、研究綱領和研究重心都與中國和西方科學技術哲學有著顯著的區別,因而成為我國乃至世界科學技術哲學界特別關注的研究領域。值得一提的是,上個世紀我國學者在前蘇聯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的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對于作為前蘇聯科學技術哲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技術哲學的研究卻大相徑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狀況是因為,一方面,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哲學顯然很晚才開始研究技術現象。……相對于實踐認識和實踐理性,哲學更偏好理論認識、理性和理論規則,顯然,這種偏好成為哲學很晚才轉向思考技術現象以及技術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的一個原因”[1]。的確,相對于其他哲學分支學科,技術哲學本身起步較晚,現代技術哲學就其本身而言僅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到目前為止發展也不是很完善,諸如技術的本質、技術是否是價值中立的焦點問題,以及技術哲學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還沒有形成壓倒多數的、相對統一的觀點。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前蘇聯時期的技術哲學往往被視為資產階級哲學加以批判。蘇俄技術哲學研究開始于19世紀末,那時“П.К.恩格邁爾(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冊子《19世紀技術的總結》(1898)中提出了技術哲學的任務。同時他的許多著作被用德語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后,前蘇聯技術哲學研究開始轉向一個特殊時期。正如俄羅斯學者所評論的:“技術哲學在俄國的命運非常悲慘。關于技術哲學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邁爾提出的。П.К.恩格邁爾是俄國工程師,他是技術哲學第一個研究綱領的提出者,這個綱領于1912被提出來。1929年,當恩格邁爾不得不再次號召建立技術哲學時,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開的反對。恩格邁爾在《我們需要技術哲學嗎?》一文中發展了技術哲學重要性的思想。而在這個雜志的同一期中還收錄了Б.馬爾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技術哲學遭到批判-‘現在沒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獨立于人類社會和獨立于階級斗爭之外的技術哲學。談技術哲學,就意味著唯心主義的思考。技術哲學不是唯物主義的概念,而是唯心主義的概念’。從這時起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把技術哲學斥為唯心主義,在蘇聯哲學界已成定論,盡管馬克思就是19世紀有興趣從社會—哲學方向研究技術的一個創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技術哲學”的提法在前蘇聯時期被禁止,但是對于“技術”的哲學思考在前蘇聯卻從未停止過。那時(也包括現在)有一大批學者長期致力于技術哲學問題的研究,其中比較重要的人物有:В.М.羅津、В.Г.高羅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羅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賓(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們的研究成果頗豐,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術哲學的典型特色,因而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為我國學者和西方學者極為關注的研究課題。
В.М.羅津等在《技術哲學:歷史與現實》一書中曾寫道:“蘇聯時期對于技術的研究開始于世紀初(指20世紀初-筆者注)。由于П.К.恩格邁爾,技術哲學在俄羅斯獲得極大發展。后來在我國,這一學科被視為資產階級科學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卻發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討論技術不同方面的學科,并且,如今它們被部分地納入到技術哲學中來。首先就是技術史。……研究技術的第二個領域被稱為‘技術的哲學問題’。恰恰在這里討論了技術的本性和本質,……第三個領域在蘇聯時期急劇發展-這就是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雖然這門學科屬于科學學和方法論,但如今它們被包括到技術哲學中來。……第四個領域是設計和工程技術活動的本性和歷史。……正如我們已經發現的那樣,如今這些研究領域不僅僅單獨發展,而且還處于技術哲學的范圍之內。”[3]因此可以說,前蘇聯時期學者們把技術史、技術的哲學問題、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設計與工程技術活動的方法論和歷史等問題不同程度地納入到技術哲學的研究范圍內。在這四個組成部分中,對于技術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最為充分,并且具有鮮明的俄式風格。
二、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重心
前蘇聯學者非常重視對技術科學認識論的研究,這主要包括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功能、任務等問題,其中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問題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1.技術科學起源的內外史要素
前蘇聯學者普遍認為:“技術科學是關于有目的地將自然物質和過程改造成技術對象,關于構建技術活動的方法,同時也是關于技術對象在社會生產體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識系統。”[4]關于技術科學的產生,前蘇聯學者們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技術科學的產生有外史和內史兩方面因素。從外史方面看,人們的生活、生產(特別是機器生產)為技術科學的產生和發展提出研究的課題,并決定技術科學的研究方向。從內史方面看,一方面,技術科學是技術知識的系統化、邏輯化的結果,它是人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對象活動中所形成的對習慣、概念、認識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術科學的產生源于對基礎科學的應用,是從基礎科學中分化出來的;此外,還有一部分技術科學源于不同知識、模型、概念和原則的大綜合,是這些要素橫向搭構的結果。
2.技術科學對象的兩重性
關于技術科學對象,前蘇聯學者們認為,技術科學對象具有兩重性,即技術科學對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區分。而且其中技術科學的“天然性”對應著技術與自然、技術與自然科學的關系;而技術科學的“人工性”對應著技術與人、技術與人文科學的關系。正如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中指出的:“在技術科學中可以統計出兩個技術對象:自然的技術對象和人工的技術對象。……技術對象的人工性在于,它們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它們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對象歸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這種觀點也得到А.Н.鮑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認同,他指出:“技術科學不僅與自然科學(這決定了技術科學的‘天然的’特征)相聯系,而且它還與經濟學和人文科學有著不同的、極為重要的交叉(而這一點相對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術科學理論的三種結構要素
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均可分為三個基本組成部分:本體論模式、數學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義卻有很大差異。其中自然科學的本體論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實驗中的理想對象的總和。而技術科學理論的本體論模式可分為三個基本層次:以數學描述為目標的函數圖像;在工程對象中進行的自然過程的連動模式;表現為構造參數和工程計算的結構模式,即研究對象的結構。此外,在自然科學理論中,數學工具首先是為了實驗計算,它們是建立和證明所獲得的理論知識的手段。而在技術科學理論中,數學則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來對工程對象的結構和工藝參數進行工程計算;第二,用它來分析和綜合技術的本體論模式;第三,用它來研究發生在工程對象中的自然過程[6]。可以看出,技術科學理論結構中的三個要素要比自然科學理論結構中的要素更為復雜。其原因恰恰在于技術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體和客體相互聯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學理論更多兼顧實踐的方面。
4.技術科學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與此相聯系,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功能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論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過程,研究理論問題,以預測和描繪理論發展的未來狀況。而技術科學理論功能的起點和歸宿,都是為了對工程對象的技術結構和工藝參數進行理想描述。而且技術科學理論功能的實驗層次不僅僅包括實際上是以概括工程師的工作經驗為目標的結構技術和工藝知識,還包括特殊的實踐方法知識。當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術理論中獲得的理論知識形成實踐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學問題。這些問題是在建立工程對象的各個階段中,在解決工程問題的過程中產生的,而且它們將會傳播到技術領域當中去,以實現技術理論的功能[6]。
5.技術科學任務的實踐特征
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結構與功能的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者在科學領域中所擔負任務的不同。作為科學知識集合的自然科學的任務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規律,預測自然過程的發展;而作為技術知識集合的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從實踐上利用這些自然科學成果,研究自然規律在技術設備中的作用,以及運用知識和計算保障工程技術活動[4]。盡管前蘇聯學者認為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實踐,但是他們仍然強調不應將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科學在工程中的應用混為一談。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指出,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科學應用于工程實踐是有區別的:前一種情況說的是獨立學科的建立,這意味著各種不同科學知識、模型、概念和方法被應用于一定的研究對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轉換程序,形成現有學科所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和任務;而后一種情況指的是在解決具體的工程任務過程中,各種科學知識、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組織化的過程[7]。
三、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特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前蘇聯學者習慣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四個角度分析自然科學哲學問題,這一傳統也影響到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即學者們往往從技術本體論、技術認識論、技術方法論和技術價值論角度來研究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因此可以說“師從自然科學哲學”是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特點。
在前蘇聯學者看來,自然科學方法論之所以能夠類推至技術科學領域是因為,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都是科學的組成部分,因此較為發達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當然可以成為技術科學方法論研究的范例。這正如前蘇聯學者們指出的:“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在起源方面,還是在起作用的過程方面。技術科學最初的理論原理、認識客體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從自然科學向技術科學傳遞過來的;同樣,技術科學自身科學性的規范、知識理論結構的確立、理想對象的結構和數學化,恰恰也都是從自然科學借用到技術科學中來的。”[4]尤其針對技術科學的數學化,А.Н.鮑戈柳波夫指出:“知識數學化的問題是歷史性的問題,從廣義上講,未必能夠在科學史和技術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別是相對于技術科學,更是如此。多虧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緊密聯系,才產生出將適合于自然科學的數學化模型轉移到技術科學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樣產生出利用自然科學數學化歷史來了解數學在技術知識發展中所起(或者說它應當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這一點,前蘇聯學者更關注自然科學對技術科學和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影響。
概括說來,前蘇聯時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人們通常只是在科學哲學的背景下研究技術哲學,把技術哲學混同于規范的科學哲學的附屬物,并且僅僅從自然科學知識附屬物的角度來研究技術。技術被歸結為科學的附屬物,而技術哲學則被歸結為運用于技術知識結構的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研究的簡單附屬物,這就是20世紀50至60年代的特點[1]。如果說這一時期運用科學哲學手段研究技術哲學是自發的,那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前蘇聯學者就開始自覺地借用科學哲學和科學學的方法研究技術哲學,特別是研究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一文中指出:“雖然很早以前,技術知識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哲學家們的興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開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這個方向范圍內提出一個目標:就是用科學學和科學方法論的手段來系統地研究技術科學。”[4]他們還補充道:“技術科學方法的特點暫時揭示得還不太清楚。一方面,應當注意專業方法獨特的多樣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廣泛地應用一般科學的認識方法(如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4]在此不可否認,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時成熟壯大起來的。
可見,由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自然科學充當了技術科學的基礎,因此我們不能脫離自然科學孤立地研究技術科學;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技術科學相對獨立的特點,正如前蘇聯學者鮑戈柳波夫指出:“技術科學從本質上應當與不斷發展的技術相適應,并且最佳的情況是應當超前于技術。……技術科學、實用科學和基礎科學是知識具體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層次。因此,技術科學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能夠變成實用科學(如果技術科學的應用范圍超出技術框架外),甚至變成基礎科學”。這表明,在技術科學與技術的辯證關系中,技術科學應當具備先驗的預測功能,而且技術科學、實用科學與基礎科學之間存在著轉換關系。這是技術科學發展過程中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總之,通過上述研究我們能夠看到,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是其技術哲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壓意識形態統治時期技術哲學研究的主要成績,其相關問題研究(如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功能、任務等問題)即使在技術哲學日趨走向成熟的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重大價值。
參考文獻:
[1]Отредакции.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93(10):24-26.
[2]СтёпинВС,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овМА.Философиянаукиитехники[EB/OL].(2006-06-20)[2007-08-02]..
[3]РозинВМ,ГороховВГ,АлексееваИЮ,etal.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история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EB/OL].(2006-06-28)[2007-08-02]..
[4]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инВМ.Философс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техническихнаук[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1(10):172-178.
[5]БоголюбовАН.Математикаитехническиенау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0(10):81-82.
第7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范文
關 鍵 詞:技術科學;技術;技術哲學
前蘇聯以及現今俄羅斯的重工業技術和軍事技術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究其原因我們不能 回避其發達的技術科學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實早在前蘇聯時期,學者們就對技術科學 哲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關研究具有鮮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蘇聯技術哲學的主要 成就,也極大豐富了當今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技術哲學體系。
一、 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背景
前蘇聯和俄羅斯的科學技術哲學是世界技術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指導思想、研究綱領 和研究重心都與中國和西方科學技術哲學有著顯著的區別,因而成為我國乃至世界科學技術 哲學界特別關注的研究領域。值得一提的是,上個世紀我國學者在前蘇聯自然科學的哲學問 題的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對于作為前蘇聯科學技術哲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技術哲學 的研究卻大相徑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狀況是因為,一方面,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哲學顯 然很晚才開始研究技術現象。……相對于實踐認識和實踐理性,哲學更偏好理論認識、理性 和理論規則,顯然,這種偏好成為哲學很晚才轉向思考技術現象以及技術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 的一個原因”[1]。的確,相對于其他哲學分支學科,技術哲學本身起步較晚,現代技 術哲學就其本身而言僅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到目前為止發展也不是很完善,諸如技術的本質 、技術是否是價值中立的焦點問題,以及技術哲學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還沒有形成壓倒 多數的、相對統一的觀點。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前蘇聯時期的技 術哲學往往被視為資產階級哲學加以批判。蘇俄技術哲學研究開始于19世紀末,那時“П.К .恩格邁爾(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冊子《19世紀技術的總結》(1898 )中提出了技術哲學的任務。同時他的許多著作被用德語出版”[2]。但是,自1917 年十月革命勝利后,前蘇聯技術哲學研究開始轉向一個特殊時期。正如俄羅斯學者所評論的: “技術哲學在俄國的命運非常悲慘。關于技術哲學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邁爾提出 的。П.К.恩格邁爾是俄國工程師,他是技術哲學第一個研究綱領的提出者,這個綱領于1912 被提出來。1929年,當恩格邁爾不得不再次號召建立技術哲學時,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開的 反對。恩格邁爾在《我們需要技術哲學嗎?》一文中發展了技術哲學重要性的思想。而在這 個雜志的同一期中還收錄了Б.馬爾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技術哲學 遭到批判-‘現在沒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獨立于人類社會和獨立于階級斗爭之外的技術哲 學。談技術哲學,就意味著唯心主義的思考。技術哲學不是唯物主義的概念,而是唯心主義的 概念’。從這時起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把技術哲學斥為唯心主義,在蘇聯哲學界已成定論 ,盡管馬克思就是19世紀有興趣從社會—哲學方向研究技術的一個創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技術哲學”的提法在前蘇聯時期被禁止,但是對于“技術”的哲學 思考在前蘇聯卻從未停止過。那時(也包括現在)有一大批學者長期致力于技術哲學問題的研 究,其中比較重要的人物有:В.М.羅津、В.Г.高羅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 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 羅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賓(В.С. Стёпин)等人。他們的研究成果頗豐,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術哲學的典型特色,因而 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為我國學者和西方學者極為關注的研究課題。
В.М.羅津等在《技術哲學:歷史與現實》一書中曾寫道:“蘇聯時期對于技術的研究開始于 世紀初(指20世紀初-筆者注)。由于П.К.恩格邁爾,技術哲學在俄羅斯獲得極大發展。 后來在我國,這一學科被視為資產階級科學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卻發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討論 技術不同方面的學科,并且,如今它們被部分地納入到技術哲學中來。首先就是技術史。…… 研究技術的第二個領域被稱為‘技術的哲學問題’。恰恰在這里討論了技術的本性和本質, ……第三個領域在蘇聯時期急劇發展-這就是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雖然這門學科 屬于科學學和方法論,但如今它們被包括到技術哲學中來。……第四個領域是設計和工程技 術活動的本性和歷史。……正如我們已經發現的那樣,如今這些研究領域不僅僅單獨發展,而 且還處于技術哲學的范圍之內。”[3]因此可以說,前蘇聯時期學者們把技術史、技 術的哲學問題、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設計與工程技術活動的方法論和歷史等問題不同 程度地納入到技術哲學的研究范圍內。在這四個組成部分中,對于技術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最 為充分,并且具有鮮明的俄式風格。
二、 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重心
前蘇聯學者非常重視對技術科學認識論的研究,這主要包括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 功能、任務等問題,其中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問題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1. 技術科學起源的內外史要素
前蘇聯學者普遍認為:“技術科學是關于有目的地將自然物質和過程改造成技術對象,關于 構建技術活動的方法,同時也是關于技術對象在社會生產體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識系 統。”[4]關于技術科學的產生,前蘇聯學者們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技術科學的產 生有 外史和內史兩方面因素。從外史方面看,人們的生活、生產(特別是機器生產)為技術科學的 產生和發展提出研究的課題,并決定技術科學的研究方向。從內史方面看,一方面,技術科 學是技術知識的系統化、邏輯化的結果,它是人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對象活動中所形 成的對習慣、概念、認識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術科學的產生源于對基礎科 學的應用,是從基礎科學中分化出來的;此外,還有一部分技術科學源于不同知識、模型、 概念和原則的大綜合,是這些要素橫向搭構的結果。
2. 技術科學對象的兩重性
關于技術科學對象,前蘇聯學者們認為,技術科學對象具有兩重性,即技術科學對象有“天 然的”和“人工的”區分。而且其中技術科學的“天然性”對應著技術與自然、技術與自然 科學的關系;而技術科學的“人工性”對應著技術與人、技術與人文科學的關系。正如В. 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中指出的:“在技術科學中可 以統計出兩個技術對象:自然的技術對象和人工的技術對象。……技術對象的人工性在于, 它們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它們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對象歸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 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這種觀點也得到А.Н.鮑戈柳波夫(А.Н.Бого любов)的認同,他指出:“技術科學不僅與自然科學(這決定了技術科學的‘天然的’特 征)相聯系,而且它還與經濟學和人文科學有著不同的、極為重要的交叉(而這一點相對于它 的‘人工的’特征)”[5]。
3. 技術科學理論的三種結構要素
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 理論的結構均可分為三個基本組成部分:本體論模式、數學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義卻有 很大差異。其中自然科學的本體論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實驗中的理想對象的總和。而技 術科學理論的本體論模式可分為三個基本層次:以數學描述為目標的函數圖像;在工程對象 中進行的自然過程的連動模式;表現為構造參數和工程計算的結構模式,即研究對象的結構 。此外,在自然科學理論中,數學工具首先是為了實驗計算,它們是建立和證明所獲得的理 論知識的手段。而在技術科學理論中,數學則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來對工程對象的 結構和工藝參數進行工程計算;第二,用它來分析和綜合技術的本體論模式;第三,用它來 研究發生在工程對象中的自然過程[6]。可以看出,技術科學理論結構中的三個要素 要比自 然科學理論結構中的要素更為復雜。其原因恰恰在于技術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體和客體 相互聯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學理論更多兼顧實踐的方面。
4. 技術科學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與此相聯系,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功能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 論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過程,研究理論問題,以預測和描繪理論發展的未來狀況。而技術 科學理論功能的起點和歸宿,都是為了對工程對象的技術結構和 工藝參數進行理想描述。而且技術科學理論功能的實驗層次不僅僅包括實際上是以概括工程 師的工作經驗為目標的結構技術和工藝知識,還包括特殊的實踐方法知識。當前工程研究的 目的是:把在技術理論中獲得的理論知識形成實踐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學問題。這些問 題是在建立工程對象的各個階段中,在解決工程問題的過程中產生的,而且它們將會傳播到 技術領域當中去,以實現技術理論的功能[6]。
5. 技術科學任務的實踐特征
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結構與功能的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者在科學領域中所擔負任務的 不同。作為科學知識集合的自然科學的任務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規律,預測自然過程 的發展;而作為技術知識集合的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從實踐上利用這些自然科學成果,研 究自然規律在技術設備中的作用,以及運用知識和計算保障工程技術活動[4]。盡管 前蘇聯學者認為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實踐,但是他們仍然強調不應將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 科學在工程中的應用混為一談。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指出,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 科學應用于工程實踐是有區別的:前一種情況說的是獨立學科的建立,這意味著各種不同科學 知識、模型、概念和方法被應用于一定的研究對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轉換程序,形成現 有學科所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和任務;而后一種情況指的是在解決具體的工程任務過程中,各 種科學知識、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組織化的過程[7]。
三、 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特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前蘇聯學者習慣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四個角度分析自然 科學哲學問題,這一傳統也影響到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即學者們往往從技術本體論、 技術認識論、技術方法論和技術價值論角度來研究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因此可以說“師從 自然科學哲學”是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特點。
在前蘇聯學者看來,自然科學方法論之所以能夠類推至技術科學領域是因為,自然科學和技 術科學都是科學的組成部分,因此較為發達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當然可以成為技術科學方法論 研究的范例。這正如前蘇聯學者們指出的:“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無論是 在起源方面,還是在起作用的過程方面。技術科學最初的理論原理、認識客體和概念的方式, 恰恰是從自然科學向技術科學傳遞過來的;同樣,技術科學自身科學性的規范、知識理論結構 的確立、理想對象的結構和數學化,恰恰也都是從自然科學借用到技術科學中來的。” [4]尤其針對技術科學的數學化,А.Н.鮑戈柳波夫指出:“知識數學化的問題是歷史 性的問題,從廣義上講,未必能夠在科學史和技術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別是相對于技術 科學,更是如此。多虧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緊密聯系,才產生出將適合于自然科學的數學 化模型轉移到技術科學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樣產生出利用自然科學數學化歷史來了解數學 在技術知識發展中所起(或者說它應當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這一點,前 蘇聯學者更關注自然科學對技術科學和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影響。
概括說來,前蘇聯時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人們通常只是在科學哲學的背景下研究 技術哲學,把技術哲學混同于規范的科學哲學的附屬物,并且僅僅從自然科學知識附屬物的 角度來研究技術。技術被歸結為科學的附屬物,而技術哲學則被歸結為運用于技術知識結構 的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研究的簡單附屬物,這就是20世紀50至60年代的特點[1]。 如果說這一時期運用科學哲學手段研究技術哲學是自發的,那從20世紀70年代中 期開始,前蘇聯學者就開始自覺地借用科學哲學和科學學的方法研究技術哲學,特別是研究 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一文 中指出:“雖然很早以前,技術知識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哲學家們的興趣,但只是 在最近五六年才開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這個方向范圍內提出一個目標:就是用科學學和科 學方法論的手段來系統地研究技術科學。”[4]他們還補充道:“技術科學方法的特 點暫時揭示得還不太清楚。一方面,應當注意專業方法獨特的多樣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廣泛 地應用一般科學的認識方法(如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4]在此不可否認, 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時成熟壯大起來的。
可見,由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自然科學充當了技術科學的基礎,因此我們不能脫離自然科學 孤立地研究技術科學;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技術科學相對獨立的特點,正如前蘇聯學者鮑 戈柳波夫指出:“技術科學從本質上應當與不斷發展的技術相適應,并且最佳的情況 是應當超前于技術。……技術科學、實用科學和基礎科學是知識具體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層次 。因此,技術科學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能夠變成實用科學(如果技術科學的應用范圍超出技 術框架外),甚至變成基礎科學”[5]。這表明,在技術科學與技術的辯證關系中,技 術科學應當具備先驗的預測功能,而且技術科學、實用科學與基礎科學之間存在著轉換關系 。這是技術科學發展過程中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總之,通過上述研究我們能夠看到,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是其技術哲學研究的重要 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壓意識形態統治時期技術哲學研究的主要成績, 其相關問題研究(如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功能、任務等問題)即使在技術哲學日 趨走向成熟的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重大價值。
參考文獻:
[1]От редакции. Философия техники[J]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3(10):24-26.
[2]Стёпин В С, Горохов В Г, Розов М А.Философия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EB/OL]. (2006-06-20)[2007 -08-02]. http:∥philosophy.ru/library/fnt/11.html.
[3]Розин В М, Горохов В Г, Алексеева ИЮ, et al. Философия техник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 нность[EB/OL]. (2006-06-28)[2007-08-02]. http:∥philosophy.ru/ iphras/library/filtech.html.
[4]Горохов В Г, Розин В М. Философско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ехнически х наук[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1(10):172-178.
[5]Боголюбов А Н. Математика и техни ческие науки[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0(10):81-8 2.
第8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科學;性質
1經濟學科學性質之“惑”
對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爭論從經濟學的出現至今就沒有停止過。羅森伯格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處于純公理系統與應用幾何學的交叉點上、類似于數學的一個分支”的科學;米塞斯(L.V.Mises)認為:“經濟學不是來自經驗,它先于經驗,是行動和事實的邏輯”,“經濟學的定理不是來自于事實的觀察,而是從行動的基本范疇中演繹出來的”。按照米塞斯的這段話,其認為經濟學因為無法進行精確可控的實驗,所以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謬爾達爾在獲獎后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因其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
2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
在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波普爾在其自傳中簡單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科學的劃分標準:可證偽性。從邏輯上來說,每次的實證描述都只是單稱描述,而一個全稱陳述的理論是不可能被一個個的單稱陳述所證實的。經濟學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可以從對某種資源的觀察得出結論來證實“資源是稀缺的”這一假定。但是我們是不可能窮盡世界所有種類的資源是否稀缺來證明這個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證實的。但它卻有被證偽的可能性。我們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假設的反例,從而推倒這個假設。但是人類發展至今,還未能找到什么資源不是稀缺的,因此這個假設暫時未被證偽。但是它有被證偽的可能性。這就是命題的可證偽性。可證偽性正說明了科學的科學性。波普爾從這個角度說明,科學的分界應該是可證偽性。此外,對科學性質無任何爭議的物理學,有存在無法實證的假定,例如物理學中的隨機性假定。
3經濟學的客觀性
3.1關于客觀性
科學的客觀性并“不是建立在脫離了科學家個人的價值判斷采取超然態度的基礎之上的”,這是波普爾的前提觀點。由于科學的客觀性在于科學方法的公共性質,所以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偏見的社會科學家們正是在充分徹底的討論中產生出客觀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學家的態度比社會科學家的態度更客觀,這是完全錯誤的。人們之所以認為社會科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因為他們將以前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于社會科學的后果,是對客觀性本身的誤解。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考察客觀性問題,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有何不同的問題。“與此相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建立在科學家們的不帶偏見的心境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事業的公眾性和競爭性的事實……客觀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評,建立在批評的方法,批評傳統的基礎上。”從中可以看出,波普爾認為的客觀性與一般意義上的理解不同。他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是方法的客觀性,而不是內容的客觀性。
3.2關于經濟學預測不準確
經濟學家預測的不準確性是受人們詬病的一個方面。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經濟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其根據之一就是預測具有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的雙重效果,波普爾把這兩種效果總結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體來說,這種效果也就是指預測既可以成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為阻止該事件的原因。如果經濟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判斷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經說過,在他認識的人里,很少有因為根據經濟預測采取行動而賺錢的人,倒是有不少靠賣經濟預測賺到了錢。
但是,波普爾認為俄狄浦斯效果屬于科學的處理操作內部的事情,即預測的準確與否不能成為一種理論是否成為科學的衡量標準。喬治•荷曼斯(GC.Homens)也認為:有效性和精確解釋等科學構成因素雖然說對一門科學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們只是社會科學的目標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喬治•荷曼斯(GC.Homens)舉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為例:雖說它并未精確地敘述進化的過程,也未從其理論中引申出有效的預測,但沒有任何科學家會否認進化論在科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對現代遺傳學的貢獻。
3.3關于經濟學受經濟學家意識形態影響
人們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比較容易保持“價值中立”,而在經濟學中,研究者既是觀眾,又是演員,很難保持“價值中立”。經濟科學中沒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則,而自然科學中卻有。羅賓遜夫人坦言:經濟學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觀性偏見的論述。
從波普爾對科學的客觀性的看法可知,經濟學常受到的關于階級屬性的質疑是無意義的。因為經濟學的客觀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觀性。經濟學發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的國家里都是可以借鑒的。在經濟學的方法上,是無階級意識之分的。因此,對經濟學的階級屬性的質疑是對經濟學不公正的對待。至于部分經濟學家的帶有階層性質的,“巧”借客觀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為某個階層服務的經濟理論,那就是那些經濟學家個人問題,而不能成為論證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據。
4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性
4.1研究對象
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會情況比自然情況更加復雜——這在經濟學科的研究中不勝枚舉,計量經濟學者更是常常為變量的選取與舍棄而大傷腦筋。也因此,認為經濟學沒有自然學科諸如物理學那樣的客觀性。波普爾認為這種偏見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我們往往把不應比較的事情加以比較,即具體的社會情況和人工隔離實驗的自然情況。二是一個古老的想法,認為社會情況的描述必須涉及有關的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乃至生理狀態。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曲解,是不加思考隨波逐流的一種看法,“社會科學不但不如物理學那么復雜,而且具體的社會情況一般說也不如具體的自然情況那么復雜……”。波普爾的話可以這樣理解,經濟學中的經濟現象分析,不必考慮進社會全部的因素,我們能夠建立一些簡單的模型來分析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而這種簡化的模型與自然科學的模型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模型中,我們同樣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變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可以更簡化,乃至可通過實驗來模擬,由此認為自然科學更具客觀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自然科學的發展更具深厚的傳統罷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進行模型分析和應用的困難只是程度問題而并不是性質問題。
第9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范文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 范式的本義與本質; 方法論閾限; 唯物史觀
中圖分類號: G64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749(2012)01-0008-05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這一命題的提出,是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堅持30多年方法創新的產物,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視界正在拓展和深入,預示著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學科建設將會出現新的繁榮和進步。然而,由于范式作為一種方法論原則是“舶來品”,思想政治教育學界很多人目前對它還缺乏切實的了解,在理解和運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這一命題、特別是在此命題下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轉換”的主張時,容易產生誤解和誤用,故而考查范式的本義與本質及其方法論閾限,是必要的。
筆者通過研讀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及其它相關著述發現,討論范式之本義、本質及其方法論閾限的問題,首先需要明確兩個邏輯前提。
第一個邏輯前提:明確范式的對象本是人類(準確地說是西方人)自然科學研究史,亦即自然科學研究歷史發展的規律與軌跡,是“人們用批判的眼光對科學在社會中的功能進行審查”[1]的產物,屬于狹義科學學的對象范疇。①而在我國一些有重要影響的學者看來,科學學是把科學技術的研究作為人類社會活動來研究的“(錢學森語),其使命在于”研究當代科學技術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思想所發生的作用,研究它對世界歷史發展的意義“(于光遠語)。[2]
第二個邏輯前提:明確自然科學研究發展史有別于自然科學發展史的界限。自然科學研究史是“關于自然科學的科學”的發展史;自然科學發展史,所指則是具體門類的自然科學亦即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論說的“常規科學”或“成熟科學”的發展史。就是說,范式雖然廣泛涉獵自然科學發展史,但并不是自然科學本身。因此,若是按照語義學要求,范式的完整語形應為“自然科學研究范式”。
托馬斯·庫恩之前,自然科學家們關注的主要是其在場的門類科學即“常規科學”的發展史,一般并不關注科學研究發展史,范式被發現填補了這項空白,它是庫恩在20世紀對科學史和科學學研究作出的重大貢獻。
20世紀末,托馬斯·庫恩提出的“自然科學研究范式”隨同科學學傳進我國,很快廣泛出現在自然科學和科學學之外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成為一個使用率很高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然而,不少人對范式的學科屬性卻不予應有的關注,以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可否和當如何“借用”范式、實行“范式轉換”這種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上,也因擱置唯物史觀方法論原理而處于“說不清,道不明”卻又振振有詞、各行其道的狀況。
由此觀之,將范式置于唯物史觀方法論視野之內進行原典性的考查和分析,進而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無疑就是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之“共同體的成員”所“共同擁有”的歷史使命和職業責任。②
一、從范式發現看范式的本義
什么是范式?回答這個“定義”性的問題,需要從范式發現說起。發現范式,緣于托馬斯·庫恩對自然科學史的精到考察與縝密思考。這可以從庫恩以“歷史的作用”為題安排《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緒論(第一章)看得很清楚。在該書第二章“通向科學之路”中,托馬斯·庫恩說他在對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考察中,發現自然科學的進步得益于一次次的“科學革命”,“科學革命”就是科學家的“共有范式”或“一個基本單位”。他在考察光學研究發展史后指出:“物理光學范式的這些轉變,就是科學革命,而一種范式通過‘革命’向另外一種范式的過渡,便是成熟科學通常的發展模式。”[3]不難看出,庫恩在這里把范式的形成和他的范式發現歸結于他對“科學革命”之意義的歷史考察。
托馬斯·庫恩在為《科學革命的結構》作的自“序”(1962年6月)中,具體敘述了他發現范式的機緣和過程。他十五年前做理論物理學研究生的博士論文期間,“有幸參加了一實驗性的大學課程,這是為非理科學生開設的物理學,由此而使我第一次接觸到科學史。使我非常驚訝的是,接觸了過時的科學理論和實踐,竟使我從根本上破除了關于科學的本質和它所以特別成功之理由的許多基本觀念”,包括需要把一些擁有“無人知曉”的作品的年輕人“置于科學共同體”的觀念。在闡發這一觀念時,庫恩特別述及一些年輕人對他成功發現范式所給予的幫助,他稱這種幫助是年輕人的“恩惠”。[4]在此筆者順便指出:從科學史來看,托馬斯·庫恩對年輕人所持的這種謙恭態度,不僅是一種尊重后學的美德,也是一種崇尚科學的智慧,應當被視為任何(研究)范式結構“共同擁有”的一種“傳統”。
范式發現的內在邏輯和學理基礎,如庫恩所說的,是“常規科學”或“成熟科學”在科學發展史上呈現的兩面性。庫恩發現,科學史上任何“成熟”的“常規科學”的巨大成就都具有鮮明的兩面性特征。一方面,因科學的巨大成就而“空前吸引一批堅定的維護者”,維護和鞏固科學“成熟”的內在特質;另一方面,又因科學的巨大成績而“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為科學“革命”和創新提供了歷史課題。庫恩告訴人們:“凡是共有這兩個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稱之為‘范式’”。由此可見,在庫恩看來,科學發展對于自身的兩面就是科學研究范式形成的內在邏輯和學理基礎,所謂范式并不神秘,不過是“一個與‘常規科學’密切有關的術語”而已。[5]只要視范式為“對研究科學發展的學者來說是一個基本單位”,那么“常規科學與范式這兩個相關概念就將會得到澄清。”[6]
通覽《科學革命的結構》,庫恩關于“什么是范式”所給出的“定義”不過如此,既似清晰又很模糊。實際上,僅從范式發現的角度來給范式本義一個定義性的界說是很困難的,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也并沒有給出“什么是范式”的嚴格定義。這并不是托馬斯·庫恩的疏漏,而是合乎科學學和科學史研究者慣用的定義研究之“范式”的。科學學奠基者之一的J·D貝爾納認為,給一概念下“什么是什么”的定義是很“刻板的”事情,可能“有使精神實質被的危險”。他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借用中國老子著名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哲學命題,開宗明義地指出:“對于科學或科學學,我們也無需下一個嚴格的定義”。[7]貝爾納推崇的這種關于“定義”的方法見解,是適用對范式本義的界說的。
從本義看,托馬斯·庫恩發現和描述的范式不同于方式、模式和模型。庫恩說:為了避免“可能誤導讀者”,不能以為“一個范式就是一個公認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他有些無奈地說:“在一定意義上,在我找不出更好的詞匯的情況下,使用“paradigen”(范式)一詞似頗合適。”同時他又明確指出,用“paradigen”(范式)一詞也不能“完全表達”他的“范式”通常包含的意義”。[8]
庫恩作這樣的區分和申明是必要的。他的范式不是人們常說的方式,方式是具體的,多具可操作性,并且多是可以事先設定和安排的。他的范式也不同于模型或模式,模型、模式都是清晰的,確定的,一般是可以用語言描述和表達的,甚至是可以用線形(直線或曲線)圖示的,用衡器來度量和測試的。而范式卻總是模糊的、寬泛的、不確定的,一般只能“意會”它的真實存在而難以言表它的確切形態,所呈現的是一種經由人工作用促成的不確定的方式,一種經由人工作用卻又是“自然形成”的不確定的因而是開放、動態的模型或模式。正因如此,如今的科學學、科學技術哲學將范式作為形上范疇攝入自己的體系。
概言之,范式作為描述自然科學研究發展史的方法論,推崇的是“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所共同擁有的研究傳統、理論框架、研究方式、話語體系”[9]之諸要素“結構”狀態的真實存在及其重要性。范式本義關注的不是其“結構”要素的固定模式和一致性,不是強調唯有經由“科學革命”實現“范式轉換”才能贏得“常規科學”的常態發展。這是范式的本義及其真諦所在。
二、范式的本質與范式“轉換”
如上所述,要給范式本義下一個嚴格的定義也許是必要的,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范式本質上反映和描述的是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真實存在的“自然歷史過程”,一種由史而來并由當下而去的永不終結的“自然歷史過程”。
在唯物史觀視野里,社會歷史發展總體上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
恩格斯在給約瑟夫·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中描述社會歷史發展總體上的這種“自然歷史過程”時指出:“我們自己創造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這個“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就是一定的經濟制度及“豎立其上”的政治等上層建筑。“第二,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總的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10]
恩格斯在這里基于唯物史觀描述的“自然歷史過程”,是我們科學認識和把握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規律和主軌跡的最高“范式”,無疑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適用于我們科學認識和把握一切科學研究發展史的規律與軌跡。
庫恩范式所描述的自然科學研究史,既不是關于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的文本記述史,也不是與文本記述史相關聯的科學研究活動史,而是這兩種“史”及與此相關的各種社會歷史因素交匯、整合而呈現的關于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這就是范式的本質。
在這種意義上理解和把握范式的本質,一要看特定的社會所能給予科學研究的“前提和條件”及社會已經提出的“社會功能”要求。二要看科學研究的范式傳統是否存在面臨“科學革命”而需要適時地給予調整、重組乃至轉型或轉向的必要,如果存在這種必要,那也不可輕率地倡導“轉換”,而應當因勢利導、憑借其“共同體的成員”形成的“合力”,順乎“自然”地去實現。不然,就可能會違反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違背“科學共同體”的集體意志,以及范式傳統維護和遵循的共同的“理論框架”、“研究方式”、“話語體系”等。一句話,背離了庫恩發現、描述和貢獻范式的旨趣。對社會科學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學的研究范式的理解和把握,更應當作如是觀。
作為一種“自然歷史過程”,范式可以為人所認知和把握,因而可以“順其自然”地促其豐富和發展,但一般不可以“人為”地“轉換”。托馬斯·庫恩在科學學和科學史的意義上探討過范式轉換的問題,他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學術態度是積極又審慎的。在他看來,“科學共同體取得一個范式就是有了一個選擇問題的標準,當范式被視為理所當然時,這些選擇的問題被認為是有解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對這些問題,科學共同體才承認是科學的問題,才會鼓勵它的成員去研究它們。”與此同時,對“其他科學關心的問題”或本學科暫時感到“太成問題而不值得花費時間去研究的問題”,加以“拒斥”。[11]庫恩對范式“轉換”問題所持的這種科學態度,是合乎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
用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觀點來看,范式所反映的“科學革命”是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正如J·D貝爾納“在通向科學學的道路上”所指出的那樣:“某些因素的數量變化,導致不同質的產生。當我們開始認識科學發展的某種模式時,科學卻又向前邁進了。”[12]
如前所說,范式的形成得益于“科學革命”,每當這樣的“革命”發生時范式就面臨“轉換”。
但是,庫恩并不輕言“轉換”,更不刻意鼓動“轉換”,范式“轉換”不是他著述“科學革命的結構”的主要目的。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第四章“常規科學即是解謎”中甚至強調,任何科學研究的結果都是有意義的,科學家在“擴大范式所能應用的范圍和精確性”的問題上,應當持“熱情和專注”的科學態度,不可隨意“轉換”范式。竊以為,這種主張本身就應屬于范式“結構”的一個要素。[13]
這是因為,“范式轉換”的命題容易產生誤解。從范式的本質來看,“轉換”不過是范式發展演變的“自然歷史過程”的一種表現,是其“自然歷史過程”因由“科學革命”而需要調整方向和改變軌跡,實則是“轉向”或“轉型”。而從實際情況看,“借用”范式的人們對“范式轉換”則多不這樣看,他們所言說的“轉換”是要“換藥”而不僅僅是“換湯”。
從邏輯上來分析,視社會事物的發展變化為“自然歷史過程”的轉向或轉型,是尊重社會事物發展規律的表現,而“轉換”卻是主觀給定的“思想過程”,不一定合乎社會事物發展的自身規律。“轉換”在“換”了事物外在的形狀和發展方向的同時,也就可能會“換”了事物的內在結構和本質特性。③
由此看來,在正確理解和把握范式本質的前提下,如果說范式“轉換”是必要的,那么慎言范式“轉換”就顯得更為重要了。
三、范式的功能與方法論閾限
如果說,發現和描述的“自然科學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具有普遍的功能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論意義,那么在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則不然。這就是范式的功能和方法論閾限問題。
自然科學研究范式基于適應“科學革命”的“轉換”,反映的是社會發展進步對科學技術提出的豐富“社會功能”和優化組織方式的要求,其學說主張顯然也不應生搬硬套到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學領域。
范式的功能在于揭示和描述隱藏在自然科學研究發展史之中的規律,進而提出科學家共同體成員應遵循的共同理念和規則,實現規則與規律的統一。任何規律都是一般與個別的統一,因而反映規律的規則也都具有普遍的認知和實踐意義。范式所揭示的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在一般性的意義上是否適應于我們揭示和描述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但須知,揭示與描述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的和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的范式是不一樣的,也不可能是一樣的。這主要是因為,社會科學研究受社會有效因素的影響與力度同自然科學研究的情況不一樣,不可能一樣,也不可以一樣。如果說,自然科學研究范式的形成和“轉換”較多地受社會需求包括體現社會需求的國家意志(政策和策略)的影響和制約,那么,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關涉經濟、政治、法律乃至文化基本制度的研究,就更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國家意志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干預和指導,其范式不能成為一種“科學共同體”或“學術權威共同體”的“利益集團”,即使這樣的“共同體”是以“百家爭鳴”的方式存在的。
由此看來,我們在理解和把握社會科學研究尤其諸如思想政治教育之類學科的研究范式的問題上,不應當在一般意義上抽象地借用托馬斯·庫恩提出的范式和范式轉換的問題。
在庫恩那里,范式轉換就是科學革命,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領域是否亟待實行這樣的“科學革命”,以至于在遮蔽和擱置基本原理的情勢下實行這樣的“科學革命”,是需要持極為慎重的態度的。因為,人可以認識和把握規律,創建和運用反映規律的規則,以發展和造福自身,卻不可以創造和“轉換”規律。社會科學研究的規律與自然科學研究的規律有相通之處,但并不相同,反映兩種研究規律的范式也不應相同。這也如同自然有生態,社會有生態,但不可將社會生態與自然生態相提并論、混為一談的道理一樣。
厘清范式的功能與方法論閾限,應是廣義科學學(將所有科學作為自己對象)之研究范式的一種基本要求。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廣義科學學對此似乎還沒有給予更多的關注。
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
范式作為自然科學研究一種方法論的理論和認知原則,是否適應于社會科學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學的研究?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已經多次涉論這個問題,但多為發現和描述范式之“一帶而過”的過渡語。
據托馬斯·庫恩自己介紹,1958~1959年間他應邀在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做研究,“在主要是由社會科學家組成的團體中度過的”,使他感到“震驚的是,社會科學家關于正當的科學問題與方法的本質,在看法上具有明顯的差異”,這是他“未曾預料過的”。[14]在科學研究范式的問題上,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究竟存在哪些“明顯的差異”以及為什么會存在“明顯的差異”,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并沒有細說。盡管如此,我們已經從中清楚地看出,庫恩已經把兩大科學領域存在的這種“明顯的差異”問題,明白無誤地提了出來。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有助于梳理和總結其有史以來的規律和軌跡之“自然歷史過程”,進而把握其方法論規則,這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中國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實踐豐富,著述紛呈,亟待今天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共同體”進行開發和描述,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傳承和創新。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首先要看到“借用”的范式本是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不可照搬照用,必須經過創新。任何一種方法,都是“神”(功能)與“形”(形體)的統一體。某種科學需要“借用”其他科學的研究方法,只有在“借”得其他方法之“神”的情況下,才可能“借用”,實現研究方法的創新,發揮被借用的方法的功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唯有“借”得范式的“傳神”之處,才可能實現方法創新,不然,實際上就成了方法套用或方法移植,毀傷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應有的邏輯結構。這樣說,并不是認為不同門類科學的研究方法不可以“移植”,更不是認為方法“移植”與方法創新是對立的,而是強調所“移植”的是方法之“神”還是方法之“形”。④
其次,要區分研究范式與“文明樣式”的學理邊界。一些中國學者已經習慣于在樣式的意義上言說庫恩范式和“范式轉換”,如“哲學范式”、“人學范式”等。這其實是一種學理上的誤解。在中國人的話語系統中,文明樣式一般是指某種知識理論體系或精神文化的內在特質、價值目標和意義向度及其顯露的形態或形式,如“道德樣式”、“文學樣式”等,而范式所指則是科學研究方法論,當“范式”搭配哲學、人學時,其語義和語形實則是“哲學(研究)范式”、“人學(研究)范式”。如今一些學者倡導的“哲學范式轉換”、“人學范式轉換”,所指,實則是“哲學樣式轉換”、“人學樣式轉換”。
再次,堅持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邏輯結構。
歷史地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之結構要素中的“科學共同體”、“研究傳統”、“理論框架”、“研究方式”、“話語體系”等都是具體的,都具有鮮明的國情特質,不僅是歷史范疇,也是民族范疇。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論》中論及“第三類科學”時指出,“第三類科學”是“研究人的生活條件、社會關系、法的形式和國家形式及其哲學、宗教、藝術等等組成的觀念上層建筑”,其間存在杜林所鼓吹的“永恒真理的情況更糟糕”。[15]思想政治教育作為理論一級學科統攝下的一門二級學科,無疑屬于這樣的“第三類科學”。這種學科屬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不可將范式抽象化、一般化,而必須放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和發展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尊重中國國情、世情和黨情。
如此來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就不會遮蔽其與庫恩“自然科學研究范式”之間存在的“明顯差異”,不至于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共同體的成員”尤其是青年成員,在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問題上陷落“未曾預料”的迷途和窘境。
注釋
①關于科學學的對象,研究科學學的人目前的意見大體有兩種:一是“整體科學”或“科學的整體”,包括自然科學之外的哲學、社會科學有門類乃至所謂中介學科如自然辯證法、唯物史觀等;另一種專指自然科學。范式是庫恩在考察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史的過程中發現的,故而筆者稱其歸為狹義科學學范疇。
②當代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強調唯物史觀在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學研究方法創新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是否也是一種帶有“科學革命”性質的亟待梳理和澄明的“研究范式”呢?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③這個道理如同理解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自然歷史過程”,只能順乎其發展規律和方向推動“社會轉型”而不可強行“社會轉換”一樣。
④筆者曾用俗語對方法借用和創新作如是比方說:“如菜刀(工具方法),可以用來切菜、切瓜,可以用來宰雞,還可以用來裁紙,其所以如此,皆因其‘貌’在‘刀’而其‘神’卻在‘切’。在這里,‘借刀’全在借刀的‘切’之‘神’即刀之功用。世上的刀有很多種,但其功用卻都在‘切’,正是‘切’使刀具有廣闊運用領域,同時又使刀作為一種工具方法而存在方法的閾限。”(參見拙文:《略論道德悖論研究的方法問題——兼談邏輯悖論對于道德悖論研究的方法閾限》,中國人民大學書報復印中心《倫理學》,2009年第6期)。
參考文獻
[1][7][12][英]J·D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M].陳體芳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8,1,2.
[2]陳士俊.科學學:對象解析、學科屬性與研究方法——科學學若干基本問題的思考[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0(5):28-35.
[3][4][5][6][8][11][13][14][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1,1,9,10,21,34,33,4.
[9]參見張耀燦.推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學轉換[J].思想教育研究,2010(7):3-6.
- 上一篇:吞咽功能康復訓練范文
- 下一篇:城市靜態停車管理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