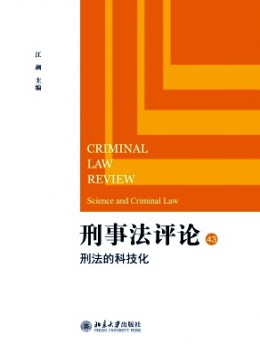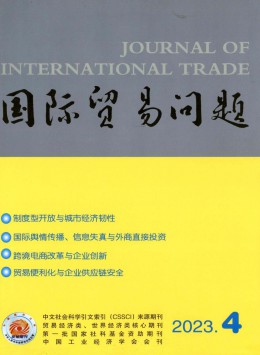證據(jù)法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證據(jù)法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證據(jù)法論文范文
證據(jù)契約[①],由“證據(jù)”和“契約”二字組成,看起來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yàn)槲覀儗Α白C據(jù)”和“契約”早已司空見慣,而對“證據(jù)契約”則比較新鮮陌生。然而,在大陸法系的德國、日本、意大利等國家,關(guān)于證據(jù)契約的研究由來已久并有不少立法采納了證據(jù)契約制度,如意大利。我國臺灣地區(qū)的學(xué)者在這方面的研究雖稍落后于德日等國,但成果不菲。相比之下,我國大陸學(xué)者的在這方面的專門研究卻比較罕見,有的也是在討論訴訟契約時論述一點(diǎn)點(diǎn)。[②]研究雖未成氣候,但前輩們的相關(guān)見解皆具啟發(fā)性,值得重視。
契約,一直以來為私法領(lǐng)域所壟斷,自從19世紀(jì)后葉訴訟法學(xué)脫離私法學(xué)的支配而開始確立其理論時期時,學(xué)者們普遍不接受在訴訟法學(xué)領(lǐng)域的存在契約。[③]學(xué)者均是以訴訟的公法性為理由排斥契約在公法領(lǐng)域的存在。但目前更多的學(xué)者均對訴訟上存在契約持肯定說,認(rèn)為訴訟上存在契約,使法律未予以明文規(guī)定的合意也并不當(dāng)然禁止。[④]筆者當(dāng)然是贊同肯定說,而且筆者同樣認(rèn)為,證據(jù)法上也存在契約。但筆者并非簡單地從“訴訟法上存在契約”、“證據(jù)法屬于訴訟法的分支”、所以“證據(jù)法上也存在契約”這樣一個三段論得出來的結(jié)論。
契約,千百年來一直與人類相依為伴,但契約并非只存在于私法領(lǐng)域。在羅馬法上,不僅私法上有契約的概念,公法和國際法上也有這個概念。優(yōu)帝《學(xué)說匯纂》就把協(xié)議(Conventio)分為國際協(xié)議、公法協(xié)議和私法協(xié)議三種。[⑤]但承認(rèn)公法領(lǐng)域也有契約,就會出現(xiàn)一個法律悖論:公法的規(guī)范不得由個人的協(xié)議變更,而契約屬于私力范疇,承認(rèn)公法領(lǐng)域也有契約,無異于承認(rèn)“公法的規(guī)范可由個人的協(xié)議變更”。如何解釋這一悖論,同樣是證據(jù)契約不可逃避的問題。但去解釋這一悖論就暗含這樣的意思,即證據(jù)法是公法。筆者雖不完全認(rèn)同證據(jù)法完全是公法,但問題終究是要解決的。到底什么是證據(jù)契約?證據(jù)契約的存在有何依據(jù)?它有什么效力?契約自由原則能否適用證據(jù)契約?證據(jù)契約在我國前景如何?
一、證據(jù)契約的概念
思維需要概念的支撐,尤其是對證據(jù)契約這樣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進(jìn)行探討。一般認(rèn)為,證據(jù)契約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證據(jù)契約是指有關(guān)訴訟中的事實(shí)確定方法的訴訟契約。廣義上還包括變更舉證責(zé)任分配原則的舉證責(zé)任契約。此外,證據(jù)契約還單指為方便法官認(rèn)定事實(shí)活動而訂立的契約。狹義證據(jù)契約的典型例子有:自認(rèn)契約、證據(jù)方法契約或證據(jù)限制契約、鑒定契約、確定各種證據(jù)方法和證明力的契約等。[⑥]“對一個概念下定義的任何企圖,必須要將表示該概念的這個詞的通常用法當(dāng)作它的出發(fā)點(diǎn)。在對法的概念下定義時,我們必須從考察下述問題開始:一般稱為‘法’的這些社會現(xiàn)象是否提供了使它們區(qū)別于其他同類社會現(xiàn)象的一個共同特征?這一特征在人的社會生活中是否重要到這樣的程度,即可能成為有助于認(rèn)識社會生活中各種概念的基礎(chǔ)?”[⑦]因此,在筆者看來,對證據(jù)契約下定義與對法下定義一樣,將表示證據(jù)契約概念的這個詞的通常用法當(dāng)作它的出發(fā)點(diǎn),要體現(xiàn)“契約”這一共同現(xiàn)象,即在表述上一是應(yīng)當(dāng)體現(xiàn)契約的共性,二是應(yīng)當(dāng)突出證據(jù)契約的特性。
證據(jù)契約與私法上契約都屬于契約,因而也具有契約最本質(zhì)的特征:首先,證據(jù)契約的訂立人是平等的訴訟主體,在訴訟中雙方當(dāng)事人的訴訟地位平等。其次,訂立證據(jù)契約是出于自愿,當(dāng)事人有選擇訂立或不訂立證據(jù)契約的自由。再次,當(dāng)事人之間達(dá)成證據(jù)契約時往往出于理性和功利的考慮。最后,卻是最重要的一點(diǎn),就是證據(jù)契約是當(dāng)事人之間意思一致的合意,只有雙方當(dāng)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時,才達(dá)成證據(jù)契約,產(chǎn)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但是,證據(jù)契約也不完全等同于私法上的契約,最明顯的區(qū)別體現(xiàn)在私法契約的內(nèi)容完全是實(shí)體性民事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的變動;而證據(jù)契約的內(nèi)容大多是民事主體對其所享有的程序性權(quán)利的自由處分和對程序性義務(wù)的自愿負(fù)擔(dān),這種處分和負(fù)擔(dān)行為可能會對各民事主體之間實(shí)體性民事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產(chǎn)生間接的影響。另一重要區(qū)別即在于證據(jù)契約產(chǎn)生的效果不同于私法上契約產(chǎn)生的效果,前者旨在產(chǎn)生訴訟法上效果,后者產(chǎn)生私法上效果。在德國,研究者一般將證據(jù)契約與舉證責(zé)任契約相區(qū)分,Rosenberg即在定義上將兩者區(qū)分開來。[⑧]筆者認(rèn)為,嚴(yán)格說來,證據(jù)契約與舉證責(zé)任契約應(yīng)有所區(qū)別,但是否有區(qū)分的必要性則仍存疑問。將兩者區(qū)分開來,其優(yōu)點(diǎn)在何處亦難以言明,再加上我們已經(jīng)習(xí)慣把舉證責(zé)任理論放入證據(jù)法學(xué)理論體系,故本文不對這兩種契約作區(qū)分,而是采廣義證據(jù)契約概念,即包括舉證責(zé)任契約。綜上所述,筆者認(rèn)為,證據(jù)契約即為平等的當(dāng)事人之間就訴訟中的事實(shí)確定方法的旨在產(chǎn)生訴訟法上效果的合意,包括在事實(shí)不能證明時的責(zé)任承擔(dān)的合意,即包含舉證責(zé)任契約。
二、證據(jù)契約存在的依據(jù)及價值
(一)法理依據(jù)
契約的本質(zhì)即合意,其得以存在的理論根基在于當(dāng)事人的“意思自治”。證據(jù)契約作為“證據(jù)”和“契約”結(jié)合生成的詞語,本身體現(xiàn)了私法精神對證據(jù)法的深遠(yuǎn)影響,同時也蘊(yùn)涵了解決民事糾紛的程序法獨(dú)特的價值。而證據(jù)法的“兩棲性”亦為證據(jù)契約的存在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1.私法精神在民事訴訟領(lǐng)域的擴(kuò)張。私權(quán)的救濟(jì)有賴于民事訴訟權(quán)利的行使,當(dāng)事人將發(fā)生的糾紛訴諸法院,目的在于通過民事訴訟解決其糾紛,保護(hù)其合法權(quán)益。此時,糾紛的解決過程可以被看作是由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實(shí)體法共同作用的“場”,因?yàn)橐环矫婷袷略V訟要依照民事訴訟程序法進(jìn)行,另一方面法官必須依照民事實(shí)體法作出判決,缺少任何一面都會使民事訴訟陷入停滯。“民事訴訟從國家對公民來說,這是公法關(guān)系,但是,從民事訴訟所要解決的糾紛的內(nèi)容來看,顯然民事訴訟又具有私法性質(zhì)的關(guān)系”。[⑨]因此,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則必然會延伸到帶有私法性質(zhì)的民事訴訟法領(lǐng)域。當(dāng)事人作為實(shí)體法的權(quán)利主體,既然可以在實(shí)體法領(lǐng)域處分自己的實(shí)體權(quán)利,同樣可以在民事訴訟領(lǐng)域自由處分自己的權(quán)利。這一自由體現(xiàn)在證據(jù)法上,則應(yīng)盡可能地樹立尊重合意的觀點(diǎn),法官在對案件事實(shí)進(jìn)行自由心證時,應(yīng)當(dāng)尊重當(dāng)事人對證據(jù)處理和選擇的合意,當(dāng)事人有權(quán)就證據(jù)事項(xiàng)達(dá)成證據(jù)契約。可見,證據(jù)契約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私法自治精神向民訴訟領(lǐng)域的延伸。
2.程序主體性原則之體現(xiàn)。近代以來,程序主體性原則已為各國所公認(rèn)。毫無疑問,當(dāng)事人是其實(shí)體權(quán)利的主體。當(dāng)事人將糾紛交由法院解決,形成“三角”結(jié)構(gòu),法官代表國家權(quán)力作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糾紛,但這并未改變當(dāng)事人的主體地位。相反,實(shí)體上的主體地位轉(zhuǎn)化成程序上的主體地位,當(dāng)事人的主體地位在程序上應(yīng)當(dāng)?shù)玫匠浞肿鹬亍R罁?jù)程序主體性原理,在涉及當(dāng)事人等利害關(guān)系人的利益、地位、責(zé)任或權(quán)利義務(wù)的審判程序中,應(yīng)從程序上保障其有參與程序以影響裁判形成的程序主體權(quán);而且,在裁判作成以前應(yīng)保障其有能夠適時、適式地提出資料、陳述意見或者進(jìn)行辯論的機(jī)會;在未被賦予此項(xiàng)機(jī)會之情況下所收集的事實(shí)及證據(jù),不得直接成為法院裁判的基礎(chǔ)。[⑩]那么在程序設(shè)計(jì)上就應(yīng)當(dāng)充分考慮程序利用者――人的自主性、自覺性與選擇性,賦予當(dāng)事人廣泛而充分的程序性權(quán)利,保證程序主體有充分地參與程序的機(jī)會。當(dāng)事人作為一個自主的理性人,有權(quán)利也有能力在程序上作出選擇,以滿足其程序主體性之要求。而契約正好符合這一要求,契約的根源之一即選擇,“沒有選擇,即使有了勞動的專業(yè)化和交換,對最簡單的契約也沒有意義。如果從契約的概念中去掉了選擇,那么,世界上最好的契約當(dāng)事人就不是人類,而是群居的昆蟲,特別是螞蟻了。”[11]當(dāng)事人通過達(dá)成證據(jù)契約行使選擇權(quán)參與程序,有了契約的權(quán)利,也就有了選擇的權(quán)利,使其程序主體性得以充分體現(xiàn)。
3.證據(jù)法的“兩棲性”為證據(jù)契約的存在提供了空間。不可否認(rèn),民事證據(jù)法由于涵括了法院調(diào)取證據(jù)、采信證據(jù)等一系列具有職權(quán)色彩的內(nèi)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法性質(zhì)。但道德與法的結(jié)合在公法領(lǐng)域亦為勢所必然。事實(shí)上,民事證據(jù)法中關(guān)于當(dāng)事人舉證、質(zhì)證、證據(jù)披露,自認(rèn)等許多規(guī)則本身即帶有強(qiáng)烈的私法色彩,并且,隨著訴訟證據(jù)制度設(shè)計(jì)上當(dāng)事人主義模式與職權(quán)主義模式的融合,當(dāng)事人主義模式漸為人們所接受,使得這種“私法化”必將更為明顯,因而以私法的理念和原則來約束當(dāng)事人之間的證據(jù)法律關(guān)系亦為必要。此外,民事證據(jù)法雖被大多數(shù)人界定為程序法,但其中關(guān)于舉證責(zé)任分配等許多內(nèi)容不完全是程序法問題,而往往是在實(shí)體法即民法中作出規(guī)定,況且,民事證據(jù)并不完全用于訴訟和審判,它同時也用于指導(dǎo)和規(guī)范民事行為,確認(rèn)和證明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產(chǎn)生、變更和消滅,保護(hù)民事權(quán)利和避免民事糾紛。也就是說,證據(jù)問題離開訴訟也會發(fā)生,也正因如此,我國亦有部分學(xué)者提出可將民事證據(jù)置于民法典中來規(guī)定。[12]因此,證據(jù)法的內(nèi)容不全為公法,總有那么一部分公益色彩不那么濃厚的“任意規(guī)定”。當(dāng)事人通過證據(jù)契約處分自己的“私”權(quán)利,即使違反了“任意規(guī)定”,如果對方當(dāng)事人并不提出異議,就沒有必要視為無效,因?yàn)檫@反而有利于訴訟程序的穩(wěn)定與經(jīng)濟(jì)。
(二)訴訟模式基礎(chǔ)
在民事訴訟領(lǐng)域,向來存在職權(quán)主義訴訟民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之爭,由于兩種模式之間的某些差異帶有根本性,這就使得某些具體訴訟制度的存在與適用實(shí)際上成為訴訟模式選擇的結(jié)果。證據(jù)契約也不例外,其制度的生存依賴于訴訟模式基礎(chǔ),那就是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所謂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一是指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繼續(xù)依賴于當(dāng)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主動依職權(quán)啟動和推進(jìn)民事訴訟程序,二是法院或法官裁判所依賴的證據(jù)資料只能依賴于當(dāng)事人,作為法院判斷的對象的主張來源于當(dāng)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在當(dāng)事人指明的證據(jù)范圍以外主動收集證據(jù)。而當(dāng)事人主義的核心和基調(diào)是辯論主義原則和處分原則。依照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理論,辯論主義是指認(rèn)定案件事實(shí)的有關(guān)訴訟資料只能由當(dāng)事人提出,否則不能作為法院裁判的根據(jù),即“當(dāng)事者以什么樣的事實(shí)作為請求的根據(jù),又以什么樣的證據(jù)來證明所主張的事實(shí)存在或不存在,都屬于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領(lǐng)域”。[13]而處分原則作為當(dāng)事人主義的另一重要表現(xiàn),包括:一是訴訟只能根據(jù)當(dāng)事人的申請開始;二是當(dāng)事人決定審理對象的內(nèi)容和范圍,而且對于訴訟標(biāo)的的變更,當(dāng)事人也有決定權(quán);三是訴訟可以基于當(dāng)事人意思而終結(jié)。其中,“當(dāng)事人對作為裁判基礎(chǔ)的案件事實(shí)的處分是當(dāng)事人行使處分權(quán)的重要內(nèi)容。當(dāng)事人對訴訟資料的處分表現(xiàn)在:當(dāng)事人沒有在特定階段和場合(辯論過程中)提出來的案件事實(shí),裁判者不能作為判案的依據(jù)”。[14]這說明,在對訴訟資料的處分上,處分原則與辯論主義原則不謀而合。
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集中體現(xiàn)了民事訴訟領(lǐng)域的意思自治;而證據(jù)契約作為反映私法自治精神的具體形式,也是意思自治原則在民事訴訟領(lǐng)域的體現(xiàn)。因而,對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辯論主義原則與處分原則的承認(rèn)與尊重必然意味著對證據(jù)契約這一民事行為方式的肯定。由此可以得出結(jié)論,證據(jù)契約與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在制度上存在契合,而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也正是證據(jù)契約制度得以建立和發(fā)展的訴訟模式基礎(chǔ)。在職權(quán)主義訴訟模式下,法院有全面調(diào)查取證的權(quán)力,可以在辯論程序之外尋求定案的依據(jù),辯論主義和處分原則對法院沒有約束力,因此在職權(quán)主義訴訟模式下討論證據(jù)契約既缺乏法理依據(jù),也無實(shí)際意義。
無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都是當(dāng)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15]這為證據(jù)契約制度在兩大法系的發(fā)展奠定了制度基礎(chǔ),但證據(jù)契約的提法只存在于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盡管在司法實(shí)踐中存在當(dāng)事人間的證據(jù)“合意”,卻不使用證據(jù)契約這一提法。
(三)價值
筆者認(rèn)為,證據(jù)契約存在以下價值:
1.有利于實(shí)現(xiàn)實(shí)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契約即公正”[16]。根據(jù)當(dāng)事人之間的證據(jù)契約認(rèn)定案件事實(shí)解決糾紛,不僅是符合實(shí)體正義而且是符合程序正義的。“當(dāng)某人就他人事務(wù)做出決定時,可能存在某種不公正。但當(dāng)他就自己的事務(wù)做決定時,則決不可能存在任何不公正。”[17]當(dāng)事人承認(rèn)對方當(dāng)事人提出的證據(jù)事實(shí),在局外人看來或許是不公正的,但作為一個理性人的選擇,其意圖并非局外人所知曉。因此,自由訂立證據(jù)契約就意味著正義。
2.提高訴訟效率,降低訴訟成本。案件事實(shí)畢竟是過去的事實(shí),是獨(dú)一無二的,想象或模擬的重建都不能確切的重現(xiàn)過去。[18]證明案件事實(shí)需要證據(jù)來證明,而人的訴訟能力又是有限的,搜集證據(jù)往往是一個艱辛的過程,使得訴訟周期變得越來越長。長時間訴訟不僅使當(dāng)事人爭議的利益得不到實(shí)現(xiàn),反而增加了當(dāng)事人訟累。而證據(jù)契約能夠便捷訴訟,比如雙方達(dá)成自認(rèn)的契約,免除了對方當(dāng)事人的舉證責(zé)任,這樣,原本必須進(jìn)行的當(dāng)事人舉證、法院調(diào)查證據(jù)、質(zhì)證、認(rèn)證等環(huán)節(jié)被簡化,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證明的環(huán)節(jié)和費(fèi)用,縮短了訴訟的周期,降低了當(dāng)事人和人民法院在時間、人力、物力、財(cái)力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同時也提高了訴訟效率。
3.有利于限制法官恣意,彌補(bǔ)立法缺陷。證據(jù)契約充分凸現(xiàn)了當(dāng)事人的程序主體地位,是個體自主決定自己命運(yùn)的行為載體,通過自主決定的形式,主體的自由得到張揚(yáng)。證據(jù)契約對法官的制約作用,亦可以促使法官充分尊重當(dāng)事人的意思自治,制約法官恣意。“法律不能完備無遺,不能寫定一切細(xì)節(jié)”[19],法律固有的缺陷使得立法追求的理想難以實(shí)現(xiàn)。通過雙方達(dá)成證據(jù)契約,對相關(guān)的可支配事項(xiàng)達(dá)成合意,制定子規(guī)則,不僅滿足當(dāng)事人的權(quán)利需要,在客觀上也彌補(bǔ)了立法的不足。
三、證據(jù)契約的性質(zhì)與效力
(一)性質(zhì)
證據(jù)契約的法律性質(zhì),則與其概念的界定密切相關(guān)。因若將證據(jù)契約以最廣義方式理解,則實(shí)體法性質(zhì)之確認(rèn)契約亦為證據(jù)契約,但一般將他們區(qū)分,并不視為同一。[20]與之相似的訴訟契約的性質(zhì),存有爭議,目前有“訴訟行為說”、“私法行為說”、“折中說”等,而“折中說”又包含兩種相對立的觀點(diǎn):“兩行為并存說”和“一行為兩性質(zhì)說”。[21]而對證據(jù)契約的性質(zhì),理論上爭議似乎不大,一般認(rèn)為是訴訟行為之一種。臺灣學(xué)者邱聯(lián)恭與陳計(jì)男即持此觀點(diǎn)[22]。但臺灣有學(xué)者認(rèn)為:“有效之證據(jù)契約既發(fā)生訴訟法上之效果,自系訴訟契約之一種。”[23]盡管其結(jié)論可能是正確的,但以其產(chǎn)生的法律效果來判斷一個行為的性質(zhì),似乎有悖邏輯。因?yàn)檎_的邏輯應(yīng)該是性質(zhì)(因)決定效果(果),以效果作為標(biāo)準(zhǔn)判決一種行為的性質(zhì)就顛倒了邏輯(結(jié)果決定原因)。筆者認(rèn)為,應(yīng)以合意的內(nèi)容為基準(zhǔn)、兼考慮目的來判斷證據(jù)契約的性質(zhì)。證據(jù)契約是有關(guān)訴訟中的事實(shí)確定方法的合意,目的是影響法官在選擇使用證據(jù)材料,以產(chǎn)生訴訟法上的效果,沒有涉及私法上權(quán)利義務(wù)的設(shè)定和分配。因此,證據(jù)契約屬于純粹的訴訟行為。
(二)效力
證據(jù)契約的效力,是指當(dāng)事人之間達(dá)成的證據(jù)契約對當(dāng)事人及法院產(chǎn)生的拘束力。表現(xiàn)在兩方面:
1.對當(dāng)事人的拘束力。證據(jù)契約既為當(dāng)事人雙方的合意,當(dāng)事人就應(yīng)當(dāng)遵守合意。如雙方當(dāng)事人在契約中約定舉證期限,超過期限向法院所提交的證據(jù)即無效。當(dāng)一方當(dāng)事人違約,另一方當(dāng)事人有權(quán)提出異議。至于當(dāng)事人違反證據(jù)契約義務(wù)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的法律后果,筆者認(rèn)為這已屬消極責(zé)任,即法院應(yīng)當(dāng)依據(jù)合法有效的證據(jù)契約確認(rèn)違約行為不發(fā)生訴訟法上的效果。
2.對法院的拘束力。根據(jù)私法中的契約相對性原則,只有契約當(dāng)事人才受契約約束,也只有契約當(dāng)事人才能享受基于契約所產(chǎn)生的權(quán)利并承擔(dān)根據(jù)契約產(chǎn)生的義務(wù)。[24]證據(jù)契約也只有在當(dāng)事人之間發(fā)生效力,對一般的第三人皆無約束力。但證據(jù)契約的目的在于發(fā)生訴訟法上的效果,如果只對當(dāng)事人有約束力,無法解釋證據(jù)契約何以產(chǎn)生訴訟法上的效果。因此證據(jù)契約的要達(dá)到目的,還依賴于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法院對證據(jù)契約的確認(rèn)。也即,盡管證據(jù)契約一經(jīng)成立,沒有必要向法院申請批準(zhǔn)即在當(dāng)事人之間發(fā)生效力,但若要產(chǎn)生訴訟法上的效果,仍需要法院的參與。但其對法院產(chǎn)生拘束力的法理依據(jù)何在?
如前所述,證據(jù)契約的訴訟模式基礎(chǔ)是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而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主要體現(xiàn)之一即辯論主義原則。依據(jù)辯論主義,法院應(yīng)當(dāng)受當(dāng)事人主張和舉證的約束。辯論主義也反映了以私權(quán)自治為基礎(chǔ)的訴訟中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這與證據(jù)契約所體現(xiàn)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基于辯論主義原則,證據(jù)契約對法院有拘束力,法院必須尊重當(dāng)事人的合意。如果法院違反了當(dāng)事人的合意,將可能成為上級法院撤銷判決的理由。
但是,證據(jù)契約產(chǎn)生效力的前提是必須合法,包括形式合法與實(shí)質(zhì)合法兩方面。一是形式要合法。證據(jù)契約的形成主體必須是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當(dāng)事人、無民事行為能力當(dāng)事人的法定人、經(jīng)特別授權(quán)的委托訴訟人,并且合意的內(nèi)容都應(yīng)當(dāng)以當(dāng)事人的名義承擔(dān)后果。必須是自愿訂立證據(jù)契約,在欺詐、脅迫等情形下訂立的證據(jù)契約當(dāng)事人有權(quán)撤銷。二是內(nèi)容要合法。以損害國家、集體和第三人合法利益為目的訂立的證據(jù)契約無效,限制法官自由心證的證據(jù)契約無效,如雙方約定某一證據(jù)的證明力低于另外一個證據(jù)。但在有關(guān)證據(jù)的合意并不侵犯自由心證主義的領(lǐng)域,而當(dāng)認(rèn)為是可以采納辯論主義時,則不認(rèn)為其已對自由心證侵害,因此并不否定其效果。[25]
四、證據(jù)契約自由及其限制[26]
“所有權(quán)絕對、過錯責(zé)任和契約自由為近代私法的三大原則,而契約自由又是私法自治(意思自治)的核心部分。”[27]既然證據(jù)契約是私法自治在私法領(lǐng)域向公法領(lǐng)域延伸的結(jié)果,作為私法自治核心部分的契約自由原則是否適用證據(jù)契約?
(一)證據(jù)契約自由原則
所謂契約自由原則,其實(shí)質(zhì)是契約的成立以當(dāng)事人的合意為必要,包括締約與否自由、確定契約內(nèi)容自由及締約方式自由。其中,締約與否自由包含是否締約自由與選擇契約相對人自由。契約自由原則是否適用于證據(jù)契約,“有謂訴訟行為原則上不適用契約自由之原則,幫不得訂立證據(jù)契約者,有謂當(dāng)事人之私權(quán)既得任意處分,自得訂立證據(jù)契約以為約束”[28],因此在理論上存在爭議。筆者認(rèn)為,證據(jù)契約符合契約的本質(zhì)特征,而且從證據(jù)契約的締約過程到締約內(nèi)容看,證據(jù)契約也應(yīng)適用契約自由原則。證據(jù)契約的締約主體是平等的訴訟當(dāng)事人,訂立證據(jù)契約是出于自愿,而且往往是出于理性和功利的考慮,當(dāng)事人可以選擇締結(jié)證據(jù)契約的方式,如書面或口頭方式,當(dāng)事人有權(quán)在法律允許范圍內(nèi)選擇證據(jù)契約的內(nèi)容。因此,證據(jù)契約與私法上的契約一樣適用契約自由原則,在表述上就是“證據(jù)契約自由”原則。證據(jù)契約由當(dāng)事人自主締結(jié),法官不得隨意干涉。
然而,證據(jù)契約畢竟不同于私法上的契約,尤其是在內(nèi)容與效果兩方面有很大不同。若證據(jù)契約完全自由,則有可能造成以下后果:
1.證據(jù)契約適用的泛化會抹煞民事訴訟制度固有的本質(zhì)特征。民事訴訟制度作為民事經(jīng)濟(jì)糾紛的解決機(jī)制不同于其它民事糾紛解決本質(zhì)屬性就在于國家公權(quán)力的介入。對證據(jù)的收集、保全、提出、質(zhì)證、認(rèn)證等法律都有一系列的規(guī)定,因此證據(jù)制度中的許多設(shè)置具有相當(dāng)程度上非選擇性,如關(guān)于證據(jù)的審核認(rèn)定的規(guī)定,須由法官依據(jù)民事訴訟程序,全面、客觀的審核證據(jù),依據(jù)法律規(guī)定,遵循法官職業(yè)道德,運(yùn)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對證據(jù)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dú)立進(jìn)行判斷。而證據(jù)契約的理念是當(dāng)事人的意思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與民事訴訟制度或證據(jù)制度的非選擇性沖突,其本身與民事訴訟制度的公法性質(zhì)存在緊張關(guān)系。若不恰當(dāng)處理兩者關(guān)系,任由證據(jù)契約自由原則泛化,則會抹煞民事訴訟制度固有的本質(zhì)特征。
2.證據(jù)契約達(dá)成的基礎(chǔ)有時并不可靠,可能淪為強(qiáng)勢當(dāng)事人實(shí)現(xiàn)不法目的的工具。契約達(dá)成的前提是雙方當(dāng)事人真實(shí)意思的一致,只有建立在平等與合意的基礎(chǔ)上的契約才是合法有效的。因此,契約自由建立的理論前提是主體平等。然而這一主體平等并非就是現(xiàn)實(shí)的平等,其忽略個體固有的經(jīng)濟(jì)上的、政治上的、知識結(jié)構(gòu)上的區(qū)別,是一種抽象的平等。這樣抽象的平等在現(xiàn)實(shí)中不免帶有神化色彩,實(shí)際上,即使在古典契約理論建立之初個體間的不平等就是存在的,“古典的‘契約自由’概念甚至從一開始便存在著某些嚴(yán)重的缺陷。”[29]私法上契約自由的缺陷在證據(jù)契約中同樣存在,當(dāng)事人在締結(jié)證據(jù)契約時很難真正實(shí)現(xiàn)地位平等與信息對稱。尤其是證據(jù)運(yùn)用的技巧性相當(dāng)強(qiáng),當(dāng)事人能否在平等的地位把握締約時的尺度不無疑問。因而往往會存在一方當(dāng)事人利用自身經(jīng)濟(jì)或信息上優(yōu)勢,誘使、欺騙甚至強(qiáng)迫對方當(dāng)事人簽訂證據(jù)契約的情況,從而導(dǎo)致意思表示不真實(shí)。并且證據(jù)契約呈現(xiàn)法院面前時是以書面或口頭為表現(xiàn)形式的,很難從契約的形式或內(nèi)容本身去判斷證據(jù)契約是否為當(dāng)事人真實(shí)意思的表示。證據(jù)契約固有的缺陷,必然導(dǎo)致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出現(xiàn)以形式平等掩蓋實(shí)質(zhì)內(nèi)容不平等的情況,淪為強(qiáng)勢當(dāng)事人一方欺騙法院、不正當(dāng)影響訴訟程序和實(shí)現(xiàn)不法目的的工具的有效手段。這樣締結(jié)的證據(jù)契約背離了證據(jù)契約制度的初衷,可能妨礙案件公正審判。
3.證據(jù)契約系當(dāng)事人主義下的雙方法律行為,為訴訟欺詐提供可能。當(dāng)事人主義要求法院裁判所依賴的證據(jù)資料只能來源于當(dāng)事人,作為法院判斷的對象的主張來源于當(dāng)事人,法院不能在當(dāng)事人指明的證據(jù)范圍以外主動收集證據(jù)。證據(jù)契約在是當(dāng)事人主義下的雙方法律行為,法院必須尊重當(dāng)事人雙方的合意。法院對當(dāng)事人締結(jié)的證據(jù)契約考察的重點(diǎn)一般只是契約內(nèi)容中權(quán)利的可處分性問題,以及該合意處分行為是否系雙方真實(shí)之意思表示。對于后一點(diǎn),意圖串通的當(dāng)事人雙方自然不會主張其意思表示不真實(shí);而前者在大多情形下當(dāng)事人對契約內(nèi)容是有處分權(quán)的,其欺詐意圖難以為法院所察覺。這就為訴訟欺詐留下了缺口。如果說,“訴訟欺詐的發(fā)生,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辯論主義所要付出的代價”[30],那么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證據(jù)契約制度所要付出的代價。
(二)證據(jù)契約限制
一項(xiàng)美好的制度在某些方面的缺陷往往讓我們陷入兩難的境地。證據(jù)契約制度作為符合市場經(jīng)濟(jì)下意思自治原則的頗具浪漫主義色彩的事物,也同樣存在固有的缺陷。這本身的局限性使得對證據(jù)契約進(jìn)行適當(dāng)限制成為必需。從前文的分析來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實(shí)現(xiàn)對證據(jù)契約的限制。
1.通過立法限制證據(jù)契約的適用范圍,以避免證據(jù)契約適用的泛化。立法應(yīng)當(dāng)從社會公共利益出發(fā),妥善協(xié)調(diào)民事訴訟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公法性與證據(jù)契約的關(guān)系,證據(jù)法的“兩棲性”應(yīng)當(dāng)為證據(jù)契約留下締約空間,把個人可以自由處分的權(quán)利――包括程序權(quán)利和實(shí)體權(quán)利賦予當(dāng)事人,努力平衡當(dāng)事人訴訟權(quán)利與國家公共利益之間的關(guān)系。因此,在完善我國民事訴訟當(dāng)事人訴訟權(quán)利體系的過程,證據(jù)契約的適用范圍應(yīng)當(dāng)被限定在當(dāng)事人權(quán)利體系內(nèi)容之中,并隨著該權(quán)利體系的變化而做出調(diào)整。
2.對于證據(jù)契約可能被強(qiáng)勢一方當(dāng)事人所利用的情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對證據(jù)契約進(jìn)行規(guī)制。一方面,借鑒私法契約救濟(jì)的規(guī)定,賦予弱勢一方當(dāng)事人以請求救濟(jì)的權(quán)利,同時對證據(jù)契約的意思瑕疵進(jìn)行救濟(jì)。這主要通過當(dāng)事人向法院請求確認(rèn)己方受脅迫締結(jié)的證據(jù)契約無效,或請求法院撤銷、變更在欺詐情形下所訂立的證據(jù)契約。在締約過程中意思表示有瑕疵的證據(jù)契約,也應(yīng)當(dāng)賦予當(dāng)事人請求救濟(jì)的權(quán)利,如允許自認(rèn)契約的一方當(dāng)事人撤回契約中約定的不真實(shí)且存在重大誤解的自認(rèn)。但救濟(jì)需要滿足三個條件:第一,需由當(dāng)事人提出申請并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這樣可以減少和防止當(dāng)事人濫用救濟(jì)權(quán)利;第二,應(yīng)當(dāng)在合理期限內(nèi)提出,以免拖延訴訟和危及程序安定;第三,提出救濟(jì)申請的當(dāng)事人一方不存在過錯。另一方面,法官要行使釋明權(quán)[31],主動審查證據(jù)契約的內(nèi)容是否公平合法。現(xiàn)代的訴訟程序復(fù)雜冗長,沒有經(jīng)過專業(yè)訓(xùn)練的一般當(dāng)事人難以勝任訴訟,盡管存在律師幫助,當(dāng)事人也并不一定能夠完全理解證據(jù)契約后果。因此,通過法官行使釋明權(quán),將證據(jù)契約的內(nèi)容和其所將要引發(fā)的法律后果向當(dāng)事人予以說明,協(xié)助當(dāng)事人雙方實(shí)現(xiàn)平等溝通與對話,使雙方當(dāng)事人信息得以對稱,并使弱勢一方有機(jī)會與對方進(jìn)一步協(xié)商以變更或解除證據(jù)契約所確定之內(nèi)容。
3.針對證據(jù)契約帶來訴訟欺詐的可能,一方面應(yīng)當(dāng)適當(dāng)強(qiáng)化法院的監(jiān)督職能,在一定范圍內(nèi)對當(dāng)事人的處分權(quán)進(jìn)行限制,尤其是對涉及公益性很強(qiáng)的訴訟案件,法院應(yīng)該依職權(quán)收集證據(jù),徹底查清訴訟案件的事實(shí)。另一方面應(yīng)賦予受詐害人一定的救濟(jì)權(quán)。通過證據(jù)契約達(dá)到訴訟欺詐的目的后,其后果往往是對第三人造成損害,但這種損害在訴訟結(jié)束前可能不會表現(xiàn)出來。因此第三人應(yīng)當(dāng)?shù)玫骄驮撟C據(jù)契約向法院提出異議、申請變更或撤銷的權(quán)利,以維護(hù)自身合法權(quán)益,如果訴訟已經(jīng)結(jié)束的,第三人有權(quán)利據(jù)此對串通的雙方當(dāng)事人提起民事訴訟。也有學(xué)者建議設(shè)立訴訟通報(bào)制度來防范訴訟欺詐。[32]
對證據(jù)契約進(jìn)行適當(dāng)限制,并不破壞證據(jù)契約自由。相反,這更有利于保護(hù)證據(jù)契約自由,防止證據(jù)契約非當(dāng)化。
五、展望:證據(jù)契約在我國的前景
盡管我國沒有明文規(guī)定證據(jù)契約制度,但在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以下簡稱《規(guī)定》)中證據(jù)契約中的相當(dāng)一部分內(nèi)容已經(jīng)得到承認(rèn)。如舉證期限契約[33]、選擇鑒定契約[34]、證據(jù)交換契約[35]、自認(rèn)契約[36]等。但這些規(guī)定的“契約”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證據(jù)契約,受到法院的過多干預(yù),如雙方當(dāng)事人對舉證期限的約定必須“經(jīng)人民法院認(rèn)可”但什么情況認(rèn)可什么情況不認(rèn)可又缺乏相關(guān)規(guī)定,隨意性太強(qiáng)。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證據(jù)契約”。
證據(jù)契約體現(xiàn)當(dāng)事人的程序主體地位,是私法自治在公法領(lǐng)域的延伸,同時又可以彰顯程序公正,促進(jìn)實(shí)體公正,還可以節(jié)約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這些優(yōu)點(diǎn)于當(dāng)事人于法院,無疑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再加上證據(jù)契約符合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下的自由、平等、理性、功利的理念,是否在我國建立證據(jù)契約制度可以說是我國的法律是否適應(yīng)社會發(fā)展的內(nèi)在規(guī)律、是否能夠跟上時代的步伐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之一。但盲目移植所謂先進(jìn)、符合時代步伐的法律制度無疑是危險(xiǎn)的,任何一種先進(jìn)法律制度脫離了它賴以生存的制度基礎(chǔ)就成了落后的法律制度,正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因此,如果我們不具備證據(jù)制度所賴以發(fā)展的制度環(huán)境基礎(chǔ),移植過來也會造成“水土不服”。那么分析我國相關(guān)制度環(huán)境,看我國是否適合建立證據(jù)契約制度就很有必要了。
(一)本土條件分析
1.公民權(quán)利觀念淡薄
權(quán)利觀念是指特定的社會成員對權(quán)利的認(rèn)知、主張和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民的權(quán)利觀念有所提高,公民的權(quán)利意識大大增強(qiáng)了。但就整體來看,我國公民的權(quán)利觀念仍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現(xiàn)代法治建設(shè)進(jìn)程的要求,制約著我國法治化的進(jìn)程。這突出表現(xiàn)為:[37](1)權(quán)力至上。公民習(xí)慣于服從權(quán)力,而不習(xí)慣、甚至不敢用法律來維護(hù)自己的利益。(2)重情義、輕權(quán)利。幾千年來,人們習(xí)慣于用情感、倫理、道德來調(diào)節(jié)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對于通過法律來調(diào)節(jié)人際關(guān)系的做法不屑一顧。人們憧憬“和諧”,講求“仁愛”,反映到法律領(lǐng)域就是“無訟”的心態(tài)。孔子曰:“聽訟,合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38]即爭訟是社會的一種惡和不道德行為,無訟的社會才是理想中的和平世界。盡管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jīng)不再把打官事看作不光彩的事情,但“情為上”、“和為貴”的“無訟”傳統(tǒng)觀念仍然具有一定影響。(3)對于權(quán)利,沒有主動追求,只知被動承受。在西方的歷史上,人們根據(jù)利益和意志自由的需要,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例如在美國,有以要求黑人權(quán)利為特征的“民權(quán)運(yùn)動”,有婦女要求權(quán)利的“女權(quán)運(yùn)動”,這些要求得到政府法律認(rèn)可,便成為一種法定權(quán)利,自然權(quán)利變成法定權(quán)利往往是人們主動要求的結(jié)果。但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鑒于期間無視權(quán)利踐踏權(quán)利的痛苦經(jīng)歷,人們曾經(jīng)呼喚民主和法制,這些呼喚固然對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shè)起到了推動作用,但人們始終沒有形成主動追求權(quán)利的習(xí)慣。形成權(quán)利觀念淡薄的原因有多方面,如民眾素質(zhì)不高,法律文化意識缺乏;也因?yàn)槭堋盁o訟”傳統(tǒng)影響至深;還因?yàn)殚L期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下經(jīng)濟(jì)主體的一元化限制了權(quán)利觀念的成長。
證據(jù)契約是當(dāng)事人對自己的權(quán)益作出理性和積極選擇的表現(xiàn),需要雙方當(dāng)事人的積極參與與處分,而公民權(quán)利觀念的淡薄與“厭訟”的心態(tài)自然是和證據(jù)契約的理念、制度格格不入的。因此,提高公民權(quán)利觀念成了建立證據(jù)契約制度的必要前提。
2.職權(quán)主義訴訟模式
我國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試行)相比有一個比較顯著特點(diǎn),即民事訴訟程序中法院職權(quán)干預(yù)的弱化以及相應(yīng)的當(dāng)事人處分權(quán)的強(qiáng)化。但“從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角度看,現(xiàn)行民事訴訟體制依然屬于職權(quán)主義類型。”[39]具體表現(xiàn)在:第一,各具體的訴訟程序的開始、進(jìn)行和終結(jié),法院具有主動性和決定性。當(dāng)事人雖然是平等的訴訟主體,但實(shí)際上他們在訴訟中的能動作用受到很大遏制,很多重要程序如保全程序、執(zhí)行程序的啟動與否仍可由法院決定,法院可以在當(dāng)事人沒有申請的情況下啟動這些程序。
第二,法院可以在當(dāng)事人負(fù)舉證責(zé)任的同時,依職權(quán)積極主動地收集證據(jù),并將此作為認(rèn)定案件事實(shí)的根據(jù)。盡管新民訴法已將試行民訴法中規(guī)定的“全面、客觀地懼和調(diào)查證據(jù)”,改為“全面客觀地審查核實(shí)證據(jù)”,但同時又規(guī)定“法院認(rèn)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jù),法院應(yīng)當(dāng)調(diào)查收集”,為法院獨(dú)立收集證據(jù)留下了自由裁量權(quán)。[40]法院在作裁判時,往往對當(dāng)事人依舉證責(zé)任提供的證據(jù)不予考慮,而完全將自己獨(dú)立收集來的證據(jù)作為裁判的根據(jù),表現(xiàn)出明顯的職權(quán)干預(yù)性。
第三,法官主宰整個庭審進(jìn)程,當(dāng)事人處在消極、被動的地位。在法庭審判中,法官控制、指揮訴訟,當(dāng)事人彼此間的對抗作用受到很大的遏制。法官甚至可以打斷當(dāng)事人辯論。
由此可見,我國的民事訴訟屬于職權(quán)主義訴訟模式。在此模式下,就不存在體現(xiàn)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核心的“約束性”辯論主義原則與處分原則。盡管我國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了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但與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下的辯論主義與處分原則相去甚遠(yuǎn)。現(xiàn)行法所規(guī)定的辯論原則僅僅是肯定了使人“有辯論的權(quán)利”,但這種辯論權(quán)的行使不會帶來任何法律上的制約效果,以至于辯論原則實(shí)際上成為一種非約束性或非實(shí)質(zhì)性原則,因此有學(xué)者將這種形式上的辯論原則稱為“非約束性辯論原則”[41]。同樣,我國民事訴訟法雖然規(guī)定了當(dāng)事人“有權(quán)”處分自己的民事權(quán)利和訴訟權(quán)利,但卻沒有規(guī)定相應(yīng)的法律后果,因而其處分行為對人民法院往往并沒有約束力,人民法院完全可以置其于不顧并基于其他各種理由而對案件作出處理,相比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下的處分原則,我們的處分原則可以稱之為“非約束性處分原則”。[42]
這就成為建立證據(jù)契約制度的基礎(chǔ)。我們在職權(quán)主義訴訟模式下不僅無法移植證據(jù)契約制度,連目前已經(jīng)具有的類似于證據(jù)契約的相關(guān)規(guī)定也難以貫徹實(shí)施。最典型的即為在最高人民法院若干司法解釋里規(guī)定的自認(rèn)制度,筆者認(rèn)為顯然是不符合我國的職權(quán)主義訴訟模式的。自認(rèn)制度建立的基礎(chǔ)是約束性辯論主義原則,是法院對案件事實(shí)的非職權(quán)探知,而我國職權(quán)主義訴訟模式顯然不符合自認(rèn)制度所要求的體制環(huán)境。同理,在沒有完全實(shí)現(xiàn)模式轉(zhuǎn)換之前,將證據(jù)契約制度移植到我國便會“水土不服”,在實(shí)踐中無法正常運(yùn)行,成為好看不好用的“擺設(shè)”。
(二)時展的要求:兩個基本作業(yè)
如上所述,我國現(xiàn)有的條件是不符合證據(jù)契約制度需求的。證據(jù)契約的實(shí)現(xiàn)需要訴訟主體在權(quán)利觀念的驅(qū)使下積極參與與處分,我國公民權(quán)利觀念淡薄成為建立證據(jù)契約制度的首要障礙。同時證據(jù)契約制度與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具有深刻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而我國是職權(quán)主義訴訟模式,使得證據(jù)契約制度建立缺乏體制基礎(chǔ)。因此,如果要在我國建立證據(jù)契約制度,至少必須完成兩個基本作業(yè):
第一,加大法治宣傳與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質(zhì),加強(qiáng)公民權(quán)利觀念。民眾的權(quán)利觀念對證據(jù)契約制度的實(shí)現(xiàn)具有重要意義。在證據(jù)契約制度中,當(dāng)事人是程序主體,當(dāng)事人的這種程序主體意識推動著其對訴訟程序的積極參與,并在訴訟過程中積極處分自己的訴訟權(quán)利,在恰當(dāng)?shù)臅r候締結(jié)證據(jù)契約。而程序主體意識來源于權(quán)利觀念的形成與加強(qiáng),權(quán)利觀念不僅包括法定權(quán)利觀念還包括應(yīng)有權(quán)利觀念。前者是指公民能夠充分認(rèn)識并維護(hù)自己享有的法定權(quán)利,后者是公民依據(jù)現(xiàn)存的社會物質(zhì)生活條件而產(chǎn)生的,但尚未為法律所確定的權(quán)利的觀念要求,并能夠在訴訟中得到滿足的權(quán)利觀念。然而,受我國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民利觀念先天不足。因此,加大法治宣傳教育力度,加強(qiáng)公民權(quán)利觀念是證據(jù)契約得以實(shí)現(xiàn)的前提。契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權(quán)利觀念的反應(yīng),權(quán)利觀念是證據(jù)契約得以構(gòu)建的文化基礎(chǔ)與心理基礎(chǔ)。證據(jù)契約的實(shí)現(xiàn)離不開訴訟主體權(quán)利觀念的驅(qū)動,權(quán)利觀念越強(qiáng),驅(qū)動越大,權(quán)利觀念越弱,驅(qū)動越小。但權(quán)利觀念的驅(qū)動功能又要受到多方面限制,如公民思想、道德及文化素質(zhì)不高,就會妨礙程序主體意識的形成,從而公民權(quán)利觀念對證據(jù)契約的驅(qū)動功能就會削弱,證據(jù)契約的實(shí)現(xiàn)就會受到制約。因此提高權(quán)利觀念的前提是必須提高公民素質(zhì),使全體公民正確認(rèn)識個人與社會、社會與國家的辯證關(guān)系,從而加強(qiáng)公民正確的權(quán)利觀念,在訴訟中確立理性價值追求與選擇,實(shí)現(xiàn)個人、國家和社會利益的平衡。
可見,在推進(jìn)證據(jù)契約的過程中,必須加大法治宣傳與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質(zhì),克服傳統(tǒng)思想,使公民樹立牢固的權(quán)利觀念、權(quán)利本位意識和自由平等精神,進(jìn)而形成體現(xiàn)自由、平等、選擇與理性正義價值觀,提高公民參訴意識與能力,使公民真正成為程序的主體,能充分理解并運(yùn)用證據(jù)契約這一有效手段解決糾紛維護(hù)權(quán)益。
第二,轉(zhuǎn)換民事訴訟模式。在我國,民事訴訟職權(quán)主義訴訟模式的缺陷越來越為學(xué)者所批判,不少學(xué)者都意識到,無論是從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建立適應(yīng)市場經(jīng)濟(jì)發(fā)展需要的民事訴訟機(jī)制方面看,還是從立法、理論上完善我國民事訴訟制度方面看,民事訴訟模式的轉(zhuǎn)換或調(diào)整都勢在必行。但在選擇適用何種訴訟模式上則存在爭議。有“激進(jìn)”的,認(rèn)為應(yīng)該對我國民事訴訟結(jié)構(gòu)進(jìn)行全方位的改革,直接引入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也有稍微不那么“激進(jìn)”但也前衛(wèi)的建議在我國建立亞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還有“保守”的學(xué)者認(rèn)為引進(jìn)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不符合我國國情,對訴訟模式的改革只能在原有基礎(chǔ)上進(jìn)行微調(diào)。筆者認(rèn)為,民事訴訟模式的問題是個基本問題,不僅是制約證據(jù)契約制度能否實(shí)現(xiàn)的關(guān)鍵,更是關(guān)系到證據(jù)制度改革、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等若干重大理論與實(shí)踐問題。從理論上探討民事訴訟模式問題,并結(jié)合證據(jù)契約作出正確選擇,是基本作業(yè)的要求。
主張轉(zhuǎn)換民事訴訟模式必然要涉及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要轉(zhuǎn)換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于現(xiàn)有的職權(quán)主義訴訟模式本身。這一模式的弊端在實(shí)踐中已經(jīng)充分顯現(xiàn)。在職權(quán)主義訴訟模式下裁判者可以依職權(quán)獨(dú)立收集和提出證據(jù),而不受當(dāng)事人主張范圍的限制,使當(dāng)事人的辯論流于形式,造成“辯論原則”“空洞化”。職權(quán)主義模式還使民事訴訟這一解決平等主體間爭議的性質(zhì)不相適應(yīng)。平等的落腳點(diǎn)在于當(dāng)事人的意思自治,民事訴訟作為解決平等主體之間糾紛的一種方式,理應(yīng)保障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但職權(quán)探知對當(dāng)事人處分權(quán)的過多干預(yù)使當(dāng)事人的意思自治權(quán)利喪失殆盡。辯論主義與處分權(quán)的“非約束性”,又反過來造成職權(quán)主義訴訟程序裁判者不中立,挫傷當(dāng)事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使當(dāng)事人在訴訟中淪為客體,顯然這樣的程序難以正義。而這都是與證據(jù)契約制度琴瑟不合,證據(jù)契約制度難以在職權(quán)主義模式下建立起來。因此,筆者建議應(yīng)當(dāng)選擇建立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因?yàn)閺淖C據(jù)契約的角度出發(fā):
首先,證據(jù)契約要求法官對當(dāng)事人訴訟權(quán)利包括處分權(quán)與辯論權(quán)的尊重與約束,這個要求只有在當(dāng)事人主義模式下才能實(shí)現(xiàn)。在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下,自由表達(dá)自己的思想與觀念,自由處分合法權(quán)利,使雙方當(dāng)事人在對抗中推動訴訟向前發(fā)展,能夠在對抗中尋求契合并約束法官。當(dāng)事人在此模式下的程序主體地位更加彰顯,雙方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也被充分調(diào)動起來。這與證據(jù)契約制度要求的當(dāng)事人具有充分主觀能動性一致。同時當(dāng)事人主義下的約束性辯論原則與處分原則使證據(jù)契約的建立才具有意義。
其次,證據(jù)契約反映的私權(quán)自治精神要求樹立起當(dāng)事人平等、當(dāng)事人主體地位的理念,這也是與當(dāng)事人主義一致。在職權(quán)主義下法官主導(dǎo)訴訟程序,而當(dāng)事人則處于被動和相對消極的地位。這與程序主體性原理相悖。而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下,雙方當(dāng)事人是訴訟的主角,程序的控制權(quán)在于當(dāng)事人,當(dāng)事人在程序中能夠積極充分地參與程序,程序的發(fā)生、變更、消滅以及證據(jù)的提供等均由雙方當(dāng)事人主動進(jìn)行,法官中立并不偏袒任何一方當(dāng)事人。這樣的訴訟程序?qū)Ξ?dāng)事人來說顯得更具有民主性,這也符合證據(jù)契約內(nèi)在的意思自治理念。
但需要說明的是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實(shí)際上還分為英美式的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和大陸式的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考慮到證據(jù)契約與法官職權(quán)有緊密聯(lián)系,即證據(jù)契約還需要發(fā)揮法官的職權(quán)作用,由法官行使釋明權(quán),以及主動審查證據(jù)契約的合法性,防止證據(jù)契約非正當(dāng)化,因此筆者主張建立大陸式的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但筆者主張建立證據(jù)契約制度并非片面主張?jiān)V訟程序的進(jìn)行完全由當(dāng)事人主導(dǎo)而使我國民事訴訟模式投向古典程序自由主義的懷抱,[43]因而筆者建議選擇大陸式的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這一方面是因?yàn)槲覈袷略V訟體制從形式結(jié)構(gòu)上與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有源緣關(guān)系,而且我國現(xiàn)行的法律術(shù)語、理論規(guī)范與大陸法系更為親近,而且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對一國的文化形態(tài)也有要求,大陸式的當(dāng)事人主義訴訟模式更適合我國的文化形態(tài),對我國無根本性排斥。[44]英美式的當(dāng)事人主義可能更關(guān)注程序正義,大陸式的當(dāng)事人主義下法官職權(quán)的適當(dāng)運(yùn)用使得在追求程序正義時更有利于實(shí)體正義與效益。因此,選擇大陸式的當(dāng)事人主義,從而以這一模式為基點(diǎn)構(gòu)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相適應(yīng),與民事訴訟的特性相一致的訴訟模式,使我國民事訴訟體制成為具有充分實(shí)現(xiàn)程序正義與實(shí)體正義,凸現(xiàn)訴訟民主的訴訟制度,不僅可以在約束性辯論原則與處分原則下建立起真正的當(dāng)事人舉證責(zé)任制度,從而為證據(jù)契約制度的建立提供訴訟模式基礎(chǔ),還與證據(jù)契約中要求發(fā)揮法官作用相一致。
雖然從我們目前的條件來看我國還不適合建立證據(jù)契約制度,但這并不是說我們一點(diǎn)有利條件也沒有。如,“無訟”傳統(tǒng)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當(dāng)事人權(quán)利觀念的形成,但另一方面“無訟”觀念下“和為貴”的思想又存在有利于證據(jù)契約制度建立的方面。因?yàn)樽C據(jù)契約本身要求處于對抗的當(dāng)事人能夠心平氣和地談判,達(dá)成證據(jù)合意。而“和為貴”的思想無疑有利于當(dāng)事人從長遠(yuǎn)利益考慮,為免挫傷今后的長久關(guān)系而在訴訟中“得不償失”,使當(dāng)事人更愿意通過證據(jù)契約和和氣氣地協(xié)商達(dá)到證據(jù)上的合意,既有助于糾紛解決,又不至于挫傷今后長遠(yuǎn)利益,使當(dāng)事人在訴訟后仍能夠繼續(xù)較好地維持原有的關(guān)系。又如,職權(quán)主義訴訟模式并不適合建立證據(jù)契約制度,但我們可以利用原職權(quán)主義法官職權(quán)探知的特點(diǎn),在轉(zhuǎn)換訴訟模式時保留小部分的法官依職權(quán)探知的權(quán)利,通過法官對證據(jù)契約進(jìn)行主動審查,排除無效的證據(jù)契約,防止證據(jù)契約非正當(dāng)化。
六、余言
綜上所述,證據(jù)契約制度是私權(quán)自治原則在公法領(lǐng)域的延伸,有充分的存在依據(jù)。其反應(yīng)了市場經(jīng)濟(jì)下私權(quán)自治的內(nèi)在要求,滿足民事訴訟當(dāng)事人程序主體性的需要,迎合社會轉(zhuǎn)型推動民事訴訟體制轉(zhuǎn)型后的制度改革方向。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我國目前還不具備建立證據(jù)契約制度的條件,而證據(jù)契約制度的建立也需要其他領(lǐng)域或制度改革的配合才能實(shí)現(xiàn)。其中兩個基本作業(yè)即公民正確積極權(quán)利觀念的樹立與民事訴訟模式的轉(zhuǎn)換。筆者在此提出這兩個基本作業(yè)并非只是為了建立一個證據(jù)契約制度就對民事訴訟制度作出那么巨大的改革提議,而是這兩項(xiàng)基本作業(yè)本身就是時展的需要。如權(quán)利觀念的樹立,本身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的內(nèi)在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是充分發(fā)揮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基礎(chǔ)的社會經(jīng)濟(jì)形態(tài),在這種經(jīng)濟(jì)形態(tài)上所形成的法律價值體系必然以理性、公正和權(quán)利作為其基本精神要素。如果沒有社會主體的自由創(chuàng)造精神,沒有社會主體的現(xiàn)代平等意識,沒有理性自律精神和對利益的不懈追求,充滿生機(jī)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就無法建成。樹立正確積極的權(quán)利觀念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觀念前提,是依法治國的文化根基,是推動法治進(jìn)程必不可少的力量。為了建立證據(jù)契約制度而對民事訴訟模式“大動干戈”,定會讓人恥笑,但民事訴訟模式的根本性轉(zhuǎn)換不僅是建立證據(jù)契約制度的需要,更主要的是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的需要。市場經(jīng)濟(jì)下經(jīng)濟(jì)主體在經(jīng)濟(jì)交往中所具有的主體性和自主性要求建立當(dāng)事人主義的民事訴訟模式。
我國社會正處于大轉(zhuǎn)型時期,各項(xiàng)改革正高歌猛進(jìn),法制建設(shè)也處于重建和轉(zhuǎn)型之中。我們應(yīng)當(dāng)利用這一契機(jī),推進(jìn)民事訴訟制度改革,在將來建立證據(jù)契約制度。而證據(jù)契約理論在我國理論研究的空白,與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的建立和民事審判方式改革方向極不協(xié)調(diào)。加強(qiáng)證據(jù)契約理論研究,也是學(xué)者們應(yīng)盡的義務(wù)。
行文至此,拙文算告一段落。但其中的許多觀點(diǎn)尚不成熟,筆者有意求教于大方之家,懇請老師與朋友對拙文批評指正。
--------------------------------------------------------------------------------
[①]本文所指的證據(jù)契約如無特別說明,皆指民事訴訟中的證據(jù)契約。因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公法色彩比民事訴訟來得更濃一些,本文暫不對他們進(jìn)行討論,又以證據(jù)契約代替民事證據(jù)契約可方便討論。
[②]訴訟契約在德、日及我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qū)同樣研究得比較多,我國大陸學(xué)者研究的比較少些。但近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已經(jīng)有不少學(xué)者對公法上的契約開始感興趣了。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陳桂明教授:《訴訟契約》,收錄在其專著《程序理念與程序規(guī)則》,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10月版;張衛(wèi)平教授:《論民事訴訟的契約化》,載《中國法學(xué)》,2004年第3期;于立深教授:《公法行為契約化》,載《法學(xué)理論前沿論壇第二卷》(文集),2003年11月版。
[③]參見陳桂明:《程序理念與程序規(guī)則》,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頁。
[④]前引陳桂明:《程序理念與程序規(guī)則》,第93頁。
[⑤]李永軍:《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⑥]前引陳桂明:《程序理念與程序規(guī)則》,第97頁。
[⑦][奧]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
[⑧]Rosenberg認(rèn)為,舉證責(zé)任契約系指當(dāng)事人以法律行為規(guī)定舉證責(zé)任之分配,而證據(jù)契約則系指意欲藉以限制法官自由證據(jù)評價之契約。參見[臺]姜世明:《證據(jù)契約之研究》,載(臺)《軍法專刊》,第四十七卷第八期,2001年8月號,第8~20頁。
[⑨]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訴訟法》,白綠鉉譯,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頁。
[⑩]參見[臺]邱聯(lián)恭:《程序選擇權(quán)之法理》,載《民事訴訟法之研討(四)》,三民書局1993年第579頁。轉(zhuǎn)引自劉學(xué)在:《我國民事訴訟處分原則之檢討》,載《法學(xué)評論》,2000年第6期。
[11][美]R·麥克尼爾:《新社會契約論》,雷喜寧、潘勤譯,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
[12]參見王利明:《審判方式改革中的民事證據(jù)立法問題探討》,載王利明等主編、湯維建執(zhí)行主編《中國民事證據(jù)立法研究與應(yīng)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0~13頁。葡萄牙、澳門、魁北克等地便是將民事證據(jù)法置于民法典總則中。
[13][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義與訴訟》,王亞新譯,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頁。
[14]張衛(wèi)平:《民事訴訟處分原則重述》,載《現(xiàn)代法學(xué)》,2003年第6期。
[15]筆者贊同張衛(wèi)平教授將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模式歸入同一類別――當(dāng)事人主義的觀點(diǎn),因?yàn)閮纱蠓ㄏ档拿袷略V訟體制完全符合當(dāng)事人主義的特征。盡管兩種程序之間有很大的差別,法官在訴訟中的職權(quán)和當(dāng)事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也不盡相同,但兩大民事訴訟體制在法院(法官)或陪審團(tuán)裁決所依據(jù)的訴訟資料是由當(dāng)事人提出,判斷者必須受當(dāng)事人主張的約束這一點(diǎn)上是完全相同的,即兩大法系奉行辯論主義和處分主義原則。參見張衛(wèi)平:《轉(zhuǎn)換的邏輯――民事訴訟體制轉(zhuǎn)型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1頁。
[16]尹田:《法國現(xiàn)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頁。
[17]轉(zhuǎn)引自尹田:《法國現(xiàn)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頁。
[18]參見沈達(dá)明:《英美證據(jù)法》,中信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
[19][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xué)》,吳壽彭譯,商務(wù)印書館1965年版,第168頁。
[20]參見[臺]姜世明:《證據(jù)契約之研究》,載(臺)《軍法專刊》,第四十七卷第八期,2001年8月號,第8~20頁。
[21]前引陳桂明:《程序理念與程序規(guī)則》,第98~100頁。
[22]參見[臺]陳計(jì)男:《民事訴訟法論》(上),三民書局1999年,第445頁。
[23][臺]王甲乙、楊建華、鄭健才:《民事訴訟法新論》,三民書局1999年,第341頁。
[24]參見王利明、房紹坤、王軼著:《合同法》,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頁。
[25]前引陳桂明:《程序理念與程序規(guī)則》,第102頁。
[26]此節(jié)寫作結(jié)構(gòu)參考了中國政法大學(xué)2005屆訴訟法學(xué)碩士畢業(yè)生劉新波的碩士學(xué)位論文,特此致謝。參見劉新波:《試論民事訴訟契約》,中國政法大學(xué)研究生院,2005年4月。來源:中國期刊網(wǎng)“全國優(yōu)秀碩博論文庫”。
[27]李永軍:《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頁。
[28][臺]陳計(jì)男:《民事訴訟法論》(上),三民書局1994年,第412頁。
[29][英]阿蒂亞:《合同法概論》,程康正等譯,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8頁。轉(zhuǎn)引自李永軍:《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頁。
[30]前引陳桂明:《程序理念與程序規(guī)則》,第122頁。
[31]釋明權(quán)是法官為澄清爭端和公正裁判而詢問當(dāng)事人及向當(dāng)事人提出建議的權(quán)限。參見楊克彬:《法官如何行使釋明權(quán)》,載《人民法院報(bào)》,1998年4月18日。
[32]參見前引陳桂明:《程序理念與程序規(guī)則》,第132頁。
[33]《規(guī)定》第三十三條第二款:“舉證期限可以由當(dāng)事人協(xié)商一致,并經(jīng)人民法院認(rèn)可。”
[34]《規(guī)定》第二十六條:“當(dāng)事人申請鑒定經(jīng)人民法院同意后,由雙方當(dāng)事人協(xié)商確定有鑒定資格的鑒定機(jī)構(gòu)、鑒定人員,協(xié)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35]《規(guī)定》第三十七條第一款:“經(jīng)當(dāng)事人申請,人民法院可以組織當(dāng)事人在開庭審理前交換證據(jù)。”第三十八條:“交換證據(jù)的時間可以由當(dāng)事人協(xié)商一致并經(jīng)人民法院認(rèn)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
[36]《規(guī)定》第七十二條:“一方當(dāng)事人提出的證據(jù),另一方當(dāng)事人認(rèn)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證據(jù)不足以反駁的,人民法院可以確認(rèn)其證明力。”
[37]參見張學(xué)亮:《依法治國與公民權(quán)利觀念》,載《理論導(dǎo)刊》,2002年第4期[38]《論語·顏淵》
[39]張衛(wèi)平:《民事訴訟基本模式:轉(zhuǎn)換與選擇之根據(jù)》,載《民事程序法論文選萃》,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頁。
[40]試行《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guī)定:“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收集和調(diào)查證據(jù)。”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guī)定:“人民法院認(rèn)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jù),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調(diào)查收集。”第三款規(guī)定:“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審查核實(shí)證據(jù)。”
[41]張衛(wèi)平:《我國民事訴訟辯論原則重述》,載《法學(xué)研究》,1996年第6期。
[42]參見劉學(xué)在:《我國民事訴訟處分原則之檢討》,載《法學(xué)評論》,2000年第6期。
第2篇:證據(jù)法論文范文
【關(guān)鍵詞】:效力依據(jù)強(qiáng)制力共同意志
【正文】
一、國際法的概念與產(chǎn)生
國際法隨著國際關(guān)系的形成與發(fā)展而產(chǎn)生。一般的概念上,國際法是指國家之間的“法”,國際社會上國家的存在是國際法產(chǎn)生的前提,在國際社會行為主體之間產(chǎn)生了范圍廣泛、內(nèi)容深刻的聯(lián)系與關(guān)系,為了調(diào)整這些關(guān)系,國際社會行為主體才在交往的實(shí)踐中以“共同意志為基礎(chǔ)、協(xié)商為方式”產(chǎn)生了一系列調(diào)整這些關(guān)系的有約束力的原則、規(guī)則和制度。
國際法在更大程度上是以國際社會為基礎(chǔ),而國際社會與一般我們所稱的社會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國”成為了國際社會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交往主體。除了國家這一必不可少的主體要件外,“際”,即國家之間的相互交往同樣是促使國際社會形成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由此可知,國際法的產(chǎn)生必須滿足兩個條件:(1)若干國家同時存在;(2)這些國家進(jìn)行交往與協(xié)作而形成各種國際關(guān)系。簡言之,就是必須有國、有際。
從國際法的概念當(dāng)中我們已經(jīng)認(rèn)識到:國際法是調(diào)整、規(guī)范國際行為主體之相互行為。國際行為主體之間的行為根源于全球資源的有限性與對利益最大化追求之間的矛盾,換句話說國際行為主體之間相互交往的行為是實(shí)現(xiàn)在全球范圍內(nèi)優(yōu)化資源配置的選擇,因?yàn)殡S著科學(xué)技術(shù)與社會財(cái)富的增加,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地域的限制使得人類不得不尋求更廣泛的空間來發(fā)展自己的實(shí)力,在此過程中"國家利益"表現(xiàn)出極強(qiáng)的意識控制力,每個國家為了自我利益的保護(hù)與爭奪使得國際社會矛盾交結(jié),戰(zhàn)爭等暴力、不公正的“國與國交往方式”終因矛盾的激化而展開,帶來的不僅僅是社會財(cái)富的嚴(yán)重破壞更嚴(yán)重的是帶來了國際社會的無續(xù),國際社會的無續(xù)就使得國際行為主體之間的交往缺乏和平、穩(wěn)定的環(huán)境,甚至“國國自危”。例如20世紀(jì)的兩次人類世界大戰(zhàn)使得人類從血與淚中理解到國際社會有續(xù)的重要性,認(rèn)識到國際法的重要作用。國際法公正、平等等一系列原則與規(guī)范在人類不斷發(fā)展的理性當(dāng)中得到強(qiáng)化,逐漸為世界普遍接受。
二、國際法的效力依據(jù)
國際法的效力依據(jù)是指國際法具有法律拘束力或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據(jù),即國際法依據(jù)什么對國際行為主體具有約束的效力。按照上述中,國際法的形成是各國協(xié)議、共同同意的結(jié)果,無論是以條約或習(xí)慣還是其他協(xié)議都表現(xiàn)了國家的意志協(xié)調(diào),也可以說的國家的同意。下面我以國內(nèi)法與國際法的比較來試分析國際法的效力依據(jù),這樣的分析基于國家是國際社會的最主要組成因素、國內(nèi)法的效力依據(jù)從未受到質(zhì)疑以及“法”在國內(nèi)法體系與國際法體系的共同點(diǎn):強(qiáng)制,以及國際法與國內(nèi)法均具有法律約束力。
(一)國內(nèi)法的效力依據(jù)
1.法的概念
對于法的產(chǎn)生與出現(xiàn)按照一般的傳統(tǒng)理論可以理解為:法的本質(zhì)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勢力依靠公共強(qiáng)制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到必須,將其定義為“由國家制定或認(rèn)可,體現(xiàn)統(tǒng)治階級意志,以國家強(qiáng)制力保證實(shí)施的行為規(guī)則(規(guī)范)的總和。”但是隨著商品經(jīng)濟(jì)已經(jīng)在全球范圍內(nèi)得到肯定與認(rèn)可,商品經(jīng)濟(jì)的繁榮帶來的是人類對自身經(jīng)濟(jì)利益(既得、欲得)的意識增強(qiáng),維護(hù)自身利益的有效武器——法律,所以在現(xiàn)代對法律的定義更應(yīng)該注重法律在社會領(lǐng)域內(nèi)所起到的作用,即社會性。這樣的定義與傳統(tǒng)對法的定義最大的區(qū)別與進(jìn)步在于:前者體現(xiàn)意志的社會群體得到了補(bǔ)充。
“法”,目前在世界上仍然主要是依靠國家制定與認(rèn)可而產(chǎn)生,并且以“國家”為保障進(jìn)行實(shí)施執(zhí)行,社會管理模式仍以國家行政管理為中心,法律的社會性仍以國家行政執(zhí)法機(jī)關(guān)為載體因而“國家意志性”與“強(qiáng)制性”仍然是法的主要特征。
2.國內(nèi)法的特征
(1)法由公共權(quán)力(國家)制定或認(rèn)可,具有國家意志性
法的產(chǎn)生是人類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chǎn)物,法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永恒不滅。法首先是作為一種客觀現(xiàn)實(shí)存在于人類社會,同時也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反映方式與現(xiàn)象之一。法由公共權(quán)力機(jī)構(gòu)制定或認(rèn)可,人類社會發(fā)展至今國家是公共權(quán)力的中心,所以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rèn)可。國家制定法律是指有權(quán)制定法律的國家機(jī)關(guān)制定的規(guī)范性文件即成文法。就現(xiàn)代國家而言,它包括國家最高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或立法機(jī)關(guān)制定法律或重大議案,國家最高行政機(jī)關(guān)制定行政法規(guī)。國家認(rèn)可法律是指國家根據(jù)需要賦予某些習(xí)慣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使之成為法律。
從法律的出臺與制定看,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認(rèn)可,具有國家意志性。制定或認(rèn)可法律是創(chuàng)立法律的兩種方式,也是法律區(qū)別于其他社會規(guī)范的重要標(biāo)志。法律由國家制定或認(rèn)可,表明它以國家的名義對人們行為進(jìn)行規(guī)范和要求,體現(xiàn)的是國家意志。同時法律的國家意志性表明它與表現(xiàn)統(tǒng)治階級意志的社會規(guī)范,如道德規(guī)范、宗教規(guī)范等等的區(qū)別,后者不具有國家意志的屬性。
(2)強(qiáng)制性及其實(shí)施保障
“強(qiáng)制性”是指壓制或強(qiáng)迫的力量。一般來說,任何社會規(guī)范均具有有一定的約束力,但是各自的性質(zhì)、范圍和方式等都不相同,如政治組織或社會團(tuán)體的規(guī)則、章程是由該組織的紀(jì)律來保證實(shí)施的;道德規(guī)范是由社會輿論、人們內(nèi)心的信念和教育的力量來維護(hù)的,違反道德一般都會受到輿論的譴責(zé)。法律作為特殊的社會規(guī)范,與一般的社會行為規(guī)范的最本質(zhì)區(qū)別在于:法律的國家意志性,進(jìn)而引起的約束效力強(qiáng)弱(效果)的不同。
法律的國家意志性決定了法律必須由國家強(qiáng)制力保證實(shí)施,法所體現(xiàn)的國家意志具有高度的統(tǒng)一性、強(qiáng)大的權(quán)威性、一定的公共性之屬性。強(qiáng)制性在國內(nèi)法表現(xiàn)為通過國家執(zhí)法機(jī)關(guān)的執(zhí)法活動,對違反行為的制裁或者強(qiáng)制履行法定義務(wù)。這種強(qiáng)制不是只適用于少數(shù)人或者個別情況,而是其效力范圍內(nèi)具有普遍約束力,強(qiáng)調(diào)任何人不得違反并且以國家之政權(quán)、軍隊(duì)、警察以及監(jiān)獄等一系列國家強(qiáng)制載行機(jī)構(gòu)(國家機(jī)器)的執(zhí)行活動為保障與后盾。
(二)國際法的效力依據(jù)現(xiàn)狀
國際法是法律的一個特殊體系,是國家在國際交往中應(yīng)遵守的行為規(guī)范。有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國際法不是法律,而是抽象的自然法則,是國際道德或國際禮讓,是一種道義的力量。其實(shí),國際法作為法律,已經(jīng)為世界各國所承認(rèn)和普遍遵守,違反國際法只是少數(shù)的例外,且要承擔(dān)法律責(zé)任,接受法律制裁,國際法并不因?yàn)橛羞`法行為的存在而失去其法律性質(zhì)。當(dāng)然,國際法與國內(nèi)法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決定了國際法的調(diào)整對象、法律淵源等方面有不同于國內(nèi)法的重要特征。
1.國際法主體主要是國家
國際法主體,是指具有獨(dú)立參與國際法律關(guān)系的能力,在國際法上直接享受權(quán)利或承擔(dān)義務(wù)的當(dāng)事者或人格者,其范圍主要包括國家、國際組織以及爭取獨(dú)立的民族。國家因其在國際關(guān)系中的主導(dǎo)地位和主要作用(或因國際法的性質(zhì)和國家所具有特殊的政治與法律屬性)而成為國際法的主要主體。
(1)由國際關(guān)系特點(diǎn)決定
國際關(guān)系是國際法賴以存在與發(fā)展的基礎(chǔ)。顧名思義,國際關(guān)系就是國家之間的關(guān)系,盡管從現(xiàn)代國際關(guān)系的基本結(jié)構(gòu)看,國際關(guān)系無論在范圍還是內(nèi)容上都得到了巨大的發(fā)展,但是國家之間的交往關(guān)系仍是國際關(guān)系的主要內(nèi)容和基本形式;離開了國家的參與和交往,國際法律關(guān)系就不能形成與發(fā)展。
(2)由國家自身特點(diǎn)決定
國家具有深刻的屬性,對外表現(xiàn)為獨(dú)立權(quán)、平等權(quán),不受其他實(shí)體管轄與制約,能夠與其他實(shí)體在國際關(guān)系的全部領(lǐng)域內(nèi)以各種形式進(jìn)行交往,具有全面的交往能力。從法律角度看,國家不僅具有完全承受國際法上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資格,而且具有以自己的行為全部形式上述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行為能力,從而決定了它是國際法的最基本主體。
(3)由國際法規(guī)定的內(nèi)容決定
現(xiàn)代國際法盡管增加了調(diào)整國際組織和民族解放組織的規(guī)范,但從整體來看,不論從國際法的傳統(tǒng)部門,還是從國際法發(fā)展的新領(lǐng)域,仍主要是調(diào)整國家之間關(guān)系和制約國家行為的規(guī)范,有關(guān)其他主體的制度僅僅是一種補(bǔ)充;從規(guī)范形式看,造法性條約的簽訂者主要是國家,國際習(xí)慣法的形成也主要依靠國家之間的反復(fù)實(shí)踐。
再從國際社會的縱向發(fā)展看,在國際社會的發(fā)展歷程中沒有形成一個完全凌駕于國家之上的實(shí)體,對于國際社會行為主體行為的規(guī)范與制約是完全自治,由法律關(guān)系的主體全面自主創(chuàng)設(shè)的法律,當(dāng)然在自主協(xié)調(diào)的過程中每個主體不同的利益需求結(jié)合在一起,并且成為國際法不斷發(fā)展與革新的動力,換句話說就是國家獨(dú)立、平等的絕對屬性使得國際法不是象國內(nèi)法一樣是一個在法律實(shí)施的有效范圍內(nèi)具有合法的政治權(quán)力和權(quán)威的主體來建立。
2.國際法的協(xié)商意志性
在國際法的發(fā)展歷史上,自然法學(xué)派認(rèn)為國際法效力的根據(jù)是“人類良知”、“人類理性”和各民族法律意識的“共同性”。實(shí)在法學(xué)派則主張,每個國家的意志或國家的“共同意志”決定國際法的效力。國際法是調(diào)整國家之間關(guān)系的法律,對國家具有拘束力,而國際法又是國家協(xié)商制定的,因此,國際法效力的根據(jù)就是各國之間的協(xié)議,或者說是各國意志之間的協(xié)議。國際社會國際之間的協(xié)議主要以國際習(xí)慣與國際條約為表現(xiàn),體現(xiàn)了國際法的意志性。
所謂國際習(xí)慣是國際交往中不成文的行為規(guī)則和國家間的默示協(xié)議,是各國重復(fù)類似行為而被認(rèn)為有法律約束力的結(jié)果。國際法最初的形態(tài)即是所謂的習(xí)慣國際法,其法律淵源都由國際習(xí)慣組成,因而可以說國際習(xí)慣是國際法最古老、最原始的淵源。國際條約是指國際法主體之間根據(jù)國際法而訂立的具有權(quán)利、義務(wù)內(nèi)容的書面協(xié)議,是現(xiàn)代國際法最主要的法律淵源。古往今來,能成為國際法淵源的條約,通常是指大多數(shù)國家參加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造法性條約,即創(chuàng)設(shè)新的、公認(rèn)的國際法規(guī)范或者修改、變更原有的規(guī)范的條約。契約性條約不能構(gòu)成國際法的淵源。當(dāng)然,國家意志之間的協(xié)議并不是指國家自由意志之間的協(xié)議,國際法是適應(yīng)國際交往的需要而產(chǎn)生的,國際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決定了國際法的發(fā)展,因此,國家意志之間的協(xié)議是指適應(yīng)一定歷史時期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的國家意志之間的協(xié)議。
國際法是通過國際社會主體平等協(xié)商而形成并發(fā)展,在國際法當(dāng)中,“平等”是一切交往的基礎(chǔ)與核心。所以國際法的國家意志體現(xiàn)為協(xié)商意志,具有相對性;而不是與國內(nèi)法體現(xiàn)的是絕對的國家意志性,所以國際法的強(qiáng)制力以及對國際法律責(zé)任的追究也就是在平等基礎(chǔ)之上實(shí)施,表現(xiàn)為集體或通過國際組織采取措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國際法強(qiáng)制基于一個國家對國際法在國內(nèi)法的適用。
3.國際法的強(qiáng)制力是以國家單獨(dú)、集體或通過國際組織采取措施為保障
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法律對其主體具有強(qiáng)制性的拘束力,任何一個主體違反了法律,都要承擔(dān)法律責(zé)任直至受到法律制裁。國家作為國際法的最基本主體,按照這一理論,那么國際法調(diào)整的行為主要是國家之行為,有強(qiáng)制力保證國家不會產(chǎn)生國際不正當(dāng)行為或國際法不加禁止的行為造成的損害,一旦國家的不當(dāng)行為造成了損害,那么國際責(zé)任必須承擔(dān)。所謂國際法律責(zé)任是指國際法主體(主要是國家)對其過不正當(dāng)行為或國際法不加禁止的行為造成的損害所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的責(zé)任。
國際不當(dāng)行為是國際法主體所作的違背國際義務(wù)的行為。依據(jù)聯(lián)合國國際法委員會起草的《國際責(zé)任條文草案》,該行為必須具有主觀要件和客觀要件,國際法律責(zé)任才能成立。國際不當(dāng)行為的主觀要件是歸因與國家,是指某一不當(dāng)行為可以歸因于國家而成為國家行為,或者說該行為在國際法上的國家行為。國際法律責(zé)任的客觀要件是指違反國際義務(wù),即該行為是違背其負(fù)擔(dān)的國際法義務(wù)的行為。
對于法律責(zé)任的承擔(dān)以及對國際法原則、規(guī)范的維護(hù)與保障主要是以國家單獨(dú)、集體或者通過國際組織采取措施為保障來執(zhí)行或由國際組織實(shí)行必要的制裁,如抗議、警告、召回駐外使節(jié)、中止或斷絕外交關(guān)系、經(jīng)濟(jì)封鎖、武裝自衛(wèi)等,使有關(guān)國家停止侵害行為,以達(dá)到保證國際法實(shí)施的目的。一旦有人破壞國際法,某個或者幾個國家,甚至也可能是整個國際社會就會遭到非法侵害,這時就需要整個國際社會聯(lián)合起來,制止打擊違法行為,使國際法得到維護(hù)和執(zhí)行,使違法者回到國際法的立場上來。國際上雖然有國際法院,但它沒有強(qiáng)制管轄權(quán)(以當(dāng)事國的自愿為前提,不具有強(qiáng)制性),因此國際法的實(shí)施除依靠各國自覺遵守外,主要依靠國家本身的力量。國內(nèi)法依靠國家權(quán)力之下的司法機(jī)關(guān)、其他行政執(zhí)法機(jī)關(guān)和國內(nèi)的軍隊(duì)來保證遵守和執(zhí)行,因?yàn)槊恳粋€國家都是國際社會平等的一員,在它們之上沒有一個超越國家同意的最高立法機(jī)關(guān),換句話即是國際法的強(qiáng)制實(shí)施是依靠國家本身的行動。例如1979年中國對越自衛(wèi)還擊戰(zhàn)、1991年多國部隊(duì)根據(jù)安理會第678號決議對伊拉克采取的軍事行動等,是國家單獨(dú)和通過國際采取措施保證國際法實(shí)施的例證是國際法具有法律強(qiáng)制力的充分體現(xiàn)。
三、當(dāng)代國際法效力依據(jù)的發(fā)展趨勢
現(xiàn)代國際社會目前雖然有國際法作為強(qiáng)制性規(guī)范,但是在世界的某些地區(qū)國際爭端與矛盾仍然普遍存在,大國強(qiáng)權(quán)政治、單邊主義肆無忌憚等等,國際秩序并未按照國際法的方向前進(jìn),甚至一些國際條約成為空紙一談,對于這樣無秩序的國際社會,國際法的強(qiáng)制性以及效力依據(jù)需要更進(jìn)一步地加強(qiáng)與邁進(jìn)。縱觀現(xiàn)代國際法的發(fā)展趨勢,國際法的強(qiáng)行法律體系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并得到良好的發(fā)展,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以及活動讓人類在國際社會內(nèi)看見了國際法效力依據(jù)的曙光。
(一)國際強(qiáng)行法概念
所謂國際強(qiáng)行法,是指國際法上一系列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特殊原則與規(guī)范的總稱,這類原則與規(guī)范由國際社會會員作為整體通過條約或者習(xí)慣,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接受并承認(rèn)為具有絕對強(qiáng)制性,且非同等強(qiáng)行性質(zhì)之國際法規(guī)則不得更改,任何條約或行為(包括作為與不作為)如與之相抵觸,完全歸于無效。
1969年的聯(lián)合國《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在國際強(qiáng)行法問題上,率先邁出了重大的一步,它是世界上第一個對國際強(qiáng)行法作出若干規(guī)定的國際性法律文件。該公約第53條對國際強(qiáng)行法作出規(guī)定:“條約在締結(jié)時與一般國際法強(qiáng)制規(guī)律抵觸者無效。就適用公約而言,一般國際法強(qiáng)制規(guī)律指國家之國際社會全體接受并公認(rèn)為不準(zhǔn)損壞且以后具有同等性質(zhì)之一般國際法規(guī)律始得更改之規(guī)律。”〖①〗《條約法公約》第53條適用于條約因與某項(xiàng)既存的國際強(qiáng)行法相抵觸而無效的情形,而該公約第64條則適用于如下情況:即條約締結(jié)后,因與新產(chǎn)生的國際強(qiáng)行法規(guī)范相抵觸,使得該條約成為無效而終止。其具體內(nèi)容為:“遇有新一般國際法強(qiáng)制規(guī)律產(chǎn)生時,任何現(xiàn)有條約之與該項(xiàng)規(guī)律抵觸者即成為無效而終止。”
以上兩項(xiàng)條款是《條約法公約》就國際強(qiáng)行法有關(guān)方面所作出的主要規(guī)定,這一創(chuàng)舉將對當(dāng)代國際法的不斷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在《條約法公約》中對國際強(qiáng)行法問題作出明確規(guī)定,這是國際法的一個新發(fā)展,表明世界各國已經(jīng)逐漸認(rèn)識到它們具有某種共同的權(quán)益和社會目標(biāo)這一不可回避的現(xiàn)實(shí);同時也體現(xiàn)了國際社會成員的相互交往正在趨于制度化、法律化,任何一個國際法主體都不能為了一己私利而任意踐踏為世人公認(rèn)的國際法準(zhǔn)則。
(二)國際刑事法院
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ICC)是根據(jù)聯(lián)合國1998年外交全權(quán)代表會議通過的《國際刑事法院規(guī)約》(又稱《羅馬規(guī)約》)的規(guī)定,于2002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根據(jù)《羅馬規(guī)約》,國際刑事法院對批準(zhǔn)國及安理會移交的案件進(jìn)行審查,國際刑事法院與現(xiàn)有的國際司法機(jī)構(gòu)不同,其他法庭均有一定的存在期限,國際刑事法院是一個永久性的國際司法機(jī)構(gòu),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與發(fā)展預(yù)示著國際強(qiáng)制執(zhí)行體系的萌芽。
1.聯(lián)合國精神的體現(xiàn)
國際刑事法院建立的宗旨與《聯(lián)合國》所體現(xiàn)的正義、和平精神一脈相承,通過懲治嚴(yán)重國際犯罪突出強(qiáng)調(diào)了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羅馬規(guī)約》同樣重申了《聯(lián)合國》宗旨的精神,特別是各國不得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或以與聯(lián)合國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犯任何國家的或政治獨(dú)立。并強(qiáng)調(diào)了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和戰(zhàn)爭罪的嚴(yán)重性及對世界的和平、安全與福祉的威脅,申明對于整個國際社會關(guān)注的最嚴(yán)重犯罪,絕不能聽之任之不予處罰,為有效懲治罪犯,必須通過國家一級采取措施并加強(qiáng)國際合作。
2.法治原則的國際性延伸
在人類歷史發(fā)展過程當(dāng)中,一戰(zhàn)和二戰(zhàn)的歷史顯示出了國際法體系的不完善、不健全的一面。依賴于國際社會公認(rèn)的法治原則,以法律為武器來解決國際利益的沖突,并懲治、威懾嚴(yán)重的國際犯罪,維護(hù)人類的正義與和平已經(jīng)成為了歷史的必然選擇。羅馬規(guī)約》規(guī)定的法庭審判及上訴程序是普通法和大陸法的混合模式,同時遵從了國際社會絕大多數(shù)國家認(rèn)可的法治原則:即罪刑法定、無罪推定和一罪不二審等原則。
3.懲治已然犯罪(實(shí)然性),防范未然犯罪(應(yīng)然性)
對于國際犯罪的審判既不是國際刑法發(fā)展的開端,也不是國際刑法發(fā)展的終結(jié)。國際社會懲治犯罪和預(yù)防犯罪的實(shí)然和應(yīng)然模式,并不僅僅依賴于締約國的多寡,而在于規(guī)定本身所具有應(yīng)然威懾性,以及締約國能否實(shí)際履行其義務(wù)。從國際刑法的意義上講,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主要目標(biāo)是有效發(fā)揮國際法懲治、威懾國際犯罪的突然以及應(yīng)然作用。
結(jié)束語
現(xiàn)在看來,要最終決定國際法的效力依據(jù)有耐于整個國際社會是否共同同意由外力來強(qiáng)制執(zhí)行這些國際社會的行為規(guī)則。要使國際社會存在同意的外力來強(qiáng)制國際社會行為主體來行使國際法的規(guī)則與規(guī)范,首先要有長期的和有預(yù)見性的共同認(rèn)識,當(dāng)然達(dá)到同一認(rèn)識是十分的艱難與不易,但也不是完全具備操作的可能性。雖然目前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tài)”使得矛盾與斗爭成為現(xiàn)實(shí),但是隨著全球化等等國際合作化浪潮以及國際社會行為主體對利益的最大化追求的趨勢也使得國際行為主體的合作成為必然。
共同的外力我認(rèn)為來自兩個方面,首先是共同的利益。全球化浪潮的國際分工與合作以及全球資源的有限性與對利益最大化最求的矛盾使得合作成為國際行為主體的首選。現(xiàn)在一個國家或國際行為主體的某一行為不單單是自己的孤立行為,隨著國際社會上行為主體的交往越發(fā)密切,一張復(fù)雜而又廣大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已經(jīng)或正在形成,任何一個參與這一網(wǎng)絡(luò)的行為體的某一行為都會對其他與之相連的主體產(chǎn)生影響,不管這影響是好是壞。全球分工必然會創(chuàng)造巨大的社會財(cái)富,增強(qiáng)各個國際社會主體的實(shí)力,并且尋求更為廣泛的共同利益。對于自身的利益的得失任何一個主體不得不警惕其他行為主體做出的任何一個行為,以有利的手段來影響對手行為形成強(qiáng)大的外力實(shí)施保障。其次是人類正在面臨的或者將要面臨的全球性的社會危機(jī)使得國際社會的行為主體為其生存與繼續(xù)的發(fā)展采取手段制止(比如全世界制定防范愛滋病的擴(kuò)散)危機(jī)的擴(kuò)散。共同利益的驅(qū)使以及共同危機(jī)的緊迫讓國際社會正在形成一個強(qiáng)大的共同的國際社會基礎(chǔ),但是這一過程的時間與空間進(jìn)程不甚遙遠(yuǎn)。
參考文獻(xiàn)
《國際法》王獻(xiàn)樞主編劉海山副主編2003年10月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
《國際法》王鐵涯主編王人杰校訂1992年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出版
《武漢大學(xué)國際法評論》武漢大學(xué)國際法研究組編2007年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
第3篇:證據(jù)法論文范文
給出企業(yè)的真實(shí)數(shù)據(jù)格式(整理后的財(cái)務(wù)報(bào)表數(shù)據(jù)),如表1所示,其中違約標(biāo)志一欄為響應(yīng)變量Y,0表示正常,1表示違約,xij,i=1,…,n,j=1,…,m表示第i個客戶的第j個指標(biāo)數(shù)值。首先要介紹經(jīng)典的線性回歸。假設(shè)響應(yīng)變量為向量Yn×1,n為樣本個數(shù);設(shè)計(jì)矩陣為Xn×(m+1),m+1表示常數(shù)列以及m個變量(表1)。將常數(shù)列放在X的第一列,經(jīng)典的線性回歸具有如下表達(dá):該式即為經(jīng)典的邏輯回歸模型。其中求解關(guān)鍵未知參數(shù)β的簡單而直接的方法是根據(jù)極大似然估計(jì)(利用式(2)寫出似然函數(shù)繼而利用NewtonRaphson方法求解極大值點(diǎn)[4])。經(jīng)典邏輯回歸相關(guān)理論已經(jīng)比較成熟并且已經(jīng)用到實(shí)際風(fēng)險(xiǎn)評級模型中,相關(guān)的結(jié)果可參考文獻(xiàn)[2]。
2證據(jù)權(quán)重邏輯回歸
在實(shí)際的風(fēng)險(xiǎn)評級模型中,經(jīng)典邏輯回歸模型有著諸多缺陷。首先變量個數(shù)m過大,例如在下一節(jié)做的真實(shí)數(shù)據(jù)中m=147,于是需要在建立邏輯回歸模型之前做變量選擇的工作,而變量選擇一直是統(tǒng)計(jì)學(xué)中的難題[1];其次,在邏輯回歸模型中,假定中間變量θ與設(shè)計(jì)矩陣X呈線性關(guān)系即θ=Xβ,這一假設(shè)在實(shí)際中也并不是都滿足的。再次,對于實(shí)際的風(fēng)險(xiǎn)評級模型,往往真實(shí)數(shù)據(jù)的采集質(zhì)量比較差(設(shè)計(jì)陣不可逆、變量方差過小或者過大等)導(dǎo)致模型偏差較大,甚至無法建立模型,需要新的手段來解決這些問題。在風(fēng)險(xiǎn)評級模型中,我們實(shí)際上更關(guān)心的是違約樣本分布與正常樣本分布之間的距離,于是利用信息論中相對熵的思想,證據(jù)權(quán)重方法(weightofevidence)與經(jīng)典邏輯回歸結(jié)合,設(shè)計(jì)了證據(jù)權(quán)重邏輯回歸模型,用以估計(jì)違約概率。
21信息價值與證據(jù)權(quán)重在這一小節(jié)中,介紹信息論中熵、相對熵與信息價值的概念,并且借此引出證據(jù)權(quán)重(weightofevidence)的定義。實(shí)際上,證據(jù)權(quán)重的概念是Good正式提出的[5],用來處理假設(shè)檢驗(yàn)問題。而真正應(yīng)用到風(fēng)險(xiǎn)評級模型中,則是近年來國際主流評級模型的發(fā)展方向[2]。對于連續(xù)隨機(jī)變量X,密度函數(shù)為f(x),熵的定義為對于風(fēng)險(xiǎn)評級模型,基于相對熵判別能力的測量工具是信息價值(informationvalue),用以刻畫違約樣本分布和正常樣本分布的差異[56]。對于某個特定的變量,將對應(yīng)違約樣本密度函數(shù)記為fD;該變量正常樣本密度函數(shù)記為f珚D。信息價值定義為違約樣本對應(yīng)于正常樣本的相對熵與正常樣本對應(yīng)于違約樣本相對熵之和[2],即從式(5)可知,信息價值的取值范圍為[0,∞)。按照定義,信息價值刻畫的是正常樣本與違約樣本分布之間的差異,對于選定的變量,為了得到具有高的判別能力的風(fēng)險(xiǎn)評級模型,該變量的信息價值應(yīng)當(dāng)盡可能的大。信息價值越高,說明該變量對于樣本違約與否的判別能力越強(qiáng)。而信息價值與響應(yīng)變量(違約與否)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5]如表2所示,此外根據(jù)信息價值可以變量選擇,將信息價值足夠大(如>03)的變量引入邏輯回歸模型,而舍棄那些信息價值偏小(對于樣本違約與否,幾乎沒有判別能力)的變量。即正常樣本與違約樣本對數(shù)似然函數(shù)的差。為使信息價值即式(5)達(dá)到最大,我們希望WOE值與該選定變量的原始數(shù)據(jù)呈單調(diào)關(guān)系,即該變量x數(shù)值越大,則對應(yīng)WOE值單調(diào)變化(越大或者越小)。此外,這種單調(diào)關(guān)系,同時反映了該變量對于違約與否的判別能力。定義式(6)反映了正常樣本與違約樣本對數(shù)似然函數(shù)的差,于是該選定變量WOE值的增加意味著違約概率的降低。利用單調(diào)的WOE值作為新的設(shè)計(jì)陣代入經(jīng)典邏輯回歸,能夠克服本節(jié)一開始討論的第二個經(jīng)典模型的困難,即中間變量θ與原始數(shù)據(jù)可能并非線性。
22算法在實(shí)際風(fēng)險(xiǎn)評級模型中,考慮第j個變量即設(shè)計(jì)矩陣X的第j列X•j=[x1j,x2j,…,xnj]T,響應(yīng)變量yi=0或1,i=1,…,n表示第i個樣本的實(shí)際違約情況。證據(jù)權(quán)重邏輯回歸的算法可以歸納如下,(1)將原始連續(xù)數(shù)據(jù)離散化,尋找第j個變量的最優(yōu)劃分,并計(jì)算信息價值。具體來說,將X•j按照升序排序,記為X(•j)=[X(1,j),…,X(n,j)]T。假設(shè)希望將X(•j)分成k個區(qū)間(即尋找k-1個分點(diǎn))且找到的分點(diǎn)必須使得WOE值為單調(diào)序列。若不存在這樣的劃分,則舍棄該變量;若存在多個這樣的劃分,則選取使得信息價值最大的劃分方式(即最優(yōu)化分)。設(shè)Gi、Bi分別表示該變量第i個區(qū)間的正常、違約樣本個數(shù),G、B表示全部的正常、違約樣本個數(shù),則由式(5)和(6)可得相應(yīng)的樣本估計(jì)形式為。在實(shí)際風(fēng)險(xiǎn)評級模型中,區(qū)間個數(shù)k依賴于經(jīng)驗(yàn),建議取8~10。(2)根據(jù)信息價值(IV)的大小選取變量。選取第一步中信息價值較大的變量(如IV>03);舍棄信息價值較小的變量。(3)將選取變量對應(yīng)的WOE值作為新的設(shè)計(jì)陣,代入經(jīng)典邏輯回歸模型。利用經(jīng)典模型中的方法解決選取變量間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問題[7],計(jì)算違約概率并給出相關(guān)統(tǒng)計(jì)推斷(系數(shù)的極大似然估計(jì)和置信區(qū)間等)。
3真實(shí)數(shù)據(jù)分析
這一節(jié)將結(jié)合某商業(yè)銀行真實(shí)的近兩年來的制造業(yè)數(shù)據(jù),給出上述證據(jù)權(quán)重邏輯回歸算法的應(yīng)用。通過與經(jīng)典邏輯回歸模型作比較,來驗(yàn)證證據(jù)權(quán)重邏輯回歸模型的功效。數(shù)據(jù)格式如表1所示,其中違約企業(yè)為60個,正常企業(yè)240家,涉及的財(cái)務(wù)指標(biāo)為147個,即該訓(xùn)練模型設(shè)計(jì)陣Xn×(m+1),n=300,m=147。此外,我們選取另外150家企業(yè),30條違約樣本、120條正常樣本作模型功效檢測。在算法第一步中,取區(qū)間數(shù)為8,計(jì)算信息價值與WOE值,選取了10個變量(權(quán)益乘數(shù)、流動負(fù)債率、全部資產(chǎn)現(xiàn)金回收率、現(xiàn)金流量凈值、固定資產(chǎn)成新率、盈利能力、現(xiàn)金比率、資本化資金充足率、(應(yīng)收票據(jù)+應(yīng)收款)/(應(yīng)付票據(jù)+應(yīng)付款)、保守速動比率)進(jìn)入經(jīng)典邏輯回歸模型。繼而利用經(jīng)典模型相應(yīng)結(jié)果(參數(shù)估計(jì)與假設(shè)檢驗(yàn)等),計(jì)算違約概率(PD)、正常樣本與違約樣本違約概率的累計(jì)分布函數(shù)曲線、訓(xùn)練樣本和檢測樣本的功效曲線(ROC曲線)[1]如圖1~4所示。從違約概率分布來看,證據(jù)權(quán)重邏輯回歸模型很好的將正常樣本(實(shí)線)與違約樣本(虛線)分開,且大多數(shù)的正常樣本的違約概率估計(jì)值遠(yuǎn)小于違約樣本的違約概率估計(jì)值。從ROC曲線功效來看,無論是訓(xùn)練模型還是檢測模型,結(jié)合證據(jù)權(quán)重的邏輯回歸方法的功效(實(shí)線)都要明顯的高于經(jīng)典邏輯回歸方法的功效(虛線)。此外,若取02為分界點(diǎn)(即若樣本違約概率>02,認(rèn)為該樣本違約,02是正常樣本違約概率分布密度與違約樣本違約概率分布密度交點(diǎn),如圖1~4。且從圖中可以看出,選取02作為閾值可以對違約客戶有較好的識別,若選另外兩個曲線交點(diǎn)為閾值則對違約客戶誤判升高),該模型對于訓(xùn)練樣本的辨識度如表3所示。特別地,對于違約客戶的辨識高達(dá)88%。而對于檢測樣本,辨識度如表4所示,對于違約客戶的辨識達(dá)83%。
4結(jié)束語
第4篇:證據(jù)法論文范文
在訴訟活動中,證據(jù)是決定案件勝訴與否的關(guān)鍵所在。而在證據(jù)提供方面存在兩種不同的立法模式。一種是證據(jù)隨時提出主義,一種是證據(jù)適時提出主義。所謂證據(jù)隨時提出主義是指當(dāng)事人有權(quán)在訴訟的任何階段隨時出證據(jù),而不受時間的限制,甚至在訴訟終結(jié)之后也可提出,引起再審程序的發(fā)生。而證據(jù)適時提出主義是指當(dāng)事人必須在法定或指定的期限內(nèi)部提出證明其主張的相關(guān)證據(jù),逾期則產(chǎn)生證據(jù)失權(quán)的法律后果。一般說來證據(jù)適時提出主義包含以下兩方面的內(nèi)容:“是舉證時限。負(fù)有舉證責(zé)任的當(dāng)事人必須在法律規(guī)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內(nèi)盡其所能地提供支持其主張的證據(jù)。二是法律后果即證據(jù)失權(quán)。當(dāng)事人逾期舉證,則喪失證據(jù)提出和證明權(quán),在以后的訴訟中不能再提出證據(jù)或提出的證據(jù)不能為法院采納而喪失其證據(jù)的證明力。
由于受追求“客觀事實(shí)”訴訟理念的影響,以及立法上舉證時限制度的缺陷,我國以前的民事訴訟實(shí)行的是證據(jù)隨時提出主義,當(dāng)事人在法院審理的各個階段包括一審、二審和再審均可提出證據(jù)。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在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6條規(guī)定的“人民法院對當(dāng)事人一量不能提交證據(jù)的,應(yīng)根據(jù)具體情況,指定其在合理的期限內(nèi)提交。當(dāng)事人在指定期限內(nèi)提交確有困難的,應(yīng)在指定期限屆滿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請延期,延長時期限由人民法院決定,含有要求當(dāng)事人限時舉證的意思,但對逾期證據(jù)的先權(quán)效果未作明確規(guī)定,我國在一定時期內(nèi)部仍然遵循著廣泛意義上的證據(jù)隨時提出主義。
實(shí)踐證明,證據(jù)時提出主義存在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弊端:一是當(dāng)事人實(shí)施“證據(jù)突襲“,嚴(yán)重地干擾了訴訟活動的正常進(jìn)行,損害了訴訟成本。由于當(dāng)事人隨時提出證據(jù),案件的進(jìn)程掌握在當(dāng)事人手中,法院喪失了對訴訟庭或多次開庭,降低了訴訟效率,也使當(dāng)事人和法院的訴訟成本不斷增加活動的控制權(quán),致使為對新的證據(jù)履行質(zhì)證程序而不得不無期限地延期浪費(fèi)了有限的審判資源。三是損害了裁判的穩(wěn)定性。證據(jù)隨時提出主義的存在,使得終局判決不斷地被撤銷,影響了當(dāng)事人之間人身關(guān)系和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穩(wěn)定性,不利于國家司法審判權(quán)威的樹立。
為了解決證據(jù)隨時提出主義所帶來的上述弊端,《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對當(dāng)事人提交證據(jù)規(guī)定了舉證時限制度,并明確逾期舉證導(dǎo)致證據(jù)失權(quán)的法律后果。《證據(jù)規(guī)定》第34條規(guī)定:當(dāng)事人應(yīng)當(dāng)在舉證期限內(nèi)向人民法院提交證據(jù)材料,人民法院審判時不組織質(zhì)證。
證據(jù)適時提出主義的制度價值在于:(1)有利于實(shí)現(xiàn)程序正義。證據(jù)適時提出主義為雙方當(dāng)事人創(chuàng)設(shè)了平等的舉證和辯論機(jī)會:當(dāng)事人還可借助于證據(jù)交換制度,了解對方的證據(jù),避免故意隱藏證據(jù)、拖延訴訟、證據(jù)突襲等現(xiàn)象有發(fā)生。(2)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舉證時限的設(shè)立,使得案件的爭點(diǎn)與證據(jù)在庭前予以固定,從而有利于法院一次開庭集中審理,減少開庭的次數(shù),縮短案件的審理周期,節(jié)約司法審判資源。另外,由于雙方當(dāng)事人對彼此的證據(jù)及訴訟結(jié)果心中有數(shù),從而有利于當(dāng)事人在庭前送達(dá)。如果說證據(jù)隨時提出主義是基于實(shí)體公正的考量而產(chǎn)生,那么證據(jù)適時提出主義是訴訟效率的產(chǎn)物。兩種立法模式孰優(yōu)孰劣,體現(xiàn)出公正與效率的沖突,平衡及其價值選擇。隨著經(jīng)濟(jì)活動的高速發(fā)展,案件數(shù)量不斷攀升,如何在公正與效率之間尋求平衡點(diǎn)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事實(shí)上司法活動追求公正與效率并不是一個不相容選言命題,在不以犧牲訴訟效率為代價的前提下,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nèi)部,我們完全可以找到公正與效率的平衡點(diǎn)。《證據(jù)規(guī)定》正是基于這一考慮,將公正與效率二者和諧地統(tǒng)一起來,把可能影響實(shí)體公正,確因客觀事由無法在舉證期限內(nèi)提出的證據(jù)界定為新的證據(jù),從而賦予其排除適時提出主義的效力,最大限度地維護(hù)了當(dāng)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所以說,新的證據(jù)是對舉證時限制度的補(bǔ)充,是證據(jù)適時提出主義的例外適用,其價值在于最大限度地實(shí)現(xiàn)法律的公正。
二、如何界定“新的證據(jù)”
在總結(jié)審判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證據(jù)規(guī)定》第一次就有關(guān)“新的證據(jù)”的范圍作出了限定。依該規(guī)定,“新的證據(jù)”是指以下幾種情形,(1)一審程序中的當(dāng)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后發(fā)現(xiàn)的證據(jù)和舉證期限內(nèi)部確因客觀原因無法提供且在延長的期限內(nèi)仍無法提供的證據(jù)第41條;(2)二審程序中一審?fù)徑Y(jié)束后新發(fā)現(xiàn)的證據(jù)和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申請法院調(diào)查取證未獲準(zhǔn)許,二審法院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準(zhǔn)許并依當(dāng)事人申請調(diào)取的證據(jù)第41條,再審程序中,原審?fù)徑Y(jié)束后新發(fā)現(xiàn)的證據(jù)(第44條)。可將上述情形概括地分為三種類型,即新發(fā)現(xiàn)的證據(jù)、延期內(nèi)未提交的證據(jù)和未準(zhǔn)許調(diào)取的證據(jù)。
研析上述條文可以發(fā)現(xiàn),因“客觀原因”不能按期舉證是“新的證據(jù)”的本質(zhì)屬性;構(gòu)成新的證據(jù)必須具備兩個要件:一是時間要件,當(dāng)事人提交的證據(jù)是舉證時限屆滿之后或庭審結(jié)束之后獲得。二是實(shí)質(zhì)要件,當(dāng)事人未按期提交證據(jù)是出于“客觀原因”造成的。“新的證據(jù)”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舉證期限內(nèi)當(dāng)事人沒有掌握的證據(jù),包括舉證期限屆滿后或庭審結(jié)束后新發(fā)現(xiàn)的證據(jù)和舉證期限內(nèi)證據(jù)雖已出現(xiàn),但是當(dāng)事人因客觀原因通常無法知道的證據(jù)以及申請一審法院調(diào)取而未獲準(zhǔn)許而二審法院準(zhǔn)許并依當(dāng)事人的申請而調(diào)查取得的證據(jù)。“舉證期限內(nèi)部,證據(jù)客觀上沒有出現(xiàn),當(dāng)事人自然無舉證之可能”,而證據(jù)雖已出現(xiàn),但是當(dāng)事人通常情況下無法知道其出現(xiàn),是指證據(jù)雖已客觀存在而為當(dāng)事人所不能認(rèn)識而沒有掌握的情況下,當(dāng)事人也無完成舉證責(zé)任之能力。而未獲準(zhǔn)許調(diào)區(qū)的證據(jù)因涉及檔案、國家秘密、商業(yè)秘密及個人隱私等材料,當(dāng)事人客觀上舉證不能是顯而易見的。二是舉證期限內(nèi)當(dāng)事人雖然已經(jīng)掌握或雖已實(shí)際控制該證據(jù),但是因?yàn)橥饨缈陀^原因無法提交的證據(jù)。比如舉證期限內(nèi)突然發(fā)生戰(zhàn)爭、地震等自然災(zāi)害,在這種不可抗力的情況下,當(dāng)事人無論如何也不能提出證據(jù)或者說提出證據(jù)的困難相當(dāng)大,當(dāng)事人自身的能力無法克服,就是法院自身也無法為之,難度很大。因客觀原因不能提交證據(jù),是構(gòu)成“新的證據(jù)”的本質(zhì)屬性。現(xiàn)在的問題在于什么是“客觀原因”?(5)借用哲學(xué)上的概念,客觀原因是指獨(dú)立于人的意識之外,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存在,一般有自身客觀原因與外界客觀原因的劃分構(gòu)成新的證據(jù)的客觀原因是兩者兼容呢?還是只是其一?我認(rèn)為,新的證據(jù)的價值目標(biāo)在于:在非因當(dāng)事人的原因?qū)е屡e證不能的情況下,給予當(dāng)事人的法律救濟(jì),以期實(shí)現(xiàn)法律公正,對當(dāng)事人確因客觀事由不能在舉證期限內(nèi)完成舉證責(zé)任的,承認(rèn)其在舉證期限期滿后所提供的證據(jù)效力,最大限度地維護(hù)當(dāng)事人法權(quán)益,彌補(bǔ)證據(jù)適時提出主義可能帶來的弊端。所以對客觀原因不能作擴(kuò)大解釋,應(yīng)將其限定為當(dāng)事人所不能克服的外界客觀原因,而不包括自身的客觀原因。
綜上之分析,所謂“新的證據(jù)”,是指當(dāng)事人確因外界客觀原因無法在舉證期限內(nèi)提供證據(jù)而在舉證期限之后或庭審結(jié)束之后所提供的證據(jù)。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證據(jù)規(guī)定》中還有“新證據(jù)”以及可視為新的證據(jù)規(guī)定。如第40條第1款:“當(dāng)事人收到對方交換的證據(jù)后提出反駁意見并提出新證據(jù)的,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通知當(dāng)事人在指定的時間進(jìn)行交換”;第43條第2款:“當(dāng)事人經(jīng)人民法院準(zhǔn)許延期舉證,但因客觀原因未能在準(zhǔn)許的期限內(nèi)提供,且不審理該證據(jù)可能導(dǎo)致裁判明顯不公的,其提供的證據(jù)可視為新的證據(jù)。”從文義上看,“新證據(jù)”與“新的證據(jù)”毫無差別,但筆者認(rèn)為,此處的“新證據(jù)”等同于反駁證據(jù),所以與我們所界定的“新的證據(jù)”完全不同,應(yīng)注意加以區(qū)別:1、“可視為新的證據(jù)”能夠產(chǎn)生與“新的證據(jù)”相同的法律后果,但是“可視為新的證據(jù)”不是“新的證據(jù)”,“可視為新的證據(jù)”從立法技術(shù)上講是一種法律上的擬制,即法律將A擬制為B,使A與B有相同的法律后果,實(shí)質(zhì)上兩者并不相同。構(gòu)成“新的證據(jù)”的客觀原因是指外界客觀原因。當(dāng)事人因外界客觀原因舉證期限內(nèi)不能提供證據(jù),在舉證期限屆滿后提供的證據(jù),構(gòu)成“新的證據(jù)”。而“可視為新的證據(jù)”強(qiáng)調(diào)的客觀原因則是自身的客觀原因。“當(dāng)事人因自身客觀原因不能按期舉證可以歸結(jié)為當(dāng)事人在主觀上存在過失,比如當(dāng)事人生病住院或出差在外時,當(dāng)事人完全可以委托他去代為取證并提供證據(jù),其不按期舉證,舉證期限屆滿后提供的證據(jù)材料則不能構(gòu)成“新的證據(jù)”,該證據(jù)材料在法律上造成證據(jù)失權(quán)的法律后果,當(dāng)事人因自身客觀原因不能按期舉證,舉證期限屆滿后提供的證據(jù)材料,只有在不審理證據(jù)可能導(dǎo)致裁判明顯不公時,才可能構(gòu)成“可視為新的證據(jù)”。為什么說構(gòu)成“可視為新的證據(jù)”的客觀原因指當(dāng)事人自身的客觀原因呢?這要結(jié)合《證據(jù)規(guī)定》第四十三條的整條規(guī)定來進(jìn)行理解,第四十三條第一款規(guī)定:“當(dāng)事人舉證期限屆滿后提供的證據(jù)不是新的證據(jù)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納。第二款是對第一款情況中的例外情況的規(guī)定,這種例外規(guī)定是法律的擬制性規(guī)定,不是構(gòu)成新的證據(jù)的原因多是指當(dāng)事人自身的原因,第二款既然轉(zhuǎn)承第一款而定,可見構(gòu)成“可視為新的證據(jù)”的原因必是指當(dāng)事人自身的原因,構(gòu)成“可視為新的證據(jù)”的客觀原因,也應(yīng)是指當(dāng)事人自身的客觀原因。構(gòu)成“可視為新的證據(jù)”“一般都當(dāng)事人在舉證期限屆滿前(這里至少是指法院準(zhǔn)許的延長期內(nèi))都已經(jīng)掌握的證據(jù)(包括掌握證據(jù)線索),而不存在沒有掌握的證據(jù)的情況,其沒有提交是因?yàn)樽陨砜陀^原因造成的”。2、“可視為新的證據(jù)”只存在一審程序中,而新的證據(jù)則存在一審、二審和再審程序。“可視為新的證據(jù)”只存在一審程序中,而新的證據(jù)則存在于一審、二審和再審程序中,根據(jù)法條規(guī)定,構(gòu)成可視為新的證據(jù)的證據(jù),是指當(dāng)事人經(jīng)人民法院準(zhǔn)許延期舉證,但因客觀原因未能在準(zhǔn)許期限內(nèi)提供,且不審理該證據(jù)可能導(dǎo)致裁判明顯不公的,其提供的證據(jù)可視為新的證據(jù)。根據(jù)民事訴訟法及有關(guān)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民事訴訟證據(jù)規(guī)定》等有關(guān)規(guī)定來看,只有在一審程序中才可能存在法院準(zhǔn)許延期舉證的問題。因此,“可視為新的證據(jù)”只存在一審程序中。而新的證據(jù)根據(jù)《證據(jù)規(guī)定》的有關(guān)規(guī)定來看,卻存在于一審、二審、再審程序中。3、構(gòu)成“可視為新的證據(jù)”的證據(jù),當(dāng)事人在舉證期限內(nèi)因客觀原因無法提供證據(jù)時,必須向人民法院提出延期舉證的申請,并獲得人民法院準(zhǔn)許。4、“可視為新的證據(jù)”在適用上具有自己的獨(dú)立性,依條文之規(guī)定,成立這類證據(jù)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例:(1)一審程序中;(2)當(dāng)事人因客觀原因無法在舉證期限內(nèi)提供證據(jù)‘(3)經(jīng)法院準(zhǔn)許延期舉證;(4)因客觀原因未能在準(zhǔn)許的期限內(nèi)提供;(5)不審理該證據(jù)可能導(dǎo)致裁判明顯不公。此處的“客觀原因”可以是自身的客觀原因,可見“可視為新的證據(jù)”與“新的證據(jù)”并不完全一樣。
三、如何適用“新的證據(jù)”
1、轉(zhuǎn)變傳統(tǒng)觀念,樹立正確的訴訟理念。公正與效率是司法活動永恒的主題,是法律最重要的兩項(xiàng)價值,任何一個訴訟制度的設(shè)計(jì)都必須顧及二者的平衡,偏廢其中任何一項(xiàng)都不利于司法活動目的的實(shí)現(xiàn)。我國用十年來的訴訟實(shí)踐告訴我們。治院的司法認(rèn)知活動必須建立在證據(jù)所現(xiàn)的法律事實(shí)基礎(chǔ)之上。過分追求個案的“客觀真實(shí)”必然要以犧牲程序公正、普遍公正和效率為代價。訴訟活動中,程序公正,實(shí)體公正,普遍公正以及訴訟效率都是我們追求的目標(biāo),我們需要做的工作是如何在這諸多的價值中找到一個平衡點(diǎn)。對當(dāng)事人在舉證時限內(nèi)無法提供的“新的證據(jù)”,在不影響程序公正和訴訟效率的前提下,給予當(dāng)事人一定的法律救濟(jì)。這充分體現(xiàn)出公正與效率的和諧統(tǒng)一。
第5篇:證據(jù)法論文范文
關(guān)鍵詞:電子簽名證據(jù);證據(jù)屬性;審查判斷
一、電子簽名證據(jù)概述
根據(jù)聯(lián)合國國際貿(mào)易法委員會《電子簽名示范法》第二條中的規(guī)定,電子簽名是指“以電子形式表現(xiàn)的數(shù)據(jù),該數(shù)據(jù)在一段數(shù)據(jù)信息之中或附著于或與一段數(shù)據(jù)信息有邏輯上的聯(lián)系,該數(shù)據(jù)可以用來確定簽名人與數(shù)據(jù)信息的聯(lián)系并且可以表明簽名人對數(shù)據(jù)信息中的信息的同意。”我國在《電子簽名法》第二條第一款中對電子簽名也進(jìn)行了規(guī)定:“本法所稱電子簽名,是指數(shù)據(jù)電文中以電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識別簽名人身份并表明簽名人認(rèn)可其中內(nèi)容的數(shù)據(jù)。”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這樣認(rèn)為,電子簽名是在電子數(shù)據(jù)交換中,附屬于數(shù)據(jù)電文中,以電子形式以表明簽名人身份的數(shù)據(jù)。當(dāng)今理論界又把電子簽名有分為廣義的電子簽名和狹義的電子簽名。廣義的電子簽名的定義可以簡單的分解成以下幾點(diǎn):一是電子簽名是以電子形式存在的;二是電子簽名能確認(rèn)電子合同的內(nèi)容;三是當(dāng)事人通過電子簽名表明其身份,并表明接受合同項(xiàng)下的權(quán)利義務(wù),繼之表明愿意承擔(dān)可能產(chǎn)生的合同責(zé)任;狹義的電子簽名則是指利用特定的加密算法而進(jìn)行的簽名,通常是指數(shù)字簽名。
二、電子簽名證據(jù)的種類
1.數(shù)字簽名(DigitalSignature),即狹義的電子簽名,是以特定的電子簽名技術(shù)所進(jìn)行的簽名。如前所述,數(shù)字簽名是電子簽名的一種,這種觀點(diǎn)被廣泛的學(xué)者所認(rèn)可,一般是指以非對稱加密技術(shù)所進(jìn)行的電子簽名。它是電子商務(wù)活動中使用最為普遍的電子簽名方式。此外,通過動態(tài)簽名的識別,也可以使個人身份與其簽名發(fā)生特定的聯(lián)系。
2.生物特征簽名(SignatureByBiometries),是指籍由使用者的指紋、聲波、視網(wǎng)膜紋等生理特征作為辨識的根據(jù),而達(dá)到鑒別作用的簽名。它是與用戶個人生理特征相聯(lián)系的。
三、電子簽名證據(jù)進(jìn)行審查判斷的方法
(一)電子簽名證據(jù)收集主體的審查
審查判斷電子簽名的收集主體是否適格問題是程序?qū)彶榈氖滓襟E。對電子簽名證據(jù)進(jìn)行收集和保全的主體都應(yīng)當(dāng)是特定的,不具備法律規(guī)定主體資格的機(jī)關(guān)和個人將會否定其證據(jù)資格。在此需要注意的是,除法律規(guī)定之外,需要認(rèn)證方能授予的主體資格一般需要具有相關(guān)資格的主體出具相應(yīng)的證明。此外,由于電子簽名其特殊的證據(jù)特征,這就要求對我們電子簽名證據(jù)進(jìn)行收集的個人進(jìn)行審查時,不僅要看其是否具有相關(guān)的身份資格,而且要審查判斷其是否掌握收集電子簽名證據(jù)的相關(guān)技術(shù)。若身份適格但是缺乏相應(yīng)的技術(shù),我們可以認(rèn)定其不具有證據(jù)收集主體資格。
(二)電子簽名證據(jù)能力的審查
證據(jù)能力,又稱為證據(jù)資格,“是指證據(jù)材料能夠作為證據(jù)使用而在法律上享有正當(dāng)性。通常情況下,必須同時具備真實(shí)性、合法性和關(guān)聯(lián)性等的證據(jù)才具有證據(jù)能力。”對電子簽名證據(jù)的證據(jù)能力進(jìn)行審查,也就是對其是否滿足作為證據(jù)使用條件進(jìn)行審查。我國《電子簽名法》第三條規(guī)定:“當(dāng)事人約定使用電子簽名、數(shù)據(jù)電文的文書,不得僅因?yàn)槠洳捎秒娮雍灻?shù)據(jù)電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第四條規(guī)定:“可靠地電子簽名與手寫或者蓋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第七條規(guī)定:“數(shù)據(jù)電文不得僅因?yàn)槠涫且噪娮印⒐鈱W(xué)、磁或者類似手段生成、發(fā)送、接收或者存儲而被拒絕作為證據(jù)使用。”從以上條文可知,我國從立法上對于數(shù)據(jù)電文和電子簽名的證據(jù)能力及證明力給予了肯定。
另外,我國《電子簽名法》第五條規(guī)定:“符合下列條件的數(shù)據(jù)電文,視為滿足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的原件形式要求:(一)能夠有效地表現(xiàn)所載內(nèi)容并可供隨時調(diào)取查用;(二)能夠可靠的保證自最初形成時起,內(nèi)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但是,數(shù)據(jù)電文在儲存和經(jīng)行數(shù)據(jù)交換時發(fā)生形式的變化并不影響數(shù)據(jù)電文的完整性。上述的規(guī)定表明我國對電子簽名證據(jù)的復(fù)印件與原件在功能相同的情況下,具有相同的證明力。
(三)電子簽名證據(jù)來源的審查
對電子簽名證據(jù)來源的審查主要包括以下幾點(diǎn):首先,審查電子簽名證據(jù)是以什么方法、在什么情況下取得的。其次,由于電子簽名證據(jù)是易變的數(shù)字信息,需要可靠的來源進(jìn)行穩(wěn)定性保障,因此我們對電子簽名證據(jù)進(jìn)行審查判斷時,要檢驗(yàn)電子簽名證據(jù)的來源是否客觀真實(shí)。例如,對生物特征簽名的收集時,我們不僅要利用計(jì)算機(jī)取證技術(shù)進(jìn)行合法的取證,而且要對取證的對象的真實(shí)性進(jìn)行逐一的審查。最后,對未經(jīng)公證的電子簽名證據(jù)的審查,不能因?yàn)槠湮唇?jīng)過公證機(jī)關(guān)公證而喪失證據(jù)資格。沒有經(jīng)過公證機(jī)關(guān)公證的電子簽名證據(jù)只會導(dǎo)致其證明力下降而非消失。例如EDI中心提供的提單簽發(fā)、傳輸記錄,CA認(rèn)證中心提供的認(rèn)證或公證書以及其他數(shù)字簽名等就具有較強(qiáng)的來源可靠性,而沒有經(jīng)過這些認(rèn)證的數(shù)據(jù),證據(jù)資格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并不因此而失去證據(jù)資格,可以通過數(shù)據(jù)鑒定進(jìn)行補(bǔ)強(qiáng)。
注釋:
何峰,.論電子證據(jù)的審查與舉證.信息網(wǎng)絡(luò)安全.2010(4).
參考文獻(xiàn):
[1]蘇鳳仙,譚德宏.民事訴訟中電子證據(jù)的審查判斷.遼寧經(jīng)濟(jì)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3(2).
[2]胡冰.電子簽名證據(jù)問題法律研究.山東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06年.
第6篇:證據(jù)法論文范文
主題詞:澳大利亞證據(jù)法 歷史發(fā)展 改革動向 證據(jù)法統(tǒng)一運(yùn)動 特點(diǎn)一、澳大利亞證據(jù)法的歷史發(fā)展英國開拓澳洲殖民地時將普通法和衡平法帶到了澳洲,直至今日,澳大利亞還是英聯(lián)邦的一部分。在民事訴訟制度上,澳大利亞雖有自己的特色,但法律原理、訴訟結(jié)構(gòu)、制度精神、乃至具體的程序都打上了“日不落帝國”之烙印。澳大利亞的證據(jù)制度亦是如此。澳大利亞最早的證據(jù)規(guī)則沿用英國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以及后來的制定法,如英國議會制定的《1831年證據(jù)特派員法》(the Evidence on Commission Act 1831)、《1851年證據(jù)法》、《1856年外國法院證據(jù)法》、《1859年證據(jù)特派員法》、《1861外國法律查明法》 (the Foreign Law AsCETainment Act 1861)、《1868年書證法》(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Act 1868)、《1882年書證法》、《1885年證據(jù)特派員法》、《1898年刑事證據(jù)法》等。
隨著經(jīng)濟(jì)和法制的發(fā)展,澳大利亞逐步發(fā)展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在證據(jù)法方面,早期的成文證據(jù)法有澳大利亞聯(lián)邦《1905年證據(jù)法》(the Evidence Act)和《1901年州、屬地法律和記錄承認(rèn)法》 (the State and Territorial Laws and Records Recognition Act),后來有聯(lián)邦《1974年證據(jù)法》,1979、1985年《證據(jù)修正法》(EVIDENCE AMENDMENT ACT),1971-1973年《澳大利亞首都地區(qū)證據(jù)法(暫行規(guī)定)》[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EVIDENCE (TEMPORARY PROVISIONS) ACT 1971-1973 ],以及《1976年涉外訴訟(禁止特定證據(jù))修正法》[FOREIGN PROCEEDINGS (PROHIBITION OF CERTAIN EVIDENCE) AMENDMENT ACT 1976]等。
而各州和地區(qū)都有自己的證據(jù)法。比如新南威爾士《1901年議會證據(jù)法》(PARLIAMENTARY EVIDENCE ACT),維多利亞《1958年證據(jù)法》,昆士蘭《1977年證據(jù)法》,西澳大利亞《1906年證據(jù)法》,南澳大利亞《1929年證據(jù)法》,塔斯馬尼亞《1910年證據(jù)法》,澳大利亞首都地區(qū)《1971 年證據(jù)法》,澳大利亞北部地區(qū)《1939年證據(jù)法》。對這些證據(jù)法的修改補(bǔ)充法案、實(shí)施規(guī)則、附屬法案(如宣誓法等)以及規(guī)定大量證據(jù)法則的聯(lián)邦和各地區(qū)的民事訴訟規(guī)則、法院規(guī)則、司法判例,加在一起不下數(shù)百種。
二、澳大利亞證據(jù)法改革和統(tǒng)一的時代背景數(shù)百種證據(jù)法規(guī)使澳大利亞的證據(jù)制度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證據(jù)法則群,但規(guī)則卻過分復(fù)雜,象是一個迷宮,互不一致,相互沖突嚴(yán)重,存在諸多不確定的領(lǐng)域[1]以及其他各種缺陷[2].根據(jù)1903年《司法法》(Judiciary Act)第79、80條之規(guī)定,聯(lián)邦法院在州或領(lǐng)地審理案件時,適用州或領(lǐng)地之證據(jù)法。而澳大利亞各州、領(lǐng)地的證據(jù)法相差十萬八千里,令人頭痛的是,不同法域適用的證據(jù)規(guī)則不同之處不僅僅在于證據(jù)法法條規(guī)定本身,還在于各法域適用的普通法存有差距。二十世紀(jì)七、八十年代,州法院和位于該州的聯(lián)邦法院、以及領(lǐng)地法院和位于該地的聯(lián)邦法院適用的證據(jù)法走向統(tǒng)一,而處于不同州的聯(lián)邦法院適用的證據(jù)規(guī)則并未統(tǒng)一,即依聯(lián)邦法設(shè)立的聯(lián)邦法院卻因法院大樓建于不同地區(qū)而適用不同法域的證據(jù)法。
在這種背景下,澳大利亞法律改革委員會[3]于1979年7月,以澳聯(lián)邦司法部長Peter Drew Durack為首組成龐大的證據(jù)法改革委員會[4],旨在全面評審澳大利亞的證據(jù)制度,以實(shí)現(xiàn)統(tǒng)一證據(jù)法之目的。
“鑒于參議院憲法和法律事務(wù)常務(wù)委員會就澳大利亞首都地區(qū)1972年《證據(jù)法案》提出如下建議:(1)由法律改革委員會對證據(jù)法進(jìn)行綜合性評審,以制訂適應(yīng)時勢發(fā)展之證據(jù)法典;(2)起草《統(tǒng)一證據(jù)法》,以便在澳大利亞首都地區(qū)和境外領(lǐng)地適用同一的證據(jù)法;以及條件成熟時,在所有聯(lián)邦法院和法庭適用同一的證據(jù)法;《統(tǒng)一證據(jù)法》內(nèi)容應(yīng)包括聯(lián)邦《1905年證據(jù)法》和《1901年州、屬地法律和記錄承認(rèn)法》涉及的所有內(nèi)容。同時,為促進(jìn)聯(lián)邦法院、首都地區(qū)和境外領(lǐng)地法院、以及聯(lián)邦和領(lǐng)地法庭適用的證據(jù)法現(xiàn)代化,使之符合時勢發(fā)展和預(yù)期要求,澳大利亞法律改革委員會對聯(lián)邦法院[5]和領(lǐng)地法院[6]訴訟程序中適用的證據(jù)法進(jìn)行綜合性評審,就如下事項(xiàng)提出報(bào)告:(1)上述法院適用的證據(jù)法是否應(yīng)統(tǒng)一,以及在何種程度上統(tǒng)一;以及(2)證據(jù)法改革適當(dāng)?shù)牧⒎ㄐ问剑约拔磥碓试S單一法域必要時對統(tǒng)一證據(jù)法作出變更的形式。”[7]證據(jù)法改革委員會認(rèn)為,基于便利和效率原則,即便證據(jù)法一定要尊重差別,也應(yīng)該是聯(lián)邦法院適用的證據(jù)法與各法域法院適用的證據(jù)法的差別,聯(lián)邦法院適用的證據(jù)法不應(yīng)存在差別,換言之,首先應(yīng)實(shí)現(xiàn)聯(lián)邦法院適用證據(jù)法的統(tǒng)一。同時,全國所有地區(qū)的證據(jù)法都急需改革,目前全國的證據(jù)法律淵源浩如煙海,由無數(shù)的非系統(tǒng)性法律文件和司法判例所構(gòu)成。即使對于大多數(shù)職業(yè)律師而言,也是一個神秘的迷宮,對沒有聘請律師的當(dāng)事人來說,則更是包含著無數(shù)陷井圈套的驚險(xiǎn)游戲,輕則令其心智困擾,重則令其稀里糊涂敗訴。證據(jù)法還存在諸多不確定的領(lǐng)域,我們知道,最后確定的法律最終是由法院來宣告的,而在司法實(shí)踐中就存在這種情形,由于證據(jù)法則過于復(fù)雜,一些法官便走向另一極端,忽略其復(fù)雜性,過分簡化證據(jù)規(guī)則,避免各種專門術(shù)語的使用等,這也是需要改變的地方。
1985年,《證據(jù)之中期報(bào)告》出臺,概括了對證據(jù)法的評價,也提出了證據(jù)法的統(tǒng)一問題,即聯(lián)邦法院和領(lǐng)地法院適用的證據(jù)法應(yīng)進(jìn)行全面、大刀闊斧地改革。《證據(jù)之中期報(bào)告》以16篇研究論文為基礎(chǔ)起草了《統(tǒng)一證據(jù)法草案(討論稿)》[8],建議采取立法形式予以頒布,并分發(fā)給法律專業(yè)機(jī)構(gòu)、地方法官、證據(jù)法研究人員、聯(lián)邦法官、州法官、退休法官、警察、律師和其他有關(guān)人士和組織,舉行征求意見的公開聽審,收集了大量建議,而且大約二年便舉行一次研討會,將所接受的咨詢和建設(shè)性意見納入統(tǒng)一證據(jù)立法。此后,制訂統(tǒng)一證據(jù)法的思想觀念已深入人心,對立法的可行性已達(dá)得了前所未有的共識。
在此基礎(chǔ)上,《1987年證據(jù)法案》 (Evidence Bill 1987)和《1987年證據(jù)(修正)法案》[Evidence (Consequential Amendments) Bill 1987]出臺,較全面地總結(jié)了改革和統(tǒng)一證據(jù)法的建議,為推動統(tǒng)一證據(jù)法走向立法議程和制訂《1995年證據(jù)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
1987 年澳大利亞法律改革委員會出版了最終報(bào)告《證據(jù)》。通過努力,統(tǒng)一證據(jù)法納入立法議程,最終成果是1995年頒布的聯(lián)邦《1995年證據(jù)法》,該法自 1997年9月30日施行。該法突出強(qiáng)調(diào)如下主題:1.證人:證人資格和強(qiáng)制作證;宣誓證言和非宣誓證言;作證的方式。2.證據(jù)的采納和排除:關(guān)聯(lián)性證據(jù);書證;傳聞證據(jù);意見證據(jù);自認(rèn);判決和定罪判決作為其依據(jù)的案件事實(shí)之證據(jù);品格證據(jù)和行為證據(jù)(包括與證人可信性有關(guān)的證據(jù));識別證據(jù);特權(quán);為公共利益排除的證據(jù);排除證據(jù)之自由裁量權(quán)。
3.證明因素:司法認(rèn)知(勿需證明事項(xiàng));書證內(nèi)容的證明;便利證明;證明標(biāo)準(zhǔn);佐證;對陪審團(tuán)的警告。與該法頒布之日起始,澳聯(lián)邦對就該法制定了一系列補(bǔ)充法案、實(shí)施規(guī)則和附屬法案。聯(lián)邦對證據(jù)法的修訂也促使了各州對證據(jù)法的重新審視,各州紛紛推出新證據(jù)法,如新南威爾士《1995年證據(jù)法》和澳大利亞北部地區(qū)《1996年證據(jù)法》等,以接近聯(lián)邦法之規(guī)定。再加上規(guī)定大量證據(jù)法則的聯(lián)邦和各地區(qū)的民事訴訟規(guī)則、法院規(guī)則、司法判例,至此,澳大利亞的證據(jù)法已形成一個較科學(xué)、較完備的法律體系,當(dāng)然這仍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體系。
三、澳大利亞證據(jù)法律淵源澳大利亞的證據(jù)法律規(guī)范除有證據(jù)字樣的法律、法規(guī)、條例、規(guī)則等外,還大量見之于澳大利亞的法院規(guī)則以及法院判例。如《聯(lián)邦法院規(guī)則》第15A條、,維多利亞《1996年最高法院規(guī)則(民事訴訟程序一般規(guī)定)》第32條規(guī)定了“初期開示和對訴訟外第三人的開示”;維多利亞《1996年最高法院規(guī)則(民事訴訟程序一般規(guī)定)》第29條、新南威爾士1970年《最高法院規(guī)則》第23條、昆士蘭《1900年最高法院規(guī)則》第35條都規(guī)定了“書證的開示和查閱”;維多利亞《1996年最高法院規(guī)則(民事訴訟程序一般規(guī)定)》第30條、西澳大利亞《1971年最高法院規(guī)則》第27條規(guī)定了“質(zhì)問書”等。 歸結(jié)起來,澳大利亞現(xiàn)行證據(jù)法的主要淵源有:(一)澳聯(lián)邦(COMMONWEALTH)
1.聯(lián)邦《1995年證據(jù)法》(EVIDENCE ACT 1995);2.《1994年(新西蘭)證據(jù)和程序法》[EVIDENCE AND PROCEDURE (NEW ZEALAND) ACT 1994];3.《1995年(新西蘭)證據(jù)和程序規(guī)則》[EVIDENCE AND PROCEDURE (NEW ZEALAND) REGULATIONS ];4.1994、1997年《(新西蘭)證據(jù)和程序修正規(guī)則》[EVIDENCE AND PROCEDURE (NEW ZEALAND) AMENDMENT REGULATIONS];5.《1998年證據(jù)規(guī)則(修正案)》[EVIDENCE REGULATIONS (AMENDMENT) 1998];6.《1994年涉外證據(jù)法》(FOREIGN EVIDENCE ACT 1994);7.《1992年公司(證據(jù))修正法》[CORPORATIONS LEGISLATION (EVIDENCE) AMENDMENT ACT 1992 ];8.1995年第44號、1996年第202號《證據(jù)規(guī)則(修正案)》[ EVIDENCE REGULATIONS(AMENDMENT)];9.《1976年聯(lián)邦法院法》(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 Act 1976);10.《1976年聯(lián)邦法院修正法》(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 Amendment Act 1976);11.《聯(lián)邦法院規(guī)則》(Federal Court Rules)。
(二)澳大利亞首都地區(qū)(ACT)
1. 聯(lián)邦《1995年證據(jù)法》(EVIDENCE ACT 1995);2.1989、1990、1991、1992、1994、1996年《(閉路電視)證據(jù)法》[EVIDENCE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ACT];3.1993、1994、1999年《證據(jù)法(修正案)》[EVIDENCE (AMENDMENT) ACT];4.1989、1990年《證據(jù)(法律和規(guī)則)法修正案》[EVIDENCE (LAWS AND INSTRUMENTS) (AMENDMENT) ACT];5.1985、1990年《證據(jù)條例(修正案)》[EVIDENCE (AMENDMENT) ORDINANCE];6. 《1933年最高法院法》(Supreme Court Act 1933);7.《1937年最高法院規(guī)則》(Supreme Court Rules 1937)。
(三)新南威爾士(NSW)
1.《1995年證據(jù)法》(EVIDENCE ACT 1995);2.《1997年(兒童)證據(jù)法》[EVIDENCE (CHILDREN) ACT 1997];3.《1999年(兒童)證據(jù)規(guī)則》[EVIDENCE (CHILDREN) REGULATION 1999];4.《1998年(視聽)證據(jù)法》[EVIDENCE (AUDIO AND AUDIO VISUAL LINKS) ACT 1998];5.《1995年證據(jù)法(間接和其它規(guī)定)》[EVIDENCE (CONSEQUENTIAL AND OTHER PROVISIONS) ACT 1995];6.《1995年委托取證法》(EVIDENCE ON COMMISSION ACT 1995);7.《1999年司法(證人出庭和出示證據(jù))規(guī)則》[JUSTICES (ATTENDANCE OF WITNESSES AND PRODUCTION OF EVIDENCE) RULE 1999];8.1995、2000年《證據(jù)規(guī)則》(EVIDENCE REGULATIONS);9. 《1970年最高法院法》(Supreme Court Act 1970);10.《1970年最高法院規(guī)則》(Supreme Court Rules 1970)。
(四)澳大利亞北部地區(qū)(NT)
1.《1996年證據(jù)法》(EVIDENCE ACT 1996);2. 《1995年宣誓法》(OATHS ACT 1867);3.1979、1993年《最高法院法》(Supreme Court Act);4.《澳大利亞北部地區(qū)最高法院規(guī)則》(Rules of Supreme Court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五)昆士蘭(Qld)
1. 《1977年證據(jù)法》;2. 《1867年宣誓法》(OATHS ACT 1867);3. 《1867年證據(jù)和開示法》(EVIDENCE AND DISCOVERY ACT 1867);4. 《1932年證據(jù)(文書認(rèn)證)法》[EVIDENCE (ATTESTATION OF DOCUMENTS) ACT 1932];5. 《1988年委托取證法》(EVIDENCE ON COMMISSION ACT 1988);6. 《1993年證據(jù)規(guī)則》(EVIDENCE REGULATIONS);7.1991、1995年《最高法院法》(Supreme Court Act);8. 《1900年最高法院規(guī)則》(Rules of Supreme Court 1900);9. 《1997年統(tǒng)一民事訴訟規(guī)則草案》[Uniform Civil Procedure Rules 1997(Consultation Draft)].(六)南澳大利亞(SA)
1.《1929年證據(jù)法》(EVIDENCE ACT 1929);2.《1928年(宣誓)證據(jù)法》[EVIDENCE (AFFIDAVITS) ACT, 1928];3.《1993年證據(jù)(出示書證)規(guī)則》[EVIDENCE (REPRODUCTION OF DOCUMENTS) REGULATIONS 1993];4.《1935年最高法院法》(Supreme Court Act 1935);5. 《1987年最高法院規(guī)則》(Supreme Court Rules 1987)。
(六)塔斯馬尼亞(Tas)
1.《1910年證據(jù)法》;2.《1991年證據(jù)(費(fèi)用)規(guī)則》[Evidence (Allowances) Regulations 1991];3.《1997年證據(jù)(指定詢問官)令》[Evidence (Prescribed Officers) Order 1997];4.《1999年(視聽)證據(jù)法》[EVIDENCE (AUDIO AND AUDIO VISUAL LINKS) ACT 1999];5.《1932年最高法院民事訴訟法》(Supreme Court Civil Procedure Act 1932);6.《1965年最高法院規(guī)則》(Rules of Supreme Court 1965);7.《1985年民事訴訟規(guī)則》(Civil Procedure Rules 1985)。
(七)維多利亞(Vic)
第7篇:證據(jù)法論文范文
眾所周知,我國現(xiàn)行的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關(guān)于證據(jù)的規(guī)定只有八條,包括:證據(jù)及其種類;證據(jù)收集的一般原則;運(yùn)用證據(jù)的原則;向單位和個人收集證據(jù);重證據(jù)、重調(diào)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原則;證人證言的審查判斷;證人的資格與義務(wù);證人及其近親屬的保護(hù)等。就以上八條規(guī)定的內(nèi)容而言,原則、籠統(tǒng)、操作性不夠強(qiáng)。由于它是歷年來辦案經(jīng)驗(yàn)的原則性總結(jié),加上當(dāng)時的立法背景,這些規(guī)定多數(shù)是一般性的原則規(guī)定,與辦案的實(shí)際過程和具體運(yùn)用存在著一定的距離。論文百事通新出臺的兩個規(guī)定,針對刑事證據(jù)的收集、審查、定案等訴訟各個環(huán)節(jié)的運(yùn)用,作了比較詳細(xì)的規(guī)定,一改過去的原則、籠統(tǒng)之弊。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對刑事訴訟法的修正和發(fā)展,是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前奏。
兩個規(guī)定的內(nèi)容完全符合中央關(guān)于司法改革的決定。2008年中央批轉(zhuǎn)中央政法委關(guān)于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完善刑事證據(jù)制度”,其具體內(nèi)容包括:明確證據(jù)審查和采信規(guī)則及不同訴訟程序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完善非法證據(jù)排除制度;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和保護(hù)制度,明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范圍和程序等。這些內(nèi)容在《辦理死刑案件的證據(jù)規(guī)定》和《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定》中都有所體現(xiàn),解決了我國刑事訴訟過程中期盼已久而尚未解決的問題。例如,審理死刑案件過程中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問題,對各種證據(jù)的審查判斷問題,間接證據(jù)的定案問題,還有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的確立,以及如何排除的問題,都很有針對性,都是對辦案中的實(shí)際困難的破解。這些做法完全體現(xiàn)了中央關(guān)于司法改革的基本精神和要求。
死刑案件人命關(guān)天,質(zhì)量問題特別重要。刑事錯案的發(fā)生主要是在事實(shí)認(rèn)定、證據(jù)審查的運(yùn)用方面出了差錯,并且絕大部分與刑訊逼供直接相關(guān)。兩個規(guī)定抓住這一核心問題,沿著刑事訴訟過程,從證據(jù)意識、證據(jù)觀念到證據(jù)的收集、固定、扣押、保管、移送、質(zhì)證、認(rèn)定等各個環(huán)節(jié),作了全面、系統(tǒng)的規(guī)定,只要辦案人員認(rèn)真地加以貫徹落實(shí),案件的質(zhì)量就有了保證。
第8篇:證據(jù)法論文范文
一、民事證明責(zé)任分配的理論學(xué)說
(一)規(guī)范說
民事證明責(zé)任分配歷來是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qū)的重要問題,學(xué)說眾多。長期以來占據(jù)通說地位的是德國學(xué)者羅森貝克(Rosenberg)在其博士論文《證明責(zé)任論》中系統(tǒng)提出的規(guī)范說。正如該論文副標(biāo)題所標(biāo)示的那樣,該學(xué)說立足于德國民法典和民事訴訟法典,通過對實(shí)體法結(jié)構(gòu)的分析,從法律規(guī)范相互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出發(fā)來尋找證明責(zé)任的分配規(guī)則。羅森貝克認(rèn)為,“相同的(實(shí)體法)法規(guī)范部分相互補(bǔ)充支持,部分又相互抵觸,而不同的(實(shí)體法)法規(guī)范彼此之間有沒有什么聯(lián)系,且在構(gòu)成要件及其后果方面相互排斥”[3](105)。與此相應(yīng),羅森貝克將實(shí)體法規(guī)范從整體上區(qū)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訴訟請求的基礎(chǔ),稱為“基礎(chǔ)規(guī)范”(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一個權(quán)利形成規(guī)范),另一類則是基礎(chǔ)規(guī)范的“相對規(guī)范”,可進(jìn)一步劃分為權(quán)利妨礙規(guī)范(該類規(guī)范從一開始就阻止權(quán)利形成規(guī)范效力的產(chǎn)生致其根本不能發(fā)揮效力,因而其法律后果也不發(fā)生)、權(quán)利消滅規(guī)范(該類規(guī)范只是后來才對抗權(quán)利形成規(guī)范,使其已經(jīng)產(chǎn)生的權(quán)利歸于消滅)、權(quán)利排除規(guī)范(又譯“權(quán)利受制規(guī)范”,該類規(guī)范賦予被要求者以形成權(quán),通過行使形成權(quán),被要求者得以排除針對其形成的權(quán)利的行使)。基于此,羅森貝克的證明責(zé)任分配原則便是:主張權(quán)利存在的當(dāng)事人,要證明產(chǎn)生權(quán)利的法律要件事實(shí);否認(rèn)權(quán)利的當(dāng)事人則要證明妨礙權(quán)利、消滅權(quán)利、排除權(quán)利的法律要件事實(shí)。需要注意的是,在其后來的論述中,又逐漸把權(quán)利排除規(guī)范納入到權(quán)利消滅規(guī)范之中[3](106~107、126),羅森貝克法規(guī)范說在德國、日本、臺灣等大陸法系尤其是德國法系國家和地區(qū)長期以來處于通說地位。但是經(jīng)過多年適用,對其不足(注釋1:主要體現(xiàn)為法規(guī)不適用原則的舛誤、權(quán)利形成要件和權(quán)利妨礙要件的區(qū)分存在困難、規(guī)范說的僵化等方面,參見姜世明:《新民事證據(jù)法論》(修訂二版),(臺北)學(xué)林文化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84頁;[日]高橋宏志:《民事訴訟法》,林劍鋒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1頁以下;陳剛:《現(xiàn)代證明責(zé)任理論的研究現(xiàn)狀》,載陳剛主編:《比較民事訴訟法》2000年卷,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頁以下。)也多有批判,修正規(guī)范理論和其他試圖取代規(guī)范說的理論先后涌出。
(二)修正規(guī)范理論及其他證明責(zé)任分配學(xué)說
由于萊波爾特(Leipold)、穆澤拉克(Musielak)、施瓦布(Schwab)、普維庭(Prütting)等人的學(xué)說在堅(jiān)持羅森貝克規(guī)范說的基礎(chǔ)上就其不足之處加以修正,所以都統(tǒng)稱為“修正規(guī)范理論”。[4](185)其中,針對規(guī)范說的法規(guī)不適用原則,萊波爾特的證明責(zé)任規(guī)范說(特別規(guī)范說)主張為了使裁判在真?zhèn)尾幻鳡顟B(tài)下成為可能,必須適用一種特別的法律規(guī)范,并將這種法律規(guī)范稱為證明責(zé)任規(guī)范;[5](172~173)[6](101)而穆澤拉克的消極規(guī)則說(消極性基本原則說)為了克服真?zhèn)尾幻鳎O(shè)計(jì)了不同于萊波爾特的一種消極性(否定性)的基本規(guī)則,即將真?zhèn)尾幻魍ㄟ^證明責(zé)任為中介虛擬為要件事實(shí)不存在,其反映的是訴訟上有關(guān)請求“被駁回”的范疇。[6](102)[5](173~174)施瓦布的操作規(guī)則說不承認(rèn)有所謂特別規(guī)則,而是將真?zhèn)尾幻鞯那樾沃苯优袛酁橐聦?shí)不存在,并將建立在此判斷基礎(chǔ)上的不適用法規(guī)則稱之為“操作規(guī)則”。普維庭的操作規(guī)則說也是以一操作規(guī)則克服真?zhèn)尾幻鳡顟B(tài),而此一規(guī)則是一種無視規(guī)范性質(zhì)的方法性工具,并充分意識到在證明責(zé)任分配基本原則外,還存有例外規(guī)則,認(rèn)為對于證據(jù)法問題也可以適用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等,主張將危險(xiǎn)領(lǐng)域、蓋然性等實(shí)質(zhì)觀點(diǎn)引入證據(jù)法規(guī)則的解釋之中,從而減輕規(guī)范說的僵化程度。[4](186)
除上述修正規(guī)范理論的觀點(diǎn)外,針對規(guī)范說不曾重視隱藏于法規(guī)范背后的實(shí)質(zhì)價值和實(shí)質(zhì)公平的缺陷,很多理論主張“全面放棄規(guī)范說的概念法學(xué)方法,不再堅(jiān)持統(tǒng)一抽象的形式標(biāo)準(zhǔn),而改從利益衡量、實(shí)質(zhì)公平、危險(xiǎn)領(lǐng)域及社會分擔(dān)等更為具體而多元的標(biāo)準(zhǔn),借以解決證明責(zé)任分配問題”[6](89)。在德國,皮特斯(Peters)的具體蓋然性理論主張應(yīng)在具體程序中,就個案的種種事實(shí)情況加以具體評價,根據(jù)與證明責(zé)任的蓋然性比例關(guān)系,由持較低蓋然性主張的當(dāng)事人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萊納克(Reinecke)的抽象蓋然性理論承認(rèn)規(guī)范說的證明責(zé)任分配基本原則,但是主張?jiān)趦?yōu)越蓋然性、證據(jù)可能性、消極效果等實(shí)質(zhì)理由存在時,完全可以背離基本原則。普霍斯(Prlss)危險(xiǎn)領(lǐng)域說主張,當(dāng)損害原因存在于加害人的危險(xiǎn)領(lǐng)域時,加害人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其所謂“危險(xiǎn)領(lǐng)域”,指的是為被害人所掌控的空間性、物體性的領(lǐng)域,即其所直接占有的動產(chǎn)與不動產(chǎn)的全部。德茲奇(Deutsch)的危險(xiǎn)提升說為解決在違反保護(hù)法規(guī)及其他含有抽象危險(xiǎn)要件的行為規(guī)范情形下因果關(guān)系證明困難的問題,主張當(dāng)損害發(fā)生是存在于此種行為規(guī)范的通常發(fā)生范圍時,應(yīng)由經(jīng)此行為之違反而致被損害法益危險(xiǎn)增加的當(dāng)事人就損害與此一行為規(guī)范的違反無關(guān)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瓦亨道夫(Wahrendorf)的多樣原則說(損害歸屬說)在否定規(guī)范說的同時,主張依照蓋然性原則、保護(hù)原則、保證原則、信賴原則、處罰原則、責(zé)任一致性原則以及危險(xiǎn)分配原則等公平正義加以衡量以確定證明責(zé)任的歸屬。(注釋2:此處德國學(xué)者諸多理論學(xué)說可參見姜世明:《新民事證據(jù)法論》(修訂二版),(臺北)學(xué)林文化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86頁以下。)在日本,石田穰的利益衡量說強(qiáng)勢背離規(guī)范說,主張法官進(jìn)行證明責(zé)任分配時,應(yīng)依次考慮立法者意思、當(dāng)事人與證據(jù)距離的遠(yuǎn)近、當(dāng)事人舉證的難易程度、事實(shí)存否的蓋然性高低誠信原則、禁反言原則等因素;新堂幸司的利益衡量說則不強(qiáng)調(diào)石田穰諸多考慮因素的順序性。龍奇喜助和松本博之的實(shí)體法趣旨說則主張以實(shí)體法趣旨和基于實(shí)體法的價值判斷為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證明責(zé)任的分配。(注釋3:此處日本學(xué)者諸多理論學(xué)說可參見[日]高橋宏志:《民事訴訟法》,林劍鋒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頁以下。)
但是綜合來看,雖然羅森貝克的規(guī)范說存在若干不足,但是經(jīng)修正規(guī)范理論的修正、補(bǔ)充和發(fā)展,其通說地位仍然難以動搖。德日學(xué)者的諸多反規(guī)范說觀點(diǎn)雖然各具洞見,但是卻缺乏法律安定性和訴訟可期待性,很難徹底取代規(guī)范說。但由此筆者認(rèn)為,我們完全可以在以規(guī)范說作為證明責(zé)任分配一般原則的整體構(gòu)架下,輔以其他各家學(xué)說來建構(gòu)證明責(zé)任分配體系。
二、民事證明責(zé)任分配的法條基礎(chǔ)
羅森貝克認(rèn)為,“《民法典》和《民事訴訟法》不僅僅以已存在的證明責(zé)任為前提條件,而且還以在爭訟雙方當(dāng)事人——原告和被告——之間的證明責(zé)任分配為前提條件”[3](95)。羅森貝克將實(shí)體法規(guī)范分成權(quán)利形成規(guī)范、權(quán)利妨礙規(guī)范、權(quán)利消滅規(guī)范(含權(quán)利排除規(guī)范),主張權(quán)利存在的當(dāng)事人,應(yīng)當(dāng)對滿足權(quán)利形成規(guī)范規(guī)范的要件事實(shí)加以證明,而主張權(quán)利妨礙或消滅的當(dāng)事人,則應(yīng)當(dāng)對權(quán)利妨礙規(guī)范或權(quán)利消滅規(guī)范所要求的要件事實(shí)加以證明。據(jù)此我們可以看出,規(guī)范說有效性的前提是實(shí)體法和程序法在立法技術(shù)上對于法條要件的證明責(zé)任意義有所注意[7](17),也就是說,證明責(zé)任分配的問題應(yīng)當(dāng)已在民法立法時為立法者所考慮及安排,因此證明責(zé)任分配自可從法律規(guī)范之間的關(guān)系中獲得。
以此標(biāo)準(zhǔn)來考察我國現(xiàn)行諸多民事法律,雖不盡理想,但大多數(shù)條文還是有邏輯性可循,尤其是作為民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法通則》、《擔(dān)保法》、《合同法》、《物權(quán)法》,其法律條文大多數(shù)都比較注意要件表述和邏輯關(guān)聯(lián)。一般而言,往往都是先對權(quán)利形成規(guī)范加以規(guī)定,權(quán)利妨礙規(guī)范則以但書形式或者單獨(dú)法條的形式加以規(guī)定,權(quán)利消滅規(guī)范與權(quán)利排除規(guī)范則往往也是以單獨(dú)法條的形式出現(xiàn)。例如就租賃合同而言,《合同法》第13章“租賃合同”第212條、第213條先就租賃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進(jìn)行了規(guī)定,隨后的第214條第1款后段通過但書的形式規(guī)定了租賃期限的權(quán)利妨礙規(guī)范,《民法通則》第12條、第13條關(guān)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規(guī)定也當(dāng)然是租賃合同的權(quán)利妨礙規(guī)范,《合同法》第227條、第232條、第233條則就租賃合同解除規(guī)定了權(quán)利消滅規(guī)范。再如就侵權(quán)行為請求權(quán)而言,《民法通則》第119條則是侵權(quán)責(zé)任請求權(quán)的權(quán)利形成規(guī)范。在《物權(quán)法》與《擔(dān)保法》中也不乏權(quán)利形成規(guī)范、權(quán)利妨礙規(guī)范與權(quán)利消滅規(guī)范的規(guī)定。可見,我國現(xiàn)行法律的法條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規(guī)范說的要求,規(guī)范說在我國法中有其適用空間。
除了實(shí)體法中三種規(guī)范的規(guī)定,在程序法中也對證明責(zé)任分配作了規(guī)定,《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以下簡稱《證據(jù)規(guī)定》)在第2條、第73條第2款等均為其適例。
三、民事證明責(zé)任分配的一般原則
如前所述,雖然羅森貝克的規(guī)范說存在不足,但是其通說地位至今無法撼動,而且從我國法條現(xiàn)狀來看,規(guī)范說也有其較大適用空間,即《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當(dāng)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zé)任提供證據(jù)”、《證據(jù)規(guī)定》第2條“(第1款)當(dāng)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jù)的事實(shí)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jù)的事實(shí)有責(zé)任提供證據(jù)加以證明”,“(第2款)沒有證據(jù)或者證據(jù)不足以證明當(dāng)事人的事實(shí)主張的,由負(fù)有舉證責(zé)任的當(dāng)事人承擔(dān)不利后果”及第73條第2款“因證據(jù)的證明力無法判斷導(dǎo)致爭議事實(shí)難以認(rèn)定的,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依據(jù)舉證責(zé)任分配的規(guī)則作出裁判”的規(guī)定,雖然頗為粗略和簡陋,但也算是初步勾勒了我國現(xiàn)行法中對證明責(zé)任分配一般原則。而且,《證據(jù)規(guī)定》關(guān)于證明責(zé)任分配實(shí)際上也是采納了規(guī)范說。(注釋4:參見張衛(wèi)平:《民事訴訟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頁。另,梁書文主編:《〈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新解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4頁則表示,總的來說,《證據(jù)規(guī)定》采用了以大陸法系法律要件分配說為主,英美法系利益衡量說為輔的分配規(guī)則。)因此筆者將羅森貝克證明責(zé)任分配原則作為筆者所欲構(gòu)建的民事證明責(zé)任分配體系的一般原則。也就是說,在我國民事訴訟中,證明責(zé)任分配一般原則即,主張權(quán)利存在的當(dāng)事人應(yīng)當(dāng)就其權(quán)利存在的要件事實(shí)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主張權(quán)利妨礙或者消滅的當(dāng)事人應(yīng)當(dāng)就權(quán)利妨礙或者消滅的要件事實(shí)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對于此一般原則,前文已有相關(guān)論述,此處不再重復(fù)。
四、民事證明責(zé)任分配的特殊規(guī)則
規(guī)范說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僵化性,面對社會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和時代形勢的變遷,的確存在力有不逮的情形;同時由于過于專注于法條本身的邏輯結(jié)構(gòu)與相互關(guān)系,對于實(shí)質(zhì)的公平正義,時常會有所背離。為修正和彌補(bǔ)規(guī)范說作為證明責(zé)任分配一般原則的不足,需要承認(rèn)證明責(zé)任分配特殊規(guī)則。所謂民事證明責(zé)任分配特殊規(guī)則,是在承認(rèn)并尊重證明責(zé)任分配一般原則的前提下,慮及某類型案件的特殊情況,在蓋然性理論、危險(xiǎn)領(lǐng)域理論、利益衡量理論等的指導(dǎo)下,對一般原則所進(jìn)行的調(diào)整。需注意的是,如果沒有對一般原則的承認(rèn),也就談不上特殊規(guī)則。《證據(jù)規(guī)定》第4條就某些特殊侵權(quán)訴訟規(guī)定了不同于證明責(zé)任分配一般原則的證明責(zé)任分配情形,內(nèi)容比較明確具體。而第7條規(guī)定的“在法律沒有具體規(guī)定,依本規(guī)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zé)任承擔(dān)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jù)公平原則和誠實(shí)信用原則,綜合當(dāng)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zé)任的承擔(dān)”,則就較為抽象,從法律安定性和訴訟可期待性的立場出發(fā),需要對該條加以類型化、具體化,否則法官會有過大的自由裁量權(quán),也容易對當(dāng)事人造成裁判突襲。
根據(jù)筆者的觀點(diǎn),證明責(zé)任分配特殊規(guī)則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是證明責(zé)任的轉(zhuǎn)換,這類規(guī)則對證明責(zé)任分配一般原則進(jìn)行了調(diào)整;二是雖然沒有直接調(diào)整一般原則的分配,但是在證據(jù)評價領(lǐng)域放寬了對證據(jù)和證明的要求(注釋5:與本文不同的是,臺灣學(xué)者姜世明在其所構(gòu)建的證明責(zé)任分配法則體系中,將與證明責(zé)任分配一般原則同為證明責(zé)任分配法則但卻相對的部分稱為“舉證責(zé)任減輕”。關(guān)于姜世明舉證責(zé)任減輕理論及其所構(gòu)建的證明責(zé)任分配法則體系,可參見姜世明:《新民事證據(jù)法論》(修訂二版),(臺北)學(xué)林文化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二編“舉證責(zé)任”;姜世明:“舉證責(zé)任分配法則之體系建構(gòu)”,收入氏著《舉證責(zé)任與真實(shí)義務(wù)》,(臺北)新學(xué)林文化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2006年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調(diào)整了當(dāng)事人證明責(zé)任的分擔(dān)。
(一)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
所謂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注釋6:有學(xué)者譯作“證明責(zé)任轉(zhuǎn)移”(參見[日]高橋宏志:《民事訴訟法》,林劍鋒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7頁),筆者此處不予采納,原因在于證明責(zé)任轉(zhuǎn)移這一術(shù)語會給人造成本來由甲方當(dāng)事人承擔(dān)的證明責(zé)任轉(zhuǎn)移給乙方當(dāng)事人承擔(dān)的誤會。),指的是法院對于個案或者經(jīng)由固定性實(shí)務(wù)見解就證明責(zé)任分配一般規(guī)則(法則)予以背反的證據(jù)法則。[4](218)亦即,在這種場合,證明責(zé)任分配一般原則所確定的應(yīng)當(dāng)由一方當(dāng)事人承擔(dān)的證明責(zé)任被免除,改由對方當(dāng)事人對本來的證明責(zé)任對象從相反的方向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8](247)可見,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的前提是對規(guī)范說的證明責(zé)任分配一般原則的承認(rèn),如果不存在這個一般原則,也就沒有“轉(zhuǎn)換”的存在。
一般而言,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包含兩種情形(注釋7:對于“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這一術(shù)語的內(nèi)容,德國有學(xué)者主張只有文章下述第二種情形屬于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而不認(rèn)可法定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參見[德]普維庭、陳剛:“關(guān)于證明責(zé)任的話題”,載陳剛主編:《比較民事訴訟法》2001年卷~2002年卷,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頁;姜世明:《新民事證據(jù)法論》(修訂二版),(臺北)學(xué)林文化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9頁。本文此處采廣義觀點(diǎn)。),一種情形是法律(實(shí)體法或者程序法)就某類型案件明文規(guī)定不同于證明責(zé)任分配一般原則的證明責(zé)任承擔(dān)方法,可以稱之為法定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也可以稱為法律對證明責(zé)任分配的特殊規(guī)定,或者直接稱為證明責(zé)任倒置。就我國而言,如前所述,尤其自《證據(jù)規(guī)定》出臺以來,可以認(rèn)為我國已采納規(guī)范說作為證明責(zé)任分配一般原則,在此基礎(chǔ)上,《證據(jù)規(guī)定》第4條所規(guī)定的某些特殊侵權(quán)訴訟的證明責(zé)任分配便可以視為法定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
另一種情形則是在法律沒有相關(guān)規(guī)定的情形下,法院根據(jù)某一類型案件的特殊情形,考慮到公平正義等因素,而對證明責(zé)任分配一般原則予以改變,可以稱之為非法定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或者稱為實(shí)務(wù)認(rèn)可的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這一類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在德國實(shí)務(wù)上已是蔚為大觀。[4](219~220)此外,德國尚且承認(rèn)當(dāng)事人證據(jù)契約對證明責(zé)任分配的特殊規(guī)定,這也是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的一種形式。
(二)證據(jù)評價領(lǐng)域的特殊規(guī)則
除了上述通過證明責(zé)任轉(zhuǎn)換來修正證明責(zé)任分配一般原則之外,在一些特定場合,雖然不需要改變一般原則在當(dāng)事人間對證明責(zé)任的分配,但是可以通過在證據(jù)評價領(lǐng)域進(jìn)行一些改變來避免由于貫徹一般原則而帶來的實(shí)質(zhì)不公正。常見的證據(jù)評價特殊規(guī)則主要包括如下一些方法。
1、法律上的事實(shí)推定。作為法律推定的一種形式,法律上的事實(shí)推定指的是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從已知事實(shí)(前提事實(shí))推論未知事實(shí)(結(jié)論事實(shí))的證明手段。法律上的事實(shí)推定并沒有改變一般原則下的證明責(zé)任分配,只是就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的一方當(dāng)事人所能證明的法律規(guī)定所要求的前提事實(shí)來推斷未知的要件事實(shí),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當(dāng)事人的證明難度,并且使證明必要性轉(zhuǎn)移到對方當(dāng)事人,這是在證據(jù)評價領(lǐng)域?qū)Ρ苊庖聦?shí)真?zhèn)尾幻魉龅呐Α!蹲C據(jù)規(guī)定》第9條第(三)項(xiàng)規(guī)定在可以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推定出另一事實(shí)時,免除負(fù)擔(dān)證明責(zé)任當(dāng)事人的證明責(zé)任,這就是對法律上的事實(shí)推定的規(guī)定。當(dāng)然反證是可以推定事實(shí)的。
2、事實(shí)推定。法官基于職務(wù)上的需要根據(jù)一定的經(jīng)驗(yàn)法則,就已知事實(shí)為基礎(chǔ)進(jìn)而推論出未知事實(shí)的證明手段,就是事實(shí)推定。事實(shí)推定同樣沒有改變證明責(zé)任分配,也只是就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的一方當(dāng)事人所能證明的一些與案件有關(guān)的事實(shí)來推斷未知的要件事實(shí),其功能與法律上的事實(shí)推定相仿。《證據(jù)規(guī)定》第9條第(三)項(xiàng)也同樣規(guī)定了事實(shí)推定:在可以從已知事實(shí)推定出另一事實(shí)時,免除負(fù)擔(dān)證明責(zé)任當(dāng)事人的證明責(zé)任(注釋8:由于事實(shí)推定比起法律上的事實(shí)推定來,其賦予法官更為寬泛的自由裁量權(quán),因此對司法解釋的這種自我賦權(quán)規(guī)定,考慮到我國司法現(xiàn)狀,有觀點(diǎn)表示憂慮。參見肖建華主編:《民事證據(jù)法理念與實(shí)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頁。)。
3、表見證明。表見證明是法官在訴訟證明過程中運(yùn)用經(jīng)驗(yàn)法則從已知事實(shí)推論未知事實(shí)的證明手段,其運(yùn)用要具備經(jīng)驗(yàn)法則和典型事態(tài)經(jīng)過兩個要件(注釋9:典型事態(tài)經(jīng)過,指的是“在經(jīng)驗(yàn)上依初步表見(證明)可認(rèn)為某特定原因?qū)⒃斐赡程囟ńY(jié)果者”,參見姜世明:《新民事證據(jù)法論》(修訂二版),(臺北)學(xué)林文化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2頁。)。表見證明是在證據(jù)評價領(lǐng)域通過運(yùn)用具有高度蓋然性的經(jīng)驗(yàn)法則來認(rèn)定事實(shí),從而減輕負(fù)擔(dān)證明責(zé)任的當(dāng)事人的證明難度、免除其證明責(zé)任并使證明必要性在雙方當(dāng)事人之間進(jìn)行轉(zhuǎn)移。《證據(jù)規(guī)定》第9條第(三)項(xiàng)規(guī)定,在可以從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法則推定出另一事實(shí)時,免除負(fù)擔(dān)證明責(zé)任當(dāng)事人的證明責(zé)任。
4、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降低。我國內(nèi)地民事訴訟證明標(biāo)準(zhǔn)與刑事訴訟證明標(biāo)準(zhǔn)基本同一,都是要求客觀真實(shí),但是基于民事訴訟的私權(quán)糾紛性,在某些案件中完全可以適當(dāng)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可以要求高度蓋然性或者較高的蓋然性,而不必苛求客觀真實(shí)性。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方法也有很多,前述兩種推定和經(jīng)驗(yàn)法則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看做是降低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方法。
5、不負(fù)證明責(zé)任一方當(dāng)事人的事案解明義務(wù)。當(dāng)事人的事案解明義務(wù)是在修正辯論主義之后,面對真實(shí)義務(wù)、陳述義務(wù)以及誠信原則的要求而逐漸產(chǎn)生和發(fā)展,其含義是指當(dāng)事人為厘清事實(shí)負(fù)有就所有對其有利與不利的事實(shí)的陳述義務(wù),以及為厘清事實(shí)而提出相關(guān)證據(jù)資料或忍受勘驗(yàn)的義務(wù)。[9](110)而對于不負(fù)證明責(zé)任一方當(dāng)事人而言,其對于對方當(dāng)事人負(fù)證明責(zé)任的事實(shí)是承擔(dān)一般的事案解明義務(wù)還是限定的事案解明義務(wù),尚有爭論。(注釋10:主張不負(fù)證明責(zé)任一方當(dāng)事人要承擔(dān)一般事案解明義務(wù)的觀點(diǎn)主要可參見許士宦:“不負(fù)舉證責(zé)任當(dāng)事人之事案解明義務(wù)”,收入氏著《證據(jù)搜集與紛爭解決》,(臺北)新學(xué)林文化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40頁以下;主張不負(fù)證明責(zé)任一方當(dāng)事人要承擔(dān)一般事案解明義務(wù)的觀點(diǎn)主要可參見姜世明:《新民事證據(jù)法論》(修訂二版),(臺北)學(xué)林文化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6頁以下;另可參見黃國昌:“事證開示義務(wù)與舉證責(zé)任”,收入氏著《民事訴訟理論之新開展》,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頁以下。)筆者認(rèn)為,就避免真?zhèn)尾幻髑樾巍⒁淮涡越鉀Q糾紛的立場而言,在嚴(yán)格要件和擴(kuò)大界限的前提下,應(yīng)當(dāng)認(rèn)可不負(fù)證明責(zé)任一方當(dāng)事人的一般事案解明義務(wù),從而緩解對方當(dāng)事人的證明困難。
第9篇:證據(jù)法論文范文
關(guān) 鍵 詞 :數(shù)字化 數(shù)字證據(jù) 視聽資料 書證 數(shù)字證據(jù)規(guī)則
包括法律在內(nèi)的社會科學(xué)往往隨著自然科學(xué)的發(fā)展,在對自然科學(xué)所引導(dǎo)的社會關(guān)系進(jìn)行調(diào)整的同時獲得了自身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與完善。從法律縱向發(fā)展歷史來看,每次重大技術(shù)進(jìn)步都會在刺激生產(chǎn)力飛躍提升的同時促進(jìn)法律進(jìn)步,工業(yè)革命時代如此,信息革命時代也是如此。數(shù)字技術(shù)的迅速發(fā)展,給法律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這其中首先是實(shí)體法的擴(kuò)展與創(chuàng)新,隨之而來的則是程序法的修正。但是由于目前研究尚處于初始狀態(tài),許多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數(shù)字技術(shù)對法律提出的挑戰(zhàn),體現(xiàn)于合同法、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行政法的一些程序流程中,我國在一些實(shí)體法中已開始逐漸解決,但在程序法上仍未開始這方面的嘗試。在當(dāng)前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大量技術(shù)含量極高的案例中,作為程序的核心——證據(jù)制度,不論是民事,還是刑事、行政證據(jù)制度在面對新問題時都處于一種尚付闕如的尷尬境地,這種尷尬在目前沸沸揚(yáng)揚(yáng)的新浪與搜狐的訴訟之爭中又一次被重演。不僅當(dāng)前制定證據(jù)法的學(xué)者們所提出的數(shù)稿中有的根本就沒有此方面的規(guī)定,即使作為對以往司法實(shí)踐的總結(jié)與最新證據(jù)規(guī)則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對數(shù)字技術(shù)引發(fā)出的愈來愈多的問題也依然未給予應(yīng)有的注意。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數(shù)字技術(shù)環(huán)境下對證據(jù)制度進(jìn)行再研究(注:數(shù)字證據(jù)可以出現(xiàn)于三大程序法中,本文針對民事、行政、刑事程序法中的數(shù)字證據(jù)問題的共性進(jìn)行討論,并不涉及基于不同程序性質(zhì)而產(chǎn)生的細(xì)節(jié)問題。同時,我們無意在此對我國原有證據(jù)體系的分類模式與合理性等進(jìn)行論證,那并不是本文所主要研究的問題。)。
一、數(shù)字證據(jù)概念評析
使用精確的概念,進(jìn)行內(nèi)涵的準(zhǔn)確界定與外延的清晰延展,對于一個科學(xué)體系的建立極具方法論意義,并且也符合社會學(xué)方法的規(guī)則,因此,建立一個體系首先進(jìn)行的便應(yīng)是概念的歸納。同時,一個精確的概念必須能夠抽象歸納出所有客體的本質(zhì)共性,必須能夠把表現(xiàn)同性質(zhì)的所有現(xiàn)象全部容納進(jìn)去。對數(shù)字證據(jù)進(jìn)行概念歸納,基于其鮮明的技術(shù)特征,在歸納時要回歸到數(shù)字技術(shù)層面,在其所使用的數(shù)字技術(shù)與存在的社會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結(jié)合中尋找恰當(dāng)?shù)耐黄泣c(diǎn)。
關(guān)于數(shù)字證據(jù)的概念,在國際上至今未有定論,如computer evidence(計(jì)算機(jī)證據(jù))、electronic evidence(電子證據(jù))、digital evidence(數(shù)字證據(jù))都具有其使用者。我國采取數(shù)字證據(jù)概念的大多是IT業(yè)界,法律學(xué)者采用的概念主要是計(jì)算機(jī)證據(jù)與電子證據(jù),進(jìn)而在這些概念基礎(chǔ)上分析證據(jù)的性質(zhì)、效力、類型等(注:還有的學(xué)者在論述中并未對其使用的概念進(jìn)行定義,如吳曉玲發(fā)表于《計(jì)算機(jī)世界》1999年第7期的《論電子商務(wù)中的電子證據(jù)》一文中使用電子證據(jù),游偉、夏元林發(fā)表于《法學(xué)》2001年第3期的《計(jì)算機(jī)數(shù)據(jù)的證據(jù)價值》一文中使用計(jì)算機(jī)數(shù)據(jù)電訊。呂國民發(fā)表于《法律科學(xué)》2001年第6期的《數(shù)據(jù)電文的證據(jù)問題及解決方法》一文所使用的數(shù)據(jù)電文等都未進(jìn)行明確的法律上的界定。)。這些概念以及在此基礎(chǔ)上的分析存在一些問題,之所以如此,或者是因?yàn)閱渭冏⒅貙ι鐣?jīng)濟(jì)層面的考查卻忽略了對技術(shù)層面的透徹分析,或者是因?yàn)殡m進(jìn)行了技術(shù)的分析,但卻未深入到進(jìn)行法律歸納所需要的足夠程度。因而有必要在與這些概念、定義的多維比較中分析數(shù)字證據(jù)概念的內(nèi)涵與外延。
(一)數(shù)字證據(jù)與計(jì)算機(jī)證據(jù)、電子證據(jù)概念的比較首先必須明確的是,雖然各個概念所使用的語詞不同,但在內(nèi)涵上,計(jì)算機(jī)證據(jù)、電子證據(jù)都是針對不同于傳統(tǒng)的數(shù)字化運(yùn)算過程中產(chǎn)生的證據(jù),在外延上一般囊括數(shù)字化運(yùn)算中產(chǎn)生的全部信息資料。不過,計(jì)算機(jī)證據(jù)與電子證據(jù)這兩個概念并不妥貼,不能充分表現(xiàn)該種證據(jù)的本質(zhì)內(nèi)涵,由此而容易導(dǎo)致概念在外延上不能涵蓋該種證據(jù)的全部形態(tài)。
1.“計(jì)算機(jī)證據(jù)”概念。有人認(rèn)為,“計(jì)算機(jī)證據(jù),是指在計(jì)算機(jī)或計(jì)算機(jī)系統(tǒng)運(yùn)行過程中產(chǎn)生的以其記錄的內(nèi)容來證明案件事實(shí)的電磁記錄物”。[1]采取“計(jì)算機(jī)證據(jù)”概念來表述數(shù)字化過程中形成的證據(jù)具有一定合理性,因?yàn)橛?jì)算機(jī)及以計(jì)算機(jī)為主導(dǎo)的網(wǎng)絡(luò)是數(shù)字化運(yùn)算的主要設(shè)備,并且目前數(shù)字化信息也大多存儲于電磁性介質(zhì)之中。從數(shù)字化所依靠的設(shè)備的角度來歸納此類證據(jù)的共性,在外延上能夠涵蓋絕大多數(shù)此類證據(jù)。然而,雖然計(jì)算機(jī)設(shè)備是當(dāng)前數(shù)字化處理的主要設(shè)備,計(jì)算機(jī)中存儲的資料也是當(dāng)前此類證據(jù)中的主要部分,但是進(jìn)行數(shù)字化運(yùn)算處理的計(jì)算機(jī)這一技術(shù)設(shè)備并不是數(shù)字化的唯一設(shè)備,例如掃描儀、數(shù)碼攝像機(jī)這些設(shè)備均是數(shù)字化運(yùn)算不可或缺的設(shè)備,但并不能認(rèn)為這些也屬于計(jì)算機(jī)之列。從國外立法來看,沒有國家采取computerevidence,采用這種概念的學(xué)者在論述中也往往又兼用了其他的概念。迪爾凱姆認(rèn)為,研究事物之初,要從事物的外形去觀察事物,這樣更容易接觸事物的本質(zhì),但卻不可以在研究結(jié)束后,仍然用外形觀察的結(jié)果來解釋事物的實(shí)質(zhì)。所以,“計(jì)算機(jī)證據(jù)”概念從事物外形上進(jìn)行定義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計(jì)算機(jī)證據(jù)”概念未能歸納出數(shù)字化過程中形成的可以作為證明案件事實(shí)情況的證據(jù)共性,不能夠涵蓋數(shù)字化過程中產(chǎn)生的全部的信息資料,而且在法律上也不能對將來出現(xiàn)的證據(jù)類型預(yù)留出彈性空間。
2.“電子證據(jù)”概念。目前,采用“電子證據(jù)”者甚眾,但對電子證據(jù)的具體含義則各有不同表述。有人認(rèn)為:“電子證據(jù),又稱為計(jì)算機(jī)證據(jù),是指在計(jì)算機(jī)或計(jì)算機(jī)系統(tǒng)運(yùn)行過程中產(chǎn)生的以其記錄的內(nèi)容來證明案件事實(shí)的電磁記錄物。”[2]有人認(rèn)為:“電子證據(jù),是指以數(shù)字的形式在計(jì)算機(jī)存儲器或外部儲存的介質(zhì)中,能夠證明案件真實(shí)情況的數(shù)據(jù)或信息。”[3]“電子證據(jù)是指以儲存的電子化信息資料來證明案件真實(shí)情況的電子物品或電子記錄,它包括視聽資料和電子證據(jù)。”[4]加拿大明確采用了電子證據(jù)概念,在《統(tǒng)一電子證據(jù)法》(Uniform Electronic Evidence Act)的定義條款中規(guī)定:“電子證據(jù),指任何記錄于或產(chǎn)生于計(jì)算機(jī)或類似設(shè)備中的媒介中的資料,其可以為人或計(jì)算機(jī)或相關(guān)設(shè)備所讀取或接收。”[5]
綜合起來,各種電子證據(jù)的定義主要有兩種:第一,狹義的電子證據(jù),等同于計(jì)算機(jī)證據(jù)概念,即自計(jì)算機(jī)或計(jì)算機(jī)外部系統(tǒng)中所得到的電磁記錄物,此種內(nèi)涵過于狹小,不能涵蓋數(shù)字化過程中生成的全部證據(jù),不如第二種定義合理。第二,廣義上的電子證據(jù),包括視聽資料與計(jì)算機(jī)證據(jù)兩種證據(jù),在內(nèi)容上包含了第一種定義,并且還包括我國訴訟法中原有的視聽資料。但我們認(rèn)為,這些定義中不僅所使用的“電子”一詞不妥,而且所下定義亦為不妥,理由如下:第一,將電子證據(jù)或者計(jì)算機(jī)證據(jù)定性為電磁記錄物未免過于狹隘。雖然數(shù)字設(shè)備的整個運(yùn)作過程一般由電子技術(shù)操控,各個構(gòu)件以及構(gòu)件相互之間以電子運(yùn)動來進(jìn)行信息傳輸,但是仍然不可以認(rèn)為該種證據(jù)即為自電子運(yùn)動過程中得到的資料。美國《統(tǒng)一電子交易法》2 (5)中規(guī)定:“電子(electronic),是指含有電子的、數(shù)據(jù)的、磁性的、光學(xué)的、電磁的或類似性能的相關(guān)技術(shù)。”擴(kuò)大解釋了電子的語詞內(nèi)涵,使用各種不同的技術(shù)載體來表達(dá)擴(kuò)大的電子語義,已經(jīng)失去了“電子”一詞的原義,原本意義上的電子只是其使用的“電子”概念中的一種技術(shù)而已,從而能夠涵蓋大多數(shù)此類證據(jù)。不過,既然如此,還不如直接使用能夠涵蓋這些技術(shù)特性的“數(shù)字”概念,在工具價值方面更有可取之處。加拿大《統(tǒng)一電子證據(jù)法》解釋中之所以采取“電子”,“因?yàn)樾畔橛?jì)算機(jī)或類似設(shè)備所記錄或存儲”,但這個理由并不充分。并且接下來又承認(rèn)有些數(shù)字信息(digital information)未涵蓋于本法,因?yàn)橛衅渌姆蛇M(jìn)行調(diào)整。第二,電子證據(jù)概念不能揭示此類證據(jù)的本質(zhì)特征。電子運(yùn)動只是數(shù)字化運(yùn)算的手段,而非本質(zhì),并且也并不是所有數(shù)字設(shè)備的運(yùn)算全都采取電子運(yùn)動手段。進(jìn)行數(shù)字化運(yùn)算的計(jì)算機(jī)設(shè)備及其他數(shù)字設(shè)備的共同之處在于這些設(shè)備的運(yùn)算均采取數(shù)字化方式,而非在于均采取電子運(yùn)動手段。第三,不論是將視聽資料這種已存的證據(jù)類型納入電子證據(jù)中,還是將電子證據(jù)納入視聽資料中,都會致使“電子證據(jù)”與我國訴訟法中的“視聽資料”相混淆,而此類證據(jù)與視聽資料證據(jù)的本質(zhì)共性并不相同。視聽資料主要為錄音、錄像資料,其信息的存儲以及傳輸?shù)纫捕疾扇‰娮舆\(yùn)動手段。錄音、錄像采取模擬信號方式,其波形連續(xù);而在計(jì)算機(jī)等數(shù)字設(shè)備中,以不同的二進(jìn)制數(shù)字組合代表不同的脈沖,表達(dá)不同信號,信息的存儲、傳輸采取數(shù)字信號,其波形離散、不連續(xù)。二者的實(shí)現(xiàn)、表現(xiàn)、存儲、轉(zhuǎn)化都不相同。傳統(tǒng)的電話、電視、錄音、錄像等都采取模擬信號進(jìn)行通訊,這是視聽資料的共性,而計(jì)算機(jī)與網(wǎng)絡(luò)信息技術(shù)則采取數(shù)字化方式通信,這是數(shù)字化運(yùn)算中生成的證據(jù)的共性,兩者不同,不應(yīng)混淆。
可見,狹義上的電子證據(jù)在外延上只能容納數(shù)字化過程中產(chǎn)生的部分證據(jù),失之過狹;廣義上的電子證據(jù)確實(shí)能夠在外延上容納數(shù)字化過程中產(chǎn)生的全部證據(jù),但卻失之過寬,如將視聽資料與計(jì)算機(jī)證據(jù)這兩種差別極大的證據(jù)容于同一種證據(jù)類型中,將不得不針對兩種證據(jù)進(jìn)行規(guī)則的制定,從而導(dǎo)致同種證據(jù)類型的證據(jù)規(guī)則不相統(tǒng)一,很難建立起一個和諧一致的體系。
(二)數(shù)字證據(jù)概念的內(nèi)涵與外延我們認(rèn)為,數(shù)字證據(jù)就是信息數(shù)字化過程中形成的以數(shù)字形式讀寫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shí)情況的資料。這里使用的“數(shù)字”(digital,digits pl.)與日常用語中的“數(shù)字”語義并不相同,雖并不如“電子”更為人們熟悉和容易理解,但重要的是根據(jù)科學(xué)的需要和借助于專門術(shù)語的表達(dá),使用科學(xué)的概念來清晰地定義相關(guān)事物,況且“數(shù)字”概念在現(xiàn)今信息時代也并不是一個新概念,早已為人們廣泛接受和使用。現(xiàn)代計(jì)算機(jī)與數(shù)字化理論認(rèn)為,數(shù)是對世界真實(shí)和完全的反映,是一種客觀存在。人類基因組的破譯說明,甚至代表人類文明最高成就的人自身也可以數(shù)字化。[6]來勢洶涌的全球信息化潮流實(shí)際上就是對事物的數(shù)字化(digitalization)處理過程,區(qū)別于紙質(zhì)信件、電話、傳真等傳統(tǒng)信息交流方式,這種采用新的信息處理、存儲、傳輸?shù)臄?shù)字方式在現(xiàn)代社會包括日常交往與商業(yè)貿(mào)易中逐步建立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毋庸置疑的是,數(shù)字技術(shù)還會不斷地發(fā)展,因此在進(jìn)行法律調(diào)整之時就更不能限定所使用的技術(shù)與存儲的介質(zhì),從而在法律上為技術(shù)的發(fā)展留存一個寬松的空間。
1.數(shù)字證據(jù)有其數(shù)字技術(shù)性。信息數(shù)字化處理過程中,數(shù)字技術(shù)設(shè)備以"0"與"1" 二進(jìn)制代碼進(jìn)行數(shù)值運(yùn)算與邏輯運(yùn)算,所有的輸入都轉(zhuǎn)換為機(jī)器可直接讀寫而人并不能直接讀寫的"0"、"1"代碼在數(shù)字技術(shù)設(shè)備中進(jìn)行運(yùn)算,然后再將運(yùn)算結(jié)果轉(zhuǎn)換為人可讀的輸出。數(shù)字證據(jù)以數(shù)字化為基礎(chǔ),以數(shù)字化作為區(qū)別于其他證據(jù)類型的根本特征。數(shù)字證據(jù)具有依賴性,其生成、存儲、輸出等都需借助于數(shù)字化硬件與軟件設(shè)備;具有精確性,數(shù)字證據(jù)能準(zhǔn)確地再現(xiàn)事實(shí);具有易篡改性,數(shù)字化技術(shù)特性決定了數(shù)字資料可以方便地進(jìn)行修正、補(bǔ)充,但這些優(yōu)點(diǎn)在數(shù)字資料作為證據(jù)使用時成為缺點(diǎn),使其極易被篡改或銷毀,從而降低了數(shù)字證據(jù)的可靠性,這個特點(diǎn)也決定了在對數(shù)字證據(jù)進(jìn)行規(guī)則的制定時應(yīng)當(dāng)切實(shí)保障其真實(shí)性。 SWGDE(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on DigitalEvidence)與IOD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n Digital alvidence)在1999年在倫敦舉辦的旨在為各國提供數(shù)字證據(jù)交換規(guī)則的會議IHCFC(International Hi-Tech Crime and Forensics Conference)上提交了一份名為《數(shù)字證據(jù):標(biāo)準(zhǔn)與原則》的報(bào)告,對數(shù)字證據(jù)從技術(shù)方面進(jìn)行了定義,“數(shù)字證據(jù)是指以數(shù)字形式存儲或傳輸?shù)男畔⒒蛸Y料”,[7]在接下來的規(guī)則中則重點(diǎn)闡述了如何對數(shù)字證據(jù)的真實(shí)性進(jìn)行保障。
2.數(shù)字證據(jù)有其外延廣泛性。數(shù)字證據(jù)概念在外延上既可以容納目前以數(shù)字形式存在的全部證據(jù),又具有前瞻性,可以容納以后隨著技術(shù)與社會發(fā)展而出現(xiàn)的此類證據(jù)。數(shù)字證據(jù)可以產(chǎn)生于電子商務(wù)中,也可以產(chǎn)生于平時的日常關(guān)系中,表現(xiàn)為電子郵件、機(jī)器存儲的交易記錄、計(jì)算機(jī)中的文件、數(shù)碼攝影機(jī)中存儲的圖片等。從美國FBI目前的犯罪執(zhí)法中可以看到,現(xiàn)在專家越來越喜歡用數(shù)字技術(shù)對一些其他證據(jù)進(jìn)行處理,例如用AvidXpress視頻編輯系統(tǒng)、Dtective圖像增強(qiáng)處理軟件對取得的錄像進(jìn)行處理,并且這種處理也往往得到法庭的承認(rèn)。這種對原始證據(jù)進(jìn)行數(shù)字技術(shù)加工后形成的證據(jù)也可看作是一種傳來數(shù)字證據(jù),即形成了一種證據(jù)類型向另一種證據(jù)類型的轉(zhuǎn)化,例如對我國視聽資料中的錄音、錄像進(jìn)行數(shù)字處理后可以認(rèn)為是數(shù)字證據(jù),適用數(shù)字證據(jù)規(guī)則。這一點(diǎn)很重要,因?yàn)椴煌淖C據(jù)類型往往適用不同的證據(jù)規(guī)則,從而在真實(shí)性等方面可能作出不同的認(rèn)定。
數(shù)字證據(jù)一般有兩種存在形式:一是機(jī)器中存儲的機(jī)器可讀資料,二是通過輸出設(shè)備輸出的人可讀資料,如顯示設(shè)備顯示出來或者打印設(shè)備打印出來的資料。前種作為數(shù)字證據(jù)毫無疑問,而后者從表面看來似乎可以認(rèn)定為書證。其實(shí),此種人可讀的輸出資料仍然屬于數(shù)字證據(jù),因?yàn)檫@些資料來源于數(shù)字化設(shè)備,是在設(shè)備運(yùn)行過程中取得的,其產(chǎn)生完全依賴于前者,人可讀的資料是由機(jī)器可讀的資料經(jīng)過一個轉(zhuǎn)化過程而取得的,兩種資料在內(nèi)容上保持了一致性,具有同質(zhì)性,只是表現(xiàn)方式不同而已。后者的真實(shí)性依賴于前者,在如何確保真實(shí)性、合法性等規(guī)則上,應(yīng)適用數(shù)字證據(jù)的規(guī)則,卻不可以因?yàn)槠浔憩F(xiàn)為傳統(tǒng)的紙面形式就認(rèn)為是書證,從而適用書證規(guī)則。
二、將數(shù)字證據(jù)納入我國證據(jù)體系具有必要性與可行性
數(shù)字技術(shù)推動出現(xiàn)的社會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提出新的要求,體現(xiàn)于法律之上,在實(shí)體法上表現(xiàn)為,要求更新確認(rèn)這種新技術(shù)指示的新類型社會關(guān)系當(dāng)事人間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在程序法上表現(xiàn)為,當(dāng)這種社會關(guān)系的當(dāng)事人因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發(fā)生糾紛時,應(yīng)當(dāng)存在與之相適應(yīng)的相關(guān)程序,或者對已有程序進(jìn)行完善,能夠滿足這種糾紛不同以往而與其技術(shù)特征相適應(yīng)的要求。而在程序法證據(jù)制度上的一個基本表現(xiàn)就是,要求數(shù)字化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一些數(shù)據(jù)資料等能夠納入到證據(jù)體系中,得到證據(jù)規(guī)則的認(rèn)可,能夠被法庭接受成為證明案件事實(shí)的證據(jù)。
雖然數(shù)字證據(jù)并不單純只是在電子商務(wù)關(guān)系中產(chǎn)生,其還可在其他社會關(guān)系中產(chǎn)生(注:以數(shù)字化設(shè)備為基礎(chǔ)而生成的數(shù)字形式讀寫的證據(jù)均可認(rèn)為是數(shù)字證據(jù),其可以為民事程序法上的證據(jù),也可以為刑事、行政程序法上的證據(jù)。不過,在現(xiàn)階段,電子商務(wù)關(guān)系中產(chǎn)生的這類證據(jù)的數(shù)量多于其他類型社會關(guān)系,但不可以認(rèn)為數(shù)字證據(jù)即為電子商務(wù)中產(chǎn)生的證據(jù),例如內(nèi)部局域網(wǎng)、個人計(jì)算機(jī)存儲的資料也可成為數(shù)字證據(jù)。),但數(shù)字證據(jù)問題主要是出于電子商務(wù)的飛速發(fā)展而提出。出于電子商務(wù)交易追求交易的快速便捷、無紙化(paperless trading)流程,在很多交易過程中很少有甚至根本就沒有任何紙質(zhì)文件出現(xiàn),電子商務(wù)交易中所存在的與交易相關(guān)的資料可能完全是以數(shù)字化形式存在于計(jì)算機(jī)等存儲設(shè)備中。一旦產(chǎn)生糾紛,如果在程序法上不承認(rèn)數(shù)字證據(jù)的證據(jù)力,當(dāng)事人將沒有任何證據(jù)來支持自己的權(quán)利主張,無法得到法律救濟(jì),商人對電子交易就難以產(chǎn)生依賴感,不利于電子商務(wù)的發(fā)展。
自20世紀(jì)90年代起,EDI數(shù)據(jù)交換方式便以其便捷、高效、準(zhǔn)確而備受青睞。一些重要的國際組織對電子商務(wù)等進(jìn)行大量的立法工作,歐美各國在實(shí)體上早已承認(rèn)以數(shù)據(jù)電文方式訂立合同、申報(bào)納稅與以信件、電報(bào)、傳真等傳統(tǒng)方式具有相同效力,在程序法上也作了相應(yīng)的規(guī)定。美國《聯(lián)邦證據(jù)規(guī)則》通過重申現(xiàn)行判例和成文法的形式肯定了數(shù)據(jù)電文無論是人工做成的還是計(jì)算機(jī)自動錄入的都可作為訴訟證據(jù)。英國1968年《民事證據(jù)法》規(guī)定,在任何民事訴訟程序中,文書內(nèi)容只要符合法庭規(guī)則就可被接受成為證明任何事實(shí)的證據(jù),而不論文書的形式如何。 [8]在1988年修正《治安與刑事證據(jù)法》(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也作出了類型的規(guī)定。加拿大通過R.V.McMullen (Ont.C.A.,1979)一案確立了新證據(jù)在普通法上的相關(guān)規(guī)則。聯(lián)合國貿(mào)法會在《電子商務(wù)示范法》中規(guī)定,“不得僅僅以某項(xiàng)信息采用數(shù)據(jù)電文形式為理由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執(zhí)行性”,又承認(rèn)了以數(shù)據(jù)電文方式訂立的合同的有效性,并且認(rèn)為,在一定情況下數(shù)據(jù)電文滿足了對原件的要求,在訴訟中不得否認(rèn)其為原件而拒絕接受為證據(jù)。這些規(guī)定運(yùn)用功能等同法(functional-equivalent),認(rèn)為只要與傳統(tǒng)式具有相同的功能,即可認(rèn)定為具有同等效力。我國也與這一國際立法趨勢相靠攏,例如我國新修訂的海關(guān)法中規(guī)定了電子數(shù)據(jù)報(bào)關(guān)方式。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在合同法中已承認(rèn)以電子數(shù)據(jù)交換方式訂立的合同的有效性,承認(rèn)其符合法律對合同書面形式的要求。要使實(shí)體法的修改有實(shí)際意義,就必須設(shè)定相應(yīng)的程序規(guī)則,使得以實(shí)體規(guī)定為依據(jù),在訴訟中尋求救濟(jì)時具有程序法基礎(chǔ),否則實(shí)體法上的修改不啻一紙空文。